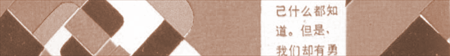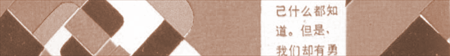|
碰撞與交融:奧林匹克與近代中國(guó)
1894年6月23日,這是世界體育史上的一個(gè)重要日子。在現(xiàn)代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創(chuàng)始人皮埃爾·德·顧拜旦的努力下,與會(huì)的12個(gè)國(guó)家79名代表在法國(guó)巴黎,一致同意成立國(guó)際奧林匹克委員會(huì),并決定將國(guó)際奧委會(huì)總部設(shè)在巴黎,規(guī)定法語(yǔ)為法定語(yǔ)言;推舉希臘詩(shī)人維凱拉斯為國(guó)際奧委會(huì)第一任主席,顧拜旦為秘書(shū)長(zhǎng);產(chǎn)生了第一批共15名國(guó)際奧委會(huì)委員,并召開(kāi)了首屆國(guó)際奧委會(huì)全體委員會(huì)議。會(huì)議決定輪流在世界各個(gè)城市每四年舉行一次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會(huì),同時(shí)決定首屆現(xiàn)代奧運(yùn)會(huì)于1896年在希臘的雅典舉行。從此,一個(gè)規(guī)模宏大的以體育為載體的國(guó)際社會(huì)文化運(yùn)動(dòng)——現(xiàn)代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正式誕生。如今,它已形成了一個(gè)龐大的體系,成為凝聚著人類(lèi)社會(huì)體育思想和體育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精華的知識(shí)寶庫(kù)。而隨著西方近代體育文化傳入古老的中華大地,現(xiàn)代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也逐步融入中國(guó),并不斷地與中國(guó)社會(huì)在多種層面上發(fā)生碰撞和交融。
眾所周知,在古代社會(huì),由于生產(chǎn)力的落后和交通條件的限制,各個(gè)國(guó)家和民族之間的接觸或聯(lián)系是很少的。體育也是一樣,它是分散的、民族的,沒(méi)有“世界的”概念。然而,自從18世紀(jì)英國(guó)產(chǎn)業(yè)革命之后,世界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隨著大工業(yè)的出現(xiàn),以及它所創(chuàng)造的近代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場(chǎng),使一切國(guó)家的生產(chǎn)和消費(fèi)以及文化,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所以,“過(guò)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guān)自守姿態(tài),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lái)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zhì)的生產(chǎn)如此,精神的生產(chǎn)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chǎn)品成了公共的財(cái)產(chǎn)。”[1]由此,世界各國(guó)或民族的體育,也都開(kāi)始從不同的起點(diǎn)和角度向世界聚集。而作為西方“精神產(chǎn)品”之一的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也正是在這一社會(huì)條件下,逐漸演變成了世界性的“公共財(cái)產(chǎn)”,并逐漸居于世界體育發(fā)展的主導(dǎo)地位。
前言碰撞與交融:奧林匹克與近代中國(guó)奧運(yùn)來(lái)到中國(guó)這個(gè)世界有了資產(chǎn)階級(jí)后,人類(lèi)歷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了世界性的統(tǒng)治者。在世界體育文化領(lǐng)域中,同樣反映了這種世界性的主屬關(guān)系。即宗主國(guó)體育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體育的關(guān)系。看一看中國(guó)近代體育的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可以說(shuō),它正是中華民族脫離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及閉關(guān)自守的孤立姿態(tài)的體育,向“世界性體育”轉(zhuǎn)變的歷史,也是與國(guó)際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日益對(duì)接的歷史。
同許多被壓迫民族一樣,發(fā)生在中國(guó)近代史上的這種體育向“世界”的轉(zhuǎn)變,以及和西方奧林匹克文化的對(duì)接,應(yīng)該說(shuō)也是從被動(dòng)和主動(dòng)兩個(gè)方面進(jìn)行的。
首先,外國(guó)資本主義的入侵,破壞了中國(guó)原有的經(jīng)濟(jì)制度和政治體制以及文化傳統(tǒng),使中國(guó)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身份歸入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在這個(gè)體系中,中國(guó)人通過(guò)“睜眼看世界”,看到了近代西方體育所具有的那種進(jìn)步性和科學(xué)性。比如,無(wú)論是瑞典體操還是德國(guó)體操,或是歐美的田徑與球類(lèi)運(yùn)動(dòng),它們都與自然科學(xué),如生理學(xué)、解剖學(xué)、衛(wèi)生學(xué)等密切相關(guān),并以近代自然科學(xué)為主要理論基礎(chǔ);比如,近代西方體育一般都有著較為科學(xué)、完整的活動(dòng)規(guī)則體系,這無(wú)論是在運(yùn)動(dòng)競(jìng)賽工作的組織方面,還是在具體的運(yùn)動(dòng)活動(dòng)中,都表現(xiàn)出一定的公開(kāi)、公平和公正性;又比如,近代西方體育具有較強(qiáng)的競(jìng)技性、趣味性、娛樂(lè)性,這特別表現(xiàn)在球類(lèi)和游戲項(xiàng)目中。所有這些,既表現(xiàn)了近代西方體育的先進(jìn)性,也是它富有頑強(qiáng)生命力的主要原因。因而它為世界上許多民族或國(guó)家所承認(rèn)和吸取。
宋太祖蹴鞠圖
處于落后條件下的中國(guó)也不能例外。這一促使中國(guó)體育向“世界”轉(zhuǎn)變、與西方奧林匹克文化對(duì)接的被動(dòng)過(guò)程,盡管對(duì)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中華民族來(lái)說(shuō),可能有些不情愿,甚至痛苦。因?yàn)樵诼L(zhǎng)的歲月里,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各族先民,用勞動(dòng)和智慧創(chuàng)造了璀璨的古代文明,其中包括中國(guó)古代體育。例如,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在山東的臨淄城就開(kāi)了世界足球運(yùn)動(dòng)的先河——蹴鞠;在秦漢三國(guó)時(shí)期又出現(xiàn)了相撲活動(dòng),甚至有女子相撲;盛唐一代,馬球運(yùn)動(dòng)更是風(fēng)靡全國(guó),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紛紛參與其中;明清時(shí)期,又有了獨(dú)領(lǐng)風(fēng)騷的中華武術(shù),并出現(xiàn)了像少林寺、武當(dāng)山那樣馳名中外的武術(shù)圣地。但是,當(dāng)14世紀(jì)興起的文藝復(fù)興和后來(lái)的思想啟蒙運(yùn)動(dòng),把黑暗的歐洲推進(jìn)到一個(gè)新的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的時(shí)候,中國(guó)則從封建之巔不斷地向下滑行,最后落后于歐洲整整一個(gè)歷史時(shí)代。乃至到了19世紀(jì)40年代,西方列強(qiáng)用大炮轟開(kāi)了中國(guó)長(zhǎng)期閉關(guān)自守的大門(mén),中國(guó)人不得不承認(rèn)自己的落后并開(kāi)始認(rèn)真地向西方學(xué)習(xí)。這其中包括對(duì)近代西方體育的引進(jìn)、學(xué)習(xí)和模仿。中華民族傳統(tǒng)體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文明的強(qiáng)大沖擊,極不情愿地退出了在中國(guó)本土的主流發(fā)展地位。即使像中華武術(shù)那樣的民族瑰寶,在近代西方體育的沖擊面前,也不得不考慮自己的生存發(fā)展道路,考慮怎樣地自我改造、與時(shí)俱進(jìn)。
唐章懷太子打馬球圖另一方面,中國(guó)體育在向“世界性”轉(zhuǎn)變,與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對(duì)接的過(guò)程中,也有著主動(dòng)求變的一面。
在中國(guó)近代歷史上,這種主動(dòng)求變主要表現(xiàn)為外國(guó)資本主義侵略和世界資本主義近代化潮流的沖擊,使沉睡的中華民族不斷覺(jué)悟并激發(fā)起他們也要努力走向世界的自覺(jué)要求。中華民族為了生存不得不變更祖宗之法,以適應(yīng)新時(shí)代的要求。
有關(guān)中西方之間的文化直接接觸,應(yīng)該說(shuō)早在鴉片戰(zhàn)爭(zhēng)前兩百多年就發(fā)生了。那時(shí)西方的傳教士,帶來(lái)了資本主義早期的物質(zhì)和精神文明,例如鐘表、地球圖、日心說(shuō)、天主教,等等。但東西方文化之間并沒(méi)有發(fā)生尖銳的沖突。清朝皇帝的一紙?jiān)t令,便可以驅(qū)逐傳教士,毀棄天主教堂。而剛剛起步的西方資本主義國(guó)家,對(duì)東方大清帝國(guó)的所作所為也無(wú)可奈何。當(dāng)時(shí)的清朝還算是強(qiáng)盛的、自信的。但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zhēng)卻最終打破了這種格局。
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zhēng),是英國(guó)資產(chǎn)階級(jí)為了搶奪中國(guó)市場(chǎng),把中國(guó)變?yōu)橹趁竦囟桫f片問(wèn)題發(fā)動(dòng)的一場(chǎng)侵略戰(zhàn)爭(zhēng)。如果從當(dāng)時(shí)世界歷史發(fā)展的大勢(shì)來(lái)說(shuō),則又可以被理解為是當(dāng)時(shí)先進(jìn)的資本主義西方文明,對(duì)落后的封建主義東方文明的沖擊。這是兩種文明不可避免的沖突。在這兩個(gè)世界的對(duì)峙中,除非舊世界能面向新世界,主動(dòng)接受西方的文明,并以此來(lái)對(duì)付伴隨先進(jìn)文明而帶來(lái)的邪惡。否則,先進(jìn)的近代文明戰(zhàn)勝落后的古代文明,乃是不可變易的社會(huì)規(guī)律。盡管這種古代文明的代表,有著正義的目的以及種種的痛苦和血淚。正是在這種條件下,中國(guó)的仁人志士開(kāi)始正視現(xiàn)實(shí),“睜眼看世界”,并在比較中鑒別和認(rèn)知西方文化的長(zhǎng)處,反思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短處,從中尋找出救國(guó)救民的道理和途徑。于是“救亡圖存”,成了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社會(huì)的時(shí)代最強(qiáng)音。要救亡圖存,就必然要反對(duì)帝國(guó)主義的侵略和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統(tǒng)治。因此,反帝、反封建斗爭(zhēng),爭(zhēng)取獨(dú)立、民主、富強(qiáng),便始終成為近代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的主題。而近代中國(guó)體育的發(fā)展,近代中國(guó)與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的關(guān)系,也同樣是圍繞著這一歷史發(fā)展的主題而展開(kāi)的。
翻開(kāi)中國(guó)近代的歷史,早在清嘉道時(shí)期,西方殖民勢(shì)力就已洶涌東來(lái),中國(guó)和西方列強(qiáng)之間在科技發(fā)展水平、軍事力量、經(jīng)濟(jì)發(fā)展程度上的差距就已經(jīng)拉開(kāi)。與之相適應(yīng)的是,西方侵略的威脅也日漸加劇,特別是在鴉片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前后,英國(guó)擴(kuò)大對(duì)華侵略與中國(guó)維護(hù)國(guó)家主權(quán)、民族尊嚴(yán)之間的矛盾已經(jīng)十分尖銳。在此背景下,一些進(jìn)步的知識(shí)分子已經(jīng)敏銳地覺(jué)察到清廷在國(guó)際關(guān)系中的不利處境,他們深懷憂國(guó)之情,想方設(shè)法了解世界形勢(shì),以圖從中找出防范和擺脫民族危機(jī)的對(duì)策。其中,有提倡“通經(jīng)致用”的學(xué)者、進(jìn)步思想家龔自珍,他提出了“更法”的見(jiàn)解,主張要留意于“天地東西南北之學(xué)”。有堅(jiān)決反抗侵略,并注意了解外情、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他主張要“向西方學(xué)習(xí)”。尤其是愛(ài)國(guó)進(jìn)步思想家魏源,他不僅主張學(xué)習(xí)西方,編成了《海國(guó)圖志》一書(shū),更提出了“師夷長(zhǎng)技以制夷”的口號(hào)。魏源所說(shuō)的長(zhǎng)技,并不僅僅是指武器裝備,還包括了軍事訓(xùn)練等多種內(nèi)容。他說(shuō):“夷之長(zhǎng)技三:一戰(zhàn)艦,二火器,三養(yǎng)兵、練兵之法。”[2]正是從練兵之法里面,我們不僅看到了軍事訓(xùn)練的內(nèi)容,而且還看到了體育訓(xùn)練的內(nèi)容。而當(dāng)時(shí)的體育訓(xùn)練內(nèi)容,主要就是采用西方的“兵式體操”。所以在我國(guó)近代體育史上,盡管一般認(rèn)為是洋務(wù)運(yùn)動(dòng)最早在編練新軍中引進(jìn)了西方近代體育,但最早提出這一要求的則可以追溯到魏源。
魏源圖
如果說(shuō)魏源還只是從理想的角度,提出要注重學(xué)習(xí)西方的科技文化包括體育的話,那么,后來(lái)發(fā)生在清政府內(nèi)部的洋務(wù)運(yùn)動(dòng)和戊戌變法運(yùn)動(dòng),則是從實(shí)踐和理論兩個(gè)層面上,開(kāi)始了對(duì)西方近代體育的吸收和引進(jìn)。大概從19世紀(jì)60年代起,洋務(wù)派就開(kāi)始編練新式軍隊(duì),以洋操、洋槍、洋炮為主要訓(xùn)練內(nèi)容。最早對(duì)軍隊(duì)進(jìn)行西方兵操練習(xí)的是曾國(guó)藩的湘軍。有資料表明,在湘軍中很早就有每天早晚各做一次體操的要求。“黎明演早操一次,營(yíng)官看親兵之操,或幫辦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日斜時(shí)演晚操一次,與黎明早操同。”在湘軍的日常訓(xùn)練中,跑、跳練習(xí)和操練洋槍也都是一些固定的訓(xùn)練科目。據(jù)《曾文正公·雜著》卷一“曉諭新募鄉(xiāng)勇”載:湘軍中每逢一、四、七日午前,均有抬槍、鳥(niǎo)槍的打靶訓(xùn)練;而逢五、逢十日的午前,則是演練連環(huán)槍法。[3]每逢二、八日午前,湘軍的將士們則要到城外的近處,集體練習(xí)跑坡、搶旗、跳坑等類(lèi)的身體活動(dòng)。
洋務(wù)派新式軍隊(duì)中的兵操訓(xùn)練,一方面是從英、法、美等國(guó)的軍隊(duì)中,聘請(qǐng)軍官充任兵操教習(xí);另一方面也派人出國(guó)學(xué)習(xí),以培養(yǎng)自己的兵操教官。如李鴻章在整頓直隸的防務(wù)中,曾于1876年選拔年少力壯的中下級(jí)軍官卞長(zhǎng)勝等7人赴德國(guó)學(xué)習(xí)。1879年學(xué)成回國(guó)后,他們即以德國(guó)兵操訓(xùn)練淮軍。
洋務(wù)派還先后創(chuàng)辦了不少軍事工業(yè)學(xué)堂和軍事學(xué)堂。如北洋水師學(xué)堂、天津武備學(xué)堂,等等。這些學(xué)堂大多依照外國(guó)同類(lèi)學(xué)校設(shè)置課程,并聘用外籍教員。其中也設(shè)置了較多的體操課程。1894級(jí)水師學(xué)堂學(xué)生王恩溥先生曾在1985年的回憶中說(shuō),當(dāng)時(shí)北洋水師學(xué)堂的體育課內(nèi)容,已有擊劍、刺棍、木棒、拳擊、啞鈴、足球、跳欄比賽、三足競(jìng)走、羹匙托物競(jìng)走、跳遠(yuǎn)、跳高、爬桅等項(xiàng),此外還有游泳、滑冰、平臺(tái)、木馬、單杠、雙杠,及爬山運(yùn)動(dòng),等等。北洋水師學(xué)堂最初所學(xué)的是德國(guó)體操,主要演習(xí)方城操和軍事操,后來(lái)到了戊戌年間,又開(kāi)始改為學(xué)習(xí)英國(guó)體操。
戊戌變法運(yùn)動(dòng)是發(fā)生在中國(guó)近代的一次愛(ài)國(guó)救亡運(yùn)動(dòng),是中國(guó)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要求發(fā)展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和擴(kuò)大資產(chǎn)階級(jí)政治權(quán)力,符合近代中國(guó)的歷史發(fā)展趨勢(shì),是一次進(jìn)步的政治改良運(yùn)動(dòng)。它傳播了資產(chǎn)階級(jí)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因此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yùn)動(dòng)。雖然戊戌變法運(yùn)動(dòng)不過(guò)百日便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勢(shì)力所鎮(zhèn)壓,其實(shí)際的改革也非常有限,時(shí)間也極短,但它卻有著巨大的思想解放的歷史影響,對(duì)促進(jìn)“西學(xué)”包括西方近代體育,特別是西方近代體育思想和理論在中國(guó)的傳播和發(fā)展,起了很大的促進(jìn)作用。例如這場(chǎng)運(yùn)動(dòng)的領(lǐng)袖人物康有為,已經(jīng)能從學(xué)校的教育內(nèi)容上,注意到對(duì)學(xué)生進(jìn)行德、智、體的多方面培養(yǎng)。他在《大同書(shū)》中說(shuō):“本院凡弄兒之物,無(wú)不具備,務(wù)令養(yǎng)兒體、樂(lè)兒魂、開(kāi)兒知識(shí)為主。”在他所辦的學(xué)校“萬(wàn)木草堂”的教育活動(dòng)中,“體育亦特重焉。”還有梁?jiǎn)⒊麆t提出了“新民說(shuō)”,即培養(yǎng)一種具有特色的國(guó)民。這種國(guó)民應(yīng)該體現(xiàn)出“民德、民智、民力”的德智體全面發(fā)展要求。嚴(yán)復(fù)則公然提出了德智體三育并重的觀點(diǎn)。他在《原強(qiáng)》一文中指出:“教人也,以睿智慧,練體力,勵(lì)德行三者為之綱。”他從強(qiáng)國(guó)強(qiáng)種的立場(chǎng)出發(fā),甚至認(rèn)為:“民之手足體力”,關(guān)系到“一國(guó)富強(qiáng)之效”。
由上可見(jiàn),無(wú)論是西方近代體育的傳入和傳播,還是后來(lái)的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傳入中國(guó),都是在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政治變革和救亡圖存的影響下而進(jìn)行的。所以,和“實(shí)業(yè)救國(guó)”、“教育救國(guó)”、“科學(xué)救國(guó)”等一樣,中國(guó)近代史上體育的發(fā)展和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的傳入與傳播,也始終都是圍繞著“救亡圖存”的歷史主題而展開(kāi)的。
所謂近代體育,從本質(zhì)上看,應(yīng)該是近代社會(huì)的產(chǎn)物,是資本主義文化的一部分。但從形式上看,它則是古希臘、羅馬體育思想與方法,并結(jié)合中世紀(jì)騎士教育與貴族教育所孕育出的一種混合物。它是14世紀(jì)以后經(jīng)過(guò)文藝復(fù)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yùn)動(dòng),在資產(chǎn)階級(jí)取得意識(shí)形態(tài)和文化領(lǐng)域里對(duì)封建文化的決定性勝利的過(guò)程中,而逐漸形成和發(fā)展起來(lái)的一種身體文化。
近代體育最早出現(xiàn)在學(xué)校。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和城市的興起產(chǎn)生了對(duì)體育的新需求,身心全面發(fā)展成為新興資產(chǎn)階級(jí)的教育理想,文藝復(fù)興運(yùn)動(dòng)和宗教改革從根本上動(dòng)搖了教會(huì)的教育體系和禁欲主義的身體觀,在復(fù)興古代體育文化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萌發(fā)了新的體育思想。大約在16~17世紀(jì),西方的貴族教育開(kāi)始脫離舊的傳統(tǒng),不但文化學(xué)習(xí)的內(nèi)容得到更新和擴(kuò)大,而且體育教育也受到重視。年輕紳士必須身心并重,使自己成為人才。一切能使他們適應(yīng)和平或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積極生活的身體運(yùn)動(dòng)形式,諸如劍術(shù)、騎馬、打獵、網(wǎng)球、跳舞等,都是日常的訓(xùn)練科目。在這種條件下培養(yǎng)出來(lái)的人,已不再是舊式的封建貴族,而是新生的資產(chǎn)階級(jí)新貴。
在世界學(xué)校體育發(fā)展史上,使學(xué)校教育沖破貴族的狹小天地從而奠定近代學(xué)校體育基礎(chǔ)的,是宗教改革時(shí)期捷克偉大的教育家夸美紐斯(JAComenius,1592—1670)。他是新教(捷克兄弟會(huì))的著名活動(dòng)家,曾在捷克、波蘭、瑞典、匈牙利長(zhǎng)期從事教育工作。他主張普及教育,重視人的現(xiàn)世生活,關(guān)心人的健康和幸福,稱學(xué)校為“造就人的工廠”。他強(qiáng)調(diào)教育的作用,認(rèn)為品德、體力和智力的缺陷都可以由教育而得到發(fā)展。他提出了“適應(yīng)自然”的原則,希望按學(xué)生的年齡及其已有的知識(shí)循序漸進(jìn)地指導(dǎo),主張“人人都應(yīng)該祈求自己具有一個(gè)健康的心理存在于一個(gè)健康的身體里面”。雖然他從未單獨(dú)提及體育課程,但正是在他的教學(xué)計(jì)劃中,體育首次成為教學(xué)的有機(jī)組成部分。夸美紐斯確立了班級(jí)制和課間休息制,采用了直觀和示范教學(xué)法。他規(guī)定低年級(jí)學(xué)生每日學(xué)習(xí)4到6小時(shí),每學(xué)習(xí)1小時(shí)即休息半小時(shí)。青年每天須有8小時(shí)用于吃飯、操練和娛樂(lè),通過(guò)郊游、旅行、游戲、跑跳和球戲等,而使身體活動(dòng),讓心靈休息。他同時(shí)指出運(yùn)動(dòng)要有一定的節(jié)制,反對(duì)從事一些他所說(shuō)的“危險(xiǎn)”運(yùn)動(dòng),如角力、游泳等。他還很重視體育和游戲活動(dòng)中的德育、智育教育。夸美紐斯作為文藝復(fù)興以來(lái)的一位體育和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影響是深遠(yuǎn)而廣泛的,所以被一些西方學(xué)者稱之為“學(xué)校體育之父”。
進(jìn)入19世紀(jì)后,源于學(xué)校的近代體育首先在歐洲的德國(guó)、瑞典、丹麥等地,開(kāi)始逐漸向社會(huì)和軍隊(duì)傳播。當(dāng)時(shí)廣為社會(huì)和軍隊(duì)接受的體育內(nèi)容,主要是那些能直接發(fā)展各種身體能力和加強(qiáng)組織紀(jì)律性的體操以及戶外運(yùn)動(dòng)。
大約從19世紀(jì)70年代開(kāi)始,自由資本主義開(kāi)始向壟斷資本主義過(guò)渡,資本輸出逐漸成為擴(kuò)張的主要方式,西方各國(guó)的民族主義和軍國(guó)主義色彩開(kāi)始減退。同時(shí)能量守恒定律、生物進(jìn)化論、細(xì)胞學(xué)說(shuō)和元素周期律的提出,帶來(lái)了現(xiàn)代科學(xué)的全面、長(zhǎng)足的進(jìn)步。在此背景下,西方社會(huì)的各種體育競(jìng)賽活動(dòng)開(kāi)始增多,早期的體育運(yùn)動(dòng)組織也開(kāi)始萌生。如1858年,全美棒球協(xié)會(huì)成立;1863年,英國(guó)足球聯(lián)盟成立,等等。這些全國(guó)性的體育協(xié)會(huì)組織成立,不僅使原來(lái)僅限于學(xué)校或俱樂(lè)部水平的體育比賽活動(dòng)獲得較大的提升,而且還直接導(dǎo)致了各種相關(guān)國(guó)際體育組織的誕生。如較早成立的國(guó)際體育組織有:國(guó)際體操聯(lián)合會(huì)(1881年)、國(guó)際橄欖球協(xié)會(huì)(1890年)、國(guó)際賽艇聯(lián)合會(huì)(1892年)、國(guó)際滑冰聯(lián)合會(huì)(1892年),等等。
國(guó)際體育組織的建立,不僅更加促進(jìn)了體育競(jìng)賽活動(dòng)的興盛,促進(jìn)了體育運(yùn)動(dòng)技術(shù)的進(jìn)步和體育競(jìng)賽規(guī)則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引發(fā)了體育的國(guó)際化趨勢(shì),促進(jìn)了體育的國(guó)際交往。而正是這種國(guó)際體育交往,才有可能將西方和東方、強(qiáng)國(guó)和弱國(guó)、宗主國(guó)和殖民地聯(lián)系在一起。于是,一個(gè)宏大的現(xiàn)代國(guó)際社會(huì)文化運(yùn)動(dòng)——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不僅借此而產(chǎn)生,而且也借此一步步走向了全世界,走進(jìn)了古老的華夏文明。
所謂中國(guó)文化,準(zhǔn)確地說(shuō)應(yīng)該稱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對(duì)于中國(guó)文化這一概念,學(xué)術(shù)界至今還沒(méi)有一個(gè)一致的看法。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是,如果從層次結(jié)構(gòu)上看,我們認(rèn)為,它似乎應(yīng)包括中國(guó)歷史上先民們所創(chuàng)造的所有物質(zhì)和觀念的全部。從內(nèi)容上看,當(dāng)然也應(yīng)包括歷史上存在過(guò)的政治制度、學(xué)術(shù)思想、科學(xué)技術(shù)、風(fēng)俗習(xí)慣,等等。但是,需要說(shuō)明的是,我們這里所說(shuō)的中國(guó)文化,并不是指中國(guó)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guò)的所有文化,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歷史上曾經(jīng)形成的、至今還在對(duì)我們發(fā)生著影響的文化。所以有人將它稱之為“文化傳統(tǒng)”。在世界文化長(zhǎng)河中,中國(guó)文化自成體系,獨(dú)樹(shù)一幟。想打破并代替這種文化體系,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如英國(guó)傳教士楊格非所描述的:這里(中國(guó))的人們通曉他們自己的文學(xué)。他們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學(xué)者。他們以擁有這些人而自豪。他們對(duì)這些人有好感,把這些人當(dāng)做神明崇拜。中國(guó)人還沉浸于可以感觸到的唯物主義世界和可見(jiàn)之物就是一切。要他們用片段功夫考慮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見(jiàn)的永恒的東西,那是難上而加難的。他們認(rèn)為,這些是物質(zhì)以外的虛無(wú)的東西,因?yàn)橹潦ハ葞熢?jīng)說(shuō)過(guò),要敬鬼神而遠(yuǎn)之。從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輸給這樣一個(gè)民族,是何等的困難啊! 應(yīng)該說(shuō)楊格非所說(shuō)的情況基本上是真實(shí)的,但這并不代表說(shuō)中國(guó)文化對(duì)外來(lái)文化是一切排斥的。事實(shí)上,以儒學(xué)為核心的中國(guó)文化,對(duì)于外來(lái)文化也有包容的一面。當(dāng)然這種包容是在不影響中國(guó)文化的內(nèi)核,并有利于其再生與發(fā)展的前提下進(jìn)行的。所以我們認(rèn)為,中國(guó)文化同樣具有開(kāi)放性的特征。
這種開(kāi)放性首先表現(xiàn)為中國(guó)文化對(duì)于外來(lái)文化的一種吸納態(tài)度。從歷史的發(fā)展看,中華民族從來(lái)不恐懼外來(lái)異質(zhì)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較小的排他性。例如從公元1世紀(jì)開(kāi)始的印度佛學(xué)的大量輸入,并沒(méi)有置換儒學(xué)的統(tǒng)治地位,反而逐漸促進(jìn)了儒學(xué)的新生。宋明理學(xué)正是在吸收了佛學(xué)的許多精華后才使儒學(xué)上了一個(gè)新的臺(tái)階。正是由于這一優(yōu)良的文化傳統(tǒng),所以當(dāng)中國(guó)歷史進(jìn)入近代以后,盡管它閉關(guān)自守的大門(mén)是在不情愿的條件下而被外國(guó)列強(qiáng)所打開(kāi)的,其所發(fā)生的社會(huì)變革也不是源于內(nèi)在能力的覺(jué)醒,而是來(lái)自外部力量的沖擊,不是主動(dòng)的,而是被動(dòng)的,不是一個(gè)和諧的成長(zhǎng)過(guò)程,而是一個(gè)不斷受挫不斷調(diào)整的過(guò)程。但是它對(duì)于外來(lái)文化的態(tài)度則依然表現(xiàn)了一種泱泱大國(guó)的博大胸懷。所以當(dāng)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傳入中國(guó)的時(shí)候,馬上就有了認(rèn)同的知音:“中國(guó)何時(shí)能參加萬(wàn)國(guó)運(yùn)動(dòng)會(huì),又何時(shí)能使萬(wàn)國(guó)運(yùn)動(dòng)會(huì)舉行中土?茲值南洋賽會(huì)之時(shí)機(jī),爰邀集全國(guó)體育家,訂期9月15日,齊聚金陵,開(kāi)第一次中國(guó)運(yùn)動(dòng)大會(huì)。”這是1910年8月上海基督教青年會(huì)發(fā)起,在南京召開(kāi)“全國(guó)運(yùn)動(dòng)大會(huì)”《通告書(shū)》上所說(shuō)的一段話。這里的萬(wàn)國(guó)運(yùn)動(dòng)會(huì)就是指奧運(yùn)會(huì)。這次活動(dòng)被認(rèn)為是中國(guó)近代體育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中國(guó)人對(duì)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的最初嘗試。實(shí)踐證明:充分地吸收外來(lái)文化,不僅不會(huì)使中國(guó)原有的文化傳統(tǒng)中斷,而且會(huì)大大地促進(jìn)中國(guó)自身文化傳統(tǒng)更快、更健康地向前發(fā)展。
中國(guó)文化的開(kāi)放性,其次表現(xiàn)為它對(duì)外來(lái)文化的一種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作為西方文化的代表,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和中國(guó)文化之間必然存在著許多的沖突。如:二者所依存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不同,一是工業(yè)文明下的文化,一是農(nóng)業(yè)文明下的文化;存在著思想理論基礎(chǔ)的不同,一是以西方自然科學(xué)理論為基礎(chǔ)的文化,一是古代東方樸素唯物主義哲學(xué)指導(dǎo)下的文化。但是,這種沖突并沒(méi)有影響東西方文化走向融合。這種融合的基礎(chǔ)便是中國(guó)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而“文化傳統(tǒng)”是指活在現(xiàn)實(shí)中的文化,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流向。中國(guó)文化正是在結(jié)合時(shí)代精神的文化流向中,在吸收外來(lái)文化時(shí),通過(guò)不斷地尋找相互共同的契合點(diǎn),而促進(jìn)外來(lái)文化在本土的生長(zhǎng)、發(fā)育,并最后融入到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中,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體系。例如,中國(guó)文化在構(gòu)建“和諧社會(huì)”的理想上,與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的“促進(jìn)世界和平”找到了契合點(diǎn);中國(guó)文化提倡的“誠(chéng)信為本”的倫理規(guī)范,與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的“公平競(jìng)爭(zhēng)”找到了契合點(diǎn);中國(guó)文化中“自強(qiáng)不息”的進(jìn)取精神,與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的“更快更高更強(qiáng)”找到了契合點(diǎn)。所有這一切,無(wú)疑都成了奧林匹克運(yùn)動(dòng)能夠在中國(guó)傳入和傳播,并最后走向發(fā)展和繁榮的重要文化基礎(chǔ)。
注釋
[1]《共產(chǎn)黨宣言》,見(jiàn)《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55頁(y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2]魏源《海國(guó)圖志·籌海篇·議戰(zhàn)》
[3]其法為6人一組,兩人一層的立體式放槍法。即6人中兩人取臥姿、兩人取跪姿、兩人取立姿,然后6人同時(shí)放槍。放完后,左人左后轉(zhuǎn),右人右后轉(zhuǎn),至隊(duì)末。第二組6人前進(jìn)一步,再放槍。以此類(lèi)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