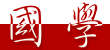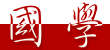|
�����¡����Ƹ�������ס
43
��Ĵ��(hu��)�ó�������ȥ���̵��I(l��ng)��(ji��ng)Ʒ���^��(ji��ng)ʮ��(g��)����(ji��ng)Ʒ������ʲô����ҲŪ���ˡ�
���ij������Ľ������M(j��n)�ʹڼ��F(tu��n)�̈����X��һ�ꎛ����̈�������{(di��o)����_�ţ�����������ձ���ٵء��ʹڼ��F(tu��n)�̈�ԭ�ɵ�̎�S���пڵą^(q��)�C(j��)�P(gu��n)��Ǹ������ģ����К��ɵ��ČӠI�I(y��)��ǣ������ûʣ���ȫ����ʹ���Ԅ�(d��ng)���ݣ����_��������{(di��o)�����Ƴ��ު�(ji��ng)�N�ۣ��I�I(y��)�~ֱ��������
��������(w��)���_(t��i)�߂�(g��)�Ĺ����(ji��ng)Ʒ�������I(l��ng)��
���ﴩ�����{(l��n)ɫ�������������m��ñ����(d��ng)�˳����ط������I(l��ng)ʲô��(ji��ng)��
��f�σ���(ji��ng)ȯ�������C��Ц���ā����I(l��ng)�Ъ�(ji��ng)�N�۵Ī�(ji��ng)����
�������(ji��ng)ȯ������(ji��ng)ȯ�f������u��(ji��ng)���Ъ�(ji��ng)̖(h��o)�a�����ˣ�
��c(di��n)�c(di��n)�^�����_������
�����̵��ϰ࣬����֪���_��(ji��ng)��̖(h��o)�a���P(gu��n)�е؆���������ʲô��(ji��ng)���Ц���b�����죺��(d��ng)Ȼ�^��(ji��ng)��
�^��(ji��ng)�����ﱠ���۾�������(ji��ng)ȯ���ֿ����ͻȻ���������_(t��i)�I�I(y��)�T�µ���ร�����"�W��"�ˣ�
���õ��Ã�(n��i)����ͺ͠I�I(y��)�TעĿ���������Լ��Ъ�(ji��ng)��������،���(ji��ng)ȯ�������C��߀�������һָ�����Ę��̈��k����ȥ�I(l��ng)��(ji��ng)��
�Ҋ���������n����^��������������Ƶر���늄�(d��ng)���ݣ��Q�������Σ��ҵ��k���ҡ�
��������(j��ng)���ǰ����ֵ�����DŮ��ͦ���ĵģ��к�����£��������Ī�(ji��ng)ȯ�������CЦ�����҂��Ĵ��ÿ���(j��ng)��ȥ�����_��(ji��ng)���(d��ng)�ģ�߀�]����Ŷ�ǣ���߀��֪�����̈�����(ji��ng)���Ъ�(ji��ng)̖(h��o)�a��
������c(di��n)������˼�ˣ�̽������������І
��������(j��ng)������ָ������Ģ���l(f��)�ͣ����ĵؽ�ጣ����f�����^��(ji��ng)����ٌ�(sh��)����(ji��ng)Ʒ�ǃr(ji��)ֵ�����fԪ��һ�v�W���I܇�����轻���fԪ�������I(l��ng)���W���I܇��
Ҫ�����fԪ����ڵ�Ŀ���������ֻ�У��������K��������Ū�@���fԪ�X��Ҫ�@�I܇��ʲô��
��(du��)���@�ǰ�Ҏ(gu��)�������ģ�������(g��)���{(di��o)��(ji��)����
�����Ҳ�Ҫ��܇���������P���I(l��ng)���ա���(zh��)�գ����B(y��ng)·�M(f��i)���_�N���ˣ��@��؛�I(l��ng)�����_�����ゃ�����۵����Q�F(xi��n)�n���Ԇ
�Q�F(xi��n)����²��С���������(j��ng)����ü�y�ò��ã����|�ۣ����]��ԭ�������⡣��ɰ��Ъ�(ji��ng)ֵ�ڱ��̈����x�ȃr(ji��)ֵ����Ʒ��
���هҲ���ˎ���С���⣬�Ļ�ˮƽ���ߣ���������F������Ҫ�I�����f�K��؛�_�ꣿ���߳��ʹڼ��F(tu��n)�̈���һ�^��˼����(j��ng)�� ��ʮ��(g��)�^��(ji��ng)��ֻ�а����_��؛һ���^��(ji��ng)�ǬF(xi��n)�𣱣�������Ԫ��
��(d��ng)�����磬��ڰ����_��؛һ�꽛(j��ng)���Ҵ��˃�С�r(sh��)���۳�������������Ԫ��(g��)���{(di��o)��(ji��)�����õ�һ����������������Ԫ��֧Ʊ������⣬ԭ��Ҫ�l(f��)�l(f��)�l(f��)�l(f��)��ӑ�ڲʣ��������F(xi��n)��ȥ�������һ��(g��)"��"�������֣�"Ҫ��ҪҪ���c(di��n)��"����ޚ⡣
��һ·�����@֧Ʊ���nƱһ��B�y�ã����ڼ���Ҳ�����U(xi��n)��
�ڹ����y�ЬF(xi��n)�����XƼ���^��������C��֧Ʊ�r(sh��)���_�����l(f��)Ц��ʮ��(ji��ng)������úǣ�
�һ�@���@����İ���Ĺ�������l����һ��(hu��)���ž��^�������Ǔu��(ji��ng)�е�һ��(g��)С�㣬�ֲ�֪��ɶ��ɶ�������ЦЦ�������@��
�XƼ�����Ҫ��Q�o��һ�����ڃ�(ch��)��Ĵ��ۣ����f����Ɍ����е��X�Á������ܴa��(ch��)���Ū�����ÿ������㷽�㡣
���һ�ΰl(f��)�F(xi��n)����ꖹ�N���������MЦ��
���ס�����L;��܇վ������С�g��ÿ����𣱣����K�����|�ϝh߀��֪�һգ����׃����ϡ�Ҋ������]ȥ�L;��܇վ�[���u���u������֡������һ�ص�������P(gu��n)�ϴ��T���õ�픺ã����_�_(t��i)ʽ��L(f��ng)�ȡ�����˴�٣��\ؔ(c��i)����������һ�Ѳ˵�����������������(d��n)ɷ��˼�����Ͼŏ��^��(ji��ng)����(ji��ng)ȯ��һ���y�д��ۣ�ِ�^ը������һ�����Ҫ���e(cu��)������
�����S�裬���L(f��ng)ʒɪ�����^�����˲��࣬�L;��܇վ�T��Ҳ�oɶ���M(j��n)ȥ��
�������еIJ��u���l(f��)�������������e�嵭��һ��ֻ�u����ֻ�� �@���^ȥ��δ�����^�ġ� �@�r(sh��)һ�v��ɫ�ĊW���I܇���L;��܇վ�����T��ͣ�£������������ꏊ(qi��ng)����ţ����̫��R������������f�����u����ȫҪ�������
���ʰ�˽�Ԫ���������߽��I܇��߀�]������ô���£��ѱ����M(j��n)�I܇�������ں����ϣ�̫��R����P(gu��n)��܇�T����һС������������(d��ng)��܇���н��⼲̫��R������p�֣�һ�Ѿ�ס����^�l(f��)�����������Ъ�(ji��ng)ȯ�������C�ó�����
��@�����������ˏ�(qi��ng)�I��٣����(d��ng)��(d��ng)���ã��^�l(f��)���ֱ���ס��ֻ������ֱ�У�����ҡ����������ϡ����ڼ��
̫��R��������ͳ��֘�������������f��Ҫ���ό�(sh��)�c(di��n)���_܇�������{܇�������ס̎�?c��)��?/p>
�Ҋ܇�w�����Լ�ס̎�����@���@�ͼ�(qi��ng)�I�۾�����ô�B�Լ���ס̎�������ˣ��f������?c��)��������Լ����һҹ�g������һգ��ʧȥ��ʹ������������ƴ�ˣ��͵�?f��)����{�T���I܇���D(zhu��n)����܇����ը��
���ˣ���@�ѣ����ѕ������Լ��h(hu��n)ҕ���ܣ����ڼ�����Ų[���ˣ����_����һ������(ji��ng)ȯ�ʹ��۶��ڡ�
����һ�������݄�һ���亹��
��Ļ�ˮƽ���ߣ��o�H�o�죬�X���Լ��݆��������ù͂�(g��)���С��Է���ġ��Ļ��ߵ��ˁ�̎���@�P���~��(ji��ng)Ʒ������˼���룬�J(r��n)�����칫�C�u��(ji��ng)�ij��幫�C�T�k��һ��������
������������W(xu��)���I(y��)�ı�����������ط��䵽�����У����������꣬���Q������(g��)���T��˾���֡��Ɏ���(w��)�������C̎����һ������(j��)�Ɏ����Y���C�������õ���sҊ���Ŀ�Ӎ���²���ҪՄʲô�¡�
���^�����Q�ϱ��b�����Ҵҵ��s�������п��ȏd���@���й����F(tu��n)ί�k�Ľ�(j��ng)��(j��)��(sh��)�w��������m�ĵ��·��ն��һ�����õ�Ů�д�������Ǹ�У����У�����_ʼ�W(xu��)Ժ����(zh��n)Ů��W(xu��)�����gȥ��(d��ng)�д�������һꇡ��F(xi��n)�W(xu��)Ժ�ώ��ㄓ(chu��ng)�գ��W(xu��)���ڹ����W(xu��)������߯�࣬��(du��)Ů��W(xu��)����(d��ng)�д�����Ҳ�W(w��ng)�_һ�档
������T��ӭ����ʰ��(j��)���£��M(j��n)���d�������o�ĵط�����������h(hu��n)ҕ��(j��)���b�꣬��(y��u)�ŵğ����£��ƓP(y��ng)��������������У��Լ��m��·�^����߀�ǵ�һ�����R�侳��
һ����(g��)����Ů�д�Ц�����߁����������Ļ���������ȹ��Ę����ʩ���y������؆���Ո(q��ng)����������Ҫʲô��
�ɱ����ȡ��� ������ȻҬ֭���� ������֭���� ѩ�̡����ǰ�����e�ßo�ģ�����^һ�Σ��������T��·����Ո(q��ng)���嵽�@�����(j��ng)�c(di��n)���µ���������·�Ŀ��ȏd���߳��塣
Ո(q��ng)�Եȡ�Ů�д�һ��(hu��)��������ϣ���Ҫ�x�_��ͻȻ�۾�һ�����������炐���l(f��)�F(xi��n)�´���Ƶģ�������ǂ�(g��)����ʮ�^��(ji��ng)����ɣ�
����ô�Եã��������֡�
Ŷ�ǣ������ҕ����^��������ش���涺��
Ů�д����o�oһЦ������Ұ�߀������^���ء�
��֣������l����²�������
�����������_��(ji��ng)�xʽ��
����Ԭ���ε�Ů����������һ߅�ij��壬�̲�ס���죬Ո(q��ng)��ԬС�㷼����
�ⷼ���@��Ԭ�@�_������Ц���·���(du��)������������ʾǸ�⡣
�����@�﹤���������ֱգ��
������W(xu��)�������ρ��@��
��ֲ�����(du��)ô����X��ͬԬС��һҊ��ʣ��fԒ����Ȼ��
ԬС��炀(g��)���ࣺ��߀���Եá�
���������������zһ��(hu��)���䶡ð��һ�䣺�Ұl(f��)�F(xi��n)�ゃ�zͦ��ġ�
���Ԭ�@������(du��)ҕһ�������s��ͬ�_�ڣ�Ϲ�f��
���˶�Ц�����p�����`��ͨ��
���ˣ��ゃ����Մ����߀Ҫȥæ�ء�Ԭ�@��������һ����Цӯӯ���x�_��
���˺��^���ȣ����eԒһ��������M(j��n)�����}������Ƹ�����ҵij��귨������f(xi��)����̎����(ji��ng)Ʒ��������(w��)��ÿ�¸��㣱�������K�����ã�
��н��������Ԫ���Ĵ_�T�ˡ��Լ����Y�����N����ͨ�M(f��i)�����N��ϴ���M(f��i)������(b��o)�M(f��i)���Zʳ���N��ú��N����(w��)���N�����ιμ��������M������Ԫ�����Y���c(di��n)Ҳ���ˣ�����Ҫ���ǹ��C̎���ǂ�(g��)�^�����б��µ��u�Ĺ����c�ģ��ݲ����ˡ��e�ˏ�(qi��ng)�����o�����������Ǐ�(qi��ng)��ϲ�g�����������˳��^�Լ��������������¹����е����֣��|�⣬���Ҫ�{(di��o)�x����һֱ�o��ȥ̎������Ĭ�����أ��ÿɏ��������Ϲ�˱������������ȻҬ֭��
��Ŷ���Ҋ��(du��)���������ĵ����c(di��n)���ˣ��˼��LJ��Ҹɲ�����"�ʼZ"���F���ģ��� �Լ��Ć
�@���ҿ��]һ�¡�����������_���Ϲܣ����������ޣ���Ҫ��đ�(y��ng)Ƹ������Ҫ����(g��)��ͬ�����Cһ�¡�
�@���k�����k����^ֱ�c(di��n)�����⣬�Է���ĵ��ײ�һ�ӣ��k�¶��Ϸ���
���D�و��J�Ј����F(xi��n)�ڶ��Ą�(l��)�C(j��)�P(gu��n)�ɲ�"�º�"�k��(sh��)�w����˾����ӆ����(y��u)�����ߣ����S�C(j��)�P(gu��n)�ɲ�ͣн���������(n��i)�������ƣ����]���F(xi��n)��һ��(g��)���з���ˣ�ƽ�������wĽ�e�˰l(f��)ؔ(c��i)���ʼ��e�˰l(f��)ؔ(c��i)���F(xi��n)�����s��ȥ��ؔ(c��i)���s�ֶ�ه�ڙC(j��)�P(gu��n)����ɳԿڰ���(w��n)���ÁG���ɲ����F���Ρ�����@һ�ښ����������֮��(n��i)�o�����(f��)��
��к�Ԭ�@���Y(ji��)�������_������һ��Ԫ�����凘һ����Ó�ڶ������@ô�F���@ô�F����]���҂��ɣ�Ӳ���^ƤҪ���X��
Ԭ�@�غ͵��f���҂������a��(bi��o)�r(ji��)�ġ�
�ҁ����ҁ�����������Ո(q��ng)���Ŀ��ˡ����ס�����ͳ�һ��Ԫ��Ʊ�ӽӻ؎��Σ������ˣ���Ԫ�oԬС�㣬��С�M(f��i)��
�x�x���gӭ�ゃ?c��)ف���ԬС��һĘЦ�ݣ����𣬺����?/p>
��x�_�r(sh��)���ֳ�ԬС�����ˎ��ۣ����^�l�ʘO�ߡ�
��������ͣн���Ĉ�(b��o)��ܿ�@������(zh��n)�����c����˺�ͬ�������˹��C���˕r(sh��)�ѣ�����Ѯ���ֵ���Ժ�k����̎����(ji��ng)Ʒ�Ă�(g��)��ί�Е������(d��ng)������������Ԫ���鱾�¹��Y��
���������@�ݹ��Y������ø��d���㆖���������ô̎���@Щ�^��(ji��ng)��
��f����������˼��]���뷨�������_�ĬF(xi��n)�n�^��(ji��ng)���I(l��ng)�ˣ�������Ҫһ���п���õ�����һ�dס����һ�ߙn��늣�һ��(j��)�Ҿ㣬������(sh��)��ȫ�۳ɬF(xi��n)��
�������S��Ҳ��Ҫ�������ѿ����^���������S���r(ji��)ֵ�����fԪ��ʮ�^��(ji��ng)��ֵ�������fԪ�����۳��X��Ҳ�o�����{�����fԪ�Ă�(g��)���{(di��o)��(ji��)�������fҪ���Ī�(ji��ng)Ʒ���[�O(sh��)Ҳ�`����È���
�ɦ�^���ٺٵ�Ц���l֪�@�S���Dz�����࣬߀�ǓQ�F(xi��n)�n���U(xi��n)��
����������������(ji��ng)ȯ����������C�͂�(g��)��ί�Е���һ�B�������ļ��̈����ش���һ�ӵģ���(sh��)�彩(ji��ng)Ʒ���p��̩�����A�β��ܓQ�F(xi��n)�𡣺���������c���ȡ�p���M(j��n)�k����һ��Ո(q��ng)���L��ؔ(c��i)�k���γ������̈��Ĺ�����һ���Ѫ������(du��)��(ji��ng)Ʒ�����ۿۣ�����������Ҏ(gu��)������(g��)���{(di��o)��(ji��)�������������o�̵ꡣ��(j��ng)�킃Ҳ����ͨ�⣬���һ�P�㣬����(d��ng)���⣬�������ļ�������ٍ�^���ֽo��^��˾��������P(gu��n)ϵ����������,���f��(ji��ng)Ʒ߀��������һ݆�_��(ji��ng)��
�Y(ji��)����ٍ�X�����^��(ji��ng)ֵ픸ߵ��̈����O(sh��)�W���I܇�^��(ji��ng)���̈��������������̎���M(j��n)�ˣ��fԪ��ֻ���O(sh��)�F(xi��n)��(ji��ng)�İ����_�̈�����I(l��ng)��ס�����Ҿ㡢��늵��̈��o�M(j��n)������(d��ng)Ȼ���̝��߀������ٵ��˽������f��(ji��ng)�𣬞��@����ʹ�˺�һꇣ��������õ��������fԪ�F(xi��n)��֧Ʊ���������������ο����Ʃ���ٵ�һ�^��(ji��ng)��
���匢�F(xi��n)��֧Ʊ���o���ԃ��������F(xi��n)��߀�Ǵ��y�У�
����˕�(hu��)�f���F(xi��n)�n�����@�ﲻ���U(xi��n)�����y�д�?zh��n)����ڣ�Ҫ���ÿ��S�r(sh��)�á�
����Ҳ�ǵ�һ��Ҋ��˽�˓�����˴�ľЦ�������渣�⣬�@�P������y��������Ϣ��Ҳ���㻨�������������벻�������ֵ��
ʲô��ֵ���Ū������
����ʹ�nƱԽ��Խ�ࡣ
��ô������ �@�Ͷ��ˣ����I��ȯ������Ʊ���_�S�k�������⡣
��������������ԵìF(xi��n)�������y����Ū�ò����gɷ�ϱ���һ⚲����ܡ���Ҫ���@�P�X�팍(sh��)�F(xi��n)ƽ������Ը��
�ÿ�춼��ʮ�����յ������R(sh��)�ֲ��࣬�Ŷ����ɳ�����̎��������ÿ���ŵă�(n��i)����o�� ��ÿ���Ń�(n��i)�ݸ�ʽ���ӣ���Ո(q��ng)��Ͷ�Y�_�S�k��ģ����������ٝ���ģ���Ƹ�����Y���ɖ|�ģ����������ģ���������۵ģ�߀���ԷQ��������Ҫ���J(r��n)�H�ġ���
����ÿ���x�@Щ�ţ��L�M(j��n)���٣��Еr(sh��)ҪЦʹ��Ƥ�����Ð��Լ�����(hu��)�ČW(xu��)��(chu��ng)������t����(hu��)��һ�����ĕ������������ŷ���棬������ķԸ����Ų��؏�(f��)��
���|��Ľ�(j��ng)������������ģ�����ЩͻȻð��������������������Ҳ�������档�����������ĸ�ӣ�ĸ�H���Ʋʞ���һ݅�ӛ]�ޣ����ú����K��
����M(j��n)�¾ӻ��������M(j��n)�˴��^�@������r(sh��)�b�̈�Ҳ���(hu��)���ˣ��^��(ji��ng)����һ�d�ض��m�Ǻ��пڣ���������δ�b��ë���������]��ˢ������˃��f�K���b�꣬ȹ������픡��ذ塢���܉��棬�������ڟ�����픟���һ��(y��ng)��ȫ�������X�Ͻ���ش����]����ǰ�����_(t��i)��ǰ���T�b���I�T�����ӽ��ٷ��I�W(w��ng)����߅��һ�g���T�ٽo�����k����Ո(q��ng)�]늾��bһֱ���Ԓ���X����һ��(g��)�£�����ʮ�״Σ��Ͳ�Ҋ�ˁ��������R������Ц���R�����ã��ҿ�Ҫ�o�]늾�ؕ�c(di��n)�|����
ֻؕƨ�����ӾͲ�ؕ�������������b�������[���u���u���r(sh��)���ǵضι������Ďׂ�(g��)���wñ����ʳ��Ҫ�㟟�X���́�⡣
���匦(du��)����һ�[ֻ��ЦЦ���u�^��
��ԏ����������˽��ܵĐ�����һֱ���@�������]�е��L;��܇վ�[���u���u���������ڼҳԳ�ʎʎ������˸��F���Ƶģ������x�_���T���������˰��㡣��@���w��(hu��)�����]���X���F�����y�^���X̫�࣬�����ӑÚ⡣
�������ˣ����ˣ��T�푡�
���^��������݃�(n��i)�ⲽ��� ���T������һ�C�����b���b�_���ߵ��Tǰ���۾����]�ұ�������؈�����⏈�������I�T�ϵ������T����ס��ҕ������������ʲô�ˡ�
�T��^�m(x��)�й�(ji��)���푡�
�������(g��)��
���ң�ؔ(c��i)�k��Ԭ��֮��
Ŷ����Ԭ���Ρ����������s�o���_���T�����I�T��
Ԭ��֮��Ҫ̤�M(j��n)�T��Ҋ�ذ�Ϟ��ù�����һ�m��Ⱦ�����QЬ��
��Ҫ�Q����Ҫ�Q����Bæ��r������ֱ�����ϡ���ؔ(c��i)�k���ο����{���R�����Ѹ��d���ѣ���ô�ٺ���˼��Ԭ����ÓЬ�ء�
Ԭ��֮����ƤЬ���_�ڵذ����ߵØO�p�������ڱ������ǘ�С����������߀������Ь��ӡ���\�\�ġ��������Į�����s�o�Q����Ь��
��к�Ԭ��֮ɳ�l(f��)���������σɱ��o�����ȣ����Ͽ��Ȱ�H���ӷ��ǣ����ϲ��P�С�{(di��o)�����ÿ����д����ˣ��dz�������⣬�_���ȵ���ˇ�dz��巴��(f��)�ְ��ֽ̕�(hu��)�ġ�������ͺȲ��T���ȣ���˱˱�ģ��`ɶ�óԣ���Ū�������ҕ��ζ���ØO�˵ďV������ô���ģ��Ї��˺ö˶˵IJ�ˮ���ã��W(xu��)��ǻ��ɶ��
����Ͽ��ȣ��к�Ԭ��֮�ȡ�Ԭ��֮���^�״ο��ȣ�Ҳ��ϲ�g���@�N����Ė|�������K�����ӣ�߀�������غ������������æʲô�ȣ�
ʲôҲ��æ���Գ�ʎʎ���ЦЦ���X���Լ����˸��F����
���Ⱥ�ͣ��(d��ng)����к�����Ԭ���Σ���ÿ�g������
���e(cu��)���UƯ����Ԭ��֮�S��ÿ�Ҟg�[��һ·�c(di��n)�^��һ�����b���cȫ��(j��)��늺ߙn�Ҿ�ʮ����Q��ͻȻ�����۾��䵽�����_(t��i)�������_(t��i)������һ��������Ƭ�����������R���̰l(f��)��ü��Ŀ�㣬���o�o�ăɂ�(g��)�ƸC����Ƭ�ڰģ����c(di��n)���S����߅���@�м��^���E����߅�ԪM����߅�Ԍ�һ�c(di��n)��
Ԭ��֮�۾�һ������һ�����@�������Ʋ�ô��������Ʋ���ʲô�P(gu��n)ϵ��
���ҊԬ���ζ�����Ƭ�������c(di��n)���е��f��Ŷ���@����ķ���������@����Ƭ����?z��ng)]�����^��
��ĸ�H��Ԭ��֮��������´���һ�飬����Ԭ�@�����c(di��n)���ϴ�Ů���ؼ����Č�(du��)���f��Ԓ���������c(di��n)���^���C��(sh��)���Լ��IJy��
���˻ص��͏d��ɳ�l(f��)��������Ԭ��֮��һꇲ�����ƽ�o����̽������ ���������������ô��
�ҏ�С��������h�����@�⣬�����һ�ж�ô���ˑ���ֶ�ô���˂��С�
Ԭ��֮Ŷ��һ�����f������Ԕ��(x��)Մ?w��)��Լ��?j��ng)�vô��
�]ʲôՄ?l��)^�����u�^���L�@һ�⣬������ϵ�һ���t��ɽ�㟟�f��Ԭ��֮��
Ԭ��֮���һ֧���c(di��n)ȼ��һ�ڣ����\���f���f�f�o�����Һ��� ��
Ԭ�����m�Ǵ�٣���ƽ���ˣ�߀���T���������������ź��eĿ�o�H��һ�ǿ�̎�]�V�f�����˴�(ji��ng)��������ڼ����y�^��Ҳ��һ�¶�������Y(ji��)��
�҂�����������y��ķ��ԭ�ǂ�(g��)֪�࣬���Ǻ����������h���(zh��n)����S��������o������һ�˵Ĺ��Y�������_�N�������M(j��n)�W(xu��)У�r(sh��)��ķ��ؓ(f��)��(d��n)�������ˣ����һ��ë��������øΰ����ˡ��S��o�������K���������㏊(qi��ng)�������꼉(j��)����?z��ng)]�X�^�m(x��)���W(xu��)�ˡ�����Ҹ�����䵽�����У����L;��܇վ�u�u���~���������ǰһ���������˰��꣬ҲҊ����ˡ����d����Ό�(du��)�Մ������һ��(g��)�����A�ӻ����£����z��ͬ���������꣬�A�ӻ�����ʧ�ßoӰ�oۙ����R�Kǰ߀�����m(x��)�m(x��)���f�A�ӻ������֡���Ԟ���Ϻ�Ϳ�����������ŵ����ֲ��У��s��߶һ��(g��)�����F���IJ��J(r��n)�R(sh��)��Ұ���š�
��ô�㸸�H�أ�Ԭ��֮���һꇰl(f��)�ᣬ��������������
�ҏ�С�͛]Ҋ�^��������(j��ng)����ķ���������ǿ��p���Ƶ�һ�䣺�����ˡ��e���R��"Ұ�N"����(j��ng)�����������ҵ�ϣ���Ђ�(g��)������ķ���f�H����Ҳ���٣���ķ�����ɿڣ���?z��ng)]���ˡ���Ҫ�������F(xi��n)�ڵ�Ҳ�����^�����ˡ������������Iˮ���������c(di��n)��㱡�
Ԭ��֮Ĩ��һ���۽ǣ��^���˰��죬������Ե�����������ô��
��u�u�^�����X��Ԭ�����������c(di��n)�֣���ô��(du��)���ҵ��½���dȤ��
Ԭ��֮Ϩ�矟���f���Ҹ����fһ���c��ĸ�H���P(gu��n)���¡�
��@Ԍ�������J(r��n)�R(sh��)��ĸ�H��
Ԭ��֮�����ش��Z�⾏�����f�����������꣬�����øߡ����Ю��I(y��)������(zh��n)��ӭ���r(sh��)���Ļ�������_ʼ�ˡ�������(j��ng)�^�����췴������ȫ��ɽ��һƬ�t�Ĵ���ϡ�����h�ЌW(xu��)�����ó��Ю��I(y��)�����Ʋ��·��ږ|�l(xi��ng)�����Aɽ���a(ch��n)�(du��)���c���·���ͬһ���a(ch��n)�(du��)���ǽ�����ʡ���ЌW(xu��)�ģ����ø��Ю��I(y��)����������Ϧ��̎����һ�㣬���L�վã����������ˡ��е�����F(xi��n)�ã����������걻�������]�ϴ�W(xu��)���@�����һ�����r(n��ng)����W(xu��)�����R��ǰ�����ϣ����е������Ʋ�̎Մ�˺ܾã����˶����Ʋ�ס�Լ���͵���˽�����
������ʲô��͵���˷�ʲô�����Ū������
�е���Ů�ı��C���x���W(xu��)��Ȣ�������š�Ů�İl(f��)�ķ������ޡ��ڶ��죬���Ʋ����еĵ��h�����(j��ng)�^�����^���е����h�ď���Ӱ����Y(ji��)�����ˏ�����ĺڰ��ա��е����A�|������W(xu��)�����������߀�Е��Ł�����������Ʋʌ��Ŵ��еĻ��Y(ji��)�飬���f�������Ĺ��⣬�е�ȥ�ń�����̥�����Ʋ��ց��^���ţ��е���Ӱ푌W(xu��)�I(y��)��һ��δ��(f��)����Ӎ���ˎׂ�(g��)�¡�
�@�е��ǂ�(g��)�쎤�|�������۲�ؓ(f��)؟(z��)�Σ����������һ�D��
һ���е�ͻȻ�յ�һ���ţ����_һ������ֻ��һ���Լ�����Ƭ,�]����,�@Ȼ�����Ʋʌ����z�ĺ�Ӱ��Ƭ���_��ā��ġ��еı������ü��ڕr(sh��)�gȥ̽��һ�����Ʋʣ����˕r(sh��)������һ��(g��)Ư����Ůͬ�W(xu��)�����š����I(y��)���������䵽�����й����������˽Y(ji��)����ޡ�
���s�N���S���ģ�ķ��������ɷ����һ݅�ӣ��@�еľ������l��Ԭ���Ξ�ʲô��(hu��)�@����Ϥ�@�£������ⲻ�_���i��
�Y(ji��)����е�����һֱ���������е������ܵ��l؟(z��)����ż�����^ȥ��֪����е�֪�����Ʋ����S֪��һͬ���ǣ��е�һ�z��ο���s��?z��ng)]�c���Ʋ����^���(li��n)ϵ�^��
�������ֵ؆������е����l������ô֪���@���µģ�
Ԭ��֮�I�i�i���f�����еľ����ң��Ҍ�(du��)�����ゃĸ�ӂz��
���������������ôҲ����(hu��)���ţ��y��Ԭ���������Ұl(f��)��ؔ(c��i)��Ҳ�������⡣��ʲô�{�C��
Ԭ��֮�ͳ�һ���ڰ���Ƭ��Ҳ���c(di��n)���S������^����Ҋ����Ƭ������l(f��)��С���ӣ����c(di��n)���Լ��F(xi��n)�ڵ�ģ�ӡ�æ�M(j��n)���g����������_(t��i)����ĸ�H����Ƭ,һ��(du��)�Ͽp,������һ�������p�˺�Ӱ�������ĸ�H�R��ǰָ������Ƭ�f��Ԓ�������������܌���һ����Ƭƴ�ϣ���Ƭ�������˾������������@ô�fԬ���ξ�������ɷ��ɷ��������Ԭ�@�����Լ���ͬ����ĸ�����ã��ֲ����c��һ����ͺ��H����
�Һ��㣬����(hu��)�J(r��n)����������߳��������ɂ�(g��)������Ƭ�������һ������������(d��ng)���⡣
Ԭ��֮������Ƭ�����l(f��)㶣��ۜIֱ�ʣ�����ǻ�f������ҽ��첻��Ҫ���J(r��n)�㣬�����Ǟ�����Xؔ(c��i)��ֻ��Ո(q��ng)�㌒ˡ��������Ҳ������Ů֪���@�º�a(ch��n)����ͥΣ�C(j��)����F(xi��n)��������ˣ���Ҳ�����ˡ�
������������ۜI��������ʮ���ί�������y�����˰��۶�ӿ���ā�����ĸ�H�x�_������һ�x�ǣ�������(j��ng)���^�@�ӵ����^���г�һ��Ҋ����������Ҫ����ǧ���f�Ρ����牋���F֮�У����Ե�Ԭ��֮����ô�x�_�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