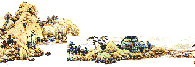|
|
|||
|
荒
|
||||
|
唐
|
||||
|
歲
|
||||
|
月
|
||||
|
□董新芳
|
||||
|
登記號:21-2001-A-(0656)-0115
|
||||||
文化大革命運動越鬧越兇,革命的洪流洶涌澎湃,正象紅衛兵小將所說,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卷大江南北,洗刷著祖國的每個角落。學校完全徹底停課了。縣城的學生革命熱情高漲,一伙伙一隊隊,穿戴著沒有帽微領章的軍裝,戴著紅袖套,舉著大紅旗,向祖國的首都進發,他們在落實偉大領袖的號召,進行革命的大串連。大山沒有參加,他背著鋪蓋卷回到了槐樹溝。重新拿起了鋤頭,拿起了鐮刀過起了莊稼人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生活。這種苦燥無味而勞累,陌生而又熟悉的生活使大山的情緒極為消沉,整日眉頭緊鎖,沉默寡言,就是與爹娘也少有話說。繁重的體力勞動,加上精神上的不愉快,沒多久大山就明顯地消瘦了。張光源和妻子惠賢看著情緒低沉,日漸消瘦,不勾言笑的兒子大山,心里產生了一種深深的不安和焦慮。他們開始琢磨兒子,大山到底咋啦?琢磨過來琢磨過去,老兩口突然明白了,啊,兒子大了,該娶媳婦了。溝南的二順不就是跟大山同年生,一年前就把媳婦娶到家了,如今媳婦的肚子上已扣上了一口大鍋。老兩口明白之后,就張羅著給大山說媳婦。說媳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兒,是要用錢夯的。想到錢,老兩口又犯愁了。多年來他們為供大山小山上學,學費也是東抓西借,家里沒有分文積蓄,住的房子也是茅草屋。每年夏天,是張光源最發愁的季節,他最害怕的就是連陰雨,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雨住了,屋里還在滴滴嗒嗒。每遇這樣的天氣,夜里他們是無法睡覺的。有一年的暑假里,連陰雨下了十多天,他們的屋里擺滿了鍋鍋盆盆,床上擺滿了碗,就這樣,屋里還是連巴掌大一塊干的地方也沒有。那夜,雨下得更猛了,一家人提心吊膽地坐在屋里,忽然墻上的泥皮嘩啦一聲落下一大塊來砸在張光源的背上,一家人如大災將臨緊張地望著黑糊糊的屋頂和被雨水泡濕了的墻壁。惠賢說,他爹,走,咱到他舅家去。張光源說你們去吧,我在家里守著。惠賢說,看這房子的樣子怪怕人……張光源看了看房頂又看了看墻壁說,走,你們快走!惠賢知道張光源的意思,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老爺們,連間瓦房都蓋不起,下雨天跑到娃子他舅家去,臉上有些擱不住,所以他死活也不去。惠賢說,走吧,到娃子他舅家又不是別的人家。張光源說,哪里我也不去。惠賢說,你在家里我們不放心。張光源說,有啥不放心,走吧。惠賢見勸不動張光源,心里有些生氣,跟大山小山說,走,咱走。咱可不死要面子活受罪。那夜他們淋著雨跑到了舅家。從那以后,蓋瓦房成了張光源奮斗的目標。但幾年過去了,目標仍未實現。做生意被當成了資本主義的尾巴,今天割明天割,弄得他門也不敢出了,娃子的學費都成了問題,哪里還有錢蓋瓦房?大山要說媳婦,要花錢,張光源能不發愁?張光源四處張羅,又是托媒人又是到處借錢,幾個月過去了,還是八字沒有一撇。 春節到了。娃子過年,大人過關。這話一點不假。為了置辦年貨,惠賢賣了兩只雞,賣了幾十個蛋,湊湊合合買了兩斤肉,兩斤粉條,三斤白菜,五斤籮卜,半斤生姜,兩錢花椒。過年穿的衣裳,惠賢早翻洗過了。新的沒錢買,舊的拆洗一下翻個面當新的穿。這是窮人家的窮辦法。大年初一,天還沒亮,村里的鞭炮聲象炒豆子一樣噼噼啪啪響了起來。惠賢沒買鞭炮,大山小山就沒起那么早,直到惠賢燴好頭腦(粉條,涼粉,籮卜,白菜一鍋煮),兩個人才起來燒香敬神。先敬的是灶王爺。灶王爺的神龕就在灶房里,近水樓臺也該先得月,何況灶王爺臘月二十三日就上天言好事去了,初一五更才回宮降吉祥,這是要隆重迎接的。既然是迎接灶王爺,就得鳴禮炮。但惠賢買了吃的,錢也就用光了,所以就沒有買鞭炮。迎接灶王爺,沒有鞭炮,這種歡迎儀式就顯得冷清了些。張光源生怕得罪了灶王爺,先在灶王爺的神龕前擺上供品,而后上香,一家人先后磕頭,之后,大山說,小山,來,咱們放炮。小山信以為真,跟著大山跑到院里,問炮在哪里。大山從口袋里掏出一個生了銹的書夾子說,這就是炮。小山一看非常失望,扭頭就走。大山說,小山,你甭走,這比放炮還來勁兒。大山說著用手捏得書夾子啪嗒啪嗒直響。小山說我不放。張光源和惠賢本來在看兩個兒子玩啥把戲,見此情景都把臉扭在了一邊。惠賢說,都來吧,扁食煮熟了。一家人一人端了一碗扁食過起了年。 年過罷,地里就有活了。施肥,耙地為春種做準備。常言說,柿葉發,種棉花。春天來了,看似干枯黑如鐵條的柿子樹的枝條上鉆出了黃豆大的串串綠珠,如青蛙的眼睛。它欣喜地告訴人們,該種棉花了。于是人們就按照它的指令在剛剛梳理過的土地上忙碌起來。棉花是點種,通常是一個男勞力挖窩,一個女勞力下種。一雙雙一對對在地里一字兒排開,那種場面尤如練兵場上的士兵。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社員們揮舞鋤頭的,彎腰下種的,有說有笑。小山也夾在中間,跟他下種的是燕子。今天,小山剛到地頭,燕子就挎著竹籃不聲不響地走了過來,輕輕地喊了一聲小山哥。他知道燕子想跟著他下種,他也希望燕子跟著他下種。小山聽到燕子輕柔的甜甜的叫聲心里頓時升起一股甜絲絲的感覺。那種感覺進入血管溶入血液漸漸擴向全身,由甜絲絲而麻酥酥,那感覺中含有一種無法言表的深情。說實話,小山也不小了,也到了談婚論娶的年齡。但因家境貧寒且上頭還壓著個光棍哥哥大山,因此小山從未敢想過此事。哥哥沒成親,弟弟就不能談婚事,姐姐沒出嫁,妹妹就不能先出門。這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老規矩,雖只是家規,但從無人違犯。而且在爺爺的爺爺輩中曾出現過光輝的典范。 據說在爺爺的爺爺那代人中有兩兄弟,老大叫張京,老二叫張南,爹娘早逝,家境貧寒,一間草房半間漏,兩人共睡一張床。張京年近三十,從無人給他提過親,張南也已二十多歲,長得人高馬大,站起來能捅天,眼看再過兩年也將進入而立,那時也就走出了閨女們擇婿的年齡之外。張京非常著急,他兩兄弟不能就這樣斷了他家的香火,要是在他倆手上斷了他那支人的香火,將來他倆就無臉面在陰曹地府與爹娘相見。于是張京勸弟弟張南說個媳婦,張南不答應,張京仍四處托媒,八方張羅。蒼天不負苦心人,終于找到了一個愿意嫁給張南的閨女。張京一說,張南死不應允,說哥哥沒娶,他豈能占先,如果哥哥堅持己見他就碰死在南墻上。張京無奈只好作罷。但張南的話使他如有所悟,他在一天,弟弟就一天不娶,如果他先走了,弟弟就無話可言。于是在一個風高月黑的夜晚張京跳進了北溝的響潭。按理張南這下可以娶親了,父輩中有位叔叔勸張南早日成婚以免哥哥之念,張南仍不從,他要為哥哥守孝三年。三年之后有人給張南提親,張南說哥哥未娶他決不先娶,來人明白他的意思,就給他哥哥說了一門陰親,張南按照陽間的風俗把女人的尸骨與哥哥的尸骨合葬在一起。這時的張南也年過三十了。年齡雖然大了,但張南的人品德行卻傳遍了方圓左近的村村寨寨,感動了不少男男女女。有一老者因受其感動,主動托媒把自己的閨女嫁給了張南。張氏兄弟的故事在神佑縣乃至更遠的地方奉為美談。幾代人過去了,但張京張南仍然是張家處理兄弟關系的典范。每當村里出現兄弟不和之事,長輩們都會搬出張京和張南,把他們的事情細細述說一遍,不和睦的兄弟就會啞口無言,羞愧難當,互相致歉。每年農歷二月十五和七月十五是上墳祭祖的日子,家家戶戶都會自覺地給張京張南的墳墓上添锨土,燒炷香,所以現在張家那一大片墳地中就屬張京張南的墳堆大,也就屬那兩個墳堆顯眼。 小山除了這個顧慮之外,他還有一個顧慮,那就是他與燕子是一個村的。一個村的成親,在他們那里也無先例。趙溝那對青年的慘死,小山和燕子都非常清楚。趙溝那對青年,自幼生活在一起,青梅竹馬,相愛至深。年齡大了,兩人就確定了戀愛關系,消息傳出,好象放了一顆炸彈,小小的趙溝頓時議論紛紛,說他倆傷風敗俗,道德淪喪,無數雙白眼投向兩個年輕人。加之雙方家庭極力反對,兩個年輕人無奈而雙雙跳進了水庫。據說跳水庫時兩人是抱著跳下去的。他們的爹娘和村里很多人都看到了,但無一人下水去救。還說象他們這種人死一個少一個,死兩個少一雙。不然今后必將成為村里的禍害。他們不但不為兩個年輕人惋惜,為兩個年輕人悲傷,反而有一種禍害被除的快感。后來兩具尸體從水底漂浮起來,男女兩家各撈各的尸體,安埋時釘棺材用的都是桃木釘子。鬼怕桃木,他倆就永遠無法出棺,永遠無法投生。 “小山哥,你在想啥?”燕子見小山心事重重的樣子問道。 “沒想啥。”小山不緊不慢地一鋤接一鋤地挖著窩。 “沒想啥,你哄人。”燕子望著小山的臉。 “真的沒想啥。” “不說就算了。”燕子不笑了,也不再看小山,埋著頭下她的種籽。 沉默。難耐的沉默。鋤頭有節奏地嚓嚓地響著,附近不斷傳來男女逗笑的聲音。 “你不說是不是?”燕子忍不住了,小聲問,但口氣強硬。 “我不知道該咋跟你說。”小山見燕子生氣了,不得不回答燕子的問話。 “你咋想就咋說。”燕子低著頭。 “我在想這棉花幾天才點得完。”小山沒有勇氣說出他想說的話,話到口邊拐了個彎兒。 “你就想這?”燕子不滿地問。 “就想這。” “那你慢慢想吧。” 兩人再次陷入了沉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