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言
本書從人地關系的理論前提出發,主要運用“地域一家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對唐代關中地域文學進行探賾,對與文學發展具有關聯性的關中地域文化和關中士族的一些歷史事實進行整理,對本地域文學的發生機制重新詮釋,在此基礎上為唐代關中文學進行定位。
所謂人地關系實際上就是人類社會生活與自然環境交互作用的關系,這是人文地理學及分支文化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文化地理學研究的是一定地理空間范圍內各種文化因素的分布結構、形成條件,以及文化景觀、文化生態的地域特徵、演化發展等內容,并強調文化集團的空間組合機能和地域系統特徵,指出地表所發生的文化差異對人地關系具有深刻的影響。其中文化景觀、文化源地、文化傳播、文化地理區或文化區是研究者最為矚目的幾方面的內容,而文化區域的鑒別、定義和分析,又是文化地理學研究的基礎。
從文學史學科的角度來理解文化地理學的人地關系,實際上就是承認文學和地理環境的相對性。它包括作家誕生的地域風貌、作家分布的地理特徵、作品的地域風格、遷徙流動所帶來的舊范式的突破,一定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特殊遭際對作家的綜合影響,由方土風氣等因素所造成的文化差異在創作上的投射,文學的傳播交流所導致的地域特徵和空間風格的淡化與消解,由地域性的空間風格向超地域性的時間風格演進過程的規律等等。
所謂“地域一家族”研究方法,是文化史學的一種操作技巧,根據筆者的理解,實際上是將文化地理學與社會史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邊際研究”。
家族制度或稱宗族制度是傳統中國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徵。家族的演生變化雖然非常巨大,但在整個前現代社會中,草蛇灰線,仍然具有其一貫性,而其與社會、政治、經濟、倫理、文化(包括文學)的影響作用,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馬克斯.韋伯稱中國為“家族結構式的社會”,許烺光乾脆以宗族作為中國社會的代名詞,藉以比較說明印度的種姓社會、美國的俱樂部社會。
被陳寅恪譽為“清代史家第一人”的錢大昕,曾提出史家所當討論者有三端:曰輿地,曰官制,曰氏族。錢大昕所說的輿地即歷史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研究,氏族即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史學中的家族研究。陳寅恪認為中國家族倫理之制度發達最早,在中古史研究中,尤其致力於地域與家族關系的探討:
蓋自漢代學校制度廢馳,博士傅授之風氣止息以后,學術中心移於家族,而家族復限於地域,故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皆與家族、地域兩點不可分離。河隴一隅所以經歷東漢末、西晉、北朝長久之亂世而能保存漢代中原之學術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與地域之二點,易言之,即公立學校之淪廢,學術之中心移於家族,太學博士之傅授變為家人父子之世業,所謂南北朝之家學者是也。又學術之傅授既移於家族,則京邑與學術之關系不似前此之重要。當中原擾亂京洛丘墟之時,茍邊隅之地尚能維持和平秩序,則家族之學術亦得藉以遺傳不墜。劉石紛亂之時,中原之地悉為戰區,獨河西一隅自前涼京張氏以后尚稱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學術既可以保存,外來避亂之儒英亦得就之傳授,歷時既久,其文化學術遂漸具地域性質,此河隴邊隅之地所以與北朝及隋唐文化學術之全體有如是之密切關系也。
從學理上說,家族是一種血緣性組織,是血緣性縱貫軸的基元。其存在具有地緣特徵,氏族郡望不過是“血緣的空間投影”,家族既具有血緣與地緣的雙重性,所以其與地域實際上是相互重疊、合二為一的。在地域文化研究中顧及到家族的因素,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意。而陳寅恪先生的一系列論述,與其說是給筆者提供了許多翔實的史料,毋寧說是方法論的深刻啟迪。當然,柳詒徵、錢穆、岑仲勉諸位史學大師對“地域一家族”研究方法亦頗多發明,并且都有示范性的成果,本書中多有借鏡采錄。
根據以上所提及的理論背景和研究方法,檢視中國古代文學,特別是唐代文學的研究現狀,筆者發現有如下特點:
首先,對文學創作與地理環境關系的認識,頗為深入,認為南北地域及其方土風氣形成了南北文化和文學的差別,隋唐政治統一促使南北文化進一步交流融合,故文學的審美情趣和風格呈現出一種融合統一狀態。政治的統一、文化的交流固然有助於弱化甚至一定程度上消融地域差別,但并不能徹底抹掉地域差別,由不同的
地域特征所造成的作家氣質稟賦、作品風格差別不僅在唐代依然存在,就是在此后的宋元明清、甚至現當代文學中依然存在。所以對統一時期地域差別的重視,可以使研究進一步深化。
其次,南北地域固然為重要的文化區分,但這種區分無論是從地理學還是文化學來看,仍嫌籠統。北方區域中關中、隴石、三晉、河洛、燕趙、齊魯,南方區域中的荊楚、吳越、巴蜀、嶺南等文化圈,其間固有相同一致處,但彼此的差別以及這種差別對文學的細微深入影響,在文學史研究中涉獵較少。以隋唐文學研究而言,討論南北文化的差別和統一固有的價值,如能同時兼顧東西的對峙與緩和,并進一步深入到江南、關東、關西、代北等不同區域中,探討其與文學演生的關系,將更有意義。尤當指出的是,關中地域作為京畿所在,既有地域文化的特徵,又因處於政治文化中心而具主流文化的特徵,所謂貞元之會合,光岳之鐘靈,故其對文學的影響也更形復雜。明人李東陽指出:“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人也。蓋周以詩教民,而唐以詩取士,絲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軌車書所聚,雖欲其不能,不可得也。”霍師松林在《唐詩與長安》一文中,曾有專門闡述,透辟精當,對筆者撰寫本書啟發良多。
第三,從家族文化的角度觀照文學現象,近年來已經取得長足的進步。如對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制度與文化學術及文學創作的關系研究,涌現出不少頗有分量的成果,其中包括一些碩博士論文。但相形之下,對唐代家族或士族與文學的關系性研究,則顯得很薄弱,已經問世的成果很少。其實,對此問題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很早。明代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三發現唐代父子、兄弟、夫妻以文學并稱者甚眾,并且分別就父子、兄弟、父子兄弟、父子祖孫、夫妻諸項,舉例加以說明。胡應麟還敏銳地指出:“唐著姓若崖、盧、韋、鄭之類,赫奕天下,而崖尤著。蓋自六朝、元魏時,已為甲族,其盛遂與唐終始。文皇首命群臣品第諸族,時以崔民為第一。嗣后達官朊仕,史不絕書,而能詩之士彌眾,他姓遠弗如也。”他還隨之信手羅列崔氏能詩者近六十人,然后總結說:“初唐之融,盛唐之顥,中唐之峒,晚唐之魯,皆矯矯足當旗鼓。以唐詩人總之,占籍幾十之一,可謂盛矣。”胡氏的具體結論或可進一步商兌,但他所提出的問題以及所切入的視角,無疑亦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職是之故,本書試圖探討唐代時期關中地域士族演變與文學發展的種種關聯性,并緣此對唐代關中文學進行文化透視,在如下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提出關中文化精神的范疇,指出關中文化精神是指關中地域所形成的文化傳統,是關中文化所特有的價值觀念和終極依據。通過對關中文化精神的建構,試圖勾勒唐代關中文學發榮滋長的文化背景。
第二,從方土風氣的角度來闡釋關中文學趣味──雄深雅健,并具體闡釋形成此趣味的原因。從文化地理學的觀點來看,文學趣味的形成,實系方土之風氣,即地域文化諸要素在歷史過程中積淀而成。通過“雄深雅健”風尚形成的追溯,描述唐代關中文學特殊的美學氛圍。
第三,士族是中古社會的一極重要特徵,但有關唐代士族的狀況,在學術界看法較分歧。筆者持唐代處於士族發展的轉型期,士族的衰亡淪替在唐末五代的觀點。本書側重對“關中郡姓”和“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兩個命題進行闡釋,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豐富的文化意涵。
第四,提出關中文學士族(或文學世家)的范疇,并從兩個方面討論唐代關中文學群體的形成。首先,從時間維度來考察關中文學士族的崛興,認為關中士族經歷了一個從文到武,又由武到文,即從經史世家到武力強宗,再由武力強宗到文學世家的演生變遷過程。其次,關中文學群體的構成頗復雜,就地域和族姓來分析,
分別有關中本土作家群,河東著姓和代北胡姓加盟關中文壇,江南和山東士人播遷關中者等幾部分組成。這是一個龐大而又松散的創作群體,關中士人與山東士人、江南士人一方面各具特色,呈鼎足之勢,另一方面又因遷徙流動,促成交流融合。
第五,指出唐代官學雖衰微,但私學仍有新發展,關中士人重視家族教育,尤其強調文學教育。
第六,循此,對中晚唐政壇上的“牛李黨爭”這一重大事件進行檢測,通過統計分析,發現“牛李黨爭”中兩派核心人物的郡望分布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徵。李黨成員主要是山東郡姓士族,而牛黨成員基本上屬於關隴士族,牛李黨爭并非是庶之爭,而是士族之間的“圈內之爭”。
第七,分別就蘇綽文體改革、柳宗元古文與關中學術資源、竇叔向家族貫望等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試圖通過文學現象個案的管錐,使人們對唐代關中文學有更深層次的認識。
本書前七章為總論,力求從大處著眼,宏觀把握。八、九、十章為分論,不求面面俱到,僅就所涉及的問題從一點開掘,盡理深入。附錄則是相關問題及材料的考證。擬議中尚有討論關中韋氏與杜氏文學各一章,因仍未最后定稿,留待將來本書訂時再補入。
本書雖偏重歷史文化研究,但仍努力追求理論概括、文本分析與史料考證相結合的學術傳統。在材料的運用上,除注意基本文獻的考訂外,還頗多留意海外漢學界的研究成果,使課題的確定和觀點的提出,既避免重復雷同,又防止學術失語癥,試圖通過這一有關地域文學的題目實現與國際隋唐史和隋唐文學研究界的銜接對話。
當然,因筆者僻處西北一隅,獲取國內外學術新成果和資訊難免受到局限,所以,筆者的這種努力,與其說是一種成果展示,毋寧說是一種希望和追求。
關中地域水深土厚,關中文學淵遠流長,博大精深,筆者雖然頗早就留意於此問題,且進行了數年的資料準備,力求排除各種干擾和誘惑,但因資質愚鈍,學殖有限,只能將這一初步的成果提交出來。對於這一課題的研究而言,本書雖然只截取唐代一段,限定在與士族相關的文學現象中,但仍然只是問題的精淺提出,而并非完滿圓融的解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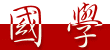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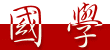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