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璇琮
大約十多年前在太原召開的第四次唐代文學學術討論會上,我結識了畢寶魁同志,并對他提供會議的《王維生年考辨》論文很感興趣。關于王維生年,學術界認為向有定論,不必再議,而畢寶魁同則從王維詩句實際出發,進行細致的考辨,提出新見。我覺得學術研究應有思辨精神,特別對年紀較輕的研究者,我們更應珍視。后來我與他作一些具體討論,他也作了一些修
改、補充,我把這篇文章推薦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主辦的《文獻》學刊上發表,發表后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在這之后,寶魁同志的研究大致分為兩路。一是關注東北文學的歷史發展,后來撰成《東北古代文學概覽》一書。此書勾勒出東北古代文學的大致輪廓和發展脈絡,材料宏富、考證翔實、結構清楚。新見迭出,拓展中國文學史地域性研究,表現出難得的開拓精神。另一方面則仍沿著唐代文學研究的路子走,近幾年來出版了《王維傳》。《李商隱傳》,這次又推出《韓孟詩派研究》。但他并不完全依照傳統模式的格局,而是努力在作家作品
研究上滲入時代的意識,并把專業研究與拓寬普及面結合起來,力求使優秀的傳統文化更易于為現代人所接受。我覺得這樣的治學格局在現在是很值得探索和倡導的。
韓愈研究一直是個熱門,有褒有貶,這種褒貶過去往往受現實政治的影響,而在研究者來說,則視野不免有所偏,對韓愈作品的探討很不全面。近二十年來,情況大有改變,中唐詩歌的流變也受到唐代文學研究界的關切,己有好幾部專著問世。本書是正式把韓愈倡導的詩派作為專題來研究的,比較全面地把韓愈詩派的形成過程,如時間、地點、主要人物、隊伍形成情況等作清晰的論述,并將韓愈詩派放在特定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進行研究,使人有具體的歷史感。書中重視從資料出發,來作理論概括在充分占有和運用資料的前提下,闡釋韓愈詩派的特點,使人有充實感。如引征韓愈。孟郊詩近百首,李賀、賈島詩有五六十首,盧仝、劉叉等人詩也在二十首左右,這對讀者認識這一詩派的總體詩風很有幫助。對詩派的研究,現在有些書往往偏重于作所謂宏觀把握,不對作品作具體分析。寶魁同志是一向重視求實學風的。書中對韓愈《感春·五首·其三》一詩考釋評析甚為透徹,對盧仝《與馬異結交詩》進行全篇講析。這樣的作法,過去同類著作是少有
的。有些爭議的問題,如李賀參加河南府試及參加進士考試受阻之時間,賈島初見韓愈的地點與時間,都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當然還可討論,但這種獨立探討的作法,以及問題提出的視角,是能給人以啟發的。
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近二十年來成果已經不少,特別是唐代文學研究,似乎更受到學界的贊譽。但隨即就產生一個問題:這種研究如何更往前推進,如何引向深入。這個問題如不引起注意,并探索新的路子,則很可能就維持現狀,重復寫作,來回雖有走動,實際仍是原地踏步。從寶魁同志的這部書,我想到,我們要把現有的研究再往前跨進一步,就要擴大作家作品的探索面,并把作家的活動與當時的社會生活更好更細的結合起來,使人覺得這一作家確是一個活的人,有個性的人,有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特色的人。要努力顯示古代文學的原貌,使我們今天能走近它的時代。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說:"我是把古書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疇里去研究",他研究的《詩經》,總是努力要"帶讀者到《詩經》的時代"。前輩的這些話是很值得我們思索的。
但可能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空想,或是一種幻想,不切實。但我覺得我們是不妨從這方面試著作一作的。我在八十年代撰寫《唐代科舉與學》,就不是按照學科性的寫作方式,而是從唐代人所寫的作品(包括詩。文、筆記,小說),把唐代士人的種種情況通過科舉考試這一共同關心的社會現象,作整體的描述。這是不妨以韓愈為例,談一些我的看法。過去把韓愈往往寫成儒家正統人物,是思想界、文學界的領袖,好似現在一些社會名流那樣,擺出一副架子。實際上韓愈是一個平常的人,容易理解的人、有自己頭腦的人。譬如他在早期,即德宗貞元時寫給他友人崔群的一封信,其中說:"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己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施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為何,無乃所好惡與異心哉?"這篇《與崔群書》是不大為為人注意的,丈其是這段話,似還未有人說起過。我在一篇短文中引錄這段話,說讀到這幾句,自然會想起司馬遷的《太史公自敘》。韓愈一開頭就說,自古以來,就是好人少,不象樣子的人多,而至現在。則賢者往往沒有好的境遇,即使謀得一個低級位置,過不久也就死了,而不賢的人卻總是能做到大宮,而且志滿氣得,長命百歲:這,天意何在呢?試問:韓愈這里發牢騷己發到什么程度?另外,貞元十九年,關中大旱,朝廷下令,說為減輕京都負擔,明年暫停科舉考試。韓愈這時任國子四門博士,自稱還不算"朝官",但卻給皇帝上了一份奏狀,以為不宜停試。就事論事,這不算什么,但韓愈在這份奏狀的后部分卻忽而引出一個高調,說"令者陛下圣",即使古代的堯、舜也及不上,但朝中群臣,其賢"不及于古","又不能盡心于國",于是突然下了八個字:"有君無臣,是以久旱"。這確是觸目驚心的。試想,當今的皇上德宗能比得上古代圣君堯、舜嗎?這大家心里都明白。"無臣"是怎么造成的,不是這個"君"的責任嗎?"有君無臣",實際上是對當時朝政的全盤否定。這在史無前例的十年"文革"中,是會作為"現行反革命"而抓起來的。
韓愈的有些行為也是值得提一提的。李翱所作《韓公行狀》,說韓愈于元和時官職升遷,任國子祭酒。有一位教官(直講),"能說禮而陋于容",而當時在國子監當學官的"多豪族子",看不起這位直講,不屑與他同桌吃飯。韓愈知道后,就讓差吏把這位直講請來,說"與祭酒共食"。大家知道,國子學是當時設在長安的最高學府,入學的,"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勛宮二品。縣公京宮四品帶三品勛封之子為之"(《新唐書·選舉志》)。也就是,國子學的學生,差不多都是高干子弟,那末在里面教出的也多是"豪族子",當然看不起這位非"豪族子"而"陋于容"的直講。但韓愈作為最高學府的校長(國子祭酒),卻能作出如此異常的舉動。韓愈還有不少超常的舉止,其他如孟郊、李賀、盧仝等也有值得注意的特異行為,限于篇幅,這里不能多講,我覺得,他們的這種生活方式,心理狀態,與其詩歌風格是有有機的關系的,很值得我們今人思考。
韓愈是很講究道統的。他在《原道》中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傳焉。"研究者一般以為韓愈這里是以孟子傳人自居的。北宋時蘇軾稱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也含有此意。陳寅恪先生《論韓愈》一文,認為"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后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并認為韓愈一方面總結儒家道統之說,而另一方面又"開啟宋代新儒家治經之途徑"。但有個現象值得注意,宋代以程、朱為代表的新儒學,并不承認韓愈的道統地位。宋代理學家認為韓愈雖然提倡道統有功,但他本人的思想并不純正,因此,一般把他排除在道統傳承之外。朱熹在《大學章句序》里明確提出:"河南程氏兩君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
傳。"南宋的黃斡在《朱子行狀》中,更進一步把朱熹列進去,說:"由孟子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嘉而始著。"因此說韓愈下接宋以后新儒子,對宋代新儒子有開啟之功,事實是否為此,尚待商榷。但這不能貶低韓愈,我個人認為這反而可以說明韓愈思想確非儒家道統所能拘限,這恰恰是韓愈可貴之處,也是宋儒所不能理解,或雖有理解而不能接受的。這是我讀了寶魁同志這部著作后所得到的啟示而產生的一些感想。寶魁同志嘗試著想把學術著作與普及結合起來,將嚴謹的學術成果轉化為輕松愉快的文學作品,嘗試著走一條學者兼作家的道路,這一想法頗有時代意義,在本書中有很好的體現。書中列韓愈為詩派的旗手,孟郊為先鋒,李賀為大將,盧仝、劉叉為
怪將,賈島等為偏將,可能有些研究者對此會有意見,但這未嘗不是學術研究走出自己小天地的一條新路。寶魁同志還在進行遼寧省教委"七"重點科研項目"東北文學史"研究,他正當事業有為之年,這樣把學術面作適當的拓寬,從整體上說對自己的治學格局是有利的。希望寶魁同志創新、求實之作絡繹問世。
1999年6月于北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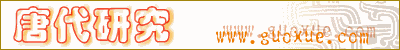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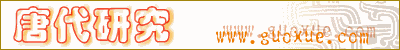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