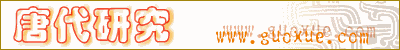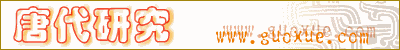|
|
|
寒山生卒年新考
在唐代詩人中,寒山的生平是一個千古之謎。"寒山生平之謎"的產生,一方面是由于他隱姓埋名,長期隱居,曾自謂"我住在村鄉,無爺亦無娘。無名無姓第,人喚作張王",顯然不愿說明根柢;另一方面,在他辭世后,有人偽托初唐閭丘胤之名,撰寫了一篇《寒山子詩集序》,而取代了寒山同時代人徐靈府的寒山集原序行世,這就使他真實的生活年代更云遮霧障,撲朔迷離了。中外學者都曾對他的生平進行過研究,尤其是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將《寒山子詩集序》證為偽作之后,寒山生活年代的"貞觀說"被否定了,寒山生平的輪廓也逐漸顯現了出來。僅就其生卒年來說,到目前為止已有海內外學者提出"700~780"(胡適)、"750~820"(孫昌武)、"740~820"(日本松村昂)、"710~815"(陳慧劍)、"691~793"(錢學烈)等。這表明寒山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但與此同時,寒山生平的歧見仍然比較多。由于寒山生活事跡不彰,也有論者對其人物的真實性表示懷疑,提出寒山真偽的問題。寒山在一定范圍內是作為一個宗教的傳說,一個神奇的故事被傳播和接受。筆者認為,雖然對寒山生平的了解存在很多障礙,甚至因時間的風塵湮沒了史實,有許多重要的事跡已無法探究,但這并不會導致寒山虛無的結論。畢竟寒山詩中有些記敘到生平行止的作品,通過參證其交游,挖掘文獻史料,可以進一步考據寒山事跡,看到一個真實的唐代詩人的基本面貌。本文試圖在中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對其生活年代進行再考訂,并對寒山部分隱而不彰的事跡作管窺蠡測,這亦或有助于全面地探討其人其詩,闡釋那一愈久而愈具魅力的"千古寒山之謎"。
一、寒山遇靈祐、從諗考
晚唐間那篇托名貞觀時代臺州刺史閭丘胤的《寒山子詩集序》是在宗教背景下產生的。說穿了,是為了消除因著名道士徐靈府所編《寒山子集》行世而產生的其人其詩的道教色彩,力圖顯示寒山的"釋氏本色"。但作偽的手法并不高明,在宋代就引起了懷疑。最早對此獻疑的是宋釋贊寧,他在《宋高僧傳》卷一九云:"閭丘《序》記三人,不言年代,使人悶焉。復賜緋,乃文資也。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閭丘也。又大溈祐公于憲宗朝遇寒山子,指其泐潭,仍逢拾得于國清,知三人是唐季葉時猶存……為年壽彌長耶?為隱顯不恒耶?"
大溈祐即靈祐,開溈仰一宗,為唐季禪門五宗之一。其遇寒山一事在歷代有關寒山的記載中是最為具體的,具有重要價值。這一事跡雖已見揭示,這里仍有必要引錄五代南唐泉州招慶寺靜、筠二禪師于南唐保大十年(952)編纂的《祖堂集》卷十六《溈山和尚》有關內容如下:
溈山和尚嗣百丈,在潭州。師諱靈祐,福州長溪縣人也,姓趙。師《小乘》略覽,《大乘》精閱。年二十三,乃一日嘆曰:"諸佛至論,雖則妙理淵深,畢竟終未是吾棲神之地。"于是杖錫天臺,禮智者遺跡,有數僧相隨。至唐興路上,遇一逸士,向前執師手,大笑而言:"余生有緣,老而益光。逢潭則止,遇溈則住。"逸士者,便是寒山子也。至國清寺,拾得唯喜重于師一人。主者呵嘖偏黨,拾得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不同常矣。"自爾尋游江西禮百丈。
《宋高僧傳》卷十一《唐大溈山靈祐傳》亦載靈祐冠年剃發,三年具戒,及入天臺,遇寒山子于途中,又旋造國清寺,遇拾得申系前意,信若合符,逐詣泐潭,謁大智師一事。"冠年剃發,三年具戒"即二十三歲之謂,與《祖堂集》所記其杖錫天臺時間相符。大智師乃百丈懷海之謚號,其"二十三游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事又見《景德傳德錄》卷九,是可信的。據《祖堂集》卷十六本傳、《全唐文》卷八二○載鄭愚所撰《潭州大溈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靈祐生于大歷六年(771),大中七年(853)示化,享年83歲。其遇寒山、拾得事在貞元九年(793)。
趙州和尚從諗,俗姓郝,青州緇丘人,童稚之歲,超然離俗,于本州龍興寺出家,后到池州,謁南泉普愿而悟禪機。年八十后住趙州觀音院講習禪法,從者甚多。得高壽,后謚真際大師。從諗遇寒山事見于《古尊宿語錄》卷十四:
師因到天臺國清寺見寒山、拾得。師云:"久向寒山、拾得,到來只見兩頭水牯牛。"寒山、拾得便作牛斗。師云:"叱叱!"寒山、拾得咬齒相看,師便歸堂。二人來堂內問師:"適來因緣作麼生?"師乃呵呵大笑。一日,二人問師:"什么處去來?"師云:"禮拜五百尊者來。"二人云:"五百頭水牯牛聻尊者。"師云:"為什么作五百頭水牯牛去?"山云:"蒼天,蒼天!"師呵呵大笑。
這段語錄又見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志南《天臺山國清寺三隱集記》和淳祐十二年(1252)普濟《五燈會元》卷二。這兩個記載基本相同,比《古尊宿語錄》簡短但有具體些的內容。如《五燈會元》卷二云:
天臺山寒山子……因趙州游天臺,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么?"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游山。"州曰:"既是羅漢,為甚么卻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么?"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以上所錄為唐代禪門公案,古今都曾有人產生懷疑。如日本元祿十四年(1701)本內以慎《寒山子傳纂》云:"志南《三隱記跋》、《趙州錄》等共載寒山、拾得、溈山、趙州一時問答之辭,疑是偽書歟。予伏考《唐年譜》,寒山唐太宗貞觀七年癸巳隱天臺山;溈山、趙州唐大中、乾寧人也,謂夫百有余年之后輩也。"又,胡適《白話文學史》云:"《趙州語錄》是一個妄人編的,其人毫無歷史知識,任意捏造,多無根據。如行狀中說從諗死在'戊子歲'而無年號……《傳燈錄》說他死時百二十歲。即使我們承認他活了百二十歲,從后唐明宗戊子(928年)倒數百二十年,當憲宗元和三年;而《語錄》說他見了寒山、拾得,又去見百丈和尚(懷海)。百丈死于元和九年(814年),那時從諗還只有六歲,怎么就能談禪行腳了呢?"
本內以慎所據之《唐年譜》蓋與宋僧志磐的《佛祖統記》同一史源,《統記》載寒山、拾得見閭丘胤在貞觀七年。但這一說法系據托名閭丘胤所撰《寒山子詩集序》衍生而出。閭序已足證為偽作,據此來質疑溈山、趙州遇寒、拾事就毫無意義了。又,胡適撰寫《白話文學史》時,惜未利用到《祖堂集》,如能發現《祖堂集》中的材料,考得貞元九年溈山遇寒山事,對趙州之事或有別論。誠然《趙州語錄》中或有虛妄的內容,但并不能說有關趙州諸事皆屬子虛烏有。且從今傳各版本《趙州禪師語錄》看,從諗見寒、拾與見百丈并非同時銜接之事,"他見了寒山、拾得,又去見百丈和尚",恐系胡適誤讀。固然從諗的卒年在《趙州語錄》所附《行狀》中記為"戊子歲十一月十日",但應該知道此處"戊子"乃"戊午"之誤。"戊午十一月"與《景德傳燈錄》卷十所記從諗卒于"乾寧四年(丁巳)十一月"只差一年,并不能說完全失據。無論其滅寂于丁巳(897)或戊午(898),在元和九年(814)百丈死時從諗已三十六、七歲,此前當然可以"談禪行腳"。雖然我們尚無確切的材料證定趙州從諗與寒山相見的時間,不過從寒山說"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的口氣來看,顯然兩人年齡相差很大。稱"這廝兒",似其時從諗在弱冠前后,以其生年(778)推之,寒山遇從諗當在798年前后,亦即靈祐遇寒山、拾得后不久幾年。
二、《寒山子集》編纂時間考
寒山貞元九年(793)遇靈祐及不久遇從諗的事跡說明,唐德宗貞元中期,寒山尚在天臺山國清寺與寒巖之間活動。有學者遂據此作為寒山的卒年,似乎稍嫌簡單。 對寒山的卒年應廣泛利用文獻資料,作進一步探考。這里,我們不妨先考察一下《寒山子集》的編纂這一相關問題。這方面最基本的材料是人們比較熟悉的存于《太平廣記》卷五十五中晚唐杜光庭《仙傳拾遺》的殘段: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居天臺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自號寒山子。好為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于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柏征君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為三卷,行于人間。十余年忽不復見。
這一資料是歷史風塵中殘存的吉光片羽,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將其列為"關于寒山材料比較可信的兩件"之一。余嘉錫和松村昂等中日寒山研究專家亦都認為這一資料是可據的。確實這一資料為考察歷史上第一部《寒山子集》編纂情況提供了重要線索。
徐靈府,號默希子,錢塘(今浙江杭州)天目山人。唐代著名道士,通儒學,先居湖湘衡岳,后遷居天臺山,以修煉為樂。著作今存《通玄真經注》十二卷,收入《正統道藏》。又《天臺山記》一卷,有圓融藏本,《古逸叢書》據收,日本《大正藏》卷五一史傳部三據《古逸叢書》本收入。在以上所引《仙傳拾遺》中具體記載道寒山詩三百余首"桐柏征君徐靈府序而集之",由此可知首編本《寒山子集》蓋以"桐柏徐靈府"題署。桐柏山與天臺山相接,為道教圣地福境。徐靈府在《天臺山記》中自述:"桐柏東北五里有華林山居,水石清秀,靈寂之境也。自觀北上一峰可五里有方瀛山居,上有平地頃余,前有池塘廣數畝……西接瓊臺,東接華林,即靈府長慶元年定室于此。"徐靈府之以"桐柏"而名聞遐邇,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曾有重修桐柏宮的盛舉。宮原系司馬承禎所建,乃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一。徐氏修葺宮觀事畢,曾狀請元稹撰寫碑文。元稹《重修桐柏觀記》云:"歲大和己酉,修桐柏觀訖事,道士徐靈府以其狀乞文于余"。大和己酉為大和三年(829)。歐陽棐、繆葵孫校輯《集古錄目》卷九記載:"《修桐柏宮碑》,浙東團練觀察使、越州刺史元稹撰并書,臺州刺史顏颙篆額。……碑以大和四年四月立。"
杜光庭何以稱徐氏為"桐柏征君"呢?考察這一問題有助于確定《寒山子集》編纂的下限年代。"征君"原指朝廷對著名隱士的征聘,后以之代稱被征聘者。徐靈府被朝廷征聘事在會昌元年(841)。《嘉定赤誠志》卷三十五載:"(靈府)居天臺云蓋峰……會昌初頻招不起。"宋陳葆光《三洞群仙錄》卷六《徐靈府傳》云:"會昌初武宗詔浙東廉使以起之,辭,不復出見廉使,獻言志詩云云。廉使表以衰槁免命。由此絕粒久,凝寂而化。"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四○、《天臺山方外志》卷九記其享年八十二。由此可知徐靈府辭世即在會昌年間,而會昌元年以后既已"絕粒",走近生命的終點,則不當有編集之舉。那么,可以確定會昌元年為編纂《寒山子集》的下限年代。
但上述"下限年代"并不等于實際編集時間。徐靈府《天臺山記》篇末云:"元和十年自衡岳移居臺嶺,定室方瀛,至寶歷初歲已逾再閏。修真之暇,聊采經誥,以述斯記,用彰靈焉。"而前已述及,徐氏正式定居桐柏方瀛是在長慶元年(821)。約三年一閏,"再閏"為五、六年。也正是從長慶元年到寶歷大約六年左右時間徐氏修真之余,采集經誥,多有著述。寶歷元年撰寫的《天臺山記》中未提到寒山,有學者認為編纂《寒山子集》當在其后,誠是。入大和后徐氏的主要活動是修葺宮觀,因此宜將編纂《寒山子集》系于寶歷二年(826)或稍后。考察這一情況,對了解寒山的卒年有重要意義,姑待后論。
三、寒山生卒年探微
對寒山的有生之年,學術界一般認為"逾百歲",其根據是他的自敘詩。如《老病》云:"老病殘年百有余,面黃頭白好山居。布裘擁質隨緣過,豈羨人間巧模樣。"這里"老病殘年百有余"句將生命狀況表述得明白如話。他約三十歲時隱居天臺山,當晚年重經故道時,有詩抒發感慨:"昔日經行處,今復七十年。故人無往來,埋在古冢間"。這首詩實際上也是道其年壽已逾百歲。又,寒山《我見》云:"我見黃河水,凡經幾度清。"拾得《從來》云:"兩人心相似,誰能徇俗情。若問年多少,黃河幾度清。"《事文類聚》前集十六引王子年《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寒、拾用此典故也同樣是暗示享年之永,超乎尋常。寒山"自從出家后,漸得養生趣。伸縮四肢全,勤聽六根具。"體察到他的這種生活狀態,對于他道明的年壽逾百是可以信據的。
在知其享年的前提下,考訂生年和考訂卒年就具有了基本相同的意義。以往學者們都是先推定卒年,然后再前推約百年以確定生年。在這里我們也不妨先梳理一下過去學者們在考訂寒山卒年問題上所依據的材料和一些值得重視的文獻記載:
(一)如前已揭示《太平廣記》卷五十五引《仙傳拾遺》:"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居天臺翠屏山,……十余年忽不復見。"
(二)如前已揭示《祖堂集》卷十六、《宋高僧傳》卷十一等載貞元九年寒山遇靈祐。
(三)清顧沅《吳門表隱》引明姚廣孝《寒山寺記》云:"唐元和中有寒山子者,冠樺布冠,著木履,被藍褸衣,掣風掣顛,笑歌自若,來此縛茅以居。"
(四)元釋念常《歷代佛祖通載》卷十五:"唐丙戌憲宗純改元和……時寒山子者,不知其氏族鄉里,隱于臺州唐興縣寒巖,故父老以寒山子稱之。"
(五)《全唐詩》卷四七四徐凝《送寒巖歸士》:"不掛絲纊衣,歸向寒巖棲。寒巖風雪夜,又過巖前溪。"
以上文獻資料中《仙傳拾遺》關于《寒山子集》編纂的記載史料價值很大。但自"十余年忽不復見"后繼云,咸通十二年時寒山已成仙人,曾對毘陵道士李褐作了一番道德訓戒,"出門乘馬而去,竟不復見。"這已顯然屬于虛構,絕不可憑信。余嘉錫將《仙傳拾遺》說寒山"大歷中隱居天臺翠屏山……十余年忽不復見"與寒山遇溈山事聯系起來,認為"從大歷下數十余年,正當貞元間",而與靈祐與寒、拾相遇事相吻合,未免牽強。另外,姚廣孝在明永樂年間是據何種文獻記載寒山在唐元和時代"縛茅以居"蘇州寒山寺的,目前書證不夠充分(關于寒山與蘇州寒山寺的關系,涉及的問題比較多,容另文對此專門探討)。相比較而言,念常的記載和徐凝的詩稍具體些。念常《通載》的內容雖有參用閭丘序者,且對閭丘胤出守臺州時間亦誤系,但在以時間為序編排"歷代佛祖"時,將寒山次于元和十三年(818)歸寂的惠覺禪師后,或有所憑依。而徐凝在浙東的活動可證于元和至長慶年間。他長慶三年曾赴杭州謁白居易,約長慶四年正月,時元稹在浙東觀察使任,徐與元交游有《奉酬元相公上元》詩,則徐凝送寒山"歸向寒巖棲",亦可能作于元和中至長慶四年(824)正月間。這兩條材料都或隱或顯地說明元和至長慶時寒山尚在世,它對我們了解寒山的生活年代有重要價值,但尚不能成為考訂寒山卒年的炳證。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也有必要換一個角度,從寒山生年入手進行疏證,加以確考。
考索寒山的生年,首先要重視其《少年》一詩:
少年學書劍,叱馭到荊州。
聞伐匈奴盡,婆娑無處游。
歸來翠巖下,席草玩清流。
壯士志未聘,獼猴騎土牛。
這首詩羼入拾得詩中。然拾得乃國清寺僧于天臺山赤城路側領回,在國清寺中長大,并無"少年學書劍,叱馭到荊州"的經歷。而寒山自謂"書劍客",亦曾道"去家一萬里,提劍擊匈奴",故此詩必為寒山所作。荊州,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如《三國志·諸葛亮傳》云:"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那么"聞伐匈奴盡"是指哪一次邊域之戰呢?考唐代自武則天朝至肅宗朝,邊戰雖多,亦時有勝利,但真正能極稱"聞伐匈奴盡"的,只有天寶五載王忠嗣對吐蕃之戰。《舊唐書》卷一○三《王忠嗣傳》云:
(天寶)五年正月,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尋遷鴻臚卿,余如故。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仍授一子五品官。后頻戰青海、積石,皆大克捷。尋又伐吐谷渾于墨離,虜其全國而歸。
此次邊戰大獲全勝,史家大書其事。《資治通鑒》卷二一五稱"虜其全部而歸",《新唐書》卷一三三本傳云"虜則奔破","平其國"。寒山所謂"聞伐匈奴盡"即指大勝吐蕃、吐谷渾,俘獲甚眾,揚威邊域的天寶五載(746)之戰。其后朝廷又組織重兵"連事西討,進收黃河九曲,拔其石堡城"詩中稱"少年",是晚年回憶時的口吻。既叱馭而行,當是成人。如果說依常例已及弱冠方堪赴邊從征,則寒山應生于開元十四年(726)前。這一考定是否能夠成立?下面讓我們進一步考察一下寒山生平的"三十之遷變"。
大約三十歲時,寒山經歷了人生的重大遷變,由家鄉"咸京"(按,當指長安)移往天臺隱居。關于三十歲時的情況,寒山詩中多次述及:
《個是》:個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
年可三十余,曾經四五選。
囊里無青蚨,篋中有黃絹。
行到食店前,不敢暫回面。
《出生》:出生三十年,常游千萬里。
行江青草合,入塞紅塵起。
煉藥空求仙,讀書兼詠史。
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少年》:少年懶讀書,三十業由未。
白首始得官,不過十鄉尉。
不如多種黍,供此伏家費。
打酒詠詩眠,百年期仿佛。
第一首詩人敘述自己早年對功名的熱衷和生活的窘迫。"南院"是唐代吏部用官放榜之處。李肇《國史補》卷下載:"自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留放。"(寒山曾身歷場屋四、五次,且曾通過禮部會試,但在吏部授官前以"身、言、書、判"為內容的考試中卻屢次被放。第二首敘述自己的漫游經歷。"行江青草合"寫南方之行,"入塞紅塵起"則是寫邊塞從征。唐代士子若科舉不第,往往都進入幕府,初、盛時代多向邊庭,以圖建功立業,攝身進級。寒山在科場失意后游幕從征,實屬必然之舉。第三者詩未見載國內各寒山集版本,是一首佚詩。但在今存的日本江戶時代的各箋注本,即寬文十一年(1671)的《首書寒山詩》、寬文十二年(1672)連山交易的《寒山子詩集管解》、元祿十四年(1701)本內以慎的《寒山詩集鈔》、寬保元年(1741)白隱禪師的《寒山詩闡提記聞》和文化十一年(1814)大鼎和尚的《寒山詩索賾》中無一例外地都收錄了這首詩。各本文字有異,當是史源不同,或傳抄有誤。交易和尚等注此詩"檢異本得之。異本者,隋州大洪住山慶預序,并劉覺先跋有之。"此異本與日本其它版本看來并非一個系統,疑徐靈府編纂的《寒山子集》在較早時已傳入日本,這一首詩或即原徐編本中的。徐編本在晚唐時被改頭換面,此詩入道士所編本無妨,但入釋氏所編書,則似乎與色空之旨相去太遠,故刪去。然而它恰恰是了解寒山生平的極其重要的第一手資料。詩云"少年懶讀書,三十業由未",與《個是》、《出生》及其它自述早年生活的敘事詩正相吻合,它再一次表明到約三十歲時,寒山經過四、五次科舉考試仍未第入仕。那么,他為什么會在此時頓生"枕流兼洗耳"的愿望,遠走江南,作出"今日歸寒山"的抉擇呢?除了不登仕版的失意及家庭矛盾以外,必然還有其它背景。要追尋這一背景的話,我們不能不注意到至德一載(756)的"遷移潮"。這是唐代歷史上無法忽視的事件,也是唐代許多士人生活的轉折點。
天寶十四年(755)安、史率所部兵南下進攻中原,次年六月潼關失守,叛軍取西京,玄宗倉惶奔蜀。肅宗至德二載唐軍收復長安,但整個安史之亂卻歷時八年方得平息。這一時期,"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舊唐書》卷一二○《郭子儀傳》)在中原地區這種毀滅性的兵燹中,大批士人避亂南下,"移家避寇逐行舟"(李嘉佑《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書相問》),"欲向山中過一生"(顧況《題明霞臺》)。尤其在"鑾駕避狄"的至德一載(756)形成了一股"移民潮"。如《舊唐書》卷148《權德輿傳》云:"兩京蹂于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穆員《工部尚書鮑防傳》云:"是時中原多故,賢士大夫以三湖五海為家,登會稽者如鱗介之集淵藪。"顧況《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東都序》云:"天寶末,安祿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吳為人海。"此時"關山慘無色,親愛忽驚離"(錢起《鑾駕避狄歲寄別韓云卿》)是普遍現象。當時大批士人南下入山避禍都是隱姓埋名的,以至"老人也欲上山去,上個深山無姓名"(顧況《廬山瀑布歌送李頎》)。因此我們可以確定正是在至德一載(756)或稍后,寒山在"三十業由未"對功名的絕望中,又驚逢安史之亂的兵連禍結,便選擇了南下隱姓埋名,寄跡山中的道路,成為南遷移民中的一員。追步巢許的道路。從此他雖"元非隱逸士",卻永遠"自號山林人"了。從至德一年(756)寒山南遷上推三十年,恰是開元十四年(726),故前考寒山應出生于開元十四年(726)前的結論,與寒山生活中的"三十之遷變"是完全可以印證、相互吻合的。
在考得寒山約出生于726年的前提下,由此再下推百余年,正是寶歷二年(826)。根據前文所考,這也正是徐明府遷居桐柏方瀛"已逾再閏",完成了《天臺山記》的寫作并著手編纂《寒山子集》的時間。因此我們發現徐靈府編《寒山子集》不僅是出于弘揚道教、警勵流俗的目的,也是為了在寒山辭世后,使其詩作得以總成于一帙而不至于散佚不傳。這正為我們確定寶歷二年(826)為寒山的卒年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四、余 論
通過以上考釋,可訂寒山的生活年代約為726年~826年。寒山這漫長的一生大致以三十多年為一階段,共形成生平的三個時期,即咸京生活期、天臺農隱期和寒巖山居期。這三個時期是寒山思想上由儒而道最終入佛的過程。咸京生活期的寒山曾是一個具有強烈入世愿望的儒生,他有過五陵年少般的浪漫和意氣,有過東堂折掛的理想和追求,但三十余歲屢歷場屋而不登仕版。歷史的巨變和個人的遭際形成一般合力,促使他南遷奔越,隱姓埋名,寄跡名山。農隱期間,他雖不無塵累,但亦莊亦陶的生活使他的人生畫卷顯得十分豐富多彩。把卷餐霞,煉藥求仙的修真是他極力在世俗與自我之間設置一道精神屏障。當終于擺脫了一切色身羈絆進入寒巖獨居時,他也走進了國清寺禪僧的世界,在對佛性的體悟中度過了最后的漫長歲月。他雖是一個"編外僧",但因帶著深厚的儒學和道教的修養而修佛,故能表現出一種特殊的禪學智慧,而這種智慧用其特有的詩的語言加以表達,他便超邁于蕓蕓詩僧。寒山,使佛教史拓境生新;寒山詩,更在詩歌史上永遠閃耀著智炬的光華。
附言:本文在修改定稿過程中吸取了臺灣大學羅聯添教授、北京大學葛曉音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趙昌平編審在學術討論會期間提出的可貴意見,在此表示謝忱。
作者:羅 時 進
(蘇州大學中文系 江蘇 蘇州 215006)
| |
版權所有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Copyright©2000
 webmaster@guoxue.com webmaster@guoxue.com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午夜精品免费视频,亚洲区欧美区,久久成人精品视频,成人免费网站观看
91国模大尺度私拍在线视频|
欧美乱妇15p|
国产欧美中文在线|
9l国产精品久久久久麻豆|
亚洲主播在线观看|
精品捆绑美女sm三区|
成人av在线资源网|
日本aⅴ亚洲精品中文乱码|
欧美国产日韩a欧美在线观看|
色综合久久66|
国产一区二区三区最好精华液|
中文字幕不卡一区|
亚洲欧洲国产专区|
欧美本精品男人aⅴ天堂|
日韩欧美国产一区二区三区|
色呦呦国产精品|
欧美性生活大片视频|
fc2成人免费人成在线观看播放|
国产不卡视频在线观看|
美女精品一区二区|
亚洲v精品v日韩v欧美v专区|
国产精品毛片无遮挡高清|
欧美变态凌虐bdsm|
国产欧美日韩另类一区|
日韩一区在线播放|
丝袜诱惑亚洲看片|
亚洲成年人影院|
久久精品国产999大香线蕉|
日韩专区中文字幕一区二区|
激情综合色丁香一区二区|
亚洲四区在线观看|
国产精品毛片久久久久久|
亚洲尤物视频在线|
韩国毛片一区二区三区|
99精品欧美一区|
91小宝寻花一区二区三区|
国产99精品视频|
欧美伦理视频网站|
日本一区二区电影|
日韩不卡一二三区|
日韩中文字幕91|
成人小视频免费在线观看|
高清不卡一二三区|
欧美日韩免费在线视频|
欧美精品三级在线观看|
亚洲国产精品99久久久久久久久|
亚洲国产精品欧美一二99|
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99樱桃|
午夜精品福利在线|
99久久精品免费|
久久久欧美精品sm网站|
国产精品久久久久影院亚瑟|
国产精品第四页|
久久99深爱久久99精品|
欧美日韩精品系列|
欧美成va人片在线观看|
亚洲国产精品久久一线不卡|
高清国产一区二区|
欧美videossexotv100|
天天做天天摸天天爽国产一区|
成人午夜激情在线|
精品国产成人系列|
国产精品短视频|
国产在线不卡一区|
日韩三级视频中文字幕|
欧美韩国日本一区|
国产成人亚洲综合a∨婷婷|
99re热视频这里只精品|
国产日韩亚洲欧美综合|
久久91精品国产91久久小草
|
亚洲国产精品久久久久秋霞影院
|
亚洲免费观看在线视频|
亚洲国产一区二区视频|
色婷婷亚洲精品|
亚洲精品国产无天堂网2021
|
亚洲激情成人在线|
av一二三不卡影片|
日韩毛片高清在线播放|
日本伦理一区二区|
亚洲成av人片在线|
欧美日韩不卡视频|
日本不卡1234视频|
日韩视频免费观看高清完整版|
日韩二区三区四区|
精品久久久久一区|
国产精品一二三|
欧美一区二区三区精品|
最新国产成人在线观看|
99re免费视频精品全部|
亚洲一区二区三区美女|
7777精品伊人久久久大香线蕉超级流畅
|
欧美日韩激情一区二区|
五月婷婷另类国产|
日韩欧美久久一区|
豆国产96在线|亚洲|
中文字幕一区二|
欧美丝袜丝nylons|
日韩成人一区二区|
欧美激情一区三区|
91福利精品视频|
日韩黄色片在线观看|
久久精品网站免费观看|
美脚の诱脚舐め脚责91|
日本一区二区动态图|
欧美性大战久久久久久久|
麻豆中文一区二区|
亚洲欧洲在线观看av|
欧美日韩成人综合在线一区二区|
蜜桃视频在线一区|
成人欧美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网页|
欧美日韩中文字幕一区二区|
国产一区二区精品久久|
一区二区三区在线观看视频|
色综合久久久久网|
美女视频黄免费的久久|
国产精品高潮呻吟|
精品国产污网站|
欧美日韩亚洲综合在线
|
欧美日韩一区二区不卡|
丁香天五香天堂综合|
视频在线在亚洲|
亚洲激情五月婷婷|
国产日韩精品久久久|
日韩一区二区视频在线观看|
91麻豆免费视频|
国产99精品国产|
国产一区欧美二区|
无码av免费一区二区三区试看|
综合中文字幕亚洲|
国产日韩综合av|
精品久久99ma|
欧美精品日韩一本|
在线视频一区二区免费|
蜜桃传媒麻豆第一区在线观看|
日韩码欧中文字|
国产精品免费av|
国产午夜精品美女毛片视频|
日韩精品一区国产麻豆|
欧美乱熟臀69xxxxxx|
欧美日韩三级一区二区|
色国产精品一区在线观看|
99久久精品情趣|
成年人午夜久久久|
高清av一区二区|
成人av电影在线网|
日本少妇一区二区|
成人va在线观看|
午夜精品久久久久久久|
日本欧美大码aⅴ在线播放|
久久国产麻豆精品|
亚洲一区二区在线免费看|
中文av一区二区|
国产精品污污网站在线观看|
久久精品在线观看|
国产欧美精品一区二区色综合|
久久久综合精品|
国产亚洲综合在线|
欧美激情自拍偷拍|
国产精品国产三级国产有无不卡|
国产精品久久久久毛片软件|
亚洲美女免费在线|
亚洲第四色夜色|
毛片基地黄久久久久久天堂|
精品一区二区免费看|
成人黄色av网站在线|
一本色道久久综合亚洲91
|
国产亚洲人成网站|
国产精品女同互慰在线看|
国产精品久久看|
亚洲欧洲三级电影|
香蕉成人伊视频在线观看|
日韩主播视频在线|
国产精品一级片|
97国产精品videossex|
欧美日韩高清一区二区不卡|
欧美一卡二卡三卡四卡|
久久精品亚洲精品国产欧美kt∨
|
激情都市一区二区|
高清不卡一区二区在线|
在线看国产一区|
亚洲精品一区二区三区四区高清|
欧美激情一区二区三区在线|
亚洲成人av电影在线|
久久成人免费网|
99九九99九九九视频精品|
欧美精品一级二级三级|
国产亚洲欧美日韩日本|
亚洲一区二区三区在线看|
蜜臀av性久久久久蜜臀av麻豆|
99热这里都是精品|
日韩一区二区三区四区|
亚洲三级视频在线观看|
国产在线日韩欧美|
欧美三级中文字|
综合分类小说区另类春色亚洲小说欧美|
日韩—二三区免费观看av|
91啦中文在线观看|
国产欧美在线观看一区|
免费成人美女在线观看.|
在线观看三级视频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