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時代,是白話小說百花齊放、異彩紛呈的歲月。此時的白話小說不僅數量浩繁,而且以其輝煌的成就贏得了眾多的讀者,在數千年中國文學殿堂中占據有很重要的位置。通俗小說能夠成為文學的主流,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自誕生那天起,身份就不甚高雅。既無“登高能賦,可為大夫”的堂皇遭際,又不像“詩言志、歌詠言”那樣受圣人青睞。它無“經”可“崇”,也無“圣”可“征”,注定了屬于世俗民間。它的崛起經過一個文學的啟蒙、繼而誕生啟蒙文學的艱苦歷程。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產生了新的城市階級。階級使社會群體重新劃分,群體的價值意識也必然出現不可逆轉的整合。法國著名史學家、批評家丹納把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稱作“精神氣候”,他說:“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精神和風俗概況。”文化是人群在特定條件下生存的表現,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存在的歷史時間和社會空間。超時間、超空間、超人群的文化是不存在的。那么,明清小說建立在怎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上,又是由怎樣的讀者、作者群體介入進而完成形而上的文學活動的呢? 明清時代,是白話小說百花齊放、異彩紛呈的歲月。此時的白話小說不僅數量浩繁,而且以其輝煌的成就贏得了眾多的讀者,在數千年中國文學殿堂中占據有很重要的位置。通俗小說能夠成為文學的主流,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自誕生那天起,身份就不甚高雅。既無“登高能賦,可為大夫”的堂皇遭際,又不像“詩言志、歌詠言”那樣受圣人青睞。它無“經”可“崇”,也無“圣”可“征”,注定了屬于世俗民間。它的崛起經過一個文學的啟蒙、繼而誕生啟蒙文學的艱苦歷程。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產生了新的城市階級。階級使社會群體重新劃分,群體的價值意識也必然出現不可逆轉的整合。法國著名史學家、批評家丹納把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稱作“精神氣候”,他說:“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精神和風俗概況。”文化是人群在特定條件下生存的表現,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存在的歷史時間和社會空間。超時間、超空間、超人群的文化是不存在的。那么,明清小說建立在怎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上,又是由怎樣的讀者、作者群體介入進而完成形而上的文學活動的呢?
假設文學活動是一個整體,那么,它是螺旋式循環的。它由四個環節:世界、作者、作品、讀者所構 成。人類生活的世界不僅是作品反映的對象,也是作者和讀者共同生存的環境;讀者這個群體不僅是閱讀作者的人,而且是與作者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人,雙方通過作品進行潛在的精神溝通;作品是顯示世界的“鏡子”,是作者本質力量對象化的顯現,又是讀者能動接受的對象。本文所論及的側重點在于小說的客體,即作者、讀者群體價值意識的整合。價值觀是社會文化中的最高層次,它表現出某個社會群體在特定環境下經過長期生活實踐所形成的心理積淀和心理定勢。然而,任何價值觀并非亙古不變。社會的進步、文化的更新最終會動搖價值觀的根基。說到底文化的變遷是價值觀的變遷;價值觀的變遷是生產者自身的革命。 成。人類生活的世界不僅是作品反映的對象,也是作者和讀者共同生存的環境;讀者這個群體不僅是閱讀作者的人,而且是與作者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人,雙方通過作品進行潛在的精神溝通;作品是顯示世界的“鏡子”,是作者本質力量對象化的顯現,又是讀者能動接受的對象。本文所論及的側重點在于小說的客體,即作者、讀者群體價值意識的整合。價值觀是社會文化中的最高層次,它表現出某個社會群體在特定環境下經過長期生活實踐所形成的心理積淀和心理定勢。然而,任何價值觀并非亙古不變。社會的進步、文化的更新最終會動搖價值觀的根基。說到底文化的變遷是價值觀的變遷;價值觀的變遷是生產者自身的革命。
白話小說在明清時代的流行代表著一種時尚與群體行為,時尚即一個時期相當多的人對特定的趣味、語言、思想和行為等各種模式和標本的隨從和追求。在中國誰不知道《水滸》、《三國》《西游記》?去瓦舍聽《今古奇觀》、《說岳全傳》;去書肆秘訪《石頭記》抄本,幾乎成了不同人休閑、評世的重要方式!明清文化的變遷,在長長的過渡期群體意識是如何消長的,可概括出若干內容,本文試圖從四個方面加以敘述。
(1)小傳統加強,大傳統弱化
每一個民族文化中都有大傳統和小傳統,我們稱雅和俗,即俗文化和雅文化,有文野之分。一個社會有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有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分野是知識分子和統治階層中流行和傳播的文化;在基本群眾當中和在統治階層中流行的文化。兩種文化風格各異,內容形式不同,也不完全同步,但兩種文化處在同一個社會共同體中,它們之間有一種交流關系,大傳統文化通過各種渠道浸透到民間文化,小傳統文化又通過各種渠道升華為上層文化。小說一詞在漢語中出現最早見于《莊子》雜篇中的《外物篇》,莊子所說的“小說”,是指與“大達”對舉的小道理。東漢時桓譚《新論》中也談到“小說”,但已不是指那種難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理”,而名之各種篇制短小、無法歸類的雜書。一直到班固《漢書·藝文志》提出“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如淳注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小說的定義才與近現代的小說有了某種聯系。《余嘉錫論學雜著·小說家出于稗官說》寫道:“小說家所出之稗官,為指天子之士,即天子為察民之好惡,便使士采傳言于市而謗譽于路,士所傳民語便謂之小說。”可見,無論是“小道理”、“雜書”,還是“稗官”,小說都處于末流而為雅所不賞。它們不能與中國文學的大傳統相提并論。中國文化的大傳統是風騷。“三百篇”被抬上了“經”的寶座,并極力將其俗部分雅化,整理刪定箋注訓詁。騷辭則更是經雅人主體化的產物。從四言為主的雜言,到漢魏五言,詩的形式越來越嚴整,再經過南唐和初唐文人的反復雕琢,以近體律絕為標志,盛唐時已登上了古典詩歌的頂峰。其后的宋詞和元曲,其演進的模式也是強辟蹊徑,反復雕琢的。因而,這種陽春白雪只為文人學士和上層社會所生產和欣賞。它們是中國文學的正宗,其態勢的不斷強化與封建社會儒家文化的群體規范和價值意識相輔相成。
然而,下層民眾也在我行我素地創造著里巷歌謠,南腔北調“下里巴人”。我國最初的白話小說出現在宋代。講史和話本的創作者和欣賞者都是底層文化的大眾。俗文學創作者大多是瓦市、瓦舍或瓦肆的說話人,欣賞者則是市鎮里的那些小商販、官匠、雇匠、店員、船工、苦力以及市井醫生、民間藝人、商女、流氓、貧民等。瓦市的演出是市民群體所喜聞樂見的,因此聚集了大量的聽眾和觀眾。如此竟造就和養活了一支龐大的民間藝人和通俗文藝作者的隊伍;形成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大眾化的市民群體的娛樂方式。他們除了維持溫飽外,在閑暇時只要花費幾文錢就可得到藝術享受,消除生活苦悶,彌補精神空虛,還可間接獲得寶貴的生活經驗。話本雖然不雅,卻成為大多數受眾的精神食糧。以至于連落魄的文人也來問津了,一些“書會先生”長期生活在下層市民當中,受到市民階層思想意識的浸染,成為市民階層的代言人。早期的通俗小說,比如元刊本《全相三國志平話》文筆粗疏簡單,詞不達意,粗具梗概,后來的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等人以自己的“雅”侵染俗文學,使小說文采斐然,面目一新。逐漸雅起來的俗文學蓬勃興旺,任何鄙夷、壓抑和焚毀都被都置之度外,無濟于事。更讓人注目的是征引“演義”的典故入詩入文的事越來越多。風氣所及,文人們自己唱起“下里巴人”來。比如《儒林外史》越出俗文化的范疇,如同“世說”一般,成為雅文化的補充和組成部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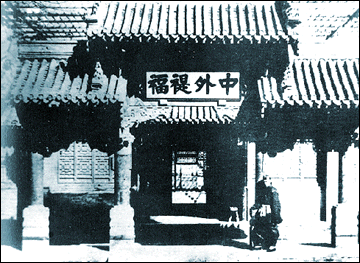
俗形式雅文學的文學格局從社會性來看已不是典型的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它是宋代社會以來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化所帶來的變化。社會群體在群體規范和價值意識方面的變化無疑是深刻的。
(2)真性意識加強,理念意識弱化
宋明之際,隨著儒文化理念的僵化,理教對人的禁錮越來越多。可是,下層意識仍然在不斷覺醒,促使俗文學沖破層層禁錮,茁壯發展起來。被朝廷和地方稱作“壞人心術”的淫詞小說和戲曲傳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浸入上流社會沙龍的。在中國,“文以載道”的思想源遠流長,千年傳統的禮教、倫理在人民的心上形成了堅固、厚重的沉淀,因此,自然本能、合理的欲念與儒家的綱常禮教常常發生激烈的沖突。
宋元話本的作者首先覺醒了。他們熟悉市民生活,飽諳人情事故,他們的作品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以故事來闡發下層社會的人生哲理。他們總體上表現出兩個毫不隱諱,其一,羨慕榮華富貴;其二張揚人性解放。二者一是傾向于物欲;一是傾向于情欲。這與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完全背道而馳。比如通過對個人的肯定,塑造了卓然獨立的平民形象。《史弘肇龍虎君臣會》寫鄭州開笛藝人閻招亮慧眼識人,發現窮困潦倒的軍兵史弘肇有“四鎮令公”之儀,便把妹妹嫁給他,又發現無業游民郭威有“堯眉舜目,禹背湯肩”,“紅光罩頂,紫霧遮身”,非常仰慕,毫不輕慢。后來兩人果然發跡。“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大富大貴的奇跡也會降臨在普通百姓身上。平民百姓們異想天開了,他們的扭扭捏捏少了。觀念上發生了革命。
在宋元話本中流露最多的是肯定血肉之軀。擬話本有許多作品不光寫愛情,而且寫情欲,寫以生理為基礎的性愛。比如《張生彩鸞燈傳》、《張舜美燈宵得麗女》寫越州人張舜美上元觀燈,與少女劉素香私自相愛,遂私奔同居,表現出市民對私通、艷遇的興趣。整個社會對人性人欲似乎更寬容、開放。其實,桑間濮上的兩性關系文人學士也未必不感興趣,但是他們囿于“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傳統思想,不敢作淋漓盡致的描寫。對于女子違背封建禮教的舉動,更不敢表現出支持甚或歌頌。
這一創作傾向的巨大變化表達了市民階層朦朧的民主要求,并開創了人情小說的傳統。使中國文壇得以產生《金瓶梅》、《紅樓夢》這樣的巨著。
(3)群體意識的加強,個體意識的弱化
魯迅把宋元話本的出現稱作“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變遷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文學的大眾化,大眾化的文學藝術必定是產業化的,在供求關系上是“市場經濟”。創作文體必須迎合接受主體,才能爭取消費者、創造經濟效益。這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供求關系,它不同于藝術為宮庭、官署或貴族士大夫家的演出,對象是有一定消費能力的廣大市民群眾,性質純粹是營業。既然作者、演出者、消費者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經濟聯系,為了體現商業原則,市民文學作品必須是通俗、有趣并具有娛樂功能的。如此,作者作為一種新型文化消費的創作群體,必須弱化自我表現的個體意識;服從于聽眾需求的群體意識。
群體意識表現在作品的內容上,當然要表達市民群眾大多數人都感興趣的群體情趣,諸如對人情世俗的 玩味,對風流艷遇的企望,對達官貴人的仰幕,對實用主義的崇拜……同時,表現在形式上,與知識分子文學唐宋傳奇不同,話本語言不能是典雅的文言而必須是通俗生動的白話。當時的民眾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即使是都市里的商人所具有的書寫和運算能力,掌握的人也不多。要使市民能聽懂說話人的故事,話本必須是通俗的、“婦孺能解”的。話本、擬話本的結構形式吸收了唐變文的特點,由入話、頭回、正話、篇尾四個部分組成,處處為了方便聽眾接受而精心設計。這種結構程式是凝固的、公共的,甚至是媚俗的,根本沒有作者個人為表現自己的思想與情懷,為了內容的需要而創造的新的結構形式的空間。于是,作者個人意識不得不弱化到最低限度并聽從于、服務于聽眾的群體意識。 玩味,對風流艷遇的企望,對達官貴人的仰幕,對實用主義的崇拜……同時,表現在形式上,與知識分子文學唐宋傳奇不同,話本語言不能是典雅的文言而必須是通俗生動的白話。當時的民眾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即使是都市里的商人所具有的書寫和運算能力,掌握的人也不多。要使市民能聽懂說話人的故事,話本必須是通俗的、“婦孺能解”的。話本、擬話本的結構形式吸收了唐變文的特點,由入話、頭回、正話、篇尾四個部分組成,處處為了方便聽眾接受而精心設計。這種結構程式是凝固的、公共的,甚至是媚俗的,根本沒有作者個人為表現自己的思想與情懷,為了內容的需要而創造的新的結構形式的空間。于是,作者個人意識不得不弱化到最低限度并聽從于、服務于聽眾的群體意識。
(4)近距離觀照加強,遠距離寄托弱化
從社會意義上看,明清小說作者、讀者的群體價值意識還表現在更加貼近生活。寫實主義的興起,縮短了小說與生活的距離,并帶來了創作方法的根本性轉變。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說:“中國人從來都把自己看作最卑賤的,自信生下來是專給皇帝拉車的。”從民族心理和價值觀念來看,我國古代歷來有歷史崇拜的習慣。在原始共產社會,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權力之爭,倫理道德上是一種原始的崇高風范。奴隸社會初期,統治者比封建社會顯得寬厚仁慈。我國民族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孔子以“信而好古”作為自己的原則。他把文、武、周時代稱為“小康”,把更遙遠的堯舜時代稱為“大同”,表示要“祖述堯舜,憲章文化”。自孔子之后,崇拜歷史便成為漢民族的一種社會心理。以古圣人為楷模塑造自己成了社會改制、重建社會的標準。凡文人雅士作文的永恒題材就是崇拜古人,侈談古事。《東京夢華錄》中所記載的北宋說話的五個科目中“講史”、“說汾”、“五代史”,三個科目都是講歷史故事的。《都城紀勝》中所記載的南宋說話中的“四家”其中有兩家講史。“說鐵騎兒”、“說經”中也有許多話本的內容發端于歷史。圣人、英雄的故事象磁鐵一樣引人們的情感共鳴。這便是中國人生存狀態、覺醒程度和心理需求的定勢。
西方現代小說家享利·詹姆斯認為:“小說生存的唯一理由是力圖再現生活。”百姓們憧憬能在圣君賢相的統治下出現一個世道公正、安居樂業的清平世界,反映了百姓對君主的依賴。但是封建社會皇帝昏昧、奸臣弄權、土豪橫行、兵燹連綿,一而再,再而三打破了百姓們的迷夢。由真命天子君臨天下的太平盛世,由賢相忠臣締造維持的公正世界,從永恒的理想變成了可望不可及的鏡花水月。在這種情況下,君權思想的強大牢籠,再也鎖不住近代民主主義的曙光。從宋元話本開始,白話小說顯示出現實主義的某些端倪,其內容漸次全轉換到百姓們的日常生活。白話小說的創作思維的定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標志著作家覺醒的代表作品是《金瓶梅》。
《金瓶梅》是源自近距離生活的所得所感而創作的。它托言于宋代,其實寫的都是十六世紀后期的社會生活。它毫不客氣將《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中籠罩在人物、事件上的理想主義一掃而空,代之而起的是對世俗人生毫發不爽的真實描寫。自此,中國白話小說的主流便沿著寫實主義的道路坎坷向前,一路西去。
《紅樓夢》繼承了《金瓶梅》的傳統,并且在思想藝術上大大超過了它,這是人所共知的。《儒林外史》則把寫實主義的方法發展到近代的現實主義。它的意義在于不僅寫世態人情,而且摒棄了《金瓶梅》對低級的自然主義描寫。它消毒了市民階層的低級情趣,提純了愛情,貫注全書的是對知識分子畸變靈魂和由這些知識分子所支撐的封建政治腐敗因素的批判,充滿了嚴肅深沉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近代寫實主義作品的成熟對封建社會全部上層建筑是深刻的反思和改造。從啟蒙文學到文學啟蒙,中國人文主義的曙光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