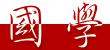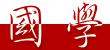|
���g�����L(zh��ng)���m(x��)��
�I(y��)���˽ӹ��ˡ�
ǧ�d�|������ˮ��
������ӿ���ڽ�
�������S����ͧ���иС������m��������֮һ��
һ
�@�����������f���^(gu��)�ĵھł�(g��)�����ˡ�
���Ϸ��������ͬ�W(xu��)��ǰ�́�(l��i)��һ����(sh��)�������^Ԋ(sh��)�W(xu��)�����賓�����Փ�����@�������˔�(sh��)��r(sh��)�g���g����(l��i)��һ�����W(xu��)��Փ��(sh��)�������������K���W(xu��)�����^���y(t��ng)�о����ġ����μs�����~��˹��������ڡ���һ�ۿ����@����(sh��)����ֱ�X(ju��)��ϲ�g������Gɫ�ķ����ϣ�һλ��˹����ʷԊ(sh��)�����������ݳ����Ϙ�(sh��)���nj�����־�� (t��ng)�����ЋD�桢�r(n��ng)�C�ˡ����mȻ�@ֻ��һ���ͮ�(hu��)�������ע�����F(xi��n)����ؐ�����R�µ�һ�Ҳ����^�������sһ�������ҵ��������Ї�(gu��)�ж�����ƵĈ�(ch��ng)�����������oֹ���L(f��ng)��(hu��)�棬�����r���ʷԊ(sh��)�ݳ����(d��ng)��
��ʲô�@����Ҫ���ἰ�@���g���أ�һ����?y��n)����ij�����҂������W(xu��)�о�����(l��i)��һ��(g��)�µ�ҕҰ�����^�����賓�����Փ���ַQ�����^��ʽ��Փ�����������ڄ����^(gu��)ȥ��20���o(j��)�аl(f��)չ����(l��i)���������W(xu��)�W(xu��)��֮һ��1997�����죬���߸�������ڳ����ͬ�W(xu��)����ͬ��ȥ��(n��i)�ɹſ��죬��;��(j��ng)�����r(sh��)�����ڱ�Ԣ�c��Մ���^(gu��)ԓ�W(xu��)�ɂ�(c��)���о�ʷԊ(sh��)�������^Ԋ(sh��)�����Փ�c����Փ�����ԣ�Ҋ(ji��n)�����@����(d��o)Փ�Ե������K�ڳ��������g�����������������ԭ����������҂���ʮ����Ϥ�İ��m������˹�����������W(xu��)�W(xu��)����Ҳ�Qԓ���ǡ����I(l��ng)���Ѕ�����(sh��)�ĵ䷶����������Ҳ�܉�?q��)��҇?gu��)���W(xu��)���������档�������ڳ����ͬ�W(xu��)���@����(g��)�ˌ������}�顶�ڂ�ʷԊ(sh��)Ԋ(sh��)�W(xu��)��ȽƤ�ա�������ʽ�䷨�о��������ǻ��ڱ�����ʷԊ(sh��)���y(t��ng)���Ă�(g��)���о����֣������{�ͽ��b�@һ��Փ�Ĺ���ԭ�t�������ģ�͵Ļ��A(ch��)�ϣ��ڽ���5����ɵ�һƪ��(y��u)�㲩ʿ�W(xu��)λՓ�ġ����g������������Ȼ؞ͨ�������˵ČW(xu��)�g(sh��)˼�������в����Լ���(d��)���Ą�(chu��ng)Ҋ(ji��n)�����x���@��������Ҫ�f(shu��)�ġ�
��1953���𣬱���������W(xu��)����ϵ��m(x��)���B(y��ng)�˔�(sh��)ʮ���Tʿ����ʿ�о����������ѽ�(j��ng)��(g��u)�����҂��������W(xu��)����һ����Ҫ���о��ߡ��e��90��������ԁ�(l��i)���յ�һ����ʿ�о����������80������I(y��)�ڲ�ͬ�W(xu��)�ƵĴTʿ������?c��)ڸ��ԵĿ��кͽ̌W(xu��)��λ�϶���һ�����^�ČW(xu��)�g(sh��)�e�ۣ��o(w��)Փ���ΌW(xu��)��·��֪�R(sh��)�Y(ji��)��(g��u)�����БB(t��i)�ȡ���Փ�^��Լ��W(xu��)�g(sh��)ּȤ�ȷ��棬���c����У�T(m��n)��У�T(m��n)�����о����������@�IJ�ͬ�����@Щ��ͬ�o�҂����W(xu��)���I(y��)�Ľ̌W(xu��)���˲����B(y��ng)����(l��i)���µĚ���Ҳʹ�҂��@�T(m��n)�W(xu��)�Ƶ��(du��)�齨�O(sh��)�����@¶��һ�N�µİl(f��)չǰ����
�����ͬ�W(xu��)���������е�һ�T������1986���ڃ�(n��i)�ɹŴ�W(xu��)�@���ČW(xu��)�Tʿ�W(xu��)λ���{(di��o)���Ї�(gu��)���(hu��)�ƌW(xu��)Ժ�ٔ�(sh��)�����ČW(xu��)�о������ڡ������ČW(xu��)�о�����(d��n)�ξ���������(sh��)����D(zhu��n)����(d��ng)���ČW(xu��)����Փ�о��ң��_(k��i)ʼ���T(m��n)���������ČW(xu��)����Փ�о����Ǖr(sh��)���㌦(du��)ʷԊ(sh��)�о��l(f��)�����dȤ��1995�������g���������˷��m���������W(xu��)�߽M�����e�k�����ڸ�(j��)���ް࣬��ʷԊ(sh��)����С�M�������ܵ�ӑՓ�������L��(w��n)�W(xu��)�ߵ�����ǰ������(gu��)�����W(xu��)������һ�ꡣ��������{���Լ��^�õ�Ӣ�Ĺ��ף��V�������ˮ�(d��ng)�����^���y(t��ng)�о��I(l��ng)������r֪�R(sh��)���M(j��n)�����W(xu��)�g(sh��)�����D(zhu��n)����ʷԊ(sh��)����Ұ���I(y��)����Փ�о����档�@һ���D(zhu��n)܉���������ڹ�����ʮ?d��ng)?sh��)��֮�����ص��x�������W(xu��)���I(y��)�Գ䌍(sh��)���{(di��o)���Լ���֪�R(sh��)�ܘ�(g��u)�����ڌ�(du��)�Ї�(gu��)ʷԊ(sh��)�о�������Փ��̽������Ҫ���ɰɡ�
1997��9�£������ͬ�W(xu��)�ԃ�(y��u)���ijɿ�(j��)���뱱��������W(xu��)���W(xu��)���I(y��)���x��ʿ�W(xu��)λ���Ǖr(sh��)�������f(shu��)�ѽ�(j��ng)��һ��(g��)���^���졢��(w��n)���ČW(xu��)���ˡ�����У���g����߀��Ҫ���Լ����W(xu��)�ٌ�(xi��)��֔(j��n)�����£��И�W(xu��)֮�L(f��ng)�����n���n�£����p�ײ�ƈ��Ц��һ���_(k��i)�ڣ�����������І��l(f��)�ԵĆ�(w��n)�}������(d��ng)���ȥ˼����ӛ��1998��Ŀ���֮�H���҂������ҵĎ�λ�ώ���96-97��(j��)�IJ�ʿ�о���һ��������һ�ܶ࣬��(du��)�������У�̲ĵġ����W(xu��)��Փ���M(j��n)�����Č�ӆ�������ͬ�W(xu��)Ҳ�������@�(xi��ng)���������T���y�c(di��n)��(w��n)�}��ӑՓ�У��_��(sh��)����(y��ng)����֪�R(sh��)�Y(ji��)��(g��u)�^��ȫ�棬�������J������Ŀ����ͽ��hҲ��������Ҫ�������Լ���Ҋ(ji��n)�⡣
����ǰ�����죬��Ҳ���������f�^��{���������ͬ�W(xu��)�R�r(sh��)��(l��i)����Сס�˃��졣�҂����������l(f��)����һƪ�P(gu��n)���ٔ�(sh��)�����ČW(xu��)�W(xu��)�ƽ��O(sh��)��Փ��Մ���S���Ԓ�}��Ȼ�D(zhu��n)����������Ҫ�_(k��i)�}�IJ�ʿ�W(xu��)λՓ�ĵ��O(sh��)Ӌ(j��)�ρ�(l��i)����(d��ng)�r(sh��)�������ɹ�ʷԊ(sh��)�о����ı���͡���ʽ���L(f��ng)���ֆ�(w��n)�}����Ұ���I(y��)��(w��n)�}����һՄ�����Լ����뷨�����Բ����䏈���f(shu��)�������电(sh��)���䡢������һ��ֱꐺ��hՓ�У�����Ҋ(ji��n)����˼�������䣬ҕҰ���_(k��i)韺������Y�ϵ��S���茍(sh��)��ͬ�r(sh��)����������������(du��)�Ї�(gu��)ʷԊ(sh��)�о���ijЩ˼������������ĕr(sh��)�g��҂���Ԓ�}ʼ�K���@��ʷԊ(sh��)��Մ�d������������Ͷ�ϣ����X(ju��)�������D(zhu��n)��ͨ�^(gu��)�@һ���挦(du��)���ӑՓ�������O(sh��)���Ďׂ�(g��)��(w��n)�}�У���������˲�ʿ�W(xu��)λՓ�ĵ���������һ���棬Ҫ�����ڱ����Ļ����y(t��ng)ȥ̽�����O(sh��)�Ї�(gu��)ʷԊ(sh��)�W(xu��)��һЩ������Փ��(w��n)�}����һ���棬Ҫ�ڷ���Փ�χLԇ������(d��o)һ�N���Y�����Č�(sh��)�C�о���ͨ�^(gu��)��(g��)��������֧�δ���ȵ���Փ̽�����@Ҳ�Ǻ��(l��i)������(xi��)���ľ��w�^(gu��)���У��҂��ֽY(ji��)��Փ�ĵ��M(j��n)չ��δ�ϥ�L(zh��ng)Մ��һ��(g��)��ҪԒ�}�������f(shu��)���@�ɷ���ČW(xu��)�g(sh��)���ԣ�ͨ�^(gu��)�����ͬ�W(xu��)�����(x��)��Փ�C�ͷ������ɹ����w�F(xi��n)���@�����������Č�����
���粩ʿՓ�Ĵ��qί�T��(hu��)�Ŀ��u(p��ng)�Z(y��)���f(shu��)���ǘӣ������ͬ�W(xu��)���@�����������ɹ�ʷԊ(sh��)���о��к��Є�(chu��ng)Ҋ(ji��n)��һƪ��ʿ�W(xu��)λՓ�ġ��������ɹ�����С�����W(xu��)�ߣ������ɡ��h��Ӣ���Z(y��)�����֣��x���n�}�����ஔ(d��ng)?sh��)ă?y��u)��(sh��)��Փ���@ʾ�����ߌ�(du��)��(gu��)��ʷԊ(sh��)�о����³ɹ��D�D���^��ʽ��Փ������־Ԋ(sh��)�W(xu��)���ͱ�����Փ�ȶ����^��Ϥ�������������գ���(du��)�������ʷԊ(sh��)���y(t��ng)�����P(gu��n)�W(xu��)�g(sh��)ʷҲ�^���˽⣻��(j��ng)�^(gu��)��Ұ�{(di��o)�飬�֫@�����µ���Փ˼�����ڴ˻��A(ch��)�ϣ����ߌ�(du��)������(gu��)��(n��i)ʷԊ(sh��)�W(xu��)��ʷԊ(sh��)�܌W(xu��)��һЩ��(w��n)�}�M(j��n)�������w���죬������S����(g��)�˄�(chu��ng)Ҋ(ji��n)����һ���棬���������ɹŸ���ȽƤ���ݳ��ġ������邀(g��)�����ڇ�(gu��)��(n��i)�״��\(y��n)�ÿ��^��ʽ��Փ����(du��)�@��(g��)���g�������~�Z(y��)��Ƭ�Z(y��)�������ʽ�;䷨�M(j��n)��������(sh��)���ܵ��о�����һ���C��(sh��)�����ɹ�ʷԊ(sh��)�д_��(sh��)���ڡ���ʽ�䷨���ĬF(xi��n)��߀���ɹ�ʷԊ(sh��)�ġ���ʽ�䷨���͡��Z(y��)���������Z(y��)���P(gu��n)ϵ��������Ѓr(ji��)ֵ�ĿƌW(xu��)��Ҋ(ji��n)���@��(du��)�������ھ��҇�(gu��)��ʷԊ(sh��)�Ļ��z�a(ch��n)��һ�N�W(xu��)�g(sh��)ؕ�I(xi��n)��ͬ�r(sh��)��(du��)��������������ɹ�����Ļ���λҲ�ЬF(xi��n)��(sh��)���á�����
��
����Փ�ĵ��о����E�����P(gu��n)����Ұ���I(y��)���@��Ͳ����f(shu��)�ˣ����dȤ���x�߿��Կ�������(sh��)�ĸ�䛺ͺ�ӛ��������ģ������аl(f��)�F(xi��n)�@һ�����Ĵ_���@Щ�P(gu��n)(li��n)�о��И�(sh��)�����^���(y��n)֔(j��n)?sh��)ČW(xu��)�g(sh��)Ҏ(gu��)�����@�����Y(ji��)���Ҍ�(du��)�Ї�(gu��)ʷԊ(sh��)�о��Ď��c(di��n)�뷨����(l��i)Մ?w��)��@�(xi��ng)�о��ČW(xu��)�g(sh��)�r(ji��)ֵ����Փ���x��Ŭ������
���ȣ���Փ�ĵ��x�}����Փ̽���f(shu��)�f(shu��)�Ї�(gu��)ʷԊ(sh��)�о����D(zhu��n)�͆�(w��n)�}�� ���Ї�(gu��)���ƌW(xu��)���x�ϵ����W(xu��)�о�������80����Ěvʷ������һ�����۵İl(f��)չ�M(j��n)���У�����Ը��{�W(xu��)�\(y��n)��(d��ng)�������^֮�����g��ˇ�W(xu��)�����}���M(j��n)���U(ku��)��������(g��)�����Ļ����@���Ї�(gu��)���W(xu��)���^(gu��)������v�̡��������ˇ���W(xu��)����һ��(g��)֧�W(xu��)��һֱ������Ҫ�ăɂ�(g��)�l(f��)չ����һ������һ������ׁ�(l��i)�����о���������������ˇ�W(xu��)��˼����^�c(di��n)�������@һ֧�W(xu��)����Փ̽���У�����(du��)�ڸ��{�W(xu��)����Ԓ�W(xu��)�����W(xu��)�İl(f��)չ���ԣ��Ї�(gu��)ʷԊ(sh��)�W(xu��)���о��t���^�����@��Ҳ���T��Ěvʷ�����c���^�l�������ơ�
20���o(j��)50����Ժ�������80����Ժ��Ї�(gu��)�ٔ�(sh��)����ʷԊ(sh��)�İl(f��)���Ѽ���ӛ䛡������ͳ��棬���H�g���˺ڸ����µ�����Փ�ࣺ�Ї�(gu��)�](m��i)������ʷԊ(sh��)��Ҳ�ش��������Ժ��Ї�(gu��)�W(xu��)������(j��ng)���F(xi��n)�^(gu��)һ��(g��)�����˵Ć�(w��n)�}�����Ǿ��ǡ��҂�?c��)��?l��i)�Ƿ�Ҳ��ʷԊ(sh��)������һ�ࡶ���cԊ(sh��)�������ң����Դ�������(sh��)���q���C��(sh��)���ږ|���@һ���χ�(gu��)�ȵı�����Ⱥ�У�������������(sh��)��Ӌ(j��)��ʷԊ(sh��)���v؞�Ї�(gu��)�ϱ�����^(q��)�����N(y��n)�����dz��긻�������Dz�����ɹ���ġ����_��˹���������ɹ���ġ������Ϳ�?t��ng)�������ġ����{˹���ѽ�(j��ng)�ɞ���u(y��)����ġ��Ї�(gu��)����Ӣ��ʷԊ(sh��)�������⣬���Ї�(gu��)��������̩�Z(y��)ϵ���ɹ��Z(y��)�������ͻ���Z(y��)�������У�����߀��������(sh��)�ٲ�Ӣ��ʷԊ(sh��)�����Ϸ��ı���������ͬ��Ҳ�������L(f��ng)��Ř�Ą�(chu��ng)��ʷԊ(sh��)���w��ʷԊ(sh��)��Ӣ��ʷԊ(sh��)���@Щ�ֵ������������m(x��)�Ŀڂ�ʷԊ(sh��)���R�۳���һ�����貵��ČW(xu��)����(k��)���������Ļ�ʷ��Ҳ��(sh��)�ٺ�Ҋ(ji��n)�����T���緶����(n��i)���S����(gu��)�ҁ�(l��i)�ø����S����ʣ�Ҳ��ֵ���Ї�(gu��)���Ժ��ľ���ؔ(c��i)����
�҇�(gu��)ʷԊ(sh��)������ӛ䛺ͳ��棬���Y�όW(xu��)����ȡ����ǰ��δ�еijɿ�(j��)����(d��ng)Ȼ���ĿƌW(xu��)�汾�ĽǶȁ�(l��i)����Ҳ�������@�ӻ��ǘӵĆ�(w��n)�}���M����ˣ��@����Ĺ����Ǒ�(y��ng)ԓ���Կ϶��ġ����磬����������ʷԊ(sh��)��ÿ����Ҏ(gu��)ģ����20�f(w��n)�����ϣ����в���ġ����_������Ŀǰ��֪�����������L(zh��ng)��ʷԊ(sh��)���s��120�ಿ��ɢ퍼��У��_(d��)1000���f(w��n)�֡����磬�����ֹ���ڇ�(gu��)��(n��i)��l(f��)�F(xi��n)���Բ�ͬ��ʽӛ���(l��i)���ɹ��Z(y��)��Ӣ��ʷԊ(sh��)����(sh��)�����^(gu��)350�N����������֮һ�ѽ�(j��ng)���档�@ЩԊ(sh��)���̄t�װ�����ǧ�У��L(zh��ng)�t�_(d��)ʮ���f(w��n)�С��������f(shu��)����ͬ���ֵĸ��N���ģ�Ҳ�ڱ���m(x��)ӛ���(l��i)���@�������ӵij̶����S�����Ї�(gu��)ʷԊ(sh��)�İٻ��@��
���@��ϲ�˵��΄�(sh��)�£�ʷԊ(sh��)�о��_��(sh��)��(y��ng)ԓ�M(j��n)��һ��(g��)���µ��D(zhu��n)�͕r(sh��)���ˡ����^�D(zhu��n)�ͣ����J(r��n)������Ҫ�ģ��nj�(du��)�ѽ�(j��ng)�Ѽ����ĸ��NʷԊ(sh��)�ı����ɻ��A(ch��)���Y�υR�����D(zhu��n)���ČW(xu��)��(sh��)�ĿƌW(xu��)������Ҳ���������^����µ����w�ղ顢ռ���Y�϶�����^�vʷ�е�ʷԊ(sh��)���y(t��ng)��߀ԭ�c̽�����@�����ҏij����ͬ�W(xu��)���@���������ܵ��Ć��l(f��)֮һ��Ҳ������ʷԊ(sh��)�ı��綨�з�ӳ���о��^���ϵ�һ���S�M(j��n)�����J(r��n)�飬���g�ČW(xu��)���Ѽ����������ЃɷN�B(t��i)�ȣ�һ�N�ǿƌW(xu��)�đB(t��i)�ȣ���Ҫᘌ�(du��)�W(xu��)�g(sh��)�Ե�̽ӑ���о�����һ�N���ČW(xu��)�đB(t��i)�ȣ�ᘌ�(du��)֪�R(sh��)�Ե��ռ��ͽ�����ǰЩ�꣬�҂����g��ˇ�W(xu��)��һֱ�ڏ�(qi��ng)�{(di��o)���ƌW(xu��)�汾������ϧ��̖(h��o)�mȻ�����ӑՓ��δ��������Փ���x�ρ�(l��i)���Ծ��wչ�_(k��i)���T���҂�һֱ�������ĵġ��Ҍ�(sh��)ӛ䛡����������ӹ����������f���¡��Ȇ�(w��n)�}��Ҳ��δ�õ������Ľ�Q��
�����ͬ�W(xu��)���о���(sh��)�`���_�ػش����@Щ��(w��n)�}���Ǿ������g�ڂ�ʷԊ(sh��)���о�����(y��ng)��(d��ng)ע����e�ı��Č��ԣ����ı������Ļ�����λ�����Ǻ�(ji��n)�����е�һ��(g��)��(g��)���ģ����Ǿ��w�����е�һ�δ��ݳ��ĿƌW(xu��)��������@�Ͳ��Ǹ��N���Ľ�(j��ng)�����ӹ���ąR��������ʷԊ(sh��)�ݳ����y(t��ng)���ЙC(j��)���(d��ng)ϵ�У�����һλ����(du��)ijһԊ(sh��)�µ�һ���ݳ�����ͬ����(du��)ͬһԊ(sh��)�µ�һ�δ��ݳ���Ԋ(sh��)��֮�g���P(gu��n)ϵ������Ⱥ�w���γ��c��ɢ����(g��)�w�L(f��ng)���׃�����ݳ����y(t��ng)���d��˥���c���D(zhu��n)�ȵȡ��@֮�У����^Ԋ(sh��)�W(xu��)���ı���Փ�����ς�(g��)���o(j��)����ʷԊ(sh��)�I(l��ng)�����ɫ�ijɿ�(j��)֮һ�������ͬ�W(xu��)��Փ���x�}��λ��ڂ�ʷԊ(sh��)Ԋ(sh��)�W(xu��)��ͨ�^(gu��)������ȽƤ���ݳ���һ��(g��)ʷԊ(sh��)Ԋ(sh��)���M(j��n)�Ђ�(g��)�����ı��������ٻؚw����Փ����Ŀ��Y(ji��)�����@Щ���棬�������ஔ(d��ng)?sh��)Ĺ��?du��)ʷԊ(sh��)������ʮ�֏�(f��)�s���ı���r���˳���������������������ʹ�˶�Ŀһ�¡����⣬�����ı����Խ綨ʷԊ(sh��)�о��ĿƌW(xu��)��(du��)���֏��ı��g����P(gu��n)(li��n)���ĸ���Ӵ����f(shu��)���ˡ��������顰ʷԊ(sh��)��Ⱥ�����ڔ��½Y(ji��)��(g��u)�γ��ϵă�(n��i)�ڙC(j��)�ƣ��ɴ˘�(g��u)�����l(w��i)�����ɹ�ʷԊ(sh��)���y(t��ng)���ı��ΑB(t��i)���@Ҳ�ǰl(f��)ǰ��֮��δ�l(f��)�ģ���(du��)���g�ČW(xu��)��������ʽ���ı��о���Ҳ��ͬ�ӵą��Ճr(ji��)ֵ�����磬Ԫ�������ͺ��(l��i)��С�f(shu��)�ЏV��ʹ�õ�
�����ġ����ڡ�����Մ䛡�С�f(shu��)�_(k��i)�١��С��f(shu��)��ʰ�����а��f(w��n)�ס������硶���������z�¡��cС�f(shu��)��ˮ�G����֮�g���ı���(li��n)�ϵ��P(gu��n)ϵ���e��Ԓ��С�f(shu��)���о����ҿ�Ҳ�����ԏ��@һ��Փ���ı��^�еõ�ijЩ���l(f��)��
��Σ��ٿ���Փ�о����D(zhu��n)�͡�
����6���ҵ��Ї�(gu��)���(hu��)�ƌW(xu��)Ժ�������ٔ�(sh��)�����ČW(xu��)�о����e�еġ��Ї�(gu��)ʷԊ(sh��)���о�����(sh��)���l(f��)����(hu��)��Ҳ�v��Ԓ���@�ׅ���(sh��)�ه�(gu��)�ҡ����塱������c(di��n)�(xi��ng)Ŀ���Ї�(gu��)�ٔ�(sh��)����ʷԊ(sh��)�о�������Ҫ�漰����������ʷԊ(sh��)���Ϸ�ʷԊ(sh��)������ԓ����(sh��)��ǰ�����f(shu��)���@Щ�ɹ��^ȫ��ϵ�y(t��ng)��Փ�����Ї�(gu��)ʷԊ(sh��)�Ŀ��w��ò�����c(di��n)ʷԊ(sh��)�ı�����Ҫ�ݳ�ˇ�ˣ��Լ�ʷԊ(sh��)�о��е�һЩ��Ҫ��(w��n)�}����ӳ���҇�(gu��)����ʮ���(l��i)ʷԊ(sh��)�о�����ˮƽ���³ɾͣ����ٴ�����˄�(chu��ng)���Ї�(gu��)ʷԊ(sh��)��Փ�wϵ�Ĺ���Ŀ��(bi��o)���@�����˱�����^�ġ������f(shu��)���@�ׅ���(sh��)���ǏĿ��w���w�F(xi��n)�����@һ�r(sh��)���ČW(xu��)�g(sh��)�L(f��ng)ò��
ʷԊ(sh��)�о�Ҫ����Ȱl(f��)��Ҫ������ʷԊ(sh��)��(n��i)���l(f��)չҎ(gu��)�ɵ���Փ̽���@�N̽���Dz��ܹ����M(j��n)�еģ�Ҳ�����܌���Փ��B������ȱ�ٸ�����ɳ���ϡ���(d��ng)ǰ�Ї�(gu��)ʷԊ(sh��)�о����˶���չ�_(k��i)�����룬�o(w��)Փ��ʷԊ(sh��)���ղ��c�l(f��)���ı����Ѽ��c���������ֵ�ۙ�c�{(di��o)�飬ʷԊ(sh��)��͵Ŀ����c���֣����������P(gu��n)�n�}�Č��T(m��n)��Փ������ȡ���˿�ϲ�ijɿ�(j��)���ʬF(xi��n)�����õĄ�(sh��)�^���e�DZ������(gu��)�Ҽ�(j��)���c(di��n)�о��(xi��ng)Ŀ�ġ��Ї�(gu��)ʷԊ(sh��)�о�������(sh��)�������������҇�(gu��)ʷԊ(sh��)��Փ�Ľ��O(sh��)��(chu��ng)���˱�Ҫ��ǰ�ᡣ�����ֹ���҂��_��(sh��)���Y�όW(xu��)�ďV������ijЩ���}����ӑ�������ஔ(d��ng)?sh��)ķe�ۣ���ͬ�r(sh��)����Փ�ϵ����w̽��߀����ϵ�y(t��ng)�����룬��ǡǡ�����@��҂��ǿ����^�m(x��)���ɿ�(j��)�ġ���������?y��n)��҂��@������ʮ���(l��i)������������Ҫ�ŵ����Ѽ���ӛ䛡������ͳ���Ȼ��A(ch��)�h(hu��n)��(ji��)���棬�о�����Ҳ�^��ؼ����ھ��w��Ʒ�Č����ϣ���ȱ�ٿv��M���(li��n)ϵ�c��ͨ��˼�����@����������Փ�о���ҕҰ������҂���(du��)�Ї�(gu��)ʷԊ(sh��)���^���ώ��С�Ҋ(ji��n)ľ��Ҋ(ji��n)�֡���ȱ�ݡ�����׃�@�N��r������(hu��)�t������(g��)�Ї�(gu��)ʷԊ(sh��)�W(xu��)�ČW(xu��)�ƽ��O(sh��)������
�F(xi��n)�ڿ����f(shu��)���҂��ѽ�(j��ng)��������Փ���O(sh��)�ό�(sh��)�F(xi��n)�D(zhu��n)�͵ĕr(sh��)���ˣ���?y��n)�r(sh��)�C(j��)�ѽ�(j��ng)�����ˣ�
����21���o(j��)�Ľ��죬�҂�?c��)��Ӳ������M(j��n)�Ї�(gu��)ʷԊ(sh��)�W(xu��)�Ľ��O(sh��)�أ������^�m(x��)�V����������_(k��i)չ���(xi��ng)���}���о��⣬���X(ju��)�ã������ͬ�W(xu��)�Ŀ��^���y(t��ng)�@һ�����Ƕȣ�ͨ�^(gu��)��(g��)���о�ȥ�����ɹ�ʷԊ(sh��)�ı��|(zh��)������̽ӑ���gԊ(sh��)ˇ�Ę�(g��u)��Ҏ(gu��)�ɣ��M(j��n)����ʷԊ(sh��)Ԋ(sh��)�W(xu��)���Z(y��)�ԽY(ji��)��(g��u)�ό�(du��)�о���(du��)���c�΄�(w��)������һ����ҕ�c�U������(du��)�W(xu��)������������ġ�ͨ�^(gu��)����Փ�C���҂����Կ�����ʷԊ(sh��)������һ�N�����������Ļ����y(t��ng)�Ŀڂ��ČW(xu��)�F(xi��n)����������(n��i)�ڽy(t��ng)һ�Եģ����mȻ��һ��(g��)��(g��)���w�ĸ��ּ���һ����Ԋ(sh��)�����M�ɣ����֛Q���ܺ�(ji��n)�ε�߀ԭ���(g��)���ּ����ı����ĵ���ӡ�
���ԣ�ʷԊ(sh��)�W(xu��)���о�Ҳ����ͣ�����Y�ϵĶ������ֳ����ąR���ϣ���횏��@Щ��(g��)���ֲ��Ă��y(t��ng)��Ԫ֮�g��؞��������������ÿһ��(g��)����ʷԊ(sh��)���y(t��ng)��ȫ�֡��Ҹ��X(ju��)�����@��(du��)��̽���ɹ�ʷԊ(sh��)���y(t��ng)��ͻ��ʷԊ(sh��)���y(t��ng)����ij��(g��)�Ϸ������ʷԊ(sh��)���y(t��ng)����ͬ����Ҫ��һ��(g��)ҕ�ǡ�ֻ���ڌ�(du��)�@һ��(g��)��(g��)ʷԊ(sh��)���y(t��ng)����ȫ�漚(x��)�µĿ�����҂������M(j��n)һ���ĸ�����ȫ���Ͽ��Ї�(gu��)ʷԊ(sh��)��
��һЩ�����Ԇ�(w��n)�}���ڳ����ͬ�W(xu��)���������Ǜ](m��i)�лرܵģ���������������Ҋ(ji��n)�ص��U���cՓ�������磺ʲô�пڂ�ʷԊ(sh��)��Ҳ�����f(shu��)��ʷԊ(sh��)֮��ʷԊ(sh��)�������|(zh��)�������������ʷԊ(sh��)�ݳ����y(t��ng)������Ʒ�������Ӯa(ch��n)���ģ���ʷԊ(sh��)���y(t��ng)�����ܳɞ�ʷԊ(sh��)���y(t��ng)���ֺ��Գ��F(xi��n)ʢ˥�����У��ڂ�ʷԊ(sh��)�������ӵķ�ʽ�����ւ�����(l��i)�ģ�����������ʲô�ӵ������Ļ��Շ�����(x��)���ݳ���ˇ�ģ��ȵȡ������f(shu��)�������ͬ�W(xu��)��(du��)�@��һЩ��(w��n)�}���������_�Ľ��Ҳ��(du��)ʷԊ(sh��)�W(xu��)���O(sh��)�������Ե����X(ju��)���c��ͬ�r(sh��)�������о�����Ҳ����ֹ�ڳ����һ��ԭ���ϣ���?y��n)����ķ������D(zhu��n)�ص��˾��w��ʷԊ(sh��)��(g��)����ȥӡ�C��ȥ�z�(y��n)��ȥ���(du��)ʷԊ(sh��)���y(t��ng)�����⡣�������@�N���w֮�ھֲ�����(g��)�e֮��һ������R(sh��)�����^�졢����ʷԊ(sh��)�����M(j��n)�^(gu��)�̣�Փ���ɹ�ʷԊ(sh��)���Z(y��)���L(f��ng)��ʽ�����������ֶεȵȕr(sh��)��Ҳ�͛](m��i)������äĿ�ľ���Փ�£�������ؽ�ʾ����ʷԊ(sh��)�Ŀڂ����|(zh��)��������ʷԊ(sh��)���y(t��ng)�ڮ�(d��ng)�����g�����(hu��)�����еİl(f��)չ�������Ҏ(gu��)�ɣ��������_(d��)���ˌ�(du��)�ɹ�ʷԊ(sh��)���y(t��ng)��Ԋ(sh��)�W(xu��)�����M(j��n)�пƌW(xu��)���Y(ji��)���о�Ŀ�ġ�
��
ֵ��һ����ǣ������ͬ�W(xu��)���о����_��(sh��)�ڡ����^�ԡ��c���ı��ԡ�֮�g���b�e�c(li��n)ϵ�ϣ��ҵ��ˆ�(w��n)�}���P(gu��n)�I��Ҳ�Lԇ����(sh��)�`��һ�N�Ќ�(sh��)���е��о��������@��һ�N�M�����������g�ڂ��ČW(xu��)�Ěvʷ�c��(sh��)�H���^���c������(w��n)�}�ķ�����ͬ�^(gu��)ȥ�҂����X(ju��)�����X(ju��)���ԕ�(sh��)���ČW(xu��)�۹��(l��i)�о����^�ČW(xu��)��������ȣ���e�Ǻܷ����ġ����e��ע�������(du��)�҂����������g�ČW(xu��)������(w��n)�}�ϵ��ٙzӑ��Ҳ�����f(shu��)�������^�ԡ����҂��^(gu��)ȥ��(j��ng)��ӑՓ��һ��(g��)Ԓ�}���������@�������еõ��M(j��n)һ����������f(shu��)��(l��i)���҂�������(du��)�����^�ԡ���Փ����ƫ���������ⲿ(li��n)ϵ������(du��)�������ă�(n��i)��(li��n)ϵ��ƫ�����c��(sh��)���ČW(xu��)�ĺ��^���^������(du��)���Ԍ�(du��)�����^�ԡ��������^������Ҳ�����f(shu��)�����ڵ��о��_���˃�(n��i)�����о����M���҂���(du��)�����^�ԡ������ஔ(d��ng)?sh��)����⣬���?du��)ʲô�ǡ����^�ԡ����^�ԡ����������Ә�(g��u)�ɵģ����������w�F(xi��n)�顰���^�ԡ��Ć�(w��n)�}�ϣ��治��V���l(f��)�����Ȼ���@�������c(di��n)���@�Ǒ�(y��ng)ԓ������J(r��n)�ģ����٣��@�������Ҹ����˼�������磬�҂�?c��)�ʷ�?sh��)ӛ䛺��������^(gu��)���У���������(j��)�W(xu��)���^��ȥ������(d��ng)���h����Щ�����؏�(f��)���F(xi��n)�Ķ����Ԋ(sh��)��(ji��)���J(r��n)�����Ƕ������٘�ģ����@��ǡǡ���ǿ��Z(y��)˼�S�^(q��)�e�ڕ�(sh��)��˼�S����Ҫ���������Ǹ��֑T��ʹ�õġ�����(f��)����(f��)������ӛ���ֶΣ��������ࡱ�����؏�(f��)�����ñ����@�ǿ��^�ČW(xu��)�Ļ������ԡ��@�H��һ��(g��)��(ji��n)�ε����ӡ������^�ԡ�����������̽ӑ�����������҂�����������֪�R(sh��)���������^���еĔ���ˇ�g(sh��)��
�^(gu��)ȥ�҂���ʷԊ(sh��)�о�����Ҫ������ʷԊ(sh��)��Փ��Ӱ푣�Ҳ������ϣ�DʷԊ(sh��)�顰���͡���(l��i)�綨�@һ�����ČW(xu��)��ʽ���@�ӵ�ʷԊ(sh��)�^�����(l��i)Դ�������Ĺŵ���ˇ?y��n)�Փ���?j��ng)�����ҵĿ������������ǂ�(g��)�r(sh��)��̽ӑ����Ʒ�t�������ӡ�ȩ��W�_���Z(y��)ϵ����ՓҊ(ji��n)���������D������ʿ��¡��ڸ�����̩���e��˹�����˵����P(gu��n)Փ���酢�գ������R��˼������˹��Փ��������(j��)���҂�֪������ϣ�DʷԊ(sh��)��ӡ��ʷԊ(sh��)���W�������o(j��)ʷԊ(sh��)�����ڎװ������ǧ��ǰ�ͱ�ӛ���(l��i)���ԕ�(sh��)�淽ʽ�����ͣ��x�_(k��i)������˹���L(zh��ng)��˹���ݳ����y(t��ng)���Ļ��h(hu��n)����������֮���w�خ�(d��ng)���˕�(sh��)���ČW(xu��)��(l��i)�����о�����(sh��)�H�ϣ��S�����䡶�¿ƌW(xu��)���л��ڏ�(qi��ng)�{(di��o)���Ļ�������(ch��ng)����(du��)���R�ͺ��RʷԊ(sh��)Ҳ����˲��٪�(d��)���Ŀ��������҇�(gu��)�s�����ˆ�(w��n)�����ԣ���һֱҪ�����W(xu��)���I(y��)���о���һ��Ҫ���@����(sh��)��
ǰ���f(shu��)��ʷԊ(sh��)�о�����Փ�ϵ��D(zhu��n)�ͣ���߀�Ǐ�(qi��ng)�{(di��o)Ҫ�J(r��n)�挦(du��)�����M(j��n)�����(gu��)���W(xu��)��Փ�����bһ�T(m��n)�µ���Փ��Ҫ�����������ݡ��M(j��n)ȥ��ֻ�С���Ӿ�����g���ܡ����~(y��)���ܡ�������Լ�����衱���e����ô���ܡ����ѡ��������κ���Փ��ֻ�Ќ�(du��)��Փ�����������������R(sh��)�����á���ȡ�����|(zh��)�ɣ�뢼��������Ų����ڸ�����Ӱ��ä�ģ��@�Ӳ���������(chu��ng)�¡��l(f��)չ��ͻ�ơ����W(xu��)�F�������f�o(w��)�����������ͬ�W(xu��)��һ�_(k��i)ʼ���|�����^��ʽ��Փ�������еذl(f��)�F(xi��n)���@һ�W(xu��)�ɵă�(y��u)�L(zh��ng)֮̎������Ŀǰ��Ҋ(ji��n)�������^��ʽ��Փ����(du��)�����ŵ�ʷԊ(sh��)��Փ��ƫ�H�M(j��n)���˷�������ęzӑ�������У���(du��)ʷԊ(sh��)�о������ڂ��ČW(xu��)�F(xi��n)��_�����^��(qi��ng)�ġ�ϵ�y(t��ng)���U������������ѽ�(j��ng)���V���ؑ�(y��ng)�õ��˶��_(d��)150��(g��)�Z(y��)�Ԃ��y(t��ng)���о�֮�У������h�Z(y��)�ġ�Ԋ(sh��)��(j��ng)���о����������A��W(xu��)�������I(xi��n)�����K���u(p��ng)��������(gu��)���R�ˡ�����?t��ng)���혱���һ�£?981�����g����(l��i)�Ї�(gu��)����Ұ�x�c(di��n)�r(sh��)�҂�?c��)����^(gu��)һ����Մ�����(l��i)?y��)?j��)�f(shu��)�� (t��ng)���ҵĽ��h���ڄ�����Ĺ��l(xi��ng)�V��һ������7�ꡣĿǰ���ѽ�(j��ng)�ɞ��о��K���u(p��ng)�����Ї�(gu��)�Ϸ��T�����ČW(xu��)�Č��ң����ȵȡ�����������J(r��n)�����а������ܶ���(chu��ng)Ҋ(ji��n)�c����֮̎����(du��)�҂���˼·��(hu��)�������l(f��)��
�ij����ͬ�W(xu��)��(du��)�@һ��Փ���\(y��n)����r��(l��i)��������ʷԊ(sh��)�ĸ����ϼ{�뵽�˿��^���y(t��ng)�����W(xu��)ҕҰ��(l��i)��������ҕ�����@һ��(g��)�Ƕ����v���@һ����һ������ʷԊ(sh��)�о��đT��·�����ڻ��ΑB(t��i)��ʷԊ(sh��)�ݳ����y(t��ng)������u��ʧ�Č�(sh��)�H�У����ı��������֣�ͨ�^(gu��)���C�����Č�(sh��)����ȥ̽��������ı�����Ŀ��^���y(t��ng)�����J(r��n)�飬����������Մ���ģ��@��������(du��)���W(xu��)�ı���(w��n)�}��һ���ą����r(ji��)ֵ���⣬�����U���ġ���ʽ���L(f��ng)�_��(sh��)���ஔ(d��ng)�̶��Ͻ�����҂�?c��)���̽ӑ�ò���������T����(w��n)�}���c��ͬ�r(sh��)��Ҳ���҂����g��ˇ�W(xu��)����ijЩ�ŵ��ČW(xu��)�о��ṩ��һ��(g��)�µ�ҕ�ǣ����磬��Ԋ(sh��)��(j��ng)���ġ��d�����Ŵ�Ԋ(sh��)Փ����̽ӑ��ֱ�������W(xu��)�ߵĿ���Ҳ�����ֿ�����Ī��һ�ǡ��ҿ�������Ǐĕ�(sh��)��Ԋ(sh��)��ġ��o�Ƕ�ȥ��������䡱֮�d���������g�ڡ�Ԋ(sh��)���о����С����d��֮�wʮ��֮�࣬�Ҵ��w߀ӛ�õ��иЕr(sh��)���d���������d���������d��ֱ���d�����d���d�������d���������d���������d�ȵȡ���(sh��)�H�ϣ��@Щ���^�ġ���䡱֮�d���ڮ�(d��ng)�r(sh��)�����ԁ���п��ܾ���һ�N���g�l(f��)�a(ch��n)�������ij�ʽҪ�����磬�Ŵ������е��e�ס���ԡ����Z(y��)һ���I�u(p��ng)�顰��~�E�{(di��o)������ĩ�T��(m��ng)��?ji��n)ڡ��p��ӛ��������Մ��������֮�ס��r(sh��)��ָ؟(z��)�飺����ȡ�ڃ�(n��i)�B�_������ֻ�ñ��^���ס������磬Ԫ�s���ġ�����(ch��ng)Ԋ(sh��)�����ЌW(xu��)���J(r��n)���������^֮�Ї�(gu��)�ČW(xu��)�С����Z(y��)�����һ�N���������������(l��i)�����~��Ҳ�ǝMĿ��נ��Z(y��)�����ƞE��Ҳ�Ǵ��Ļ�һ؞�����L(f��ng)������Ҋ(ji��n)���Ę�(bi��o)�����Ї�(gu��)��ʷ�����ⲻ֪���@Щ��(g��)�s���׳ɵġ���ʽ��ǡǡ�f(shu��)������Դ�����g�������g���L(zh��ng)������ı���Ҳ�Կ��������ġ������������@һ��Փ����ȥ����ǡ��(d��ng)��ጵģ�����߀��Ԓ��С�f(shu��)�ǷN���Z(y��)���Ĕ���ģʽ�������״�ŵ�С�f(shu��)������ء�ͨ�Ž��_(k��i)������Ҫ�f(shu��)��Փ�أ�������������µ�Ш�ӣ��ȵȡ���������ˇ�g(sh��)���ܣ����������ڵ�Ԋ(sh��)Փ������(j��ng)�ᵽ��
һ�ι��£� һ��(g��)˼�룬������������ı��������܉�ס�@�N����ģ����Ǹɾ���ˇ�g(sh��)�ҡ�����Ԋ(sh��)�ġ���
����Փ�������v���҂�Ҫ��(du��)�Ї�(gu��)ʷԊ(sh��)�����������g�ڂ��ČW(xu��)�F(xi��n)����о���(j��ng)�(y��n)�M(j��n)�и�������Ŀ��Y(ji��)��̽ӑ����ô�ڽ��b���^��ʽ��Փ��ͬ�r(sh��)���҂�Ҳ��Ҫ��ӛ���������W(xu��)�g(sh��)�����Ļ����y(t��ng)������@һ��Փ���A(y��)�O(sh��)�c�z�(y��n)�ṩ��ǰ�ᣬҲ�����f(shu��)���@һ�W(xu��)�ɵĸ�����(l��i)���������Ļ����y(t��ng)�c�W(xu��)�g(sh��)�^��҂���횱������ѵ��J(r��n)�R(sh��)��
�������T������о��¸�ֺ���˼·��(l��i)���@����(sh��)�������f(shu��)�������ͬ�W(xu��)���x�����(gu��)���W(xu��)��Փ���@һЩ��(g��)��(w��n)�}���ǙC(j��)���ģ�Ҳ���J(r��n)�挏���ġ����ڎ������W(xu��)�v��(x��)�������v���^(gu��)�������M(j��n)���\(y��n)�����(gu��)��Փ�Ć�(w��n)�}�ϲ�������̗��������ͬ�W(xu��)���g��������֮�g�����Ĺ������dz�ֵؿ��]�������ա��������ڕ�(hu��)��؞ͨ�����ء����Tʿ�r(sh��)�������ǬF(xi��n)���ČW(xu��)�����^�õ���ˇ?y��n)�Փ֪�R(sh��)�����������½��l(w��i)���غ̓�(n��i)�ɹſƠ��ߵȵص�ʷԊ(sh��)��Ұ�{(di��o)���У����c�^���^(gu��)��N�����h(hu��n)���µĸ����ݳ���(ch��ng)����������C(j��)�������R(sh��)���˕�(sh��)��ʷԊ(sh��)�c�ڂ�ʷԊ(sh��)֮�g�IJ�c(li��n)ϵ����ᘌ�(du��)���g�ď�(f��)�s�P(gu��n)(li��n)��(y��ng)ԓ�в�ͬ���о��ֶΡ��@��(g��)�P(gu��n)�I��(w��n)�}�����⣬�tֱ�ӵ���������1995���_(k��i)ʼ�¹���ġ����^��ʽ��Փ�������Ⱥ��g����B���о��@һ�W(xu��)�ɵ�������m(x��)���F(xi��n)������˹�����ͻ��Ӣ��ʷԊ(sh��)�е�ƽ��ʽ����ʽ���䷨��Ԋ(sh��)�W(xu��)̽�������������Ç�(gu��)�H���W(xu��)��(hu��)�������ްຆ(ji��n)�驤����Մ��(gu��)��ʷԊ(sh��)��Փ���������^��ʽ��Փ�����^���y(t��ng)�о������������ڂ�ʷԊ(sh��)�ġ���(chu��ng)������(w��n)�}�������ڂ�ʷԊ(sh��)����Ұ���I(y��)��(w��n)�}���ȣ����п���Ҋ(ji��n)������(du��)�@һ��Փ�ā�(l��i)��ȥ�}���m�ó̶ȡ�������ܡ���Փ���Ȇ�(w��n)�}���С��W(xu��)֮������(w��n)֮����˼֮������֮���V��֮���ĿƌW(xu��)�B(t��i)�ȣ���ʼ�K��(ji��n)���Ԃ��y(t��ng)�鱾����(du��)�Լ����о���(du��)�������˷����Լ�����ڂ��ČW(xu��)��(sh��)�H�����w���գ����@�N�����в��ܱ������鱾���о��ߵ������c��ȡ�Ҳ�����f(shu��)�������@ЩŬ���������������������W(xu��)�I(l��ng)��l(f��)չ����(l��i)�ġ����^��ʽ��Փ�����о��ɹ��������ܡ��Ͷ���ͬ��������������������R(sh��)�،�(du��)�������յ��ɹ�ʷԊ(sh��)�ı��M(j��n)������������������������(sh��)�c��(sh��)�C�����������Ǻ�(ji��n)�ε��հ�����á��@���������H���]��������ʷԊ(sh��)���y(t��ng)�c����ʷԊ(sh��)���y(t��ng)�Ĺ�ͨ�ԣ���Ҫ̽���ڂ�ʷԊ(sh��)�ھ��w�Ěvʷ���Ļ��h(hu��n)���������@ʾ�䱾�|(zh��)�ϵ�����Ԋ(sh��)�W(xu��)������
��ˣ�����(sh��)����Փ̽ӑ�����ͻ����һ�c(di��n)�LJ�(y��n)֔(j��n)?sh��)Č?sh��)�C���о��������ġ����^��ʽ��Փ����Ҫ�����ڌ�(du��)�����R��(w��n)�}���Ľ�����D�����o�B(t��i)���ı����������D(zhu��n)��ǰ��˹�����һϵ����Ұ����ı��^�о���(l��i)�(y��n)�C��Փ�ļ��O(sh��)��������(sh��)�������Ї�(gu��)�ɹ�ʷԊ(sh��)�Į�(d��ng)ǰ�Ŀ��^��(sh��)�H���ڷ���Փ�Ͼ͛](m��i)���ಽ��څ��ǡǡ�����������֮��������Փ�cՓ�C�^(gu��)�̿����������ɹ�ʷԊ(sh��)���y(t��ng)��ʢ˥�c׃������������ʷԊ(sh��)���������ӻ��Ŀ��^�ı��c��(sh��)���ı��ď�(f��)�s�P(gu��n)(li��n)�����ڌ�(sh��)�ص���Ұ�^������Ҫ��������־�LՄ���Ѽȶ��ı��ŵ��������[�](m��i)���ݳ��h(hu��n)�����M(j��n)�Ќ�(du��)�պ�߀ԭ�����ı��U����������(g��)���о����ձ������x��Ҳ��һ������Ͻ�ʾ���ڂ�ʷԊ(sh��)����׃Ҏ(gu��)�ɼ����ı����^(gu��)���е�Ԋ(sh��)�W(xu��)���x���@�Ӳ��ܵó����Ϛvʷ��(sh��)�H����Փ˼��������������������Փ���С��ľ����ԡ����ԣ��@��һ��?g��u)?qi��ng)�{(di��o)����(sh��)�Č�(sh��)�C�о�·�������҂���(y��ng)ԓ���Ը߶���ҕ�ġ�
���⣬��Ҫ혱��ἰ��߀��һ��(g��)���棬�Ǿ��Ǿ����(x��)��Ԋ(sh��)�W(xu��)�������dz����ͬ�W(xu��)�@����(sh��)�o���������ӡ�����һ��(g��)���c(di��n)����Փ��?f��)?j��)�E�������������ı���(sh��)֮����ֱ�������һ���Ќ�(sh��)���еĹ������E��������(gu��)�HʷԊ(sh��)�о��繲���ķ���ģ�ͣ�����(j��)�ɹ��Z(y��)���ķ����c(di��n)��ʷԊ(sh��)���y(t��ng)�������O(sh��)Ӌ(j��)��6�N���w���ı��������������Գ�һ�w�ġ��ڴ˻��A(ch��)�ϣ���(y��n)�����x����һ��(g��)�ض���ʷԊ(sh��)Ԋ(sh��)��������Ҫ��������ȽƤ���ݳ��ġ��F���_����������ݗ������������ʷԊ(sh��)�ı����Ķ�ѭ��u�M(j��n)�ؾ͡���ʽ�䷨���ĸ������M(j��n)���˼�(x��)������Ԋ(sh��)�W(xu��)�������f(shu��)�����w�IJ���Ҳ�����䪚(d��)��(chu��ng)�r(ji��)ֵ�ġ����磬����(sh��)�״β�������X��(sh��)��(j��)�y(t��ng)Ӌ(j��)�����Ķ���(g��u)����������������з������ɴ�ϵ�y(t��ng)�ؽ�ʾ���ɹ�ʷԊ(sh��)���~�����䷨�ij�ʽ����(g��u)�ɷ�ʽ���@�N���C��������Ҫ�ஔ(d��ng)��Ĺ������ģ���Ҋ(ji��n)��ʮ����ҕ�����g���^Ԋ(sh��)��ľ��w������(l��i)�U�l(f��)��Փ�c(di��n)���������^(gu��)�̵ď�(f��)�s�̶����@����Ҋ(ji��n)�ģ��@�N��η������{(di��o)���������@�о��������pһ���W(xu��)����Ҳ���y�ܿ��F�ġ���
���R����Ʒ�mȻ�����r(sh��)�������÷N�N��ͬ�������b�p�������ǣ�����Ȼ������һ���Ŀ��^��ˇ�g(sh��)�r(ji��)ֵ������Ԋ(sh��)�ġ���
�@�Nˇ�g(sh��)�r(ji��)ֵ�����ͨ�^(gu��)Ԋ(sh��)ˇ�������õ�ӡ�C�����^(gu��)ȥ��һƪ����������(j��ng)ָ�����҂�?c��)����g��ˇ�W(xu��)�о��д�����һ�N��������҇�(gu��)�ٔ�(sh��)���嶼������һ����(sh��)���Ŀ��^�����Ʒ�����@�N�����ˇ�g(sh��)����(k��)�У��������Լ���һ��Ԋ(sh��)�W(xu��)�����P(gu��n)��Ԋ(sh��)��(ji��)��Ԋ(sh��)�С�����(ji��)��Ѻ퍵�һ����ʽ���@�NԊ(sh��)�W(xu��)�Ǹ�����������(g��)Ԋ(sh��)��ˇ�g(sh��)���в��ɷ��x�ġ��^(gu��)ȥ�ஔ(d��ng)�L(zh��ng)�ĕr(sh��)����҂���(du��)�����gԊ(sh��)��������c(di��n)��ֻ������Ʒ�ă�(n��i)�ݷ��棬����(du��)�c���o�����B��ˇ�g(sh��)���w���s����ע�⡣�@��һ�N���۲��۵�ƫ���@���о��ijɹ��f(shu��)����ô���ǚ�ȱ��ȫ�ģ����������ġ����Ԋ(sh��)�W(xu��)�f(shu��)����ô����һ�N�����������
�����M(j��n)չ�е����g�ČW(xu��)�I(y��)��1981�꡶�ٿ����b���� ��(du��)��һ�N�Ļ��F(xi��n)�H��һ�N��Փȥ����Dz���ģ��F(xi��n)�ڲ��ٌW(xu��)���ᳫ��Ƕȵ��о������R���Z��˹���ġ�����Փ�����ձ��g�����C(j��)��Փ���������_�յ����g����31�N�C(j��)���f(shu��)����(du��)���ض��Ļ����y(t��ng)�еĹ��¬F(xi��n)�����^��Ľ����������������ֲ��ʷԊ(sh��)�Y(ji��)��(g��u)������ȥ�����ͬ�������g�����ČW(xu��)��ĸ�}�ϵ��P(gu��n)ϵ���@һ�c(di��n)��(d��ng)Ȼ����Ҫ�����Dz��Ǿͺ�ȫ�棿����ʷԊ(sh��)������w�ģ��ڔ����Ͽ϶������ض��ķ�ʽ����Ԋ(sh��)�W(xu��)���^�c(di��n)������(w��n)�}������ʷԊ(sh��)�о���һ�N��Ҫ�Ƕȡ��������@�����_��˼��ָ��(d��o)�£������ͬ�W(xu��)���ˎ���Ŀ������������(d��ng)���Ŀ��^���y(t��ng)��Փ�����^���L(zh��ng)���ɹ�ʷԊ(sh��)���y(t��ng)�����µ��۹��(l��i)����ҕ�����S���茍(sh��)�����C����(xi��)���Լ����ɹ�ʷԊ(sh��)Ԋ(sh��)�W(xu��)��
��ϣ���@�Nע��̽�����g���^Ԋ(sh��)�W(xu��)���L(f��ng)�⣬Ѹ�ٔU(ku��)չ����(l��i)��Ҳϣ���҂����о��܉���ɹ�ʷԊ(sh��)Ԋ(sh��)�W(xu��)�U(ku��)չ������(g��)�����Ԋ(sh��)�W(xu��)����������ʹ�҂�?c��)�ijһ�ض���������gԊ(sh��)����о��ϸ�ȫ�桢�����룬Ҳ��ʹ�҂��C�ϵ�ʷԊ(sh��)�W(xu��)���������gԊ(sh��)ˇ�ƌW(xu��)�Ľ����������ɿ��Ļ��A(ch��)���x��ǰ�̡�
��(y��ng)��(d��ng)ָ�����ǣ�����(sh��)ֻ�dz����ͬ�W(xu��)�о�ʷԊ(sh��)Ԋ(sh��)�W(xu��)�@��(g��)���n�}�ĵ�һ��������(j��)�����о�������߀��һϵ�Эh(hu��n)��(ji��)��δչ�_(k��i)����˱���(sh��)����������㵽��Ҳ������ƽ������������ʷԊ(sh��)��Փ��̽��Ҳͬ����Ҫ�^�m(x��)���غͰl(f��)չ�����ڲ���̎���ɣ������M(j��n)�ӡ������h�ڽ��Ĺ����У���(du��)ʷԊ(sh��)�ġ���ʽ�������غ͡��dz�ʽ�������ؼ������P(gu��n)�������x�����M(j��n)һ�����о����ԏ����w��������ʷԊ(sh��)��Փ�о��@��(g��)����ČW(xu��)�g(sh��)���������⣬߀��(y��ng)�^�m(x��)�ڂ�(g��)���о��Ļ��A(ch��)�����M(j��n)����(zh��ng)ȡ�ڸ��V���İ��������У��z�(y��n)��У�������ơ��䌍(sh��)ʷԊ(sh��)�W(xu��)���о���
��
ƽ�Ķ�Փ���Ї�(gu��)��ʷԊ(sh��)�о��������ֻ�����ڷN�Nԭ������δ���ڇ�(gu��)�H������(y��ng)�е���ҕ������һ�l���ҿ�������ȱ����Փ�ϵ������Ϳ��Y(ji��)�����磬�����ŵ�ʷԊ(sh��)��Փ���о�����ӡ��-�W�_���Z(y��)ϵ����Ʒ�����Ї�(gu��)ʷԊ(sh��)��r�ͱ�����ĸ����S�����Ӵθ��࣬������Щ��Փ�Ͳ��ܟo(w��)���Ƶ�ʹ�á�����ʷԊ(sh��)�Ľ綨�����@��(g��)��Ҫᘌ�(du��)Ӣ��ʷԊ(sh��)����Փ�^(gu��)����ȥ�ã��Ͳ�һ�����m���Ї�(gu��)�Ϸ��T��������ӻ���ʷԊ(sh��)��͡��҂���(y��ng)ԓ����Փ�ό�(du��)�Ϸ�ʷԊ(sh��)�����^��ϵ�y(t��ng)����͌W(xu��)�о����@�ӟo(w��)��Ҳ��(hu��)���_(k��i)��(gu��)�HʷԊ(sh��)�W(xu��)���ҕҰ���S����������ʷԊ(sh��)���L(zh��ng)�ȡ�
���⣬߀Ҫע��һ�Nƫ�����Ї�(gu��)����(j��ng)���^(gu��)�����W(xu��)��Դ����һ�ɣ���(l��i)�������ČW(xu��)�f(shu��)����Փ����Ҫ�M(j��n)��һ��Դ���Ї�(gu��)�Ŀ��C���Ա�Ω�Ҫ�(d��)����f(shu��)һ�䡰�쳯�Թ���֮��������Ȼ�Եõ�ͣ����ǰ���P(gu��n)�ڡ���ʽ�����S������Ԟ�Ȼ���J(r��n)���҂��������^(gu��)ȥ�Ĺʼ��Ѱl(f��)�F(xi��n)�@�N��ƵĿ��Y(ji��)������ǰ�������ġ���ԡ��������Z(y��)���ȵȣ�ֻ���^(gu��)�҂��Ĺ��˛](m��i)�á���ʽ�������T�ˡ��҂���(y��ng)ԓ�J(r��n)�R(sh��)�����ǘӵĿ��Y(ji��)��������Ƭ��ֻ�Z(y��)�ģ���Ƭ��ģ�ȱ��ϵ�y(t��ng)����Փ�������҂�Ҳ��(y��ng)ԓ�J(r��n)�淴˼����ʲô�҂��^(gu��)ȥ�͛](m��i)����ȥ�M(j��n)��һ���ƌW(xu��)�Ŀ��Y(ji��)���Ķ���ֱ��ѵؿ϶����g�ڂ��ČW(xu��)֮������(g��)�Ї�(gu��)�ČW(xu��)�l(f��)չ�Ěvʷ��(d��ng)�����Ķ��ó�һ��(g��)�и߶ȵġ����ձ����x����Փ�����أ�
�f(shu��)���@��ҵ�����һ��(g��)��(l��i)�����ǻ۵Č�(sh��)����1986�����죬�ҏ����g�ČW(xu��)�Ҍ�(sh��)ӛ䛵ĽǶȣ����ѹ��R�W(xu��)�����ڵ��ļ����؈@��������һ��(g��)С�����@���ļ�������ע���(d��ng)�r(sh��)���g����������ʷԊ(sh��)�����^(gu��)�̣����ڬF(xi��n)��(ch��ng)����(j��)���ֵ��ݳ��M(j��n)��ӛ䛵ġ��Ǖr(sh��)�R������ָ��������ʷԊ(sh��)��ȫ�����á��P(p��n)�衱�Č�(du��)����ʽ���@�c����Ӣ��ʷԊ(sh��)�Ͳ�һ�ӣ���������һ�����ǂ��y(t��ng)�ĹŸ裬�еąs�Ǽ��d�����ġ��R������(d��ng)�r(sh��)�Ͱl(f��)�F(xi��n)�@��ʷԊ(sh��)��Ԋ(sh��)���ʽ�̣������ԏ�(qi��ng)�����^���ͣ�׃����С������(j��)�����v���ڽ̳�ʷԊ(sh��)�r(sh��)�����g��(x��)�T�Ľ̷���ֻ�̡��ǡ������̡�������Ҳ�����f(shu��)�����ǡ��DZ��^���͵ģ��Ǹ�Ļ������֣����O(sh��)��(w��n)�ͽ��Ĕ������֣��������mȻҲ�ǂ��y(t��ng)�Ė|����������(sh��)��Щ���d֮������?y��n)�ٝ���?du��)����ˣ���?y��n)邀(g��)���t�~����?y��n)����?zh��n)�Եģ������cԊ(sh��)�豾���ă�(n��i)�ݛ](m��i)��ʲô(li��n)ϵ���@����Ҋ(ji��n)�������ǷN�ض��Č�(du��)��h(hu��n)�����ͺ��y�ŷų��ǘӵġ�������(l��i)���R�W(xu��)�����؈@����191�(y��)����������һ��(g��)��(ch��ng)��߀ָ�����������x�_(k��i)�˸質�h(hu��n)�����ͺ��y�����������N�ġ�������(l��i)����(sh��)�`�_����ˣ���(d��ng)�҂�Ҫ������v��Ԋ(sh��)���(n��i)�ݕr(sh��)�������質�r(sh��)���S����(y��u)����(d��ng)�˵ĸ��~��Ҋ(ji��n)�ˣ������еĸ��֣�ֻ�����������������f(shu��)��ӛ�������f(shu��)������ӛ���꣬�f(shu��)��ӛ��ȫ�����@Ԓ���е������@Ҳ�ǿ��^�ČW(xu��)�����c(di��n)���Q���ġ���?y��n)飬�](m��i)������ӛ䛵Ŀ��^�ČW(xu��)������������Ͽڣ������������ʴ���Dz�ȡ�質�ķ�ʽ�������{(di��o)��ɂ��b��(l��i)���x�_(k��i)���{(di��o)��ɣ�Ԋ(sh��)����ͬʧȥ���`�ꡭ�������R�W(xu��)�����؈@����126��127�(y��)�����@�Δ����У��҂����Կ���������֪�R(sh��)�ķ�����(n��i)����(du��)ʷԊ(sh��)�Ă���Ҏ(gu��)���ѽ�(j��ng)�����ؘ�ġ���ֱ�ĸ��������е�ijЩ��ԭ�����c�����W(xu��)�ߵ���Փ�A(y��)�O(sh��)��һ�µġ����ǣ������(l��i)���҂���Ȼ����������Ҳ�](m��i)�Ќ�(du��)�������������롢�ص���������֮���A��һ��(g��)��Փ�ĸ߶ȡ���ˣ��҂���(y��ng)ԓ���J(r��n)�Լ��IJ��㣬�����ҵ��l(f��)չ�Լ��������c(di��n)��
��һ���棬�����R(sh��)�����������^Ԋ(sh��)�W(xu��)��Փ�酢�գ����Դ��_(k��i)�҂���˼·�����҇�(gu��)�S�����ء��ΑB(t��i)�r��Ķ�����ʷԊ(sh��)�YԴ����ף�ȥ���������Ї�(gu��)��ɫ��ʷԊ(sh��)�W(xu��)��Փ��Ҳ����ȫ���еġ����돊(qi��ng)�{(di��o)���ǣ��@�N��Փ�wϵ�Ľ���(g��u)�c���Y(ji��)����회�(sh��)�����ǵؽY(ji��)���Ї�(gu��)������ı����Ļ���Ҫ��Խ���⽛(j��ng)�(y��n)����(sh��)����������Փ�ĸ߶ȣ����������Ļ��W(xu��)��ҕ�ǩ��������ڿ��^���y(t��ng)��(l��i)�M(j��n)���о�������ʷԊ(sh��)Ԋ(sh��)�W(xu��)�c�����Ļ����y(t��ng)�ЙC(j��)�����Ϟ�һ�w����(y��ng)�Ǯ�(d��ng)���Ї�(gu��)ʷԊ(sh��)�W(xu��)�@�T(m��n)�W(xu��)������(y��ng)��Ļ���Ŀ��(bi��o)�c�W(xu��)�g(sh��)��ܡ�
�҈�(ji��n)�������ţ��Ї�(gu��)�����W(xu��)�о��������飬��?y��n)��҂���Դ�h(yu��n)���L(zh��ng)�����W(xu��)���y(t��ng)���҂����N(y��n)���S����ȡ֮���M�������о��YԴ�����^(gu��)ȥҲ�f(shu��)�^(gu��)�����Ї�(gu��)����Ԓ�cʷԊ(sh��)�@�ɂ�(g��)��Ҫ�I(l��ng)�����܉�Ҳ�Ǒ�(y��ng)ԓ���ԡ����l(w��i)�ǡ��ġ������ǣ�ʷԊ(sh��)�����P(gu��n)���徫�����Ҫ�Ļ�ؔ(c��i)�����҇�(gu��)�����������?zh��n)��(y��u)��҂��?chu��ng)������ˠN��������_����ʷԊ(sh��)����(k��)���������ӌO������҂��^�в��l(f��)չ������ƾá��������L(zh��ng)����������ʷԊ(sh��)���y(t��ng)����һ���W(xu��)�ߞ��҂��_(k��i)��(chu��ng)��ǰ���f(w��n)���ʷԊ(sh��)�о��I(y��)���@һ�ж����҂���ʷԊ(sh��)�W(xu��)���O(sh��)�춨�ˈ�(ji��n)�̵Ļ��A(ch��)������(gu��)�W(xu��)���о�ʷԊ(sh��)Ҫ����˹����Ҫȥ���_�������҂����쪚(d��)��������һ��(g��)ʷԊ(sh��)�Č��أ�����(y��ng)ԓ���ɹ�����������о��ɹ�����������(sh��)����Փ�ɹ���
���^(gu��)������������ˡ�������ɢ���L(f��ng)����ɽ���]����
һ��(g��)�r(sh��)����һ��(g��)�r(sh��)�����ČW(xu��)��һ��(g��)�r(sh��)��Ҳ��һ��(g��)�r(sh��)���ČW(xu��)�g(sh��)��һ��(g��)�r(sh��)������һ��(g��)�r(sh��)���ČW(xu��)�ˡ����֮�꣬����21���o(j��)���Ї�(gu��)���W(xu��)�l(f��)չ����ϣ�����F(xi��n)�������ͬ�W(xu��)�@�ӵ���һ��ʷԊ(sh��)�W(xu��)�ߣ����_(k��i)韵�ҕҰ�����J��˼�룬ȫ����Ͷ�뵽ʷԊ(sh��)�о��@һ����ϵ��I(y��)֮�У�Ŭ���_(k��i)��(chu��ng)һ��(g��)���ӹ�ʊZĿ�ČW(xu��)�g(sh��)��ء�
���ؓ(f��)ǧ��I(y��)��
����ǰ�˱Ӻ��ˡ�
��ϣ���c���p��һ�����W(xu��)�о��߹��㲻и��
2000��8��5���ڱ������������f�r(sh��)��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