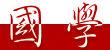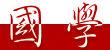作為“中國佛教典籍選刊”叢書之一的《高僧傳》,199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封面題為 湯用彤校注,扉頁則在“湯用彤校注”下增加“湯一玄整理”。湯錫予先生為近代以來治中古
佛教史之第一人,《高僧傳》乃案頭必備之中古史籍,龍鳳之配,莫與比隆。我在1993年春天 買到此書后,夏天就匆匆翻閱一過,然而大失所望,對于校注水平實在不敢恭維。細讀湯一玄
《整理說明》,才知道是錫予先生“未竟之稿”,大概是錫予先生的哲嗣一玄先生在雜亂的筆 記中整理出來的。據一玄先生的話,原稿中只有“開頭六個僧傳及三個附錄”是已經定稿的,
曾于1963年底(就是我出生那會兒)油印出來征求意見。我不明白“開頭六個僧傳”究何所 指,是前六卷呢還是第一卷的前六個僧人(攝摩騰、竺法蘭、安清、支樓迦讖、曇柯迦羅、康僧會)?如果是后者,那么現在的“定本”與錫予先生的原計劃比較起來,不知有多大差距?
我寧愿相信,只有開頭六個僧傳為錫予先生手訂本,其它都是整理者依據筆記工作的結 果。為什么這樣說呢?我查閱自己的讀書筆記,是從第九個僧傳(帛遠)開始,我就遇到了大
量的校注硬傷,以錫予先生之博學精謹,這些問題決無可能出在他的手下。這樣說也許有不公 平的地方,但整理者既然是錫予先生的哲嗣,承擔這一指斥原也是責無旁貸的。
上周在北大南門外的風入松,我看見了新印(第三次印刷)本,與我那第一次印本比, 盡管封面仍然選用了龍門盧舍那大佛的圖像,但新本縮小至書名上方,不似舊印本藍靛色的大
圖像傖傖唐突,而且用紙、裝訂,都遠遠超邁舊本,握在手中,別有風致。我想,正如封面包 裝已經大大改善,書內的錯誤當也有所訂正吧?于是咬牙買下(舊本12.95元,新本
27.50元)。
今天下午講了三節課,晚上微覺疲倦,不能做正經事,就拿出這兩本《高僧傳》來比勘,希望證實我原先的想法。新本果然有了一些改動,比如,頁26,
“太宰河間王顒鎮關 中”,舊本在河間下標一地名符號,在王顒下標一人名符號;注曰:按王顒《晉書》列傳二十
九有傳全無改動,王顒下又標人名符號。顯然是以王顒為一姓王名顒的人,不知這是指西晉河 間王司馬顒。容易看出,錫予先生舊稿是沒有這個錯誤的,否則他不會指出司馬顒在《晉書》
中的本傳來。新印本改掉了這個錯誤,是很可歡迎的,但是許多其它錯誤,一仍其舊。這是令 我非常失望的。嶄新的包裝,依然的迷誤,時代在進步嗎?
姑舉數例,以證吾言不虛。
1)【26頁, “後又甚盛”】校注:據《洪音》及各本“後又”似應為“俊義”之形偽。 案,“後又”顯然是“俊乂”的形偽,乂舊常誤為義,校者竟不敢遽斷。
2)【27頁, “時天水故涱下督富整”】未出校。 案涱下督顯為帳下督之誤。
張輔,《晉書》卷六○有傳,曰“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只要稍翻《晉書》,便 可校出誤字,并可出注。
3)【27頁, “后為武都在楊難敵所圍”】校注指出各本有作在者,有作互者,有作氐 者。但無斷語,究竟應當作何字?
案,后一校注已指出張光《晉書》有傳,何不一查《晉 書》及相關史書之涉及楊難敵者?《晉書》卷七成帝紀咸和六年:“秋七月,李雄將李壽侵陰
平,武都氐帥楊難敵降之。”楊難敵為仇池氐酋,史書或稱武都氐,或稱仇池氐,或稱南氐, 斷在字為氐字之誤,何難之有?
4)【33頁, “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把釋道安三字冠以書名號,不知何謂? 案,原句意思,共之,與也,名德法師者,尊敬道安之辭也,書名號之設,表明整理者沒有看
懂這句話的文意。
5)【73頁, “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 把天竺與王、何理解為并列關系了,顯 然沒有理解王、何所指,王者王弼,何者何晏,原文是說覺賢妙徹玄義,是天竺人中的王弼、
何晏。
6)【78頁, “蒙遜伐乞伏暮末于抱罕……暮末于興國俱獲于赫連定定,后為吐谷渾所 破”】校注:別本赫連定定作赫連勃勃。
案,抱罕當作枹罕。又赫連定為赫連勃勃之子,魏滅夏后率殘部西奔。此句當句讀為:“暮末于興國俱獲于赫連定,定后為吐谷渾所破。”
書中類似的問題之多之可笑,令人實不敢相信此書與錫予先生有什么干系。可見整理先人著述,還是應當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