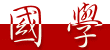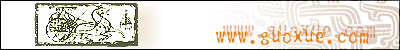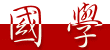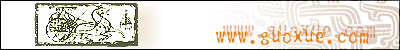|
□祁龍威
1956年春,在近代史研究所舉行的中國近代史分期和太平天國革命性質問題的座談會上,我第一次見到羅爾綱先生,從此得聽教誨。流光如駛,距今已三十年了。到會的邵循正、榮孟源等史學前輩已先后物故,而羅先生巋然無恙,雖經喪亂,年逾八十,但仍治太平天國史不輟。積學六十載,著述等身,士林稱頌,除精力過人外,實得力于下述八字:“鍥而不舍”、“虛懷若谷”。茲以整理太平天國文獻為例,敬述見聞,公之于世。
鍥而不舍
羅先生整理太平天國文獻,功績之巨,前所未有。其主要成果已出版者有《太平天國印書》、《太平天國文書匯編》、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等書。其中《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乃羅先生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而完成。他克服了兩個方面的巨大困難,于成此不朽之作。
其一、三次調整版本。
按《李秀成自述》經過曾國藩刪改后于安慶刊刻,即世所傳“九如堂本”。光緒末,有一個署名捫色談虎客的再加刪改,,交由日本廣智書局刊入《近世中國秘史》中。1931,羅先生開始對《李秀成自述》作注,他當時所能看到的就是《近世中國秘史》本。曾刻本共有27818字,文字較為通順,但因妄加篡改,所以更加失真。如太平軍攻克永安時,《李秀自述》有“困打后移過仙回”一語,“仙回”系嶺名,而捫虱談虎客卻妄改為“困打后欲移兵回”。再如戊午八年天王任命陳陳玉成、李秀成等人為五軍主將,《李秀成自述》有“又得一將朝用”之語。“一將”指李世賢,而捫虱談虎客卻妄改為“又得一蔣朝用”。又如《李秀成自述}說:“龍游有王宗李尚揚把守”。“王宗”系太平天國所封銜名,為對天王堂兄弟和東西、南、北、翼五王兄弟輩的稱謂。后期,對起義較早的老兄弟廣封“開朝王宗”。幼主詔旨:“特詔封李尚揚為天朝九門御林開朝王宗裨天義”。[1]而捫虱談虎客卻妄改為“宗王李尚楊”。由此以誤傳誤,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志》在《王爵表》中)也刊入“宗王李尚揚”。面對這樣謬妄叢生的《近世中國秘史》本《李秀成自述》,羅先生辛苦摸索了十幾年。直到1944年暮春,在廣西通志館工作的呂集義先生才在湘鄉曾氏家里看到了秘藏多年的《李秀成自述》原稿。他窮兩日之力,用隨帶去的北京大學影印九如堂刻本,據以對勘,抄補了五千六百多字,并拍攝了十五幀照片,帶回廣西。其時,羅先生也在廣西通志館工作,看到了呂氏所攝照片四幀及其抄補本,便摒棄了《近世中國秘史》本,改據呂氏抄補本作注,取名《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發表,一時轟動學術界。1951年,開明書店一版再版。1952年,神州國光社版《太平天國》(資料叢刊)據以輯入“諸王自述”中,1954年,中華書局印行《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第三版。1955年,張秀民等編成的《太平天國資料目錄》斷言:“《忠王自述原稿》,久成學術界之謎,今既公布于世,其余二十種版本,幾均可廢。”這是羅先生在注釋《李秀成自述》過程中,第一次調整版本。其實,這時羅先生并沒有機會親見湘鄉曾氏所藏《李秀成自述》原件。對呂集義氏所拍得的十五幀照片,他也僅看到了其中的四幀而已。1954年,原來也在廣西通志館工作的梁岵廬公布了這十五幀照片,取名《忠王李秀成自傳真跡》。并指摘羅先生《箋證》本的訛誤。1957年,中華書局出版《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增訂本),作為該書的第四版。羅先生公開聲明,這書的一、二、三版在版本上有兩點錯誤:一、由于未看到十五楨照片的全份,使自己無法發現呂集義氏補本中的錯誤。二、羅先生憑自己的判斷改動了若干字,以訂正李秀成的訛漏,但未加注明。羅先生說:“現在為了要改正我以前的錯誤,特地根據我在桂林從呂集義先生補抄本和梁岵廬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傳真跡》的十五張照片校對,把《忠王自傳原稿》重新著錄。”這是第二次調整版本。其實,“箋證增訂本”與呂氏“抄補本”仍有出入。于是根據郭沫若同志的提議,1960年,中華書局影印呂集義《忠王李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這個本子雖直接從湘鄉曾氏所藏原件抄補而來,但也未能全部恢復原貌。呂氏自稱:“在兩天內匆促校補完畢,這就很難保證沒有掛漏錯誤的地方,原稿中別體,訛字被曾國藩改過的,只因時間倉促,不及一—改回。”所以呂氏深切盼望原件尚在人間。曾國藩后人所藏《李秀成自述》原件,自呂集義看過后,下落不明。1950年,湖南省文物工作委員會調查了湘鄉“曾富厚堂”的藏書,從書目中發現此件已被“四少爺取去”[2]。按“四少爺”指曾昭樺,已在香港飛往曼谷的途中,因飛機失事而墜死。郭沫若同志曾慨嘆:“‘自述’原稿如為此人所隨身攜帶,則已可能不復存在于人間了。”[3]但到1962年,臺灣世界書局影印出版《李秀成親供手跡》。這件稀世之珍即公開于世。于是羅先生第三次調整版本。由于臺灣世界書局在影印該書時,技術上有缺點,使它的原貌受損害。所以書的首頁原有“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云云,“難”字出格,竟被沖洗掉了。幸而有呂集義所拍照片在,羅先生據以補上。在我國學術史上,注釋史籍的名家下少,如裴松之注《三國志》,胡三省注《資治通鑒》等等。但在版本方面遭到如此曲這,還是沒有過的。
其二,不斷增訂注釋。
羅先生注《李秀成自述》,“是訓詁與事實的考證并重”。訓古方面,他列舉了十二項:太平天國制度、太平天國的避諱字、太平天國的特殊稱謂、人物、地名、事物、專門名詞、特殊的簡寫字、典故、辭句、方言、鄉土稱謂。事實的考證方面,羅先生列舉了十項:事實錯誤,時間錯誤……等等。總起來說,他疏通了史料的脈絡。只有經過長期積累資料,才能得來這樣的結果。例如,對“沖天炮”的一條注釋,就是不斷增訂的產物。按李秀成說:“十一年正初,由常山動身,上玉山廣信河口而行,到建昌屯扎,攻打二十余日未下,外有清軍來救,是沖天炮李金旸帶兵。”其后又說:“先有沖天炮李金旸帶有清兵十余營屯扎陰岡嶺,我部將譚紹光、蔡元隆、郜永寬等迎戰。兩軍對陣,李金旸兵敗,其將概已被擒,全軍失散,拿其到步。……過了數日,發盤川銀六十余兩,其不受而去江西,后聞被殺。”對“沖天跑李金旸,羅先生在《箋證》的一、二、三版,都未注釋。四版(“增訂本”)始據歐陽兆熊《水窗春囈》注:“沖天炮是李金旸的綽號。”[4]還不能說明問題。以后,羅先生陸續掌握了有關資料,在1982年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里便完整地交待了其人其實。他據《王鑫遺集》里的一篇稟牘弄清沖天炮的來歷:“本是天地會員,在湖南起義,稱統領元帥,后來叛變投相清朝。”又據《曾國藩奏稿·李金旸張光照正法片》及南京圖書館所藏左宗棠給曾國范的一封信,補充說明沖天跑與太平軍戰敗被俘,李秀成釋放了他,走歸南昌自首,左宗棠認為其人兇悍難制,力勸曾國藩“不用則殺”。后來江西巡撫毓科把李金旸解送曾國藩,曾借失律罪將李處斬。[s]這一事實表明,由于充分掌握了沖天炮李金旸的有關資料,羅先生才能給《李秀成自述》這一節內容疏通證明,使讀者了解透徹。而這一點一滴的資料,不是靠一時突擊所能獲得的。正如羅先生自序所說:“四十九年來,好似烏龜爬行一樣,一點一滴地去作注。有些注真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到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卻又自笑無知。[6]從無知到有知,這是長期努力的結果。有的太平天國史老專家如簡又文山對《李秀成自述》作過解釋,但不能做到充分掌握有關資料而造成失誤。例如《李秀成自述》記永安突圍之役說:“姑蘇沖是清朝壽春兵在此把守。”簡又文在《太平軍廣西首義史》里卻曲解“壽春”為人名,說什么“守古蘇沖者為滿將人壽春”[7]云云。后著《太平大國全史》,始加以訂正。[8]羅先生注這條不僅不誤,而且據《剿平粵匪方略》卷十六所載咸豐二年八月初六日兩江總督陸建瀛奏:“前已調派安徽壽春官兵一千名前赴廣西”[9]之語,嚴肅地提供了確鑿的佐證。從這里,也顯示出羅先生對太平天國史料所下的功夫,超越了他的同輩。
眾所周知,為了研究《李秀成自述》,羅先生還遭受到特大的壓力,深受林彪、“四人幫”的政治迫害。然而羅先生以驚人的毅力,度過了“十年浩劫”,繼續積累資料,終于在1982年出版了《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事實證明,羅先生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代太平天國史學的泰山北斗,就是因為他具有鍥而不舍的精神,這是值得我們后學稱頌和學習的。
虛懷若谷
羅先生之所以成為太平天國史的泰斗,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具有“虛懷若谷”的美德。茲舉數事為例:
一、不護短。
從太平天國己未九年起,天王詔旨之前都開列著一個接旨者的名單:“朕詔和甥、福甥、玕胞、達胞、玉胞、秀胞、恩胞、賢胞、輔胞、璋胞、萬侄……”,上述高級官員除“福甥”外,前輩學者已考明了他們的姓名。但“福甥”究是何人,一直沒有明確的答案。1974年,我注釋《洪秀全選集》,判斷其人為蕭朝貴的次子懿王蔣有福。曾向羅先生請教,舉龐際云所藏《李秀成答詞手卷》為證。該卷有曾國藩親書提問太平天國親貴下落的名單,其中列名在幼西王之下的,即:“懿王蔣有福”。羅先生當即取出《手卷》核對后發問:“蕭朝貴之子為何姓蔣?”我答:蕭朝貴之父王親蔣萬興,見《太平天國史料》所錄幼主詔旨。[10]由于父子異姓,所以長子從父姓蕭,次子從祖姓蔣。”羅先先生認為這條詔旨系據向達抄本排印,“蕭”、“蔣”形近,難免差錯。最后,羅先生婉轉地說:“你可以這樣注,但證據還嫌不足。”實際他不同意我的解釋。其后,廣西紫荊山區發現了一座道光二十四年刻石的《建造佛子路碑》,上有太平軍老兄弟傅學賢、蔣萬興等捐錢的記錄。羅先生收到拓本,便放在手邊。1975年底,我又去北京請教,羅先生立即取給我看,并非常高興地說:“你說法有了確證,可以成立了。”于是在羅先生的支持,我繼續找到其它旁證,終于寫成《懿王蔣有福考》,作出了結論。
二、從善如流。
《秀成自述原稿注》出版后,我撰文評介,高度贊揚其巨大功績,并指出小有疵病,建議在再版時修訂。其中說到:“對個別新資料,尚未引用”。如羅先生說:“李秀成所說的天王兩個小子,是第三子光王、第四子明王(據戊午八年頒行的《太平禮制》,其名不詳。”我的文章說:“其實,天王洪秀全的兩個小子,一名天光,一名天明,見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幼天王自述》,已經蕭一山《清代通史》公布。”隔了一年多,1985年1月,我偕同張一文同志謁見羅先生。他新病初愈,當著初見面的一文同志向我道謝,興高采烈地說:“你幫助我知道了原來不知道的事情。”其實,以掌握太平天國史料而論,我比起羅先生來,不過如滄海之一粟而已.羅先生的謙抑,令我深愧!
三、不委過。
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太平天國文書匯編》。據浙江省博物館藏原抄件著錄太平天國東陽縣卒長汪文明所遺下的“稟”和“呈”以及“批示”,共三十件。我據內容判斷,這批文書的后十四件乃是清朝的地方公牘,不是太平天國的文書。最顯著的證據是:前十六件凡王姓一律改汪姓,而后十四件卻不避諱“王”字。前十六件稱地方官為大人,而后十四件卻稱“太爺”或“青天大老爺”,不避諱“爺”字。1980年,我撰《東陽文書考辨》[18]寄給羅先生。羅先生立即復信承認疏誤,并準備公開作自我批評。稍后我到北京,面懇不要這樣,他才沒有寫文章。其實,該書雖由羅先生主編,但以后補進了不少新資料,是由別的同志經手的。由于羅先生不愿委過于人,所以他一肩承擔了責任。
四,有功不居。
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洪秀全選集》,輯錄了一篇《整頓屬員詔》。我注釋,“扁員,即屬員。‘廁’是太平天國用的—個簡化字。太平天國制度,屬員由各將領保舉”。[14]這全是羅先生教給我的。原來,我誤解“屬員”為病員。羅先生給糾正了,但以后他從來不提此事,不讓人知道這是他教給我的。
所有這些,只有用“虛懷若谷”四字才能加以概括。如如果羅先生單具有“鍥而不舍”的精神,而沒有“虛懷若谷”的美德,那還不可能受到學術界如此景仰。正因為這樣,所以羅先生的史德更值得后學稱頌和學習。
羅先生以六十年的工夫,經歷重重困難,為太平天國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際斯盛世,我圣賢廣大年輕的后一代必將繼承和發揚羅先生的業績,做出更大的貢獻。
注:
[1]《太平天國史料》(開明版) 111頁。
[2]《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1期。
[3] 郭沫若:《<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序》
[4] 詳見中華書局版《水窗春囈》5—6頁。
[5] 見(李秀成自述原稿注》245頁。
[6]同上書17頁。
[7]《太平軍廣西首義史》276頁。
[8]見《太平天國全史》上冊327頁。
[9]見《李秀成自述原稿注》96—97頁。
[10]見《太平天國史料》(開明版)104頁。
[11]見《太平天國學刊·第一輯》261頁。
[12]見《中學歷史)1983年第4期。
[13]此文已輯入《太平天國學刊·第二輯》。
[14]《洪秀全選集》7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