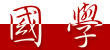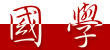近著《人心與人生》于第七章中曾自述其對人類心理之認識前后轉變不同,因亦言及其
人生思想嘗有三期之不同:(1)近代西洋功利主義思想,(2)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3) 中國古時的儒家思想;顧未遑道其間轉變由來。茲用申述其概略如次。
第一期思想與近代西洋功利主義同符
今以暮年追憶早年之事,其時期段落難于記憶分明,大約十歲以后,二十歲以前,可說
為第一期。此期主要受先父思想之影響,以利害得失來說明是非善惡,亦即以是非善惡 隸屬于利害得失之下也。認為人生要歸于去苦、就樂、趨利、避害而已。是非善惡者,
社會之公名,從其取舍標示其所尚與所恥,而離開利害得失又何有取舍恥尚乎?此一哲 學思維,與西歐邊沁、穆勒諸家為近,原非吾父所有,而出于我的頭腦。然父實啟導之
。
愚生于1893年,即甲午中日戰爭前一年。國難于此,既日亟矣;先父憂國之心于此彌切 。尋中國所以積弱不振,父謂是文人之所誤。“文人”指讀書人居于社會領導地位而什
九唯務虛文,不講實學。說話,不說實話(虛夸);做事,不做實事,循此不改,不亡其 國不止。反觀西人所以致富強者,豈有他哉?亦唯講實學,辦實事而已。東鄰日本蕞爾
小國,竟一戰勝我者,亦唯其步趨西洋求實之效耳。凡此“實學”“實事”之云,胥指 其用實用者。(1)(清季北京有私立“求實中學堂”,又有國立的“高等實業學堂”。此
高等實業學堂入民國后改稱“工業專門學校”,蓋其內容正是講習工礦業各門學術也。 此可見當年吾父識見未有大異于時流,獨以吾父為人感情真摯,一言一行之不茍乃非一
般人所及耳。)此種實用主義或實利主義,恒隨時見于吾父一言一行之間,而在我繞膝 趨庭日夕感染中。此即此期思想形成之由來。(2)(先父生平言論行事極近古代墨家一流
,亦似與清初之顏(元)李(王+恭)學派多同其主張。然實激于時勢輒有自己的思想,初 非有所承受于前人。)
轉入古印度的出世思想為第二期
功利主義對于人生是肯定其欲望的。徑直可以說,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人生不就 是在欲望的滿足或不滿足中度過乎?然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卻與此相反,恰好是完全否
定欲望的,亦即根本否定人生的。我如何竟從功利主義一轉而抱出世思想呢?
我生來有一好用思想的頭腦,因而于所謂利害得失者不囫圇吞棗,而必究問其詞之內涵 果何所指?利害云,得失云,非二事也;異其名,同其實。核求其實,則最后歸著當不
外苦與樂乎?苦與樂是人生所切實感受者。人之趨利避害亦在去苦就樂耳。利害得失信 非必就個體生命而言之,然一家一國乃至世界范圍的利害得失,其最后結果不仍歸落在
其人的苦樂感受上耶?
于是又當究問:何謂苦?何謂樂?我乃發現一真理曰:苦樂不在外境。通俗觀念恒以苦樂 聯系于外境,謂處富貴則樂,處貧賤則苦。因為人類仰賴外在物資而生活,物資之富有
或貧乏就決定著生活欲望之易得滿足或不易滿足,而人當所欲得遂時則樂,所欲不遂時 則苦也。——這自然不是沒有理由的,卻有一種淆亂錯誤隱伏其間。
“所欲得遂則樂,所欲不遂則苦”這兩句話是很好的概括,即可據為準則以事衡論。欲 望出自主觀,其或遂或不遂則視乎客觀際遇;是故苦樂殊非片面地從主觀或片面地從客
觀所得而言之者。凡指目任何一種外境為苦,或指目任何一種外境為樂,如世俗流行的 觀念都是欠分析不正確的。苦樂問題于其著重在外境來看,不如著重在吾人主觀方面猶
為近真——較為接近事實。試申論之如次——
欲望通常表見于吾人意識上,而欲望之本則在此身。苦樂之直接感受在此身,卻每因通 過意識而大有變化:或加強,或減弱,甚或苦樂互相轉易。此常識所有而必須提出注意
者一。注意及此,便知苦樂不定在外境矣。欲望在人不是呆定的,一欲望過去,一欲望 就來,層出不窮,逐有增高。此又必注意者二。注意及此,便知千金之子所欲不在千金
,而別有其所欲;所欲不遂之苦,在彼亦同乎一般人耳。一般貧人豈無其遂心之時;彼 富貴人亦自有其苦惱之事;善觀其通,則平等,平等。又個性不相同的人其欲望不相同
,其感受不相同;欲望感受既隨從乎人的個性不一,便往往難于捉摸。此又必注意者三 。注意及此,便知從外境而妄臆其人之苦樂,是不免混淆錯誤的。
研究思辨至此,又得一結論曰:人生基本是苦的。試看,人生從一墮地便帶來了種種缺 乏(缺食、缺衣、缺……),或說帶來了一連串待解決的問題;此即欲望之本,而苦亦即
在是焉。苦非缺乏不得其滿足之謂乎?苦非問題不得其解決之謂乎?很明白,苦是與生俱 來的。試再看,人之一生多得其所欲之滿足乎?抑不得之時為常耶?顯明的是不得之為常
也。歷來不是有不少自殺的人嗎?加以曾懷自殺之念者合計之,為數就更多。凡此非謂 其生之不足戀而苦之非所堪乎?勿謂人類文明日進,所缺乏者將進為豐富,許多問題可
從科學技術得其解決也。章太炎先生“俱分進化論”最有卓見(1)(《俱分進化論》一文 ,我于六十年前讀之深為佩服。今檢《章氏叢書》內《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二可得。
),指出遠從原始生物以來其苦樂皆相聯并進的。特如高等動物至于人類,其所有之樂 愈進,其所有苦亦愈進,事例詳明,足以戡破世俗之惑。
你莫以為人類所遇到的問題,經人類一天一天去解決,便一天從容似一天也。我告訴你 :所謂問題的解決,除掉引入一更高更難的問題外沒有他義。其最后便將引到一個無由
解決的問題為止。什么無由解決的問題?要生活而不要老死,就是個無由解決的問題。( 2)(此義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小字本第105頁。原文略云:宇宙不是恒在而是相續;
相續即無常矣,而吾人則欲得宇宙(此身生命)于無常之外,于情乃安,此絕途也。)。
一切問題原都出自人類生命本身而不在外面;但人們卻總向外面去求解決。這實在是最 普泛最根本的錯誤!放眼來看,有誰明見到此呢?恐怕只有佛家了。其余的諸子百家,古
今中外一切圣哲,盡你們存心解救生民苦難,而所走的路子卻全沒有脫出這根本錯誤之 外,都是不足取的。于是我此時一轉而趨向古印度人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思想。我當時
初非受了佛家影響而傾慕出世的,乃是自家思想上追尋到此一步,然后覓取佛典來參考 學習,漸漸深入其中的。(3)(我對于苦樂之分析、觀察、思索、體驗,蓋始于十四五歲
時。參加辛亥革命后即結念出世,從琉璃廠有正書局覓得佛典及上海出版之《佛學叢報 》讀之。其時前青廠有一處圖書分館亦藏有佛經,恒往借讀。凡此處所述早年出世思想
,具見1914年夏間所撰《究元決疑論》一長文。此文先刊出于商務印書館之《東方雜志 》,后收入《東方文庫》為一單行本。)
“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那種看法,此時并未改變;只不過由肯定欲望者,一變而判認 欲望是迷妄。慨嘆人生不外是迷妄苦惱的一回事,誠如佛家之所說:起惑,造業,受苦
。
再轉而歸落到中國儒家思想為第三期
大約1911年后1920年前,都是我志切出家入山之時;雖以老父在,未即出家,而已守佛 戒茹素不婚。后來我在清理先父遺筆手澤時(1925年春)所撰《思親記》一文,有如下的
幾句話:
漱溟自元年(指民國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 矜尚遠西;于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尤大傷公之心。(下略)(原文
見《桂林梁先生遺書》卷首)
我轉歸儒家思想之晚,即此可證。
我于1920年冬放棄出家之念,于1921年冬末結婚,所以第三期思想應從1920年算想。在 思想上如何起變化的呢?略說如次——
當我幼時開蒙讀書,正值吾父痛心國難之時,就教我讀《地球韻言》一類的書,俾知曉 世界大勢,而未曾要我讀“四書五經”。其后入小學,進中學,讀一些教科書,終竟置
中國古經書未讀。古經書在我,只是像翻閱報刊那樣,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閱讀的。
經典各書的古文字,自己識解不易,于其義理多不甚了然;唯《論語》《孟子》上的話 卻不難通曉。特使我思想上有新感受者是在《論語》。全部《論語》通體不見一苦字。
相反地,辟頭就出現悅樂字樣。其后,樂之一字隨在而見,語氣自然,神情和易,僂指 難計其數,不能不引起我的思尋研味。卒之,糾正了過去對于人生某些錯誤看法,而逐
漸有其正確認識。
頭腦中研尋曲折過程不可殫述,今言其覺悟所在。我覺悟到欲望之本,信在此身;但吾 心則是卓越乎其身而能為身之主宰的。從而吾人非定然要墮陷糾纏在欲望里。何以見得
?即于此出思想而可見。
語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非即本于身體構造而來者乎?此伏表著個體存活和 種族蕃衍兩大欲求,固為一切生物之通性,莫能有外。但在生物進化途程上,人類遠高
于一切,其所欲望乃大不簡單,幾于千變萬化不可方物。然直接間接,若近若遠,何莫 非自此身衍出者?唯獨置此身欲望于反省批判否定之中的出世思想卻明白地超越此身了
。此非以我有自覺能反省而不為身所掩蓋之心乎?唯人有人生觀,而牛馬卻不能有牛生 觀馬生觀;彼諸動物豈曰無心哉,顧惜其心錮于其身,心只為身用耳。此一分別不同,
則緣于脊椎動物頭腦逐漸發達,至于人類而大腦乃特殊發達,實為其物質基礎。儒書云 “形色,天性也;唯圣人然后可以踐形”。又云“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這些說話證以今日科學家言,便見其字字都有著落(1)(此處所引古語, 均出《孟子》書中。形色指身體說。人類生命托于大腦特別發達之身體構造而有其種種
活動;凡天賦之性能(不斷成長發展的)即在是焉。大腦者,人心之所寄;而一切性能則 統于人心。人所區別于禽獸者,從其見于形體構造上說是很小的,從其無形可見之心理
性能上說,則似乎不大,卻又是很大的。說區別不大者,人與禽獸的生活詎非同趨于為 生存及傳種而活動乎?又說很大者,人心超卓于其身體而為之主,禽獸卻不足語此也。
然人心之超卓于其身體,只是其性質上之所可能,初非固定如是;在一般人(庶民)的生 活上,其流于“心為形役”者乃是常事,曾何以異于其他動物?大約只有少數人(君子)
不失此差距耳。真正充分發揮人類身心的偉大可能性(偉大作用),那就是圣人。近著《 人心與人生》說此較詳,可參看。)。儒家之學原不外是人類踐形盡性之學也。
人非定糾纏于欲望,則亦非恒在苦中而已耳;儒家之樂又何自來乎?前說“所欲得遂則 樂,所欲不遂則苦”者,應知是片面之見,未盡得其真際。苦樂真際視乎生命之流暢與
否。一言以盡之:生命流暢自如則樂,反之,頓滯一處則苦。說苦樂之視乎其所欲遂不 遂也,蓋就一般人恒系乎外來剌激之變換以助其生命流暢者言之耳。外在條件長時不變
,其樂即轉為苦矣;此不難取驗于日常生活事實者。人們欲望所以層出不窮,逐有增高 者,正為此也。有道之士——得乎生命自然流暢之道者——更不須待外來剌激,固可以
無時而不樂。
后世如宋儒,每言“尋孔顏樂處”。明儒王心齋更作有《樂學歌》云:
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見《明儒學案》中《泰州學案 》一章)
王氏又云“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其云“有事”者, 指此心有所掛礙,即失其流暢也。其云“無事”者,指此心隨感而應,過而不留也。此
樂是深造自得之樂,與彼有所得于外之樂迥然兩回事,恰為生活上兩條脈絡。
前后綜合起來,人生蓋有三條路向:
一、肯定欲望,肯定人生;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
二、欲望出在眾生的迷妄;否定欲望,否定一切眾生生活,從而人生同在否定之中。
三、人類不同于其他動物,有卓然不落于欲望窠臼之可能;于是乃肯定人生而排斥欲望 。
儒家自來嚴“義”“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者,蓋皆所以辨別人禽也。
1920年講于北京大學,次年出版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即以此三條路向或云三 種人生態度為其立論之本,謂儒家、佛家之學從人類生活發展變化歷史途程上看,實皆
人類未來文化之早熟品;瞻望前途,中國文化即將在最近未來復興于世界。自己既歸宿 于儒家思想,且愿再創宋明人講學之風——特有取于泰州學派之大眾化的學風——與現
代的社會運動融合為一事。其詳具見原書,茲不多及。后此我之從事鄉村運動即是實踐 其所言。
1969年國慶節前屬草,10月21日草成。
附: 我早年思想演變的一大關鍵
往年舊稿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茲略有補充,題曰:我早年思想演變的 一大關鍵。
此一大關鍵者,即在我幼年以至少年時,先父未曾教我一讀儒書是也。距今七八十年前 的老社會一般開蒙讀書,通是誦讀《論語》、《孟子》、《詩經》、《書經》一類古籍
,況在世代詩禮仕宦人家如我家者乎。先父之為教卻破例地不如是。先父之意蓋謂童稚 之年不曉其間義理,且容后圖。于是我讀書入手即讀上海出版之教科書。信如《自述早
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中所說:古經書在我只是像翻閱報刊那樣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閱 讀的。我在思想上既未先蒙受儒家影響,而從我好為觀察思索的頭腦,不期而竟自走入
佛家厭世出世一路去了。
對于人生苦樂的留心觀察,是我出世思想的開竅由來,從而奠定了此后一生歸宿于佛法 。蓋認定“人生是苦”實為古印度社會的一種風氣,是即其所以產生佛法者;而我從少
年時思想上便傾心于佛家者亦正在此。
然而從來為中國社會文化之正脈的主流的儒家孔門思想理趣,恰恰與此相反。試看往時 人人必讀的《論語》一書,既以“子曰不亦樂乎”開頭,而且全部《論語》都貫串著一
種和樂的人生觀——一種謹慎地樂觀態度。如云: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貧而樂;飯疏 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如是等等。此
其顯示出來的氣氛又何等不同!宜乎后儒便有“尋孔顏樂處”之倡導了。
正是由于我懷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發現先儒這般人生意趣,對照起來頓有新鮮 之感,乃恍然識得中印兩方文化文明之為兩大派系,合起來西洋近代基督教的宗教改革
下發展著現世幸福的社會風尚,豈不昭昭然其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體系?
假使我循舊社會常例先讀儒書《論語》,早接觸得夙來的中國式人生意趣,那么,我將 不易覺察世界有如上三方社會人生文化文明之劃然各具有特色異彩的。我或將囿于見聞
之一偏而從吾所好;或將疏忽漠視此其間的分異焉。此所以早年未讀儒書實為我思想演 變上一大關鍵也。
1921年我第一部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即寫成于上述思路之上。
附注:翻譯西文求其信、達、雅非易。蓋中文西文之間難得相當適合之詞匯也。上篇文 內文明、文化兩詞不惜重疊用之,蓋以文明譯
Civiliztion 而以文化譯 Culture,若 從中文簡潔以求,固所不宜。
(寫作于1969年,初次發表于1979年
《中國哲學》第一輯。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