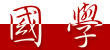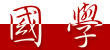一九一九年我任北京大學(xué)講席時(shí),忽接得熊先生從天津南開中學(xué)寄來一明信片,略云,
你在《東方雜志》上發(fā)表的《究元決疑論》一文,我見到了,其中罵我的話卻不錯(cuò);希望有 機(jī)會(huì)晤面仔細(xì)談?wù)劇2痪茫鲗W(xué)校放暑假,先生到京,借居廣濟(jì)寺內(nèi),遂得把握快談——此
便是彼此結(jié)交端始。
事情的緣起,是民國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編的《庸言》雜志某期,刊出熊先生寫的札記內(nèi)
有指斥佛家的話。他說佛家談空,使人流蕩失守,而我在《究元決疑論》中則評議古今中外 諸子百家,獨(dú)推崇佛法,而指名說: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無知云云。
因此,見面交談,一入手便是討論佛氏之教,其結(jié)果便是我勸他研究佛學(xué),而得他同意 首肯。不多日,熊先生即出京回德安去了。
一九二○年(民國九年)暑期我訪問南京支那內(nèi)學(xué)院,向歐陽竟無大師求教,同時(shí)即介紹
熊先生入院求學(xué),熊先生的佛學(xué)研究由此開端。他便是從江西德安到南京的。附帶說,此次 或翌年,我還先后介紹了王恩洋、朱謙之兩人求學(xué)內(nèi)院。朱未久留即去;王則留下深造,大
有成就,后此曾名揚(yáng)海外南洋云。
我入北大開講印度哲學(xué)始于一九一七年,后來增講佛家唯識之學(xué),寫出《唯識述義》第
一第二兩小冊。因顧慮自己有無知妄談之處,未敢續(xù)出第三冊。夙仰內(nèi)學(xué)院擅講法相唯識之 學(xué),征得蔡校長同意,我特赴內(nèi)學(xué)院要延聘一位講師北來。初意在聘請呂秋逸君,惜歐陽先生以呂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時(shí)熊先生住內(nèi)學(xué)院約計(jì)首尾有三年(一九
二○——一九二二年),度必飫聞此學(xué),我遂改計(jì)邀熊先生來北大主講唯識。 豈知我設(shè)想者完全錯(cuò)了!錯(cuò)在我對熊先生缺乏認(rèn)識。我自己小心謹(jǐn)慎,唯恐講錯(cuò)了古人
學(xué)問,乃去聘請內(nèi)行專家;不料想熊先生是才氣橫溢的豪杰,雖從學(xué)于內(nèi)學(xué)院而思想?yún)s不因襲之。一到北大講課就標(biāo)出《新唯識論》來,不守故常,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事情到此地
步,我束手無計(jì)。好在蔡校長從來是兼容并包的,亦就相安下去。 熊先生此時(shí)與南京支那內(nèi)學(xué)院通訊中,竟然揭陳他的新論,立刻遭到駁斥。彼此論辯往
復(fù)頗久,這里不加敘述。我自審無真知灼見,從來不敢贊一詞。 計(jì)從一九二二年熊先生北來后,與從游于我的黃艮庸王平叔等多人,朝夕同處者歷有多
年。一九二四年夏我辭北大,應(yīng)邀去山東曹州講學(xué),先生亦辭北大同往;翌年我偕諸友回京,先生也是同回的。居處每有轉(zhuǎn)移,先生與我等均相從不離,其事例不必悉數(shù)。然而蹤跡上
四十年間雖少有別離,但由于先生與我彼此性格不同,雖同一傾心東方古人之學(xué),而在治學(xué) 談學(xué)上卻難契合無間。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書我必先睹。我讀之,曾深深嘆服,摘錄為《
熊著選粹》一冊以示后學(xué)。但讀后,心有不謂然者復(fù)甚多,感受殊不同。于是寫出《讀熊著各書書后》一文甚長,縷縷陳其所見!
如我所見,熊先生精力壯盛時(shí),不少傳世之作。比及暮年則意氣自雄,時(shí)有差錯(cuò),藐視
一切,不惜詆斥昔賢。例如《體用論》、《明心篇》、《乾坤演》,即其著筆行文的拖拉冗 復(fù),不即征見出思想意識的混亂支離乎。吾在《書后》一文中,分別的或致其誠服崇敬,又
或指摘之,而慨嘆其荒唐,要皆忠于學(xué)術(shù)也。學(xué)術(shù)天下公器,忠于學(xué)術(shù)即吾所以忠于先生。 吾不敢有負(fù)于四十年交誼也。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