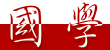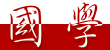|
□金克木
眼前道路無經緯,皮里春秋空黑黃
——薛寶釵
■聽說你近來看了幾本新書,又有了不同尋常的怪論,是不是?
□這是你聽來的,不是我說出的。
■那么你現在說說,好不好?
口我要說的不見得是你要聽的。你聽去的也未必是我說出的。對話不容易。現在有人進行問答,如同接見記者或口試,這不是對話。有的雙方經過別人翻譯,成為三人雙重對話。還有的仿佛是對話而實際是聾子對話,各說各的。也有的進行辯論,不聾了,仍舊是各說各的。我們能不能對話而不屬于這幾種?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柏拉圖式和狄德羅式的對話,或則《論語》式、《孟子》式、《金剛經》式等等對話。恐怕你說的那幾種還不能概括。
口概括?談何容易。現在很多人談論中外文化;又有人進行中外對比,說是比較文化;都未必能概括所說的對象。有時看來有點象比較三角形和正方形,或則比較空氣和靈魂。各比其所比,各有巧妙不同。
■不論怎么說,講文化的定性、變革、動向,總是反映世界上文化“交會”時產生的所謂“張力”(或說矛盾激化)吧?這是世界性的世紀末的焦灼狀態。各國論文化者的目光都是從本國望到世界,或則從外國望到本國;講的也許是往古,眼光卻遙指下一世紀。不論講得多么抽象或超然,總會有狐貍尾巴在隱隱現現。
口上個世紀末歐洲有文學中的“世紀末”頹廢派。現在不是頹廢而是惶惑。世界上的人,不論生活圈子大小,眼光遠近,地位高低,恐怕是不安的多而安的少。不過有的人是自安于不安,不覺得。也有人喜歡別人不安,惟恐天下不亂,可并不想亂自己,結果卻往往是事與愿違。
■你不由自主又在概括了。也許是歐洲人喜歡分析而中國人喜歡概括吧?
口你也是在概括,自己證明自己的話,你也是中國人。
■你也是中國人。那么,你對世界文化也會有概括看法吧?
口請問,怎么講文化?是照符號學或則結構主義的路子,還是照詮釋學(解說學)或則存在主義的路子?現在又在吵什么解構主義,是想打破這兩種路子,好象還沒有定型。前進了一些,提出了新問題,作了新探索,甚至文體也有新花樣(如法國人德里達),不過還是可以用前面兩條路子概括吧?至于實用主義,那是到處都有的,不在話下。
■據我看,國際上討論的主題是客觀性,問題在語言和思想。據我所知,法國人黎克爾想打通一條合二而一的新路子,但仍是偏于一方。他將弗洛伊德化為“玄學鬼”,好象是企圖把本世紀的各種思潮,語言學、心理學、物理學,包括相對論、量子論和格式塔理論等等都納入一個思想體系。看來喜歡概括的不僅是中國人。你我前面說的不準確。
口可以有種種概括法。我想從思想傳統來概括。目前世界上爭論文化和哲學的都著眼于傳統。德國伽達默和法國德里達都解說過傳統。結構主義人類學者法國列維-斯特勞斯的概括原始社會思想也是追溯傳統。傳統是指傳到今天的。這是逃不出也割不斷的,仿佛如來佛的手掌心,孫悟空一筋斗翻出十萬八千里也出不去。因為這不僅僅是在時間和空間的量度之內的。現在外國人提出的“語言先于思想”(伽達默)或則“書寫先于文字”(德里達)的問題,仍然是客觀性(結構、系統)或則主觀性(主體、意識)的問題。這也是如何看待傳統的問題。這樣說有點玄虛。外國人照他們的參照系說話,對于中國人又隔了一層。加上或則換上中國傳統哲學說法也會同樣玄虛。我們還是用普通人的語言來談吧。
■普通就是尋常,也就是一般,這也是概括。
口概括文化,劃分類型,雖然出于本世紀,也是古典或古董了。我們為了從所謂東西文化或則中外文化的說法稍稍前進一步,不妨在世界文化中概括出大類型。我看可以概括出三個(當然不能包羅一切)。這是很普通的看法,但也不是持各種觀點的人都承認的,只算是概括的一種吧。這三型是:一、希伯來——阿拉伯型。二、希臘——印度型。三、中國——日本型。
■你說的這三型毫不新鮮。聽聽你的解說。
口三型名稱只是符號,并不是說中國人個個必屬于中國型。三型中可以用第一型為標尺。這一型中的要點是:一、上帝。有一個上帝創造世界和人,主宰一切。二、原罪。人類始祖違反上帝禁令,被逐出樂園。從此人類有了后代,個個人生下就有罪。要到世界末日審判時才能回樂園和上帝再到一起。三、靈魂。每人都是上帝創造的靈魂。靈魂是不會消滅的。四、救世主。上帝為拯救人類使世上出現救世主(彌賽亞、基督、先知),信仰他的人得救。信仰不需要講道理。五、“選民”。人類中有的人,例如猶太人,或則信仰基督耶穌的人,信仰先知穆罕默德的人,是上帝的“選民”,受到上帝特殊眷顧,是從樂園來又回樂園去的。其他人屬于另一種。這一文化型可以把猶太教、基督教各派、伊斯蘭教兩派、一直到上帝教都概括在內。這種文化可說是有上帝和一元的文化。
■我可以由此推出第二型。那是無上帝和多元的文化。所謂上帝是指創造一切并主宰一切而又獨一無二的上帝。古希臘和印度都沒有這一類型的上帝。他們的神不是上帝,管不了什么事,而且多得很,互不相下。他們的神都很快樂。人也不是生來有罪命定吃苦而是以享樂為第一要義的。希臘神話、宗教和哲學以及印度教各派、耆那教兩派都是這樣。佛教也是這樣,有過去、現在、未來(這三個原詞都是印度字)三世佛。佛多得不計其數。說一切是苦,只因以樂為標準。苦不是第一義。樂不了,才處處覺苦,力求從苦中解脫,“往生極樂世界”。沒有靈魂、原罪、救世主、“選民”。無論阿彌陀佛或則觀世音菩薩都是要你誦他的稱號。聞聲救苦,不叫就不見得會應了。神、佛、菩薩、耆那(大雄)和救世主的意義不同。“我”、命”和靈魂也不同,仿佛是沒有個性的。
口這兩型都要用宗教語言說,因為各種形態的宗教歷來是文化的綜合表現,最為普及。可是文化并不只有宗教形式。文化是遍及各方面的。“上帝、救世主、選民”不是都采取宗教形式和名稱的。靈魂可化為意識、自我、主體、存在等等,哲學家一直追問到今天。“樂園——世界——樂園”的公式,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也沒能逃出去。這兩型文化的想法對立而問題共同,所以可以用第一為標尺而說第二。若以第二為標尺,以印度為準,那就要首先提出循環論。世界是無始無終的。有始有終的世界是要循環、要重復的。循環的宇宙有始終而又無始終,“如環無端”。人也是要“輪回”的,生而復死,死而復生。希臘只講人神相混,無始無終。不重循環而重還原,另有發展。希臘講的智和印度講的智不同,但都不是信仰。重還原,于是哲學上有柏拉圖、亞理士多德以至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等人的種種宇宙解說。他們都從外而內,從現象到本質,由二元、多元追一元。印度講循環也是說明多面實一,無窮而有限。他們說的不是希伯來——阿拉伯那樣的由上帝而人再由人而上帝的循環,而是生老病死、成住壞空這樣的循環。這一文化傳統并沒有隨古希臘、羅馬滅亡,仍散在各處,不限于印度,特別是在哲學思想中。
■中國——日本文化為什么列為第三型?看來好象是前二型的混合。用第一型作標尺來看,這一型更原始些,還沒有達到第二型,更沒有達到第一型。
口十九世紀歐美人從基督教觀點出發持有這種進化論的看法。近代印度也有不少人受其影響,極力把印度傳統文化的多神解說為一神,但并不成功。二十世紀中對所謂原始社會思想的看法改變了。野蠻未必低,文明未必高。十八世紀的盧梭講復歸自然,并不是倒退而是前進。現在對原始文化改變看法也不只是歷史的如實還原而是要前進。大家看到了文明的德國暴露出納粹的野蠻。現在的人忽然大講傳統,有兩種情況:一是保衛被破壞的,一是去破壞現存的。兩者都可以打出傳統的招牌。其實革新也有類似情形:有的是迎新,有的是復舊。兩者都可以打出新招牌要求改變現狀,和打出傳統招牌一樣。
■仍以第一型為標尺,這第三型該怎么解說?
口說中國——日本型,因為日本已有不少發展而中國也正在變化,只說中國概括不下日本。這一型的文化也同第一型對立,卻又不是第二型。簡單說,中國是無上帝而有上帝,一而又多,多而歸一。也許正因此你說看來好象是前二型的混合或則未完成,其實是另一類型。中國沒有創世兼主宰的上帝,但是又有不固定的上帝。中國是把前二型中分為雙重或則三重的都歸入人間。樂園和地獄都在現世,可以“現世現報”,從根本上改變了印度的報應說。可以“魂飛魄散”,又從根本上否定了不滅的靈魂。中國可以收容前二型,但必加以改變,因為自有一型。中國重現世,因此重人,可是中國傳統說的“人”不等于前二型文化所認為的人。第一型的人是歸屬上帝的靈魂,大家都有原罪。第二型的人是無拘無束各自獨立或則各自困在“業報”中一切注定的人。中國的是另一種“人”。有些歐洲語和印度語中有不止一個人字,而漢語中只有一個。“人格”、“人道”,中國沒有相應的傳統詞,只好新造或用舊詞改新義。在社會表現中,對待人的中國的律、刑決不等同于羅馬和歐美的法,也不是印度的“法”(佛“法”、“法”論)。中國的禮、俗也不相當于歐美的法。不能把同類作為相等。中國的“心”、“物”在哲學中和歐洲的、印度的都不相同,因為文化中的“人”不一樣。在中外對話中恐怕不止是人、心、物、法這幾個詞各講各的,還有別的詞,由于意義有差別,也是對話的障礙。我們往往只見其同,不見其異。例如“對話”就可以不專指兩人相對講話,其中有歧義。
■所以不僅要研究正解,還有必要研究“誤”解。為了破除中外對話的障礙,找不到共同語言,只好用彼此了解的對方語言。一個講英語,一個講日語,雙方又不能共用法、德、俄語,只好是講英語的懂日語,講日語的懂英語。那樣,各講各的,可是又各自懂得對方說的是什么。中國家庭中有夫婦各講自己方言終身不改的。
口可是要懂得對方必然要有個翻譯過程,或則說是自己不覺得跳過去又跳回來的過程。對傳統文化也是這樣。我們要能把傳統文化用兩種語言解說,要能同傳統“對話”。
■文化范圍太廣,還是縮小到可以擴充為文化的哲學思想核心吧。不過我們不是還原古人怎么想,而是問古人想的和講的現在怎么樣。這是傳到今天的傳統。然后,傳統語言化為今天語言,中國語言又化為外國語言。這是現在和過去的對話,又是中外對話。由解說而了解,又由了解而解說;由主觀到客觀(文本、原作者),又由客觀回到主觀(解說者)。這個循環過程是對話過程,也是思考過程,又是轉化過程。從書本理論到實際行動也是這樣一個循環過程。在解說之中,從符號到意義,得出代碼本結構,再由符號體系到意義體系。由部分到全體,又回到部分。由語言到意義,又回到語言。如此等等,都是日常不知不覺進行的對話和循環過程。隱喻意義不同于符號意義;還有“剩余意義”和言外之意。象征不同于符號。象征既是能指,又是所指。例如神像不是神,卻等于神,同樣不可觸犯。“故居”的意義往往是新居,有新意義。如果照這樣進行對傳統文化思想的“翻譯”對話過程,那么我們對中國文化可以挑選什么書著手?
口照這種途徑,我覺得有四個對象是有中國兼世界意義的,可是被忽略很久了,不妨由此著手。已經有國內外討論的大題目不在內。這可以說是四種學吧。一是公羊學。二是南華學。三是法華學。四是陽明學。
■這不正是儒、釋、道的史學、哲學、宗教學、政治學嗎?這是現在還存在的傳統嗎?難道要把這四者說成讀史之學、處世之學、傳教之學、經世之學嗎?
口還不僅如此。《春秋公羊傳》既是漢朝今文經學的要籍,又是清朝龔自珍、康有為等改革派想復興或改造的經典。書的內容是史論,制度論,又是表現詮釋文本的方法,又是由口傳而筆錄的對話及思考過程的文體。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書。古今解說不少,還需要現代解說。“尊王”思想在日本明治維新中起過作用。“大一統”(不僅原意)的說法我們現在還在用。既有歷史意義,又有現代意義,可作很多新解說。《南華經》即《莊子》,正是現在國際間哲學語言中所謂“寓言”、“隱喻”、“轉義”的書。《逍遙游》、《齊物論》,古今有多少解說和應用?不久前還在人們口上說和心中想。就其意義的多層復雜和文化影響的巨大說,豈止是道教的主要經典?是否可以說是一部流行的處世秘訣?其中的宇宙觀也未必不能象《老子》那樣和現代天文學及物理學掛鉤。《法華經》全名《妙法蓮華經》,原文本的語言是文白夾雜,內容是包羅萬象,和印度孔雀王朝佛教之間有很大距離,可能是公元前后南亞次大陸西北部由大月氏人建立的貴霜王國的流行讀物。書由西域進入中原,鳩摩羅什的譯本傳誦極廣,一直傳到日本。其中的“三乘”歸一(三教合一)以及觀世音(包公、濟公、俠客)聞聲救苦是中國文化思想的一部分。古今以至全世界研究的人很多,也有用現代方法解說的,但是中國還缺乏以現代“語言”作新解說。至于王陽明(守仁),近來才在國內有人提到,不以唯心論而摒棄。王學是有大眾影響的。日本明治維新志士曾應用王學。在明末清初衰落,實際上暗地仍有發展。不但由他可以上溯朱熹、陸九淵直到漢代的《大學》,而且可以由他的“知行合一”下接孫中山的“知難行易”。他提出四句話:“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用,知善知惡是良知,行善去惡是格物。”這里面“無、有,心、物,體、用,善、惡,知、行”五對哲學基本范疇都有了。“物、心”對上了“天、人”。他說的“心”指什么?“良知”指什么?從前人人都會說“憑良心”,這是什么意思?他為什么這樣說?對什么人說話?有什么影響?就這個人說,他既作高官,又被貶謫到最低層;能文、能武;有儒、有禪;既重事功,又講義理;具有中國人心目中的諸葛亮式格局,卻不是柏拉圖的“哲學王”。
■這也是第三型文化和前兩型相區別的一個要點吧?不但又合(一)、又分(多),又常、又變;而且又文、又武,贊美文武雙全的風流儒將。象中國這樣的多戰爭、善兵法、長于武術而又重文的文化,世界少有。
口中國“人”的理想形態,既不同于希伯來的“選民”,也不同于希臘和印度的“英雄”。王陽明屬于這種孔子(至圣先師)式的具體而微的“完人”(包括缺點),也屬于神化的老子(太上老君)式的“仙人”(包括俗氣)。還有一點,陽明學要研究的“上下文”是,上承秦、漢、唐、宋、元,下啟清代、民國的明代的關鍵時期(十五、十六世紀)的文化和思想。這也是全世界文化大匯合、大轉變時期。(十五世紀末哥倫布到美洲,發現“新大陸”。)至于王守仁這個人的是非功罪、高大或渺小,那是另一問題。提出這四部書,講的是學,是思想和文化,不限于書本及其作者。《傳習錄》和《大學問》并不是王陽明自己作的書,是他的學生記的。
■至于這些在今天中國的文化思想中還有沒有,是什么形態,起什么作用,和現代化有什么關系;若消滅了,那又是為什么;這些更是另一層的問題了。我們的“三型”、“四學”就談到這里吧。
口我們的對話是一個思考過程。意見不一定正確,總算是一個思考結果吧。
(本文為金克木先生訪談,原文載自《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