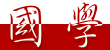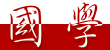|
□金克木
作為人類社會精神生活一部分的藝術,作為藝術一部分的文學,作為文學一部分的詩,
是不是可以作為社會現象中的一個流通過程看待呢?明顯是這樣一個公式:
詩境(自然中的社會)—→詩人A(作者)—→詩(作品)—→詩人B(讀者)—→詩境(社會)
這是從社會到社會。第一個人作出詩來,是詩人。第二個人吟誦這首詩是將詩重現,所
以也是詩人。詩若無人作出又無人讀出,還原為自然和社會,不通過人,就不以詩的形態存 在。人總是社會的人,必然生活在自然的和人工的世界中,所以公式兩頭的項是不必要列的
。結果是:
作者詩人A—→作品詩—→讀者詩人B
B再通過社會影響作者。這是一個循環。這和人類其他社會活動類似。例如經濟活動。
自然經濟除外,只要到市場上去觀察,就可見商品流通過程是:
商品—→貨幣—→商品(W—G—W)
馬克思在《資本論》開篇就列出這個公式。物的交換關系后面隱藏著人的社會關系,所以單純的一次買賣過程實際是:
賣主(商品=交換價值)—→貨幣—→買主(商品=使用價值)
貨幣也是一種商品,作為交換的中介。 再看思想流通過程,也是這樣:
說者(思維語言=信息)—→語言符號(代碼)—→聽者(思維語言=信息)
語言是人類信息交流的中介(不是唯一的)。
由此,詩(語言作品的一種)是作者和讀者在社會中的一種藝術通訊活動,即使用藝術語
言中介的信息交流。這種活動和經濟活動及一般信息交流一樣是循環流通的。若不循環,便
不再生,不擴散,停滯了,死亡了。古今許多詩就是這樣。若是單行線交通,進入死胡同,
墜入遺忘的深淵,就脫離了社會活動的“萬古流”。
這個“簡化”的抽象公式是從實際活動過程得出來的,是為了駕馭那復雜變化的具體情
況的。我們要研究的是這個互相聯系的三項式的具體變化。
這里有必要先說明一點:照一般哲學語言說,這個不變的抽象公式和其中的項是“內容
”,即“實質”,而變化的具體情況是“形式”,即“現象”。但照我們所習慣運用的哲學
觀點說,正好相反,具體的變化是“內容”,而抽象的“公式”是“形式”,不承認抽象的
是“實質”。可是我們常說的“實質”又往往是指那抽象的公式,即“形式”。(例如說什
么、什么的本質、實質。)那么,“實質”究竟是內容還是形式呢?由此,許多人講的話,
還有外國人和中國人、古人和今人,講的話常常用詞相同而意義大異。現在預先定下:抽象
公式及其項是形式,而千變萬化的是具體內容,也就是實質。因此,我們可以從形式達到內
容,從形式理解內容或實質。換句話說,把抽象的作為形式而具體的作為內容。這個抽象公
式本來是從實際中總結出來的,所以這樣的從形式到內容就是從一般到特殊,并不是從主觀
概念出發。例如上述的流通公式。
還需要說明:我們平常分析文學作品有兩種情況。一是從公式出發。這是從形式出發而
以為是實質,所以從形式到形式,具體內容成為例證、附屬品、指示形式的符號,因此陷入
形式中兜圈子,作品千篇一律。另一是從語言現象出發,探索所指物或感受。這是內容脫離
形式,因此目迷五色。兩者對理解、欣賞、創作文學作品可以有所啟發,也可以無所啟發,
自成體系,不相關聯。這兩種情況,古代現代各有側重,形式內容說法混淆。
現在試從上述信息流通或藝術通訊的形式方面研究,結合內容分析,著重在中介如何為
雙方傳達信息。注意從“上下文”解說“文本”,即從作者和讀者解說作品,亦即由“句”
說“詞”。這是詩的“語法”,姑且稱之為形態學研究。下面以中國古詩為對象,試作簡略
考察。
試從《詩經》考察起。
不論孔子是否確實編輯過現傳《毛詩》的本子并作“定稿”(“刪詩”),《論語》中孔
子多次講“詩”。其他先秦著作(經過漢代人整理的)中也有不少“詩云”。從這些議論和引
用中可以看出當時的詩是交流信息的中介,是藝術語言通訊的一種。《論語》引孔子說,“
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從吳國季札“觀風”的記載以及其他,如《論
語》所說《關雎》之“亂”,可以知道,詩中的“風、雅、頌”都是配樂的歌詞,是“禮、
樂”之中不可缺少的,是不脫離音樂、舞蹈的,也是和樂舞一同為了縱向(對后代)或橫向(
互相間)交流信息的。詩是那時人的文化教養內容之一。無詩不能暢通信息。“不學詩,無
以言。”(《論語》)當時各國語音不一,方言有別,口頭定下的通行語標本就是詩。唱起來
都知道。寫下來,規范化,讀音不同也能互通。
《詩經》包括了黃河流域中的人的作品,還收羅不到長江流域的楚和吳越。那地區住的
是“南蠻<SPS=1024>舌之人”(《孟子》),“斷發文身”,與北方雖有來往,但一般人語言
不通,或不被北方人認為“文明”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都算是“化外”。《詩經》
不收,不知道或不承認他們的“風”。
《詩經》的編訂是依照樂曲的。“樂正”,然后“雅、頌各得其所”。沒有提到“風”
,可見“風”是樂曲的另一部類。樂曲是為不同場合應用而有不同風格的。所以區別了“風
”和“雅、頌”即分開了民間之樂和廟堂之樂。民間之樂又隨地區而不同,所以又分地區編
排,與“雅、頌”不同。由于“禮、樂”都是社會性的,所以自然而然也伴隨著信息交流即
通訊的類型而分別。這樣,民間交流的詩中有對唱、輪唱、合唱、獨唱等等音樂形式,而“
雅、頌”就不同。那是對神和王等統治者說話或代表他們說話的。盡管也可能有獨唱、合唱
之類形式,卻不是平等的人對話,而是上對下的訓話,或下對上的稟報,或代表上層的宣告
。《小雅》作者是中間的人,既屬統治階級,又是其中下層,所以處在夾縫中間,“怨誹而
不亂”。“風”(風、謠)和“雅”(雅、頌)是詩的兩種形態,各具有不同內容,對不同的人
傳達不同的信息。
楚文化興起并傳播開來,出現了第三種形態:“騷”。從現存的《九歌》等看來,這也
是配樂舞的,是巫者在集會上(包括民間和廟堂)應用的歌詞。這是“楚”風,和中原的“風
”大有差別。差別更大的是屈原的《離騷》。這是新的形態,和風、雅鼎足而三,成為古詩
形態的主流。此后詩人便又稱為“騷人”。楚“風”從《九歌》形態中巫的表演派生出又演
又唱又說的“優”。《史記》中現存優孟演孫叔敖時唱歌和演戲的記錄。那是對楚王傳達一
種不便直接講出的信息,是復合的代言形態,超出了詩的范圍,但唱的歌詞仍然是詩。
屈原位于詩人之首,并不是由于他第一個作詩而是由于他第一個作出了個人的詩。在他
以前,無論是風、雅、頌,或是巫者、優人唱的歌,都沒有個人的作者或讀者明白顯現。從
前面說的三項式看來,作者和讀者,即信息的發送者和接收者,都不是有個性的個人主體。
有的是無主體,如雅、頌。有的是可轉移的模糊的主體,如“風”和“小雅”的有些詩中說
的個人。那是可以更換演員的腳色。唯有《離騷》,盡管夾雜著譬喻和象征,卻鮮明地有一
個作者,而且作者所預期的接收對象也顯然不是集合的群眾而是“知音”,所以最后說:“
國無人莫我知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既無人知,何必還作詩?還是盼望有知音。第一
個也是最大的知音是司馬遷。他作了千古高文《屈原列傳》。《離騷》還有個特點是:雖然
采用楚“風”的樂歌形式,卻不一定是配樂唱的,而是可以個人吟誦的。本來是音樂舞蹈為
主或則樂、舞、歌并重的,現在歌詞宣布獨立了。詩中樂舞可有可無,若有,也成為配角了
。狹義的詩的傳統應當從屈原的“騷”開始,而不是《詩經》的“風”和“雅”,那是廣義
的詩的開始。《九歌》是兼“風、雅”的,不是第三形態。從三項式來看,它還屬于“風”
,不過表演和信息收發者又與“雅、頌”相通。《九章》則屬于“騷”。
從秦代以前的《詩經》、《楚辭》看來,詩的形態是三種:風、雅、騷。其中的風和雅
以及巫的歌和優(優孟、優旃)的唱、演、道白都可以說是代言體,說的不是自己,不突出個
人。唯有騷是個人的詩又訴諸個人。作這一形態的詩的第一人是屈原。作這一形態的文的第
一人是司馬遷。屈原的詩不是代言體。司馬遷的文不但有他自己的《報任安書》和“太史公
曰”,而且往往仿佛代別人說話而實際是讓別人出面代自己說話。這開辟了中國文學中的一
種重要形態,變化多,流傳廣而且久。不過那不專屬于詩,所以這里不論。(李斯的《諫逐
客書》之類是議論一事,仿佛“對策”,不是個人自己說話,和《報任安書》不同。)
中國文化的基礎大概可以說是奠定在秦的前后。政治和社會和統一國家的許多制度都是
秦代首先制定而漢朝遵循下來的。詩作為文化語言的一種形態,自然也在這時大體定下了基
礎(或說模式)。這便是風、雅、騷三分天下。從三項式的首尾兩項(即人)來說便是:民間(
風)、廟堂(雅)、個人(騷)。從中項(即通訊方式和代碼)來說便是代言或自言,代碼系統由
此而異。
本文不過提出一種看法,不能再分析從漢到清的詩的三種形態的豐富內容變化。不過我
想引一下杜甫的意見,以見我這說法并非販賣舶來品而于古無據。杜甫稱為“詩史”,不僅
是作詩的史家而且是詩的史家。他本人既是詩人,對詩的歷史也有獨到見解。他的《戲為六
絕句》中提到的詩的時代是漢、魏、齊、梁、當今(唐),提到的詩人是屈、宋、庾信、初唐
的王、楊、盧、駱以及“爾曹”、“今人”,提到的詩“體”是風、騷和風、雅。這可以算
是他心中的詩的歷史綱領吧?至于評價和意見,因為他用的是絕句詩體而不是論文,用藝術
語言而不是科學術語、公式,那就盡有討論余地了。那里有價值觀念體系問題。
關于詩的形態學的其他問題當另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