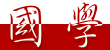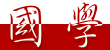|
□金克木
我國有一大筆文化遺產(chǎn)現(xiàn)在還沒有整理,這就是那些從古代印度傳來的佛教文獻(xiàn)。大略
可以說有下列幾項(xiàng),都不包括中國人自己的著作:
一、漢語譯的佛教文獻(xiàn),即《大藏經(jīng)》中的原著部分。
二、藏語譯的佛教文獻(xiàn),即《甘珠爾、丹珠爾》。蒙古語譯文可以算在這一系統(tǒng)之內(nèi)。
三、新疆發(fā)現(xiàn)的古代一些兄弟民族語文字母寫的或譯的佛教文獻(xiàn)。
四、傣族的所謂“貝葉經(jīng)”,其中應(yīng)有抄寫下的或翻譯的佛教文獻(xiàn)。
五、西藏、新疆等地區(qū)陸續(xù)發(fā)現(xiàn)的古代印度語的各種字體寫本,還有附漢譯或藏譯的原
文寫本或木刻本,用漢字或藏文字母等音譯的印度原文,各種文物中附的不同文字的印度語
原文,這些也多半是佛教文獻(xiàn)。
以上這些文獻(xiàn)是中華民族的財(cái)富,也是世界文化的,尤其是印度文化的重要資料。在國
際上早已有人進(jìn)行研究并且校刊,甚至大部頭的尚無原文的漢譯本如《成唯識論》、《阿毗
達(dá)磨俱舍論》(釋論)、一百卷的《大智度論》,陸續(xù)有了法文譯本(末一種尚未完成)。但是
國內(nèi)從清末至今只有極少數(shù)人作認(rèn)真的科學(xué)研究。甚至漢譯文獻(xiàn)除許地山編的《佛藏子目引
得》(和翁獨(dú)健編的《道藏子目引得》一樣體例,都是燕京大學(xué)出版),呂<SPS=0701>編的《
新編漢文大藏經(jīng)目錄》(齊魯書社出版)以外,就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梵、藏、漢對照的《
大寶積經(jīng)迦葉品》的出版者是商務(wù)印書館,編校者卻是外國人鋼和泰。
這些文獻(xiàn)雖說是佛教文獻(xiàn),其中卻也包括了非佛教的書籍。佛教文獻(xiàn)也不僅僅是宗教宣
傳品。宗教色彩濃厚的也是古代文化遺留的一種資料。若以現(xiàn)代科學(xué)的眼光觀察,這些就成
為語言學(xué)、宗教學(xué)、哲學(xué)、文學(xué)、史學(xué)等等研究的古代文化資料。不但印度人認(rèn)為這些是他
們的文化遺產(chǎn),而且從中國文化史的角度看來,這些也是中國古代文化變化發(fā)展的重要因素
,甚至還可說是研究現(xiàn)代文化來源和構(gòu)成的一個(gè)不可缺少的環(huán)節(jié)。特別有意思的是,若依照
比較文化的觀點(diǎn)來研究,這些恰恰是不同文化相接觸而產(chǎn)生變化的一個(gè)頭,是輸入口,由此
產(chǎn)生一系列的矛盾、沖突、“反饋”、新生等等變化而從輸出口顯現(xiàn)了新的文化。這種情況
在中華民族的整個(gè)文化發(fā)展過程中不斷出現(xiàn)。黃帝戰(zhàn)蚩尤的傳說姑且不論,商和周以及黃河
流域和越、楚的“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直到近代、現(xiàn)代的對外文化接觸,都需要
有全面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xué)研究,其中也可以說要有一個(gè)現(xiàn)代文化人類學(xué)的所謂“全局性
的”(holistic)研究。同樣重要的是現(xiàn)代文化人類學(xué)的一個(gè)研究方法,“比較文化”(cross
-cultural comparison)研究。這一類工作當(dāng)前還在發(fā)展中。例如,在美國,有人比較南亞
的印度教人物和美國的中層人物的“世界觀”;有人比較中國人的和美國人的家庭核心關(guān)系
,以為中國的是父子,美國的是夫婦,這種關(guān)系形成民族性格的一部分。他認(rèn)為中國人頌祖
先,印度人頌神,美國人重視兒童,故中國人特重傳統(tǒng)。雖然這種研究主要是依據(jù)生活調(diào)查
,用在歷史上也是重視文物過于文獻(xiàn),但是豐富的文獻(xiàn)若同文物以及生活實(shí)際相結(jié)合,其價(jià)
值和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我國歷史上從三國到唐是一個(gè)極重要的文化轉(zhuǎn)變時(shí)期,是一個(gè)各
民族文化激烈沖突和變化的時(shí)期,單獨(dú)在漢族文化上著眼就難見全貌,對以后的五代、宋、
遼、金、西夏直到元朝大一統(tǒng)帝國的文化淵源也不易索解。這個(gè)大體上從公元三世紀(jì)到八世
紀(jì)的一段恰恰是佛教傳入引起巨大文化矛盾的時(shí)期。從新疆即古代所謂西域的各民族方面說
,開始得更早,從晚唐到宋也還有高潮之后的波濤、轉(zhuǎn)換,但最重要的是中間這幾百年。究
竟經(jīng)過“西域”以及“南海”還有西南的藏、印之間的通路傳到中國境內(nèi)的原來的文化因素
,怎樣恰好碰上了國內(nèi)各民族文化(包括政治)矛盾的重要時(shí)機(jī)而起了巨大作用,從而產(chǎn)生輝
煌的唐代文化?這個(gè)外來因素究竟有什么特點(diǎn),經(jīng)過了怎樣的轉(zhuǎn)化,如何被“揚(yáng)棄”而成為
新的東西?如果溯其本原,對于了解它們所引起并參加的變化必然會有幫助。歷史唯物主義
當(dāng)然著重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決定性,但是對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tài)(大體上可說是人類學(xué)所謂文化
,但這個(gè)“文化”還包括政治以及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甚至生產(chǎn)力,還講到文化生態(tài)學(xué)。)的“反饋”
作用能夠忽視嗎?包括中華民族的各民族在內(nèi)的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不應(yīng)該讓外國人占先了。
不過,“參照系”(frame of re-ference)應(yīng)當(dāng)具備“全局性”,著手點(diǎn)還得是“深入的各
案(個(gè)案)研究”(indepth case study)。這就有一個(gè)如何整理這些漢譯佛教文獻(xiàn)的問題(限
于篇幅,這些問題當(dāng)另文寫出)。
這些佛教文獻(xiàn)傳入中國,標(biāo)志著中國文化史中的一個(gè)變化,這里面有一些問題。因此我
在發(fā)過上述這一番很可能為通人所笑的未必正確的議論之后,愿就這些問題來談一談。
第一是這種佛教文化怎樣傳進(jìn)來被接受的?這是“文化移入”問題。它第一步到“西域
”(新疆境內(nèi)),第二步入中原,很快就風(fēng)、靡一時(shí)。少數(shù)民族接受它不能因?yàn)槭且粡埌准垺?
文化上沒有“白紙”;人類只要組成社會就有維持這個(gè)社會所必需的文化,只有指文字之類
的狹義的文化可以有空白而全部借別人。接受外來的完全破壞性的文化以導(dǎo)致自己的瓦解和
滅亡,這是不可思議的。進(jìn)來的新文化必定對原來社會中至少是某一集團(tuán)有利,最終導(dǎo)致對
社會結(jié)構(gòu)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有利,才能被轉(zhuǎn)化吸收成為新文化的一部分。這也不是少數(shù)統(tǒng)治者或
則知識分子所能決定的。佛教傳進(jìn)來的,第一是和尚,第二是寺廟。這正當(dāng)印度佛像藝術(shù)開
始大發(fā)展之時(shí)(公元初),同時(shí)來的就有佛像和經(jīng)文。立刻出現(xiàn)的是中國社會中原來沒有的一
種社會成分,破壞了原有結(jié)構(gòu)。簡單說就是出現(xiàn)了寺廟經(jīng)濟(jì)。這在后來成了地主收租,但開
頭并不是那樣,是靠化緣集資(包括“敕建”),帶集體公有的性質(zhì)。佛陀在世時(shí)就有大商人
“黃金漫地”買“精舍”捐獻(xiàn),就有殺父的國王“歸依”當(dāng)“護(hù)法”。佛教的經(jīng)濟(jì)和政治的
性質(zhì)及作用很明顯。更明顯的是它還起一種組織群眾的作用,這是幾乎所有宗教直到今天都
有的。一個(gè)有嚴(yán)密組織的佛教宗派可以從物質(zhì)上和精神上組織起很多人在自己周圍。這對于
少數(shù)民族的鞏固自己的社會結(jié)構(gòu)有利,因而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都可以各自加以利用。這種文
化隨少數(shù)民族傳到中原,在民族雜居而經(jīng)濟(jì)和政治結(jié)構(gòu)復(fù)雜變化的歷史條件下,佛教作用勝
過了原有的所謂儒家文化。稍一檢查石窟造像的題名,就可以看出這實(shí)際上起了組織跨行會
的人的作用。當(dāng)“會首”的是組織者,寺廟是集中聚會地,佛像是核心的象征,香火是聯(lián)絡(luò)
的信息。這種社會力量一旦形成,就不能不為統(tǒng)治者(尤其是由弱族而要成為大國的王者)所
重視。一切宗教行為都是圍繞著這一寺廟文化(應(yīng)當(dāng)說“僧伽文化”)進(jìn)行的儀式,包括塑像
和經(jīng)文在內(nèi)。用比較文化的方法唯物地考察,就可以看出,這和世界上許多同類宗教派別都
遵循著大致相仿的模式。物質(zhì)利益和社會效果是根本的。古人并不是不要實(shí)利的超人。
第二是佛教文化中的思想成分怎樣會被接受?這個(gè)新來成分主要是因果、報(bào)應(yīng)、輪回、
轉(zhuǎn)世。這在印度思想中原來也是新成分,其發(fā)展過程這里不提。在中國,特別是在漢族中,
這怎樣能適應(yīng)原有的文化形態(tài)?說來話長,只要指出一個(gè)要點(diǎn):這種理論的強(qiáng)有力的“隨機(jī)
”性。看來是僵死的教條卻有無比的靈活性。它可以是承認(rèn)“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
為有前定的因;又可以肯定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因?yàn)榧扔星岸ǖ奈粗囊驔Q定,又有今世種
下來世的因的可能。人們可以拜佛求來世,也可以偽托彌勒佛降生而造反。佛教是戒殺的,
但不排除降魔。中國廟一進(jìn)“山門”便是“四大金剛(天王)”橫眉怒目;殿上笑嘻嘻的菩薩
背后是手舉降魔杵的“護(hù)法”韋馱。關(guān)于報(bào)應(yīng)和輪回思想的社會作用,需要仔細(xì)的科學(xué)的分
析研究。至于其他的信仰和道德的理論,佛教的和漢族原有的并無根本差別。“沙門不拜王
者”,后來和尚讓步了。外國和尚至今還是受拜不答禮的;中國和尚除做法事時(shí)外已經(jīng)是平
等待人,甚至是逢人便拜的“常不輕菩薩”了。
第三是佛教中的哲學(xué)思想怎樣被吸收的?這首先要分析。那些佛教的基本論點(diǎn)如“無常
”、“無我”、“緣生”、“空”、“有”之類,大概從來也沒有真正照原樣進(jìn)入中國哲學(xué)
,進(jìn)入的是轉(zhuǎn)化了的中國式理解,往往是新術(shù)語、舊范疇。有些在佛教哲學(xué)中原來并不著重
討論的,如“涅槃”、“佛性”等等的解說,卻在漢族哲學(xué)史中成了變幻莫測的論
題。從比較文化的角度說,重要的是“世界觀”的模式。佛教的和印度其他教派的基本上是
一類,是樂生而不是尋死。耆那教承認(rèn)絕食自殺,那是象道教“尸解”一樣;他們最愛惜生
命,以“戒殺”為最高的“法”。佛教同樣是,否認(rèn)變化現(xiàn)象的永恒真實(shí),同時(shí)肯定復(fù)雜現(xiàn)
象的感覺真實(shí)。在中國,這一個(gè)模式在知識分子書中講來講去,實(shí)際上在信教者的實(shí)踐中不
成問題。連佛陀都有生老病死,一切照常。坐禪的人必須大吃大喝,否則不能在一炷香、一
炷香的長時(shí)間內(nèi)練功。至于真實(shí),那是指“涅槃”,是另一回事。巴利語《長阿含
經(jīng)》中,佛陀否認(rèn)他說過世界是丑的,只承認(rèn)得“涅槃”者才知道美,因?yàn)檎婕疵?
,美即真。這些關(guān)鍵詞或關(guān)鍵概念的意義,漢族知識分子在自己的思想的“上下文”和“句
法”的模式中作了自己的理解;一般人在實(shí)踐中卻沒有弄錯原義。真正提出佛教“文化移入
”后新文化思想的第一人是反對佛教的韓愈。他要“人其人,火其書”,其實(shí)不過是為了和
尚“不出粟米麻絲以奉其上”;他反對出家人不生產(chǎn)以養(yǎng)活帝王、官僚。它的《原道》的第
一句話“博愛之為仁”,就不象孔仲尼的話而象釋迦牟尼的話。韓愈是善于“揚(yáng)棄”的,他
的哲學(xué)體系經(jīng)過晚唐、五代,在幾個(gè)政權(quán)并存的宋代完成了,經(jīng)過了蒙古族統(tǒng)治的元朝大帝
國以后成為明清兩代承認(rèn)的“道統(tǒng)”。漢代知識分子是儒生加方士,以后又經(jīng)過長期變化,
知識分子成了儒生加道士加和尚。“西游演了是封神”,三教合一,《紅樓夢》里也一樣。
文化是一般人的,他們心里明白得很。
第四是佛教文化怎樣中國化了?首先是寺廟變了,成了“十方叢林”和“子孫叢林”。
出家人也變了,受戒、游方、“掛單”、“化緣”等等發(fā)展了。魯智深從五臺山到大相國寺
,提轄做和尚;武松成行者。四大菩薩(文殊、普賢、觀音、地藏)住在四大名山(五臺、峨
嵋、普陀、九華),連迦葉羅漢也搬到云南雞足山了,佛弟子目犍連成了下地獄救母的孝子
目連,而且是地藏菩薩,成為敦煌變文的題材。這種“文化移入”情況是國際上數(shù)見不鮮的
。一九七九年前,印度有人將基督的生平寫成梵文(古文)長詩得了獎,一九八一年三月新德
里電臺廣播了新編的演德國梵文學(xué)者馬克斯穆勒生平的梵文戲劇,一九八一年七月印度浦那
還上演了梵文戲劇《丹麥王子哈姆雷特》,改了名字,將莎士比亞印度古代化了。這和我們
演“霸王別姬”芭蕾舞其實(shí)是一樣的。在當(dāng)前世界上,在民族性宗教的國際化之后,國際性
宗教的民族化又在進(jìn)行中。宗教作為團(tuán)結(jié)自己人以應(yīng)付外來危險(xiǎn)的組織者的社會功能,看起
來還沒有完結(jié)。
以上四個(gè)關(guān)于佛教傳入中國歷史的“文化移入”問題只是提出來供參考,我的看法僅僅
是一種臆說。為了研究這類問題,佛教文獻(xiàn)中原來歸入戒律一類的書是重要的資料,也許整
理漢譯佛教文獻(xiàn)可以從這方面開始。戒律是內(nèi)部讀物,照說是不許未受戒者看的,現(xiàn)在可以
打破這一禁區(qū)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