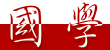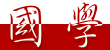|
□金克木
現在將我發表過的研究或論及古代印度文化的24篇文章結
成一集出版,以便讀者參閱。這些多是“草創”之作,不足人“方家
法眼”,但也許還可以借給后來人做墊腳石。其中有不少附了譯
文也是為了便利讀者。除說明是出自古譯的書以外,文言的,白
話的,都是我直接從印度古文(梵語)譯出的。有些還附了原文和
對照表,以供核對。這增加了印刷排校困難,但方便了讀者。我希
望這些文章能有研究印度的專家以外的讀者,所以盡量寫得不那
么專門,使有些讀者看時可以略去專門的內容而依然能懂。《梵語
文學史》和《古代印度文藝理論文選》(人民文學版)和《中印人民友
誼史話》(中國青年版),盡管已經絕版而且估計不會再版,也仍作
為專著單行,不收入集。關于有些文章,下面再略作說明。
《梵語語法〈波你尼經〉概述》列為第一篇。《波你尼經》是一部
概括全部梵語語法的“經”體的書,是用符號語言編成口訣仿佛咒
語的封閉的書。照印度傳統,學文法的人只背誦零散經句作為口
訣。除專門學習“聲明”(語言學)的學者以外,很少人讀原著。國
際上從19世紀到20世紀陸續出版了德文、英文、法文的譯注本,
也是只能供專門學者應用。照我所知道的情況說,到20世紀80
年代初期,國外還只有極少數學者對此書作單方面的專題研究,缺
少全面系統而且“通俗”寫給注意語言思想文化的讀者看的書。我
這歷盡滄桑終于在“劫余”寫定的《概述》,曾于80年代初《語言學
論叢》第七期(商務版)得到發表,后來收入《印度文化論集》(社會
科學版)。現在排為首篇,不僅是有“敝帚自珍”之意,而且想引起
注意,希望多些人知道這部名聲極大而讀本文者極少的“經”體的
書。我在文中還提出了和別人不盡相同的意見。我不認為這僅僅
是教人學習梵語的手冊,而認為是概括表述當時知識界內形成的
通行語(梵語)的規范,是一種文化思想建構的表現。波你尼總結
前人成果編成口訣,一為容易記誦,二為可以保密以見“神圣”,三
則是自覺發現了(實是建構了)規范語言的總的結構體系,以為是
發現了語言的規范,亦即思想文化的,亦即宇宙一切的規范,因而
必須作成“經”體,賦予神秘性。這部《經》和我們的《內經》、《參同
契》有類似之處。現在我又覺得這部語言符號的文法書更類似形
象符號的《易經》。兩書雖都以符號組成,但所蘊含及傳達的信息
和傳達信息的方式彼此不同,而符號網絡的構成及內含的思想根
源卻有相通之處。可惜我這八十老翁縱使竭盡衰年余力也難以一
字一字寫文來談這世界上的兩部“難念的經”了。
第二篇是《梵語語法理論的根本問題》。這也是據我所知很少
有人注意的。古印度人口頭傳授經典,不寫下來,不重文字,只重
視聲音符號的語言,以為語言存在于口頭聲音。他們從語音表現
的詞搜查語根,分析語法,建立結構體系。這里出現了一個哲學思
想問題。名詞(概念)在先還是動詞(行動)或稱“述詞”(述說行為
的詞)在先,即,是不是名出于動?有兩派爭論,以主張“名出于動
(述)”的勝利而結束。全部語詞歸于不到兩千語根,全是動詞,即
“述詞”。這樣分析并歸納聲音語言為語根和中國人分析并歸納形
象語言的文字為五十“部”,而建立“部首”是同一思想路線。一個
是以聲音為主的語詞網絡系統。一個是以形象為主的文字網絡系
統。印度的《波你尼經》成于公元前幾百年,而中國的《說文解字》
成于公元后百年。較早的《爾雅》的語詞分類體系不知是不是也可
以算是同一思路而以意義為準。漢語將漢字作為通行語的符號,
重視形象。《說文》的《序》中就以伏羲觀象畫八卦為文字開始。印
度正統思想認為“聲是常”,認為聲音語言永恒,即,口口相傳的《吠
陀》經典永恒。反正統的佛教思想認為“聲是無常”,即,《吠陀》不
是永恒的。他們的“聲”就是詞,就是中國的“字”,就是語言。中國
人重視形象,以字為詞,文字也就是語言。重音的以為名出于動,
行為在先。重形的是不是以為名是第一?一動,一靜。在方音不
同而文字統一的中國人看來,音有生滅而形常在,如八卦。用希臘
語寫成的《新約·約翰福音》開頭就說,“太初有道”。這“道”字是
logos,邏各斯,亦即語言。記得歌德在《浮士德》中寫浮士德博士宣
布“太初有為,”(行為,Tat)。音和形,動和名,行為和語言,不同理
論出于同一思路。中國人思想重形,重名,兩者相通(形式,符號)。
孔子立“名”,老子破“名”,都是重視語言符號。中國人的傳統宗教
思想是祖先崇拜。拜的本來不是偶像而是“神位”,是“木主”,是
碑,是文字,是名,代表活人或“死而為神”的人。基督教在拜占廷
羅馬帝國時期改變了原來希臘(地中海)的文化思想。東方影響了
西方。伊斯蘭教人印度,影響了印度人本來的哲學思想。佛教入
中國也影響了中國人的傳統思想。兩者都是從西到東的影響。這
三大系的文化思想都有前后兩大時期的差異。如不把前后時期分
開對照以見其有同(傳統)有異(變化),研究思想史就難以深入思
想內涵而停留于排列組合。古代印度的文法理論中討論這一名動
問題的材料雖留下極少,但可能是點明這一問題的現存最早文獻。
因此把這篇放在《波你尼經》概述之后,希望引起注意。這和前一
篇都不僅是語言學問題,而是語言哲學問題,又不僅是古代哲學問
題而是連貫下來的思想文化問題。人的群體思想是不可能攔腰
一斬“徹底決裂”的。
《試論梵語中的“有——存在”》,這一篇是由語言析思想的試
作,還不能說是論哲學思想范疇。近年出版的汪子嵩、陳村富、范
明生、姚介厚四人著的《希臘哲學史》第一卷(人民版)中引了我的
文章并且和希臘語聯系分析。這正是我想做而未能做的。我曾受
史學家傅孟真(斯年)指引并鼓勵從希臘語入手學習歷史。因為抗
戰時鄉間找不到書才學拉丁語從羅馬史入手。隨后到印度忙于學
梵語,以致始終未能學希臘語,讓后來得到的希臘語的字典、荷馬
史詩、《新約》在書架上至今嘲笑我的遺憾。
《印度哲學思想史設想》只是在已有的哲學史框架外的一種構
圖,將哲學史作為人類思想發展史是黑格爾早已提出了的,是作為
絕對精神之展現。作為人類認識發展史來寫的有汪子嵩等四人的
《希臘哲學史》。能不能用比排列組合更統一而明白的表述法來繪
思想發展的地層圖?明白過去的思想是為理解現在的思想打底
子,又為照見未來提供方向。解說歷史往往是自覺或不自覺的解
說現在。解說現在又往往是投射向未來。獲得第二屆諾貝爾文學
獎(1902)的德國蒙森(Th.Mommsen,1817—1903)的注重考據又有
文筆史識的《羅馬史》(1865-7)恰好是以普魯士為首的德國統一
(1871)前夕的產物。羅馬的凱撒是不是德國的“凱撒”(德文Kaiser
是皇帝)?史學家能覺察出歷史趨勢,但不能受雇傭去造假。假的
揭穿了會傷害制造者。歷史懲罰不知道歷史的人、隱瞞或抹殺歷
史的人、以為歷史可以偽造的人。我相信歷史學到21世紀必將有
如同19世紀對以前那樣的突破,因為人類思想將有突破。中國有
最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文獻、文物。例如歷代農民起義“史不絕書”,
這是任何其他國家比不上的。這里有史事、史料和史識,不僅是給
人供給史料。從《尚書》和《春秋》開始,歷朝歷代都有“官修”、“欽
定”的史書。一開國便擬編訂史書,也就是改造以至創作歷史,為
第一位的文化工作。那時的人已經懂得,要摧毀對方,要穩定自
己,統治者都要從改造歷史修訂史書入手。若不能定出新調子而
只是破壞舊的,結果是自己也難穩定下去。原地踏步,善破不善
立,善戰不善治,多亂世而少太平,“資治”的《通鑒》已用史實說明
這一點。現在該要突破《通鑒》才能“資治”了。中國的史學也將不
會被外國人看做提供資料給他們寫史的了。史學的突破需要哲學
即思想的突破,所以突出的史家是以人和事的語言符號演算的數
學家。蒙森的“羅馬的”歷史寫的是活的羅馬。歷史書
如此,哲學史也如此,所以我把哲學家的對外界的認識發展看做在
思想繼承中不斷回答當代問題。當然,我所說的只是一種設想而
以印度為例。
《略論印度美學思想》及譯解《吠陀》詩和以下各篇不必一一說
明了。這些文章是介紹加上我的解說、闡釋。例如從《蛙氏奧義
書》引出一種思維結構模式,對于婆羅門和沙門兩種人兩種文化的
看法,關于佛教哲學中的“意識流”問題,都是可以一望而知不是因
襲來的意見或為已有結論作證明。20世紀初王國維提出要以出
土文物和文獻對證古史。他那時依據的殷墟甲骨書契和敦煌寫本
仍是文獻。以后的發展說明,無文字的文物,如兵馬俑、編鐘,和有
文字的文獻,如漢簡、帛書,同等重要。到20世紀末期,國際上更
有加上對活人的調查的趨勢,而且不止是為證古史,同時也是以文
獻、文物、人互相對照并結合以了解文化以及人類的過去、現在和
將來。這不僅是打通了文和物和人,而且打通了古和今,現在和過
去、未來。這一趨勢剛剛開始,窒礙多而且大,下一世紀當有新的
面貌出現。常有人說,不要割斷歷史,心目中以為歷史是可以割斷
的。這是不知歷史,不知今人是古人的延伸,古人是今人的影子,
未來的人是今人的投射,是從今天的人脫胎而出的。根本不存在
“割斷”歷史的問題。不說,不寫,不知,也不是“斷”。“割斷”是由
無知和自大產生的想象。“反”往往是“返”,本是一個字。將“返
祖”、“復歸”當作創新,這是歷史對掩蓋它的人的懲罰和嘲弄。由
今天理解昨天,結果是可以望見明天。這不是為古而古,也不是取
來利用,是尋找對事實的解說。歷史允許不同解說。如何將文獻、
文物、活人和死人打通,而且從文,從物,到人,再到人的行為和語
言,再到深入解析指導人的行動的思想,這個問題,我想到21世紀
當有進展。我這些文章仍然是文獻研究,但已經注意到人及人的
語言、思想,注意到文化,本族和外國,古人和今人,算是望見苗頭。
這里我必須提到半個世紀以前在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退隱的
喬賞彌老人(DhamanandaKosambi)。是他在給我講梵語時提出試
驗“左右夾攻”《波你尼經》,指導我和他一起試走他自己一直沒有
機緣嘗試的途徑。也是他提出對沙門的見解,更是他使我能親見
親聞一位今之古人或古之今人,從而使佛教的和非佛教的,印度的
和非印度的人展現在我面前。我若沒有因緣遇合這位毫無現代學
歷而任過哈佛大學和列寧格勒大學教授的老人,就不會有這些文
章。以后幾十年間我“枉拋心力”于他處,只在晚年才能趕出一點
微末答卷來還債,遠不能達到他的期望,只好說是“緣盡于此”、“非
人力所能左右”了。我之所以還把這些文章結集出版,也是由于我
無法“傳薪火”,姑且留此“雪泥鴻爪”以待后人了。
人的思想總是不斷變化的。現在我翻看自己的文章,幾乎對
于每篇都有滿意和不滿意之處,都想改寫或者刪補。不過,不僅已
無此精力,而且,一則文章發表以后除法律產權外便不屬于我私人
所有而屬于讀者,二則現在的意見不一定比以前的好,將來還會有
新意見,改不勝改。自己看自己的文章也不過是一讀者。我既不
想,也不能修改古人和外國人的書,又何必對署我的名字的印刷品
那么介意呢?
1994年初,癸酉歲尾,立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