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世界文明共有的一種創造,如同藝術一樣。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習俗。中國歷史也不例外,在多元文化的中華文明中,宗教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20世紀以前,學術界對中國古代的宗教形態及其歷史很少加以關注,幾乎沒有出現過什么系統、深入的研究專著。這在號稱史學大國的中華,應該說是一個令人驚奇的現象。其實,探究這其中的內在原因,就不難知悉這種現象的存在。一方面,傳統學術的慣力把宗教排斥在學術研究的范圍之外,甚至把宗教生活和宗教信仰也斥為異端,認為儒學才是文化與學術的正宗。另一方面受觀念的束縛,人們對宗教史料缺乏了解,因而也就無從對宗教文化加以了解,逞論對其研究了。以代表中國古代學術發展里程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而論,不僅對宗教史籍取予失當,而且乖謬之處,俯拾即是,近代以來,幾成蒿矢之的。
本世紀初,歐風美雨吹拂著中華大地,傳統學術大規模崩塌,新的學科應運而生,一代學人秉承著歷史的傳統,開拓著新的時代,新的學術不斷產生發展。宗教歷史也突破了塵蝕的世界,走向了新的時代。如果說考古學的引進把中國傳統學術帶人了一個以物質為實證的學術世界,那宗教史學的建立與拓寬,把人們的視野放寬到了一個更為廣索的天地。這一切,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本世紀初開拓中國文化新紀元的大師們,而其中對宗教史學最有貢獻的莫過于陳垣、陳寅恪這些大師的努力,其中尤其是陳垣先生,開拓建設之功最大,著述最多,影響最為深遠。
一
1917年,陳垣發表了震撼學壇的《元也里可溫教考》。從此,陳垣棄政言學,開始長達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同年,胡適的文學改良在文化界掀起喧然大波。新文化運動宣告正式開始。1919年,刊布了他《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更一步贏得了文化史上啟蒙者的地位。
這并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既是時代的安排,也是學術的一種抉擇。終陳垣一生,以基督教研究開始,不斷擴大學術范圍,不僅遍及中國古代宗教,而且鉆研到元史,中外交通史等學術領域,而以集資料、撰著作,育人材為主,困守學術,有功于文化甚巨。繼《元也里可溫教考》刊布之后,陳垣不斷耕耘,陸續刊布了大量的宗教史專論、專著,最著名的有古教四考,其他三考分別是:
一、《開封一賜樂業教考》,二、《火祆教人中國考》,三、《摩尼教人中國考》,連同后來發表的《回回教人中國史略》。這些專論對遺存在中國歷史上的非主流宗教史跡進行了開拓式的清理。從而實證出:在中國歷史進程中,除流行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外,還曾傳入過其他世界文明的古老宗教,或一些主要宗教的不同教派。研究表明:宗教的存在與發展在中國歷史上并非只有幾條直線,而是同樣存在著多樣化,復雜化的史實。
《古教四考》系列論述表現出的共有特征是:資料完備,考證精細,文筆簡古,都是研究宗教史,乃至學術史不可多得的作品。
除考古教之外,陳垣更為系統全面、深入的研究中國文化史上主要宗教的形態,對主要宗教用力尤多,成為學術史上第一個開啟中國古代宗教史大門的學者。中國古代的宗教主要形態為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這也是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對這些,陳垣無不留意,并且都以精細的研究,結撰出經典性的論著,下面從其治學的歷程分別加以敘述。
基督教,這是陳垣著手研究最早的宗教。《元也里可溫教考》就是一部元代基督教史。也里可溫即基督教聶思脫里(Nesteranisne)派的譯稱。陳垣通過對這一關鍵性詞語的譯讀,從浩瀚史料中爬梳出有關史料,為元代基督教發展史寫上了精彩的一章,從而探明了在唐代景教流行至利瑪竇來華傳教這近千年間,基督教在中國發展存在一個重要時期。這不僅是利瑪竇以來所期冀得到認識的傳教史實,也是了解元代文化宗教發展的重要課題,因為元代文化中的重要因子就是基督教文明。它與漢族的佛道文明及儒學發展共同構成了元代文化中的中西拼盤以及西方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在中華大地上的華化現象,這一點,陳垣在后來的論著《元西域人華化考》中討論得更為詳盡。
《元也里可溫教考》既是陳垣宗教史研究學術研究的起點,也是關于中國基督教前史的重要成果。繼此,他一方面不斷完善和修正這一專論,而且進一步拓寬其基督教研究的領域。在基督教史,基督教人物及基督教文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貢獻。他為了全面研究基督教歷史,曾肆力搜集有關史料,并計劃仿《開元釋教目錄》及《經義考》、《小學考》體制而為《乾嘉基督教錄》,為中國基督教文獻作一次全面的清理,也為《四庫全書總目》補閾拾遺。這一計劃最終僅完成了一部分,即附刊在《基督教錄入華史略》后的《明清間教土譯述目錄》,雖然眼于條件只及說理與教史部分,未及天文、歷算、地理、藝術這些傳教士重要的著述范圍,但在徐宗澤《明清間耶蘇會土譯著提要》及羅馬梵蒂崗教廷及巴黎圖書館公布珍藏目錄之前,是一份搜聚天主教文獻最多的一個目錄,其中未刊本較多于已刊,足見其搜訪之勤。為聚集、調查天主教文獻,他遍訪國內公私收藏,并遠足日本。陳垣的設想,今天仍未能實現。但其創意著鞭之早,至今讓人欽敬不已。
陳垣治基督教史曾有一個大計劃,即結撰出一部中國基督教史。終限于文獻條件,加以他后來學術的領域的擴大與轉移,如同《乾嘉基督教錄》一樣,始終沒有完成,但是他一直沒有放棄對基督教史的研究。只不過是采取了各個擊破的辦法,步步前進。讀一讀他的基督教人物研究及一些專論,就會感受到他在基督教史研究上的深入開拓。如陸續發表的“基督教人物四傳”,《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都是研究明清以來天主教史的重要收獲。
伊斯蘭教,古稱為回回教,這也是他二十年代著手的一個重要領域。他在伊斯蘭教研究方面有兩個重要貢獻。一是編撰了一部研究所必需的工具書《中西回史日歷》,時在1925年。他運用西方紀年的科學手段,在完成了《二十史朔閏表》的豐富經驗上,以建中西回三歷歲首為干,為治伊斯蘭教史樹立了一個歷史坐標。他的這一創舉,為創建中國伊斯蘭教史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礎。第二個貢獻是他提出了一個系統全面研究伊斯蘭教的計劃《中國回教志》,分十大門:一、宗派志;二、典禮志;三、氏族志;四、戶口志;五、寺院志;六、古跡志;七、金石志;八、經籍志;九、人物志。又分經師、卓行、政績、武功、文苑、方術、雜流。列女八項。十、大事志,并附中回歷對照年表歷代哈里發世系表,唐宋遼大食交聘表,元明清回回科表。這個計劃前無古人,意在為中國回教立正史,其用意不可謂不偉,其艱難也一望而知。但他這種識見、創舉,在學術史上是足以讓人驚倒的。如果真能如他所期待的那樣早日實現,中國回教史的研究將是多么幸運。
佛教,作為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廣的宗教,陳垣對此研究尤為用力。先后刊布了《釋氏疑年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以及《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四大著作及若干篇重要論文。在近代學者中,可謂論著最多。
陳垣的佛教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四十年代,重點在佛教文獻學、佛教工具書及區域佛教史等怫教史研究學科。《釋氏疑年錄》是一部通貫古代的佛教人士史料工具書,它不僅可以查考本來十分復雜的佛教人物生卒年,而且可以循此書所蘋取的史料細索,探討所需人物的生平及歷史,示學問以門徑,給研究者一導航。《中國佛教中籍概論》是從浩繁的佛教文獻中披沙撿金,結合自己實際的研究與利用,甄取五十余種最具有史料價值、學術意義的典籍加以品評,明其源流,別其高下、抉發其價值。圍繞歷史與宗教,或考史,或糾謬,集評論與研究于一體,初學者可得而入,專攻者亦可大獲而歸。它為史學研究開了一條新路,也為佛教文獻立了一門新課。《明季滇黔佛教考》及《清初僧諍記》主要是根據他從《嘉興藏》中得到珍貴、獨有史料,對區域宗教及地方宗教進行考論,并結合明清怫教發展的特點,探討晚世佛教文化的走向。由于陳垣最清元明以來歷史,因而能運用內外文獻,尤其是文集、方志。碑版、雜交,包舉萬端而又融會貫通,論教闡史,自成一格。
道教,雖然他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刊布于三十年代末,但他著手于道教的研究則始于二十年代。刊行于八十年代的《道家金石略》竟是他在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時輯錄的資料。《道家金石略》的輯錄,在道教文獻,乃至歷史文獻編纂上均有很高的價值和史學意義,它的編成,為本來十分叢雜的道教史料提供了一份可資利用的珍貴史料。在《道藏》內外,沒有一部書有如此高的史料價值。它出于道藏而超越道藏文獻,集合了眾多文集、方志碑拓中的嚴肅史料,讓人第一次感受到,歷史上的道教并不全是自弘其道,難測其實,而是具有自己真實而又光輝的歷程。陳垣對道教史料的建構與搜集,超越了古今道教研究的成就。他據此抽繹而成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就是一份由史料積累到史實勾勒的積極成果。“新道教”的提出為道教史料的發展提供了輝煌的一頁,盡管是逝去了的光輝。這樣,把備受忽略的道教史研究推想了熱鬧的學術天地。在陳垣所耕耘過的宗教史領域中,他對道教文獻的搜尋是最為用力、最為成功也是最有意義的。因為是他的積極推動,使道教史研究尋找到了可資依靠利用的史料基石。他作為道教文獻史料的建設者和道教史研究的一代宗師,將永遠為學術研究界所認同。
二
以上綜述了陳垣宗教史研究的成果,下面探討其特點與方法。我們認為,陳垣宗教史研究最大的特點歸結到理論上講,就是創建并發展了具有時代意義的宗教史學。這一點,早在四十年代初陳寅恪為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已經提出:
中國史學,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獨由于意執之偏頗,亦其知見之狹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學識,更不逮宋,故嚴格言之,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實自近歲新會陳援庵先生之著述始。
前此,陳寅恪為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撰序,也以陳垣史學繼承錢大昕,超越清人,直接宋代。而此則更接他五年以前論提,歸結為陳垣的超越在于構擬“完善之宗教史”。陳寅恪不拘佛教,從整個史學加以闡發,其標論之高,令人欽敬。具體研究陳垣的宗教史論,也足印證陳寅恪之論略無不當。今就陳寅恪序更進一步申論。所謂宗教史學,實際上是以治歷史的方法研究宗教史,把宗教史研究歸結為歷史研究之一端。這在今天,似乎已不必究論,但對開拓者而言,這是一種突破,因為自來宗教的發展有著自己的軌跡和邏輯。在正統學術史上,從未見過有人敢越雷池一步,跨越到“異端”之宗教研究領域中。所以,自宋以來,史學家不僅不知宗教,而且處處在辟佞。這佞妄之本就是各類宗教,即陳寅恪先生所述之“意執之偏頗”。而陳垣首先放棄了這種對宗教的偏見,并視宗教研究為歷史研究之一域,以系統、全面的研究開創了20世紀的“宗教史學”。這里有必要探討一下陳垣的宗教觀及宗教思想,以認識其“宗教史學”。過去不知是回避還是否定,大多數學者竟不提陳垣是一名天主教徒,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他早年信教是一回事,晚年加入共產黨又是另一回事。人有信仰,并發生改變,都是常事。不然陳垣早年何來“上帝呵護之靈”、“我主耶穌”之類的言辭形于論著之中?更遑論他與天主教名士馬相伯、英華之相知相近了。以主掌教會大學——輔仁大學之職而不奉教,那才是難以征信的悖論。顯然,他也是一位東傳基督教史上之李杕、吳歷,20世紀的司鐸。他后來的業績較之李之藻、楊廷筠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他的奉教經歷倒類似于天主教中的許纘曾。 表彰出陳垣曾作為一個奉教者并不是一項艱難的事,其實更有利于探討他在中國基督教研究上的貢獻。正是因為有過信仰經歷,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更應該研究宗教,以體察宗教在文化歷史中的地位,信教的經歷及體驗,也更有助于研究的把握,不至于隔靴搔癢。這大概也是陳垣宗教史研究得力之點。
當然,曾經作為一名天主教徒并沒有把陳垣圈在宗教信仰的道路上。他在深入的研究過程中,宗教觀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即主張信仰自由,不排斥任何宗教,他在《胡注通鑒表微·釋老篇》中論道:
信仰貴自由,佛教不當辟,猶之天主之不當辟也。
且孟子嘗距楊墨矣,楊墨何嘗熄!楊墨而熄,亦其有以自致,非由孟子之距之也。韓昌黎辟佛亦然。唐末五代禪宗之盛,反在昌黎辟佛以后,其效可睹矣。次隋唐以來,外來宗教如火襖、摩尼、回回。也里可溫之居,皆嘗盛極一時,其或衰滅,亦其教本身之不據,非人力有以摧殘之。吾國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故爭雖微,牽涉民族,則足以動搖國本,謀國者豈可不顧慮及此。孔子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使孔子而知有異教,必以為西方之圣而尊敬之。故魯人當法孔子之問禮老聃,不當法孟子之距楊墨矣。
這段話,足以表現陳垣后期的宗教觀。藉此足以說明,陳垣的宗教觀與宗教史學是相一致的,信仰的經歷并沒有成為他治學的障礙。
陳垣宗教史學最具體表征是運用傳統歷史研究的方法來探討宗教歷史,如年代學、校勘學、目錄學、版本學、考據學、辨偽學、金石學,無一不被嫻熟地運用至其中來,因而獲得超乎一般的成就。
其實,對宗教進行歷史研究,最大的困難在于史料的真實性及成果的難以利用。要求得歷史的本源,必須去掉宗教發展史上的迷霧與障礙,而傳統的歷史學方法正是探得歷史真相的利劍。陳垣之所以能在宗教研究史上一舉成名,并且備受歷史學界的重視,除了其良好的史學素養外,史學方法在宗教史研究中的移植與開拓居最重要的一面。如年代學是歷史學家的工具,陳垣在年代學上創獲了《二十史朔閏表》這部歷史研究的必備工具書,又難而及回回教,成《中西回史歷日表》。用之佛教,則撰為《釋氏疑年錄》。這些都是年代學的新收獲,又是宗教史研究的開創性成果。又如,他延續傳統目錄學的方法,希冀在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研究中建立各宗教各自的目錄學著作,構擬了《乾嘉基督教錄》、《中國回教志·經籍志》,最終完成了《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這部繼解題體傳統,而又融匯考據學成果的重要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每一部專論之后,都附有《引用書目》,這在二三十年代較為稀罕。他這樣作,能給進一步研究者提供指南。再如他發表的《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可以說是宗教考古學的先驅。
下面試以金石學為例,談談陳垣宗教學研究中對此的利用。我們知道,金石學是宋代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史學,以考校金石文獻,結合史籍史料研究為特征,發展到清代,金石學達到了很高的成就,也走向了末途。陳垣雖非以金石收藏著稱,但他最擅利用,充分發掘金石文字證信的特征,以之考史,借其明事,以非凡的識見,時創新見。他的《開封一踢樂業教考》即先敘碑文,再引史料,互為比勘,左采右獲,疑義頓釋。最能代表他利用金石和宗教研究相結合的是《道家金石略》的纂集。這部著作雖刊于后世,但發凡起例,資料積聚均為陳垣初定,且增補者也與原輯相別,因而以之作論,也無不當。《道家金石略》實際上是以道家道教之名,循金石學之路,以碑拓為主,積聚道教史料。既破了道書之雜,以碑拓為主,集錄文集、方志中之碑拓材料,如蒼海縛龍,氣勢非凡,又不為金石所約,求古綴殘。大大更新了金石學的內涵,又為治道教史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此外,他對檔案的利用,語錄的采擇,都是前無古人,這些傳統與新興歷史學方法的運用,為他宗教史學的建立注入了嶄新的活力。因而,他的宗教史研究成就,也突破了宗教史領域,而有貢獻于整個歷史學研究。換句話說,宗教史研究的創立與開拓,也為歷史學研究展示了一片新的學術樂園。只要積極地運用歷史學的方法,掌握宗教發展的特征,宗教史的研究是一個富于生命力的陣地。
如果說傳統歷史學方法的利用為陳垣宗教史學的創立提供了工具,那么他對宗教文獻的清理則為他發展宗教史研究提供了創造歷史的場地。用佛教的話說,有了研究宗教之人這個“因”,而獲新史料之接觸這個“緣”,所以臻現于多方創獲之“果”。
誠然,陳垣宗教史料得以大量采獲,也有得力于時代之賜。以佛、道兩藏為例,自來只有少數教內之士知悉接觸其書,學界罕有寓目者。“讀藏”成了不少學者的一種奢望,有清一代,也只有錢大昕、嚴可均、孫星衍、劉師培等人有過這種幸運,大多數只有看過零本殘冊的資歷。生于晚清民初的陳垣,較之他所景仰的前輩,大大幸運了,他自己曾開玩笑說過:唐玄共有三藏,我備有四藏。推測起來,此話不虛。因為《道藏》在1924-1926年印行,《大正藏》也于1936年結集,當時看到龍藏,永樂南北藏以及高麗藏,頻伽藏也不足為奇,自然這是學術時代的幸運。陳垣很好的利用了這一時代之賜,并以卓越的成果回賜了時代。
其實,在當時能觸及到新印各種大藏的在學界也居少數,利用者更是寥若晨星。但陳垣不僅能披沙撿金,而且為了全面系統地探討中國主要宗教,于搜集挖掘史料上更上層樓。他足跡遍天下,登私藏,檢公庫,搜孤本,探秘書。蒼天不負有心人,許多良機接踵而至,無數珍品,一經觸及,即拂塵揚卷而出。象事涉康雍乾嘉四代的天主教史事,陳垣也從清宮檔案、嘉興藏語錄中獨發其秘,可謂讓人稱奇。而《嘉興藏》這樣大套的史料,其中孤本語錄達兩百多種,三百年來,無人知悉,雖得之考釋的艱難,但對他論著的撰成,史事的發明不可謂不大。人們總是羨稱敦煌出土之富,甲骨文發掘之奇,其實,像嘉興藏這樣系統珍藏一類文獻,貌若出土,其價值、作用于佛教而言,也不在敦煌、甲骨文之下。陳垣契機加以開拓并利用,既長成了其學術成就,也為這些史料彰幽闡微,點鐵成金,進而受到后世研究者的重視。因此,陳垣在宗教史料發掘上既導夫先路,又收獲頗豐。同時還襄成了在宗教史學上的獨到造詣和開拓之勞。
固然,由于時勢、機遇乃至地位,新的宗教史料日曝于陳垣眼前,但他對固有史料的把握也至巨至微。從而,借助于他對歷史的把握及方法的造詣,始得開拓出一條中國近代宗教史學的燦爛之道。
三
處于開拓期的20世紀中國宗教研究十分幸運,不僅有陳垣這樣的史學大師全力投入,還有為數更多的杰出學者同樣關心宗教史學的建設,把陳垣視為同道,備加推崇的陳寅恪也對宗教史研究頗為投入,并且碩果累累,為史界所景仰。
由于時局的艱難和健康等原因,陳寅恪的學術研究不如陳垣那樣系統和廣闊地表現出來。他的宗教史研究僅在中古佛教和道教之兩大領域中進行。但他們在宗教研究中互相引為同調,并有許多契合之處,尤其是都以常有的歷史學方法,如考辨、目錄、文獻等為手段,將宗教納入學術研究范圍之中。陳寅恪有關宗教史研究的論著雖然有限,但與陳垣相比較而言,論高旨約,有著其獨特的意義與特征。
首先,他們的著眼點不同,陳垣所注意的是對歷史上諸種宗教形態及其發展史跡的勾勒,以表述其存在,即著眼于歷史的真實,以改變那種漠視、回避甚至讓宗教滯留在迷信、虛幻狀態之中的歷史。陳垣的探討,讓我們在歷史的視野中獲得許多新的知識和新的史料,從而使宗教也進入歷史的范疇之中,使歷史也獲得了更為完整的顯現。陳寅恪則不然,他著力的是佛教,尤其是中古佛教與中國文化、學術的聯系,以之尋找佛教作為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交流、重構、創新,歸根結蒂,從文化的角度出發,探討中外文化的交流,進而探討宗教與政治、文學的內在聯系。因而,他把宗教,尤其是中國佛教視之為一個豐富、多層的學術世界,必然也是一種文化創造。進而論證出,佛教在傳入以后,在文化之中的影響力及關系等。如他論佛典與四聲問題,這不止是一個文化發展問題的解決,也是對佛教華化后與文化的新融匯以及佛教對漢文化的推動力。人們都熟知陳寅恪十分關注漢譯佛典,尤其利用其外語所長。但透過這種具體表征,實際上他所關注的是一種本土文化對外來文化的選擇力及接受度的問題。因為佛教文化作為一種智慧宗教在傳入中國之前,已有高度的繁榮期,并自成體系、特色。與此相應,中華本土文明的創造隨著時代的前進也在不斷地開拓,一種上升期文化與成熟的異質文明的交流的場面如何,其后來的發展怎樣,正是處于五四以來異質文明對中華本土再一次沖擊給陳寅恪所帶來的思考。因而,緊扣文化的脈搏去把握陳寅恪的佛教研究,對我們今天仍然有著巨大的啟示作用。
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揭示出的“學術宗教恒與地域及家庭有關”這樣一項原則,可謂是一種深深的文化思考,《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一文秉此理論觀念的具體闡發在各種論述中,因而只了解其具體的宗教史研究,并不足以明白他對宗教史的論斷,因為時代不允許他作專門的文化史闡述,他對宗教史的闡述既是一種自覺的,又是一種不系統的表達。雖然他曾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讀報告中,較為全面而深刻地表述了他對儒、佛、道三教的看法,但其考察的重點仍在從系統繼承上論道佛的演進的經驗與教訓。
其次,陳寅恪雖也在肆力于箋釋《高僧傳》,批校《弘明集》,比勘《真法》,一秉考據學之真工夫,但他更多的具體考察是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論宗教的史實。人們都知道,陳寅恪精通多種西方文字,與佛經相關之巴利文、梵文、藏文亦無不曉。正是便于此,他從比較語言學的角度,對漢譯佛典問題進行精心的探討。這也是中國宗教史研究上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自然,也只有他才具備這種能真正探本得真的學術手段。當年他曾以“佛典翻譯”一課而馳名清華,正是得力于他西方語言的積累,而對中古史實,尤其是與佛教相關史實的闡釋與解決。顯然,他在語言學領域的嘎然獨造,為他剖析歷史的本真獲得了析疑披霧的利斧。這大概也是陳寅恪所獨有,陳垣所無,其他史學家所難能的史學特征。
綜上所述,二陳都是ZO世紀學術史上卓有貢獻的大師。他們在史學研究,尤其是宗教史研究上表現出各自的特色,并創構出獨有的成果。陳垣對宗教史的全面開拓,史料的整理,學科的建立有著重大的作用,其眾多的成果更為學術的發展提供了典范,是近代宗教史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而陳寅恪同樣以宗教史探討歷史的中心,從文化史的角度,以語言學為特色,析千古之疑,解讀歷史,雖著作為稀,但精審難移,不僅為文化史之大匠,也為宗教史之功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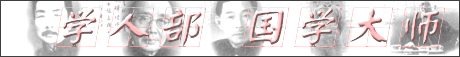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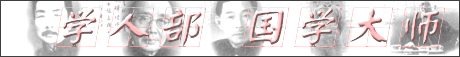

![]() mailto:guoxue@guoxue.com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