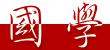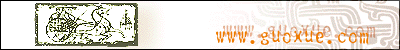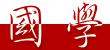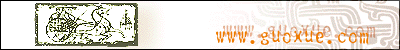|
白壽彝教授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他致力于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已有六十多年,在中國通史、中國史學史、民族史等學術領域里,多有建樹,為我國的歷史科學的建設做出了貢獻。
早年的生活
1909年2月,教授出生在河南開封一個回族家庭。他的父親白吉甫,曾同友人在開封和鄭州兩地合辦電燈公司和商場、飯莊、劇場等,這在當時都是屬于新興資產階級性質的事業。母親錢相云,以能誦讀《古蘭經》受到穆斯林的敬重。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里的教授,從小跟姑祖母誦習阿拉伯文和《古蘭經》,受到民族的傳統教育。
幼年時期的教授,好學,喜讀書,喜歡接受一些新事物。他經常到書攤上翻閱一些介紹科學知識的書,還把書中的內容講給父母兄弟及小伙伴聽。念私塾時,在所聘請的教書先生中,最受他稱道的是呂先生和凌先生。前者崇尚新學,反對死記硬背,教學生讀書,講求理解。后者喜歡談科學知識,教學生讀書,講求系統和比較。這兩位啟蒙教師對教授以后的治學道路有重要的影響。在凌先生的影響下,他進入了由加拿大人開辦的開封圣安得烈學校。當校長問他為什么要學習英語時,他回答說,我要了解世界。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日本廠主開槍打死紗廠工人顧正紅,英國軍警鎮壓為伸張正義而游行的示威群眾,造成流血事件。帝國主義欺壓中國人民的野蠻行徑,使教授思想上深受震動,感到極大憤慨。他同友人張鑄千、賽成惕等發起河南回民滬案后援會,聲援上海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此后,教授不愿繼續留在外國人開辦的學校里念書,認為是一種恥辱,便抱著尋求進步的思想到上海求學,在文治大學讀書。當時他只有17歲。
一年后,他回到河南,在中州大學(今河南大學)繼續學習。
1929年,教授考入原北平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攻讀哲學史。少年氣盛的教授想用二、三年的時間寫出一本超過前人的哲學史。在導師黃子通的教導下,他懂得了讀書的目的和做學問要付出艱辛。燕京大學云集著一批頗負盛名的老一輩學者,陳垣、張星?、郭紹虞、馮友蘭、許地山、顧頡剛、容庚等。他們雖然都不曾親自指導過教授后來所從事的研究工作,但他們是起了作用的。
1932年秋,教授完成了他的學術論文,回到河南,準備服務于家鄉的教育事業,但沒有能夠找到工作。后來,他又回到北平,在禹貢學會和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會做編輯工作,開始對回族史和伊斯蘭教史進行研究,逐漸把研究的重點轉向歷史,寫出了《中國交通史》一書。這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文化史叢書之一。
1937年,教授參加了顧頡剛組織的西北考察團到綏遠(今內蒙)、寧夏一帶考察民族、宗教、水利、文化。在考察中,教授憂慮地注意到西北地區的文化教育,特別是少數民族的文化教育之落后,并把見聞一一作了記錄。由于"七.七"事變,考察中斷。
他和幾個同事由甘肅、青海碾轉回到河南,這時已是1937年冬。
教授回到內地后,攜帶家眷離開開封,經武漢來到廣西,任教于桂林成達師范學校,講授治學材料和方法的課程,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以后,教授來到云南大學文史系任教,系主任楚圖南同志請他主講歷史,并建議他開設史堂史課程。這時,他接觸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深受感動,提高了對抗戰前途的信心。從此,教授并毛主席視為中國的希望,不斷接受進步思想的影響。他參加了回民救國協會,主編幾種穆斯林的刊物,宣傳抗戰救國、民族團結。他講授歷史,從先秦一直講到明清,從單純知知識性的傳授轉向旨在啟發學生掌握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上。因此,學生們都感到很有興趣。日本投降后,教授在南京大學任教,同時還先后同顧頡綱,臧克家主持文通書局《文訊》月刊的編輯出版工作,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籠罩下,《文訊》不斷刊出進步作家和黨的地下工作者的作品。
1949年,教授參加了有范文瀾住處的中國新史學會,擔任常務理事,并與史學界進步學者共同迎來了新中國的黎明。這年夏,他作為南京教育界代表出席中國教育學會籌備會來到北京,隨后又作為少數民族的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加了開國大典。從這時起,他受聘于北京京師范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以后又兼任系主任三十余年。
教育實踐
新中國的成立,給教授增添了無窮的力量和信心。他以極大的熱情投身于社會主義文化教育事業的建設中。作為老一輩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他一直從事歷史科學的研究教學和普及工作,為新中國的歷史科學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付出大量的心血。
建國初期,教授協助郭沫若、侯外廬等籌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并兼任二所研究員,主持明清史研究組的工作。還參加創辦《歷史研究》,宣傳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方向。1956年,他出席了全國科學規劃會議,參與了歷史學科的草擬工作。1958年,他光榮地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
教授是一位有政治頭腦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反映在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兩個方面。他認為,高等學校教育的宗旨,應該是著重培養學生們的智力,啟發他們的思維活動,使他們逐步形成獨立思考和獨立工作的能力,正確地認識對時代所擔負的責任。自覺地做社會主義新人。高等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要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寬厚的知識,以便他們走出校門后能更廣泛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他認為,高等學校的歷史系,除去教授學生必須的歷史課程,還要培養他們的歷史感和時代感,民族自豪感,使他們具有借鑒歷史、觀察未來的能力。為此,他不但強調要重視歷史學科的基本訓練,還強調要指導學生正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
五十年代初,教授在歷史系推廣教研組的教學組織,提倡集體教學,這在當時師資條件的具體情況下是十分必要并且是行之有效的。他還提倡實習教育、直觀教育、課堂討論和歷史晚會等多種教學形式。為了開出文理科八個系的《中國通史》,教授組成了中國通史教學小組,親自指導青年教師編寫教材以至課堂講授,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后來這個小組的教師多數成為歷史系的教師骨干。
1950年,教授在《光明日報》主辦《歷史教學》副刊,結合教學實踐,對歷史問題、歷史教育、歷史教學問題、歷史教材的編寫問題,都努力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進行經驗的介紹理論的探索,這對于當時的歷史教育推進起了積極的作用。
1952年,在蘇聯專家的主持下,教授參與了師大課程教學計劃文科部分的改革。按照計劃,歷史系在理論課程和教育課程以外,設立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紀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現代史等八門課程。經過多年的教學實踐,他感到,這一體系的優點是提倡有系統地進行歷史學習,保證了其完整性,但課程安排得比較死板,缺乏與其他學科的相互配合,有很大的局限性。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系里其他同志的配合下,1979年,在教授倡議下,歷史系進行了第二次課程體系的改革,提出在原有系統教學計劃之外,增設選修課,提倡在全校各系設立現代科學概論的課程,提倡中外歷史比較。時至今日,這一方案豐富了學生學習的深度和廣度,提高了教師的講授能力和水平。它在全國各大院校引起重視并得到推廣,影響是相當大的。1989年,它作為歷史系本科課程體系改革成果,獲得了由國家教委頒發的國家級優秀獎。
數十年來,教授一直關注著歷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他的歷史教育思想也在不斷發展之中。他提倡把歷史教學推向社會,普及歷史知識,讓更多的人懂得歷史,認識時代,提高對祖國前途和人類前途的認識和信心。他認為歷史教育應受到社會上的廣泛重視,應在禮會主義建設中起更大的作用。他所著《歷史教育和史學遺產》,反映了他對歷史教育的主要思想,表達了他對史學應發揮的社會功能的真摯愿望。
學術思想
教授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正象他作為一個教育家一樣,對于他所從從事的事業始終是在不斷地開拓和創新。他的學術研究領域廣泛,造詣深厚,這主要體現在對民族史、中國通史、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的研究上。
教授對于民族史的研究,是從回族史開始的。后來他把對本民族歷史的研究同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的研究結合起來進行,這使他能夠擺脫民族的偏狹性,以科學的態度看待和研究民族史,從而而為民族史理理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從青年時期起開始研究回族史和伊斯蘭教史,寫出不少有學術價值的文章。其中,《從怛羅斯戰役到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錄》是他回族史研究的代表作。這篇論文的重要價值在于它以嚴密的研究成果論證了唐天寶年間中國同大食間的這場戰爭之后,中國國勢并不絕跡于西方,而且唐在西域仍舊保持相當的勢力。戰爭帶來的偶然性影響是:中國造紙術的西行和伊斯蘭教義之開始有漢文的紀錄。1937年他發表的《論設立回教文化研究機關之需要》和《回教文化的運動》(代顧頡剛寫),表述了他對回族史和伊斯蘭教史研究的最早看法和建議。他認為回族應該了解自己在祖國歷史上的貢獻,回漢之間應該加強相互間的理解,這對國家和本民族的發展均為有利。他認為設立伊斯蘭文化研究機關,不只對純學術研究有許多好處,并且對于祖國邊疆問題和國內民族問題的解決也是不可少的。伊斯蘭教文化是世界各種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文化系統,研究過程中,要把學術跟宗教情緒嚴格分開。這些論點,在今天看起來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教授研究回族史近半個多世紀。他的研究成果,主要收輯在《中國伊斯蘭史存稿》中。他還編著了《中國伊斯蘭教史綱要》及參考資料、《回回民族的歷史和現狀》、《回回民族的形成》、《回民起義》、《回回民族的幾個問題》等論著,系統地闡明了回族的發展歷史,認為回族的形成經歷了數百年,是在中國境內形成的民族。他的這一論斷,對鞏固祖國大家庭內部的團結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也是他對民族史學理論的一項重大貢獻。
教授關于民族史的理論,還主要體現在他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論述上。他根據歷史的分析,提出了統一的四種形式,即單一民族的統一、地方性多民族的統一、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社會主義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他認為,中國的統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特點,但全國性的多民族統一是中國歷歷史發展的主流。在民族問題上,在民族關系上,在民族發展史上,民族意識問題是很重要的。歷史上某段時期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分分裂與分散,并不妨礙統一意識的存在。統一和多民族之間是辯證的統一關系。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點,都有他的對歷史上的貢獻。任何民族的利益脫離不了國家的共同利益,任何民族受了損害,國家也必然受到損害。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民族關系是曲折的,有分裂,有統一,有戰爭,有友好。友好是民族關系發展的主流。漢族在全國各民族種,是我們國家的穩定力量,少數民族的合作互助和進步,同樣是中國整個社會進步的主要標志。
教授還十分重視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發展,認為-個民族要振興,必須培養各方面的人材。少數民族的文化和教育是否能振興,既聯系到民族發展的前途,也關系到祖國發展的前途。民族教育應適應各民族的特點而進行,不應一般化,同時又要學習內地教育的經驗,吸取教訓。
教授關于民族史問題的這些論點,在當前民族關系和民族問題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最近,他的《民族宗教論集》已由北京師大出版社出版。
教授重視中國通史理論的研究工作。他對中國歷史上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集中體現在他主編的《中國通史綱要》和多卷本《中國通史》的導論中。這兩部書,是他出于一個歷史家的高度責任感,響應周總理1972年在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上提出的號召而編寫的。書的宗旨在于教育青年認識祖國數千年悠久歷史的面貌,從而增進愛國的熱情。他于1975年開始組織編寫力量。
1980年,《綱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年之間,發行量達八十多萬冊,深受廣大讀者喜愛。《綱要》還有英、日、西班牙、法文、德文和即將翻譯出版的阿拉伯、意大利文版向國外發行。多卷本《中國通史》,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有十二卷,第一卷導論已出版。其它各卷正在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它不同于以往的中國通史之處在于:對民族史給以應有的重視;重視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注意全面考察各歷史時期的社會性質;肯定封建國家的歷史作用;力求表述我國在科技上的歷史成就;重視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位置和作用;注重史書體例的編撰形式。
教授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歷時代長久,它本身的分期問題應受到重視。一般史書都以皇朝作為歷史階段劃分的標準,這是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封建社會的分期應該以社會經濟的發展、階級關系、民族關系和意識形態的總相作為主要劃分的依據。封建社會不同歷史時期的剝削階級、勞動階級的身份上的變化是封建社會的分期標準,也是封建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標志。少數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之階段性發展是劃分封建社會階段的又一重要標志。他提出封建社會階級結構形式主要是封建等級制,所有制的關系主要是封建等級所有制的理論。
由于各地區各民族發展得不平衡,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是單一的。教授認為,在各個歷史時期,有一個主導的生產方式,同時也有多種生產方式的并存,其具體情況是相當復雜的。他提出了多種生產關系并存的論點,他的這個論點,便于對歷史問題進行更深入的觀察,也有利于中國古代社會分期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教授認為,詳細地研究國家職能的起源流變,探索其發展規律,是歷史工作者應擔負的責任。封建國家的性質不能離開一定時代的制約。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封建國家有它的統治職能,也有它的社會職能,應進行具體分析。
教授認為,中國歷史是中國境內多民族的歷史,要遵重各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貢獻。寫中國史,要把中國各民族的歷史跟歷代皇朝史的歷史區別開來,中國史的發展同歷代皇朝史的發展并不能完全一致。從中國歷史發展的總過程來看,如跳不出皇朝史的圈子,就不能說明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歷史的過程,也不能很好地發現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不利于民族團結。
教授主張研究中國歷史,要重視整個歷史的貫通,這是他研究歷史的一個特點。與此同時,又要了解各個歷史時期,中國社會各方面、各層次間的關系,包含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相互之間、各民族相互之間的發展關系,還要研究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包含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國與外國往來和經濟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外社會歷史之比較研究等。
史學史工作是教授近年努力開創的新的史學領域。這個領域,老一代學者中也有拓荒者,但他們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停留在史籍目錄的解題上。四十年代初,當教授開設史學史課程時,所能找到的有關著作,內容也多是關于歷代名著的介紹。解放后,教授以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來解釋歷史問題,對中國史學的發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在六十年代初寫了《寓論斷于敘事》、《談史學遺產》和《中國史學史任務的商榷》,認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是要闡明我國史學發展的規律和民族特點,發掘史學史上唯物主義因素及其同唯心主義間的斗爭。
1963年,教授受高等教育部的委托,編寫供高校學生使用的史學史教材,這就是于1964年8月內部印行的《中國史學史教本》(上)。這本教材擺脫了舊目錄學式的教材體系,力圖通過對歷代史學撰述的探討,探索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在結構和文字表述上都有自己的特點。《中國史學史教本》(上),在史學史學科的建設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教授史學思想進一步發展的標志。
十年動亂結束后,教授在北京師范大學建立了史學研究所和史學史研究室,招收了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還恢復了他在1961年創辦的《史學史資料》,現改名為《史學史研究》。《史學史研究》是國內外僅有的一份研究史學史的專門刊物,它是以歷史理論、歷史教育、歷史文獻學、歷史編纂學為研究宗旨,通過研究以達到建立和建全史學史學科體系的目的。三十年來,刊物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登載了大量有重要價值的文章,為史學史學科隊伍的成長,對這門學科的深入研究,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近幾年來,教授的史學思想不斷在充實和發展。在史學理論上,他提出了歷史的二重性和歷史認識的辯證發展。他認為研究歷史,是研究客觀的歷史而不是寫的歷史。研究客觀歷史不能離開寫的歷史,但寫的歷史不等于客觀歷史。客觀歷史本身有它的雙重性,這就是說,作為一個簡單的歷史事件看,歷史是過去了的,但從歷史事件的各種社會聯系及其影響看,歷史并沒有完全過去。他認為,歷史知識是客觀歷史同主觀認識相結合的辯證關系。就歷史本身講,它是客觀的存在,但對歷史進行的研究、表述,還是主觀的東西,是歷史工作者通過研究工作對于客觀歷史的理解。我們只能努力使主觀認識盡量符合于客觀實際。歷史是可知的,又是不斷發展的,人的認識也是沒有止境的。在一定時期的認識,會比過去有所進步,也必然會有所局限。歷史上某個事件是過去的事情,但過去事情對于歷史的影響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改變它的歷史意義。對歷史的認識越前進一步,就越接近歷史的真實,這是歷史認識上客觀性同主觀性的關系,是絕對真理同相對真理的關系,是認識過程上辯證的統一。
教授強調史學的社會功能,認為史學的主流必須是回答現實生活中提出的問題。他重視對史學遺產的研究,在《史學史研究》刊物的研究方向之外,還提倡對歷史文學和科學技術史的研究。1990年,中國科學院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翻譯出版委員會聘請他為本書的顧問。而他目前正在主編的多卷本《中國史學史》,是繼多卷本《中國通史》之后又一項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科研項目。教授認為編寫這部書是建立史學史學科體體系的一項基本建設工作。這部書的第一卷已經出版,書中詳盡的闡述了教授對史學、史學史的認識和他對史學史學科建設的設想和建議。他認為:史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及其規律,史學史是研究史學本身發展過程及其規律和人們曾經如何研究歷史。從學科體系上說,史學史是更高層次的工作。他主張擴大史學史的研究范圍,在漢族史學史之外還應包括少數民族的史學史,并重史國外史學史的研究狀況,這是十分必要的。他的這種思想同他編寫中國通史的思想脈絡是相一致的。
教授在古籍整理、民俗學等方面也有很大的興趣。他認為,古籍整理工作是認識祖國的工作。古籍中優秀的部份是我們民族精神的結晶。他在學生時代曾編有《朱子語錄諸家匯輯》148卷。七十年代,曾協助顧頡剛主持二十四史標點工作。1983年,他創辦了北京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并擔任所長,主持制定了大型古籍項目《文史英華》的整理計劃。他是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成員,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指導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在中國民俗學會,他是副理事長。
學者的風范
教授學風謹嚴。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論點,也敢于堅持自己認為正確并被事實證明了的論點。他堅持馬克思主義方向,尊重不同的學術意見,既不迎合時尚,也不輕于立異。這種學者風度,在十年動亂期間表現得更為鮮明。當時,"四人幫"大搞影射史學,他們要求史學界全盤肯定秦始皇的歷史作用,作為他們反革命的歷史依據。面對這股歪曲歷史事實的丑惡行徑,教授堅持以科學的態度對秦始皇作出公正的評價。"四人幫"為了徹底摧毀解放以來十七年的教育制度,用突然襲擊的辦法對教育界的專家學者進行文化考試。教授憤然不著一字,拂袖而去。這一舉動使"四人幫"大為惱火,利用他們手中的宣傳工具作不點名的通報。教授保持了一個史學家所應具有的風范,得到了學術界的尊重。
教授研究歷史問題,從不簡單地重復別人的研究成果,也不輕易作沒有根據的結論。這使他能擺脫門戶之見,視野開闊,不斷地深入自己的研究領域。
教授治學,最注重"認真"二字。他認真對待自己的著作,每寫成一章,都要反復思考,推敲。有時為了更正確地表達一個觀點,一種說法,不惜把數萬字的成稿推翻,重新撰寫。他主張,作者應對讀者負責,不應回避個人的辛苦。五十年前,當他潛心于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時,過著流亡的生活。每移居一地,他都利用流動的條件做實地的考察。他在桂林、重慶、昆明等地都做過這樣的工作。在昆明居住期間,教授走遍二十幾個縣,對當地回族的生活風俗、文化、宗教等進行了調查工作。在占有了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礎上,通過分析,第一次寫出了回族自己的歷史和中國的伊斯蘭教小史。五十年后的今天,教授的作風依然如故。在多卷本《中國通史》的編撰工作中,他是名符其實的總主編。為了這項工作,他幾乎是從未有片刻的停歇。教授的眼睛高度近視,有一時期,雙眼幾乎近于失明。在這種情況下,他以驚人的毅力,請助手反復誦讀,完全通過思維能力組織文稿的寫作和審定。在審稿的過程中,他態度非常認真,如果遇到史料問題上的疑點,一定要不厭其煩的予以核實。他不放松任何機會孜孜不倦地工作,這包含四次住院手術和去北戴河療養的日子。
教授認真治學的態度還體現在他在歷史研究的用語上。他斟酌每一個詞匯的使用,注重它們的歷史內容和政治內容。比如,他認為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歷朝應稱為"皇朝"而不是"王朝",王朝應是封建統一國家形成以前的稱呼。他認為封建皇朝的最高統治機構應稱為朝廷,而不是中央。因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不同于朝廷同地方的關系。前者是行政分工的關系,沒有貴賤尊卑之分,后者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是有貴賤尊卑的意義的。
教授重視對中青年學者的培養和提攜。他平易近人,喜歡和年青人交談,教導他們在學術領域里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研究方向;提倡要認真讀書,提倡在寫作之前先要掌握原始材料,養成獨立思考的良好學風;提倡準確、凝練、生動的文風。他努力把自己的思想論點無保留地傳授給后學,并注意他們領悟理論,駕馭資料和文字表述的能力。數十年來,教授為國家培養了不少的教學人才和研究人才,其中包含少數民族的教學人員和研究人員。他曾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民族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宗教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中國教育學會歷史分會會長、北京史學會會長等多種社會學術團體職務。現在是中國民族史學會長、中國明史學會顧問等。
教授在繁忙的教學研究工作之外,還擔任著多種社會職務。建國初期,他是新中國政協代表,,此后,又當選第三至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四至六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同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第五屆全國人大民委副主任,法制委員會委員。還曾擔任國家民委委員、中國回民文化協進會副主任、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民盟中央委員,還是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代表。他以極端負責的態度從事各項有關的工作。1984年10月1日,教授作為少數民族的代表登上天安門,參加了文革后第一次舉行的國慶大典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
在對外活動方面,教授是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曾出席過在芬蘭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他還曾擔任中蘇友好協會、中國印尼友好協會、中國國際文化交流協會、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中國亞非友好學會、國際和平中國組織委員會、中國統一促進會等的理事和中國阿富汗友好協會會長等。曾訪問蘇聯、日本和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科威特、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國,促進國際友好往來和學術文化交
流。
精神矍鑠的白壽彝教授,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極其樂觀。他始終以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自勉。他認為,歷史、歷史學,不只是一門研究過去的學科,更重要的是一門繼往開來的科學。六十年來,他已編著了二十余部書,主編了多種有影響的刊物。然而他并不滿足。他常說:我覺得自己在七十歲以后,才真正開始懂得一點學問。現在,我還有許多工作正處在起步階段。
六十年過去了,教授的工作是鏤金、是琢玉,為我們樹立了為人師表的典范。
輯自《白壽彝史學論集》,本文作者劉雪英曾長期擔任白壽彝學術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