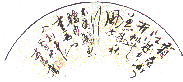馬一浮先生原名馬浮,浙江紹興人,1883—1967,生于成都,卒于杭州。梁漱冥譽其為:千年國粹,一代儒宗。
先生論詩“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細,第四要神韻高”謂“四者備,乃足名詩”最感其第一要胸襟大點的痛快。先生喜陶公,陶公作詩直抒胸意,大含細入,元氣磅礴,真堪大胸襟。得陶詩之旨即可明先生之境。
十一歲時,母病劇,卒即,考其學業,指庭前菊花命作五律,限麻字韻,先生應就而答:“我愛陶元亮,東籬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種,移來處士家。晨餐秋更潔,不必羨胡麻。”其母聽后且喜且憂。喜的是,“兒將來不患無文”,馬一浮16歲赴縣試,列榜首,人稱奇。17歲游學上海,習多種文字,直讀原著;創辦翻譯雜志興動學風;赴美日窮究知識。至24歲寄居杭州廣化寺,發憤杜門,專研國學,廣讀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一代高僧弘一法師曾喻,若有人日讀兩本書,讀輒能誦,窮其一生也不及其學。概先生學問之精博可窺一般。其母憂的是“詩乏煙火味,則少福澤耳。”后來學人劉夢溪謂“馬一浮為二十世紀師儒中一個真正隱者。”兩種說發不同角度闡述:一位母親如何也是不情愿自己的兒子獨立寒處,哪怕所居的是人生境界的最高點。而做為歆羨者則不能不為所瞻仰者立一名目,讓后學者知其秉性境界。
先生廣涉西術而終歸東學“博涉諸子,精研老莊,深探義海,返求六經。”故其道直接孔孟,印合濂、洛、關、閩諸賢,深究義理,畜德躬行,明學問而化成血脈。值亂世異說惑眾,人為戲論所宥,雖先生有“為往圣繼絕學”之志,然儒術見拙于世,慮“若稱性而談,則聞者恐窩”,遂有“化民成俗,固將望諸師友,窮理盡性當敕之在躬。”之說,取道并行不悖之旨。故有北大校長蔡元培、陳百年等多次力邀而未就。然一生亦有兩次公開講學,第一次,38年避戰江西泰和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貞大師禮聘而講授國學;第二次,39年聘為四川樂山烏尤寺復性書院主講。兩次講學總共不過七年,稱其隱士也是允當。而性格狷介,不肯流俗害性,一生持道固守,亦可說少了許多世俗之福。而我認為先生一生只是盡了性份內的事,做人做事做學問從自己胸襟內直出而已。
馬一浮先生認為人人性份具足,只須向內體究:知性而率性,而踐形,而盡性。先生知性深,率性任意,踐形用力,識見自然高卓,復性書院時曾提四教教人“一曰主敬,二曰窮理,三曰博文,四曰篤行。”所謂主敬,為涵養之要者,持志率氣,“先以收攝,繼以充養,則其沖和廣沛之象可徐復也。”敬為入處,得門而入方可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再而優游涵泳,得以淘養,一收一縱間,語盡了為學入德之道。敬,是二程夫子提出的一個哲學概念,馬一浮先生繼之進行了更系統充實的闡述。所謂窮理,為致知之要者。凡與物事當須“反求自心,仔細體究,隨事觀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故要“反求自心”。要將自心所具與所求了解的端詳,故要“仔細體究”。“隨事觀察”則是要通曉事與理間的互證。所為博文,為立事之要者。博,通而不執。立,確乎其不可拔。文,天地間一切事相。事,家國天下事皆事。簡單的說,也可稱為“通經致用之要”。所謂篤行,為進德之要者。即是知行合一之旨,馬一浮一直強調“中土先哲,本其體驗所得以為說。”體即知性;驗即為踐形。體用不曾為二。書院時曾有一學生被委派負責帳房,學生以為自己是來學道的確來做了這等雜事,多有不快,馬先生即以此意教誨。這四教將學問、德行漸頓之旨說得痛痛透透,圓融無礙,學者可由此徑終身而不改。
然而世事多有變術,中國學術千年來本已枝蔓旁雜之極致,而復有西學沁入,亂世中群淆混亂,本此馬一浮于江西泰和時講學始標六藝之說,《論六藝該攝一切學術》、《論六藝統攝一心》、《論西來學術亦統于六藝》、《舉六藝統類是始條理之事》,其說振聾發聵。亦有議其偏疏者,而識其大者即見先生是在對中國傳統固有學術進行著思想上的疏理整合,對外來學術與固有學術的糾纏本著極高明的識見與躬行心得而進行了大的統類。遂六藝之旨得以彰顯,中國傳統生命得以復興。
先生本述而不作之旨,鮮有專著,其今之書,多是講稿、信扎的集刊,但涉及的問題之廣令人驚嘆,然往往一兩句話即撥明事相,令人洞開,如論三氏,“從本源上看,儒佛等是閑名,孔佛所證之是一性,果能洞徹心源,得意忘象,則千圣所歸,無不一致。”“大抵儒家簡要,學者難于湊泊,釋氏詳密,末流又費分疏。”生死之說,“通乎晝夜之道,即通死生之說。”論學,“夫學無古,不可以自固;學無內外,不可以自礙;學無終窮,不可以自封。”凡此種種,啟人深思。
先生之說包羅萬象、致幽致玄、細密嚴謹,其理說真堪謂大含細如。
“小學不經,則遣詞不能安;經術不深,則說理不能當。”先生學術精微,故引用古語從心所欲不逾矩,化裁字句遣放安排于文章但覺古今中縱橫而不生突兀,字字稱量而出,緇珠不差,故而謂其文章元氣磅礴。
終論先生之胸襟謂何,取宋賢張載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