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中國古代文化融合在經(jīng)典之中,漢魏以來的思想文化變化,首先表現(xiàn)在對于經(jīng)典的重新闡釋之中。王弼的玄學(xué),并不是通過自創(chuàng)得以建立的,而是經(jīng)過對于經(jīng)典的闡釋得以建成。在這種闡釋過程中,化入了他卓著的思想智慧。王弼善于尋找儒道兩家思想的共同點,加以調(diào)和,同時,也大膽地進行重解。通過其思想與智慧的運用,融合了儒道兩家思想,重新確立了新的人格范式與情性倫理,從而使六朝文論有了新的形而上之精神蘊涵。通過闡釋智慧的角度去認識王弼哲學(xué)與六朝文論的生成,是大有意義的。
關(guān)鍵詞 王弼哲學(xué) 闡釋智慧 六朝文論
作者簡介 袁濟喜,1956年生,中國人民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王弼是三國時魏國的著名思想人物。 [①] 他的思想智慧對于六朝文論與美學(xué)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從現(xiàn)有簡略的傳記中可以看出,王弼是一位聰慧的少年哲學(xué)天才,悟性極高。 《三國志 ·魏志·鐘會傳》載:“(王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馀卒。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馀,好老氏,通辯能言。”又說“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 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tǒng),著《道略論》,注 《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 嘗云 ‘ 見弼《易》注,所悟者多。 '” [②] 從這些資料來看,王弼在附會文辭,即文本注解上不及何晏,但在 “自然拔得”,即悟性上卻遠遠超過何晏。文本注解主要依賴于知性,強調(diào)的是客觀性,而經(jīng)典闡釋則主要得力于悟性,它依賴的是創(chuàng)新的勇氣與能力,是智慧的彰顯。顯然,人性的奧區(qū)在智慧領(lǐng)域更能得到顯現(xiàn)。六朝思想風采所以蓋過兩漢,正是在這一人性的奧區(qū)上超越了前人的皓首窮經(jīng)。當然,他們的注經(jīng)功夫也絕不亞于漢代。王弼的經(jīng)典闡釋,善于調(diào)和學(xué)說,啟人智性,輻射到其他的思想與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六朝文論在人格理想、審美價值觀、以及自然之道方面,深受其沾溉,這已為學(xué)界所承認。尤其要強調(diào)的是,六朝文論與美學(xué)受其影響,充滿著智慧與悟性成份,比如《世說新語》中蘊涵的文藝觀念,《文心雕龍》和《詩品》中的文學(xué)批評風采等,足可以顯出這一點。
本文想強調(diào)的是, 王弼的意義不僅在于創(chuàng)建了貴無的玄學(xué)思想體系,而且體現(xiàn)在他重新解釋儒道,會通兩家學(xué)說方面所作的闡釋貢獻方面。如果說王弼玄學(xué)是一座至深的堂奧,那么闡釋功夫則是進入這座堂奧的橋梁。堂奧固然是主體,但是如果沒有津梁與階梯,則無法進入其中。就此而言,津梁與階梯又成為決定性因素。以往學(xué)界研究王弼哲學(xué)對于六朝文論與美學(xué)的貢獻,大多留意其學(xué)說影響方面,而對于闡釋智慧則關(guān)注不夠,包括筆者自己關(guān)于六朝美學(xué)的著論方面。 [③] 近年來,隨著六朝文論研究的深入,人們開始注意王弼在闡釋智慧方面的成就,本文想就此作一些討論。
一
王弼的闡釋智慧,首先體現(xiàn)在他通過這種智慧的運用,消解了兩漢經(jīng)學(xué)文本注解方式對于人們思想的禁錮,開啟了文論精神的解放先河。
要理解王弼的闡釋智慧,首先要從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本特點談起。中華民族的文化起源于黃河長江流域,至先秦時代即已奠定了以經(jīng)典為主要載體的思想文化。嗣后,經(jīng)典的價值與作用在兩漢進一步獲得發(fā)展。尤其是儒家經(jīng)典在漢代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相結(jié)合,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上面。當然,道家老子的經(jīng)典地位在漢代也一直受到重視。正如劉勰《文心雕龍》中的《宗經(jīng)篇》所說:“ 經(jīng)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qū),極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份,這段話至少說明了經(jīng)典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載體,從王弼主要詮釋過的《周易》、《老子》、《論語》這三本經(jīng)典來看,它是儒道兩家的主要經(jīng)典,其中蘊涵著極為豐富的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容,有著充分的闡釋空間,王弼正是鑒于此而施展了其才華與智慧的。王弼的這種闡釋選擇,本身就極具智慧的意義。從文化傳統(tǒng)的接續(xù)來看,盡管東漢末期儒家經(jīng)典受到挑戰(zhàn),但是要從根本上替代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文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更何況王弼只是一位家境一般的少年。因此,王弼要創(chuàng)建新思想、新學(xué)術(shù),就只能走經(jīng)典解釋的路徑。這樣一方面可以獲得傳統(tǒng)的承認,另一方面也可以出新意于經(jīng)典之中。這種智慧其實也是一種雙贏的策略。
盡管史籍上稱王弼是年少天才,將玄學(xué)貴無論歸結(jié)為王弼的獨創(chuàng),但是從漢魏以來學(xué)術(shù)思想史的演變路徑來看,王弼的思想變革與漢代經(jīng)學(xué)的末途是互為因果的。 兩漢的封建最高統(tǒng)治者很注意通過行政力量來壟斷對于儒家經(jīng)書的解釋。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六章《兩漢之際的思想》中,曾根據(jù)史料,詳細地臚列了西漢至東漢末年時期,最高統(tǒng)治者通過官學(xué)的壟斷形式,以使經(jīng)學(xué)服從于統(tǒng)治者的意愿,從西漢武帝組織的經(jīng)學(xué)射策,到東漢肅宗時的白虎觀會議莫不如此。作者指出: “漢代統(tǒng)治階級思想的宗教化,是通過了官學(xué)形式的復(fù)活,在政權(quán)與教權(quán)合一,帝王而兼教皇的嚴格思想統(tǒng)制下而實現(xiàn)的,并由此而顯示出露骨的奴婢作用。” [④] 這一觀點,對于兩漢思想界的官學(xué)壟斷形式特點的把握是很準確的。文本原來是用來載道寫意的,然而一旦與權(quán)力相結(jié)合,反而成了一種拜物教般的文本守護,對于文本的捍衛(wèi)成了衛(wèi)道的首要任務(wù)。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異化。西漢經(jīng)師為了爭立學(xué)官,產(chǎn)生了種種怪誕之事,隨之而來的對于經(jīng)學(xué)的解釋,也是見仁見智。西漢學(xué)者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就指出: “往者綴學(xué)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茍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xué)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xué),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劉歆指責那些經(jīng)師固守一些既定的經(jīng)學(xué)文本,在學(xué)術(shù)上惟知分文析字,煩言碎辭,而根本不能通曉古代典章制度的來由;只知道抱殘守闕,將經(jīng)學(xué)變成自己的吃飯家伙,而拒絕新發(fā)現(xiàn),對于事關(guān)朝廷的禮義制度則一無所知。通過這件學(xué)術(shù)個案的剖析,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學(xué)術(shù)與權(quán)力相結(jié)合的結(jié)果,勢必喪失求真務(wù)實的精神,而多了一些保守專橫的味道。錢穆先生也在他所著的《國學(xué)概論》第四章《兩漢經(jīng)生經(jīng)今古文之爭》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博士經(jīng)生之爭今古文者,其實則爭利祿,爭立官與置博士弟子,非真學(xué)術(shù)之爭也。” [⑤] 這種情況在東漢末年王充的《論衡》中,成為激烈批評的對象。 王充為此在《論衡·超奇》中提出了新的思想價值觀:“ 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王充強調(diào)士人的價值不在于皓首窮經(jīng),而在于從文籍中引出自己的獨立見解,并且能夠應(yīng)用自如。他之所謂“鴻儒”,是指那些敢于創(chuàng)新,不拘一格的思想家,重在精神智慧的運用上面。而那些惟知固守一經(jīng)的儒生是最沒有出息的。王充呼吁產(chǎn)生王弼那樣大膽革除學(xué)弊,開拓一代學(xué)風的人物。
王弼哲學(xué)對于漢魏之際思想的革新,不僅在于他提出了以無為本的玄學(xué)思想,從而推動了魏晉南北朝思想文化的變革,而且在于他的理論智慧是超人的。過去的研究者對于他在這方面的貢獻關(guān)注不夠,其實,古人對于王弼在這方面的良苦用心倒是很關(guān)注的。《三國志 ·魏志·鐘會傳》云:“(王)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馀卒。”裴注引何劭《王弼傳》載:
弼幼而察慧,年十馀,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yè),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 ” 弼曰: “ 圣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xùn),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 ” 尋亦為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嘆之曰: “ 仲尼稱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 ”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王弼與漢儒的迷滯經(jīng)術(shù),沉溺章句截然不同,善于引發(fā)新論,不拘舊說。王弼好論儒道,其長處是將二者之間加以溝通,尋求二者之間的共同點與可以互補的地方。王弼在應(yīng)答別人所問孔老同異時回答得很巧妙,也很智慧。自古以來,孔老學(xué)說的同異一直是學(xué)者們關(guān)注的中心話題。孔老作為不同的流派,固然在自然觀與社會人生觀上面有許多差異,但是從總的背景來說,又有許多共通的地方。比如他們都是植根于中華農(nóng)業(yè)文明基礎(chǔ)之上的學(xué)派,對于天人合一的人生與文化追求是認同的,只不過在途徑與方法上有著許多不同的主張,他們都不反對階級社會的存在,孔子的大同社會與老子的小國寡民可以互補,都是以人際社會的和諧相處為前提的。從文化出身與來歷來說,孔老俱出于西周王官,這一點班固的《漢書 ·藝文志》說得很清楚。甚至有人指出他們有著師承關(guān)系。(如司馬遷的《史記》與近代章太炎的《論諸子學(xué)》)但是在理想之治與理想人格的建構(gòu)方面,孔老確實有著很大的差異。老子與莊子主張將天道自然置于社會人事之上,力主在自然無為的狀態(tài)下,實現(xiàn)人生的自由與人格的解放,而孔子與儒家則將禮法之治作為天道秩序的最好體現(xiàn)。因此,“圣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
當然,名教與自然并不是不可以調(diào)和的。老莊的自然之道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可以從更高的哲學(xué)層次來為名教立法,使名教即階級社會的政治與意識形態(tài)獲得本體論上的支撐,從而更加穩(wěn)固。聰明的統(tǒng)治者與哲學(xué)家怎能對如此豐厚的思想資源棄置不顧?這豈非愚不可及?因此,王弼以其天才與早慧,在回答裴徽時提出,無是最高的自然與人生境界,圣人以無為體,處處體現(xiàn)出以無為貴的境界,因而他們無需多說。而老子未免于有,還不能到達無的境致,因此倒是常常以無為訓(xùn),告誡世人要重視無的作用。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王弼清醒地認識到孔子的作用與地位,即使是在陵夷如三國的年代也是不可動搖的,要想從正面去推翻孔子的權(quán)威是徒勞無益的,于是最好的辦法便是偷梁換柱,盡力會通孔老,表面看來是抬高孔子,貶低老子,實際上其立論的大前提是倡言作為精神本體與自然之道的 “無”,它是萬物最高的范疇,孔子則是實踐無為之道的楷模,老子體無不足,未免于有。
王弼在倡言以無為本的思想前提下,表面尊孔抑老,實際上,使人們不知不覺入其彀中,成為王弼貴無論的思想俘虜。這是王弼的聰明所在。而他的這種左右逢源,借力打援的解釋智慧實在令人嘆為觀止。何晏對王弼的嘆語是 “可與言天人之際”,意思是指與王弼可以重新討論天人之學(xué)。中國哲學(xué)的中心問題也可以說是天人之學(xué),孔老儒道的根本差異與可以會通的地方也可以說表現(xiàn)在這方面。何晏的意思,也并不是認為只有到了王弼時才可以討論天人之際。事實上從先秦到兩漢思想界,人們一直在討論天人關(guān)系,董仲舒的哲學(xué)以探討天人感應(yīng)為軸心,是兩漢思想的典型。與此相適應(yīng),自然與名教的關(guān)系也一直是儒道兩家關(guān)注的中心,只是所提出的答案不同而已。之所以說可以與王弼討論天人之學(xué),是指王弼重新開始了對于天人之學(xué)這一古老命題的討論,賦予這一古老的哲學(xué)題目以全新的思路,從而蕩開了思想與學(xué)術(shù)的心扉。“言天人之際”,是思想闡釋的智慧高低的分野,也是魏晉名士辨才優(yōu)劣的體現(xiàn)。六朝文論中關(guān)于天人關(guān)系的突破,即從兩漢文論與思想界濃重的天人感應(yīng)的神學(xué)氛霧中掙脫出來,將天人關(guān)系建構(gòu)在新的人文與理性基礎(chǔ)之上,賦予山水自然以全新的神韻,使人格主體在對于天人關(guān)系的重新審美觀賞中得到解放。這不能不說同王弼的重新闡釋過的玄學(xué)天人觀相關(guān)。最典型的便是嵇康玄言化的山水詩中透發(fā)出來的清峻鮮麗的人文氣息。這是與兩漢沉滯的大賦不同的審美新觀念。與此相適應(yīng)的便是文論中對于自然界建立在感興說之上的情物范疇。它是六朝文論中最基本的范疇之一。
與天人關(guān)系相聯(lián)的,魏晉文論與美學(xué)的另一主題便是人格理想,體現(xiàn)出人生與藝術(shù)的統(tǒng)一。王弼通過闡釋智慧,重新樹立了新的人格理想,影響到嵇康與《世說新語》中的人格模式與美學(xué)思想。對于儒家的理想人格,王弼也力圖用道家與玄學(xué)的理想人格來充實與改造。儒家的人格執(zhí)著而堅實,但往往失之于小氣與拘執(zhí),而道家人格則高蹈無為,通脫自然,兩種人格的互補方能成就所謂既入乎其內(nèi)又出乎其外的人格境界。王弼正是利用他的闡釋功夫力圖打通二者之間的關(guān)節(jié),使之融會貫通,在這種闡述中顯示出他的哲學(xué)天才與智慧。《論語 ·述而》中有“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王弼闡釋道:
溫者不厲,厲者不溫,威者不猛,猛者不威,恭則不安,安者不恭。此對反之常名也。若夫溫而能厲,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調(diào),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質(zhì)備,五材無名也。(《論語釋疑》) [⑥]
《論語》中說孔子的 “溫而厲”云云,原意是指孔子用中庸之道來做人,顯示出至中不偏的人格精神。儒家主張為人處世要恪守禮義,符合中庸無偏的標準。而道家與玄學(xué)所提倡的中和則是從精神本體論的角度去說的。這便是倡導(dǎo)一種精神超越,深藏不露的為人處世的態(tài)度,如果說儒家的中和是力主精神與人格的持中守和,不偏不倚,以禮度為約束,而道家的中和范疇則有著特定的含義,即主張超離塵世,合于天道,是與儒家的中和大相逕庭的。 [⑦] 老子在他的學(xué)說中一再倡言這種人格精神,用來明哲保身,蹈光晦塵。王弼用他的理論調(diào)和自然與名教的矛盾,使人格境界達到內(nèi)外兼周的境致。并且與政治人格相融合。從政治學(xué)意義來說,王弼所倡言的中和質(zhì)備,五材無名的理想人格顯然帶有魏晉特有的名理學(xué)意義上的君王之材,即人主無為于上,臣子有為于下。是將劉劭《人物志》中的理想人格加以向前發(fā)展。這樣,王弼通過將孔子中庸型人格修養(yǎng)改造成兼容儒道玄的理想人格,進一步確立了他的玄學(xué)思想。這種人格也是當時年代中的人格范式。共特點是用道家的形而上與儒家的形而下融為一體。這種人格理想在曹操的政治實踐,以及劉劭的《人物志》中,有著鮮明的貫徹與闡述。是時代思潮的表現(xiàn)。后來宋代的理學(xué)思路也大致同于此。
王弼的玄學(xué)人格境界論,還通過對于《周易》的闡釋得到了很好的發(fā)揮。王弼之所以選擇《周易》來注解,也是看到了《周易》這本書中充滿了宇宙與人生的奧秘。它是認識與體驗的統(tǒng)一,介于宗教與哲學(xué)之間。 《論語 ·述而》中有:“子曰: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xué)易,可以無大過矣。”王弼通過對孔子晚而喜《易》,從《周易》中學(xué)習(xí)與掌握人生自由的史例,對此加以發(fā)揮:“《易》以幾神為教。顏淵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訓(xùn),微言精粹,熟習(xí)然后存義也。” [⑧] 王弼認為《易》的博大精深,貫穿天地人之間,是神靈世界與現(xiàn)象世界無窮奧秘的演繹。他對于人格境界的闡釋,在對于《周易》的解讀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 《周易》關(guān)于宇宙和諧之美的觀念,是通過陰、陽這一對立統(tǒng)一的范疇來架構(gòu)的,它在陰陽、剛?cè)岬葘χ胖衼碜非缶猓非蠛椭C,追求流變,這也是它超軼孔子、荀子和《中庸》作者的地方。《周易》認為和諧就是兼容對立的兩端。《周易》的乾卦《文言》指出:“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fā)于事業(yè),美之至也。”也就是說,君子之德如黃色一樣,居中不偏,含蓄內(nèi)在,發(fā)散應(yīng)物,是最美的德行。王弼在注坤卦“六五、黃裳、元吉”時指出: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坤為臣道,美盡于下。夫體無剛健,而能極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順之德,處于盛位,任夫文理者也。垂黃裳以獲元吉,非用武者也。極陰之盛,不至疑陽,以文在中,美之至也。” ((《周易·坤卦注》)
王弼認為坤卦的六五之爻體現(xiàn)了陰柔含蓄之美,他對坤卦的美德作了詳盡的贊述。又如《周易·履卦》的“九二”為“履道坦坦,幽人貞潔”,王弼釋曰:“履道尚謙,不喜處盈,務(wù)在致誠,惡夫外飾者也。而二以陽處陰,履于謙也,居內(nèi)履中,隱顯同也。 履道之美,于斯為盛,故履道坦坦,無險厄也。在幽而貞,宜其吉。”(《周易·履卦注》) 這是說履卦的“九二”充分展示了履道的美德,它以陽處陰,謙虛居中,不好外飾,所以是美和利的。相反,處于二、五之外的卦,往往有兇兆,深宜防之。如乾卦的“六四”為“括囊,無咎無譽”,意為處于此爻,應(yīng)該緘默不言,謹慎防之。王弼解釋此中原委道:“處陰之卦,以陰居陰,履非中位,無直方之質(zhì),不造陽事,無含章之美。括結(jié)否閉,賢人乃隱,施慎則可,非泰之道。”(《周易·坤卦注》)意謂“六四”以陰居陰,不得互補,所以“履非中位”,宜謹慎行事。尚“中”的觀念,是《周易》教人判斷吉兇、立身行事的一條重要原則,它也滲透在對事物的審美判斷之中。
《周易》的“中和”觀念還吸收了春秋間思想界“泄其太過,濟其不及”的觀點,用互相補充來營造“中和”之美。《周易》六十四卦首尾兩組四卦,體現(xiàn)了這種安排。它開頭一組兩卦是乾和坤,然后二卦的互相交感,產(chǎn)生各種變化,呈現(xiàn)“二二相偶,非覆即變”的狀況,經(jīng)過中間六十四變的反復(fù)變化,最后以“既濟”、“未濟”二卦結(jié)束了整個過程。這二卦的卦象正好是開頭兩卦乾卦和坤卦的交互補充,也就是各以所有,濟其所無。六十四卦的演變體現(xiàn)了由對立開始到互相補充,最后達到平和均衡的效果。再從許多卦的演變來看,也體現(xiàn)了這一點。如《周易·萃卦》的彖辭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yīng),故聚也。”王弼闡釋道:
但順而說,則邪佞之道也,剛而違于中應(yīng),則強亢之德也。何由得聚,順說而以剛為主,主剛而履中,履中以應(yīng),故得聚也。 (《周易·萃卦注》)
這也就是說,萃卦得妙處在于互相補濟,如果一味順從討好,則為邪佞之道,但一味剛厲也會失之強亢,只有剛?cè)嵯酀拍堋奥闹幸詰?yīng)”,獲得“萃”的效果,“萃”,也就是和合聚會之美,但這種美是互相補充之美,也就是孔子說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意思。王弼通過《周易注》所闡發(fā)的這些原則與方法,對于中國古典文化和美學(xué)的辯證法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文心雕龍》的“唯務(wù)折衷”的方法論就直接受益于《周易》與魏晉玄學(xué)。
二
王弼還從崇尚自然的思想出發(fā),對儒家的情性論作了重新解釋。情性論是中國古代哲學(xué)的中心范疇,也是文論與美學(xué)的立論基礎(chǔ)。儒家的情性論是主張性善情惡,以性控情,這顯然違背了自然之道。從方法論上來說,也沒有使情性獲得本體論的論證,只是停留在情性論的社會學(xué)范疇上。兩漢的情性論無論是董仲舒的性善情惡論,還是劉歆的性靜情動說,都存在著這樣的不足之處。這樣的觀念在漢末魏初仍然具有相當?shù)挠绊憽?
王弼在與何晏辨圣人之有情無情時,依恃于他的思想智慧,提出圣人有情而不累于情。《三國志 ·魏志·鐘會傳》裴注附何劭《王弼傳》云:“何晏以為圣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圣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yīng)物,然則圣人之情,應(yīng)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fù)應(yīng)物,失之多矣。”很顯然,玄學(xué)家何晏顯然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根本否認理想人格圣人存在著現(xiàn)實的情欲,圣人無喜怒哀樂。 何晏《論語集解》中注“性與天道”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聞也。”可見何晏比較強調(diào)“性”的合于天道,而天道又是神圣幽微的精神本體。這一說法,區(qū)別了他之不同于兩漢哲學(xué)家將情性說成是五行血氣化生的人性論。固然精妙,但是 違背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實文化心理基礎(chǔ)。因為中國文化本是一種世俗文化,若沒有現(xiàn)實的基礎(chǔ)支撐,再玄妙的學(xué)說也不可能走向人間,為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尤其是為上層人物所喜歡。王弼對于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再者,人倫范圍的情性怎能不食人間煙火呢?即使是孔子也提出過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并不否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樂。
王弼深契于性情之道,對于儒道兩家的情性精神是掌握得很好的。他充分發(fā)揮了中國文化善于調(diào)和的特點。通過闡釋傳統(tǒng)的情性說,再次提出,儒家的情性觀的現(xiàn)實性基礎(chǔ)可以作為立論的依據(jù),但是道家的性情觀可以作為向上提升的形而上的精神本體,二者之間并非水火不相容,恰恰相反,它們是可以互補互融的。圣人既非沉弱世俗的俗人,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人,而是既同于凡人又能超越凡人的高人。王弼強調(diào)人格精神的現(xiàn)實性與理想性二者的融合一體,精神的高尚與世俗的享受可無大礙,兩不相妨。從而使儒道人格理想在情性觀上得到調(diào)和,也使兩漢儒家的情性觀得到修正。它對于六朝文學(xué)理論中的緣情感物,超越世俗的基本價值觀念顯然有著直接的啟示。
王弼這種應(yīng)物而無累于物的情性觀,在注釋《周易》中得到了很好的闡就。中國古代文論,不僅啟示人們關(guān)注文藝的審美對象與主體的感應(yīng)互動關(guān)系,而且深入到文藝生命精神層次上面。《周易·咸卦》敘說了兩性的交感不僅是生理的交配,更是情感與精神因素的激活,從而區(qū)別了人類交感與動物交配的不同之處。《周易·咸卦》云:“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yīng)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卦》(兌上艮下)為《周易》下經(jīng)之首,是《周易》作者歸納的人倫要義之首,故王弼注曰:“天地萬物之情 ,見于所感也.凡感之為道,不能感非類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類之義也。”在《周易》的作者看來,天地萬物化生來源于萬物所感,感是陰陽二氣的交感化生,在男女兩性的交配中得到最典型的展現(xiàn)。作者認為,從感應(yīng)的角度可謂說盡萬物演化與生存的要義。而照王弼的理解,感是有條件的,即同類相感。最有代表意義的是男女之間的交配,不僅兩性相引,而且要位置得當。王弼注《咸卦》中九四爻時曰:
處上卦之初,應(yīng)下卦之始,居體之中,在股之上。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感而不以之于正,則至于害,故必貞然后乃吉。
王弼認為此一爻中所指位置是最佳位置,男女身體位置相合方能享受到性生活中的快感,不僅肉體上有快樂,而且心神上也能得到快感。王弼強調(diào)男女交感的高峰時表現(xiàn)為“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強調(diào)感應(yīng)的最佳狀態(tài)并不僅僅是肉體快感,而是心神即精神的快樂,這種說法對于理解審美感受的本質(zhì)是非常有啟發(fā)作用的,因為并不是任何感應(yīng)對于人類都有是意義的,其中存在著一種高峰體驗值所在,審美與文藝創(chuàng)作則是這種高峰體驗的集中表現(xiàn),這種體驗即是生命精神的爆發(fā)與激活,中國古代文論大力主張的即是這種文藝的生命體驗,將其視為最高的境界。王弼的闡釋對于六朝文論重在精神蘊涵的感應(yīng)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啟發(fā)作用。
王弼對于情性觀的重釋,蘊含著人性論上的變革。《三國志 ·魏志·鐘會傳》裴注附何劭《王弼傳》在緊接著上面的一段話之后,又記載:
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 “ 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yù)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nèi),然而隔逾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顏子,可以無大過矣。 ”
表面看來,這是王弼答荀融的一封開玩笑的信。然而其中卻蘊藏著極深的思想火花。荀融與何晏的思想方法一樣,表面在推舉老莊與玄學(xué),然而卻抽去了老莊與玄學(xué)最根本的人性論本體,這就是王弼所說的 “自然之性”,即人的自然本性,人有自然本性,故“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據(jù)《晉書·王衍傳》記載 :“ 衍嘗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不自勝,簡曰: ‘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則情之所鐘,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王弼在《論語釋疑》中說:“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yīng)感而動,則發(fā)乎聲歌”,又說:“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情正實而后言之不怍”,這段話實際上宣明了一個哲學(xué)的道理,即荀融與何晏張揚的“ 尋極幽微 ”,也就是玄學(xué)的本體論如果不能以人為本,建立在對于人的自然本性的認同與尊重上,則只會成為一種失卻人格靈魂與人生意義的“玄遠之學(xué)”,是不會被士人與社會所接受的。這是王弼思想最值得珍視的亮點之一。它說明哲學(xué)的終極追尋必須建立在以人為本的基礎(chǔ)之上。形而上的精神是以人的自然存在作為平臺的。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特定形態(tài)下的人道情懷與人文精神。贊同王弼思想的西晉玄學(xué)家王衍公然指出,何晏所說的那種“圣人忘情”是士大夫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世界,人們寧肯要那種“情之所鐘,正在我輩”的人格,也不愿意去作不及人情的“圣人”。“情之所鐘,正在我輩”,實際上是魏晉風度的人格宣言。對比后世理學(xué)家的所謂“存天理,滅人欲”,人們更可以看出魏晉風度的人格精神之美。王弼強調(diào)“ 自然之不可革 ”,認為即使是孔圣也不能革除人的自然情感,更何況凡人?同時代的名士 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正是緣于這種人性論的。王弼建構(gòu)人格精神,正是將玄學(xué)本體論作為人格精神的形而上的依據(jù),而不是將二者對立起來。王弼用自然作為人格精神的基本屬性也正是從這一點上去立論的。在此基礎(chǔ)上,他也主張對于情性加以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儒家的情性觀。王弼認為人性本靜,性發(fā)而為情,他主張對情控引:“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利而正者必性 ( 其 ) 情也。” ( 《易·乾卦注》 ) 王弼通過會通儒道,為他的人性論與人格精神的建構(gòu)作了堅實的鋪墊。通過這些分析,我們是不能不為王弼的明于“天人之際”的智慧與悟性所嘆服的。王弼對于現(xiàn)實的人際關(guān)系不諳,但惟其如此,正應(yīng)了老子所說的“大智若愚”,他才能在最高的智性與哲理層面對于天道人事作出精神上的闡釋與建構(gòu)。
作為 處于魏晉之際政治動蕩紛爭的亂離年代的士人,王弼既沒有高深的政治背景,也不喑世情。他的玄學(xué)用思辨的形式,倡導(dǎo)精神本體的作用。然而這種精神本體與其說是思辨的產(chǎn)物與對象,還不如說是現(xiàn)實中人格理想的產(chǎn)物。它通過對于形而上學(xué)精神意蘊的張揚與推舉,塑造出特定年代中的理想人格。將精致的玄學(xué)思辨與理想人格模式巧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這是魏晉玄學(xué)對于傳統(tǒng)的道家哲學(xué)與儒家哲學(xué)的融合與重構(gòu),而此中的闡釋與再建,王弼當功不可沒。同時,將玄學(xué)思辨中的精神之道(無)與人格理想融合一體,這就在美學(xué)與文學(xué)理想中楔入了天然的相通之處。因為文學(xué)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就是人學(xué),美學(xué)是這種人學(xué)在審美領(lǐng)域的直接表現(xiàn)。因此。人格的精神化與精神的人格化是天然接榫的。明乎此,我們就能明白王弼玄學(xué)與嵇康等人的文藝實踐與美學(xué)主張雖然并無直接關(guān)系,但卻能殊途同歸。前者是哲學(xué)的詩化,后者則是詩化的哲學(xué)。我們只要看一下嵇康充滿玄思的詩作,以及他的《聲無哀樂論》說可明白這一點。 《晉書》卷 43《王衍傳》有這樣一段常為研究者所引用的記載 :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 “ 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wù),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 ” 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 “ 口中雌黃。 ” 朝野翕然,謂之 “ 一世龍門 ” 矣。累居顯職,后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
人們常關(guān)注這段話的前半部分,而對后面部分不甚重視。其實,從接受理論來看,王弼的貴無論價值所以為王衍欣賞,并不只是它的精致的思辨與理致,而是它所為士族中人儀的理想人格提供了形而上的精神哲學(xué)。從這段話的概括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名士對王弼哲學(xué)感興趣乃是由于它將無作為天道與人道相通的一種形而上學(xué),可以成為處于既思想解放又動蕩不安年代中的精神慰藉。精神本體向人格生成,人格向精神本體無超升,它既有思辨的成分,更有美學(xué)與人生的意蘊,所以王衍這樣名動一時,盛才美貌,明悟若神的士人成為后進之士的人格楷模。惟其帶有濃重的美學(xué)與理想人生的意味,沉溺其中的人自然難免飄飄然忘乎所以,而在嚴酷的現(xiàn)實人生中則很難行得通。《三國志》說 “(王)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因英年早逝而逃脫了當時的政壇之禍,而另一與他齊名的玄學(xué)人物何晏則在與司馬氏的斗爭中慘遭殺害。追步他們的西晉名士王衍也在西晉末年的“五胡亂華”中遇害,被石苞稱為清談?wù)`國。然而哲學(xué)與文學(xué),營造至善至美的意境,陶冶著人們的性情,長于哲思與文學(xué)的人,在政治與現(xiàn)實中往往是不成功者,甚至慘遭不測,死后還要受人詬病與譏嘲。魏晉南北朝的大部分的文士都是在當時動亂中遭受橫禍而亡的。精神的超脫逍遙與事功的失敗凋零,這種巨大的反差在魏晉南北朝名士的人生中比比皆是。近代王國維曾說過可愛之學(xué)不可信,可信之學(xué)又不可愛,實際上也指出了人類精神生活中的兩難境地,美的境地是超越功利的,而功利之學(xué)則又不可愛。人們很難將兩種人格統(tǒng)一于一身。王弼、何晏就是屬于這類人物。他們在政治上都不能算成功人物,但王弼哲學(xué)對于中國古代文論精神的深化產(chǎn)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是非常明顯的事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據(jù)《三國志·魏志·鐘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王弼生于 226 年(魏黃初七年),死于 249 年(魏正始十年)
[②] 《三國志·魏志·鐘會傳》,中華書局標點本,第 795 頁。
[③] 在筆者初版與再版的《六朝美學(xué)》中,都未從闡釋智慧的角度去談王弼的美學(xué)與文論。
[④] 侯外 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191頁。
[⑤] 錢穆:《國學(xué)概論》,商務(wù)印書館 1997 年版,第 81 頁。
[⑥]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下冊,中華書局, 1980 年版,第 625 頁。
[⑦] 參見筆者所著:《和:審美理想之維》的第一章第一節(jié)《道家的“和以天倪”》,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1 年版。
[⑧]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下冊,中華書局, 1980 年版,第 624 頁。
(原載《江海學(xué)刊》, 2006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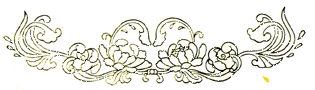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