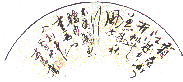內容提要:《詮賦》是劉彥和《文心雕龍》“論文敘筆”(“文類論”)的第三篇。從文論的角度看,《詮賦》中的疑點主要有三個:一是“體”“用”之辨,二是“物以情觀”的理論意義,三是“風歸麗則”的理論內涵。本文認為,彥和的“賦”觀是“賦體”兼“賦用”。所謂“物以情觀”,是指“以情觀物”。“物以情觀”把“感物”和“吟志”聯接起來。“麗”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物象的選擇上追求“唯美”。二是寫法上“極聲貌以窮文”。三是語言上講究“綺麗”。“則”是賦體的創作規范。它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體物寫志”。二是關乎“風軌”。
關鍵詞:詮賦;體用;物以情觀;風歸麗則
《詮賦》是《文心雕龍》“論文敘筆”的第三篇。因賦是古詩的流變,“不可歌”[1](P86),“不宜聲樂”[2](P60),故居《樂府》之后,列第三。本篇闡明賦的含義和特點,追述賦的來源,考察其發展和演變,銓評重要作家作品,最后確定“立賦之大體”,是一篇完整、成熟的文類論(體裁論)。
從文論的角度看,《詮賦》中的疑點主要有三個:一是“體”“用”之辨,二是“物以情觀”的理論意義,三是“風歸麗則”的理論內涵。
“體”“用”之辨
“賦”是“體”(體裁),還是“用”(表現方法),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或曰“體”,或曰“用”,或曰“體用兼備”。其實,在彥和之前,“賦”是“體”還是“用”,似乎并沒有明確的劃分。《周禮·春官》云:“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毛詩序》只是把“六詩說”改作“六義說,其內容、次序沒有變:“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無論是《周禮·春官》,還是《毛詩序》,都沒有指出這六者是“體”或“用”,沒有把“風雅頌”和“賦比興”區別對待——相反是等同視之,而且“其二曰賦”。也就是說,“賦比興”和“風雅頌”一樣,既可以作為“詩體”,也可以作為“詩用”。
彥和撰《文心雕龍》時,則把“比興”置于“文術論”,作為“詩用”;將“賦”置于“文類論”,作為“賦體”。這就把“賦比興”從“六義”中剝離出來,使之有別于“風雅頌”。彥和之所以把“賦”單列在“文類論”中,是因為荀況的《禮》、《智》賦,宋玉的《風賦》、《釣賦》,“爰錫名號,與詩畫境”,由“六義附庸,蔚成大國”。但這是不是表明彥和否認“賦用”呢?事實上,賦的“體與用”在彥和的看來可以兼容:“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即“賦”的含義是鋪陳,其特點是“鋪采摛文,體物寫志”。這里對“賦”的界定,既適用于“賦體”,也適用于“賦用”。亦此亦彼,“體”“用”不悖。他在談到“立賦之大體”時指出:“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雜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這是從表現方法(用)角度講如何作賦(體),提出“睹物興情”和“麗詞雅義”,是“賦體”之“用”。彥和的“賦”觀是“賦體”兼“賦用”。《比興》篇雖然是把“比興”作為“用”來講的,可在具體論述中,彥和也視之為“體”: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
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于是賦頌先鳴,故比體云構,紛紜雜遝,倍舊章矣。
這就是說,彥和的“比興”觀是“詩用”兼“詩體”。由此可見,彥和將“賦比興”從“六義”中分離出來,對它們是持“體用合一”的觀點來看待的。
唐代以后才嚴格區分“賦比興”與“風雅頌”[3](P387)。前者為“用”,后者為“體”。孔穎達《毛詩正義》有云:
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并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
元代的《詩法家數》(舊題楊載撰)則講得更簡明:“詩之六義,而實則三體。風、雅、頌者,詩之體;賦比興者,詩之法。”
由此看來,彥和的“賦比興”論,一方面是承先秦兩漢“六詩說”、“六義說”而來,一方面又為唐以后“三體”與“三用”說作了必要的理論鋪墊,處于承上啟下的轉折階段。即:《周禮·春官》、《毛詩序》之“體用不分”—→彥和《文心雕龍》:“體用合一”—→《毛詩正義》、《詩法家數》:“三體三用”。
“物以情觀”的理論意義
正如筆者在《<文心雕龍·明詩>辨疑》中所言,“感物吟志”揭示了詩歌“生發—轉化”的過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但怎樣從“感物”(眼中之竹)到“吟志”(手中之竹)——二者之間的中介環節是什么,《明詩》沒有回答。而《詮賦》講的“物以情觀”恰好添補了這個疏漏的環節:“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
所謂“物以情觀”,是指“以情觀物”——把“睹物興情”、“應物斯感”的“眼中之物”轉化為帶有濃厚主觀情志色彩的“胸中之物”。作者的個人情志表現,必須賦予一定的客觀形式,才能成為感染讀者的作品。“而不能只憑空里說些‘我喜呀'‘我悲呀'等等”[4](P134)純粹“私人話語”。否則,起不到應有的審美作用。而主觀情志客觀化、對象化的必由之路是“心與物”的融合。其關鍵在于“物以情觀”。即把主觀情志投射到客觀外物,使之由“眼中之物”(客觀物象)轉化為“胸中之物”(審美意象),從而成為作者主觀情感的審美載體。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心物交融”,將主觀情志對象化、客觀化。《神思》的“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色》的“心亦吐納”、“情往似贈”,都是強調“以情觀物”。也只有通過“物以情觀”,才能把“感物”和“吟志”聯接起來。即:感物(眼中之物)—→情觀(胸中之物)—→吟志(手中之物)。“物以情觀”是必不可少的中介環節。這也就是彥和主張“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的緣由。
“物以情觀”是對“感物吟志”的必要補充。它之所以在《詮賦》中被提出來,首先是因為賦的特點是“體物寫志”,較之其他文體更講究“情”與“物”的關系:大賦“京殿苑獵,述行序志”,小賦“因變取會,擬諸形容”,無不與“情”與“物”相關。其次是為了保證賦的語言“巧麗”。只有巧妙綺麗的文辭,才能寫“物”表“情”,體現賦的風采。再次是因為“宋發夸談,實始淫麗”,其后的一些作者“蔑棄”“體物寫志”的賦之根本,片面追求文采,“無關風軌,莫益勸戒”,結果造成“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的流弊。“物以情觀”對賦體創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物以情觀”似與西人“移情”(德文Einfühlung,英文Empathy)理念相近。“移情”“表示旁觀者自身與眼前的人或物的渾然劃一,其中旁觀者似乎切身體驗到對方的體態和情感。這種移情現象經常被描述成‘我們的主觀感情不自覺地向客體投射',也通常被描述成‘內模仿'的結果。”[5](P87)就表述而言,二者十分相似:“物以情觀”是把主觀情志投射到客觀外物上;“移情”是“我們的主觀感情不自覺地向客體投射”。就本質而言,差別較大:“物以情觀”的“物”主要是指自然景物;“移情”的“物”是“人或動物,甚至是無生命的東西”。“物以情觀”的“情”是“情志”,包含“理”的因素;“移情”的“情”則是純粹的情感,不含理性因素。“物以情觀”是“情變所孕”,把外物主觀化、情志化,把看到的“自然景物”變成“為我之物”;“移情”是把自我融入客體中,追求“客觀化”、“物化”——“當人們聚精會神的時候,面對芭蕾舞演員就會感到要與她旋轉同舞,見到蒼鷹也會覺得要和它一起騰飛,看到勁風中的樹木時則會產生一同搖曳的感覺……”[5](P87),即成為“自己視野中萬物的一部分”[5](P88)。
“風歸麗則”的理論內涵
揚雄在《法子·吾言》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他把賦分為“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詩人之賦”,是指以屈原為代表、繼承《詩經》傳統的賦;“辭人之賦”是指景差、唐勒等人撰寫、文辭靡麗的賦[3]P391。揚雄褒“詩人之賦”貶“辭人之賦”的看法或許有可以商榷之處,但他指出了屈原騷賦與漢賦的區別,還是有道理的。彥和《詮賦》篇進一步闡發揚雄的看法,提出“風歸麗則”的理論命題。
“風歸麗則”是指賦體創作要綺麗而有法則[6]P65。“麗”是賦體的文體標志。賦之“麗”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物象的選擇上追求“唯美”。大賦的對象多為京都、宮殿和苑囿,如司馬相如《上林賦》的上林苑、班固《兩都賦》的西都(長安)和東都(洛陽)、揚雄《甘泉賦》的甘泉宮等;小賦的對象多為物色、鳥獸和音樂,如謝惠連《雪賦》的白雪、禰衡《鸚鵡賦》的鸚鵡和王褒《洞簫賦》的洞簫等。對象不論大小,大多是“美”的事物。二是寫法上“極聲貌以窮文”。盡管不同的賦作風格各異——或“繁類以成艷”,或“窮變于聲貌”,或“明絢以雅贍”,或“迅拔以宏富”,可大都采用鋪敘、夸飾、比喻等表現手法,極盡鋪排之能事。如揚雄《甘泉賦》:“蛟龍連蜷于東厓兮,白虎敦圉乎昆侖……乘云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飏翠氣之宛延。”場景壯觀、奇麗,寫法崇尚鋪張。三是語言上講究“綺麗”。即所謂“賦取乎麗,而麗非奇不顯,是故賦不厭奇。”[7](P132)大賦辭采富麗,多用奇字:
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慧云,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俯仰乎乾坤,參象乎圣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蕩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班固《東都賦》)
小賦文辭奇巧,風格清新:
其妙聲,則清靜厭瘱,順敘卑達,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其仁聲,則若颽風紛披,容與而施惠。(王褒《洞簫賦》)
漢賦創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漢語的狂歡”。它充分展示了漢語的獨特之美,把漢語的“能指”發揮得淋漓盡致。“則”是賦體的創作規范。如果只講“麗”,不講“則”,容易走上“繁花損枝,膏腴害骨”的“麗淫”之途,因此,彥和主張“麗則”。“則”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體物寫志”。彥和指出,“登高能賦”是為了“睹物興情”。正因為“情以物興”,所以作賦要“寫氣圖貌”,表達情志。大賦是通過描繪京都、宮殿、苑囿和田獵來“序志”;小賦是是借助草木、鳥獸、“庶品雜類”來“象其物宜”,“側附”情理。“辭賦英杰”賈誼的《鵩鳥賦》“致辨于情理”;“魏晉之賦首的”郭璞和袁宏,前者“縟理有余”,后者“情韻不匱”;他們都通過物象來抒寫情志。故此,清人劉熙載《藝概·賦概》云:“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賦寓之”,“志因物見”。二是關乎“風軌”。彥和指責“逐末之儔,蔑棄其本”,“無貴風軌,莫益勸戒”,發揮了鄭玄“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的看法,從反面說明賦應該接續《詩經》“吟詠情性,以諷其上”的“為情而造文”傳統。他提出作賦“義必明雅”(內涵明白雅正),就是要宗法《風》《雅》,補“麗淫”之偏,糾不涉及風教法度、無益勉勵勸戒之弊。顯然,彥和倡導的是揚雄“詩人之賦”,是以《詩經》的《風》《雅》創作范式來銓評賦的創作。他認為,“賦自《詩》出”,盡管后來與詩“分歧異派”,但“賦、頌、歌、詩,則《詩》立其本”,體現了他以經為體、“正末歸本”的主導理念。他指摘“辭人賦頌”,不滿近人“遠棄《風》《雅》,近師辭賦”的原因正在于此。劉熙載《藝概·賦概》有云:“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諷諫……一以言志……言志諷諫,非雅麗何以善之?”來裕恂《漢文典·文章典》亦云:“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義在托諷,是為正體。”劉氏的“諷諫”、“言志”,來氏的“托諷”,都是承傳彥和賦宜“寫志—風戒”的觀點。如果作者真能做到“麗”而“則”,那么,他的賦就是“文雖雜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麗詞雅義”的佳作。
彥和“風歸麗則”的觀點,對今天的文學創作亦有借鏡意義。時下文壇“麗則”者少,“麗淫”者多。怎樣把握好“麗”的尺度,寫出“吟詠情性”、感動讀者的上乘之作,是需要作家和文學理論家認真省思的。
參考文獻:
[1]章太炎.國故論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章太炎.國學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趙則誠,張連弟,畢萬忱.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辭典[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4]周汝昌.神州自有連城璧——中華美學特色論叢八目[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
[5](美)M.H.艾布拉姆斯.歐美文學術語詞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6]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劉熙載.劉熙載文集[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