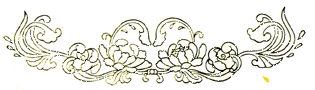嚴復不僅是近代中國譯介西方自由主義的第一人,也是批判西方自由主義的第一人。與那些將自由主義視為洪水猛獸的頑固派或對自由主義頂禮膜拜的西化派不同,嚴復以其學貫中西的學學術實力和嚴謹的思辨力,不斷地深化著他對西方自由主義的認知,改變著他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態度,并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了他較成熟的自由觀。
嚴復的自由觀反映出的是中國倫理本位文化所能容忍與接受的自由意志,而非西方個體本位文化中原汁原味的自由意志。概括說來,經過嚴復思想過濾過的“自由主義”,與形形色色西方自由主義的根本不同之處,就體現在處理“個人與群”的關系上。
一、提倡以富國強民為目的的、倫理本位的“個人自由”觀
最能代表嚴復自由觀的著作,莫過于嚴譯《群己權界論》。<1> 美國學者 史華茲 教授指出:
嚴復的《群己權界論》,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最明顯的通過翻譯闡明他自己觀點的例子……假如說穆勒常以個人自由為目的本身,那么,嚴復則把個人自由變成一個促進“民智民德”以及達到國家目的的手段。 [1 ](P141)
這一來自西方的、對嚴復自由觀的“目的抑或手段”的質疑,使一些學者發現,原來嚴復的自由主義不僅與穆勒的自由主義大不相同,而且,在處理“個人與群” ( 個人與國家 ) 的自由關系時,還是“大有問題”的。于是,不少人開始步其后塵,比照穆勒的《論自由》文本以及包括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古典經濟學在內的西方各色自由主義論,考察嚴復的自由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的差異與差距;同時,又從中國文化傳統中,追究嚴復“沒有把個人自由作為目的”的“所以然”,甚至開始質疑嚴復“以富國強民為目的”的自由觀的“現代意義”。綜其要,大抵認為嚴復在救亡的威脅下“大聲疾呼舍己為群,己輕群重,重視‘國群自繇',這樣一來他的思想雖然不具有集體主義的色彩,也肯定個人自由具有的終極意義,卻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壓倒啟蒙'的特色,而忽略了強調群體的觀點對個人自由可能會有的威脅” [ 2 ](P250) ,即在他“企圖建立一種環繞著‘積極自由'的民主觀念”時,卻“沒有注意到積極自由有偏向專制的危險” [2]( 墨子刻序, Pvii) 。 更鮮明的一種觀點是:
嚴復的自由主義所服務的目的,一開始就偏離了斯密為其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所規定的目的。
自由主義的根本目的是致力于增加個人的普遍幸福,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卻只用自由主義來追求國家的強盛,把自由主義以個人的幸福為目的變成了以國家的富強為目的。而自由主義在直接服務于國家的強盛的目標上遠不是最有效的手段,這樣自由主義不得不讓位于其他更有效服務于國家富強的主義。 [3 ]
更極端的一種說法是:近代以來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對西方自由主義的這種“偏離”,不僅代表著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落”甚至是失敗,也導致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專制集權思想及其社會勢力的死灰復燃,不僅是“救亡壓倒啟蒙”,而且是“革命取代改良”,進而是“專制戰勝民主”。 <2>
在眾多中國學者仍把自由主義視為富國強民的手段,或者把富國強民當作引進西方自由主義的最終目的時, 史華茲 教授以西方學者的眼光,敏銳地發現了嚴復的“自由主義” ( 其實也是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 ) 與西方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不同點。盡管在對嚴復的“自由主義”的價值判斷上, 史華茲 教授又難免陷入西方文化的云霧中,未能準確把握嚴復“自由主義”的中國文化內涵,但對于廣大“身在此山中”的中國學者而言,這一發現無疑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然而,卻很少有人比照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探究嚴復“把個人自由置于國富民強大前提之下”在中國文化傳統上的“所以然”;更少有人反思一下嚴復以及以嚴復為代表的大多數中國人,可不可能認同并實行穆勒那種“把個人自由主義作為目的”的個體本位自由觀。
事實上, 史華茲 教授在用西方人的眼光審視嚴復的“自由主義”時,一方面指出了嚴復“自由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的最大不同之處;另一方面,也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場上,對中國式的自由主義提出了一個“偽問題”——根據波普爾的“證偽學說”,不能證偽的命題決非“科學命題”,而指責嚴復“沒有把個人自由作為目的本身”,對于中國文化而言,顯然是無法證偽的“偽命題”。因為在中國倫理本位文化傳統中,個人與群的關系從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用嚴復的話說:
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圣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
中國理道與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 絜 矩。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何則?中國恕與 絜 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于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 [ 4 ](P2-3)
也就是說,在個體本位文化中,個人生存的前提條件就是“個人自由”,凡是侵害個人自由的“斯為逆天理,賊人道”。故在西方,“侵人自由,雖 國 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為此設耳” [ 4 ](P3) 。 但對于中國人的“自由意志”而言,在家國同構、倫理本位的文化體系中,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生存之道”,所謂“一枯俱枯,一榮俱榮”,就是指中國人大大小小、圈圈相套的血緣擬血緣群體的生存與繁衍模式。所以,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沒有比以大大小小的圈子構成的群體本位文化生存的“自由”更可貴的自由了。故中國文化曰恕,曰絜矩,提倡“張公百忍”,無論用今天的西化了的自由觀來看多么“不人道”,卻是實實在在地運行了數千年的中國式的“仁道”——中國人的生存之道。正如中國諺語所說:“人有人道,蛇有蛇道”,“和尚有和尚的經,強盜有強盜的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文明,各有各的特質,生發之道也就各不相同,怎能硬將烏蓬船劃到鐵軌上去行駛呢?起碼,在近代以前的中國人觀念中,沒有因此而產生過強烈的“不自由”的感覺。用金岳霖的邏輯分析來看,在自由意志與因果關系的關系上,其實存在著諸多的“可能性”。自由與不自由,實在是一種活的感覺,一種因人而異、因時因地而異、因文化而異的感覺。就是我們把傳統中國人都看做“有自由意志”但“受到現實環境約束”的,也還存在著“不覺得不自由,也不覺得自由”、“覺得自由”和“覺得不自由”三種關系 ( 可能性 ) [5 ](P125-136) ;更何況,在一個提倡著“恕”與“絜矩”的文化中,個人與個人之間,原本就不存在西方人那種建立在個體本位之上,彼此對立、彼此競爭的緊張關系。沒有了文化層面的“群己對立”,又何來“己重群輕”或“群己并重”?如果站在中國文化本位立場上看,當中國人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之時,不僅是中國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脅,更重要的是中國文化傳統面臨被西方文化殖民的危機。在這樣一個大格局下,富國強民、尋求中國文化傳統的窮變通久,不正是每一個中國人理所當然夢寐以求的“個人自由”嗎?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為謀求民族獨立與解放而展示出的強大凝聚力與抗爭力,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站在這樣一條歷史主線上來看嚴復,他從一開始向西方尋求的,就是包括自由在內的那些能激發起中華民族內在活力、凝聚力與抗爭力的異質文化因素,而不是西方文化本身。
歷史地看,在個體本位文化傳統的西方,對自由的追求,必須“以個人的自由為目的”;而在倫理本位文化傳統的中國,“個人的自由”與國富民強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聯,追求民族的獨立與自由與追求個人的獨立與自由,大抵不存在著彼此對立、彼此競爭的緊張關系。所以,嚴復以及以嚴復為代表的大多數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自由”觀,不僅從一開始就是以富國強民為目的的,而且始終立足于中國文化倫理本位,本著為民造福的宗旨,為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幸福而著想的。只不過此自由非彼自由,此幸福非彼幸福而已。對于那些站在非中國倫理文化本位立場上的人而言,子非嚴復,焉知嚴復們“自由主義”的根本目的不是“致力于增加個人的普遍幸福”?更何況,嚴復在研究了西方各國的不同政體之后,早就認識到:“知民之自由與否,與政府之仁暴,乃絕然兩事矣” [4](P1284) ;甚至在自由與幸福之間,亦沒有等號:“以自由為幸福,有時而然,而自由為災害者,亦有時而然。” [4](P1288) 故而,我才將嚴復的“自由主義”觀概括為:提倡以富國強民為目的的、倫理本位的“個體自由”觀。這也正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的根本不同之處。
二、關注倫理本位中的“個體自由”問題,反對個體本位的自由觀
由于對西方個體本位的歷史文化內涵缺乏深入研究,一些學者將西方文化中的個人自由視為一種至高無上、不容懷疑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理念,并努力證明嚴復早期所提倡的“自由主義”如何修正了西方的古典自由主義,又如何貼近于柏林的“積極自由主義”、忽視了“消極自由主義”……他們認為嚴復所反對的,只是西方文化中“極端的個人主義”自由觀;而且,似乎沒有人對嚴復反對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提出過什么質疑。
“個人與群”是人類社會的一對基本矛盾,為東西方所共有;但在如何處理個人與群的關系上,不同的文化會有大不相同的對待方式。所以才有了張申府那句至理名言:“自然與人,個人與群,東西思想所由分,人生問題于此盡。” [6 ](P1) 大體說來,在西方個體本位文化中,個人與群對立兩分,權利與權力界限清晰,二者在對抗與制衡中謀求發展;中國倫理本位文化中,個人與群交織共生,權利與權力彈性滲透,二者在關系調適中謀求共存。
在這樣一個關乎不同文化如何處理個人與群的關系的大問題上,嚴復的態度一向是謹慎而實際的。他從中國倫理文化本位出發,一方面積極向西方異質文化尋求能夠增強自身國力、發揮每一個中國人內在潛力的刺激因素,以改變倫理本位文化中過于強調群體至上,忽視個體發展的狀況。正如黃克武所看到的:“嚴復并不就個體來談自由,而是把自由放在群己密切相關的架構中來思索其意義” [2](P214) ;“嚴復思想中的思想、言論自由是以愛國為前提,換言之,愛國是一個真理,所以人們沒有不愛國而從道的自由” [2](P282 ,注釋 19) 這是嚴復引介與傳播西方個人自由的本土文化大前提。在這一前提之下,嚴復對西方文化中可能有助于提高中國國民個人素質、能力,增強其活力,以及應對世界格局變化的適應力等諸多文化因素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比如他介紹穆勒自由觀中有關個人獨立、自由,以及對自己負責的思想,以提高每一個中國人的國民主體意識和自覺性;引入斯密的經濟學說,刺激中國百姓言利富國的積極性,增加他們對西方經濟發展一般理念的了解,增強他們經濟入世的信心與能力;引進西學、普及新式教育,開民智、興民德,讓每一個中國人了解世界,提高自身素質……通過方方面面的努力,使每一個中國人不僅能為國家發揮各自最大的潛力,同時也享有各自最廣泛而得體的自由。一句話,嚴復的“個人自由”觀,不僅是以愛國為前提的,更是打著中國文化傳統深刻烙印的——在倫理本位文化中,通過內求諸己而獲得群己之間最大的自由;而非西方個體本位文化中,在盡力劃清個人與國家、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嚴格界限的同時,依靠個人的奮斗,努力向外擴張的個人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嚴復實際上關注的是倫理本位文化中“個體自由度”的調適問題,而不是個體本位文化中“個人自由權”的擴張問題。所以,嚴復才將穆勒的《論自由》譯為《群己權界論》。“群己權界”不是“群己平衡”。“權界”,權宜毗連事物的分界,非劃清對立物界線后的制衡。《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者也。”經者,常也,指至當不移的道理,也就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繁衍的綱常倫理。嚴復權群己,求自由,心有“經”在,目的在于“反于經而后求其善”,也即為的是中華倫理本位文化的窮變通久,這與將自由視為生命甚至近乎宗教信仰的西方自由觀有著天壤之別。他可以向西方學習,卻絕不 ( 也不可能 ) 唯西方自由觀念而是從。
綜上以觀,如果說從有關“積極自由主義”、“消極自由主義”,以及“幽暗意識”之類的視角來判斷當代中國少數自以為西方化了的個人主義者們的自由思想還有幾分靠譜的話,用它們來判斷嚴復以及他所代表的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自由觀,卻是無異于嚴復所謂“懸意虛造,而不詳諸人群歷史之事實” [4](P340) 了。
另一方面,嚴復則對西方文化中那些旨在擴大個人自由極限的各色自由主義,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有時甚至是一種近乎本能的文化抵制。比如,他反對盧梭的“民生而自由”思想,質疑他的“國民自治”主張 <3> ,指出:人類并非生而自由、平等,好比新生嬰兒既無自由可言,也不會與成人平等;不從實際出發,一味強調國民自治,“即斯民宜令得享最大自由是已。夫此語為是為非,關乎人道最巨,今不佞且不為定論” [4](P1296) 。“所不敢云其語為是為非者,蓋鄙意以為,政權乃對待之事……國眾有大小之殊,民智有明暗之異,演進程度,國以不同,故于此中,不得立為死法 。 ” [4](P1296) 說是“不為定論”,實際上,隨著嚴復對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入,特別是親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過程之后,他對于西方個體本位文化中貿易、掠奪、殖民、擴張的“自由”本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中國倫理文化本位也就有了更堅定的維護。他看到:“盧梭所謂自然之境,所謂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亦自言其為歷史中之所無矣。夫指一社會,考諸前而無有,求諸后而不能,則安用此華胥、烏托邦之政府,而毒天下乎 ! ” [4](P337) 他堅定不移地指出:“夫言自由而日趨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實之發生,此真無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 [4](P337)
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之弊,隨著一戰的爆發而日益顯露出來。嚴復不僅在第一時間把握了這一發生在世界文明進程中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而且,通過“一戰”,進一步看清了西方個體本位文化中“為惡”的一面。在《歐戰感賦》中他寫道:
三年西宇戰天驕,海上金銀氣盡銷。
( 自注:“只以英計,每日費金錢殆五百萬鎊,今六七百萬鎊矣。” )
入水狙攻號潛艇,凌云作斗有飛軺。
壕長地脈應傷斷,炮震山根合動搖。
見說傷亡過十萬,不堪人種日蕭條。 [4](P396)
他感嘆“世界總歸強食弱,群生無奈渴兼饑” [4](P394) ;驚詫“誰信百年窮物理,翻成浩劫到人群” [4](P394) ;并為自己引進西學可能導致的社會后果而憂心忡忡:“豈謂圖強法,翻成失國因。” [4](P384) 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向西方文化中尋求中國富強之路的想法是否正確:“平等復自由,群龍見無首……寧知人道尊,不在強與富。恭惟天生人,豈曰資戰斗 ! 何期科學精,轉把斯民蹂。君看四年戰,茲事那可又。” [4](P409) 進而,他不得不改變對西方文明的整體看法:“太息春秋無義戰,群雄何苦自相殘。歐洲三百年科學,盡作驅禽食肉看。” [4](P403)
嚴復深知“一戰”在歐洲的爆發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根源。侵略擴張的國家行為背后,有著極度擴張個人自由的歷史文化傳統。比較中國的仁恕文化,他又怎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 [4](692) 從這個意義上看,嚴復所反對的,絕不僅僅是“遺世獨立的‘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 [2](P248) 的所謂“極端個人主義”,而是西方個體本位的自由觀本身。所以,嚴復才鄭重地在遺囑的最后,寫下“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重,更切毋造孽” [4](360) 。這里所說的“造孽”,絕不是指“遺世獨立的個人主義”或“自私自利”所造的“小孽”,而是指“毀地脈,震山根,傷亡十萬,人種蕭條”的“人間浩劫”之“大孽”。他最終摒棄了的,是他曾經有過的對西方自由的美好想像和希冀;保留下的,是經過西方文化洗禮后,對西方有限民主與自由兩面性的理性認知和價值選擇。
綜上以觀,如果說包括“消極自由主義”和“幽暗意識”在內的文化內檢意識對西方縱欲文化還有幾分制約作用的話,用它們來批判所謂的“嚴復的‘積極自由主義'”,進而消弭中國本土文化中的“家長意志”、“專制主義”,真應了嚴復常用的那個典故:“蒸砂千載,成飯無期。”
三、“兩害相權,己輕群重”——嚴復自由觀的升華
由于對中國倫理本位的歷史文化內涵缺乏深入研究,一些自由主義者們對嚴復的“己輕群重”深感失望。他們斥嚴復反本復古,回到封建主義的懷抱;背叛了自由主義,走向自己的反面;成為“拉車屁股向后”的人,一個掉隊的先行者……但又不得不承認他是那個時代真正“學貫中西”的第一人,“真正立身嚴正并用理知思考問題”的第一人,“真正能將西方近代典型的學術思想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 [7 ](P278) 為了在這諸多的“第一”和最終的“落伍”之間找到一種大體說得通的“解釋”,他們可謂煞費苦心,絞盡了腦汁——卻少有人反思這“落伍”的結論是否成立。
倫理本位的文化傳統在中國已有數千年之久,像一個左撇子習慣了用左手做事一樣,中國人在群己問題上,也習慣了用天人合一、三綱六紀的“關系學”來處理、對待。用金岳霖的話說,“我雖可以忘記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記‘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 [ 8 ](P17) 。這種倫理本位的文化傳統,已經深入每一個中國人的骨髓之中,并形成一種舉世無有的龐大文化態勢—— 13 億中國老百姓中,懂得西方個體本位文化的能有幾人?在嚴復那個時代,雖然人口只有 4 億,知道西方個體本位文化的,恐怕只有嚴復等屈指可數的幾位。在既沒有歷史文化資源,又沒有現代社會環境的條件下,靠“己重群輕”的提倡,可能救中華民族于個體本位極度擴張的西方列強殖民侵略之水火么?唯有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資源,依靠“己輕群重”的文化理念,萬眾一心,才能首先謀得國家與民族的獨立——此乃全人類所共同遵循的自由的基本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講,嚴復的“己輕群重”,又怎能與“復古”二字相關?
更何況,當這些學者在“己重群輕”、“己輕群重”、“群己平衡”上糾纏不清時,卻大都忽視了“兩害相權”這四個字。
倫理本位和個體本位,是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各有其長,也各有其短;且往往長短互見。比如在群己對待這個問題上,中國倫理本位文化,一方面講究對待,講究因勢利導、順其自然;另一方面則不鼓勵個人欲望的擴張,沒有外拓意識和發展觀。這種內斂的、安于現狀的生存態文化,用張東蓀的話說,原本自在地生存下去是沒有問題的,怎奈卻偏偏遇上了西方文化的侵入,于是“沒有問題”也就隨著西方文化侵入的加劇而日益“問題嚴重”,直至危機四伏。 [ 9 ](P431) 這些“嚴重的問題”,在嚴復的《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和《救亡決論》諸篇中說得很明白。綜其要,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人已經富強起來,中國人已經處在積貧積弱、被動挨打的態勢;抱殘守缺,安步當車,民族前途渺茫;非學西方以自強,不足以救中國于水火。今天的我們,已經很難體會當年那些真正的保守頑固派們的抱殘守缺,以及安于生存態的中國老百姓們的不思進取之“害”了。但讀些近代中國史,或可從嚴復等先覺者當年激憤的言詞中,感悟到老大中華民族那種積重難返的“惰性”與“暮氣”。
什么事情都怕比較,沒有了西方人的“活力”與“朝氣”,我們也許不會顯得如此不堪。作為一個中國文化中的先覺者,嚴復的第一反映,必然是內檢自己國家、民眾乃至文化中存在的問題。對西方文化的優長了解越多,對自身文化的問題也就認知越清,如此形成嚴復的第一個否定——通過內檢式的文化對比,否定中國文化的現狀,并深究造成這種現狀的歷史原因。卻絕無否定中國文化之意。何以見得?首先,嚴復深愛中國文化,所謂愛之愈深,責之愈切,這從他一生的言行以及“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的遺囑中在在可見。其次,便是在中華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之時,嚴復也只是主張通過富國強民,自強、自救來改變中國現狀,以保證中國文化的窮變通久,絕無我們要走西方人掠奪、殖民、擴張的文化發展之路的意念。最后,他探索中國文化自救之路的過程,自始至終不離中國倫理文化本位。在引介穆勒的自由思想時,他過濾了穆勒自由觀念中所包含的“趣味上的獨特性”和“行為上的怪僻性”這一類東西,摒棄了他“視個人自由本身為一種目的”的目的論;在傳播西方的自由理念時,他從來就把一切有關自由的新觀念、新思想置于富國強民的總目標之下,合之則學則用,不合則舍則棄,比如他對盧梭“民生而自由”的揚棄;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崇尚“自由”,甚至急功近利地實行“自由”時,作為引進自由觀念的第一人,嚴復卻又發現了西方自由帶給中國社會的各種弊端,特別是“一戰”的爆發,更讓嚴復認識到西方“自由”的“惡之花”——其為“害”之慘烈,遠較老大中華帝國的“惰性”與“暮氣”之“害”更甚。
正是在打通了東西文化、全方位地比較了兩種文明的優劣之后,才形成了嚴復的第二個否定——對于前一個否定的否定之否定,即通過以我為主、放開眼界的文化考察,發現西方文明之弊,并深究其歷史文化根源,從而徹底否定中國文化走西方文明之路的可能性選擇。卻絕無閉關自守、否定西方文化之意。何以見得?首先,遺囑中他勸勉子孫“新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希望他們永遠不要固步自封。其次,便是在對西方文明極度失望的情況下,嚴復沒有 ( 也不可能 ) 將西方文化從他的視野、思辨與文化坐標中徹底清除。他罵西方人三百年的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卻仍是“回觀孔孟之道”,希望“澤被寰區”而已;而不是一如今日西方一些學者和思想家們,一味將普適的自由主義向全世界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中擴張,更不會為了自由而發動侵略戰爭。這樣的文化對待,與 費孝通 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可謂異曲同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嚴復在探索中國文化自救之路的過程中,自始至終從西方文化中獲益良多。可以說沒有西方文化也就沒有作為翻譯家、學貫中西的思想家的嚴復。正是在對西方自由的所然和所以然的認識過程中,嚴復才抓住了“個人與群”這一關鍵問題,并最終道出“兩害相權,己輕群重”這中國式自由的八字箴言。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八字箴言,不僅不是什么“復古”、“落伍”或“倒退”,反而正是他一生坎坷人生經歷、艱辛思辨歷程的總結,是他對西方自由觀的否定之否定,更是他的自由觀的升華——為中華倫理本位文化在東西方文明沖撞時代尋找到的一條大體可行的、窮變通久的自由發展之路。
四、一點啟示
嚴復對西方個體本位文化的認識,有一個與時俱進的過程。一是隨著他比較西方各種自由民權理論而不斷深化并有所選擇,正如黃克武所言:“嚴復對于天賦自由的批判大約是 1902 年左右他閱讀赫胥黎對盧騷‘民生而自由'的駁斥之后才確立的。” [2](P286 ,注釋 60) 二是隨著他觀察西方文明的進程而不斷深思并有所取舍,比如他通過“一戰”進一步認識西方文明自由貿易、掠奪、殖民與擴張的本質。三是反觀西方文化引入中國之后的各種跡象,反思西方文化對中華文明的實踐作用,比如他在 1895 年的《救亡決論》中,談的是必須向西方學習格致之學:“富強之基,本諸格致。不本格致,將無所往而不荒虛,所謂‘蒸砂千載,成飯無期'者矣 ! ” [4](P43) 然在 1920 年寫給熊純如的信中,他卻又針對辛亥后盲目引進西方政治體制所造成的中國政局混亂,再次引用了“蒸砂”之典:“自靳閣成立,報端日說之事,不是南北統一,便是國民大會、廢督、裁兵各等語,其實細而觀之,皆成戲論,徒借政客與不用功學生,騰口叫囂而已。所謂蒸砂作飯,救饑無日者也。” [4](P711) 四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經驗與閱歷的豐富,不斷反思自己在包括自由在內的中西文化比較與抉擇上的問題,揚棄了許多為一般學人所抱定的新的觀念或西方的結論,既不唯西,也不唯中,更不唯己。用他自己的話說:“不得立為死法” [4](P1296) ,“惟自歷史中求之而已” [4](P1282) 。所以在人們尚不了解西方文化之時,他踏踏實實譯出《嚴譯世界名著八種》,其數量特別是質量,為今人所莫及;在人們將他推舉為“引介西方文化第一人”時,他卻開始反思西方文明中“為惡”的一面,尋找包括“盡作禽獸看”的“一戰”在內的“惡行”的歷史文化根源;在人們把他當成復古的典型,以為他“回歸到群體本位文化之中”時,他實際上卻過起了“惟有坐視遷流,任其所之而已” [4](P712 ) 的幽閉生活,道出“成毀相因果,賢愚孰判分?立誠斯感物,執象總迷真” [4](P384) 的困惑,發出“天意高難問,吾身藐自孤” [4](P399) 的悲嘆。在一般人看來,一個曾經熱烈擁抱西方個人自由的人,卻向本土倫理文化回歸了;而當他回歸到倫理文化本位之后,卻又實際上成為一個孤獨的人——這就是東西文化劇烈撞擊過程中,帶給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痛苦而又奇特的遭際,不僅是古未有之,恐怕也是世界少有的。
個人與群,真是東西方文化的千古之謎。
( 備注:此文在《天津師范大學學報》 2006 年第 1 期上發表,發表時略做刪節 )
作者簡介:汪丹(1964-),女,北京市人,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副編審。
參考文獻:
<1> 無論是出于學者們所說的“自覺的修正”還是源于“不自覺的誤解”,該書的自由觀是嚴復而非穆勒(Mill,一譯彌爾)本人的,這一點已為學者們普遍認同。相關研究綜述請參見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的第二章:清末民初以來學者對嚴譯的討論。
<2>此類觀點,網上多見,以年輕學者為主,間有年齡老而思想新的學術前輩亦不甘寂寞,熱烈呼應。唯因多見,故不舉例。
<3>請參閱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接受與批判》一書中第四章第三小節“丁、嚴復對盧騷思想的駁斥”。
1[ 美 ] 本杰明·史華茲 . 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 [M]. 葉鳳美譯 .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6.
2黃克武 . 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 [M].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0.
3劉軍寧 . 自由主義與儒教社會 [EB/OL].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ll/t20050816_6774.htm, 2005-08-16 .
4王栻主編 . 嚴復集 (1-5)[M]. 北京:中華書局, 1986.
5金岳霖 . 自由意志與因果關系的關系 [A]. 劉培育編 . 哲意的沉思 [M].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0.
6張申府 . 所思 [M]. 北京:三聯書店, 1986.
7殷海光 . 中國文化的展望 [M]. 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 1988.
8金岳霖 . 論道 [M].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7.
9張耀南 . 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 [Z].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