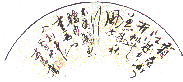摘 要:文章在描述和分析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的劉薩訶研究的基礎上,指出:無論是資料的考訂、匯集和闡釋方面,以及通過跨學科的全面系統的研究呈現劉薩訶在宗教史、學術史上的意義等其它方面,劉薩訶研究都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余地和必要。
關鍵詞:劉薩訶研究,綜述
劉薩訶[1]是活動于東晉末到南北朝初期的一位稽胡族的游方僧人。稽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的一個部族,主要聚居在今天陜西、山西交界黃河兩岸的山地,是由當地人、匈奴和西域胡人組合而成的“雜胡”。[2]王琰《冥祥記》中記載了他三十一歲暫死后巡游地獄;慧皎《高僧傳》又主要敘述了他在江東尋覓、禮拜阿育王塔、阿育王像;道宣的《續高僧傳》、《集神州三寶感通錄》等著作中又補記了唐初居住在黃河左右慈、隰、嵐、石、丹、延、綏、銀八州之地的稽胡族對劉薩訶的崇奉狀況,以及劉薩訶西行河西走廊、在涼州番禾郡授記——由此誕生了著名的番禾瑞像、最終遷化酒泉;敦煌石窟中從初唐到歸義軍時期、尤其是曹氏政權時期有關劉薩訶和的番禾瑞像的塑像、壁畫、絹畫、遺書又透露出許多新的信息。總之,在東晉到唐五代漫長的時間里,在江東、秦晉、河西走廊廣闊的空間中,劉薩訶傳說不斷地增殖繁衍,劉薩訶也逐漸積淀成為一個牽扯涉到宗教信仰、民族、民俗、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的一個極為復雜且極有價值的問題。
因此,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敦煌相關文物一被發現,劉薩訶研究立即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點。今天,雖然熱潮已過,但是,不可否認劉薩訶的相關問題并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所以,以學術史的眼光梳理以往的劉薩訶的研究、并且尋找更好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這也就是寫作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一、資料的匯集、考訂和闡釋
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敦煌劉薩訶文物和文獻的發現引發了國內外學界對劉薩訶的關注。起先關注的是敦煌本《劉薩訶因緣記》和莫高窟的相關壁畫,后來又陸續發現敦煌遺書中其它一些相關的詩文以及以番禾瑞像為題材的造像、壁畫、絹畫作品。可以說劉薩訶研究的起點和中心都是這位高僧和敦煌莫高窟的關系。總體看來,研究的重心放在敦煌遺書和莫高窟相關文物的解讀和研究之上,且在解讀敦煌材料的同時注意到關于劉薩訶生平、傳說的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對劉薩訶事跡的考證。重要的研究成果有:
陳祚龍《劉薩河研究》[3]以校勘《因緣記》為主并排列了內典、外典中與劉薩訶相關的資料,論述之中處處表現出遠見卓識。魏普賢《敦煌寫本和石窟中的劉薩訶傳說》[4]、《劉薩訶和莫高窟》[5]二文利用敦煌文獻文物和《大藏經》中的相關資料梳理了劉薩訶傳說,考訂細密。史葦湘《劉薩訶與敦煌莫高窟》[6]集中在對莫高窟壁畫、塑像、絹畫的解讀上,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問題。孫修身于劉薩訶研究用力最勤,其主要成就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對莫高窟相關文物的解讀,如《莫高窟佛教史跡故事畫介紹三》[7]、《莫高窟佛教史跡故事畫介紹四》[8]、《斯坦因〈千佛圖錄〉圖版十三的內容考釋》[9]。二是對劉薩訶生平事跡的考訂,其《劉薩河和尚事跡考》[10]一文是當時研究劉薩訶生平事跡最為詳細的一篇文章。[11]三是對番禾故地和武威的兩件文物進行了解讀。孫氏在番禾故地進行實地調查時發現一尊與莫高窟所見形象相同的番禾瑞像,經過考證,推測其為文獻所記載番禾瑞像的原物(參孫修身《古涼州番禾縣調查記》[12]一文);結合這一發現,又對武威出土的擬名“涼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緣記”的石碑進行了解讀(參孫修身、黨壽山《〈涼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緣記〉考釋》[13]。孫氏的發現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張寶璽《圣容寺與“涼州山開瑞像現”》[14]、杜斗城《劉薩訶與涼州番禾望御山“瑞像”》[15]二文都是在孫修身的相關研究基礎上展開,不過均未超過孫氏的研究水平;曾德仁《四川安岳石窟的年代與分期》[16]一文中指出在安岳石窟中亦存有一尊盛唐時期的番禾瑞像的造像,這是首次在河西走廊和敦煌之外的地方發現的以番禾瑞像為題材的造像;馬德《敦煌文書題記資料零拾》[17]中公布了《宋乾德六年修涼州感通寺記》,為研究宋代番禾瑞像的情況提供了一條資料。饒宗頤《劉薩河事跡與瑞像圖》[18]一文在陳祚龍、魏普賢、史葦湘、孫修身諸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從史源學的角度來分析劉薩訶的相關文獻文物資料,考證尤精。霍熙亮的《莫高窟第72窟及其南壁劉薩訶與涼州圣容瑞像史跡變》[19]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由于72窟自晚唐、五代開鑿之后就遭水浸,后又被風沙掩埋,下部壁畫幾乎完全消失,霍先生借助燭光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努力完成了一幅線描圖,為學界研究72窟南壁壁畫提供了最為全面細致的材料。此外,還有其它一些比較重要的文章:劉銘恕《劉薩訶與敦煌》[20]、張先堂《S4654〈薩訶上人寄錫雁閣留題并序〉新校與初探》[21]、汪泛舟《〈薩訶上人寄錫雁閣留題并序呈獻〉再校與新論》[22]等都是對《因緣記》之外的敦煌文獻的發現和解讀。
經過考古發現和文獻的搜集、整理使得劉薩訶的相關研究資料逐漸趨于完備可靠。不過,隨時都有可能發現新資料,因為隨著研究視野的拓展、研究水平的提高,新資料、新認識隨時都會出現。例如我們在下文中論及的方廣锠的《〈劉師禮文〉及其后代變種》[23]一文中就將敦煌遺書中的《劉師禮文》視為配合禮拜劉薩訶儀式的禮懺文。因此,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資料的匯集、考訂和闡釋還有很大的余地。
二、問題的提出
《因緣記》的校讀、番禾瑞像文獻和文物的解讀、以及由此而展開的劉薩訶生平的考訂是上個世紀劉薩訶研究的中心內容。不過,恰恰正是在文物和文獻的解讀闡釋過程中,研究者陷入了亦真亦幻的史實與傳說構建的迷宮之中[24],材料的性質決定了劉薩訶研究決不可能停留在劉薩訶生平的考訂上,正如巫鴻所言“文獻和藝術中的劉薩訶更多地是一個傳奇式的虛構,而非真實的歷史人物。為什么他如此頻繁地出現在文獻和藝術作品中?對于從5世紀到10世紀精心編制劉薩訶故事的作家和藝術家來說,他的身世和靈跡意味著什么?”[25]
其實從劉薩訶研究開始之初,專家學者就提出了許多有價值觀點。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陳祚龍在評價《因緣記》時已經指出:“只要大家確有興趣,改行追問‘為什么'當年的‘知識分子'竟會抄寫這樣的篇章,以及其它一連串的‘為什么',我相信,大家一定可從此‘記'之中,找出一些有關的答案!就我所知,此‘記'除可直接用以稽核劉薩河的‘行誼'之外,它還很有助于我們考究中世中華哲學、文學、佛學、語言學、宗教學、歷史學、民俗學、社會學……,各種專門‘學術'的演化!”。[26]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史葦湘提出“劉薩訶的故事給佛教史、美術史和民族文化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劉薩訶由一個胡人出家‘成圣',在大西北地區受到漢胡各族民眾的崇敬,這件事在地域與民族關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27]
可見,雖然目前所發現的劉薩訶的相關材料都是與佛教有關的,但學術界早已敏銳地發現不能簡單地將劉薩訶定義為佛教史上的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高僧”。劉薩訶研究首先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以宗教信仰為中心、牽涉到民族、民俗、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復雜問題。基于這種認識,研究者們已經進行多方面的探討;其中,在宗教、文學、美術三方面的研究較為突出,現總結如下。
劉薩訶由凡人而高僧而菩薩、佛這一現象是所有研究者都極為關注的,但長期以來,一直未能作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究其原因,是因為沒有找到一個最合適的切入視角。上個世紀末期,在宗教研究領域中,學者們越來越關注下層民眾的信仰問題。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既有精細、高深的哲學形態,也有比較粗俗、普及的民間信仰形態。四到十世紀的劉薩訶信仰絕對不可能是知識階層的哲學形態的佛教信仰,因此,從佛教在民間傳播過程中對民眾宗教信仰之影響這一角度切入劉薩訶研究,許多難題會迎刃而解。筆者認為劉薩訶傳說所展示的由凡而圣不斷神化的過程典型地展現了佛教入華后在民間傳播的一個側面,折射出四至十世紀對民間佛教信仰的原始狀況和傳播方式。[28]方廣锠在其《〈劉師禮文〉及其后代變種》一文中指出:劉薩訶是早期中國信仰性佛教的領袖人物;敦煌遺書《劉師禮文》中的“劉師”即是劉薩訶,《劉師禮文》是配合禮拜劉薩訶儀式的禮懺文;《劉師禮文》中的禮拜法實際上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
劉薩訶也長期吸引著文學界的目光,文學界的研究集中在劉薩訶的冥游故事和《因緣記》的文體的探討上。劉薩訶地獄巡游的故事備受關注。佛教研究者多從地獄觀念、觀音信仰來看待這一故事。如樓宇烈《東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的觀世音靈驗故事雜談》[29]、《法華經與觀世音信仰》[30]二文從觀音信仰的角度指出《冥祥記》中劉薩訶冥游故事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則觀世音菩薩信仰應驗故事”;侯旭東《東晉南北朝佛教天堂地獄觀念的傳播與影響——以游冥間傳聞為中心》[31]則將之視為游冥傳聞的一例。文學研究者則是從敘事、小說的角度來關注劉薩訶的冥游故事,如王國良《劉薩荷故事研究(之一)——以〈冥祥記〉為主的考察》[32]以及《〈劉薩訶和尚因緣記〉探究》[33]、張瑞芬《從〈冥報記》到〈劉薩訶和尚因緣記〉看唐代釋氏輔教書的幾個特色》[34]、鄭阿財《敦煌佛教靈應故事綜論》[35]等。關于《因緣記》文體的探討更是一個復雜而有趣的問題。周紹良對《因緣記》與僧傳和講唱因緣文的關系作出一個大膽的設想——“故此等因緣記可見為說因緣之底本。”周紹良、顏廷亮、伏俊璉等人都或深或淺地從文體的角度探討了“因緣記”與變文的關系。[36]拙文《敦煌本〈劉薩訶因緣記〉解讀》在周紹良先生相關論證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了敦煌本《劉薩訶因緣記》是講唱因緣文的藍本,極有可能是為了講唱搜集整理素材。[37]
劉薩訶研究起始于對敦煌相關文物的發現,文物在研究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要大于文獻。要研究劉薩訶不僅僅是解讀文獻,而且還要解讀文物——雕像、壁畫、絹畫等組成的宗教藝術作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劉薩訶研究是一個美術問題。劉薩訶研究也因為藝術學界的加入而更加豐富多彩起來。金維諾[38]、馬世長[39]、史葦湘等人都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在這里我們想著重介紹巫鴻的研究成果,他的《再論劉薩訶——圣僧的創造與瑞像的發生》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這篇文章對第323窟南北兩壁的壁畫、203窟的主尊佛像、第61窟中心佛壇背屏后五代壁畫、第72窟南壁的壁畫作了詳細的圖像學的闡釋,探討了中國中古佛教藝術中對宗教偶像的觀念和表現。對第72窟南壁的壁畫的闡釋尤為深刻。巫文稱其為“一幅極其復雜、可能是傳統中國藝術中對宗教偶像最為深刻的思考的畫”,畫中番禾瑞像的“這14身佛像所共同構成的是一個佛教圣像系統的邏輯和存在——從它的概念到物化,從它的神學起源到塵世間無休止的復制。這一系統的基本觀念是‘表現'(presentation)而非‘再現'(representation):當一身瑞像被認為是天上形象的自我顯現時,人類藝術家的作用只能是一個復制者,而他的任務是復制不能被復制的一個對象。”[40]這些論斷足以引發學界更多的關注和更深的思考。
三、多學科視野下的劉薩訶研究
可以說,學者們對與劉薩訶相關的問題均作了十分深入的探索,這不僅顯示了專家學者們獨到的見識和開闊的視野,同時也提出了新的有待解決的問題。如果說,上個世紀劉薩訶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學者們是出于一種學術敏感對劉薩訶研究的價值作出預估,那么,在這個世紀則是要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地來解決這個問題。
劉薩訶研究首先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以宗教信仰為中心、牽涉到民族、民俗、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復雜問題。可以說,它是一個由宗教、民族、民俗、文學、藝術等構成的有機系統。只有在相關的民族、民俗、文學、藝術等各個方面都取突破性進展的前提下,宗教信仰這一核心問題才能得到比較圓滿的解決;同樣,宗教信仰的問題解決又會促進各方面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這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這樣看來,劉薩訶研究絕對是一個涉及到多學科的問題。在這篇文章的里,我想略談拙見,對多學科視野下的劉薩訶研究作一點簡單的推測。
(一)宗教信仰
首先來談宗教信仰問題。不可否認,劉薩訶研究的主線和中心思想是個宗教信仰的問題。劉薩訶的出現是中國宗教史上一個非常復雜的現象,所牽涉的問題甚多。劉薩訶活動在四世紀后期至五世紀初期,他的事跡雖然被記載在《高僧傳》、《續高僧傳》等佛教著述中,但他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佛教高僧,通過分析使之成為民眾的崇拜偶像眾多的神奇傳說,可以發現:劉薩訶是佛教信仰在民間傳播過程之中,民眾在原有的民間宗教信仰的基礎之上創造出的一位著染了佛教色彩的新神。與其將劉薩訶信仰的性質定義為佛教信仰的民間形態,不如更進一步、更直接地說它是披著佛教外衣的民間宗教信仰。
民間宗教研究的意義在于以“眼光向下的革命”來探索“作為文化體系的宗教”。隨著宗教研究的深入,中國民間宗教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從最初的無人問津逐漸發展成為一門越來越受重視的學科。可惜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民間宗教信仰由于史料的匱乏而長期沒有引走學界足夠的重視。但不容忽視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宗教大發展、大變革的時期,也是民眾信仰非常真摯、非常熱忱的時期;佛教對中國原有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和改變,在這樣一個轉型期內的民間宗教信仰應該是極為豐富、極為復雜、且極具典型意義的。萬幸的是,劉薩訶這樣一個內涵豐富、傳播范圍廣泛、時間久遠的個案,將為探索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民間宗教信仰發展和變遷的規律提供特殊的價值和意義。
(二)民族
對于北朝至唐五代西部民族問題的研究,劉薩訶具有特殊的意義,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稽胡族的研究,二是西北少數民族的研究。劉薩訶是稽胡人,也是稽胡人的民族神。稽胡是四世紀至九世紀五百年間聚居在今天晉陜交界處的黃河兩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民族。稽胡人的歷史就是一個部落民族如何融入主流文化中的歷史。從史籍上,我們看到的只是輔之以“誘化”的戰爭,所幸的是,劉薩訶這個特例給我們提供了宗教文化方面的寶貴信息。宗教在民族融合方面起了非常巨大的、超乎想象的作用。劉薩訶這個從稽胡民族自身中產生出來的神,既符合了稽胡人的心理祈愿,又為稽胡人傳入了一種異質文化,他起著提升本民族文化和滲透外來文化的雙重作用。同樣,在河西走廊、敦煌為代表的西北地區,番禾瑞像信仰的隆盛也具有一樣的民族學的意義和價值。
劉薩訶相關的民族問題的研究對于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的宗教信仰也具有重要的意義。正是在稽胡中劉薩訶完成了由人到神的轉折,由洗心革面奉行佛法的凡夫變為一個兼具胡師佛、蘇和圣、觀音化身、利賓菩薩四種身份的全能的神,這種身份的轉變,也標示著佛教影響之下的民間宗教信仰發展過程中的一種轉折,即由外來神佛變為本土神佛、由他力救濟轉變為自身成佛,這種轉變體現出民間宗教信仰在迅速吸收消化外來佛教信仰的同時也表現出民間宗教信仰的一貫的簡單化傾向。
(三)民俗
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有這樣的記載:“晝在高塔,為眾說法;夜入繭中,以自沉隱;旦從繭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為蘇何圣。‘蘇何'者,稽胡名繭也。以從繭宿,故以名焉。”“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柏剎,系以蠶繭,擬達之止也。”[41]這番記載顯然表明劉薩訶在稽胡八州之地是備受供奉的蠶神。劉薩訶何以成為稽胡的蠶神,這是一個有趣但難以解釋的問題。在這里我們只能先作一個簡單的猜測。稽胡人選擇本民族的劉薩訶作為他們的蠶神蘇合圣,并未受到中華其它蠶文化的影響,而是稽胡民間文化與佛教信仰交融之后的產物,具有區域文化的明顯特征,這是與中華其它蠶神的區別之處。蘇何圣產生在佛教大盛于稽胡的背景之下,透露出稽胡人佛教信仰方面的另一種信息:早在五世紀之末,在稽胡人的信仰之中佛教神明已被俗神化。蘇何圣的存在,揭示出佛教神明俗神化是與佛教在民間的傳播相同步的。
(四)文學藝術
劉薩訶傳說是一個文學藝術問題,因為文學與藝術是劉薩訶信仰的傳播手段。在上文中我們已經提到劉薩訶研究也是一個美術問題,在這一方面巫鴻開了一個好頭,相信將來還會有更為深刻細致研究成果面世。在這里我們想著重談談作為文學問題的劉薩訶研究。劉薩訶傳說是一個文學問題,而且是一個復雜的文學問題——一個關于敘事藝術與講唱藝術、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的復雜的文學問題。劉薩訶傳說的記錄沿著雅、俗兩條線索發展:諸如王琰《冥祥記》、慧皎《高僧傳》等士人、知識僧侶對劉薩訶傳說的記錄體現的是知識階層雅文化的一線,敦煌本《劉薩訶因緣記》則是民間俗文化的一線。知識階層記錄宗教信仰構成了古小說的部分敘事藝術,這一部分恰恰是以往的古代小說研究中因缺乏文學價值而被忽略掉的部分。這種忽略當然是不客觀的,恰恰是今天小說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知識階層對于劉薩訶傳說的記錄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相當典型的個案。我們還注意到,對劉薩訶傳說的記錄,不管是雅文化的還是俗文化的,它們都有共同的來源——圍繞著當時流行的劉薩訶信仰所產生的各種傳聞,它們成為記錄劉薩訶傳說的雅、俗兩條線索的交點。如果能從源頭上梳理清楚劉薩訶傳說雅俗二線的關系,那么對于研究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雅文學與俗文學之間的復雜關系必然有一定的幫助。
總之,無論是資料的考訂、匯集和闡釋方面,以及通過跨學科的全面系統的研究呈現劉薩訶在宗教史、學術史上的意義等其它方面,劉薩訶研究都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余地和必要。
注釋:
[1]“薩訶”這個名字在不同的記載中有多種寫法,例如《冥祥記》作“薩荷”、“屑荷”,《高僧傳》作“薩河”,《梁書》、《南史》作“薩何”,敦煌本《劉薩訶因緣記》作“薩訶”,《續高僧傳》作“窣荷”等。僅《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一書就有“薩荷”、“薩何”、“薩訶”、“蘇和”四種寫法。溯其本源,應是稽胡語“蠶繭”的不同音譯。
[2]林干《稽胡(山胡)略考》,《社會科學戰線》1984年第1期,第148—156頁。
[3]《華岡佛學學報》1973年第三卷,第33—56頁。
[4][法]謝和耐等著、耿升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30—463頁。
[5]《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第464—475頁。
[6]《劉薩訶與敦煌莫高窟》,《文物》1983年第6期,第5—13頁。
[7]《敦煌研究》1982年第2期,第101—107頁。
[8]《敦煌研究》1983年第1期,第41—46頁。
[9]《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第87—94頁。
[10]《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研討會論文·石窟藝術論》(上),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310頁。
[11]《劉薩訶和尚事跡考》之外,孫氏尚有《劉薩訶和尚因緣故事》(載《陽關》1983年第1期)、《從凡夫俗子到一代名僧的劉薩訶》(載《文史知識》1988年第8期)二文。
[12]《西北民族文叢》1983年第3期,第147—154頁。
[13]《敦煌研究》1983年第1期,第102—107頁。
[14]《甘肅日報》1984年10月7日。
[15]《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1996年版,第162—166頁。
[16]《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第54頁。
[17]《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111頁。
[18]《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349頁。
[19]《文物》1993年第2期,第32—47頁。
[20]《文史》1988年第1期,第286頁。
[21]敦煌研究院文獻研究所編《敦煌佛教文獻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6頁。
[22]《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第134—140頁。
[23]2006年11月1日中國人民大學“第二屆中日佛學會議”會議論文。
[24]筆者認為劉薩訶的材料是史實與傳說的混合物,而且越到后期,傳說的成份越大。對于劉薩訶研究來說,應當將重心放在研究傳說的產生、衍變和影響上。參拙文《“敦煌高僧”劉薩訶的史實與傳說》,《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第76—82頁。
[25]巫鴻《再論劉薩訶——圣僧的創造與瑞像的發生》,載《禮儀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P431頁。原題為“Rethinking Liu Sahe:The Creation of a Buddhist Saint and the Invention of a ‘Miraculous Image'”發表于Orientation vol.27,no.10(November 1996),pp.32-43。
[26]陳祚龍《劉薩河研究》,第36頁。
[27]史葦湘《劉薩訶與敦煌莫高窟》,第9頁,第13頁。
[28]尚麗新《劉薩訶信仰解讀》,《東方叢刊》2006年第3期,第6—23頁。
[29]樓宇烈著《中國佛教與人文精神》,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頁。
[30]《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第69—74頁。
[31]《佛學研究》1999年(總第8期),第247—255頁。
[32]南開大學文學院中文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文化論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368頁。
[33]項楚、鄭阿財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年版,第582—597頁。
[34]臺灣“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編《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第二屆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
[35]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編《佛學與文學——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學部份》,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21—152頁。
[36]參周紹良《唐代的變文及其它》(原載《文史知識》1985年第12期、1986年第1期,后收入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敦煌文學芻議及其它》)、顏廷亮《敦煌文學概論》(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伏俊璉《論變文與講經文的關系》(載《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中的相關論述。
[37]《文獻》2007年第1期,第65—74頁
[38]金維諾《敦煌壁畫中的佛教故事》,《美術研究》1958年1期。
[39]馬世長《莫高窟第323窟佛教感應故事畫》,《敦煌研究》1982年第1期,第80—96頁。
[40]巫鴻《禮儀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第450、454頁
[41]《大正藏》第52冊,第434頁c、第435頁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