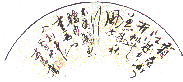內(nèi)容提要:賀麟是我國現(xiàn)代著名的哲學(xué)家、哲學(xué)史家、黑格爾研究專家,他建構(gòu)了較為成型而且成熟的文化哲學(xué)體系。本文結(jié)合賀麟的著作(側(cè)重于1949年以前),從“人與文化”、“歷史與文化(古今)”、“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中西)”、“赫然名家的‘新心學(xué)'”四個層面梳理其文化史觀。
關(guān)鍵詞:賀麟;文化史觀;新儒家;新心學(xué)
作者簡介:彭華(1969-),四川丹棱人,宜賓學(xué)院社會科學(xué)系、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歷史學(xué)博士,主要研究領(lǐng)域為先秦史、古代思想文化、近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史。
基金項目:本文是宜賓學(xué)院2004年博士啟動基金項目“賀麟與儒學(xué)”(編號:2004B02)階段成果之一。
賀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省金堂縣人。我國著名的哲學(xué)家、哲學(xué)史家、黑格爾研究專家、教育家、翻譯家。早在20世紀40年代,賀麟就建立了“新心學(xué)”思想體系,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新儒家思潮中聲名卓著的重鎮(zhèn),被尊為現(xiàn)代新儒學(xué)八大家之一。《近代唯心論簡釋》、《當代中國哲學(xué)》(后易名為《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xué)》)、《文化與人生》是賀麟“新心學(xué)”思想體系的代表作。賀麟學(xué)貫中西,在中西哲學(xué)方面均有極高的造詣,《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講演集》、《黑格爾哲學(xué)講演集》是賀麟治西方哲學(xué)的重要成果。
作為中國20世紀杰出的哲學(xué)家,賀麟建構(gòu)了較為成型而且成熟的文化哲學(xué)體系。本文將結(jié)合上述論著,梳理賀麟的文化史觀。
人與文化
人類學(xué)認為,文化是人類有別于動物的標志;因此,所謂“文化”,實即“人的文化”(賀麟稱之為“人文化”[1])。賀麟所理解的“文化”,亦著眼于“人”(寬泛的人類而非狹隘的國家)這一視角,認為“文化乃人類的公產(chǎn),為人人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不能以狹義的國家作本位”[2];而賀麟所理解的“文化”,尤側(cè)重于人類精神一端,認為文化“應(yīng)該以道,以精神,或理性作本位”[3],“所謂文化,乃是人文化,即是人類精神的活動所影響、所支配、所產(chǎn)生的。又可說文化即是理性化,就是以理性來處理任何事,從理性中產(chǎn)生的,即謂文化。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4]。換句話說,賀麟所持文化觀是以精神為本位的“唯心論”文化觀[5],是建立在“精神科學(xué)”基礎(chǔ)之上的“唯心論”文化觀[6]。
在《文化的體與用》[7]一文中,賀麟根據(jù)柏拉圖式的絕對體用觀和亞里士多德式的相對體用觀建構(gòu)起文化體用的層級結(jié)構(gòu),并把精神確定為文化的本體和主體。賀麟指出,文化的體用分四個層次,分別是道(價值觀念)、精神(價值體驗/精神生活)、文化(價值物)、自然(與價值對立的一個觀念)。其中,“道”是純體,“自然”是純用,而“精神”和“文化”兼有體用。賀麟認為,雖然從絕對體用觀的角度看,“道”是文化之體,文化是“道”之用、“道的顯現(xiàn)”,但嚴格說來,文化只能說是“精神的顯現(xiàn)”、“精神的產(chǎn)物”,“精神”才是文化“真正的體”,“精神”在文化哲學(xué)中居于“主要、主動、主宰”的地位,“文化是道憑藉人類的精神活動而顯現(xiàn)出來的價值物”。精神具有主客觀統(tǒng)一、體用合一、兼為主體和文化本體的特殊性質(zhì),同時又包含了豐富的內(nèi)容,所以它對于文化來講具有特殊的意義。
具體點說,上論又可分為四個層面,“就個人言,個人一切的言行和學(xué)術(shù)文化的創(chuàng)造,就是個人精神的顯現(xiàn)”,“就時代言,一個時代的文化就是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的顯現(xiàn)”,“就民族言,一個民族的文化就是那個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顯現(xiàn)”,“整個世界的文化就是絕對精神逐漸實現(xiàn)或顯現(xiàn)其自身的歷程”。
賀麟此論,使我聯(lián)想到《孔叢子》上的一句話,“心之精神是謂圣”(《記問》),章太炎說此語“微特于儒言為超邁”[8]。賀麟后來情有獨鐘地皈依中西方唯心論(黑格爾哲學(xué)、陸王心學(xué)),絕非空穴來風(fēng),其于文化哲學(xué)已顯露端倪。
歷史與文化(古今)
“古今”問題,一如“天人”、“心物”,曾經(jīng)是中國哲學(xué)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哲人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大問題。今人思想體系的建立與闡發(fā),離不開對古人思想的繼承與弘揚;而研究古人及其思想,無疑就是一條重要的渠道,并且行之有效。對此,賀麟有著高度自覺的認識。他曾經(jīng)這樣說:“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圍里,現(xiàn)代決不可與古代脫節(jié)。任何一個現(xiàn)代的新思想如果與過去的文化完全沒有關(guān)系,便有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絕不能源遠流長,根深蒂固。”[9]他后來又再次申述此旨,“談學(xué)應(yīng)打破中西新舊的界限,而以真理所在實事求是為歸”,對各種學(xué)說要以“求真、求是的眼光去批判”[10]。這既是賀麟對學(xué)界同仁的殷切期望,也是他辛勤治學(xué)的一貫宗旨,更是他數(shù)十年追求真理的最真實的最良好的體現(xiàn)。
賀麟既反對奴顏婢膝的民族文化上的虛無主義(如“全盤西化”論),又反對因循守舊的民族文化上的復(fù)古主義(如“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觀),也反對夜郎自大式的民族主義(如“中國本位文化”論)。賀麟主張在徹底把握中西文化精華與糟粕、長處與短處的基礎(chǔ)上,貫通古今文化、融會中西文化,繼承和發(fā)揚人類一切優(yōu)秀的文化遺產(chǎn)和思想成果,從而改造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爭取中國文化的獨立自主,以滿足時代的需要,以迎接未來的挑戰(zhàn)。
賀麟假其精通西學(xué)之長,進而研治國學(xué),不但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而且成為卓爾不群的名家、獨樹一幟的大家,“在前期的哲學(xué)研究活動中,他善于抓住程朱和陸王兩派矛盾斗爭的這一重要環(huán)節(jié),上溯先秦,下達明清,探索我國哲學(xué)發(fā)展的脈絡(luò),從而在貫通古今的偉大歷史工程中,進行了可貴的重點開挖工作”[11]。國學(xué)不僅是賀麟研究的重點之一,也是其“新心學(xué)”的一大思想來源,“我的思想都有其深遠的來源,這就是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和儒家思想”,但他“發(fā)揚傳統(tǒng)文化,卻并不頑固守舊”[12]。
在賀麟的理論視野里,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主體、主干,雖然說“宋以后的中國文化有些病態(tài),宋儒思想中有不健康的成分”,但切不可因此妄自菲薄,而只能說“須校正宋儒的偏弊”,進而“發(fā)揚先秦漢唐的精神”,此“尤為我們所應(yīng)努力”[13]。降而及于近代,它雖然受到?jīng)_擊、面臨挑戰(zhàn),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儒家思想的中流地位,也無須悲觀至極而取虛無態(tài)度;相反,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和決心以復(fù)蘇儒家思想。賀麟說:“民族復(fù)興的本質(zhì)應(yīng)該是民族文化的復(fù)興。民族文化的復(fù)興,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復(fù)興,儒家文化的復(fù)興。假如儒家思想沒有新的前途、新的開展,則中華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會有新的前途、新的開展。換言之,儒家思想的命運,是與民族的前途命運、盛衰消長同一而不可分。”[14]而吸收、融會西洋哲學(xué)文化以復(fù)興中國文化、發(fā)揚中國哲學(xué),可謂任重而道遠,此舉目在“從舊禮教的破瓦頹垣里,去尋找出不可毀壞的永恒的基石”,“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會的行為規(guī)范和準則”[15]。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中西)
中國文化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其犖犖而大者有二:第一次以佛教為代表(后人所謂“泰西之學(xué)”,初始即指印度佛教之學(xué)),歷千余載而完成,終融入中華文化;第二次以明季來華之傳教士為代表(后人所謂“西學(xué)”,主要即指此),至今尚處于融合之中。而影響之大、挑戰(zhàn)之巨,則以第二次為甚。
和“古今”之爭一樣,“中西”(文化)之爭可以說是近現(xiàn)代學(xué)者無法回避的一個大話題,并且是一個具有關(guān)鍵性質(zhì)的中心問題,賀麟亦然。套用賀麟的話說,“中國近百年的危機,根本上是一個文化的危機”;而中國文化之危機,其直接原因是西方文化的輸入,即“文化上有失調(diào)整”而“不能應(yīng)付新的文化局勢”,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權(quán),喪失了新生命”,這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危機”;西方文化的輸入,表面上看似乎是壞事,但實質(zhì)上并非如此,“西洋文化學(xué)術(shù)上大規(guī)模的無選擇的輸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發(fā)展的一大動力”,它“給了儒家思想一個考驗,一個生死存亡的大考驗、大關(guān)頭”[16]。危機與發(fā)展同在,挑戰(zhàn)與機遇并存,關(guān)鍵之點便在于能否把握機遇,亦即把握、吸收、融合、華化西方文化,以充實自身、發(fā)展自身,從而轉(zhuǎn)危為安,求取生存,獲得發(fā)展。
賀麟極力主張融合中西哲學(xué)文化,即其所自謂于“溝通中西文化,融會中西哲學(xué)”而“提示一個大概的路徑”[17]。確立了這一態(tài)度和立場,接下來便是如何將其付諸實施了。至此,問題的關(guān)鍵遂轉(zhuǎn)而為“中國人是否能夠真正徹底、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認識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而“真正認識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換言之,“能夠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轉(zhuǎn)化、利用、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18]。深為遺憾的是,“西洋文化的傳入,少則數(shù)十年,多則可推至明末西洋教士利瑪竇等之來華,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但我們對于西洋文化卻始終沒有真正清楚的認識,沒有以正確的態(tài)度加以接受”,因為“我們認識西洋文化,一向只看其外表,從外去了解,而沒有把握住西洋文化的核心”[19],“缺乏直搗黃龍的氣魄”[20]。有鑒于此,我們在認識和吸收西方文化時一定要徑直“進入西洋文化的堂奧”,既了解西方文化之“體”,又了解西方文化之“用”[21]。
在清華求學(xué)時,賀麟就打算“步吳宓先生介紹西方古典文學(xué)的后塵,以介紹和傳播西方古典哲學(xué)為自己終身的‘志業(yè)'”[22]。在美國和德國留學(xué)的六年中(1926—1931),賀麟博覽西方文化和哲學(xué)書籍,浸潤于西方哲人的思想海洋,使他真切地了解了西方的學(xué)術(shù)精髓,精當?shù)匕盐樟宋鞣轿幕幕揪瘛;貒螅R麟依然孜孜不倦于西方哲學(xué),大量翻譯、介紹西方哲學(xué),尤其是黑格爾哲學(xué);賀麟是中國現(xiàn)當代思想史上第一位系統(tǒng)地、全面地介紹、研究黑格爾哲學(xué)的中國哲學(xué)家,是國內(nèi)外久負盛名的黑格爾哲學(xué)專家,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并且是交口稱贊的美譽。但賀麟清楚地認識到,研究西方哲學(xué)本身并不足以成為終極目的;他研究西學(xué)的目的在于以西學(xué)為鑒,找到一條弘揚民族文化、發(fā)展中國哲學(xué)的道路,從而更好地建構(gòu)中國文化、弘揚中國文化。
賀麟說,“談學(xué)應(yīng)打破中西新舊的界限,而以真理所在實事求是為歸”,對各種學(xué)說要以“求真、求是的眼光去評判”[23]。在中西文化問題上,賀麟既反對“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的復(fù)古主義,也反對“全盤西化”的民族虛無主義,主張東西文化辯證補充、交融會合。他尊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但決非泥古不化;他虛心學(xué)習(xí)西洋文化,但從不崇洋媚外。賀麟認為,從根本上說,作為人類高層文化之一的哲學(xué),是“人性的最高表現(xiàn)”,是“人類理性發(fā)揮其光輝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類精神生活的努力”;無論是中國哲學(xué)、還是西方哲學(xué)抑或印度哲學(xué),都是整個哲學(xué)的一個分支而已,僅“代表整個哲學(xué)的一方面”,同為哲學(xué)大樹上的枝椏,同為“人類的公共精神產(chǎn)業(yè)”[24]。也就是說,中西文化應(yīng)該理所當然地融合起來。
賀麟在中西文化問題上的“新開展”是,先求透徹理解西方文化,再回頭創(chuàng)建中國新哲學(xué);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西洋哲學(xué)中國化與中國新哲學(xué)之建立”[25]。在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shè)上,賀麟始終堅持要以中國文化(或民族精神)為主體,主動地“華化”或“儒化”西洋文化,反對被動地受西洋“西化”影響;否則,“中國將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權(quán),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因此,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就是“要求收復(fù)文化上的失地,爭取文化上的獨立與自主”[26]。賀麟試圖把儒家傳統(tǒng)哲學(xué)同西方哲學(xué)融合起來,以推進儒家哲學(xué)的現(xiàn)代化,這是他開始從事中西哲學(xué)比較的標志。
在文化方針上,賀麟主張“以體充實體,以用補助用”。比如說,作為中華民族精神中流砥柱而時下又處于激變潮流之中的儒學(xué),究竟該如何促進“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呢?其不二法門,無疑就是“華化”或“儒化”西洋哲學(xué)。賀麟斬釘截鐵地指出,“今后中國哲學(xué)的新發(fā)展,有賴于對于西洋哲學(xué)的吸收與融會”[27],“不能接受西洋的正統(tǒng)哲學(xué),也就不能發(fā)揮中國的正統(tǒng)哲學(xué)”[28];“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徹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欲求儒家思想的新發(fā)展,在于融會吸收西洋文化的精神與長處”[29]。
賀麟明言,“儒學(xué)是合詩教、禮教、理學(xué)三者為一體的學(xué)養(yǎng),也即藝術(shù)、宗教、哲學(xué)三者的諧和體”,即儒家有理學(xué)“以格物窮理,尋求智慧”,有禮教“以磨煉意志,規(guī)范行為”,有詩教“以陶養(yǎng)性靈,美化生活”。因此,“新儒家思想的開展,大約將循藝術(shù)化、宗教化、哲學(xué)化的途徑邁進”[30]。具體而言,“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第一,必須以西洋的哲學(xué)發(fā)揮儒家的理學(xué)”,“第二,須吸收基督教的精華以充實儒家的禮教”,“第三,須領(lǐng)略西洋的藝術(shù)以發(fā)揚儒家的詩教”[31]。
所謂“哲學(xué)化”,即“以西洋的哲學(xué)發(fā)揮儒家的理學(xué)”。儒家的理學(xué)是中國的正宗哲學(xué),故亦應(yīng)以西洋的正宗哲學(xué)發(fā)揮中國的正宗哲學(xué);即會合融貫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的哲學(xué)與中國孔孟、老莊、程朱、陸王的哲學(xué)。當然,融會、貫通的原則應(yīng)當是“以儒家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即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為主體,去“儒化”西洋文化。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儒家的哲學(xué)內(nèi)容更為豐富,體系更為嚴謹,條理更為清楚,不僅可作道德可能的理論基礎(chǔ),且可奠定科學(xué)可能的理論基礎(chǔ)”。
所謂“宗教化”,即“吸收基督教的精華以充實儒家的禮教”。賀麟所說的“基督教的精華”,是指滲透在現(xiàn)代基督教好的現(xiàn)代意識、理性精神。賀麟斷言,“如中國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華而去其糟粕,則決不會有強有力的新儒家思想產(chǎn)生出來”。照賀麟看來,儒家思想宗教化以后,將重新成為信仰的權(quán)威,獲得“范圍人心”的力量。
為此,賀麟對“幾千年來支配了我們中國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傳統(tǒng)觀念之一”的“五倫的觀念”做了“新檢討”。賀麟認為,“它是我們禮教的核心,它是維系中華民族的群體的綱紀”,探索的目的是“要從檢討這舊的傳統(tǒng)觀念里,去發(fā)現(xiàn)最新的近代精神”[32]。
所謂“藝術(shù)化”,即“領(lǐng)略西洋的藝術(shù)以發(fā)揚儒家的詩教”[33]。儒家特別注重詩教、樂教,后因《樂經(jīng)》失傳,致使樂教中衰、詩教式微,“故今后新儒家的興起,與新詩教、新樂教、新藝術(shù)的興起,應(yīng)該是聯(lián)合并進而不分離”。賀麟明確倡導(dǎo)吸收西洋藝術(shù)的浪漫主義精神來改造迂腐、嚴酷的舊道學(xué),以使儒學(xué)藝術(shù)化、情感化,從而更富有感召力和生命力。以此為基礎(chǔ),賀麟還以儒家思想的某些重要概念(如仁、誠)為例說明“新開展”的途徑。
二十世紀上半葉是大師巨子輩出的時代,置之于在當時的“話語背景”,賀麟此言此語或許是“淵源有自”,但更貼切的說法恐怕應(yīng)當是“英雄所見略同”。三十余年前的1911年,國學(xué)大師王國維(1977—1927)明就確指出,“學(xué)無新舊也,無中西也”,“中西二學(xué),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fēng)氣既開,互相推助”[34];并且斷言,“異日昌大吾國固有之哲學(xué)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學(xué)之人無疑也”(《哲學(xué)辨惑》)。也就是說,中學(xué)西學(xué),共為一體,切不可將它們截然分割;但援引西學(xué)以“為我所用”并非生吞活剝的單純引入,需要有一個“能動化合”的過程,“即令一時輸入(西洋思想),非與我中國固有之思想相化,決不能保其勢力”(《論近年之學(xué)術(shù)界》)。與王國維“風(fēng)義平生師友間”的陳寅恪,也明確斷言,“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jié)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xué),在吾國思想史,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xué)說,一方面不忘本國民族之地位”[35]。斯言斯語,振聾發(fā)聵,至今依然“余音繞梁”!
赫然名家的“新心學(xué)”
相較于梁漱溟的“新孔學(xué)”、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馮友蘭的“新理學(xué)”而言,賀麟的“新心學(xué)”在現(xiàn)代新儒家的陣營中是比較晚出的新儒家哲學(xué),它產(chǎn)生于20世紀40年代。“新心學(xué)”雖然起步較晚,但它在新儒學(xué)的思想發(fā)展史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或許正因其晚出,因而能對前此的新儒學(xué)思潮作出公正而恰當?shù)脑u判和總結(jié),因而能合理地吸收他人(家)的經(jīng)驗與教訓(xùn),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前人的理論缺陷,從而使“新心學(xué)”的面貌與其他新儒學(xué)頗為不同,而且更具圓融色彩。
賀麟將“中國新哲學(xué)”冠之以“現(xiàn)代新儒家”之名,使他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明確、正式提出“新儒家”概念的第一人。賀麟說,“廣義的新儒家思想的發(fā)展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就是中國現(xiàn)代思潮的主潮”,“無論政治、社會、學(xué)術(shù)、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爭取建設(shè)新儒家思想,爭取發(fā)揮新儒家思想”[36]。毫無疑問,賀麟的“新心學(xué)”就是那一時代的產(chǎn)物。
賀麟的“新心學(xué)”,是他匠心獨創(chuàng)的思想體系,是他作為哲學(xué)家的智慧結(jié)晶和獨到貢獻。“新心學(xué)”是對中西文化的融通,是中國的陸王心學(xué)與西方的新黑格爾主義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與其他新儒家(如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等)頗為不同的是,賀麟的“新心學(xué)”不是建立在中西文化的“對立”之上,而是建立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礎(chǔ)之上。準此以判,賀麟“新心學(xué)”思想體系的特點之一便是調(diào)解兩個對立面,使之融和合一。賀麟如此而為,實可從其文化觀追尋根基。
作為賀麟“新心學(xué)”重要思想來源之一的新黑格爾主義,它以主觀唯心主義來代替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以形而上學(xué)來修正黑格爾的辯證法(賀麟稱之為“矛盾法”)。賀麟用新黑格爾主義“絕對唯心主義”的觀點印證陸九淵“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觀點和王陽明“心外無物”的觀點,提出了“心為物之體,物為心之用”的本體論思想,并自覺地從哲學(xué)基本問題的角度加以論證。有研究者指出,“與他同時代的新儒家學(xué)者相比,在吸收、融會、儒化西方哲學(xué)方面,賀麟取得的成績最大,這對他以后的新儒家學(xué)者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37]。此為公允之論。
賀麟的哲學(xué)立場,大體可歸于“新陸王”的范疇。相對于梁漱溟的“新孔學(xué)”、馮友蘭的“新理學(xué)”而言,時人稱之為“新心學(xué)”。“新心學(xué)”雖然沒有形成像“新唯識論”或“新理學(xué)”那樣嚴密、完整的思想體系,但它公開打出“回到陸王去”的旗幟,同“新理學(xué)”相抗衡,在學(xué)術(shù)風(fēng)格與學(xué)術(shù)旨趣方面皆有其獨到之處。賀麟不同意馮友蘭只講程朱而排斥陸王的哲學(xué)立場,“講程、朱而不發(fā)展至陸、王,必失之支離;講陸、王而不能回復(fù)到程、朱,必失之狂禪”[38]。賀麟認為,“心即理”一語足可調(diào)和程朱理學(xué)和陸王心學(xué),調(diào)和客觀唯心論和主觀唯心論的矛盾。賀麟承襲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并從心理學(xué)、生理學(xué)角度加以論證,提出“自然的知行合一觀”,構(gòu)成其“新心學(xué)”的基本內(nèi)容。
賀麟“新心學(xué)”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即吸收西洋文化的精華以充實、發(fā)展自身,求得文化上的獨立與自主,并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里達到新與舊、今與古、中與西的交融、匯合。在中國哲學(xué)史上,賀麟起到了一種會通、融合的作用——即融通中西文化,從而使西方文化的“華化”成為可能;打通理學(xué)與心學(xué),從而使中西哲學(xué)會融一家。在哲學(xué)方法上,賀麟自覺地把儒家思想方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結(jié)合起來,從而形成了一個將直覺方法與抽象方法相結(jié)合的方法論系統(tǒng),賀麟尤其重視從本體論和宇宙論理論角度來為新儒家思想奠定哲學(xué)理論的基礎(chǔ)。
賀麟堅信,“中國許多問題,必達到契合儒家精神的解決,方算得達到至中正、最合理而無流弊的解決。如果無論政治、社會、文化、學(xué)術(shù)上各項問題的解決,都能契合儒家精神,都能代表中國人的真意思、真態(tài)度,同時又能善于吸收西洋文化的精華,從哲學(xué)、科學(xué)、宗教、道德、藝術(shù)、技術(shù)各方面加以發(fā)揚和改進,我們相信,儒家思想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文化的前途也是光明的”[39]。此言信矣!
哲人其逝,惠澤長存!
2005年8月—9月,于宜賓
注釋:
[1]賀麟:《文化、武化與工商化》(1946年),《文化與人生》,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8年,第280頁。
[2]賀麟:《文化的體與用》,《哲學(xué)與哲學(xué)史論文集》,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0年,第354頁。
[3]賀麟:《文化的體與用》,《哲學(xué)與哲學(xué)史論文集》,第354頁。
[4]賀麟:《文化、武化與工商化》(1946年),《文化與人生》,第280頁。
[5]本處所說“唯心論”,取賀麟本人的理解和定義。在《近代唯心論簡釋》一書(重慶:獨立出版社,1942年6月初版)中,賀麟詳細闡述了自己的“唯心論”。
[6]“所謂精神科學(xué),是指道德史、宗教史、藝術(shù)史而言,以研究人類精神歷史為主”(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xué)》,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2年,第74—75頁)。
[7]賀麟:《文化的體與用》,《哲學(xué)與哲學(xué)史論文集》,第343—354頁。
[8]章太炎:《康成子雍為宋明心學(xué)導(dǎo)師說》,《章太炎學(xué)術(shù)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7年,第277頁。
[9]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1941年),《文化與人生》,第1頁。
[10]賀麟:《黑格爾哲學(xué)講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42頁。
[11]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xué)術(shù)》,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3年,第32-33頁。
[12]賀麟:《序言》(1946年),《文化與人生》,第2頁。
[13]賀麟:《宋儒的新評價》(1944年),《文化與人生》,第197頁。
[14]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1941年),《文化與人生》,第4—5頁。
[15]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1940年),《文化與人生》,第62頁。
[16]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1941年),《文化與人生》,第5—6頁。
[17]賀麟:《中國哲學(xué)與西洋哲學(xué)》,《哲學(xué)與哲學(xué)史論文集》,第130頁。
[18]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1941年),《文化與人生》,第7頁。
[19]賀麟:《認識西洋文化的新努力》(1947年),《文化與人生》,第304頁。
[20]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xué)》,第24頁。
[21]賀麟:《認識西洋文化的新努力》(1947年),《文化與人生》,第305頁
[22]賀麟:《康德黑格爾哲學(xué)東漸記》,《中國哲學(xué)》第二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0年,第376頁。
[23]賀麟:《黑格爾哲學(xué)講演集》,第642頁。
[24]賀麟:《中國哲學(xué)與西洋哲學(xué)》,《哲學(xué)與哲學(xué)史論文集》,第127頁。
[25]賀麟:《黑格爾哲學(xué)講演集》,第662頁。
[26]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1941年),《文化與人生》,第6、7頁。
[27]賀麟:《中國哲學(xué)與西洋哲學(xué)》,《哲學(xué)與哲學(xué)史論文集》,第127頁。
[28]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xué)》,第75頁。
[29]賀麟:《儒家思想的新發(fā)展》,《文化與人生》,第7頁。
[30]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1941年),《文化與人生》,第9頁。
[31]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文化與人生》,第8—9頁。
[32]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1940年),《文化與人生》,第51頁。
[33]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文化與人生》,第8—9頁。
[34]王國維:《觀堂別集》卷四《國學(xué)叢刊序》(1911年),《觀堂別集》(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75、877頁。
[35]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xué)史下冊審查報告》(1932年),《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2頁。
[36]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1941年),《文化與人生》,第1頁。
[37]宋志明:《賀麟》,《現(xiàn)代新儒家人物與著作》,方克立、鄭家棟主編,天津:南開大學(xué)出版社,1995年,第133頁。
[38]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xué)》,第33頁。
[39]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1941年),《文化與人生》,第17頁。
本文原載《湖南科技學(xué)院學(xué)報》(永州),2006年第3期,第96—9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