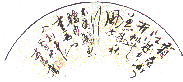一、古“今文經”的典籍
這里要說的古“今文經”,也就是儒家主要景點在先秦乃至秦漢之交前后不斷涌現,西漢學者為其整理,鉆研并形成今文經學學派時期的今文經主要典籍。
所謂今文經,是相對兩漢后出的古文經而言的。皮錫瑞《經學歷史》中明確指出:“案今古文經皆述圣經,尊孔教,不過文字說解不同而已;而其后古文家之橫決,則有不可訓者。”因此,今文經是一個歷史意義上的概念,只有同古文經比較,才有價值。
由于遭秦始皇焚書之厄,漢代搜求儒家經典的途徑有兩種:一種是憑記憶、靠背誦,根據先師口授,成當時通行文字即隸書記錄成書,作為傳本,稱作今文經。另一種則是從地下或孔壁中發掘出來的古本,使用古文也就是先秦六國文字即所謂蝌蚪文寫的,稱作古文經。但收藏在朝廷秘府中的今文經以及漢初今文經師所用傳本實際上都亦應為六國文字寫本。不過,習慣上仍稱之為今文經。
《漢書·藝文志》比較完整地記載了古“今文經”的流傳情況。據此,我們可以了解到早期今文經典籍的簡錄: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傳周氏二篇。”
“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顏師古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也即申公、后蒼、韓嬰三人所傳。
“(禮)記百三十篇,其實子后學者所記也。經七十篇,后氏、戴氏。”
“樂記二十三篇。”
“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春秋…經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有公羊、谷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學宮,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孝經一篇二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龔氏四家。”
時今文經典籍,主要就有如此種類。后世《十三經》之中,包括在內的就有《周易》、《今文尚書》、《詩經》、《禮記》、《儀禮》(即禮《經》)、《論語》、《春秋》及《公羊傳》、《谷梁傳》、《孝經》共十部。沒有算《爾雅》、《左傳》、《周禮》及以上諸經中一些“古文”本在內的古文經典籍。另《樂記》就已佚,不論。
二、《四庫全書總目》中古“今文經”的目存狀況
在中國古代典籍編纂史與目錄學著作史上《四庫全書》及其《總目》無疑占據了費藏重要的地位。從經學學術角度上看,《四庫全書總目》是研究儒家經典源流以及概況的重要參考依據。下面,便是《四庫全書總目》中有關古“今文經”目存狀況的一些敘錄:〈據中華書局之《欽定四庫全書》(整理本)〉
“《儀禮注疏》十七卷(內府藏本),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出殘闕之馀,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一曰戴圣本,一曰劉向《別錄》本,即鄭氏所注。”“玄注參用二本。”且陳述道:“蓋由《儀禮》文古義奧,傳習者少,注釋者亦代不數人,寫刻有訛,猝不能校,故紕漏至於如是也。”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內府藏本),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另敘:“知今四十九篇實戴圣之原書,《隋志》誤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內府藏本),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內府藏本)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并論曰:此書或“則為谷梁子所自作”或“則當為傳其學者所作。”
以上就是關于古:“今文經”的不多且零散地記錄下的目存情況。由于《四庫全書總目》各條目偏重于近世尤其是明清時期以來的書籍版本元流域優劣情況的分析與敘述,所以關于秦漢時今文經典的目錄學方面的內容就不多且亂。不過,我們還是能夠歸納一下這一方面的一些要點。
首相,經過兩千多年的歷史流變,古“今文經”除了很少一部分流傳至清代,大多數典籍已蕩然無存。當年西漢今文經僅五經即有十四博士,文本尚多,后來便歷經劫難,《樂記》、《今文尚書》終于失傳,其余傳世之作,夜空南說就是當年的本來面目了。
其次,東漢訖兩晉是古“今文經”一個難度的隘口。《儀禮》、《禮記》全屏東漢鄭玄注本得以延續后世,《公羊傳》、《谷梁傳》分別為魏晉間何休(解詁)、范寧(集解)而尚存。西漢的古本要靠東漢乃至魏晉之人或注或疏方能或多或少保留些原來面目,實是不幸中之幸事。
最后,現存“今文經”古本全都唐人之疏。賈公彥、孔穎達、徐彥、楊士勛諸公上承兩漢遺經,為之傳疏,相當于重新鑒定的作用。因此,古“今文經”尚能保證其“古”的本色,不至于受后世改經、疑經、駁經之患。而《四庫全書總目》中最早的古“今文經”版本再往上也無非是唐人疏后寫本,亦起了上承下接的作用。
三、《四庫全書總目》對于古“今文經”評述及影響因素等
《經部》開篇《總敘》首句即曰:“經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便對群經之價值作了高度概括,抬高到無以復加的神圣地位。今文經典的脂膏地位,也是不可置疑的。
其下《易類》敘中未貶今文,只斥“漢儒言象數……《易》遂不切於民用。”《書類》敘稱:“諸家聚訟”,不辨今古文,也是事實。《詩類》則曰《毛詩》或有“經師口授”,“去古未遠,必有所受。”或是猜測其中也有今文經的東西,或今文經師的意旨。《禮類》指稱:“《儀禮》難讀”,《禮記》“無庸聚訟。”也算肯定其古老性和同下敘《周禮》(古文經)之異。《春秋類》“三傳”并舉,曰:“訖能立于世。”貶《公羊傳》、《谷梁傳》之說,也不贊同,所持尚允。《孝經類》敘稱其文,“去二戴所錄為近。”認為可能是《禮記》一篇,述其源于今文經。《樂類》直書:“考諸古籍,惟《禮記·經解》有“《樂》教”之文。”稱其漢世錄譜其后便佚。這也可算如今文經典。
總覽有關敘文,對于古“今文經”的評價并不詳核。對于古今文經學流派之爭,《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者所流露出的也是一種看起來有些“超然”的態度。古“今文經”既無熱評,也無冷諷,數筆帶過,似乎正是《四庫全書總目》對于古“今文經”這一早期重要典籍類別的主要態度了。
我想,《四庫全書總目》對于古“今文經”的評價時受到一些重要因素影響而產生的結果。
首先,古“今文經”的原貌在兩千余年的流傳過程中,難得一窺。存世的經文能有明確源流關系的不多,所以對其的論說也就僅僅是“語焉不詳”的狀態。
其次,編輯、纂寫《四庫全書總目》的四庫館臣們,大都受清代漢學思想的影響,形成所謂的“四庫館派”。他們重實學,對于今文經學大致取排斥態度,對今文經也并不過份推崇。戴震、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等人的治經思想對于其經部目錄無疑會有明顯的影響;總纂官紀昀也不會例外。
另外,清代學術發展到乾隆時期,韓雪鼎盛,考據之風日起,學術氛圍比較濃厚,各種思潮也在這樣的背景下做小范圍、淺層次的交融。常州學派劉逢祿、莊存與等公羊學家的努力,拉開了后來今文經學復興的序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四庫館臣對今文經比較公允的評價,不能不說受到了今文經學一定程度的影響。
《四庫全書總目》是對中國傳統學術在目錄學意義上的一次重要總結。由此可以引出,古“今文經”演變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時間段之后,幾乎已經失去了它在早期經學中的地位,以致于存世典籍都有很多質疑。《四庫全書總目》中有關古“今文經”的評與述,似乎告訴了我們:這一頁早已翻去,所剩的記憶不足為訓。傳統的、早期的學術與典籍,也大抵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