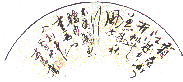內容提要:明朝,是一個程朱理學觀念官學化的時代。作為明中期最為杰出的文學家之一的歸有光,其思想態勢一方面繼承了儒家正統,接受的更多的卻是秦漢時期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呈現出兼及道家、佛家的態勢。他的文學觀有著不同于傳統、比較開明的一面,這與當時的王學思潮、個性經歷和生活環境關系密切。從審美接受者的角度入手,從震川作品中尋找其思想的根源,可以窺見其思維的脈絡,也有利于更好的切入欣賞其詩文的感人之處,更全面的解讀文字背后的歸有光。
關鍵字:震川;思想態勢;儒家;道家;佛家
作者簡介:李雅蘭,女,1985年生,漢族,湖南桃江人,現就讀于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古代文學專業。
和一般社會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一樣,美是受歷史制約的。它不僅牽涉到美學領域內的一切問題,還要牽涉到具體的藝術創作實踐情況以及時代文化思想,要涉及審美意識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歷程歷史。我們在解讀震川作品的同時,不得不先從時代的大背景和具體的文化思想著手。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七》中說過:“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顧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在強調全篇全人的同時,還要把作家作品放入一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中,作具體的歷史分析。
震川所在的時代,主要處在明嘉靖、隆慶之世。統治者昏庸腐朽,皇帝迷信道教。明初,社會動蕩,時代的使命感讓文人常浸透著深沉的憂患意識。經濟復蘇后,憂患逐漸銷蝕,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專制下的創作不安全感。欣賞美的角度逐漸從人心思治、崇拜英雄轉移到了欣賞平穩和諧、雍容典雅。以八股文取士的文化體制,精神上的匱乏,讓文人學子致力于學寫古文與八股文,憑八股文博取功名。程朱理學流行,陽明的心學與禪宗思想日漸滲透,商業經濟的繁榮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資本主義的萌芽這許多的因素加之在一起,使得生活在這個孕育重大變革時代的文人們在追求著仕進和自我平衡的同時,又關心著世運民情,有了“重道德主義”和“格物致知”、“經世致用”的思想。筆者認為,他的文學思想主要呈現了一種古典儒家思想為本,道釋并存的態勢。[1]
一、兼具先秦儒家的古典原型,摻雜三綱倫理和天人感應
當明之時,朝以重儒尊道,理學立國。程朱理學擁有著儒家正統地位,普及官學化。歸有光思維中的儒家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
余少時出入學,見里師必以《小學古事》為訓。時方五、六歲,先生為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師之語,竦然知慕之。[2]
《先妣事略》一文中就有記載:
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人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3]
他寫了不少經解文,它們比較明顯而集中地體現了其文章“根抵六經”的特點。黃宗羲《明文海》提到有光:
其言“為文以‘六經'為根本,遷、固、歐、曾為波瀾”,圣人復起,不易斯言。[4]
在現今通行版本的《震川先生集》中,卷一就是經解。錢謙益片言指要:“先生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如《易圖論》、《洪范傳》是也。故以《經解》為首。”[5]震川所受教育蓋系儒家思想,其思維方式和偏愛喜好也是以儒家思想為本,重視經、史。然而,他身處于發展宋明理學的新儒家時代,其儒家思想卻是較接近先秦與兩漢時代的思想。
(一)積極入世
在政治作為與個人面對仕宦的態度上,有光表現出上進主動,對社會關懷的一面。在《沈次谷先生詩序》提到:“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晚年臨終前還在給兒子的手書中還流露出事業未竟的遺憾,積極用事的政治思想貫穿了他的一生。他還曾在《碧巖戴翁六十壽序》中寫道:
余少時有志于古豪杰之士,常欲黽勉立一世之功;既老不遇時,始益悟人時倏忽。[6]
雖然“垂老尤困在閭中”,但歸有光卻大大跳出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偏狹。可謂符合孔子美學思想的基礎——仁學。仁學是孔子一種具有倫理性的美學,它將心理欲求的滿足,導向符合社會倫理的道德規范,并使人對現實世界保持高度熱忱。所以,盡管他身份卑微,卻依舊關心著世運民情。在他為數不多的一卷古今詩中,有不少詩篇是應時事而作的。《鄆州行寄友人》中,就寫的是水災后人民生活中水深火熱之中,賣兒鬻女、呼告無路的慘況。他曾考察三江古跡,寫下《三吳水利錄》(四卷)、《水利論》等,提出太湖入海的道路——吳淞江只需合力浚治,使太湖的水向東流,其它的水道就可不勞而治。后海瑞采用、實施后頗見成效,“全活江蘇生靈數十萬”。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作亂,他先下了《甲寅十月紀事二首》、《海上紀事十四首》等詩作,入城籌守御,提出具體的作法。可見其思想抱負并非空談,而是有完整想法與實質措施,建設性的提供見解改善問題。同時還寫有《備倭事略》、《昆山縣倭寇始末書》以備后世借鑒之需,頗具史料價值。這些都體現了他經世致用的思想,把國計民生作為始終關心的頭等大事。
(二)仁物愛民
《明歸震川先生有光年譜》中還錄有:
嘗謂縣官為天下牧民,宜求所疾痛苦,不當過自嚴重,令閭不自通,每聽訟民作吳語,務得其情。[7]
這種深入人心、感化人民的做法,使人心悅誠服,才能維持長久。有光就是抱持這種想法,“俗刁悍,樂以命誣訐富家,有光必親至其地,呼村落愚民,察問縣政。縣故多盜賊,依湖山間,用計擒獲其魁,誣服者釋之,出獄中死囚枉濫者三十余人。一重囚母親死,許其歸葬,如期詣獄。”[8]震川認為為官之道不在刑罰之酷而重仁民愛物、以德化民,他甚至可以不顧身份低微,無懼權貴和輿論的壓力,奔走呼告,為民請命、申冤。在他的文集中至今還收錄有不少這樣的文章,如《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冊揭貼》、《九縣告示》、《乞休申文》、《長興縣編審告示》、《張貞女死事》等。《長興縣編審告示》言:
長興縣示。當職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不恤也。[9]
當職為民父母,豈不欲優恤大戶,而專偏重小民?特以俱為王民,爾等大戶,享有田宅僮仆富厚之奉,小民終歲勤苦,糟糠裋褐,猶常不給;且彼耕田商賈,大戶又取其租息,若刻剝小民,大戶亦何所賴?況大戶歲當糧長,不過捐毫毛之利,以助縣官;若小民一應役,如今之里遞者,生計盡矣。如之何不為之憐恤也?[10]
在強調家庭倫理、重視孝道與伸張正義公理方面,則部分偏向董仲舒的儒家思想。
(三)孝悌恭敏,重視綱常
從《震川先生集》中看歸有光的文章,可以發現他對三綱五常的倫理規范可說是循規蹈矩的接受,幾乎很少懷疑。他的文學觀制約著他寫出的大部分文本,其文集中的倫理文章,數量最多的是表彰女性節烈的。他曾聲稱:“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于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出現這種偏重,是因為他少有所見忠臣行為,并非其文學文本的價值所在。
卷二十六《歸氏二孝子傳》中,他立傳贊譽歸鉞對父母的絕對服從,歸繡對母親、弟弟及兄弟之子的無微不至的關愛,集中描寫二孝子之孝行與友愛,而對于父母為何對孝子產生不悅的原因,和父母兄弟行為是非的評價卻未涉及。可見有光對人倫綱紀的重視,也顯現了他著恪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原則,卻忽略了倫理思想是包含了義務但也有權利,著實有著一種我們現今不可理解的迂腐和愚昧。這或許意味著歸有光思想深處,父母、兄弟的任何行為對子女、手足來說都天經地義的,只允許接受,不允許反抗。他在恪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余,卻忽略了傳統儒家有重生重義的一面、對父母從義但也可爭諫、倫理思想是包含了義務但也有權力的雙向原則,因此把近乎愚孝的行為合理化的揭示稱揚。
他也曾寫過《見村樓記》以緬過友李憲卿,并作有《李中丞行狀》。見村樓樓主李延實為憲卿第五子,有光還曾為延實的祖父寫有《李南樓行狀》,提及與憲卿之交。
余聞而傷之。余始與憲卿游,見其豐儀俊清,皎然不染坋埃。時相過從,談笑竟日,醴善豐嘉,不索而具,憲卿一無所經意。乃知府君所以縱其子游學如此。[11]
《見村樓記》中的:“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挽父之母知而告之,余可以為挽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是以告知延實之父其人其事,以點其不忘先人、水木之思、桑梓之懷、霜露之感的人倫美德,以點不忘本之主旨。震川也說過“情之所在,即禮也”之類的話,但恰恰是那些他自己較為獨特深厚的生存體驗,尤其是情感體驗,又使他不自覺地超越其文學觀念的拘囿,創作出其最具價值的“事關天屬”類散文。
董仲舒建立的“三綱五常”,是把儒家仁道的施行建立在“天意”的基礎上。為了締造漢代一統帝國的意識型態,同時又把君子說成是天意的代表者,將朝代更替、四時變化、宇宙人生等一切事物,幾乎無一不包含在“天人感應”中,讓儒學摻染了黃老學說和陰陽思想。他依據的所謂天意,實際上就是吸取法家而提出的“三綱”的思想。較之于先秦儒家所說的禮,這不再是個體自覺的自律行為,而是具有更大得多的束縛人們個性發展的作用,帶有統一性、威懾性和強制性。“天人感應”要求人們必須絕對的服從,否則就會遭到上天的懲罰。加上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學定于一尊成為官學后,儒家的學術路線便著重于應世的外王事功之學,先秦儒家反求諸己的人性理論反而被忽略而逐漸衰微。我們從綜述中可見,有光對于倫理的遵從似乎有這樣的傾向。
另外歸有光也有意將“天人感應”帶入文章中,將冤屈事件的內幕與神異事件想結合,如將張貞女之死與安亭發生大旱結合的描述,通過神異事件寫出安亭大旱是上天顯示貞女冤情的懲罰方式。這些神異現象可能是當地居民的各種附會,透過歸有光耳聞目睹而匯集文中。由此也可以體現當時民眾便有一種以天人感應維護倫理的思維定勢,而這也成為了有光維護倫理的正義性證明。他在伸張正義的文章里加入神異色彩,一方面是因為神異有昭示善惡、懲惡揚善的效果,另一方面又對天不能保護節義之人在世時無遭禍害而感到困惑傷感,因此在死后附會神異現象以慰人心。有光也能從中獲得一份慰藉和滿足,這是屈于自然權利而達成的一種心理平衡。然不論是何種原因,都顯示歸有光不懷疑天人感應的可靠性。這兩點與董仲舒的美學思想是相近似的。董仲舒將陰陽五行思想與先秦儒家思想摻和在一塊,使得傳統儒家思想雜染了神秘的色彩。傳統儒家對于人與天或自然的關系,主要是從人的道德精神所達到的境界及人的活動同自然的規律性的關系來說;但是董仲舒認為天是有意志情感,能賞罰善惡的,且是儒家君主的形象,人與天變成主從關系,將儒家學說神學化。
震川崇信儒學,認為朱子之說也“有過于離析附會者”,與圣人之意“未必一一盡合”,這是與固守傳注、拘泥于宋儒之學的一般儒生不同的。他講“道”較多的帶有儒道的原本色彩,講文道合一,尤其重視“原本六經”、以“圣人之經”為“原”。另一方面呢,又可為自己道其所道留下活動空間,歸有光說“六經、圣人之言有非一人所能定者”,批評理學流弊必引圣人之言為據,都說明他們宗經、原道以秦漢儒道為歸,是十分有利于他們在散文中表現獨特的思想觀點和生活感受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歸有光的儒家思想是兼具先秦儒家的古典原型和摻雜三綱倫理、天人感應的雙重思想觀念。
二、兼有道釋并存的態勢,仁者靜與以釋其懷
儒家思想雖是震川人生哲學的主要基調,但在現實世界中不斷受挫卻長期挑戰著他入世積極的觀念,五次南京鄉試不第、八次春官不第,科考不斷失利。在別集卷六《己未會試雜記》中,他道出科考不公平的現象。仕途的不得意,家庭的種種不幸,社會的不公允,生活之負而不勝其重,這些理想與現實的激烈沖突讓震川疲于奔命,他需要心靈的慰藉,需要一個休息的港灣。
(一)以道安心,放于天壤之間以為達
安亭授學時期他曾潛心研究莊子,《震川先生集》別集卷七《與沈敬甫》中就可以看出:
《莊子》書自郭象后,無人深究。近欲略看此書。欽甫有暇,可同看,好商量也。[12]
他還曾經大手筆的做過《道德南華經評注》十二卷,且不論其質量如何,單從這十二卷的數量,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在其中耗費的精力,許是人生的不短的一個時間段。而這期間他的心定是因為不平靜而安于做注,以書之理和本身體會去平息內心。在他的作品中也可見老莊之語,《戴楚望集序》中引《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讀史二首》中,他直取《莊子·逍遙游》,有如莊子之文思般的筆觸:
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雕與鳩,相笑榆坊間。[13]
《西王母圖序》云:“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書沈母貞潔傳后》:“余以是之仙人之在天地間,常乘云氣,千歲而不化也。”皆是莊子筆意。在《碧巖戴翁七十壽序》文中“自放于天壤之間以為達”類似于《莊子·逍遙游》中那種心靈自在的境界。那是一種無羈絆的狀態,不需要考慮名祿權利那些世俗的價值標準,不光是形體上的自由,而是“與造化者同其逍遙”。恐怕此時震川非單為贊敘戴翁曠達的心態,也是道出了其內心的向往吧。這樣寧然自得、祥和天成的境界,可是不用為世事所累,可以忘卻塵喧,那是的他才是自己的,那時的心才是散淡灑脫,不為塵俗之事所傷神。
卷十七《陶庵記》,有光還直言對淵明的嘆羨。
平淡沖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于窮,而直以窮為娛。
贊說他
融融然塵查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直善處窮者也!
震川嘆羨淵明的“復得返自然”,而淵明尚自然的思想與老子“反璞歸真”的人生哲學又相類似。返自然的心是要超出塵俗的,需要放下一些世俗的價值觀念,需要消解心中的欲望,是“知足之足,常足矣。[14]”才能如《飲酒詩》中所提,做到“心遠地自偏”,這全在人心之欲的舍與棄以一種超越世俗的虛靜的心胸面對山水、田園。
與儒家的積極入世不同,道家思想就為他提供了這樣一個暫憩的港口。以道家思想為文學修養之資,創作動力與創作對象常指向自然的“興趣”。無人世利害關系的自然景色,只能進入虛靜之心而呈現其美的意味。“致虛極,守篤靜,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老子》十六章)[15]自有道者應肉體生活與精神生活臻于和諧之境,拂去心中雜念,靜定自然。因為在虛靜的審美感知過程中,必須力排外界干擾,向內沉潛、探索,讓生命回歸本真。莊子推崇的也是這種精神狀態,稱“無己”、“無功”、“無名”和“外天下”、“外物”、“外生”狀態為“心齋”“坐忘”,從內心排除利害觀念。這讓長期處于對理想執著付出的震川,內心得以平靜和休憩。《碧巖戴翁七十壽序》中歸有光這樣自敘心聲:
古有莊周之徒。常思自放于天壤之間以為達。彼誠有見,謂當世之事,一切皆中吾之心,吾以有為應之,雖百年之內,足以有所成,則吾亦可以少自苦,而庶幾所至有涯而不辭也。[16]
(二)兼及釋家,愿為神仙眷屬
居安亭之際,震川與不少僧侶往來,他的佛家思想大多出現于詩中,如《甫里天隨寺》中:
斜日半庭雨,清風數卷詩。空門往遺像,千載爾為思。[17]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己亥庚子余嘗讀書于此》言:
鄧尉山前古佛宮,湖波萬頃貯群峰。欲尋老子當年處,五杏參天寶殿東。[18]
《請斥命事略》中也有說:“有光自嘆生平與世無所得意,獨有兩妻之賢,此亦釋家所謂神仙眷屬者也。”在《滄浪亭記》雖僅透露了他曾與浮圖文瑛交往,但《讀佛書》、《光福山》等詩作中不但已經指明他與佛家有淵源,常來往于廟宇,也道出了他生活中對佛家典籍有研讀的現象。《贈菩提寺坤上人序》開篇即言:
予昔年讀書吳郡西萬峰山中。舊有大藏經,在佛閣下。間往觀之,因得盡見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而妙法蓮華經、維摩詰諸上品,皆略究其大旨。[19]
可見“讀佛書”是真有其事,不光是讀,還“究其大旨”,有些研究。此后,文中又提到:
嘉靖辛亥,予因悼亡,為延僧誦經,取其疏觀之,往往懺罪求福之語。蓋布施持戒之說下矣,而又如是,失逾遠矣。因以為亡者之心,與佛之心一而已。即輕舉遐覽,乘云御風,逍遙于兜率之天[20],豈有所謂三道六趣云者?于是悉取其語而更之,直著此心,達之空王而無怍;使世間果有佛,即其理如是。長老唯唯。率其徒誦數十晝夜,予蓋恍然真見珠宮貝闕生天之處矣。[21]
順帶一提的佛家思維,雖不自成一思想體系,但不可忽視。
我們可以在《震川先生集》中找到諸如《跋佛頂尊陀羅尼經幢》、《跋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幢》、《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僧扶宗傳》[22]等文章,皆為佛家所做。《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張氏女子神異記》等文,體現他對佛家“因果報應”說的認同。《張氏女子神異記》是繼《書張貞女死事》后,對其事雜以神異之說,強調“因果”:
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大雨如注。賊子吁天拜,拜乎兩腋血流。[23]
作者的崇敬和憤慨是不言而喻的。卷三十中,他有數量可觀的廟文、神文,多是以官吏之名祈雨求神,如《吿祭昆山縣山神文》、《告昆山縣城隍神文》、《祭長興縣城隍廟文》、《祈雨文》、《祀厲告城隍神文》等“實體的精神”文字是帶有一定的佛家色彩的,也體現了他認識的時代局限性。
有光生活在陽明心學興起的時代,他贊美陽明“固聰明絕世之姿,其中必獨有所見”。在《示徐生書》中提到:“圣人之道,其跡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主之,跡以征之,爛然、炳然,無庸言矣。”又說:“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證無心之理,則本原洞然,意趣融液,舉筆為文,辭達意勝。”[24],“頗有感發人處”(歸有光:《文章體則》)。他認為:
文字又不是無本源,胸中盡有,不待安排,只是放肆不打點[25]。
實已將心學精神注入散文藝術精神。陽明心學雖屬于新儒學,而其陽明哲學成分多來自禪宗,禪宗同樣標榜“心是道,心是理”。慧能《壇經·疑問第三》說:“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故劉宗周也曾稱王陽明為“陽明禪”,兩者頗有相通之處。禪宗大師也認為“率性之謂道,率情之謂倒”(《紫柏老人集》卷二《法語》),有“即心即佛”[26]之說。由此可知,震川所提倡的散文藝術精神也不是死守儒道以為本。而且我們在他的《史記評點》、《文章指南》都能看出,二者都重視“法”的特點,和專“為舉業而設”的嫌疑。在《文章體則》中他提到的“文章非識不足以厚其本,非才不足以利其用,才識俱備,文字自爾高人”,由此,他的文學思想可見一斑。
歸有光的思想兼受著儒、道、釋三家的思想,人格修養也勢必受到相應的影響。思想是意識的,以其中的思想轉化、提升一個人的生命,使抽象的思想,形成具體的人格。此時,人格修養所及于創作時的影響,是全面且由根而發的影響。立足于現實世界,道家的“虛靜之心”可以成就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中對自然之美的觀照,與儒家的“仁義之心”可以說是心體的兩面,皆為人生而所固有。孔子也曾提過“仁者靜”的意境,老莊也提出過“大仁”、“大義”。面對現實的不公允,佛家的“因果”之說又給這顆不平的心帶來一些主觀的安慰,以求達到一種人格和精神、心理的平衡,彌補自然力量的不足。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有光,將自己有限的生命轉化提升為儒家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此與客觀事物相感,必然而自然的對人生、社會、政治有無限的悲心和責任[27]。
主要參考文獻:
①(明)歸有光著、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沈新林:《歸有光評傳》[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8月版
③(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四部叢刊》集部,清康熙十四年刊本
④(清)張延玉撰:《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⑤王云五主編,張傳元、余梅年著:《明歸震川先生有光年譜》[M],臺北: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初版
⑥《歸震川先生未刻集》,清光緒八年吳祖畬抄本
注釋:
[1]沈新林:《歸有光評傳》[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8月版,P91-109。
[2](明)歸有光著、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M],《跋小學古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P119。
[3]同注2,P594。
[4]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十一冊《明文海評語匯輯》一卷。
[5]同注2,首附錢謙益《新刊展川先生文集序》,P10。
[6]同注2,P343。
[7]王云五主編,張傳元、余梅年著:《明歸震川先生有光年譜》[M],臺北: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初版,P87。
[8]同注7,P87,《震川政績》,選錄自《湖州府志·名宦錄》。
[9]同注7,P924-925。
[10]同注7,P927。
[11]同注2,《李南樓行狀》,P579。
[12]同注2,P863。
[13]同注2,P939。
[14]衛廣來譯注:《老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第2版,P79。
[15]朱光潛:《西方美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4月版,P16。
[16]同注2,P341。
[17]同注2,P960。
[18]同注2,P968。
[19]同注2,P274。
[20]兜率之天:出自《法苑珠林》。“兜率天雨摩尼珠,護世城雨美膳,阿修羅天雨兵仗,閻浮世界雨清凈。雨者,被其惠,猶言賜也。”
[21]同注19。
[22]見《歸震川先生未刻集》,清光緒八年吳祖畬抄本,卷三。
[23]同注2,P422。
[24]同注2,《山舍示學者》,P151。
[25]同注2,《與沈敬甫》,P865。
[26]出自《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個恁么,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即佛。曰: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白于馬祖,祖曰:梅子熟矣。”
[27]參照趙利民主編:《儒家文藝思想研究》[C],徐觀復《儒道兩家思想在文學中的人格修養問題》,北京:中華書局,P165-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