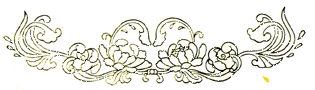一
霍金在《時間簡史》中說了些什么,他說:終極問題可以解決,而且,“解決”是人類理智的最終勝利。那時候的霍金熱情洋溢,陶醉在奧秘的掌握里。很多年過去了,與霍金一同興奮的人們卻得到這樣的消息,他放棄對終極理論的尋求。“我們不是能從宇宙之外觀察宇宙的天使”,理由也簡單,聽起來卻刺耳。霍金和相信他的人何時成了“天使”,他們把自己打扮成天使?
霍金在西方思想界作為一標識,讓我們認出幾千年來西方人運思的軌跡。沒有中斷,不過在人和神之間閃爍不定。按照這樣一種說法:如今科學家對神學家的尊重較過去為多,那么,是否可以認為,運思之在西方,始終一迷途而已。愛因斯坦,這個科學的象征性人物,當記者詢問是否有上帝時,他的回答是不要問我這個問題。問題何以讓愛因斯坦為難?他拿不準。
迷途羔羊!愛因斯坦或霍金不過一迷途羔羊罷了。
二
《圣經》說人只能看見上帝的背影。西方人從古至今的運思拖長了這“背影”,命定埋沒在其中。
一切努力均告多余,如托馬斯晚年所言,他以前所寫的全部作品對他來說毫無價值。西方人學聰明了,最聰明者莫過于維特根斯坦:“與我們關系最密切的問題不可言說”。
維特根斯坦的全部努力,搞明白的就是什么是可說的、什么是不可說的。這下好了,他應該清爽。維特根斯坦沒理由讓人費解。然而他為什么一會指出形而上學都是胡說八道,一會又表示對歷史上偉大的形而上學家肅然起敬呢?他搖擺于說與不說之間,作為人的處境之無奈完全暴露出來了。最要命的是,維特根斯坦把問題對人的逼迫推向極致。他認為人若確實能夠提出問題來,就會有答案。這是什么意思?問題不是一直讓他揪心嗎?怎么到頭來連問題都提不出來?
在問題面前,維特根斯坦之難堪讓人印象深刻。悶罐,試著想象一悶罐,他就住在里頭。
其實,就西方的思想傳統而言,人都住在悶罐里,能打開這悶罐的只有上帝。
三
羅丹的雕塑《思想者》很有看頭,對思的肯定連同對人的肯定。但此種肯定注定無法完成。《思想者》雖然痛苦但自信,少了點惶惑。“惶惑”很重要,它表明人不可能找到終極問題的答案。西方思想的大傳統在于承認人無知,這傳統的延續雖然出現過叛離,譬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學革命等,終究因其沒有撬動問題而歸于淺薄。《圣經》說得明白不過:看見我的人不能存活。人終其一生無緣親睹上帝,即是人無知。西方人從來都樂于談論人的無知,只是到了后來,腦袋發昏才把這事忘了。當然,有些人沒忘。“但澄明從何而來,何以有澄明?在這有中什么在說話?”,海德格爾如是說。海德格爾畢生運思 ,目的只有一個:恢復對上帝的信仰。要恢復信仰其實簡單——只需問題,海德格爾找到的也就是問題。
蘇格拉底是希臘最有智慧的人,因為他知道自己無知。注意,這是神說的。
四
《莊子》說:“不知深矣,知之淺矣; 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中國人也講無知,但此“無知”不是彼“無知。彼無知有一個高于人的知,在他那有答案。此無知昭告的是人向外或在外求知會誤入歧途,亦即所得“淺矣”。中國人早就知道不可站在宇宙之外求知,亦即“外矣”則“淺矣”。從這樣的視角看西方人,他們的孜孜以求真乃糊涂。人的思胡攪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便在預料之中了。中國的思想傳統沒有高于人的知,因為中國人自古以來沒有溜出宇宙之外。“內矣”則“深矣”,從此可進入中國思想之核心。“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司馬承禎如是說。不知就是讓人放棄思,因為宇宙之存在與人類認識無關。上帝的知打殺人的思。人不思,上帝連出場的份兒都沒有。《易經》說:天下何思何慮!
五
中國思想有一個謎,中國人從來不受終極問題的困擾。
為什么會有?老子說:有生于無。有學者稱,這等于沒有回答終極問題。沒有回答還是無意于回答?何以不回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里有答案:道生萬物。什么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萬物自己如此!所謂無中生有,最后的答案就在這里。
《易經》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說:“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乾坤為萬物的本原。乾坤不在萬物之外,可以具體為天地、男女、日夜等等。追溯萬物的本原,而在萬物之內,即回到自身。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開句便為:無極而太極。無極,也就是無。“無”,打斷了人的思。藉此“打斷”,中國人的思始終被定位在存在之內。
在存在之內,問題無法提出。
中國人回避終極問題,這種看法很流行。實際上,沒有回避,只是問題消失了。
探求萬物的本原,為什么中國人講“自本自根”,而西方人講“被造”?因為后者帶著問題去思,前者之思卻起自問題消失之后。
六
維特根斯坦徘徊于說與不可說之間,他的不可說是說的失敗,而說暴露的是不可說之痛。維特根斯坦很慘,作為哲學家的他遠不如神學家幸福。當然,其“慘”,正好為神學鋪路。
問題在中國思想里消失了,中國人就是清爽!“非樂不足以語君子”,程子如是說。有學者指出,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不錯,但深層原因卻不是他說的那些,而是中國人之思不受問題的侵害。張子說:“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若有問題,則不得說“不能”,而“不得已而然”,也就是自己如此。因為沒有問題,中國人心靈澄澈。
同一個問題,在中國,它消失了,在西方,卻如梗在喉。結果,由問題導出的本原很不一樣,一者在內,一者在外。只有觸及問題,才可懂得天道與上帝是不可比的。中國人講“天生萬物”或“道生萬物”,一個“生”字,說的是本原與萬物如母子般不可分。西方人講上帝創造世界,“創造”,有一個從無到有的時刻,以此時刻劃界,本原與世界判然有別。不可比就是這樣凸顯出來的:中國人之思消解于無,西方人之思越過無不肯止息。
問題,把西方人帶到上帝面前。
問題消失,中國人回歸自身。
象維特根斯坦那種尷尬,不會出現在中國哲人身上,因為中國的智慧讓問題消散無余。
七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子罕言性與天道”,孔子的弟子如是說。不可說或少說,在此,似乎找到了中西思想共通之處。但與前面談到“此‘無知’不是彼‘無知’”一樣,此“不可說”亦非彼“不可說”。彼不可說是想說卻說不出來或說不到底,此不可說不再有意于說。當老子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以他的知見,當已透識一切。而耶酥,那個自稱上帝之子的人,談到其父時卻極盡謙卑,甚或誠惶誠恐。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區別?問題在而無答案,人何其失魂落魄!問題消失,人無須向外祈求,又何其悠游自在!孔子的見道之言可謂從容不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大道流行,就在眼前。其實孔子也沒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道就在人之所見中,說為贅說。與中國不同,西方的說難免隔靴搔癢。玩味一下奧古斯丁的這句話吧,“信,就是信你所未見的,信的回報,就是看見你所愿見的”。走到生命的盡頭,人依舊一無所見,只得靠信來維持期盼。期盼什么呢?上帝!這個問題答案的最終掌握者。
有學者把老子和海德格爾捆在一起做研究時,興奮地發現后者是前者的異域知音,真是謬之千里了。海德格爾說得再清楚不過,“還只有一個上帝能夠救渡我們”。海德格爾認為真理自遮蔽,又自敞開。敞開即澄明。海德格爾見道而又與之隔了一層,即他終有一問,露出了西方人的本色。老子叫人復歸于嬰兒、復歸于無極、復歸于樸,當然沒有此問。
敞開而在其中,這是中國人。
置身于外,鉆入悶罐,這是西方人。
八
中國的思想傳統沒有“救渡”一說,因為中國人從不受困于問題。《易經》,為儒道兩家所尊奉。這部經典,其對世界的解釋是自圓的,沒有人之思夾雜在里頭。它模擬宇宙生化,得其要領進而順從之。所謂“天地變化,圣人效之”,就是此意。易之六十四卦皆由乾坤兩卦推衍而來,對這樣一個系統,中國人沒有異議。“異議”指拒斥或不接受。人何以不接受這個世界?理由只有一個:問題。此世界對人來說是有問題的。有問題,大的方面講,意味著宇宙之存在在人只得被動接受,小的方面講,人之生死非人所能決定。不幸!人因其不幸而需要救渡。救渡來自上帝。異議,在西方思想傳統中舉足輕重。為什么西方人必得有另一個世界,方可減緩存在之沉重,對準了問題,就一點也不難理解。
對海德格爾所說“人在大地詩意地棲居”,很多人頗為欣賞。試問有多少人透識此種“詩意”的創傷?對海德格爾來說,棲居只是暫居。他精心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事,其墓碑上方那顆星星最能表明其心跡。事實上,海德格爾到死都沒搞清楚存在是怎么回事。
別樣的詩意在中國,這種“詩意”洋溢于天地萬物間,無須他者介入。
九
對準問題,看看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怎么說:“你從虛空中創造了近乎虛空的、未具形質的物質,又用這物質創造了世界。”再看看漢代儒者在《易緯·乾鑿度》中怎么說:“夫有形者生于無形,則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 一者創造,一者生,是否已看得分明?這未具形質的物質或氣,前者是造出來的,而后者,在太易與太初之間,即“未見氣”與“氣之始”之間沒有他者介入,實為自生。中西思想之歧異,如果忽略了問題之有無,不管怎么看也看不出來。
問題,是人之思,西方思想傳統因此而打上人的烙印。與之相反,中國思想傳統了無人的痕跡。
什么是自然?只有在中國思想傳統中領悟。
十
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一個“損”字,就是要把人之思清除干凈。惟獨如此,才能還道之本然。對道之本然,莊子領會至深:“南海之帝為脩,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脩與忽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脩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道無為而人有意,渾沌的死因就在于人之思。
對道,這一存在的根本,若存有一絲一毫的人意,便無法領受。中國思想的源頭是沒有人的因素的。這是說,對存在為何,人必須保持無所作為。
不以人之思干涉存在,中國思想做到了這點。
西方人不懂自然為何。在其思想傳統里,上帝就是自然。而這個“自然”,卻是人之思的產物。
沒有問題,被造意識就不會產生。沒有問題,純粹之思就是存在本身。
十一
西方人的被造意識,除了從無到有的被造,還有這“有”的被安排。宇宙秩序何以如此井然?如果不是上帝安排了一切,將從何解釋?上帝“用尺度、數字、衡量處置萬物”,《圣經》如是說。在西方人看來,上帝是數學家、物理學家等,萬有之精妙都是由他創設的。
中國人也贊嘆宇宙之神奇。但神則神矣,卻非有意為之。《易經》說:“陰陽不測之謂神。”對此,韓康伯在《系辭注》中說:“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嘗試論之曰:原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于太虛,欻然而自造矣。”無“使之然”者,即無創設者。中國人之思只用在領悟上,人的籌劃是沒有的。
人一旦被問題逮住而不能脫身,西方思想就是一條出路。
沒有問題,中國人無需那條路。
十二
在西方思想中,找不到“閑”的說法。而“閑”卻是中國思想的底色。
請看道士說“閑”:“一個閑人天地間,大笑一聲天地闊”(白玉蟾)、“乾坤許大無名姓,疏散人間一丈夫”(鐘離權)、“三峰千載客,四海一閑人”(陳摶)。道家窺破天機,無為為修行的極致,沒有人的一點事兒,故而能閑。
儒者怎么說呢?儒家入世,與道家相較,似乎不夠格說閑。然而推到最后,一樣能閑。這點,孔夫子便是榜樣。《論語》載,夫子讓四弟子各言其志,當曾點答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即刻大加贊賞:“吾與點也!”在此,只需指出孔子所贊賞者沒有超出這個世界就夠了。若這世界有問題,怎可如此悠游?
西方人被問題擊中,緊迫成為精神常態。聽聽帕斯卡爾在《思想錄》中怎么說:“正象我不知道我從何而來,我同樣也不知道我往何處去;我僅僅知道在離開這個世界時,我就要永遠地或則是歸于烏有,或則是落到一位憤怒的上帝的手里……”其實,落到了問題的手里,這使他活著如同接受鞭打。其樂也融融,那來那閑工夫!再聽聽波納文圖拉在《獨白》中怎么說:“靈魂啊,通過凈化你那靜觀的雙眼,你認識到了那神圣救贖的恩典,你的新郎已用它將你從原罪中解救出來。”原罪的一頭系著問題,另一頭則系著此生。此生是拿來贖罪的,試問如何敢閑?
一個“閑”字,說來簡單,其中卻有問題需要掂量。
十三
西方人的緊迫當然不是兒戲。但如果這世界沒問題,則視同兒戲又有何不可?
海德格爾稱人為“終有一死者”,是其所在思想傳統的回音。尼采不是討厭天主教神父老是提醒人你將要死嗎?然而這“提醒”,為問題所必需。
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有點莫名其妙,他們好象沒有死亡問題,或者聲言不怕死。證據還挺大,孔子不是說過“未知生,焉知死”嗎?有結論稱:中國人回避死亡問題。這結論如果由西方人作出,當然不奇怪;如果由國人作出,則入其彀中了,即“鉆入悶罐”。
正如中國人沒有回避終極問題一樣,也沒有回避死亡問題。如果問題在,則有所謂“回避”,沒有問題,何來回避?死亡問題就包含在終極問題里頭。若終極問題可以解決,死亡問題便迎刃而解。儒家從來沒有試圖解決死亡問題,它講順化,即大化流行,順而應之。孔子把人從對死的關注導向關切生,是讓生來消解死。“生生之謂易”,這與《易經》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皇帝陰符經》說:“天生天殺,道之理也”。道不可改變,死的事實豈可改變?中國人達觀,原因在這里。
把死當作問題來解決的是西方人。人豈能解決死亡問題?“解決者”為上帝。“讓我死,為了不死,為了瞻仰你的圣容”,奧古斯丁這么說。這條死亡的暗道,由問題砌牢,人是永遠都走不出來的。
王夫之論死,以為“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反觀西方,以死為患。西方人為什么惶惶然于死?為患者何?問題!何來問題?故張子說:“老不安死……賊生之道也”。
十四
人不能免除死亡,讓西方人手足無措。宇宙必將毀滅,更使他們凄凄惶惶。此種情狀,只有帶著問題去思,才能作至深體驗。人之死生、宇宙之終始,皆非人所決定,黑暗的深淵!對西方思想傳統而言,聽不到人向上帝呼告,沒有比這更糟糕的事情了; 如果聽到了,就是最美的語言。
這世界的從無到有,源自上帝的大能;這有的精巧,源自上帝的大智。
抹掉上帝,除非抹掉人之思。
亞里士多徳認為:神是只思想思想的神圣思想。人能思,但不是思想本身,神才是。思,作為路標,指向上帝。希臘人的神學思想是理性的,即人繞著己思起舞,企圖通達神思。為什么在西方思想傳統中,希臘哲學作為婢女的地位不可改變?因為它從人之思到神思,神是被推想出來的。希伯來人的神學思想就很不一樣了。“起初,神創造天地”,《圣經》開篇第一句,神憑空而來。這“憑空”,也就是啟示。啟示是一種咬定,神從來就在,在人之思之前。基督教被斥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謊言!但“謊言”何以有這么大的魅力?當然不僅僅是謊言。有問題在,謊言就是真實的。希伯來人給世界貢獻了一神,他們為此而驕傲。神之魅出自問題,即出自人之思。但這神的臨場卻從打殺人之思開始。這點,希臘人的確望塵莫及。
希臘或希伯來思想固然有所不同,但均出自人之思。西方思想這兩個源頭的最后歸向,決定了人類命運的悲慘。
十五
終極問題在中國思想里消失,使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絕然有別于西方。以儒家論,其典籍浩繁,找不到關于生命悲慘的說法。倘若人擔憂死、毀滅等等,怎能免于悲慘?其悲在于:問題非人所能解決。儒家講天命,講的就是聽天由命。這是說:對于人存在、宇宙存在,包括其死、其毀滅,人必須接受。接受,則人無所憂。儒者更有“不必言命”的說法,這就把“無憂”推到極致。道家、道教讓西方人感覺親近,特別在有關死的問題上。葛洪在《抱樸子》中說:“況彭祖輩,何肯死哉!”不肯死,與西方人追求靈魂不朽是一致的。但如何求不死,又大不一樣。還是葛洪,他說:“我命在我不在天,成金還丹億萬年。”道士不服天命,要自己搞定生死,叫人震撼!這可是西方人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基督教的修士不管怎么修也成不了上帝。因問題作梗,西方人只好聽從上帝。道士修煉完全自主,要理解這點,須從根子上講。如果中國的思想傳統有一丁點兒問題的陰影,即中國人之思自外于存在,怎么可能自主?道就在存在之內,道人是與道冥一之人。佛教是外來思想,曾受到儒家的阻擊,還是扎下根來。中國思想為什么能夠包容佛教?如果佛教沒有“閑”的底色,即不受困于問題,就不可能。佛教說空,人之思被掃得干干凈凈。
十六
科學改變世界。事實上,它什么也改變不了。
要判明宗教與科學孰是孰非,只須抓住問題來講。科學能夠解決終極問題嗎?不能。對終極問題這個“人之思”,科學盡顯其怯弱。科學家不是想尋找宇宙的總方程式嗎?神學家只需一問:這方程式從何而來?他便蔫了。曾有報道稱,科學家將在實驗室里造出物質。然而這實驗室是什么東西?有這“物質”,有這“總方程式”,人就可以玩轉一切,此乃科學之迷狂!
西方思想,由于它的起點在人之思,而這“人之思”的要害為終極問題,其骨子里有一種改變的企圖。對存在這一事實,西方人總是心懷不滿。神學熱衷于講死、講毀滅,目的在于拯救。問題驅動下的拯救,其實質是要改變。因上帝,或死、或毀滅變得可以接受。起初,西方人一點自主都沒有,上帝藉問題掌控一切。在問題仍在的情況下,上帝被毀,人狂妄起來。當今科學甚囂塵上,最聒耳的是,就算宇宙毀滅,人也能處理。只要科技發達,人便有重新安排宇宙秩序的能力。當然,此“安排”更合人意。在“改變”這點上,科學與宗教是一致的,就象一枚硬幣翻轉過來還是那枚硬幣。
說科學什么也改變不了,也許叫人失望。失望之余不妨想想那個問題。
存在是個事實。人之思可以請出上帝,從被請出來的“上帝”轉而打殺人之思的角度看,上帝指涉的恰是這“事實”的不可改變。
十七
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何為天命?天命在中國的思想傳統中意味著什么?天命就是事實,指的是人對存在這個事實無可如何。中國人從來沒有試圖改變人所在的世界,因為這世界與人之思沒有任何關涉。在中國思想中,世界保持原樣,人做不得任何手腳。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第一畏便是畏天命。“畏”,就得尊重。
西方思想破壞原樣的世界。破壞由問題引致。人解決不了終極問題,上帝介入世界。“介入”,以中國思想觀照,是一種侵犯。人不知自然為何,乃侵犯的惡果。
由問題切入,西方人的思想經歷大起大落。篤信上帝的年代,人之思被遏止,人服帖如羔羊。有問題轟頂,誰敢挑戰上帝?科學之所以激揚澎湃,說起來叫人沮喪。什么時候科學自以為是,當下即可確認必定是置問題于不顧了。正是對存在這一事實的追問,啟動了科學,最終又把它逼上絕路。科學依仗人之思,這“人之思”始終只能對著“事實”,而無法創造“事實”。科學發現了許多自然的奧秘,使人對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預期,了解會進一步深入。但無論如何,發現與創造畢竟是兩碼事,這決定了重提上帝是西方思想的唯一出路。
上帝自有永有,此乃西方人的“自然”。此自然當然不是中國人的自然。
西方思想企圖改變世界。
中國思想揭示世界本身。
2006年3月5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