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大學》一書言簡意賅,卻被認為是儒家學派“初學入德之門”。究竟這種評價有無道理?本文旨在從文本出發尋求正確定位其理論功能的依據。本文的觀點是“格物”“知止”是理解《大學》理論價值的關鍵概念,《大學》的邏輯結構與實質內容正是據此得以建構,并具備了啟蒙的理論功能。
關鍵詞: 格物 知止 致知
《大學》在儒家學派思想傳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一點在《大學》開篇處“子程子曰”中本已明確指出:“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但是由于一直以來學界圍繞《大學》思想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存在爭論,所以仍然有必要找到能夠印證這一觀點的有力證據。
從“初學入德”這一評價來看,《大學》篇應當著重于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及其之間的邏輯關系的表述;從“為學次第”的評價來看,《大學》篇應當具有方法論的理論價值。也就是說《大學》的主要理論貢獻在于“授人以漁”。其重點并不是要詳解思想內容,而是如同一本工具書或者說概述,使后人只要研習此篇就能夠基本掌握儒家思想的主體脈絡和進學方法。那么事實是否如此呢?我們可以從《大學》文本中尋找答案。
理解《大學》的關鍵在其首篇。第一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實際上揭示出儒家學派的進學的重要方法或者說思路:從個體的道德體認和實踐開始,通過道德觀念的普及,實現大眾道德實踐的至善目標。盡管對于此句向來有許多種解釋,但是,本文認為“ 萬變不離其中”,從儒家學派治學目的來看, “明明德”是道德理論與實踐教育的過程,“親民”是道德觀念與民眾生活實踐相結合的過程,而“止于至善”則是不斷推進前面兩個過程以達到天下大治的政治目標的過程。“明明德”與“親民”都是可以具體操作的,而“止于至善”卻是一個漸進和接近的過程,難以準確衡量。因此理解《大學》的明線是 “明明德”與“親民”,也就是下文中所說的“明明德于天下”。
《大學》全篇并未詳解何謂“明德”,但是卻指出了“明德”是“自明”的。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德”,也都具有“自明”此“德”的潛質,但是這一潛質并非人人都能駕馭自如,大多數人需要被激發、被引導。因此“明明德于天下”,就是那些能夠駕馭其潛質“自明”其“德”的君子或圣人,啟發、引導其他人“自明”進而“自新”,并以“至善”為目標,不斷“自明”“自新”,實現類似于螺旋式上升的自我發展的過程。這就是“大學之道”,是《大學》成書的旨趣所在。因此《大學》文本主要是就如何能夠達成這一旨趣展開說明的。
“知止 ……能得。”一句指出了人們需要被啟發引導的關鍵或者說突破口。前面我們談到“止于至善”是一個漸進接近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往往可能因為各種因素的干擾而動搖、放棄“自明”“自新”,以致出現倒退。為此必須保持謹慎、不斷檢查、防范和匡正,以確保每一階段和環節始終處于上升發展的狀態,只有這樣才能達到“至善”的目標。也正因為如此,“知止”本身應當不僅包涵著知道自己人生理想和目標是“止于至善”這一含義,而且包涵著知道與這一目標相悖離的思想和行為并禁止其發生發展這一層含義。過去的研究往往只從單一的積極的一面去解釋,卻很少從其對立面去考察,本文認為這是不符合《大學》作者的原意,也不符合人類認識規律的。我們知道教育孩子認識事物,必須告訴他“什么是什么”,同時也必須告訴他“什么不是什么”,通過比較區別才能在全面意義上建立起對事物的認知。仔細閱讀《大學》文本,我們也不難從中找到證明:
如釋“止于至善”時,一方面指出“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另一方面又在解釋《詩經》中的“如琢如磨”時,強調“自修”的環節。朱熹批注“自修”說:“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省察克治”就是對與至善相悖離的思想與行為的“知”和“止”,說明“知止”當包涵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用功。
再如在釋“誠其意”時,它沒有正面解釋而是直接用“毋自欺也”從反向進行說明。朱熹解釋說“毋者,禁止之辭。自欺去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說明即使被告知應當“止于至善”,人們也不一定能夠做到,所以還是先從禁止錯誤的“慎獨”開始。
在釋“正心修身”時,也使用了這一手法:“身有所忿懥, 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朱熹解釋說,有所“ 忿懥”、“ 恐懼”、“好樂”、“憂患”是人之常情,但同時也是使心不得其正的原因,因此君子必須常存檢點之心“察乎此,而敬直之”。
釋“修身齊家”時,文本首先指出由于人性所決定,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總是存在偏差:“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因此修身的關鍵在于全面認識事物的兩面性,糾正這些悖離“至善”目標的偏差,做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否則“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朱熹批注)。
在解釋“絜矩之道”時,先從正面談上行下效以建立“當為”之規范,再從反面設立“不可為”的底線:“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這樣就構建起一個行為框架,從而使人們知道何為當為,何為不可為,從而既有目標在前又有鞭策在后,自然就能夠不斷進步以達成“至善”。
在《大學》右傳十章的文本中基本上都是如此之類的表述,足以證明“知止”才是《大學》真正要探討的核心問題和本質所在。
接下來的要解決的問題是何以“知止”。基于前面的分析 我們重新返回到《大學》首章,可以過濾出從“知止 …… ”一句開始,到“ …… 致知在格物。”這一段的關鍵詞句如下:“知止 …… 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欲……先……致知在格物。”既然被“……”掉就是說它們不是該部分真正所要闡明的重點,真正的重點是這些關鍵詞本身所傳達的儒家學派進學方法的信息:“格物”→“知止”→“得”。 這個過程也就是儒家所謂“致知”。
為什么是這樣的一個條理呢?我們看第一句“知止……能得”。 我們已知“知止”是指“ 知”“至善”之所“止” ,那么“能得”則是指對如何“止于至善”有所心得。而且接下來的一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更清楚地說明了“得”就是“知(事物之本末、終始)所先后”而“近道”的狀態。怎樣“致”這一“知”呢?答案就是“格物”。
在儒家理論里,所謂“物”就是指人類社會關系中的各種事物,而且這些事物的存在意義必須通過其相互之間的關系得以體現。所謂“格”,盡管歷來學者莫衷一是,但是從人類認知發展規律的角度來說,無論是自然科學知識或是人文科學知識的增長都必須從對事物的對比、分類開始,在把握事物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基礎之上形成基本概念,并以此作為思維發展的邏輯起點。因此本文認為,“格”就是“研究和界定”。研究和界定社會關系中的各種事物及其他們之間的關系就是“格物”。它與“方物”一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國語 ?楚語下》:“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韋昭注:“方,別也。物,名也。”“方物”就是分辨事物的名實或名分。“格物”與其意很接近。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主張“格物”即孔子所說的“正名” ① 。孔子在《論語 ? 子路》中指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在這里“正名”是言順、事成、禮樂興、刑罰中、民措手足的條件和基礎,這一點與《大學》將“格物”作為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起點和途徑的確具有相同的邏輯思路, ② 因此也頗有道理。 通過“格物”了解事物的內涵和外延(本末),明確事物的各種內在和外在的規定性(終始),就如同給事物設置了一個標準的“ □”,把事物框在其中,繼而在此基礎上規范和限定事物之間社會關系的處理原則(先后)。沒有限定,則事物不可知;沒有界線,則事物無法區分。所以“致知在格物”。不僅如此, 在儒家學派看來,任何事物之間關系的處理均有至善之所,這反過來又使得處于關系中的事物本身也具有了更高的道德價值訴 求 。 如果把框于 “ □”中的事物看作是該類事物至善的標準,那么 “ □”所架構起的四個方向上的底線就代表著人類“止于至善”的道德實踐最基本的要求 。 結合對“知止”的分析來看,這些要求同時意味著人們在進德修身過程中應當防范和避免有違于這一底線的思想和行為。
由此可見,“格物”所要解決的是“什么是什么”的問題,“知止”所要解決的是“怎樣才是什么”的問題。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辯證思維的發展是令人矚目的。很早我們的先人們就發現了事物有條件地向其相反方向轉化的規律。事物的現有性質和狀態并不是永遠不變的,僅僅固守“什么是什么”,思想必然會陷入僵化,無法準確把握事物的發展方向。因此必須“知止”以了解事物是其自身的條件,并據此判斷是否應當保持或者應當突破現有狀態。而這個當“止”之所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度”。不論事物是在哪一個維度上保持其自身的存在性,對于該事物的準確界定都具有重要影響。“格物”的目的就 是研究和界定事物的內涵、外延,使人處于事物關系之中而“知所當止之處”。簡言之,“格物”是“知止”的學術方法,“知止”是“格物”的學術目的。
當然“格物”“知止”的最終目的是“能得”,而“得”就是后文所說的“知至”。在《大學》中有“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后知至”兩句。這個“致”與“至”的區別當然不是筆誤,“致”講的是一個過程,“至”則是“致”的目標。同理可證,不存在朱熹所認為的“蓋釋格物致知之義”的專門一章的“亡矣”的問題。因為,“致知在格物”不過只是對“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的再強調,并沒有新的內容。正是因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所以才要“格物”以“知”其“本末”、“終始”,“知所先后”,“致”物之所“止”之“知”以至于“得”而“近道”。理順了這一思路才能真正理解和落實“大學之道”。
按照朱熹編訂的《大學》章節來看,首篇之后還有十章,這十章內容基本上是通過同一種語法表述出來的,這就是“所謂……此謂……”。僅從這一點來說,就可以證明 《大學》之所以成為儒家“初學入德之門”的關鍵就在于它提出并運用了“格物”這一方法界定了儒學理論的基本概念,從而為儒學發展奠定了本體論與方法論的基礎。雖然其言簡意賅的特點,給后世學者留下了廣闊的發揮余地,但是由于概念的主體框架已經明確,因此即使僅“由是而學”,也“庶乎其不差矣。”
在《大學》開篇處,朱熹曾對“大學”進行了批注:“大學者,大人之學也。”這一批注事實上點出了歷代儒學的理論基點。人的肉體是客觀存在的,不可能有超出生理發展之外的大小變化,然而人的精神世界卻有著“致廣大而盡精微”(《中庸》)的潛質。“大人之學”關鍵要使人的精神世界得以發展,從而使宇宙中渺小之人體能憑借其博大精深之智慧彰顯出其 “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道德價值。所不足的是人的優秀潛質容易被塵世的各種污垢所蒙蔽,因此才需要得道的君子或圣人進行啟發和引導,要“明明德”、要“新民”。那么普通人自己怎樣才能擁有博大精深的智慧,又怎樣將這種大智慧轉化為頂天立地的大德性呢?“尊德性而道問學” (《中庸》),簡言之就是“知止”、“格物”。
孔子曾有一段對自己一生求學經歷的總結性描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按照本文整理的《大學》所提倡的為學路徑來分析,“立”就是“知”“止于至善”,“不惑”就是“格物”,“知天命”就是“致知”,“耳順”就是“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就是“知”所當禁止。由此旁證本文的論點:“格物”“知止”奠定了《大學》作為儒家理論傳承啟蒙之作的理論地位。
注釋及參考文獻:
①楊柳橋:《 <大學>的“格物”即是<論語>的“正名”》,《哲學研究》1978年12期。
②梁濤:《 <大學>新解 —— 兼論〈大學〉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中國哲學第 23輯》, 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01 年 10 月 。
《大學集注》(朱熹注)
《中庸集注》(朱熹注)
《論語集注》(朱熹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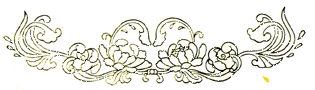
![]() guoxue@guoxue.com
guoxue@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