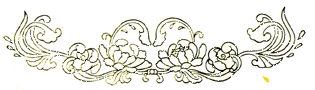摘要在儒學義理、考據、訓詁和經濟四個學術面向中,曾國藩承繼程朱之道統,把義理推到儒學學術的首位,成為理學在清代的繼承人。他主張氣生成論,認為稟氣之不同造成了圣人之性與常人之性的差別;面對世俗生活中日益微略的常人之性,圣人應擔當起教化、“復性”的天職;圣人教化的途徑有二:一是格物,二是誠意。在漢宋不同學術理路的學術爭執中,曾國藩以“務實”為契入點,不僅調和了漢宋之爭,而且以經世致用之洋務思想實現了對漢宋學術的超拔,進而使得儒學原有的狹小、禁忌繁多的范閾得以豐富和發展。
關鍵詞:曾國藩; 理學;格物; 誠意; 經世致用
O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Zeng Guofan
Abstract Zeng Guofan claimed that Doctrine of Principle is most important in all Confucian theories. He thought that everything is made up of qi (material force), whose difference leads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e of sage and ordinary people. Facing the weakness of ordinary people, sages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eaching the ordinary people to restore their nature by handling things and sincerity. The cause that Zeng Guofan paid attention to both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Han school of Confucianism is that he held a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spirit, whose purpose is to mediate the above two schools and the more important is to surpass the levels of the two schools by advocating ‘put knowledge to practical use to society’ and ‘foreign affairs’.
Keywords: Zeng Guofan; Doctrines of Principles; handling things; sincerity; put knowledge to practical use to society
作為士大夫和一代儒者,曾國藩按部就班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在他的學問路途中,既有“不為圣賢,即為禽獸”的勵志條目,更有“躬自入局、荷道以躬”,意欲承擔晚清“中興”大業的救世激情。就前者看,曾國藩對自己約束非常嚴厲,他不跟惡社會跑,立個標準,漸次從自己做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種氣派。這些可從其與朋友往來的書札中考見。就后者講,曾國藩處于清政府陷入深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機之時,時局幾至于不可收拾之地步,他以對傳統倫理秩序眷戀不舍又翼借西學以自強的積極主張,對晚清時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貢獻。中國古人歷來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作為人生之理想,曾國藩即因“道德、文章、事功”都比較完滿而被譽為“末世完人”。曾國藩不僅給后人帶來了人格上的魅力,也給儒家文化帶來了新的榜樣寄托。正因為如此,時下文化思想界興起一股關于曾國藩的研究熱潮。但稍加留意就會發現,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功利層面,其濃烈的用世心理和狂熱的功利性情溢表于外。在此,筆者擬通過四個方面來就支撐這位“末世完人”精神世界的哲學思想做些探討。對其哲學思想探討的現實目的有二:一是填補時下曾國藩研究中較為虛乏的一面,以增加整個曾國藩研究的哲學厚重感;二是沖淡時下曾國藩研究中的用世心理,減少相關研究中的功利因素。當然,這兩個方面都是以曾國藩哲學思想的“本來面目”為依據的。
一
曾國藩曾被人推許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復興儒學的圣哲。但,在儒學諸多的學術面向中,曾國藩所畢生研究和服鷹的只是理學。自31歲始向理學大師唐鑒、倭仁學習理學后,他便開始以“道學先生”自居。歷時性地看,“義理”、“考據”、“經濟”、“辭章”都是儒學的重要學術面向,但曾國藩認為,雖四者均是儒學題中之意而不可缺一,但對于如此龐富的內容,人的一生不可能“遍觀而盡取之”,而只能“先其所急”,“擇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的“義理之學”。(曾國藩,2003年,文集,第205頁)“義理之學”被曾國藩推上了儒學學術的首位,成為統攝其他學術面向的核心。當然,曾國藩所謂的義理既不是心學之義理,亦不是實學之義理,而是程朱所闡發的理學之義理。他說:“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同上)
曾國藩不僅對于義理之學堅信不疑,而且對于理學人物也不乏褒揚之辭,甚至當這些人受到攻訐時,不惜全力為之辯護。他說:“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后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群言以自隘乎?”(同上,第58頁)曾國藩認為以程朱為代表的上述宋代諸子“上接孔孟之傳”,承繼著原始儒學之肯綮,其義理合于儒學原典之原則。因此,即便程朱等大師的言論有所欠缺或不當,今世學者理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為其修補和完善,而絕不可采取“屏棄群言以自隘”因其小過而完全否定之的偏狹態度。照著曾國藩的邏輯,“屏棄”程朱理學即是“屏棄”孔孟所開創的原始儒學。可見,曾國藩不僅崇奉儒學義理的學術面向,而且以理學諸大師為原始儒學之正傳和道統。前者是邏輯的,就“道”而言說;后者則是歷史的,就“統”而討論,因此,就儒學之“道統說”來論,曾國藩屬于程朱理學的信守者這一點已無可置疑了。
就其整體思想來看,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言行舉止無不以宋儒程朱之學為根本,不過,程朱理學雖為其思想的重心,但曾國藩對于程朱之學并未盲目的崇拜,事實上,他對于宋明儒學其他支派之思想亦有許多的汲取。眾所周知,作為一個時代思潮,宋明儒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在這三個學術派別當中,曾國藩固然恪守程朱理學為學宗,但他在政治實踐和軍事斗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于隘”、或“病于瑣”、或“偏于靜”的局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于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訟,他認為,雖然程朱理學得儒學之正傳,但陸王心學亦江河不廢之流,并不是毫無意義之廢話;因此,對于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共同推進儒學的發展。進而,曾國藩還轉而訴求于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這也正是他之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曾國藩,2003年,書札,第691頁)的緣由。正因為如此,曾國藩在和太平軍作戰的最緊張、最激烈的時刻,親自校閱并組織刊刻了《船山遺書》。基于此,對曾國藩一生治學始終堅持“居敬而不偏于靜,格物而不病于瑣,力行而不迫于隘”(曾國藩,2003年,文集,第20頁)的原則便不難理解了。
以程朱理學為基點和立場訴求于張載和王夫之的氣學,只是曾國藩在宋明儒學框架內對氣學資源的一種共享;事實上,曾國藩雖承繼了程朱理學的傳緒,但他的思想已超出了理學乃至宋明儒學的樊籬,表現出明顯的調和漢宋、博采眾長的傾向。曾國藩雖把理學作為儒學學術的首位,但他的思想并未局限在理學的范閾之內,他對儒學的其他三個學術面向都力持無所偏倚的態度。面對漢宋之爭,曾國藩曾言自己雖宗宋儒,但亦不廢漢學。他明確表示自己于“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曾國藩,2003年,書札,第692頁),并提出以“經濟之學”、“治世之術”即他所言的“禮治”來“通漢宋兩家之結”。(曾國藩,1990年,書信,第1576頁)當然,曾國藩“兼綜漢、宋”的一貫之道仍是“禮”,即程朱理學,故“其論學兼綜漢、宋,以謂先王治世之道,經緯萬端,一貫之以禮”。(清史稿·列傳一九二)因此,曾國藩曾極力推許清初的經學家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于秦的《五禮通孝》可以通漢宋兩家之結,漸息漢宋兩派之爭。此外,曾國藩在文章方面非常崇拜清文學家姚鼐,他甚至認為自己就承繼了姚鼐的文章統緒。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針對乾嘉漢宋之爭,姚鼐試圖引入漢學家求實、考證的實證學風以彌補理學的空疏和腐弱,曾提出義理、考據、文章三事合一以調和漢宋。姚鼐的這一思想頗得曾國藩的贊同,遂曾國藩認為“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曾國藩,2001年,第26頁)。
二
如前所述,曾國藩在程朱理學的基點上汲取了張載和王夫之的氣學思想,因此,在生成論上,曾國藩比程朱等理學家走得更遠。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所以,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圣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并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圣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故圣人智且恒,而常人卻愚且微。他說:“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同上,第29頁)通過氣生成論的闡述,曾國藩不僅解釋了天地萬物的“同體性”,而且也解釋了天地萬物的差別性。
在曾國藩,論證天地萬物的“同體性”與差別性有著相同的意圖,即通過圣人后天的教化,以恢復常人微略的先天之性。曾國藩認為,因稟氣之不同,圣人在后天生活中不會受世俗的牽累,他們能夠充分地踐履仁義,此即所謂的圣人盡性。而與圣人不同,常人卻極易拘泥于后天之瑣事,本有的氣質常常遭到世俗的污染和遮蔽,以致于先天之性越來越微略。因此,他們在世俗生活中,常常會出現“喜歡不當”和“厭惡不當”的情況。“喜歡不當”是“賊之仁”,“厭惡不當”則是“賊之義”。“賊之仁”與“賊之義”均不合儒學的仁義之道,若任此發展則有背離“天下歸仁”這一儒學宗旨的危險。曾國藩說:“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同上)面對常人在后天世俗生活中的墜落以及所導致的危險,圣人理應責無旁貸地擔當起對常人的教化責任;而教化的目的在于恢復常人先天的本性,“學者何?復性而已矣。”(同上)圣人教化常人以復其性便是天下學問(儒學)得以產生的原因,換句話說,儒學(理學)的社會職能便是對常人進行教化以復其本性。可見,圣人與常人的差別性賦予了圣人以教化的天職,而“同體性”則賦予了常人以“復性”的可能性。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曾國藩教化思想的理論基礎。
此外,無論在生成論意義上,還是在有關教化的思想中,曾國藩對于辯證法亦深有洞見。他說:“一則生兩,兩則還于一。一奇一偶,互為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曾國藩,2003年,文集,第16頁)又說:“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有所謂道者。”(曾國藩,2001年,第29頁)后來更概括說:“國藩亦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成兩片。”(曾國藩,光緒本,第5頁)這就是說,每個事物都是一個統一體,其中必有對立的兩個方面。這個思想今天被作為了辯證法的一個基本原則。據曾國藩說,“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成兩片”這個原則對于他已經不是一種理論上的知識,而是一種經驗,一種體會,甚至已成為一種直覺。這充分說明曾國藩對這個基本原則有了比理論知識更進一步的認識。當然,論其淵源,這些辯證思想顯然是從張載《正蒙》的辯證法理路推演而來。張載說:“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有象斯有對”(《正蒙·太和篇》),“地所以兩,分則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正蒙·參兩篇》)由此而看,此辯證法思想亦是曾國藩對程朱理學的一種豐富。
三
圣人對常人的教化在曾國藩這兒是神圣的天職,但圣人如何教化常人呢?或者說,圣人施教的內容是什么呢?曾國藩認為,教化的內容是引導常人認識萬物之理,因此,理學的宗旨就在于即物求道而已。他說,天下萬物莫不各有其各自的道理,而天下的學問(儒學)就在于認識這萬物之理,自古以來從堯、舜、禹、湯到文、武、周公和孔子的學問莫不如此。不過,天下萬物是無窮的,天下之理亦是無盡的,所以,要求得萬物之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可行的辦法是首先認識并求得其最根本者。這最根本者,在曾國藩看來,莫過于仁義之道,因為仁義之道是天下萬物之理的基礎和核心;如果仁義之道不明,天下萬物之理亦不會求得;即使求得,也沒有實際意義。他說:“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曾國藩,2001年,第29頁)
那么,如何識得仁義之道并進而擴展以掌握萬物之理呢?曾國藩說:“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同上)他甚至認為,“《大學》之綱領,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共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同上,第31頁)格物誠意就是求得仁義之道的手段和路徑,這是《大學》之綱領和理論旨趣。那么,什么是格物誠意呢?如何去格物誠意呢?曾國藩認為,所謂格物,就是指即物求道,即通過具體的物事來透顯其中蘊含的道理。所謂物,在此指如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等關于本末的東西;所謂格,在此指去認識上述物中所蘊含的道理的行為。比如,事親定省是物,而尋求之所以事親定省的道理,就是格物。曾國藩認為,格物時要從事物的差別處入手,“故凡格物之事所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同上,第29頁)他說,世上萬物是千差萬別的,親親與愛民不同,仁民與愛物有別,親疏有差,賢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區分而去妄加施舍,就會過于仁,這樣會導致墨家偏執的兼愛之蔽;如果不加以區分而統統厭惡,就會過于義,則會導致楊朱極端“貴生”“重己”之蔽。不論是墨翟,還是楊朱,其學說雖為兩個極端,但它們在生于心,害于政,達到極點足可亂天下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由此可見,在差別處入手以尋求物事之道確是理學甚至儒學一個方便法門。
所謂誠意,曾國藩認為就是指以仁義為標準來區分好惡進而努力去踐履。誠意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不欺騙,二是身體力行。他說:“誠意,力行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字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同上,第31頁)很明顯,在曾國藩,格物的意義在致知,而誠意的重心則在力行;他不僅重致知,而尤重力行。因此,他反對陽明心學的知行合一之說。王陽明認為心外無理,心即理,求理無須做向外求理的心外工夫,只須做心上工夫即可,因為“一念發動處即是行了”(《傳習錄》下)。曾國藩認為這種“即知即行”的良知說忽視了天地萬物的差別,而且也不重做分辨事物的工夫,屬于一種“攝行入知”的學術傾向,而實際上這種傾向是一種受佛教影響的“禪障”。他說:“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曾國藩,2001年,第30頁)既然陽明心學有導致浮屠的危險,因此其泯滅萬物差別的思想是萬萬不可輕信的。儒與佛的紛爭與劃界是自佛教傳入中國后長期縈繞儒者心頭的一塊心病,在此可見,曾國藩作為一代大儒也不例外。
如果從差別處這一方便法門入手尋得了某一物事所蘊含的道理,是否就意味著格物、誠意的完成進而圣人施教天職的實現呢?曾國藩不贊成對圣人施教天職的這種簡單化處理,他認為,因為物事是無窮無盡的,物之理遂亦是無窮無盡的,因此即物求道之格物與身體力行之誠意就不應有停止的時候;如若停止下來,則仁就會有所不“成熟”,而義則亦會有所不“精煉”。這樣,問題并不在于圣人是否能夠完全把握仁義之道,而在于常人因此而在接近仁義之道的道路上停頓下來而可能產生前功盡棄的后果。曾國藩認為,自古以來,認識就有精有粗,行動就有實與不實,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間的區別。事實上,圣人之所以為圣人,就在于永不停息地格物誠意;圣人是不可能停頓下來的,他們會孜孜不倦地引導著常人進行著不懈的追求的。這種觀點,與其說是對負有施教天職的圣人施加了壓力,倒不如說是對千千萬萬的常人的格物誠意增加了動力。很明顯,在儒學內部心學與理學關于本體與工夫的爭執中,曾國藩不僅選擇了理學的立場,而且凸顯了工夫(誠意、力行)的意義,因為在曾國藩看來,無論是格物,還是誠意,其中所蘊含的行的成分比知的成分更重。更為重要的是,曾國藩通過從理論上設定和宣揚工夫的無止境性,進一步深化了程朱的理學思想。
事實上,照曾國藩的理解,圣人的施教天職有兩個方面的展開,一是如前所述的通過格物誠意去尋求仁義之道,二則是通過禮樂的約束以恪守仁義之道;如果說前者是內在的心意層面的教化的話,那么后者則是外在的社會道德規范層面的教化。毫無疑問,曾國藩的這種理路汲取了船山之學的精神,所謂船山之學的精神就是“內仁外禮”。“內仁”就是“幽以究民物之同原”,“外禮”就是“顯以綱維萬事”。(曾國藩,2003年,文集,第72頁)仁是體,禮是用,“內仁外禮”就是“明體達用”。但是“內仁”是“幽”,看不見;“外禮”是“顯”,透露在外邊。承繼著這樣的理路,曾國藩進一步認為:“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荀卿、張載兢兢以禮為務,可謂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同上,第129-130頁)曾國藩又更加簡單明了地說:“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同上,第61頁)所以李鴻章說曾國藩的“學問宗旨以禮為歸”。李鴻章還認為,在曾國藩,從天地萬物以至一家之柴米油鹽,都是他的禮學的對象,都是有禮可循的。正因為如此,李鴻章才把曾國藩的學問稱為“禮學”。
嚴格地講,李鴻章的把曾國藩的學問概括為“禮學”并不全面,因為這種概括極容易產生曾國藩只重視“外禮”而忽視“內仁”的誤解。實際上,曾國藩的“禮學”仍然強調以“內仁”為本,“外禮”為用;在曾國藩,如果說“外禮”是活水的話,“內仁”則是源頭。他崇信二程“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公法度”(《二程集·程氏外書·龜山語錄》)的理路。二程和王安石都主張行“周禮”,但王安石是從富國強兵的“利”出發,二程的出發點則是“《關雎》、《麟趾》之意”,即“至誠惻怛之心”(《二程集·程氏文集·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也就是“內仁”,而認為行《周禮》就是“外禮”。曾國藩一貫主張“不誠無物”(曾國藩,2001年,第25頁),當然也就“不誠無禮”。“《關雎》、《麟趾》之意”即“至誠惻怛之心”,概括起來就是仁,所以也就是“不仁無禮”。但是,在“內仁”與“外禮”的關系上,曾國藩并未“銷禮入仁”,取消“外禮”的實際意義,相反,曾國藩十分重視“外禮”的作用,他曾主張“舍禮無所謂道德”、“舍禮無誠”、“舍禮無仁”,否則,李鴻章就不會把曾國藩的學問稱為“禮學”了。總而言之,曾國藩認為圣人施教時應將“內仁”與“外禮”融為一體,而不是單論“內仁”或單論“外禮”。當然,常人受教時亦應“內仁”與“外禮”的修行并重,二者不可偏頗。
四
如前所述,面對漢宋之爭,曾國藩曾言自己雖宗宋儒,但亦不廢漢學,表現出調和漢宋、博采眾長的學術理路。實際上,綜觀曾國藩的整個學術,其思想并未停留于調和漢宋以漸息爭執而止步,而是向著超拔于漢宋學術大膽地向前推進。曾國藩的這種超拔可以用“務實”兩個字來概括,因為他不僅在“務實”的意義上找到了漢宋學術的契合點,而且也是在“務實”的意義上實現了對漢宋學術的超越。總的來講,無論漢學,還是宋學,在“務實”方面都有所欠缺而因此倍受攻訐;而這種欠缺放在內圣與外王的語境下,就表現為過于內傾自閉而缺乏外在事功,即內圣與外王理論模型的失諧。在堅持“內仁”與“外禮”融合為一的基礎上,曾國藩也堅持內圣外王的并重,一方面他堅守程朱義理,另一方面特別強調經世致用,力求通過外王的開拓實現對漢宋學術的超拔。當然,曾國藩的身世、經歷和其所處的時代也決定了他理解的和所致力的外王已與前代不同。
“務實”是曾國藩終生恪守的價值理念。他主張不說大話,不騖空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強調“禁大言以務實”。(曾國藩,2003年,文集,第181頁)針對當時理學家們沉溺于心性之學,“毋以詩書為迂闊”,“非圣之書,屏而不讀”的理路,曾國藩主張不能迷信經籍。他說:“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征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從事耳。”(同上,第224-225頁)務實的精神還表現在曾國藩實際的政治主張中,比如在對外關系上他就主張舍去虛儀,重視自尊自強。他提出了一個處理對外關系的重要主張:“爭彼我之虛儀者可許,其奪吾民生計者勿許。”(清史稿·列傳一九二)這個意見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內涵。從清乾隆朝開始,中國和西方各國交往的一大障礙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禮等禮儀問題。在清廷看來,這類禮儀“體制攸關”,難以讓步。曾國藩則認為,要取得別國的敬畏,全在自尊自強的實力上,而不在裝模作樣的虛儀上。這些務實之主張頗得后人的贊許,有評論曰:“國藩事功本于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同上)
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現實上來看,務實與經世致用二者之間是相通的。在曾國藩生活的時代,經世致用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漸漸復興。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就強調在“義理”、“詞章”和“考據”三種學問之外詩文還應表現“經濟天下之才”,另一位代表人物梅曾亮也認為“經世致用”有補于世甚至高于“性命之學”,他批評“考證性命之學”無事于讀書窮理,而陶醉于經生章句,了無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和經世精神。作為桐城派“中興”重要人物的曾國藩不僅受到桐城派學者的影響,也深受龔自珍和魏源等站在經世致用思潮前列的思想家的影響,所以,曾國藩治學也非常倡導理學服務于現實。據其日記所載,他在從學理學大師唐鑒時,唐鑒以理學經世思想相指點,曾國藩聽后“昭然若發蒙也”。(曾國藩,2003年,日記,第88頁)曾國藩一生雖堅守程朱理學,但他著力發揮理學中的“事功”因素,他對洋務的提倡與實踐就是其經世致用思想的具體化。
鴉片戰爭前后,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思想界涌現出一批研究世界史地和西方堅船利炮的經世著作,使傳統的經世之學注入了西學的內容。此時許多經世思想家雖堅守程朱義理,但他們重視應變求新,開始關注和學習西學。曾國藩洋務思想的核心便是學習西方的“技藝”、“術數”以自強和“衛道”,體現出一個既視程朱理學為身心性命,又注重務實經世的傳統士大夫在內憂外患、西學漸侵時的艱難選擇。曾國藩在《勸學篇示直隸弟子》一文中提出作文要端在“義理”、“考據”、“文章”、“經濟”四事。其實,將“經濟”納入文章要則并非曾國藩的創見,姚瑩就曾提出“義理”、“經濟”、“文章”和“多聞”四事為作文之要。但是,曾國藩所言的“經濟”還納入了輿圖算法、步天測海和制造機器等新內容,因此,他的“經濟”思想較姚瑩向前發展了一步。在其著名的《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折》中,曾國藩更是認為購買、仿造“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同上,奏稿,第588頁)顯然,漕運、水利等傳統意義上的經世之術在曾國藩那里已退居次要,洋務尤其是購買、仿造西方船炮成為他關注與致力的主要方向。正因為如此,曾國藩才有了創辦安慶軍械所和江南制造總局、派遣學童赴美留學等經世濟民的舉措。
需要注意的是,曾國藩的經世思想始終是在義理與經世并重、內圣與外王并舉的理論模型下展開的。或者說,曾國藩在堅守理學義理的基礎上,致力于拓展經世濟民之洋務;但他在拓展經世濟民之洋務時,并未遺棄理學之義理。他說:“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其施功之序詳與體而略于用耳。”(同上,文集,第205頁)在曾國藩看來,“義理”與“經濟”是體與用的關系,因此“經濟”之學從屬并服務于“義理”。因此,曾國藩認為,“經濟”之事尤其是學習西學不能脫離“義理”的軌道。在為晚清打開學習西學的門徑時,他不僅沒有絲毫削弱儒學義理之意,而且特別強調學習西學和辦洋務其終極目的是強化“義理”進而維護道統。故而,他反復明言治學“莫急于義理之學”、“以義理之學為先”、“以立志為本”等,(同上)惟恐儒者文人溺于“經濟”之學而迷失了“義理”航標。但是,在曾國藩,西方的器數之學確實可充實傳統儒學的“義理”,即“經濟”可強化儒學“義理”。這樣,實際上曾國藩把“經濟”嵌入了儒者之事。這種觀點在當時不僅提升了“經濟”及學習西學的重要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為儒者學習西學進而對傳統儒學補空救弊掃清了理論障礙。
曾國藩一方面宣傳“義理”和“衛道”,另一方面又宣傳“經濟”和學習西學,這種理路反映了一代大儒對儒學傳統倫理秩序眷戀不舍而希又翼借西學以自強的積極心態。重要的是,曾國藩的這些主張,尤其是其在洋務運動中對“經濟”之學和學習西學的主張,在儒者和國人看來均是陌生之事,正因為如此,其思想使得儒學原有的狹小、禁忌繁多的范疇得以豐富和發展。
參考文獻
曾國藩,2003年,曾國藩全集,中國華僑出版社。
1990年,曾國藩全集,岳麓書社。
2001年,曾國藩全書(第一卷),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光緒刊本,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