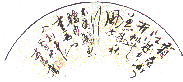唐中后期,在經(jīng)歷了“開天盛世”的繁榮之后,這個已經(jīng)擁有近兩個世紀(jì)歷史的王朝走向了衰敗。當(dāng)今史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唐王朝中后期面臨的主要問題無非是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quán)、朋黨之爭以及由此而引發(fā)的財政社會等等一系列危機。透過這些紛繁復(fù)雜的政治現(xiàn)象,我認(rèn)為唐中后期的一系列的政治問題的出現(xiàn),其最終的糾纏點正在于宦官專權(quán)。
首先不妨從這段著名的“宦官感言”談起。這是唐武宗時期太監(jiān)頭子仇士良說的一句話:
“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
這句話該從何說起呢?史書記載唐武宗時期,在以李德裕為核心的朝臣士人集團的輔佐下,武宗朝取得了唐中后期歷史上罕見的政績:在藩鎮(zhèn)問題上平定了盧龍鎮(zhèn)張絳之亂;在邊境問題上,以“分化瓦解,軍事進攻”雙管齊下的策略大大削弱了回紇的力量;在對宦官的態(tài)度上也不如他的前幾任皇帝那樣親熱,似乎有以朝臣代宦官的意思。于是以仇士良、魚弘志等為首的宦官集團企圖通過打擊李德裕的勢力來重新控制武宗,然而終是陰謀敗露。唐武宗采取明升暗降的方法剝奪了其對禁軍的控制權(quán),仇士良最終被迫辭職,就在宦官們送他返回宅第的時候,他“語重心長”地發(fā)了那一通感慨,很有一點“離職心得”的意思。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得看出皇權(quán)以及士人集團與宦官之間尖銳的矛盾斗爭和利益沖突。由于武宗對宦官的壓制,他那一朝宦官的勢力跌落到了低潮。但是我們縱觀整個唐代中后期的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宦官、皇權(quán)、士人集團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宦官專權(quán)的問題并非如此輕描淡寫似的簡單,只是彼此之間的斗爭。唐中后期的宦官問題正是其諸多政治問題的糾纏點之所在。
就說皇權(quán)與宦官的關(guān)系吧,并不像白壽彝所說是“一般來說,在皇帝勤于政事,積極有為的時候,宦官是難于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腐敗,皇帝不理政事后難于理政的時候,宦官則往往乘隙而入,染指于政,甚至左右政局。”①來得這樣的簡單。這兩者的關(guān)系其實是不斷的在變化著的。這種變化的實質(zhì)反應(yīng)或最終的歸結(jié)點便是一個在中國政治史上已經(jīng)糾纏了一千多年的問題:講小一點是皇權(quán)的爭奪以及皇權(quán)與相權(quán)之間的斗爭,講大一點是君主政治與貴族政治斗爭的又一表現(xiàn)。也就是在皇權(quán)與相權(quán)或是皇權(quán)的本身的爭奪問題上為了平衡各方面的力量皇帝不得借助于宦官或是外戚的力量來達到這一目的。
而唐代的宦官專權(quán)就是在皇權(quán)的爭奪中興起的,對比一下唐玄宗和唐太宗時期的政治局面就很容易理解了。首先我們發(fā)現(xiàn)太宗和玄宗的上臺都經(jīng)歷了一個腥風(fēng)血雨的奪宮的過程,所不同的是兩者的處理方法。
面對與兄長李建成爭奪繼承權(quán)的斗爭,李世民憑借的是團結(jié)在自己周圍的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等杰出人才組成的士人集團,并沒有依靠宦官的勢力。而且唐初的時候,對宦官不論是數(shù)量上還是權(quán)利上始終有著嚴(yán)格的限制,如他規(guī)定內(nèi)侍省不設(shè)三品官,宦官的主要職責(zé)就是侍候皇帝和管理宮廷事務(wù),不得過問政事。太宗之所以能夠這么做,一方面不得不承認(rèn)在處理君權(quán)與士人集團權(quán)利的矛盾時他是很有氣量的,它能夠積極的收羅天下英才盡為己用,也能夠大度地接受魏征的犯顏直諫;一方面也要看到這是建立在新朝伊始清明的政治風(fēng)氣的基礎(chǔ)上的;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就是太宗時期人才之盛已經(jīng)將朝廷之權(quán)分而治之(文臣中房玄齡、杜如晦、魏征、長孫無忌等等一大批人各司其職并沒有形成一個整體集團;武將中同樣是如此),并不能構(gòu)成單一龐大的士人集團對于皇權(quán)的直接的威脅,再加上新朝伊始,士人們在政治上的腳跟都尚未站穩(wěn),所以唐太宗并沒有必要引入宦官這個局外的勢力(對于宦官實用不當(dāng)而導(dǎo)致的巨大危害,唐太宗這么英明的君主定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會使用宦官干預(yù)政治)。
在對付韋后亂政和太平公主奪權(quán)的斗爭中,除了依靠了所謂“龍虎功臣”集團外他還依靠(不太恰當(dāng),應(yīng)該是“使用”更確切)一些其他的政治勢力,典型的就是高力士了。這其中當(dāng)然不能排除高力士逢迎拍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筆者認(rèn)為還是玄宗個人的因素。一方面,唐朝發(fā)展到了玄宗時期,士人集團經(jīng)過近一個世紀(jì)的發(fā)展壯大,根基已經(jīng)大大鞏固,不乏一些能形成與皇權(quán)抗衡的強大的士人群體,玄宗故不敢過分依靠,所以玄宗朝宰相的職務(wù)有多人擔(dān)任,從來沒有幾個能長久的固定的擔(dān)任的;而宦官則“皆家臣”并非是政府機構(gòu)的行政人員或是貴族集團中的成員,加上其后天的缺陷,并無法作為士人集團或是貴族群體的代表取代皇權(quán)的統(tǒng)治;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玄宗作為皇室的旁支,誅滅韋氏集團、剪除太平公主從血淋淋的宮廷政治的殺伐中走出來,在加之之前的武后代唐等等事件使他在人情和宗族情感上感到十分不可信,于是他即位之后便對宗室、皇族的極力控制,他只有轉(zhuǎn)向平時與自己最親近的宦官尋求安慰。高力士在玄宗當(dāng)政的時期權(quán)勢不斷壯大,主持內(nèi)侍省,權(quán)侔將相,甚至太子李亨也稱之為“二兄”,親王公主更是敬稱之為“阿翁”,駙馬稱之為“爺”②。其他太監(jiān)則“雞犬升天”參與軍國政事,或批閱奏章,或監(jiān)撫軍隊,于是玄宗朝遂成為唐代宦官專權(quán)的起始點。對于玄宗我們不能說他前期的統(tǒng)治是荒廢的或是“腐敗”“不理政事”“難于理政”等等云云,然而以高力士為代表的宦官集團還是參與了政治,所以從這里便可以清楚的看出上文所引的白壽彝的那一段話的疏缺之處,皇權(quán)與宦官的關(guān)系從來不能簡單化。
唐中后期接下來的幾代皇帝,宦官的專權(quán)愈演愈盛,肅宗時的程元振“發(fā)詔征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莫敢發(fā)言”③、魚朝恩,代宗時李輔國掌握了禁軍,尊為尚父,加中書令“政無巨細(xì),悉委參決”,“大家但內(nèi)里坐,外事聽老奴處置”④,從此宦官們狼狽為奸,相互傾軋,搞得政治一塌糊涂:藩鎮(zhèn)問題(宦官與藩鎮(zhèn)勾結(jié),成為藩鎮(zhèn)發(fā)展壯大的一個很好的掩護,像玄宗時的高力士與安祿山之流、順宗“永貞革新”時的俱文珍與藩鎮(zhèn)勾結(jié)而使這一革新失敗等等;而且唐中后期宦官專權(quán)的激烈性使得皇帝無法集中有限的力量來對付地方的藩鎮(zhèn)割據(jù),故而藩鎮(zhèn)力量能夠迅速發(fā)展壯大,成為唐滅亡的直接原因)、財政問題(宦官們當(dāng)政時,肆意揮霍,引導(dǎo)皇帝荒淫無道,將政府的財政浪費殆盡)、民生社會問題、農(nóng)民起義(宦官的橫行霸道,作威作福,皇帝的荒淫無道使得政治極端的黑暗和腐朽,宮市、賦稅、徭役等等對百姓的壓榨使得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白居易在《賣炭翁》中對此有深刻的批判)等等問題一一凸顯,此起彼伏,統(tǒng)治者應(yīng)接不暇,束手無策,最終只能亡國。所以上文說宦官專權(quán)是中晚唐紛繁政局的癥結(jié)之所在。
到了唐中后期,宦官對皇權(quán)的影響已經(jīng)不再是幫助皇帝爭奪皇權(quán)了,而是直接決定皇帝的廢立,這也是唐代宦官專權(quán)在中國歷史上的典型意義之所在,唐中后期的君主自順宗至昭宗,凡10帝,其中順、憲、穆、文、武、宣、懿、僖、昭9帝皆有宦官廢立。⑤皇帝當(dāng)政期間更是為宦官操縱成為傀儡。就連那個后來大力壓制宦官的唐武宗在剛即位那會兒為了報答擁立自己登位的仇士良、魚弘志等人,竟將二人分別封為楚國公、韓國公,可見宦官專權(quán)在某些條件下與皇權(quán)之間那種十分曖昧的關(guān)系了。
由于宦官勢力的極端的增長,大大壓制了皇權(quán)和士人集團,引起了皇權(quán)和士人集團的極度不滿,遂有了上文一開始提到的武宗與宦官的較量。而當(dāng)時處于宦官、藩鎮(zhèn)等諸多勢力包圍之下的皇權(quán)顯然沒有那種消除宦官的實力,即使他聯(lián)合了士人集團,力量依舊顯得十分的薄弱。所以后期的南衙北司之爭中多以皇權(quán)和士人集團的失敗而告終。
直到唐朝滅亡的前夕,宦官集團的勢力最終被一個叫朱溫的割據(jù)政權(quán)徹底消滅了,其后唐朝便宣告滅亡進入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jù)時代。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宦官勢力的最終滅亡似乎就是唐王朝滅亡的前兆。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比如東漢吧,宦官勢力消滅之后東漢政權(quán)很快也覆亡。這正是宦官勢力在平衡政治力量這一方面重要性的表現(xiàn)(一旦宦官被滅,那么政治力量的對比平衡很快就失去);而且因為宦官勢力的最終的消除必然是在皇權(quán)、士人集團、地方政權(quán)等集中力量中有了能夠?qū)蛊鋭萘Φ牧碛幸还闪α浚@一股力量在中晚唐顯然不會是來自那個風(fēng)雨飄搖的中央政府,只能是地方的割據(jù)政權(quán)。當(dāng)皇權(quán)剛剛從宦官的操控中離開后不久,又一次陷落于割據(jù)政權(quán)手中。而割據(jù)政權(quán)與宦官甚至是士人集團相對于皇權(quán)而言其本質(zhì)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是皇權(quán)政治的輔助也可能發(fā)展成黃泉政治的威脅。但是他們?nèi)咧g的顯著的不同在于:地方政權(quán)及士人集團擁有宦官所沒有的貴族集團的代表權(quán),自然也就擁有比宦官更大的將皇權(quán)取而代之的合法性,他們能夠走出宦官專權(quán)時永遠不能走出的最后一步,雖然只是名義,于實質(zhì)并無差別,但足以改變歷史——那就是自立稱帝,顛覆舊朝,改朝換代(中國歷史的改朝換代出了西漢和明是農(nóng)民起義成功后建立的政權(quán)外,其他的政權(quán)大都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建立的)。
再看宦官專權(quán)與士人集團之間的關(guān)系。其實這一關(guān)系在東漢時已有表現(xiàn)。中晚唐的這一段歷史讀起來,總能讓人想起東漢末年的許多事來。
宦官專權(quán)的日盛,引起的不僅僅是皇權(quán)的不滿,還有士人集團的不滿。這種士人集團與宦官集團的矛盾關(guān)系在東漢末年的“清流運動”和何進預(yù)謀誅殺所有宦官未果而自己被殺的事件中已經(jīng)表現(xiàn)得很充分。唐代最典型的表現(xiàn)就是“南衙北司之爭”:一為王叔文領(lǐng)導(dǎo)的“永貞革新”,一為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永貞革新”是士人集團與皇權(quán)聯(lián)合試圖從政治制度的角度清除宦官專權(quán)的一次努力,他試圖奪回宦官手中掌握的軍權(quán),卻被宦官察覺,徒然打草驚蛇,最終落得一場空;“甘露之變”則是士人集團與皇權(quán)聯(lián)合企圖以暴力的方式從現(xiàn)實的實際中直接的清除宦官勢力的努力,最終同樣是失敗了。表面看來,這兩次的失敗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如“永貞革新”是因為藩鎮(zhèn)對宦官集團的提醒而使宦官們明白了王叔文的釜底抽薪之計,“甘露之變”更是由于行動埋伏的不小心不嚴(yán)密這一十分偶然的因素而導(dǎo)致的失敗,實際上,這兩次失敗都是有其必然性的。“永貞革新”除了要清除宦官勢力之外,還極力的打壓藩鎮(zhèn)的勢力,試圖掃除藩鎮(zhèn)對中央集權(quán)的威脅,必然使得藩鎮(zhèn)與宦官兩者相聯(lián)合,使得原本力量就很有限的皇權(quán)和士人集團的力量更顯得弱小,只有失敗;“甘露之變”中行動倉促,策略粗糙,計劃不嚴(yán)密,必然遲早暴露,再加上宦官手中還握著軍權(quán),也只有失敗無疑。對于這一點,陳寅恪先生有一段深刻的論述:“夫唐朝河朔藩鎮(zhèn)有長久之民族社會文化背景,是以去之不易;而牛李黨爭之政治社會文化背景尤長于河朔藩鎮(zhèn)且此兩黨所連結(jié)之宮禁閹寺,其社會文化背景之外更有種族問題。故文宗欲去士大夫之黨誠甚難而欲去內(nèi)廷閹寺之黨則尤難,所以卒受‘甘露之禍'也。”從社會文化背景的根深蒂固的角度解釋了失敗的原因,是十分深刻的。而其我們發(fā)現(xiàn),唐代的反宦運動與漢代的反宦運動的一個很大的不同在于,唐代多是在有皇權(quán)參與下的與士人集團聯(lián)合的反宦,而漢代多是外戚或士人集團單獨力量下的反宦,他們的力量弱得很,失敗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唐朝的兩次失敗,除了陳寅恪先生講的社會文化背景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唐代宦官掌握著軍權(quán)(高力士官拜大將軍、李輔國任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繼之、魚朝恩任觀軍容使,這時還只是暫時的管攝,尚未常主兵權(quán);到了德宗時以神策、天威軍權(quán)與竇文場、霍仙明,則禁軍之權(quán)自此盡歸宦官),而上面的兩次的反宦運動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以奪回軍權(quán)為目標(biāo)的。關(guān)于這一點,司馬光曾經(jīng)指出“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quán),憑借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管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如唐之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⑥
再對比漢唐的這兩次的反宦官運動,我們還發(fā)現(xiàn)了一個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不論是漢還是唐,最終徹底消除宦官勢力的都是地方的割據(jù)政權(quán):東漢時是董卓,唐時是朱溫。那么宦官與藩鎮(zhèn)之間又有什么關(guān)系呢?前面已經(jīng)比較過了宦官與地方割據(jù)政權(quán)在合法性上的差別,這里又涉及到兩者的另一個不同:盡管兩個集團都是處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從事與皇權(quán)及士人集團的斗爭的,但是由于兩者在政治合法性上的差異,又導(dǎo)致了他們在具體目標(biāo)上存在不同:宦官多是貪圖權(quán)勢和享受,而藩鎮(zhèn)則是看準(zhǔn)一個目標(biāo)就是皇權(quán)。藩鎮(zhèn)在這一點上顯然高出宦官許多,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安史之亂”前夕高力士宦官集團與安祿山藩鎮(zhèn)集團之間以及“永貞革新”中的藩鎮(zhèn)與宦官的勾結(jié)而唐滅亡前夕朱溫卻對宦官集團的大屠殺了,誅殺宦官符合當(dāng)時的要求,最終能憑此而贏得取得皇權(quán)的資本,故為之也。
在這樣的以宦官專權(quán)為焦點的皇權(quán)、宦官、士人集團以及藩鎮(zhèn)的不斷的角力中,,最終唐王朝歸于滅亡。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宦官以及宦官專權(quán)都是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制度的產(chǎn)物。這一制度發(fā)展與衰亡離不開宦官的參與{就皇帝的內(nèi)宮而言:這種經(jīng)過閹割而喪失了生殖能力的男子的存在,承擔(dān)了大量的職役工作;對于皇帝本人而言,出了上文提到的在皇權(quán)的爭奪及政治勢力的平衡問題上有重要的作用外(比如漢唐宦官勢力一旦別消滅了,政治的平衡很快被打破,接著漢唐政權(quán)的覆滅就為時不遠了),一個專制獨斷統(tǒng)治廣袤大國的而又身處九重之外與外隔絕的皇帝,他能夠也是唯一可以信賴的只有那些在皇帝自己認(rèn)為是日夜守奉在自己周圍、同樣與外界孤立、且由于生理因素?zé)o法形成威脅自己政權(quán)的勢力的宦官們;尤其是女主專政時期,這一依賴性更加突出(而事實證明這一看法大錯特錯)},所以宦官是古代政治發(fā)展中不可缺少的一個角色。由此我們說宦官專權(quán)是在皇權(quán)的爭奪中興起的(明代專制主義達到頂峰的一個標(biāo)志正是其東廠西廠及錦衣衛(wèi)的等宦官特務(wù)機構(gòu)的設(shè)立以及其中后期的宦官專權(quán)的激烈),接著在與皇權(quán)和士人集團的斗爭中不斷的壯大勢力,最終又會在政治力量的角逐中由某一力量消滅(多是地方割據(jù)政權(quán)),也正是在這樣的政治的斗爭中我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制度由新興走向沒落,最終滅亡。與之相伴,宦官制度也隨即滅亡,宦官亦不復(fù)存矣。
參考書目:
[1]《新編中國通史》(第一、二冊),周一良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2001年9月版
[2]《細(xì)說隋唐》,趙劍敏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3]《隋唐五代史》(上、下冊),王仲犖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中國通史》(第六卷、中古時代)白壽彝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9年版
[5]《中國通史》(第三冊),范文瀾主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6]《唐代政治史論稿》,陳寅恪著,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56年版
[7]《舊唐書》、《新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
[8]《皇帝與皇權(quán)》,周良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4月版
[9]《資治通鑒》,司馬光撰,中華書局點恔本
[10]《宦官的歷史》,李新偉、謝茂發(fā)、歐陽森編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6月版
[11]《中國宦官制度史》,余華青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注釋:
①《中國通史》(第六卷、中古時代),白壽彝主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舊唐書》卷一八四《高力士傳》
③《資治通鑒》卷二二三,代宗廣德元年
④《舊唐書》卷一八四《李輔國傳》
⑤《新編中國通史》(第二冊),周一良主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第58頁
⑥《資治通鑒》卷二三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