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09 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說:君子不應該像器具一樣。
此章言簡意賅,意義既廣泛亦深遠,屬“兩端四角式”啟發教學的例子之一。小弟先前也已就本章討論過,在此在整理一下:
要了解本章應先自器具本身開始分析,器具的特性主要有三。一是用途:有較為固定用途;二是定量:有一定的容量;三是定性:有一定的性質。
就固定用途而言:“君子不器”為君子無論是做學問還是從政,都應該博學且才能廣泛,如此才不會像器物一樣,只能作有限目的之使用。這與以下這章有部分相似: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說:君子必須要能做到廣泛地閱讀典籍,吸收知識,以禮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如此便不至于偏離人生的正道了)。此章另有一點要注意,如果“約之以禮”按以上的解釋,則亦有人性非絕對為善的意思。但“約之以禮”另有一種解法:以躬行實踐來解禮,故“約之以禮”即解為:能歸納到實踐之上。
論語中還有一章與此解有關。公冶長篇,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貢問孔子說:老師以為我的表現如何啊?孔子說:你啊,像是一種器具吧!子貢又問:我像那種器具啊?孔子回答說:就像那宗廟里頭用來盛裝黍稷的玉器——瑚璉)。若以器具的用途來看公冶長篇此章,應是孔子贊許子貢已學有專精,但要想成為君子則仍有待努力。
論語中另有一章,字面上似乎與此解有所沖突。子罕篇,大宰問于子貢曰: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大宰問子貢說:孔先生真是一位圣人啊,他竟然能做這么多種事啊!子貢說:這必定是天意要他成為一位大圣人的也,也是天意要他有這么多種才能的吧。孔子知道此事之后說:大宰了解我的情形嗎?我年少時因為貧窮,所以學會了做這么多瑣碎的事。君子真的只在乎多能嗎?不是只在乎多能的)。這章有幾點要注意:
一、此章主旨為大宰及子貢以多能為圣,孔子說明:就算君子,也不是只做到多能就可稱為君子的。并不是說君子不需多能,故與為政篇本章這種解法,并未沖突。
二、圣由天意,多能則在人為。
三、人以圣人稱孔子,孔子以君子回之。這不僅是自謙,事實上以孔子的標準而言,無人能達圣人的境界(博施濟眾)。整部論語也不見孔子許何人為圣。
四、此章孔子雖字面上是回大宰的,其實是講給子貢和所有人(含我們)聽的。
就定量而言:君子之氣度應似江海納百川,不像器物一般有容量之限制。這與以下這章相呼應:為政篇,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己(去攻擊那些與自己不相同的思想言論,是會造成害處的)。此章又有另解,容后表。
就定性而言:是指君子待人處事時,不應像器物一般定型不變,而應適時適地適人適事地采取合宜之行動。這是近似于以下這章: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比(君子對于天下一切的事物,沒有一定怎樣才可以的,也沒有什么一定怎樣才不可以的,唯一行事的標準就是義)。
綜言之,小弟覺得將上述三個角度的看法都合并起來更為完整,也許也更接近孔子之原意。即君子在個人品性修養時,不可像器物一樣只針對某些特別的目地,而必須廣泛地涉獵各種知識,培養各種才能;在個人之氣度與態度方面,則應不像器物一般,僅有一定的容量,須要以寬廣的胸襟來看待萬事萬物;在待人處事的原則方面,則不應像器物一般定型而一成不變,須因時因地制宜,采取最合宜的行為舉止以收取最大最好之成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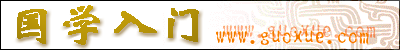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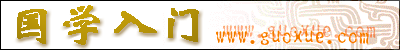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