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03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孔子說:以政令來教導,以刑罰來管束,百姓會因求免于刑罰而服從,但不知羞恥;以德行來教化,以禮制來約束,百姓會知道羞恥并且可以走上正善之途。
本章字面上的解釋看似單純但還是有兩個字要注意一下。1.“道”為“導”;2.“格”為“正”及“至于善”。這第二點尤其重要,因為“有恥且格”還可分為兩個層次。一為知羞恥而正,因為害怕恥辱而走上正途;二為至于善而正,因為以善為樂而走上正途。以下會就此點再加以解釋。
以內涵而言本章也有幾點仍值得討論一下:
1.政、刑之意義。
“政”字在論語中一共出現于30章,其中或只表示簡單的名詞;或屬兩端四角啟發式教學,列出了為政時需要注意事項的部分條目;談及“政”的廣義定義的僅一章,顏淵篇: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向孔子請問為政之道。孔子回答說:政的意思就是正。你帶頭走正道,那又有誰敢不走正道呢)?
另有兩章可與顏淵篇此章相呼應。子路篇,子曰: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說:如果真能端正自己的言行,于從政有何困難的呢?不能端正自己的行為,又怎能使別人端正呢)?此章間接指出:政即是正人,而其基礎則是正己身。
顏淵篇,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康子向孔子請問為政之道說:如果殺掉為非作歹的人,親近修德行善的人,這樣做如何?孔子回答說:您負責政治,何必要殺人呢?您有心為善,百姓就會跟著為善了。政治領袖的言行表現像風一樣,平民百姓的言行表現像草一樣,風吹在草上,草一定順著風的方向倒下)。此章說明了正己身即可經由教化而正百姓,這就是政。當然也指出了政治、社會風氣好壞的責任乃在居上位者自己的身上。
由此可知:孔子所說的政就是正,其旨在正眾。換句話說就是大眾的教育。而其進行的方法主要是教化。
論語中“刑”字一共出現于4章,連同為政篇的本章在內似乎都可以用法律上處罰罪犯方法總稱來解之。唯一可能有例外的是里仁篇,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孔子說:君子關心的是德行,小人在乎的是產業;君子注重的是規范,小人擔心的是利益)。
此處的“刑”好象以常法、典范來解或許較好。
2.是否不需政、刑?
關于這點,已略述于小弟前帖「孔子的德治思想」一文:http://cnlu.org/club/club/disp.asp?owner=A202&ID=1975
3.性善性惡。
以性善的角度來看,不論是清明的政、合理的刑、美好的德、適宜的禮都應該可以使大家直接因為快樂、因為好善而走上正途。然而從為政篇本章看來,以政、刑、德、禮都有可能使人民只止于害怕刑罰或害怕恥辱才走入正軌,雖然害怕刑罰而正或害怕恥辱而正有程度上的不同但這兩者似乎都顯示著人性中除了善還有些什么別的東西吧。
綜合以上論述,小弟以為為政篇本章的意義應是:政、刑是可以達到正眾的目的,但“民免而無恥”僅是一旦刑罰法律的訂定有漏洞或執行有困難,人民便有出軌的可能。做得最好,社會可能也僅能止于秩序井然。
德、禮也可以正眾,且“有恥”在層次上比較高了一點,人民除了外在的刑罰法律的約束之外,還多了一層來自內心的自我約束,因此就算法律有漏洞、執法有困難之處,這自我約束應可大大地降低脫序行為的發生。社會除了井然有序之外,也能更多添了份祥和。
如果德、禮能發揮其極致的作用就使人民的內心除了自我的約束之外,還有更進一層積極向善、以善為樂的動力這就是格(至于善)了。如此社會將不僅僅是祥和、井然有序,還會產生一股快樂且向上進步的積極動力,這也許就真的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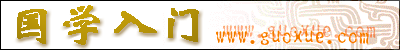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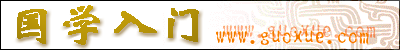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