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認(rèn)為,20世紀(jì)的嵇康研究,走過了一條由古典型向近代型不斷演化的道路;其近代化過程可分為四個時期:1900——1928年,可稱為嵇康研究的第一階段。此階段嵇康研究是從古典型向近代化的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nèi)以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xué)史》和魯迅的《魏晉風(fēng)度及藥與酒之關(guān)系》中,對嵇康研究成就最為突出。劉師培對嵇康的研究,重視時代思潮、文學(xué)發(fā)展、比較研究、點面結(jié)合、溯源探流等研究方法的運用。劉氏的嵇康研究已初步完成了從古典型,向近代化的過渡。魯迅在劉師培研究方法的基礎(chǔ)上,又重視魏末晉初的社會風(fēng)氣和玄學(xué)興盛等方面,并初步做到了運用文史哲擴(kuò)通的方法。此外,魯迅還重視嵇康作品的思想新穎,往往與舊說反對,這是劉師培所不及的。
1928-1949為嵇康研究的第二時期。其特點互為研究的細(xì)密化。如陸侃如、馮阮君研究嵇康詩時,重視嵇寫四言詩運用五言詩句式的規(guī)律;并述而指出“他的六言詩每首均四句,四句均入韻。”如此細(xì)微地分析嵇康詩歌,乃此前所未見。特點之二,鄭振鐸從四言詩發(fā)展的角度,肯定嵇康四言詩的風(fēng)格;并從當(dāng)時社會思想主潮——玄學(xué),分析嵇康的《雜詩》和《游仙詩》,亦體現(xiàn)了在分析作品方面既細(xì)微又深刻。特點之三,劉大杰從嵇康所處的時代及環(huán)境,并認(rèn)為魏末文學(xué)“完全是當(dāng)時那種玄學(xué)與宗教思想的反映”。在那些作品里,明顯地表現(xiàn)出當(dāng)代文人的性情理想嗜好和行為,間接地把那一個紊亂的時代留下一個分明的子。劉大杰在論述“竹林名士”時還與“建步士子”的對比,特別是將嵇、阮同曹植對比;體現(xiàn)劉氏的文學(xué)史專著能對魏晉文學(xué)的整體把握,論述其史的發(fā)展脈絡(luò),這在30年代末是頗為難能可貴的。
1949-1978年為嵇康研究的學(xué)科統(tǒng)一時期。在這一時期,國家力求把各種思想觀點統(tǒng)一到唯物史觀方面來。本時期的嵇康研究成就較突出者是林庚。他在其《中國文學(xué)簡史》一書中,把嵇康視為“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為實行民主政治而斗爭的代表”,這樣的論點乃是此前的稽康研究中所未見。此外,霍松林對嵇康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特點的分析,也較為公允。
1978-1999年為嵇康研究的第四階段,其主要研究特征為觀點與方法的多文化。本階段嵇康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是羅宗強(qiáng)與徐公持。羅氏在其《玄學(xué)與魏晉士人心態(tài)》的專著中,由對嵇康的研究基本上離開了劉師培的《中古文學(xué)史》和魯迅的《魏晉風(fēng)度及文章與
及酒之關(guān)系》的講演,而用玄學(xué)分析嵇康的為人與心態(tài),認(rèn)為“嵇康的悲劇不僅因為他的
偌,而終于導(dǎo)致殺身之禍,更在于他的玄學(xué)人生觀的本質(zhì)。”徐公持在其《魏晉文學(xué)史》中,對嵇康為人,特別是嵇康魅力的論述,嵇康與玄學(xué)思想的分析,對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的考證,乃是百年來的魏晉文學(xué)史中研究嵇康所取得成就之最突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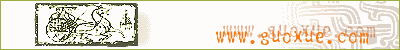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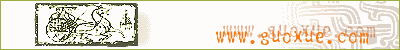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