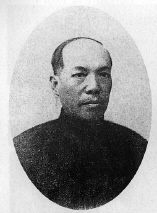|
www.ffhyjd.com
|
|

| 出行參考 | 天 氣預(yù)報 |
呂文浩 |
討論老清華的人文學(xué)術(shù)史的人一般都是從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談起的。
這當(dāng)然是很對的。在1925年國學(xué)研究院成立之前,清華的人文學(xué)術(shù)研
究大體是零星的、淺陋的,在學(xué)術(shù)界不占什么重要位置。國學(xué)研究院
的學(xué)術(shù)研究和人才培養(yǎng)才第一次真正地給清華帶來學(xué)術(shù)上的聲譽(yù),樹
立了清華作為學(xué)術(shù)重鎮(zhèn)之一的地位。
每每想起國學(xué)研究院,我心里總是充滿了一種復(fù)雜的感情:和大
多數(shù)人一樣,我羨慕那時師生熱心向?qū)W的氛圍,高度評價他們的研究
工作;另一方面,也許是由于國學(xué)研究院的“好景不常”的緣故,我
常常惋惜其未能“盡善盡美”。研究院一直是在校內(nèi)的重重矛盾下發(fā)
展的,最初的主持人吳宓先生因不能實(shí)現(xiàn)其設(shè)想而引退,后來研究院
的規(guī)模大體上是處于不斷萎縮的狀態(tài),1927年以后王國維自沉、梁啟
超因多病不能常川住院繼而辭職,研究院失去兩大“臺柱”,盛況大
不如前。想起梁啟超在一次茶話會上說“我院如繼續(xù)努力,必成國學(xué)
重鎮(zhèn)無疑”,言猶在耳,國學(xué)研究院沒過幾年就已成為歷史的陳跡,
怎能不令人嘆惋!
人生活在一個布滿著種種現(xiàn)實(shí)利益沖突的世界上,不可能事事
“盡如人意”。以這種眼光來看,過分地停留在惋惜上似乎也不必要。
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雖若曇花一現(xiàn),但確有足觀者在。它只存在了4年(
1925-1929),培養(yǎng)了4屆學(xué)生,總數(shù)70余人,而成材率頗高,其中尤
以高亨、徐中舒、吳其昌、劉盼遂、王力、姜亮夫、陸侃如、戴家祥、
衛(wèi)聚賢、謝國楨、楊鴻烈、陳守實(shí)、劉節(jié)、蔣天樞等成就突出。記得
在1995年紀(jì)念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70周年國際學(xué)術(shù)討論會上,有人呼吁總
結(jié)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學(xué)術(shù)研究與人才培養(yǎng)的經(jīng)驗(yàn),頗有反響。當(dāng)此母校
90周年大慶之際,筆者應(yīng)約執(zhí)筆撰寫此文,以國學(xué)研究院為例略述老
清華人才培養(yǎng)經(jīng)驗(yàn)之一斑,想必也是讀者諸君所樂于一讀的。
國學(xué)研究院人才輩出的第一個原因是學(xué)生本身素質(zhì)好。“玉不琢, 研究院起初打算不辦學(xué)術(shù)刊物,理由是:(1)雜志按期出版,內(nèi) 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人才輩出的第二個原因是校方眼光很高,慧眼識 (一)本院聘宏博精深,學(xué)有專長之學(xué)者數(shù)人,為專任教授。常 (二)對于某種學(xué)科素有研究之學(xué)者得由本院隨時聘為特別講師。 國學(xué)研究院的“四大導(dǎo)師”中,王國維、梁啟超成績卓著當(dāng)時已 研究院的幾位教授和講師在普通演講里講授的都是當(dāng)時最前沿的 葉企孫解放后有一次和人說起老清華辦學(xué)成功的經(jīng)驗(yàn),他認(rèn)為主
不成器”,但前提是你琢的是一塊玉,而不是一塊普通的石頭,如果
琢的是一塊普通的石頭,任你如何用心雕琢,也成不了一塊器。維持
教育品質(zhì)的第一個因素是提高生源質(zhì)量。國學(xué)研究院的學(xué)生中以服務(wù)
教育界及學(xué)有根底者居多,應(yīng)屆大學(xué)畢業(yè)生尚不足一半,不少人在入
學(xué)前已有著作問世,已經(jīng)是相當(dāng)成熟的青年學(xué)者,所以能夠很快進(jìn)入
狀態(tài),加以名師點(diǎn)撥,很快便脫穎而出。國學(xué)研究院的學(xué)制只有1年,
但如題目較難,可以申請延續(xù)1年或2年。實(shí)際的情況是有近一半的人
延長了學(xué)習(xí)期限,多數(shù)是延長1年,也有極少數(shù)延長兩年的。讀過研究
生的人都明白,我們現(xiàn)在上3年研究生時常還覺得時間很緊,1年學(xué)制
是很短的,根本不容許你在這一年時間內(nèi)打基礎(chǔ)。國學(xué)研究院要求學(xué)
生入學(xué)兩星期內(nèi)確定論文題目,以自己研究為主,有問題可以向?qū)?br>
請教。研究院給學(xué)生安排的是必修4門普通演講課,定期和導(dǎo)師見面,
向?qū)熣堃妗?/font>
容材料難得精粹,若以照片祝詞等充塞敷衍,于本院名聲有損無益;
(2)學(xué)生研究期限,暫定1年,研究時間已苦無多,若再分心于雜志
之著述及編輯,必荒學(xué)業(yè);(3)佳作可刊于叢書,短篇可刊于周刊及
學(xué)報中分別刊登,而編印叢書,由教授指導(dǎo)學(xué)生為之。也許是由于不
少學(xué)生有意于延長學(xué)習(xí)期限,他們主辦了《實(shí)學(xué)》月刊,不少學(xué)生還
參加了北京述學(xué)社《國學(xué)月報》雜志的編輯和撰述工作,在研究院創(chuàng)
辦的《國學(xué)論叢》季刊上,學(xué)生們也屢有著述發(fā)表。這些豐厚的學(xué)術(shù)
成果充分說明,研究院學(xué)生的學(xué)術(shù)根底與研究能力非同一般。
英才,物色到一批貨真價實(shí)的大師或一線學(xué)人,為清華人文學(xué)科開了
一個好頭。研究院章程中對教授(即導(dǎo)師)和講師的要求是:
川住院,任教授及指導(dǎo)之事。
經(jīng)廣為人知,陳寅恪和趙元任則屬于潛在的大師,有一定的知名度但
主要著作還沒有產(chǎn)生,也被校方延攬到校。他們4位都站在當(dāng)時學(xué)術(shù)的
最前沿,是真正的一線學(xué)人。而只有在學(xué)術(shù)的最前沿打過勝仗的才配
得上稱大師。任研究院講師的先后有李濟(jì)、馬衡、林宰平,也都是一
時的績學(xué)之士。王國維辭世、梁啟超去職以后,陳寅恪建議校方聘請
的導(dǎo)師是章太炎、羅振玉,也都是當(dāng)時的大師級人物,可惜他們沒有
應(yīng)聘。
學(xué)問,如王國維的“古史新證”、梁啟超的學(xué)術(shù)文化史、陳寅恪以比
較語言學(xué)來證史、趙元任的描寫語言學(xué)都是非常嶄新而且精深的。客
觀地說,研究院的學(xué)生雖然根底深厚,但他們以前的知識結(jié)構(gòu)與導(dǎo)師
們的學(xué)問要想順利銜接起來也絕非易事,尤其是陳寅恪與趙元任的學(xué)
問屬于新的領(lǐng)域,常使學(xué)生們感到聽講十分費(fèi)力。姜亮夫在回憶里說,
聽陳寅恪的課很吃力,非常苦惱,認(rèn)真記筆記,課后和同學(xué)對筆記,
再加上看書,大約能懂1/3左右。在鉆研過程中感到在方法上很有收
獲。他坦言,他自己是以舊的為基礎(chǔ),對新的略有所知的“半掉子”。
姜亮夫的情況可能很有代表性。所以,學(xué)生們以王國維和梁啟超為導(dǎo)
師的居多。研究院的學(xué)生中學(xué)術(shù)境界達(dá)到或超過導(dǎo)師的大概還沒有,
這不能不說是必然的。但是,從游于大師或一線學(xué)者門下,即便不能
得心應(yīng)手地運(yùn)用其所指示的路徑,至少打開了視野,能明了自己所處
的位置,在題目的選擇和方法上得到啟迪,也是很值得的。研究院的
制度是分科不分系,以教授個人為主,仿書院制度,期于在教授與學(xué)
生的密切接觸中使學(xué)生掌握治學(xué)方法,受導(dǎo)師的人格熏陶,短期內(nèi)確
有所獲。從4年的實(shí)踐來看,這種辦法應(yīng)該說是成功的。
要是兩點(diǎn),一是經(jīng)費(fèi)充裕,二是慎選師資、寧缺毋濫。繩之以國學(xué)研
究院的經(jīng)驗(yàn),經(jīng)費(fèi)充裕是一個前提條件,自不必說,國學(xué)研究院最為
突出的也許應(yīng)該是禮聘大師,完全信任他們,放手讓他們依照學(xué)術(shù)研
究和人才成長的規(guī)律辦事。這當(dāng)是老清華辦學(xué)經(jīng)驗(yàn)里最為寶貴的成分。
|
《中華讀書報》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