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李絮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被偶然發(fā)現(xiàn)。豐富精美的敦煌文書和壁畫震驚了世界。但是,被發(fā)現(xiàn)的同時也是被破壞的開始。從此,敦煌文書大量流失,壁畫被不斷破壞,更有無情的沙害、病害時刻威脅著莫高窟……
研究敦煌學(xué),保護(hù)莫高窟。這是幾代人為之付出心血甚至生命的事業(yè)。
敦煌研究院:邊研究,邊保護(hù)
6月20日,就在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100周年前夕,我親赴敦煌莫高窟。此
行的目的本在于感受敦煌的藝術(shù)魅力、了解敦煌學(xué)的研究歷程。但出
人意料的是,真正吸引我的,竟是長年堅守敦煌,從事莫高窟保護(hù)工
作的人們。
1944年,常書鴻等人在敦煌建立了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即現(xiàn)敦
煌研究院前身。當(dāng)時,莫高窟一層洞窟已被流沙掩埋,搶救和保護(hù)刻
不容緩。從那時起,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就開始了搶救、修復(fù)莫高窟、
臨摹敦煌壁畫的工作。
這種邊研究邊保護(hù)的工作方式成為一種特殊傳統(tǒng)。今天敦煌研究
院的人們?nèi)匝匾u這一方式,在進(jìn)行敦煌學(xué)研究的同時,投入巨大精力,
不斷摸索和實踐科學(xué)保護(hù)莫高窟的方法。他們防沙治沙、加固崖壁、
復(fù)制洞窟、挽救病害壁畫。事實上,敦煌研究院承擔(dān)著學(xué)術(shù)研究、文
物保護(hù),和公園管理等多方面職責(zé)。這些職責(zé)使得他們的工作比國內(nèi)
其他任何研究機(jī)構(gòu)的工作都更復(fù)雜和沉重。現(xiàn)任院長樊錦詩女士曾說
過這樣一句話:“保護(hù)敦煌就象照顧一個有病的孩子,你總得惦記著
他。”
站在莫高窟主體建筑“九層樓”的崖頂上,可以看到遠(yuǎn)處的敦煌
研究院的公墓,最大的墓碑就是老院長常書鴻的。沙丘上星星點點的
18座墳塋,背靠三危山,面向莫高窟,仿佛在默默凝視、放心不下。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就是這樣年復(fù)一年、前仆后繼地工作著。
為了防沙,保護(hù)所治沙站的4名工作人員取消休息日,守衛(wèi)在莫高窟崖
頂?shù)纳城鹕稀O奶焐城鸨砻鏈囟雀哌_(dá)70攝氏度,而他們卻需身著長衣
長褲,以防皮膚被灼傷。他們的飲用水也是咸苦腥澀,難以下咽,但
我在采訪中沒有聽到一句怨言。
參觀莫高窟,當(dāng)然是先去第17窟——著名的藏經(jīng)洞。藏經(jīng)洞的洞
口就在16窟甬道的北側(cè),大小剛好能容一人進(jìn)出。100年前,當(dāng)晚清道
士王圓偶然發(fā)現(xiàn)這個洞窟時,這里堆滿經(jīng)卷、絹畫、法器、石碑和
塑像,但是很快,王道士就將這些無價之寶賤賣給了英人斯坦因、法
人伯希和等外國探險家們。今天人們所能看到的,只剩一尊唐人洪
和尚的塑像和滿墻斑駁的壁畫了。
欣賞藝術(shù)、喟嘆歷史的同時,我注意到莫高窟講解員的與眾不同
之處。這里的每名講解員都帶有一串鑰匙。他們帶領(lǐng)游客來到石窟前,
開鎖讓游客魚貫而入,并對窟內(nèi)情況逐一講解。講完以后,他們則要
求全部游客走出石窟,然后很小心地將洞窟的黑褐色鋁合金門鎖好,
這才帶領(lǐng)游客來到下一個洞窟前重新開門。
工作程序如此繁難,可謂事出有因。據(jù)了解,敦煌研究院曾于
1991年做過一個實驗,即讓40名學(xué)生在第323窟內(nèi)滯留了37分鐘。研究
結(jié)果表明,這些人在這段時間呼出的氣體使窟內(nèi)的二氧化碳和濕氣含
量迅速增高。而要使這些空氣散盡則需6個小時。有關(guān)人員解釋說,二
氧化碳和濕氣對壁畫的破壞作用相當(dāng)大。那次實驗使他們更清楚地認(rèn)
識到問題的嚴(yán)重,因此他們采用了這種參觀之后窟內(nèi)不留人的做法。
就是為了減少參觀為文物保護(hù)帶來的危害。此外,莫高窟的400多個洞
窟現(xiàn)采取輪流開放的辦法,而且每批只開放十幾個。
|
崖頂治沙站:用綠化帶和尼龍網(wǎng)阻擋風(fēng)沙 |
與二氧化碳和濕氣相比,更大的破壞來自病害和沙害。目前,除
防治洞窟自身酥堿、起甲、霉變等病害外,防沙治沙已成為保護(hù)莫高
窟最重要的工作。據(jù)治沙站工作人員詹鴻濤介紹,防治莫高窟沙害的
主要屏障,就是綠化帶和尼龍防沙障。據(jù)統(tǒng)計,自1990年崖頂開始種
樹并設(shè)置了尼龍防沙障以后,每年吹向莫高窟的沙粒已由1990年的
3000立方米減少到了現(xiàn)在的幾十立方米。
綠化帶就從“九層樓”崖頂?shù)闹紊痴拘∥輧蛇呴_始延伸,兩排綠
化帶總長1850米。事實上,這些被詹鴻濤稱作“樹”的梭梭、花棒和
沙拐棗,在平原上只能算是“草”。它們沒有明顯的樹干,淺綠色的
葉子也都退化為柔軟的針狀。這些“樹”大多不到半米高,生命相當(dāng)
脆弱,僅靠根部人工埋藏的滴管一滴滴地滲水而存活,所以治沙站的
工作人員需要24小時照顧它們,“但是”,詹鴻濤欣慰地說,“它們
防沙固沙的效果非常明顯。”
在治沙站與“九層樓”之間,有三層長達(dá)3240米的尼龍防沙障。
在第一層防沙障的兩側(cè)已堆起了半人多高的沙子,側(cè)面看就象一道沙
筑的小長城。而離莫高窟最近的一道防沙障兩旁,積沙就已經(jīng)非常少
了。據(jù)了解,從1990年至今,防沙障已積沙21000多立方米。這個驚人
的數(shù)字不容置疑地說明了尼龍網(wǎng)的重要作用。
除綠化帶和尼龍網(wǎng)以外,治沙站的工作者還在“九層樓”的崖壁
上噴涂了硅酸鉀,用以防止崖壁上的沙粒滑落,起到固沙作用。詹鴻
濤說:“目前看來,這個辦法非常有效。”
威脅莫高窟安全的,還有“水”患,這包括下雨和山洪。石窟管
理科龔鴻鵬說:“石窟崖頂因噴涂過硅酸鉀,所以不會因雨水而造成
大面積滑落,而且洞窟內(nèi)也不會滲水。但是,如果雨天開放石窟,游
客腳下帶進(jìn)的水就會使壁畫受潮,容易發(fā)生霉變。因此,下雨后的第
二天我們往往都會閉館。或者在下陣雨時閉館一、兩個小時,雨停以
后再開放。”聽說有游客因這種臨時閉館而抱怨研究院的人“不懂經(jīng)
濟(jì)”、“不會賺錢”,工作人員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說,保護(hù)文物是
他們的首要責(zé)任。
與下雨相比,山洪的危害就大得多了。莫高窟前有條大泉河,河
床長年干涸,但只要一下雨,就會導(dǎo)致山洪爆發(fā)。據(jù)說,大的山洪每
年都要有一次,而我正好目擊了今年的洪峰。
6月24日晚8點,山洪爆發(fā)了。大泉河水發(fā)出巨大的吼聲,大浪裹
挾著粗大的樹干樹枝沖向下游。莫高窟內(nèi)一片忙碌。石窟外的防水設(shè)
施——滲水井已被灌滿,水漫到了地面上。有的工作人員在用水泵抽
井里的水,有的鏟土將易進(jìn)水的洞窟門縫堵住,還有人在查看水情、
檢查河堤,或是搶修被小股山洪沖毀的要道。一時間,氣氛相當(dāng)緊張。
晚9點,距莫高窟九公里處的一座橋梁被沖垮,通向外面的唯一公
路被切斷。人們密切關(guān)注著斷橋附近兩座泵房的安全。因為如果泵房
被毀,莫高窟就失去了水源,研究院及山上居民就將面臨吃水困難的
問題。研究院陳秘書說:“1997年的山洪比這次還要大得多。當(dāng)時洪
水就要漫過大泉河的橋面,莫高窟面臨著進(jìn)水的危險。是樊院長親自
帶領(lǐng)全院的人扛沙袋一起加固的河堤。”
直至我離開敦煌,這次山洪仍未退去。看來,保護(hù)莫高窟的工作
的確復(fù)雜而艱巨,任重而道遠(yuǎ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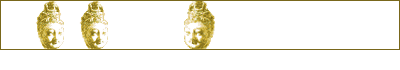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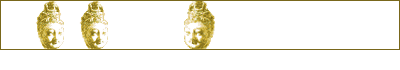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