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郭彧 |
|||||
| 提要 :本文結(jié)合筆者十多年的易圖學(xué)專門研究成果闡述了宋代《河洛》、《先天圖》、《太極圖》和《卦變圖》四大易圖的流變情況,解答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特別指出:為了能準(zhǔn)確地闡述宋明理學(xué),就需要汲取宋代易圖學(xué)的專門研究成果。 |
|||||
先見于北宋的易圖主要有:劉牧《易數(shù)鉤隱圖》中的黑白點(diǎn)《河圖》、《洛書》;鄭夬《明用書》中邵雍的《伏羲八卦圖》(即是《先天圖》,經(jīng)朱震采入《周易圖》);二程所傳周敦實(shí)《太極圖易說》中的周子《太極圖》(經(jīng)朱震采入《周易圖》);朱震《周易圖》(后人更名作《漢上易傳卦圖》)中所列李廷之兩幅《卦變圖》。這些易圖在流傳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流變,以至于演變出不少新的易圖。本文旨在以筆者多年研究易圖學(xué)的專題成果闡述一下這四大易圖的流變情況,以彰顯宋代易圖的來龍去脈,此舉或許會(huì)對(duì)闡明宋明理學(xué)有所裨益。 一 《河圖》、《洛書》的流變 今見于《道藏》中的《易數(shù)鉤隱圖》為三卷本,而《中興館閣書目》記作一卷,且曰:“本朝太 常 博士劉牧撰┄┄采摭天地奇偶之?dāng)?shù),自太極兩儀以下至于河圖,凡六十四位,點(diǎn)之成圖,于圖下各釋其義。”俞琰《讀易舉要》記作二卷,且曰:“太 常 博士劉牧長(zhǎng)民撰┄┄黃黎獻(xiàn)為之序。”今見三卷本,對(duì)于八卦的由來有兩種說法:卷一曰“太極者一氣也┄┄一氣所判是曰兩儀┄┄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謂也┄┄備七八九六之成數(shù),而后能生八卦。”(并且針對(duì)“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謂:“圣人易外別有其功,非專易內(nèi)之物。”)這就是說,八卦是由太極一氣步步生來,此為一說。卷下列《河圖》(九宮數(shù)圖)、《河圖四象》、《河圖八卦》等圖,曰:“龍圖呈卦,非圣人不能畫之┄┄河出圖,洛出書,在作易之前也┄┄龍圖止負(fù)四象八純之卦┄┄河圖八卦垂其象也,故可以盡陳其位┄┄仲尼稱‘河出圖,洛出書',于宓犧畫易之前。”這就是說,八卦是伏羲準(zhǔn)《河圖》畫出來的,此又為一說。北宋時(shí)期有彭城劉牧與三衢劉牧,前者字長(zhǎng)民,宋真宗時(shí)為太 常 博士,后者字先之,宋神宗時(shí)為尚書屯田郎。如果一卷本《易數(shù)鉤隱圖》為黃黎獻(xiàn)之師彭城劉牧撰,則《河圖》、《洛書》就未必出于其手(有后人竄入的可能)。至于今見《易數(shù)鉤隱圖遺論九事》原名作《先儒遺事》,南宋鄭樵就已經(jīng)懷疑非劉牧撰(謂出于陳純臣)。是書列《太皞氏龍馬負(fù)圖第一》,圖說謂八卦由此圖生出曰:“天一起坎,地二生離,天三處震,地四居兌,天五由中,此五行之生數(shù)也。且孤陰不生,獨(dú)陽(yáng)不發(fā),故子配地六,午配天七,卯配地八,酉配天九,中配地十,既極五行之成數(shù),遂定八卦之象。”而《重六十四卦推蕩訣第二》則又謂八卦之由來曰:“原夫八卦之宗起于四象,四象者五行之成數(shù)也,水?dāng)?shù)六除三畫為坎,余三畫布于亥上成乾;金數(shù)九除三畫為兌,余六畫布于申上成坤;火數(shù)七除三畫為離,余四畫布于巳上成巽;木數(shù)八除三畫為震,余五畫布于寅上成艮,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顯然,二書如果是同一位劉牧撰,怎么會(huì)對(duì)八卦的由來有如此不同的多種說法?由此看來,一卷本《易數(shù)鉤隱圖》的作者劉牧,既然說“河出圖,洛出書”是“易外別有其功,非專易內(nèi)之物”,而且說八卦是由太極一氣步步生來,那么,他就不會(huì)主張八卦是“圣人則之”什么“圖書”畫出來的。進(jìn)一步說,他也不會(huì)造出什么黑白點(diǎn)的“河圖”與“洛書”(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卷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二圖,到了卷三就改名作《河圖四象》、《河圖八卦》。卷一《兩儀得十成變化》圖,到了卷三就改名作《十日生五行并相生》,而卷三所列兩幅“洛書”圖,正是卷一《兩儀得十成變化》圖的生成數(shù)分列圖)。這就是說,今見三卷本《易數(shù)鉤隱圖》不全是彭城劉牧的作品,而黑白點(diǎn)《河圖》、《洛書》是出于彭城劉牧之后。經(jīng)考察,《易數(shù)鉤隱圖遺論九事 ?重六十四卦推蕩訣第二》之圖說就是《道藏?周易圖》中范諤昌的《四象生八卦圖》之圖說。范諤昌是三衢劉牧之師,活動(dòng)于宋仁宗年間(非為彭城劉牧之師)。即便是范諤昌亦謂“四象生八卦”,不說八卦為圣人則之黑白點(diǎn)《河圖》而畫。對(duì)此,我們的結(jié)論是:黑白點(diǎn)《河圖》、《洛書》不出于彭城劉牧,也不出于范諤昌,更談不上出于陳摶(似乎有可能出于三衢劉牧)。 今見三卷本《易數(shù)鉤隱圖》之《河圖》為“九宮算”變黑白點(diǎn)之圖,而“洛書”則有兩幅圖(一為《洛書五行生數(shù)》圖,一為《洛書五行成數(shù)》圖),時(shí)至李覯著《刪定易圖論序》,則將二幅圖合而為一稱之為《洛書》。 時(shí)至朱熹著《易學(xué)啟蒙》,則把三卷本《易數(shù)鉤隱圖》中的《河圖》更名作《洛書》,把李覯書中五行生成數(shù)《洛書》更名作《河圖》。 時(shí)至明代章潢結(jié)集《圖書編》,則出現(xiàn)“古河圖”與“古洛書”。原來,元代吳澄對(duì)黑白點(diǎn)圖書的載體問題“直以為馬負(fù)一片之圖而出于河,龜負(fù)一片之書而出于洛”提出了疑問,并以“馬背之毛其旋有如星點(diǎn)”與“龜背之甲其坼有如字畫”之說而重新畫出《河圖》、《洛書》(今見《易纂言外翼》旋毛《河圖》脫,原圖全見明初朱升撰《周易旁注前圖》)。至章潢《圖書編》則于此二圖名前各加一“古”字。可知,說“古”而實(shí)不古。 今天有人聲稱“破譯《河圖》千古之謎”之《河圖》,原來就是三卷本《易數(shù)鉤隱圖》中的兩幅“洛書”合二為一之圖。此等人,對(duì)圖的根本都沒有弄清楚,就在那里大言“破譯千古之謎”,結(jié)果卻是:以自己的“先迷”而誤導(dǎo)眾人入迷。 二 《先天圖》的流變 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列《伏羲八卦圖》,圖說:“右《伏羲八卦圖》。王豫傳于邵康節(jié),而鄭夬得之。”據(jù)邵伯溫《易學(xué)辨惑》說,此圖是鄭夬趁王豫病重之際,賄其仆而得,載之于所著《明用書》中。此圖方圓各六十四卦,圓圖在外象天,方圖在內(nèi)形地。初,邵雍于共城給王豫講學(xué)時(shí),稱此圖為《伏羲八卦圖》,至邵雍至洛陽(yáng)之后“先天之學(xué)”完備,便在給張岷講學(xué)時(shí)改稱此圖作《先天圖》。因?yàn)檫@樣的“天圓地方”之圖,可以用來說“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所以又有《先天圖》的命名。邵伯溫《易學(xué)辨惑》謂邵雍“止有一圖,以寓陰陽(yáng)消長(zhǎng)之?dāng)?shù)與卦之生變”。之所以邵雍先稱此圖為《伏羲八卦圖》,是因此圖“一貞八悔”,“八卦”是指“八貞卦”而言。所謂此圖寓“陰陽(yáng)消長(zhǎng)之?dāng)?shù)”,是指邵雍賦予八貞卦圓圖之?dāng)?shù)為“逆數(shù)之,震一,離兌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見《觀物外篇》),是為“時(shí)必逆知”之?dāng)?shù);賦予八貞卦方圖之?dāng)?shù)為“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見《觀物外篇》),是為“物必順成”之?dāng)?shù)。所謂寓“卦之生變”,是指邵雍以獨(dú)特的卦變方法得到此《伏羲八卦圖》(以乾或坤為祖,逆爻序“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四變而十有六,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而六十有四”的邏輯卦變方法)。邵雍有說無圖的是:“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后人衍作《伏羲八卦圖》)與“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后人衍作《文王八卦圖》)。 朱震在《進(jìn)周易表》中說《先天圖》是由陳摶傳下來的,后經(jīng)李廷之傳給了邵雍,而在《伏羲八卦圖》圖說中卻又稱“王豫傳于邵康節(jié)”。《伏羲八卦圖》即是《先天圖》,其圖所寓“卦之生變”方法與李廷之兩幅《卦變圖》迥然不同,既然不是傳自李廷之,更不能遑論陳摶了。對(duì)此,我們的結(jié)論是:《先天圖》為邵雍作,不是傳自陳摶。 首先對(duì)邵雍《先天圖》加以改變的人是朱熹。“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是某挑出。”(《朱子語類》)朱熹主張:“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卻,待取出放外。”(同上)朱熹僅以六十四卦圓圖為“先天圖”(是有天無地),為的是以“中間虛者”為“太極一理”。接著至宋末元初,學(xué)本朱熹的俞琰則以黑白塊替代卦爻原本符號(hào)作出上標(biāo)“月窟”、下標(biāo)“天根”之《先天圖》(見《易外別傳》),并將此圖之內(nèi)涵與《周易參同契》的丹道掛鉤。 朱熹還本邵雍“乾坤縱而六子橫”說,在《易學(xué)啟蒙》中畫出《伏羲八卦方位》圖(小圓圖),并把邵雍說六十四卦方圖“物必順成”之八數(shù)標(biāo)于圓圖八卦之上,于是本來是“逆知四時(shí)”的六數(shù)“○”型模式之圖就成了“逆知二時(shí)、順知二時(shí)”的八數(shù)反“ S”型模式之圖。于是,朱熹就有了“圓圖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的終身迷惑(見《文公易說》)。 朱熹不明白《先天圖》是由“卦之生變”而得,以為是由六十四卦橫圖“中間拗轉(zhuǎn)”而圍成,于是就用黑白塊替代卦爻的原本符號(hào)制作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并以此圖起乾至坤為“順”,待其圍成“大圓圖”之后,起震至乾為“逆”,起巽至坤為“順”。同樣,朱熹也以為小圓圖是由《伏羲八卦次序》圖“中間拗轉(zhuǎn)”圍成,所以他要給此圖標(biāo)上八個(gè)數(shù)。為了探討《先圖圖》的由來,朱熹教人曰:“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文公易說·答葉永卿》)并直言不諱地承認(rèn)“黑白之位”大、小二橫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和《伏羲八卦次序》圖)“其圖亦非古法”,是自己“但今欲易曉,且為此以寓之耳”(《文公易說·答袁樞》)。此皆為朱熹針對(duì)邵雍《先天圖》所作演變之圖。時(shí)至清代,毛奇齡于《仲氏易》中辨“《先天圖》其誤有八”,實(shí)則皆是針對(duì)朱熹演變易圖而發(fā)。 今人在闡述宋明理學(xué)時(shí),大都引用朱熹爻畫“一分為二”成卦之說轉(zhuǎn)述邵雍的理學(xué)思想。殊不知邵雍主張“獨(dú)陽(yáng)不生,寡陰不成”與“八卦相錯(cuò)”說,他根本不以陰陽(yáng)爻畫的“一分為二”法說八卦及六十四卦的疊加生成。程顥所謂邵雍的“加一倍法”另有所指,是言“卦之生變”的“加一倍”,是言給六十四卦賦予易數(shù)的“加一倍”。時(shí)至今日,尚沒有學(xué)者能在闡述邵雍的理學(xué)思想時(shí),把這些問題說清楚,以此足見借鑒易圖學(xué)的專題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時(shí)至明代之初,趙撝謙于《六書本義》中列一《天地自然河圖》(“黑白魚”形圖。章潢《圖書編》定名為《古太極圖》,也就是今日多數(shù)人所稱之《太極圖》)。實(shí)則此圖本為邵雍“乾坤縱而六子橫”圖說或朱震《周易圖》所列《納甲圖》或楊甲《大易象數(shù)鉤深圖》所列《伏羲八卦圖》的演變圖。演變此圖者的前提條件,必須先以黑白塊替代卦爻的原本符號(hào)。具體的演變過程是:先作三個(gè)同心圓(三圓半徑比例:內(nèi)圓半徑為 1,中圓半徑為1.5,外圓半徑為2),八分之,上以三白為乾,下以三黑為坤,左上外二白內(nèi)一黑為兌,右上外一黑內(nèi)二白為巽,左中內(nèi)外各一白中一黑為離,右中內(nèi)外各一黑中一白為坎,左下內(nèi)二黑外一白為震,右下內(nèi)一白外二黑為艮。然后以弧形曲線對(duì)角中分巽“初爻”、接著中分坎“中爻”,接著中分艮“上爻”,接著中分兌“上爻”,接著中分離“中爻”,接著中分震“初爻”。然后以巽“初爻”之外半黑補(bǔ)震“初爻”之內(nèi)半白,以離“中爻”之外半黑補(bǔ)坎“中爻”之外半白,以兌“上爻”之外半黑補(bǔ)艮“上爻”之外半白。然后抹去內(nèi)二同心圓之圓周線,把離“上爻”之白色扇形塊縮為“水滴狀”,坎“上爻”之黑色扇形塊縮為“墨滴”狀,既成趙仲全所列《古太極圖》。(或以 高雪 君《易經(jīng)來注圖解·周易采圖》中之《心易發(fā)微伏羲太極之圖》反推至《伏羲八卦圖》,可謂分毫不差。)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不是朱熹開了以黑白塊替代卦爻原本符號(hào)的先例,就不會(huì)演變出這樣的“太極圖”。其實(shí),卦爻的原本符號(hào),特別是“ --”符號(hào)是不可“一分為二”的。朱熹為著能“一分為二”,就只好用黑白塊替代了。因而袁樞批評(píng)說:“黑白之位,尤不可曉”(《文公易說·答袁樞》)。“一陰一陽(yáng)之謂道”,以獨(dú)陽(yáng)或獨(dú)陰的“一分為二”而成“四象”,乃至“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就是反劉牧、邵雍等人所謂“獨(dú)陽(yáng)不生,寡陰不成”之道而行,的確是“尤不可曉”。 南宋四川人張行成作《翼玄》,曰:“易先天圖渾天象也,太玄圖蓋天象也。渾、蓋之理無異,唐一行能知之。”清道光五年及光緒七年刻本《翼元》均于“易先天圖渾天象也”八字之后插有“先天圖”和“太元圖”,道光本“太元圖”在前,“先天圖”居后,而光緒本則反之。所插“先天圖”為用黑白塊所作六十四卦圓圖內(nèi)置“陰陽(yáng)魚”形之“太極圖”。至今仍有人以為是書出于南宋人之手,即謂“陰陽(yáng)魚”形之“太極圖”先見于南宋。殊不知此圖是本俞琰《先天圖》演變而來,俞氏圖“中間虛處”標(biāo)以“太極”二字,后人即以所謂之“太極圖”替代之。為此圖者,一本朱熹黑白塊替代卦爻符號(hào),二本朱熹以六十四卦圓圖為“先天圖”之說,三本朱熹“中間虛處”為“太極”之說,順手將所謂的“太極圖”拿來替換俞琰《先天圖》中“太極”二字,是非常“順理成章”的舉動(dòng)。此圖的出世時(shí)間當(dāng)在明趙撝謙公布《天地自然河圖》及章潢命名此圖為“古太極圖”之后。書中的這二幅圖,是清乾隆年間李調(diào)元初刻《函海》因戰(zhàn)火而缺《翼元》之后,其弟李朝夔補(bǔ)遺以當(dāng)時(shí)流行的易圖而順手插入的。張行成有曰“先天方圖”、“易方圓二圖”、“方圓二圖合于一者,以圓包方,地在天內(nèi),渾天象也”,顯然是指邵雍方圓六十四卦的《先天圖》而發(fā),而今圖有圓圖而無方圖,有天無地,豈能體現(xiàn)“以圓包方”之義?對(duì)此,我們的結(jié)論是:“陰陽(yáng)魚”形之“太極圖”是《伏羲八卦圖》的演變圖,其出世時(shí)間在元末或明初,絕對(duì)不是南宋時(shí)期就已經(jīng)流行的易圖。 一些演義性質(zhì)的劇目中,表演漢唐道家人物時(shí)多使用這樣的“陰陽(yáng)魚”形“太極圖”,這也無可厚非。然而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中,是黑是白,確要實(shí)事求是。不經(jīng)過專題研究而輕下結(jié)論,似不可取。 三 周子《太極圖》的流變 周子《太極圖》是為周敦實(shí)《太極圖易說》中的一幅易圖。是繼劉牧一○《太極第一》圖之后的一幅四層太極圖式之圖。此圖實(shí)為周子為了闡明《易傳·系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yè)”一段文字而作。其圖之內(nèi)涵與《太極圖易說》及《易通》內(nèi)容相通。上一○為佐“易有太極”之義而畫;二○為佐“是生兩儀”而畫,與圖說“太極動(dòng)而生陽(yáng),動(dòng)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fù)動(dòng),一動(dòng)一靜,互為其根”有合(黑白相間半弧圖形表“陽(yáng)中有陰,陰中有陽(yáng)”之義);水、火、木、金四象數(shù)一、二、三、四連下一○為一層,表達(dá)“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義(“乾道成男”與“坤道成女”就是乾坤三索生六子共成八卦),最下一○表達(dá)“生大業(yè)”以八卦相錯(cuò)生六十四卦說“萬物化生”。邵雍曰:“老子,知《易》之體者也。”(《觀物外篇》)《系辭》中的這一段話,就是在敘述“《易》之體”。周子制作易圖之模式就是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一為太極”為上一○,“一生二”為二○,“二生三”為五行四象連下一○,“三生萬物”為最下一○。 我們從朱震所列《太極圖》中可以考察周子《太極圖》原圖的面貌。是圖在“子”位標(biāo)有“動(dòng)陽(yáng)”二字,以漢儒“陽(yáng)生于子,陰生于午”之說考之,其上“午”位當(dāng)是“靜陰”二字。此“動(dòng)陽(yáng)”與“靜陰”正是周子《易說》“太極動(dòng)而生陽(yáng)┄┄靜而生陰”之義的縮略語。周子是在說“太極”的動(dòng)與靜,而不是說陰與陽(yáng)的動(dòng)與靜。邵雍曰:“太極一也,不動(dòng)。生二,二則神也。”(同上)周子《易通》曰:“發(fā)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又曰:“動(dòng)而無靜,靜而無動(dòng),物也;動(dòng)而無動(dòng),靜而無靜,神也。”二○“是生兩儀”是“神態(tài)”,而不是“陽(yáng)動(dòng)”與“陰?kù)o”的“物態(tài)”。由此可見,既然周子《太極圖》原圖二○之“子”位標(biāo)有“動(dòng)陽(yáng)”二字,則其“午”位就應(yīng)該標(biāo)有“靜陰”二字。對(duì)此,我們的結(jié)論是:有四重圖式,而且子位標(biāo)“動(dòng)陽(yáng)”、午位標(biāo)“靜陰”的《太極圖》,是周敦頤為解釋《易傳》有關(guān)文字而作,不是傳自陳摶。 兩宋間人楊甲集《六經(jīng)圖》,其卷一《易經(jīng)》圖名曰《大易象數(shù)鉤深圖》。所列《易有太極圖》就是經(jīng)過演變的周子《太極圖》。其演變之處有二:一是變“子位”的“動(dòng)陽(yáng)”為“陽(yáng)動(dòng)”,并外加一橢圓移至五行四象圖式的“火”與“水”之間;一是將五行四象圖式與三○斷開,變四層圖式為五層圖式。朱震所列圖,二○右上方為豎寫“陰?kù)o”二字,楊甲所列圖之所以要改“動(dòng)陽(yáng)”作“陽(yáng)動(dòng)”,蓋出于與“陰?kù)o”對(duì)應(yīng)的考慮。殊不知朱震所列圖已非周子原圖,其“子位”所標(biāo)“動(dòng)陽(yáng)”實(shí)出于周子本意,而右上方“陰?kù)o”實(shí)不當(dāng)豎寫,當(dāng)把“陰”字移至“靜”字之左(古人讀橫寫字自右向左,如下方自右向左“萬物化生”例,既然二○之下是“動(dòng)陽(yáng)”二字,那么其上就應(yīng)當(dāng)是“靜陰”二字)。以訛傳訛,以己之誤而導(dǎo)人之誤,楊甲實(shí)當(dāng)之。 朱熹主張“太極一理”,而“理”本身不會(huì)“自動(dòng)靜”,他認(rèn)為“動(dòng)靜”應(yīng)該是“陰陽(yáng)”的“動(dòng)靜”(比喻為“人乘馬”,太極隨陰陽(yáng)之動(dòng)靜),于是就把“陽(yáng)動(dòng)”二字標(biāo)于二○圖式之左,“陰?kù)o”二字標(biāo)于二○圖式之右。顯然,與周子“太極動(dòng)而生陽(yáng)┄┄靜而生陰”之義相悖。周子本當(dāng)時(shí)“分土王四季”之通說,以中“土”四通“水”、“火”、“木”、“金”。而朱熹則不以水、火、木、金為四象,而是以陰陽(yáng)爻畫的“一分為二”疊加組合為四象。于是他就把周子《太極圖》五行四象圖式的“分土王四季”改為“五行相生”,把“水”繞過中“土”,改為直接與“木”相連。又朱熹不同意“老子,知《易》之體者也”之說,出于“一分為二”的加一倍考慮,就把原圖五行與三○相連的圖式斷開,反而將五行四象圖式連結(jié)在二○之下。如此,“兩儀”與“四象”為一體,而不是“四象”與“八卦之象”為一體(“二生三”之三)。 周子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是一“質(zhì)變”模式,而朱熹的“一分為二”則是一純粹的“量變”模式,真不知從其所謂的“太極一理”,是如何變到“萬物化生”的? 顯然,這是朱熹出于創(chuàng)建其理學(xué)思想的需要,而對(duì)周子《太極圖》進(jìn)行了本質(zhì)上的演變。今人在闡述周敦頤的理學(xué)思想時(shí),仍然在使用經(jīng)朱熹改造過的圖式。試想,如此能把周子原本的理學(xué)思想說清楚嗎? 時(shí)至明代結(jié)集《正統(tǒng)道藏》,其《上方大洞真元妙經(jīng)圖》中列一幅《太極先天之圖》。是圖本楊甲圖與朱熹圖演變而出。取楊甲圖外包橢圓之“陽(yáng)動(dòng)”置于“水”與“火”之間,又本楊甲圖分五層圖式。又取朱熹圖之“五行相生”,“水”繞過中“土”與“木”直接相連。此圖特意改動(dòng)之處有二:一是將“陰?kù)o”二字分開,“陰”字標(biāo)于二○之右,“靜”字標(biāo)于二○之左;一是將原三○左右之“乾道成男”與“坤道成女”提升標(biāo)至五行四象圖式之左右,將四○下方之“萬物化生“四字分開,“萬物”二字標(biāo)至三○之右,“化生”二字標(biāo)至三○之左。演變此圖的道士,自以為得計(jì)地認(rèn)為這樣一來就會(huì)合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殊不知周子原圖本義本與之有合,而妄加改動(dòng)者,卻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今日,有人以此圖見于《道藏》并有“唐明皇御制序”為理由而說此圖出于唐代,于是就據(jù)之而論曰周子《太極圖》源于道家,更有人進(jìn)一步論出周子的理學(xué)思想與道教有著一定的淵源關(guān)系。究其病根,皆在于對(duì)宋代易圖的流變沒進(jìn)行過專門研究的結(jié)果。我們說周子《太極圖》的模式與《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有合,但明確提出《太極圖》是周子為了講明“《易》之體”而作的“佐以文字”之圖。須知,北宋五子都不諱言《老子》、《莊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講的是宇宙生成論,是大自然自組織的學(xué)說,是質(zhì)變化生萬物的學(xué)說。北宋的邵子、周子可不管誰是什么家,誰說的有理就用誰的學(xué)說。今日之人還持“門戶之見”,駭可怪也! 四 李廷之《卦變圖》的流變 朱震《周易圖》列有李廷之《變卦反對(duì)圖》與《六十四卦相生圖》兩幅卦變圖。《變卦反對(duì)圖》以乾坤為祖而“變卦”,《六十四卦相生圖》則以六辟卦的“直變”或“復(fù)變”而得其余卦。 時(shí)至南宋,朱熹篤信邵雍《先天圖》傳于李廷之之說,力圖從李氏“卦變圖”中推出所謂的“先天卦變”。我們考察《周易本義》卷首《卦變圖》可知,其下卦的排列順序,就是力圖遵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其實(shí),邵雍的《先天圖》,雖然以乾或坤為卦變之祖,但是并不以辟卦為“變母”,而是以“加一倍法”自乾或坤的上爻變起。邵雍曰“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卦成,四變而十有六,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矣”(《觀物外篇》),就是講的這種逆爻序的卦變之法。一變乾上爻得夬,是為“一變而二”;二變乾、夬五爻得大有、大壯,是為“二變而四”;三變乾至大壯之四爻得小畜、需、大畜、泰,是為“三變而八”;四變乾至泰之三爻得履至臨,是為“四變而十有六”;五變乾至臨之二爻得同人至復(fù),是為“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乾至復(fù)之初爻得姤至坤,是為“六變而六十四卦備”(同樣可以坤為祖如此變卦)。邵雍的這種逆爻序卦變方法,屬于個(gè)人獨(dú)創(chuàng),其以乾或坤為變祖的思維,除來自《易傳》外,也可以說與李廷之《變卦反對(duì)圖》以乾坤為變祖的思維有關(guān),僅此而已。而朱熹不明白邵雍這一獨(dú)特的卦變之法,僅是本李廷之《六十四卦相生圖》以辟卦為“變母”推敲“先天卦變”,其結(jié)果只能是南轅北轍。 時(shí)至宋末元初,俞琰仍篤信朱熹《卦變圖》為“先天卦變”,并作出《先天六十四卦直圖》(見《易外別傳》)。是圖以《否》、《泰》所變得卦之下體之序?yàn)椋呵瑑秲秲峨x離離震震震巽巽巽坎坎坎艮艮艮坤。如此所謂“先天卦變”與邵雍《先天圖》內(nèi)方圖下卦之序還是大有區(qū)別的。邵雍《先天圖》方圖下卦之序?yàn)椋呵瑑峨x震巽坎艮坤,而且賦予了“物必順成”的八數(shù)。試看:“乾兌兌兌離離離震震震巽巽巽坎坎坎艮艮艮坤”之序,將如何賦予八數(shù)? 從朱熹、俞琰力圖從李廷之《六十四卦相生圖》推出邵雍“先天卦變”的失敗努力中,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先天圖》是邵雍獨(dú)創(chuàng)的,并非傳自李廷之,更不能遑論來自陳摶了。 結(jié)語 研究宋代易圖的流變,是研究宋明理學(xué)的前提。如果對(duì)宋代易圖的流變情況把握不準(zhǔn),就不可能把宋明理學(xué)的發(fā)展態(tài)勢(shì)闡述明白。我們注意到,之所以一些國(guó)學(xué)大家在闡述宋明理學(xué)時(shí)出現(xiàn)相互矛盾的現(xiàn)象,就是因?yàn)閷?duì)宋代易圖的流變情況有所不明。近年來,北京大學(xué) 陳少峰 先生在闡述宋明理學(xué)時(shí)明確指出:“許多綜合研究并沒有吸收專題研究的成果┄┄理學(xué)整體研究的新進(jìn)展,必須是在專門領(lǐng)域的深入研究之后,集專門研究之大成。”(見《宋明理學(xué)與道家哲學(xué)》)可謂慧眼識(shí)得問題癥結(jié)之所在。 誠(chéng)然,搞易圖學(xué)專門研究的人似乎不能系統(tǒng)地而且長(zhǎng)篇大論地闡述“宋明理學(xué)”,但是卻能以易圖學(xué)的專門研究成果去國(guó)學(xué)大師們的著作中“挑刺兒”。譬如,民國(guó)以來有關(guān)闡述“宋明理學(xué)”的書或論文中,凡涉及宋代易圖淵源問題時(shí),皆謂宋代“三大易圖”來自道士陳摶,皆把朱熹的爻畫“加一倍法”當(dāng)作邵雍之法。《河圖》《洛書》、《先天圖》、《太極圖》的原圖面貌如何?“三大易圖”果真?zhèn)髯躁悡粏幔可塾赫嬲囊讛?shù)“加一倍法”究竟是什么內(nèi)容?等等,筆者闡述宋代易圖的流變,就是要試圖回答這些問題(對(duì)象明確,有關(guān)的易圖就沒有必要再一一羅列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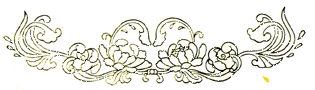
版權(quán)所有 北京國(guó)學(xué)時(shí)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 2000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