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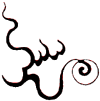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
|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與王學之流變 第四節王畿——三教合一與士人心態的新變化 三、王畿的人生實踐與人格心態 王畿的心學以其自然良知與不顧世俗毀譽的超越精神而著稱于世,這 既是其人生經歷的結晶,也是其對時代的回應,當然他也想將此種理論反 過來用于指導自己的人生實踐。然而,人生理論與人生實踐能否求得一致, 非但要視當事人的真誠程度而定,更重要的還要看歷史環境是否給他提供 了合適的機遇。從歷史上看,完全將自己的人生理論付諸實踐者幾乎沒有。 王畿雖不缺乏真誠,但他的理論卻遇到了現實人生的挑戰,因而不得不隨 著現實境遇的改變而矯正其人生的價值取向,可以說王畿的人格心態乃是 其人格理論與其人生實踐的綜合產物。換言之,他主張入世與出世二者并 舉的雙向人生價值取向,在其人生實踐中不得不發生一定的傾斜,更多地 表現為自我超越與自我適意的人生現實。 王畿人生理論所遇到的最嚴峻的挑戰當然是來自于官場。當他邁開仕 途的第一步時,便毫不猶豫地將其真誠的態度付之于實踐。他在關系到終 生命運的科考中,竟然“直寫己見,不數數顧程式。”而且此次竟然遇上 了“有識者”,將其“拔置高等”。(徐階《龍溪王先生傳》,見《王龍溪 先生全集》附錄)但是遺憾的是現實沒有再給他第二次這樣的機會。在接下 來的官場生涯中,他的理論與人格遭遇到了兩方面的挫折:一是其耿直獨 立的人格難以被權貴及復雜的人事關系所容納。李贄《續焚書》記載:“ (王畿)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宮僚,其婿吳儀制春,公門生也,首 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為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 ‘補宮僚而求之,非所愿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卻耶?若負道 學名,視我為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卷二二,《郎中王公》) 最后終于尋找機會將其罷官了事。王畿的失誤在于用自己的正直顯示了權 貴與其他官員的結黨營私,所以也就難以在官場中繼續存在下去。二是他 那通達圓融的人生價值取向難以被環境接受。王畿希望既照顧到士人的基 本情感欲望,又不違背應具的名節,因而無論對自身還是對他人均持寬容 的態度。《明史》本傳記載說:“畿嘗云:‘學當致知見性而已,應事有小 過不足累。’故在官弗免干請,以不謹斥。”(卷二八三,《王畿傳》)王 畿是否說過這些話今已不可考,但他的確是因“不謹”的罪名被罷職的,而 且將龍溪置于察典的竟是同門王學弟子薛應旂。盡管有許多人認為薛氏此 舉是為逢迎權相,甚至“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但黃宗羲在為 薛氏立傳時卻依然指出:“其實龍溪行不掩言,先生蓋借龍溪以正學術 也。”(《明儒學案》卷二五)可知黃氏也是承認王畿的以“不謹斥”是并 不冤枉的。此外,從當時唐順之給王畿的一封書信中,也證明他確有干請 之舉,該信曰:“世人之不能疑于吾輩也久矣。近有士大夫自浙中來者, 云及吾兄以佃寺之故,使憲司有言,且云兄以寺地據風水之勝,欲作令先 大夫墓地,上官某人者既予之矣,而憲使持之,故若此紛紛也。仆聞而竊 嘆,以為兄安得有此?……仆竊觀于兄矣,惟兄篤于自信,是故不為形跡 之防;以包荒為大,是故無凈穢之擇;以忠厚善世不私其身,是故或與人 同過不求自異。此兄之所以深信深慕于相知者,亦所以生微疑于不相知者 也。”(《荊川先生文集》卷四,《與王龍溪主事書》)“主事”即南職方 主事,是王畿初入仕途時所任職務。“兄安得有此”只不過是一句表示委婉 的面子話,否則不必說下面的“不為形跡之防”、“無凈穢之擇”的責備語。 因為這足以說明王畿干請之舉確為事實。其實,王畿本人并未將此視為什 么大不了的污點,以他的人生價值取向講,只要于大節無損,不必處處做 形跡之防,他曾說:“君子處世貴于有容,不可太生揀擇。天有晝夜,地 有險易,人有君子小人,物有麒麟鳳凰虎狼蛇蝎,不如是無以成并生之功。 只如一身清濁并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浞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王龍溪先生全集》卷三,《水西精舍會語》)王畿的話當然沒有錯,當時 的官場干請納賄已是普遍的現象,此種現象甚至連世宗都已予以默許,程朱 理學過于嚴苛的禁欲理論顯然已不能有效地限制士人,那么提出一種更為富 于彈性的通達理論也就勢所難免。然而,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尤其是在 官場中,盡管貪污受賄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但你只能心照不宣,卻不能 公然承認,以致形成了誰都心明如鏡,卻誰都不能說出,大家明知都在虛 偽地活著,卻又心甘情愿地接受這虛偽,如果誰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將此 事實和盤托出,那他便會理所當然地被群體所唾棄。在這方面,起來反對 的不僅是蠅營狗茍的政客,還有那一大幫道德理想主義者。后來袁宏道抱 著理解的態度對此評價說:“龍溪、近溪非真有遺行掛清議,只為他鍛煉 甚久,真見得圣人與凡人一般,故不為過高好奇之行。世人遂病之云:‘彼 既學道,如何情景與我輩相似?’因訾議之。久之即以下流歸之耳。若使 二公不學道,世人決不議論他。蓋眾人以異常望二公,二公惟以平常自處。 故孔子曰:‘道不遠人。’”(袁宏道《珊瑚林》下)身處晚明的袁中郎的 確是夠通達的,但嘉靖官場中的士人們卻不具備這份通達。故而龍溪先生的 “以平常自處”,便只能使貪濁者以為攻訐之口實,道德理想主義者視之 為敗行。王畿的尷尬境遇在于,他既要堅持自我的節操,又要承認現存的 人性事實,他的官場失敗命運也就不可避免了。王畿的獲罪其實主要不在 于其具有“干請”的事實,而在于他以圣學講求者的身份卻不免干請,更 在于他說出了這干請的事實。丟官的打擊對王畿來說也許并不是毀滅性 的,但卻足以改變其一生的人生道路,依他的本愿,儒者的第一選擇理所 當然地應該是出仕,所以他說:“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出與處而已。出則 發為經綸,思行其所學以兼善天下;處則蘊為康濟,思善其身以先細民。 未嘗無所事事,若惟借冠裳假面貌輕肥蕩恣,役役終身,甘與草木同朽腐, 名為士流,實則凡夫之不如也,可恥孰甚焉。”(《王龍溪先生全集》卷十 五,《云間樂聚冊后語》)丟官的結果是他再也沒有發為經綸而兼善天下的 可能,這意味著他必須別無選擇地接受“思善其身以先細民”的事實,除 非他“甘與草木同朽腐”。這是王畿對其人生理想作出的重大調整,也是 迫不得已的調整。 然而,如何實現其“蘊為康濟”的人生理想,也還是要經過一番認真 思考的,因為在充滿瑣屑庸常事務的鄉居野處中,并不是很容易便可轟轟 烈烈的,否則那些欲展現才能抱負的士人就不必紛紛地擠向仕途,爭相將 自身貨與帝王家了。王畿最終的選擇是講學明道,在他的心目中,這或許 是唯一可能的選擇。從其個人特長講,他具有上佳的口才,又有在陽明門 下做教授師的閱歷,能力是決無問題的,何良俊曾說:“陽明先生之學, 今遍行宇內,其門弟子甚眾,都好講學,然皆粘帶纏繞,不能脫灑,故于 人意見無所發明。獨王龍溪之言,玲瓏透徹,令人極有感動處。余未嘗與 之交,不知其力行如何,若論其辯才無礙,真得陽明牙后慧者也。”(《四 友齋叢說》卷四)可知龍溪先生的辯才當時是出了名的。從其個人愿望上 講,講學乃是其不容已的責任。他曾如此表示自己的人生愿望:“不肖百 念已灰,而耿耿于心,不能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游, 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一脈。”此可稱之為報師門之恩,則非講 學無以實現之。同時,“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圣學脈,賴以復續。不肖 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自己“若 復秘而不傳,后將復悔”。所以必須講學,此可稱之為傳圣學。當然,在 完成報師門與傳圣學這“不能自已”的個人志愿后,也就實現了他“康濟” 的萬物一體之責。這是王畿講學的重要心理動機之一,也是王艮、顏鈞、 何心隱、羅汝芳們講學的重要心理動機之一,更是中晚明講學之風大盛的 重要原因之一,士人既然無法在仕途中實現自我濟世的人生理想,而又不 甘于默默老死草野間,他們便不能不選擇講學之一途。 既然說報師門與傳圣學是王畿講學的重要心理動機之一,也就意味著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重要動機。尤其是王畿在“百念已灰”的境遇中,他 不可能只想著“康濟”的責任而不考慮如何安頓其人生自我,于是我們看 到了王畿的另一面,一個追求個體解脫與自我適意的龍溪先生,他曾在另 一處談及其出游講學的原因說:“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仆相 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才離家出游, 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 晨夕聚處,專干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 入,精神自然專一,意思自然沖和,教學相長,欲究極自己性命,不得不 與同志相切劘相觀法。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眾中自 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為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 生。”(同上卷五,《致知議略》)他渴望超越家庭親朋的世俗關系之網, 在漫游中自由無拘的講學,“究極自己性命”。從世俗的觀點看,一個儒者 應先齊家而后方可治國平天下,這乃是《大學》中所明講的,如今龍溪要跨 過家族此一層面而與同志相與講學,是否意味著放棄了自己應負的人生責 任呢?其實也不盡然,且不說孔子周游列國以講學游說已早有先例,即使 在明代也有以講學為使命、以朋友為性命的何心隱,但他仍是一位濟世熱 情甚高的儒者。從王畿的初衷而言,他的出游講學與何心隱具有相近的目 的,所以才會說:“不肖冒暑出游,豈徒發興了當人事,亦頗見得一體痛 癢相關,欲人人共證此事。”(同上卷十六,《萬履庵漫語》)然而若從另 一角度看,龍溪不顧家族利益而只欲成就自我之出世大豪杰聲譽,是否也有 一些自我解脫的意味?比如后來的李贄,他為了斷絕與家族的來往,便將 頭發剃去,并聲稱其學為自私自利之學,只為了悟自己性命,不管他人非 議,而他恰恰是王畿的崇拜者,在他們的出游講學的目的之間,有無一定 的聯系呢?這很難說。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擺脫家族親朋的 關系網絡后,在與朋友無所顧忌的交往中,在與自然山水相親融的過程中, 的確能夠開闊心胸,增加情趣,提升自我的人生境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 改變其人生的價值取向。對此王畿是頗有心得的,他說:“素性好游,轍 跡幾半天下,凡名山幽怪奇勝之區,世之人有終身羨慕思至而不可得者, 予皆得遍探熟游。童冠追從,笑歌偃仰,悠然舞雩之興,樂而忘返,是雖 志于得朋,不在山水之間,不可不謂之清福。”(同上卷十五,《自訟長語 示兒輩》)在此,山水奇勝的審美享受,笑歌偃仰的生活樂趣,都毫無保 留地流露在龍溪先生的字里行間,盡管他在此處所言的“樂而忘返”中所 忘的不是圣學,但他卻很容易將圣學與樂聯系起來。果然,當有人問起“夫 子與點之意時”,王畿便興致勃勃地予以詳盡解說:“天下事不吃人執定做 得,必須淡然超然,若一毫無意于天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寶,得于無 心;赤水之珠,索于象罔。故運甕者在甕外,以無用為用也。三子皆欲得 國而治,未免執定做去。曾點卻似個沒要緊的人,當三子言志時且去鼓瑟, 眼若無人。及至夫子問他,卻舍瑟而對,說出一番無意味話。時值暮春, 春服始成,三三兩兩,浴沂雩泳,其日用之常一毫無所顧忌,狂態宛然。 若是伊川見之,必在所擯斥,夫子反喟然嘆而與之,何異說夢?觀其應用 之跡,未嘗有意為三子而三子規模隱然俱于其中,且將超于政教禮樂之外。 春服熙熙即唐虞垂衣之治;童冠追隨,即百僚師讓之化;舞雩風詠,即明 良庚歌之氣象。易地皆然,此千古經綸手段,所謂以無用為用也。”(同上 卷七,《華陽明倫堂會語》)依王畿之見,則政治之最高境界,在于天下同 歸于和樂,如曾點所理想者,浴風沐雨,童冠追隨,一派從容和樂景象。 但此種景象在歷史上是否真正存在過實在無法驗證,即使真的有過,也已 然成為遙遠的過去,成為永遠難以重復的夢想。如此美夢堯夫先生做過, 白沙先生也做過,現在該輪到龍溪先生做了。但正由于這景象只能成為夢 想,也就對現實政治無絲毫的補益。因而龍溪所言的“以無用為用”,到 頭來便真的只能歸于無用,充其量只能升華為一種具有審美性質的人生理 想了。 然而,在王畿這里,曾點之樂決不僅僅限于美好的理想,他更想將其 落實在自己的人生實踐中。“道人自戴華陽巾,滿目鶯花入暮春。坐對鷗 鳧機自少,步隨童冠道還真。江空不礙龍成窟,地僻何妨樹作鄰。悵望舞 雩千古夢,猶疑風詠未傳神。”(同上卷十八,《暮春登北固山用韻示諸 友》)時間也是暮春,也有童冠追隨,有山有水,自然也就不缺乏浴風沐 雨之條件。然而,這戴著華陽巾的龍溪先生能有欣賞太平景象的心情嗎? 他穿上春服難道就是“唐虞垂裳之治”?他有童冠追隨,難道就代表了“百 僚師讓之化”?他也能浴風沐雨,難道就成了“明良庚歌之氣象”?他當 然知道不是,所以才對著這“舞雩”的千古之夢而“悵望”,才懷疑自己 的“風詠”是否能傳曾點之神。盡管如此,這個夢依然時時縈繞在王畿的 心頭,使他不斷吟詠出曾點之樂的詩句:“行歌郊外寺,亦復舞雩風。” (同上卷十八,《永慶寺次荊川韻》)“浮世已回蕉鹿夢,清溪不減舞雩 春。”(同上,《用韻酬王巖潭年兄》)“幾回東頂看明月,又向西林歌暮 春。”(《用韻酬涂罈江學博》)“千古舞雩傳圣事,西津童冠即東沂。” (同上,《西津白云寺留別諸生》)無論他重復多少次,夢畢竟是夢,永遠 變不成現實,因而他的樂也就不是理想中的曾點之樂,而只能是現實中的王 畿之樂。這兩種樂最大的區別在于:他理想中的曾點之樂是建立在政治太平 之上的從容之樂,而他現實中的樂是與現實政治相分離的樂。試看:“時事 紛紛渾不定,未妨抱膝樂天吟。”(同上,《和王西野闿陽別業韻四首》其 四)“人間榮辱無拘管,萬頃風煙一杯酒。”(同上,《賀南渠年兄眾樂園 之作四首》其二)“更說黃山堪避地,還期一笑白云邊。”(同上,《訪胡 屏山話舊》)是由于時事的無定方才歸隱抱膝而樂,這如何能夠樂得從容? 超越了人間的拘管而與自然合一,當然是一種心靈的享受,可人間的拘管畢 竟難以徹底忘卻;因而黃山也就只能成為逃避現實的棲隱之地,則這白云 邊的笑便不能不掛上一絲無奈的苦澀。此種心態在《送荊川赴召用韻》一 詩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詩曰:“與君卅載臥云林,忽報征書思不禁。學 道古應來眾笑,出山終是負初心。青春照眼行偏好,黃鳥求朋意獨深。默 默囊琴且歸去,古來流水幾知音。”(同上)荊川的出山是被朝廷所征召, 是要去濟世救民,盡管說不上致君堯舜,起碼也想力挽狂瀾,對此甚至連 一向歸寂的念庵先生也不曾表示異議,可講究出世與入世兼顧的龍溪先 生,竟然說他的出山有負“初心”,在其默默囊琴而歸去的動作中,我們 看到了他失望中的孤獨;而在“古來流水幾知音”的嘆息中,我們又感受 到了對唐順之的些許責備之意。而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王畿對現實的失 望與疏離,在如此的心境下,他如何能寫出理想中的曾點之樂呢?于是, 他不得不更現實一點地吟出如下詩句:“梧桐露冷荷衣薄,無復春風舍瑟 時。”(同上,《次久庵中秋洗心亭玩月韻三首》其三)此時的情景非但已 難與孔子時代相比,連當年陽明先生天泉橋上的和樂境界亦難以為繼,于 是王畿便不能不呈現出一副凄涼的心境。由此使我們感受到了,王畿的樂 是一種個體自我適意之樂,這種樂以超越現實為前提,所謂“朝披半蓑煙, 夕弄一竿水。浩氣凌萬乘,紛紛寧有此。”(同上,《秋日登釣臺次陽明先 師韻二首》其一)他那沖天的浩氣是在超越了紛紛世俗的自我精神世界里 獲得的,“凌萬乘”也只能是一種主觀心理感覺,而落實到實踐的層面上 便只能是披蓑獨釣的自我之樂。因而很顯然,實現此樂的途徑也只能是內 外兩忘的自我之悟,所謂“青山寂無言,至樂云在此。無古亦無今,忘物 亦忘己。”(同上,其二)實在是莊子至人真人的最生動體現,所以王畿有 時也就不客氣地以“道人”而自居了,他有兩首類似禪家偈語的詩,其詩 前小序說:“八山居士閉關云門之麓,玉芝上人往扣以偈相酬答,時龍溪 道人偕浮峰子叔學生訪上人于龍南山居,語次出以相示,即席口占數語呈 八山與玉芝共參之。”此時他不僅以“道人”自稱,而且與道人相參,可 見已深深沉浸在追求自我解脫的道家氛圍之中。再看其詩之內容:“魔佛 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若于見處能忘見,三界縱橫乃爾何?”“禪 家但愿空諸有,孔氏單傳只屢空。儒佛同歸較些子,翠屏山色自穹隆。” (同上)前一首言成佛之要在于不起心,而不起心的關鍵在于能忘,只有 忘了方可縱橫自在;后一首則將禪儒同歸于一空,對此不必深較,而最終 只要均達到如翠屏山色那般自然自在,便是人生實在受用。然而,現在要 追問的是,王畿的認同佛道到底是一時的逢場作戲呢,還是一種認真的價 值選擇?我以為他初始只是一時用來擺脫自我的精神苦悶,而到了其生命 的后期,則將其當作了生命的寄托。他在萬歷五年時曾對查鐸說:“我每 乘月起坐,自試問心,眼前有許多玩好珍美妻子童仆,可割舍而去否?但 亦無甚眷戀,可以逝即長逝矣。”果然,到了萬歷十一年六月初七日病革 之際,龍溪先生“早晨盥櫛,冠唐巾,食粥,從容出寢室,端坐于琴堂之 臥榻而逝。”他的確做到了無所牽掛地從容而逝,故而查鐸贊嘆說:“今觀 臨革之際,先生氣息奄奄,心神了了如此,自非能超脫死生者,孰能與于 斯?夫子謂朝聞夕死可,惟先生云云。”(查鐸《紀龍溪先生終事》見《明 文海》卷三四七)但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王畿所獲的超越生死之道果 然是儒家之道嗎?答案顯然應該是否定的。他最終得到的還是自我生命的 解脫,其價值取向仍在向著佛道作出極大地傾斜。 從王陽明到羅洪先再到王畿,從他們的本意講,都是想通過對圣學的 悟解與講論而改變士風,并通過改變士風從而改變現實政治狀況的;最起 碼他們也想使自我的人生價值取向定位在濟世與自適的兼顧層面上,但是 令人遺憾的是,他們都未能如愿,而且越到后來越向著自我適意的一端傾 斜。這種傾斜是不情愿的甚至是不自覺的,然而卻又是無可奈何的甚至是 不可逆轉的。這種自我解脫、自我適意的求樂傾向如細細的春雨,形跡朦 朧,潤物無聲,但由多方滲透,無處不在,從士人的日常生活,興趣愛好, 詩文創作,文學思想諸方面時不時地體現出來。從文學思想上看,王陽明 已有追求自我受用的傾向,而到了嘉靖中后期,這種傾向便在更多士人身 上表現出來,羅洪先如此,王襞如此,甚至連權相嚴嵩也受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當然在王畿身上便更明顯了,盡管他在不少場合想盡量往經國治世 方面靠攏,但落腳點又總是在自我超越的人生受用上,比如他為邵雍的《擊 壤集》作序,一開始說:“康節之學,洗滌心源,得諸靜養,窮天地始終 之變,究古今治亂之原,以經世為治,觀于物有以自得也。”眼光集中在 “治亂”與“經世”上。但一旦談起康節之創作,便說:“于是本諸性情 而發之于詩,玩弄天地,闔辟古今,皇王帝伯之鋪張,雪月風花之品題, 自謂名教之樂異于世人之樂,況于觀物之樂又有萬萬者焉。死生榮辱輾轉 于前,曾未入乎胸中,雖曰吟詠性情,曾何累哉?其所自得者深矣。”在 此,“皇王帝伯之鋪張”已成了陪襯,主題轉到了自得之樂,不僅有名教 之樂,更有觀物之樂,而樂之前提又在于死生未入乎胸中的超然境界,這 顯然已在向自我移位。再接下去總結詩之創作規律時便走得更遠了:“予 觀晉魏唐宋諸家,如阮步兵、陶靖節、王右丞、韋蘇州、黃山谷、陳后山 諸人,述作相望,雖所養不同,要皆有得于靜中沖淡和平之趣,不以外物 撓己,故其詩亦皆足以鳴世。竊怪少陵作詩反以為苦,異乎無名公之樂而無 所累,又將奚取焉。”(同上卷十三,《擊壤集序》)他所贊賞的全是超然 于現實之外而自得其樂的自然山水派詩人,所關注的也是“不以外物撓己” 的沖淡和平之趣,從中可明顯看出龍溪本人的價值選擇。尤其是他對杜甫 的態度更須留意,這位一向以憂國憂民而出名的詩圣,到了王畿眼中,卻 由于未達到“樂而無所累”的境界,而不為其所取,則他原來“治亂”、 “經國”的觀點不知跑到何處去了?如果不從其人生價值取向的深層轉變 上著眼,便很難解釋他這種前后不一致的態度。這種并不情愿卻又不得不 轉變其價值取向的情形,固然說明了士人在面對殘酷的現實生存環境時的 無奈,讓我們認識到了士人心態轉變過程的曲折復雜,但更重要的是它將 對后來萬歷士人的人生價值選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