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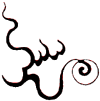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
|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與王學之流變 第三節羅洪先——歸寂與自保的代表 二、“徹悟仁體”與羅洪先的晚年心態 黃宗羲將念庵學術的第三階段概括為“徹悟仁體”,這當然是有道理 的,因為有大量的羅氏原話可作為證明。但究竟如何理解此“徹悟仁體” 的內涵,便成了重要的問題。前人對該問題研究的并不是很充分,曾作出 過明確解答的是侯外廬諸先生所撰的《宋明理學史》,他們認為羅氏所言 之仁即萬物一體之仁,而萬物一體之仁的內涵又是以天下為己任,并具體 解釋說:“羅洪先的‘仁體’說的主旨則在于以天弘人,讓人從天上回到 人間,因而具有‘入世’、‘用世’的思想特點。”(見該書下冊第326頁) 如此闡釋羅洪先的“徹悟仁體”,即使不是完全的誤讀本文,起碼也是作 了極其狹隘的理解。因為所謂的“以天下為己任”、“入世”、“用世”等 提法與羅氏本人晚年的人格心態幾乎完全對不上號。幾種羅洪先的傳記幾乎 都提到了他晚年的出世意識,如:《明史》言其晚年“嚴嵩以同鄉故,擬 假邊才起用,皆力辭。”(卷二八三,《羅洪先傳》)《明儒學案》曰: “三十七年,嚴相嵩起唐順之為兵部主事,次及先生。先生以舉志林壑報 之。”(卷十八,《羅洪先傳》)李贄《續藏書》曰:“年垂五十,觀時事 日非,乃絕意仕進。”(卷二二,《光祿少卿羅文恭公》)錢謙益《列朝詩 集小傳》曰:“達夫罷官后,杜門講學,攻苦淡,煉寒暑,彎弓躍馬,考圖 觀史,以經世為己任。年垂五十,絕意仕進,默坐半榻,不出戶者三年。” (丁集上,《羅贊善洪先》)很難設想,一位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在國家 處于危難之中而他又有機會重入仕途時,會如此堅決地拒絕出仕。假如說是 由于避嚴嵩之惡名而欲自潔其身,那么其好友唐順之何以會毅然出山。還有 心學的開山大師陽明先生,也是無論在任何險惡的境遇中,都抱著“用之則 行舍即休”的濟世精神,以致最終病逝于征討途中。如果說上述材料尚不 足以作為充分證據的話,還有羅氏本人的詩作可為例證,如其《稱拙》詩 曰:“我從盛年來,常憂行及老。取友歷險難,所志在聞道。一日復一日, 如饑望得飽。外為名所驅,內苦意不了。蹉跎五十馀,坐令顏色槁。齒發 日變衰,智慮始欲掃。回首憶盛年,空負筋力好。偃形向巖扉,束書置窮 討。冥心聞斗蟻,縱目對飛鳥。身安忘卑高,分足任多少。聊稱拙者心, 得此悔不早。”(《念庵文集》卷十九)“五十馀”可稱之為晚年了吧,然 而他所深悔者,乃是年輕時“外為名所驅,內苦意不了”的汲汲進取之舉, 而所向往者是束書偃臥的寧靜生涯,是聞斗蟻、觀飛鳥的悠然自在,是知 足常樂的隨遇而安,你能相信這便是以天下為己任、用世與入世之心甚強 的念庵先生所寫的詩作?并且還不是其系一時興之所致的寫景抒情小詩, 而是深思熟慮的五古長篇。若證之以錢謙益的“五十絕意仕進,默坐半榻, 不出戶者三年”的記載,就更可視為是其五十后相當穩定的人生志趣了。 如果說對其學術思想的研究結果與其人生志趣大相徑庭,難道不應該懷疑 這結論的是否合乎研究對象的實際情形? 《宋明理學史》的作者當然是言之有據的,他引用了下面一段材料來 支撐自己的觀點:“近來見得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為己任。不論出與處, 莫不皆然。真以天下為己任者,即分毫躲閃不得,亦分毫牽系不得。…… 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亦是此胚胎。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為天地立心、 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內,此方是仁體。孔門開口叫人從此立根 腳。……《西銘》一篇,稍盡此體段。”(《念庵文集》卷二,《寄尹道 與》)對于明代中后期士人來說,張載的《西銘》及王陽明的《傳習錄》都 應是非常熟悉的著作,尤其對王門后學就更應是如此,而萬物一體之仁也是 儒者常言之話題,關鍵要看是誰在講以及講話者的具體語言環境是什么,方 可判斷出言說者的真實意圖。念庵此番言語當然并非言不由衷,但我以為 他主要是從談話對象身上著眼的。如今雖一時尚難徹底弄清念庵與尹道與 之關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尹氏是一位尚未取得功名并正在努力爭取的儒 生,而不是象念庵這樣已歷經磨難的過來人。羅洪先有一首《送尹道與會 試》詩曰:“經綸自屬吾儒事,溫飽何嘗慮見侵。況是義方同尹母,可無 善養似曾參。萬言為試陳王道,一飯應知待士心。但得廟堂多爾輩,豈妨 枯槁臥山林。”(同上卷二二)當他說“經綸自是吾儒事”時,此“吾”乃 復數之大我,猶“吾等”之意,而具體所指乃系被贈詩之尹道與,念庵以 忠孝激勵之,以期得到君臣和諧之結果。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本人也有出山 之念頭,因為他在詩之結尾處分明說,只要朝廷之上多有正人君子如爾等, 那我即使退臥山林以隱居又有何妨呢?大約在一年之后,念庵又有《重登 海天樓有懷王龍溪尹道與》詩曰:“高閣憑闌思惘然,舊游回首又經年。 山陰留滯歸舟后,薊北飄飖去雁邊。樹影乍疑風侍側,江流猶見道參前。 風塵已覺閑人少,得共閑時信有緣。”(同上)此刻,王畿遠在山陰,而尹 道與則已去薊北求取功名,于是念庵感到了孤獨,仿佛身邊樹影都成了朋 友的身形,其思念之情自可想見。他感嘆如今閑適者的日見其少,于是更 珍惜從前那一段共同優游閑適的美好時光。如果根據這首詩,是否可以得 出羅洪先不愿讓尹道與出仕而與自己共隱山林的結論呢?顯然不能,因為 這也是孤證,不能由此推出念庵的整個人生價值取向與學術思想。既然此 詩不能,則《宋明理學史》引述的那封并不完整的信照樣也不能。我以為, 念庵的真實思想應是,他并不反對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態度,所以他也不 反對尹道與科舉入仕的追求;但由于自身的種種具體情形與對時局的考 慮,他本人并不想重新入仕,也就是說,他本人此時以天下為己任的“出 世”、“用世”思想并不強烈,甚至可以說相當淡漠。因此,也就有必要來 重新闡釋念庵“萬物一體之仁”的確切涵意及其所體現的人生價值取向了。 要闡釋其“萬物一體之仁”,必須首先弄清念庵絕意仕進的真實原因, 李贄所講“見時事日非”當然是不錯的,可惜語焉不詳。其實,念庵在給 朋友的信中,有過相當具體的心跡坦露。他在《寄聶雙江》(《明文海》 卷一九五)中,曾專門論及其堅不出山之原因,約而言之有三:一是懼禍: “昨得書歸語之婦已,曰:‘不做吧,無若往年被罪恐嚇人也。’嗚呼!婦 人之見何遽至此哉!”可見他是認可其夫人的見解的。二是自身有四種不 宜出山的特性:“顧其所不能者有四:學問空疏,高之不能善世利物;性 氣悻直,卑之不能諧俗同人;識見淺陋,內之不能追陪贄御;筋力綿縱, 外之不能效死封疆。”三是人生志趣之相異。他曾對唐順之曰:“兄不可不 出,吾則終老山林。”而他在信中解釋其終老山林之原因說:“長林邃谷, 一介不通;瞑目委形,百念皆弛。考其言,無一編之書;責其實,無尺寸 之效。泯泯默默,以還造化。豈于性分有歉乎哉?”就是說即使不出山效 命于朝廷,也并不會對自身之性情有分毫損害。可知他已抱定自我完善的 志向。應該說,荊川先生的急于用世與念庵先生的堅不出仕,各自代表了 王學的一個側面。然而,盡管羅氏與聶氏同為王門學者且又同主歸寂,但 因聶氏當時已為朝廷官員,故念庵信中便多有保留而不肯傾心相訴。在其 《與王堯衢書》(同上)中,面對此位更加親近的朋友,他講出了一番發 自肺腑的真心話: 當今之士隱居獨學,修名砥節,如湖州唐子,平涼趙子輩者,凡若干。 仆之駑駘,十不及其二三。然此輩皆淪胥流落,淹滯已十數年,少者壯, 壯者且老以衰,或餒凍無以存活。又其初皆以盡力國事,誤觸網而抵禁, 非如仆之自以私罪去也。此輩尚不得為當事者所與,則仆得與此輩同陸沉 焉,固無憾也,更何有所覬乎!凡人出處利鈍,數固不偶,始言官謬相薦 舉,仆固知終必且棄去,以為萬一不棄去,則仆之自為處亦有甚難者。何 也?若使仆復如舊時隨逐行隊,進退以旅,趑趄囁嚅,于明時無粟粒之補, 則將毀平生而弁髦之。且向惟不能為此,所以甘心去官而無所悔耳,不然 則柳士師所謂何去父母之鄉者也。若便不如此而如彼,守其愚憨固陋而不 變,恐日月漸久,積嫌積忤,自作禍孽,更有甚于向時。既不能為邯鄲之 步,竟當匍匐而歸耳。是以終夜思之,進退狼狽。乃今得自脫禍于此,固 可謂之幸,而不可謂之不幸也。 觀此羅氏之心態即昭然若揭矣。他的退隱,決非一時之沖動,而是深 思之結果。他知道,他所代表的不是自身一人,而是一批堅守氣節的士人 的共同命運。當與之同獲罪的正直士人皆“淪胥流落”時,他能夠與這些 士人“同陸沉”已是難得,更不應該有什么非分之想。因為多數正直士人 的淪落意味著朝廷的政治依然無公平可言,官場士風也無好轉之跡象,則 此時出山必歸于失敗狼狽便已在不言之中。此時出山,其處境之尷尬當一 如從前,要么默默無聞地隨波逐流,那不僅于事無任何補益,且有損自我 之氣節。當初自己離開官場之原因,不就是欲保持一己之氣節嗎?那今日 又何必再去貶損氣節呢?既然未出山時已知將來必然會終棄之,則今日又 何必要勉強出山呢?更何況象自身之為人,若再處官場還會帶來種種的禍 患呢?如此看來,今日的脫離官場已是人生之大幸,又何以會去重蹈禍機 呢?他很清楚,這不是一個正直士人立功揚名的時代,而是一個藏身自守 的時代,因為出則于事無補而于己有害,你唯一的選擇便是入山不出了。 然而,他的歸隱卻又有自身的特點,他不同于李夢陽、康海輩的狂飲高歌 以寄其郁悶憤激,也不同于楊慎、李開先輩的留連于倡優技藝以消其豪杰 之志,又不同于文征明、茅坤輩的寄情于詩文書畫,而是要“隱居獨學, 修名砥節”,用傳統的儒學術語講也就是隱則獨善其身。之所以能夠如此, 這得歸功于他對陽明心學的介入并在此基礎上所進行的自我體驗,從而具 有了人生的自信與平靜開放的心態,而支撐此種心態的便是下面要闡釋的 “萬物一體之仁”。 羅洪先曾在許多場合表示過此種“仁”之意識,《宋明理學史》曾引 用其《答蔣道林》(《念庵文集》卷四)的信以說明之,現引全文如下, 以作完整觀: 未幾入深山靜僻,絕人往來,每日塊坐一榻,更不展卷,如是者三越 月,而旋以病廢。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虛寂無物,貫通無窮,如氣之 行空,無有止極,無內外可止,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 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 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于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于吾聽,冥吾之心而 天地不逃于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之精神,未嘗往矣,否則聞 其行事而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遠矣, 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衋然矣乎!是故感于親而為親焉,吾無分于親也, 有分于吾與親斯不親矣;感于民而為仁焉,吾無分于民也,有分于吾與民 斯不仁矣。是乃得之于天者,固然如是,而后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 與萬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即在物,合吾與物同為一體,則前所 謂虛寂而能感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為一者也。故曰視不見, 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者也,與之為一體故也。 據《宋明理學史》作者考,此信作于嘉靖三十五年念庵五十三歲時, 故可作為論證其晚年徹悟仁體之材料。讀該信須先注意兩個問題:一是羅 氏晚年并未完全放棄其歸靜主張,而是歸靜說之深化,此處所談感受即從 其靜悟中得來;二是信中所談情狀全為“塊坐一榻”時的心理感受,而并 非欲在現實中真正實現之計劃安排。此猶如讀《莊子·逍遙游》,其中所 言景象均為作者內在超越之精神意象,若有人欲將其視為是莊周本人實有 乘風高舉之追求,則無疑于癡人之前說夢,誠為膠柱鼓瑟矣。本段文字充 其量說明了念庵由靜悟而帶來的精神世界的充實與廣大,即其所言“虛寂 而能感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為一者也”。如果將此文字與其 現實行動直接相聯,從而說明其出世或入世的人生價值取向,那是很危險 的。因為首先必須弄清作者寫作此信之目的,否則不宜將此作為論證材料。 在《明儒學案》中,黃宗羲也引用了此信,但與四庫本《念庵文集》略有 不同,在上引文字后尚有數句可供參考,其曰:“若二氏者有見于己,無 見于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于自賊其身者耳。諸儒辟二氏矣,猥瑣于 掃除防檢之勤,而迷謬于統體該括之大,安于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智 能而不適于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棲棲于一 室,身口是計,其堂奧未窺,積聚未復,終無逃于樊遲細民之譏,則亦何 以服二釋之心哉?”(卷十八)此仍是從胸襟處立意,佛道將己與物置于 對立的地位,故顯其小;而諸儒“猥瑣于防檢之勤”,亦足見其拘。而正 確的做法應是象明道先生所言,“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 (同上)從而達到“虛寂無物,貫通無窮”的境界。因而《答蔣道林》乃 是屬于討論學術方法與由此方法所獲得的精神境界的范疇,而與是否用世 無關。故而此所言“萬物一體之仁”與《寄尹道與》中所言“以天下為己 任”之用世,不屬同一層面的論題,不可渾而言之以說明念庵晚年之人生 態度。 士人之精神境界與其現實人生價值取向盡管并非同一層面之問題,但 又決非是互不相干的。比如“萬物一體”的仁之境界,既可以體現為陽明 鏟除禍患的現實政治操作,也可以體現為白沙觀物體仁的精神感悟。落實 在念庵身上也同樣如此,他晚年雖絕意仕進,但又不忘儒者仁民愛物之責, 《明史》本傳記其晚年曰:“歲饑,移書郡邑,得粟米數十擔,率友人躬 振給。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為畫策戰守,寇引去。”(卷二八三)在 《念庵文集》中,保存著一首為民請命的長詩,其詩前有小序曰:“南游赤 子,永豐賊自稱也。圍城四日,投書聶太保,訴言財盡民窮,救死不贍,不 得已而至此,且乞濟施。辭頗恭遜,余讀而感焉,作長謠憐之,亦因以風世 云。”此所言“投書聶太保”,可知聶豹此時已賦閑家居,聶氏于嘉靖三十 三年封太子太保,并于次年致仕回鄉,則此詩當作于嘉靖三十四年后無疑, 顯系念庵晚年。詩中指出當時情景為:“末代遞變遷,澆風散淳樸。公家 競侈靡,大姓工椎剝。”而身處其中的百姓,“迫脅不自聊,激發恣為虐。” 并替他們代言說:“倘免饑寒憂,肯棄畎畝樂?”(卷十九)念庵的用意當 然還是為了朝廷穩定,天下太平,而不希望百姓鋌而走險,但他認識到今 日“為虐”之徒皆昔日善良之民,只是由于身處“末代”,遭致大姓之“椎 剝”,弄得“財盡民貧,救死不贍”,方出此下策,如果能夠免去饑寒的威 脅,誰又愿拋棄太平安穩的生活?倘若對百姓缺乏“萬物一體”的關懷之 仁心,怎會講出如此體貼百姓的詩句來?因此,念庵“萬物一體之仁”的 真實涵意首先應是對民生疾苦的同情與關注,而不是急于“用世”的現實 行為。但更重要的是,此仁體還指與物無忤的渾融境界與和樂之心。他在 晚年曾告知王畿,自己前此的“收攝保聚偏矣”,如此則分“動靜為二”, 最終“必至重于為我,輕于應物”。而當他體悟到“萬物一體之仁”后, 便是另一種境界了,所謂“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 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盡斂之,則亦塊然不知,凝然不動,無一物之 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然在此,攸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這顯 然已接近陽明體用不分,即動即靜之自然良知了,故而王畿聽后說:“兄 已見破到此,弟復何言!”(《明儒學案》卷十八,《甲寅夏游記》)正是 有了如此的學術思想轉變,使得念庵晚年的人生情調向著自然和樂的境界提 升,具有了與當年曾點之樂相近似的人生樂趣,吟出了如下的詩句:“卻喜 舞雩歸來晚,春風多少柳條新。”(《念庵》卷二一,《贈黃洛村》)“竊 比舞雩吾所志,年年將奈暮春何。”(同上卷二二,《東郭先生貽連生書屋 落成詩次韻奉贈》)此種曾點之樂是念庵晚年所追求的主要人生境界,它 是與物我一體之仁緊密相連的,其《病起自警》一詩對此作出了很好的描 述:“五尺身軀一丈夫,百年事業竟何如?每思曾點三春樂,豈用康成萬 卷書?物我同觀從混俗,見聞俱泯似逃虛。古來豪杰幾先定,肯向迷途錯 駕車。”(同上)他不再象從前那樣廣讀博學以苦其身心,而要學曾點在春 風中舞詠而樂,物我渾一而無阻隔,但心中自有良知主持,而不同于是非 不分之鄉愿;泯去見聞而一任自然自得之情韻,形似逃虛而實有仁者萬物 一體之心。這是一種審美的人生,但并不以放棄儒家的人生責任為代價。 于是,在念庵晚年的作品中,就有了非常美的詩篇,其標志便是物我相融 的高超意境的存在,試觀以下數首:“桃花滿村郭,山雨鳴鳩鳥。柴門午始 開,苔蘚無人掃。”(同上卷二十,《山水四詠》其一)“曾伴淵明栗里間, 千年流落影闌珊。何知寂寞荒山里,亦有知心為破顏。”(同上,《十月黃 花滿庭把玩開顏遂有短句二首》其一)“春霽媚行游,春潮靜不流。衣薰疑 日近,棹動覺天浮。纚纚煙光合,絲絲柳色柔。江南風物美,大半在汀洲。” (同上卷二一,《晴日江上》)盡管它們全都是山水詩,其中沒有出現除 作者之外的其他人物,但詩作卻清而不空,充滿了生機與情趣,虛掩的 柴門,靜靜的苔蘚,卻被滿村的桃花與知情的鳥鳴賦予了生命的情調;而 那寂寞荒山中的菊花,本來是形影相吊,闌珊孤獨的,但有了知心的作者 為之破顏而笑,則立時透露出物與人的相互理解與愛憐;至于那向游人獻 媚的雨后晴空,那親近人衣的春天暖日,那水天一色的空明境界,那醉煙 中含情脈脈的絲絲柔柳,究竟是人因景而生欣喜之情,還是人之喜悅之情 賦予了景色以明麗格調,實在已難以分清,而只見其一片渾融和樂的境界。 此處所顯之仁乃是自然之生機,詩人之情趣,亦即《易》之所言生生不已 之宇宙精神。而這方是念庵晚年主要的生命情調。 然而,如果說念庵在晚年歸隱自適的生涯中保持了純粹的儒者情懷, 那也是不合乎實情的。在他歸寂的人生體悟中,在他物我一體的審美享受 中,在他極力擺脫“末世”現實的糾纏時,佛、道之意識往往乘虛而入, 在其心靈世界中占據了一定的位置。因為他要實現內在超越的心靈自由, 便不能不流露出“一見真我在,形骸豈足私”(同上,《老至》)的莊子 情韻。于是,他主張將儒釋道打成一片,而以自我生命之順適為核心,故而 在《答何善山》中曰:“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 多為人說長道短耶?弟愿老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 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妥。原來性 命,設計恢復。益于我者取之,而非徇其言也;害于我者違之,而非徒以 言也。如是,尚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明儒學案》卷十八) 可知,念庵先生是真正通達了,于是我們看到了他物我一體的另一種境界: “中日營營與外物交,以我應之,未始見其非我也,久而見化于物。故舍 事無心,舍物無身,暫爾暝目,彷徨無垠,有如處于寂寞之鄉,曠莽之野, 不與物對,我乃卓然。”(同上)此種以無心應萬物而超然自得的境界,既 可用儒者情順萬物而無情的仁者胸懷釋之,亦可用莊子物我合一而與天地 同在的道家境界說明,還可用禪宗無所住而生其心的隨緣任運情調表述。 然而,念庵先生依然是儒者,我們看他的《述懷示友人》,便可清晰地感 受到他晚年的心態,詩曰:“悠悠望千載,千載未久陳。共此山川居,世 代遞疏親。貽謀逮孫子,遼遠如越秦。名氏成杳絕,坵墓同飄塵。骨肉尚 如此,況彼鄉與鄰。所賴在簡書,遺言亦多湮。百不一可究,六藝俱沉淪。 默默忽返顧,造化如我賓。形骸聊一寓,旋當去吾身。吾身既非有,其他 復奚因。踽踽誠爾異,煦煦徒為仁。經營慷慨業,冀以名自伸。簸弄上世 語,讎校忘疲辛。酣謔恣放達,破滅稱天真。俱謂發狂疾,胡云詣精純。 我思魯中叟,兩楹夢何頻?怡然曳杖歌,曾不贈笑顰。達者識其源,頃刻 為秋春。愚人不解事,駭怵褫魂神。林中多敗葉,喬柯歲華新。彼此更互 見,修短寧足論。默觀發獨慨,證我意中人。”(《念庵文集》卷十九)在 本詩中,作者將人生置于永恒的時間之流中,突出了人生的短暫與功業的 不可憑借。子孫后代也難有意義,祖孫之間已遠隔如越秦;古人之名氏如 同其墳丘一般早已煙消云散,其親族后代尚坐視不管,更何況那些不相干 之鄉鄰?自我之形骸猶是暫寄于世間,頃刻間便會灰飛煙滅,既然我身尚 不屬我有,那其他又合足掛齒?在死亡面前,什么建功立業名垂千古,什 么著書立說以圖不朽,都成了沒有價值的誤入歧途。但倘若由此而放縱自 我,恣意享樂,那也屬發病發狂,而并未尋求到人生的真諦。理想的人生 應該是如孔子那般,既抱有致君堯舜的遠大理想,而一旦世不我用,便曳 杖而歌,無牽于懷,“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史記》卷四七,《孔子 世家》)在春秋更迭、歲月輪轉的大化之流中,不喜不懼,從容自得。這便 是念庵先生的理想人生。盡管他的“意中人”孔子已不是純粹的儒者身份, 而是混合了莊禪的意識,但在念庵本人看來,他仍是儒,仍是孔子之傳人。 在嘉靖時期,象羅洪先這樣因人生的挫折而歸隱,從而抓住自我的生命之 源不放手,融合釋、道以求精神的解脫,而又不放棄儒家身份者,可以說 大有其人。比如說薛蕙先生,雖并非王門弟子,但其人生經歷與思想特征 幾乎與念庵如出一轍。薛蕙(1489—1541),字君采,號西原,亳州人。 正德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他曾諫武宗南巡,與世宗爭大禮議,為此而 下獄,后又被人攻訐而被罷官。在這險惡的境遇中,他成了一只無助的孤 雁,“聲未鳴而先絕,翅將舉而復墜。”“延性命之茍存,非初心之所營; 遭志意之摧折,中無故而或驚”;“避繒繳而往來,困鷹隼之縱橫”。其精 神空間被大大壓縮,憂讒畏譏,心境凄涼,他雖以“鷹隼”自比,并仍有 “志激昂而將躍”的意愿,但卻失去了鼓起自我志向的憑借。(見《考功 集·孤雁賦》)故而最后終于走向老莊,注《老子》以見志去了。但作為 儒者的薛君采并不甘心淪入佛老中去,據《明儒學案》記其為學過程曰: “先生初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明,如是者若干 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 《老子》及佛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 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 以復性為要。未發之中,即性善也,情則始有善不善。圣人盡性,則寂多 于感,眾人私感不息,幾于無寂。”(卷五三)可知從為學宗旨上言,薛氏 之學亦可用“歸寂”二字概括之。若證之薛氏原話,則黃宗羲的確所言不 虛,比如薛蕙說:“寂然不動,本一理耳,感而遂通,乃散為萬事。雖散 為萬事,因物感之不同,故應之亦不同,千變萬化,皆是物也。”(同上) 念庵稱其所歸之寂為良知本體,而薛氏則言其為“理”,顯示了心學與理 學的差異,但無論本體為何,都是為了求得既有主宰又可自然而應物的超 然境界,如薛蕙又說:“寂然之時,物物本不相礙,及其感也,雖物各付 物,而己不與焉。誠如是也,從容萬物之間,夫何為哉?”(同上)這“從 容萬物之間”,實即是對自我生命的安頓。從為學過程看,他開始是因佛 老而得悟的,亦即在失意中尋求到了自我生命的支點,但作為一位儒者, 又不免對佛老有一種天生的排拒感,從而顯得不那么心安理得,非要從《中 庸》里尋到相似的說法,于是欣然而喜,遂持之不疑。所以黃宗羲對其理 論不滿曰:“若止考靜中覺性,以為情發之張本,則一當事變紛紜,此體 微薄,便霍然而散矣。”(同上)其實,薛氏之求寂,正是為了避開那紛紜 的事變而尋求精神的安寧,黃氏不免錯會其本意。在這方面,時人文征明 倒是比黃宗羲更理解薛蕙的心態,他說薛氏:“晚歲自謂有得于老聃玄默 之旨,因注《老子》以自見,多發前人所未發。又喜觀釋氏諸書,謂能一 生死,外形骸,將掇其腴,以求會于吾儒性命之理。蓋亦閑居無事,用寄 其淵微深寂之趣耳。或以為有所陷沒,而實非也。所居之西,隙地數弓, 即所謂西原者,故有水竹之勝;至是益加樹藝,室廬靚深,松竹秀列,陂 魚養花,日游衍其中,著書樂道,悠然自適。”(《文征明集補遺》卷三二, 《吏部郎中西原先生薛墓碑銘》)此處所言“著書樂道,悠然自適”,其生 命情調實有近于念庵,而其融合儒釋道以“寄其淵微深寂之趣”的學術方 法與心態,亦幾與念庵完全一致。從儒之一面言,他們只是借用了佛老, 故可言實非“有所陷沒”也;但從佛道一面言,由于他們必須解決自我生 命的安頓問題,就必須借用佛老,故可言實不可不染指佛老也。 抱有此種退守自保而默默無聞的人生態度者,在嘉靖之后的士人群體 中占有一定數量,他們不再介入官場,只在民間講學論道,甚者連學亦不 肯講,只在家中默默自悟,比如耿定向之弟耿定理,他“雖學道,人亦不 見其有學道之處,故終日口不論道,然目擊而道斯存也”;其學術宗旨乃 是守定“未發之中”,自修自證。究其心態,則在于“世人莫可告語者,故 遂終身不談。”(李贄《焚書》卷四,《耿楚倥先生傳》)他不會象何心隱 之類的狂者那般,具有強烈的出位之思而進取不止,所以當楚倥先生聽到何 氏的所作所為時,便感嘆說:“有是哉!神明默成,存乎其人,彼離其本矣, 無成,將有害也。”(《耿天臺先生全書》卷八,《觀生記》)無論是 從精神上還是肉體上,他只求自保,但他又決不放棄儒者所應有的節操, 決不流于放蕩無忌。此類心學傳人因無涉于政治紛爭與士人糾葛,故往往 不被后世學者所注意,但又的確是一種有特色的士人類型,具有獨特的人 格心態,代表了明代中后期王學流行中士人的一種生存狀況。而且,他們 對士人群體還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故應予以相當的留意。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