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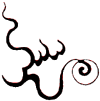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
|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與王學之流變 第三節羅洪先——歸寂與自保的代表 一、“歸寂”的原因及其所蘊含的人生追求 羅洪先(1504—1564),字達夫,號念庵,江西吉水人。嘉靖八年舉 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次年告歸。嘉靖十一年起充經筵講書官,旋丁 父憂而家居。嘉靖十八年召拜左春坊左贊善。次年冬,因世宗多日不視朝, 與校書趙時春、司諫唐順之請來歲元日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世 宗震怒,三人皆被黜為民。此后終生非復再仕。嘉靖四十三年卒,年六十 一。隆慶元年,贈光祿大夫,謚文恭。他于陽明在世時雖未及其門為弟子, 但自幼服膺王學,與王門高足錢德洪、王畿、鄒守益、黃弘綱交誼甚篤, 且參與陽明年譜的修撰,故其亦為王學后勁無疑。就地域言,他屬于所謂 的江右王學;就學術宗旨言,他與聶豹(1487—1563,字文蔚,號雙江, 江西永豐人。)一起被后世稱為歸寂派。本節意在通過對歸寂思想與時代 環境關系的考察,以說明王學對士人心態影響之一途,故以羅洪先為主要 研究對象,同時亦兼及聶豹思想與人格。 羅洪先在其《甲寅夏游記》中,曾對其歸寂的學術思想概括敘述說: “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為傳授口訣,蓋合內外前后一起包括,稍 有幫補,稍有遺漏,即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是 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余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久而后悔之。 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即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 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為主于中者乎? 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 于既發之后,能順應于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 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為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 反求其根源。蓋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動之妄也,主靜以復之,斯道 凝而不流矣。神發為知,良知者靜而明也,妄動以雜之,幾始失而難復矣。 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為充達長養之地,而后定靜安慮由此以出,必于 家國天下感無不正,而未嘗為物所動,乃可謂之格物。”(《明儒學案》卷 十八)他認為陽明所提出的良知應該是“至善”之“明覺”,其特性是“靜 而明”,而不是王門弟子常說的知善知惡之知,那只是一時之“發見”,是 一般之“知”而非良知。此良知用另一種表述便是“未發之中”,也就是 本體,故而他又說:“自知之所以能良言之,則固有未發者主于其中。” (《念庵文集》卷十一,《困辨錄序》)因而念庵所言良知之狀態為“虛寂”, 其特性為“靜而明”,合而言之亦可稱之為“虛明靜定”,有時他用“止水” 以喻之。(見《寄歐陽南野》,同上卷二)正是如此的特性也就決定了他求 得良知的主靜方式,即所謂的“主靜以復之”,同時也叫“收攝保聚之功”。 當時許多王門弟子都不能同意羅、聶二人的歸寂主張,認為一味主靜將割 裂動與靜、知與行為二,而這是不符合陽明先生致良知的本意的。但歸寂 說之所以能夠在眾多的王學流派中占有一席之地,自有其本身的學術價 值。就陽明致良知的本意講,實分為中下與利根兩類人而分別對待之,這 在“天泉證道”解釋四句教時已有明確的表述。陽明認為天下利根之人甚 少,因而也就要求必須有為善去惡的致良知功夫,方可獲無善無惡的虛明 良知本體。但在陽明病逝后,其后學弟子卻根據各自的理解作出了進一步 的發揮。比如同屬江右王學的鄒守益,他也承認良知之寂,故而說:“夫 良知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是也。指其寂然處謂之未發之中,謂之所存者神,謂之廓然而大公。 指其感通處謂之已發之和,謂之所過者化,謂之物來而順應。”(《東郭 集》卷五,《答黃致齋使君》)但他更重視良知之“一”,主張體用不分, 常感常寂,實際上也就等于懸空了本體,落實在具體人性上,便有了天命之 性與氣質之性合一的見解,因此說:“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 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 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 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滾出來,如何說 得論性不論氣?后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卻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 (《明儒學案》卷十六)一般哲學史著作都認為,在明代到了劉宗周、黃 宗羲時,才提出了道心不離人心、天命之性見于氣質之性的觀點,其實, 在鄒守益這里已經有了如此的表述。而鄒氏所以會有如此的見解,在于他 承認了人性的既成狀況,并試圖消除天理與人心之間過于緊張的矛盾關 系,從而解決人性之偽的時代癥節。因而江右王學中的許多人論起人性來 一般都較宋儒更有人情味一些,如鄧以贊曰:“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 色之內,如眼能視,耳能聽,手足能持行,這是什么?就是天性。在圣人 之踐形,全得這個,視聽言動以理,自然聲為律,身為度,耳成個耳,目 成個目,手足成個手足。賢智者知有個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之內,是知 天而不知人;愚不肖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同上 卷二一)這既非佛家之“作用見性”,因為還有個理在;又不是象朱子那 樣只認天理而斥形色,而是既知人又知天。鄒守益等人顯然采取了一種折 衷的態度:既要通過道德修練以保持自我品格之純潔,從而去改造世風, 同時又不忽視已經發展了的現實,即人們對物質欲望的追求。這是一種較 為平實的理論,故而明人很少非議鄒氏等江右王門諸子,黃宗羲甚至說: “夫子之后,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沒,不失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指鄒 守益)為宗子也。”(同上卷十六)但羅洪先卻認為這是善惡交雜,而不是 純然之良知,所謂“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耳”,如此“妄 動以雜之”,又豈有純然良知之可言?也就是說,他提出歸寂說的原因之 一是要糾正鄒氏之弊。同時,浙中的王畿堅持自己的“四無說”,反對為 善去惡的致良知功夫,強調良知之現成自然特性,下面還會對其作出詳細 的論述。羅洪先對此更是不滿,固而曾與龍溪多次展開爭論,他曾致函說: “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才拈工夫,便指為外道,此等處恐使陽明復生, 亦當攢眉也。”(《念庵文集》卷二,《寄王龍溪》)“不說工夫”之所以 遭致念庵反對,是因為“持此應世,安得不至蕩肆乎?”而“蕩肆”便會 “亂天下”。(同上,《與雙江公》)他曾與王畿辯論說:“求則得,舍則 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 應乎?是故不可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 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妄;談學而不本真 性,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于蕩也。”(同上卷十, 《良知辨》)可知羅洪先之提出歸寂主張,又是直接針對王畿之自然現成良 知說的。盡管羅氏之分動與靜、知與用為二,并不完全合乎陽明的本意,但 他強調致良知的功夫,強調良知虛明的特征,依然未離王學的路徑,故而 自有其理論價值。 然而,王學最大的特征乃是有切于個體之身心,可以說在心學諸派別 中完全從純理論上來談學者幾乎沒有,有不少人曾將此稱為王學的實踐品 格。故而羅洪先歸寂說的提出除了具有學術價值外,主要是為了解決自我 的現實存在問題,因此,不了解羅氏的生存狀況與人格心態,要真正弄清 其學術思想是很困難的。黃宗羲曾如此概括羅洪先的學術思想演變:“先 生之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于仁體。”(《明儒學案》 卷十八)所謂“踐履”便是前所言“知善知惡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 知”,也就是根據自我的主觀認識來判斷事物之善惡。此一階段大概是其 四十四歲之前。據史載羅洪先自幼即有大志,嘉靖八年中狀元及第,則更 鼓起了他用世的愿望,其岳父聞其及第消息后喜曰:“幸吾婿建此大事。” 他卻說:“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為大事也!”(同 上)這并不是夸張,他本人亦有《初登第》詩曰:“溫飽平生非所愿,君 臣今日系綱常。”(《念庵文集》卷二二)為了實現其大志,他自然會一切 依其良知而踐履之。這甚至在嘉靖十九年經歷了上疏罷官的變故后,他也 未能改變此種“踐履”的風格,《明史》本傳記其家居時,“甘淡泊,煉寒 暑,躍馬挽強,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 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至人才、吏事、民情,悉加意諮訪。 曰:‘茍當其任,皆吾事也。’”(卷二八三)可見其用世之心不減。 那么羅洪先是何時又是何因改變了此種踐履的學風而轉向了歸寂 呢?他作于嘉靖庚戌(二十九年)四月的《困辯錄序》對此述之頗詳,其 曰:“雙江先生系詔獄經年而后釋。方其系也,身不離接槢,視不離垣戶, 塊然守其素以獨居。久之,諸子群圣之言涉于目者,不慮而得,參之于身 動則有信。慨曰:‘嗟乎!不履斯境,疑安得盡忘乎!’于是著錄曰困辯, 以明寂感之故。歸質之友人,或然或否,或正以師傳曰:‘陽明子所謂良 知不類往歲。’癸卯(嘉靖二十二年),洪先與洛村黃君聞先生言必主于寂, 心亦疑之。后四年丁未,而先生逮送之境上,含涕與訣。先生曰:‘嘻! 吾自勝之,無苦君輩也。’其容翛然,其氣夷然,其心淵然而素,自是乃 益知先生。遂為辯曰:先生于師傳如何吾未之知,請言吾所嘗。昔者聞良 知之說悅之,以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吾惟即所感以求其自然之則,亦庶 乎有據矣。已而察之,持感以為心,即不免于為感所役。吾之心無時可息, 則于是非者亦有時而淆也。又嘗凝精而待之以虛無,計其為感與否也,吾 之心暫息矣,而是非之則似亦不可得而欺,因自省曰:昔之役役者其逐于 已發,而今之息者其近于未發矣。”(《雙江先生困辯錄》卷首)嘉靖丁未 羅洪先四十四歲,已開始接受聶豹之歸寂主張;而在其作《困辯錄序》時 為四十七歲,其本人的歸寂理論已趨于成熟。其中與其說他是被聶豹的理 論所說服,倒不如說是被其人格魅力與人生境界與所折服。文蔚先生被逮 時的從容鎮靜,臨危不亂;在鎮撫司監獄中時“塊然以守其素”的沉穩自 若,平和充實,都深深打動了羅洪先。然后又經過其本人的反復心理體驗, 對比了從前與今日的不同心理感受,終于對聶氏之學說深信不疑,并開始 親自探討歸寂的理論。羅洪先之所以能被聶豹的理論及人格所影響,是因 為他們之間有著相似的經歷。羅氏本來懷著一腔報效朝廷的忠誠,不料非 但未能被世宗所理解接納,反而遭到罷官為民的處罰,其心中之冤屈自不 待言。他在剛被罷官時也許并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故而賦詩曰:“幻 跡識從榮宦后,道心堅自險途間。歸家若問躬耕處,五柳門前有碧山。” (《念庵文集》卷二二,《望鄉》)仿佛有虎穴抽身的因禍得福之感,決心 要學陶潛躬耕南畝了。但是具有強烈用世之心的他畢竟不是陶潛,隨著時 間的推移,他逐漸感到了隱居生活的無味與失落,于是詩中的語氣也多有 改變,其《讀京華舊稿》曰:“少年高揖談王道,今理殘篇愧舊封。世事 白云終莫定,故人青鬢豈重逢?閑垂書幌穿斜日,坐聽樵歌對晚峰。卻笑 儒冠空結束,此身已向遠游慵。”(同上)他深愧難以實現當年的大志,感 到了時間的流逝而青春難保,更痛心于世事如白云般飄忽不定,而自己已 無機會施展原本遠大的抱負,只能空戴儒冠而閑對斜日,坐聽樵歌,去打 發這慵懶無聊的生涯。盡管他用世之心尚在,并以廣泛的知識涉獵為用世 作好準備并填補閑散的生活,但依然難以使心情平靜下來,其《逢雁》詩 曰:“幾時來塞下,烽火近何如?道路多知己,寧無一札書。江鄉今苦旱, 瘴癘且難除。處處多繒繳,投身未可疏。”(同上卷二一)看到一只大雁, 竟然會引起他如此復雜的感想,他欲從大雁處獲知邊境戰事如何,可見其 仍心憂國事;他盼望大雁能給他帶來知己的書信,可見他感到了人生的孤 獨;而在災害流行之時,他又告誡大雁,千萬小心啊,到處都布滿了可怕 的弓矢!那大雁身上顯然又寄托了他憂懼世事的心情。他也想極力地排解 自己的郁悶心情,以免于身心的折磨,比如:“浮蹤從此定,塵土莫相侵。” (同上,《龍池》)他要用龍池之水沖洗掉世俗的塵污,以保持自我的高潔; “數息知天度,冥心養谷神。翻憐塵世者,何異夢中身。”(同上,《游龍 虎山二首》其二)仿佛他被罷官是得了大便宜似的;“神解應難遇,生涯 早自知。馬歸折臂后,鹿失夢醒時。歲久惟存櫟,朝饑且刈葵。學農吾分滿, 肉食莫相期。”(同上,《貽相者》)仿佛他一切全想明白了,從而已抱 定歸隱自全的決心。然而,總提“塵土”意味著他懼怕“塵土”,譏笑“塵 世”透示出他未忘“塵世”,而“馬歸折臂后,鹿失夢醒時”也完全是痛 定思痛之言,說明他仍未能彌合心靈的傷痕。否則他何以會在曠達的同時 又寫下如下的詩句:“流光不可駐,斜日難再晨。不惑云希圣,無聞只畏 人。容身依一室,食力已二春。卻憶劬勞德,翻憐心動頻。”(同上)本詩 題為:“癸卯十月十四日予生四十矣,撫己自悲而有此吟。”“癸卯”即嘉 靖二十二年,其罷官時間已滿二年,又是其剛滿四十的年頭。孔子言四十 而不惑,可他此刻卻被罷官躬耕于野,念及父母的養育之恩與殷切希望, 難怪他會有逝者如斯的感嘆了。而此時用知善知惡的良知顯然無法解決其 現實的人生難題。正在此刻,他看到了聶豹被逮時的情景,他何以能在危 急時刻而處亂不驚,又何以能身陷囹圄而從容鎮定?難道果真是靠歸寂之 學獲得了良知的真體了嗎?這促使他不得不去了解聶豹的學說,并結合自 我的人生體驗加以思索。比如說,聶豹認為“勞苦饑餓,困窮拂亂,是鍛 煉人的一個大爐錘,承受得這個大爐錘鍛煉者,金是真金,人是真人。” 而經受鍛煉的關鍵是要能守之以“素”,何謂素,聶豹曰: 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養于己者也。位之所值,雖有富貴貧賤夷狄 患難之不同,然不以富貴處富貴而素乎富貴,不以貧賤處貧賤而素乎貧賤,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一,一則無入而不自得。 得者,得其素也。正己居易,皆反求諸身之素也。不怨不尤,非有所強也。 《易》曰:素履之往,獨行愿也。故不愿乎外,愿外便有不得,怨尤之念 興而僥幸之事作矣。大意全在素字上,素即溫故之故,豫立之豫,先天之 先,前定之前。故養之有素者隨其所值,坦然由之而無疑,卒然臨之而不 驚,無故加之而不懼。(《雙江先生困辯錄》卷四,《辯素》) 這是聶豹在監獄中所體悟出的處世之道,或曰處危難之道。“素”乃 自身所固有,然欲獲之必須要有“養”之功夫。只要“養之有素”,便會 無入而不自得。難怪念庵讀后深有會心曰:“素位一段,全是鄙見,不期 暗合。”(同上)所謂“暗合”,便是二人具有相近的經歷,從而得出了相 近的人生體驗。而這所謂的“素”就是寂,就是靜,就是虛,念庵曾有詩 述曰:“靜極初生動即消,無端風雨入清霄。誰知擾擾氛塵內,自有元聲 在寂寥。”(《念庵文集》卷二十,《天籟》)而只要在寂寥中得其“元聲”, 便會排解紛擾,心情平靜,無入而不自得,此時他的詩中很少再出現煩惱 躁動,而顯出一派安然平和的心態,如:“影滿棠梨日正長,筠簾風細紫 蘭香。午窗睡起無他事,胎息閑中有秘方。”(同上,《靜坐二首》其一) 可知他果真從歸寂中獲得了真實的人生受用,則他又為何不持之彌堅呢? 當然,念庵之歸寂并非只得力于雙江,同時亦與其汲取白沙之學關系密切, 他曾說:“某自幼讀先生之書,考其所學,以虛為基本,以靜為門戶,以 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為功用,以勿忘勿助 之間為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為實得。蓋雖未嘗及門,然每思 江門之濱,白沙之城,不覺夢寐之南也。”(同上卷四,《告衡山白沙先生 祠文》)可見白沙之學并未被士人忘卻,其靜中養出端倪的心學方法又在 念庵這里得到了有力的回應,這一方面固然顯示了白沙心學的生命力,同 時不也說明了在明代中后期大致相近的政治境遇中,士人們也必將會有大 致相近的人生選擇嗎?因而,在梳理明代學術思想時,若不能合白沙與陽 明共觀之,將很難真正把握其底蘊。 當然,念庵之歸寂并非只是為了應付險惡的政治環境與安頓躁動煩亂 的情緒,更具有擺脫世俗,砥礪德性的正面意義。在嘉靖中后期,世風趨 于奢靡而士風趨于貪婪,士人身處其中如何保持自我的純潔成為一個不小 的考驗,當時順風而化者可以說比比皆是,念庵在給朋友的書信中曾反復 提及此點,他說:“京華衣冠之萃,可觀法者不少,然世情擾擾,亦易汩 沒,非夫豪杰之士,固莫能于此力精于學而自有生意。”(同上卷二,《與 林東峰》)“京國名利場也,名利人之所易惑者,執事此行順矣,于極順中 不動乎意,其能乎?視極順中與不順,其能乎?于名利之去來無少加損, 而吾之所以不因之有增減其能乎?此亦千百年之一辨也。絲毫牽系,終身 之累。”(同上卷四,《與王塘南》)在念庵眼中,京師仿佛一個大染缸, 稍不謹慎,便會玷污其身,可謂視官場如畏途,雖談不上恐懼害怕,起碼也 是如履薄冰。其實,非但京師如此,各地又何嘗不是如此,比如說他的講 學朋友王畿,早已脫離了官場,但念庵依然認為他受到了世風的浸染而有 失賢者風范,故而致函規勸說:“今風俗披靡,賄賂公行,廉恥道喪,交 際過情,所賴數公樹立風教,隱然潛奪其氣,庶幾不言而信,豪杰嗣興。 猶恐習染錮蔽,未易移改,況助瀾揚波,令彼得為口實。果有萬物一體之 心,宜有大不忍者矣。好名若節,欺誑耳目以為身利,此誠不可入于堯舜 之道;若冒善之名,借開來之說,以責后車傳食之報,不知與此輩同條例 否?”(同上卷二,《答王龍溪》)龍溪之學以無善無惡之自然良知為宗旨, 講究物來順應、一過而化的廓然大公,故而歷來對生活小節不甚在意,也 可以說是學術導致人格吧。念庵也承認人之欲望難以避免,但他認為從事 圣賢之學者便不能聽任自我欲望之放縱,他說:“人生有知不能無欲,欲 不得其道始流于惡。然自古圣賢未有不由嗜好淡泊用度簡省而能有成者。” (同上卷四,《閑書》)而要養成淡泊習性,便須擺脫世俗而歸寂,從環境 上說,要入山而靜處;從心境上說,要一塵而不染,正如他向聶豹所談體 會說:“奉謁五日,密自省察,終是入山滋味與出山較別,歸來再驗,尚 須對火煉金,未是精瑩純全,無鉛銅混雜,以此方覺全未濟在,長者于此 默識,更要如何,要當以一塵不染為極至處,實吾后生拳拳也。”(同上卷 二,《答聶雙江公》)當然,要達到一塵不染是相當艱難的,因為這不僅是 一個心理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生理的問題,對此念庵曾忍受了極大的清 苦與寂寞,用李贄《續焚書》中對他的概括,便是所謂的“攻苦淡,練寒 暑”。(卷二二,《羅洪先傳》)在這方面,他可以說是奉身守潔的模范儒 者,在學術上也是一個真正歸寂的學者。 但主歸寂時的羅洪先卻并不是要拋棄世界的隱者,他的主靜與佛氏之 寂滅并不相同,盡管有許多王門學者擔心他陷于禪寂而不能自拔,但他在 此時卻恰好是主于入世的。他的主靜只不過是求得良知本體的功夫,而并 非其最終目的。他獲得靜明之本體也并非用以避世自適,而是要以之應世, 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為本。惟無欲,然后出而 經世,識精而力巨。”(《明史》卷二八三,《羅洪先傳》)此亦即其詩中 所言的“雖從靜里得,卻向動中知。”(《念庵文集》卷二十,《知幾吟用 康節韻》)此種“動中知”實可包括兩個方面:在野與在朝。若在野,則 可表率士人,著書傳世,他解釋自己淡泊其欲的目的說:“若夫假之以二 三年,孜孜早夜敏行而不敢怠,則子輿所謂獨善兼善與退之所謂行道為書, 傳今化后,或者不能兩讓矣。”(《明文海》卷一九五,《與王堯衢書》) 若在朝,則可以念庵所言聶豹之行為為例,他敘述雙江嘉靖后期為兵部尚書 時說:“當是時,敵歲窺塞旰食,內外洶洶,先生臨以鎮靜,事必己出, 從容籌計,不奪于橫議,異時紈绔之子囊金竊符溷爵恩賞者,不敢一過其 門,天下始有羔羊之節。”(《念庵文集》卷十一)依實而言,念庵的話具 有很大的夸張成分,因為聶豹的此次出仕結果是很狼狽的,盡管當時他得 到了嚴嵩與徐階的支持,卻并沒有出色的表現,《明史·本傳》言其對南 北之亂“卒無所謀畫,條奏皆具文”,弄得“帝切責大怒”,最后“竟以中 旨罷”。(卷二0二)其中所敘與念庵之言相距甚遠。但是念庵之語仍不失 其資料價值,我們可將其視為是其本人對歸寂說之自信與其在現實政治領 域中之理想狀態之企盼。可以設想,假如念庵有機會再入官場的話,他便 會以此來立身行事。至于是否可以達到他所說的理想狀態,則因為他后來 轉變了人生志趣而與官場永遠決絕,再也沒有了表現的機會,其效果也就 不得而知了。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