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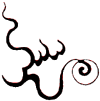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
|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與王學之流變 第一節嘉靖朝政治與士風演變以及王學之遭遇 二、世宗獨裁與陽明心學之際遇 從嘉靖八年至嘉靖二十六年,可視為世宗在位的第二個時間段落。這 也許與史學家的時段劃分不太一致,也可以說前此并沒有人作過如此劃 分。其實,時間之流并無間斷之時,因而從本質上說也就無任何段落之可 分。人們為了討論問題的方便,便人為地強行將時間分割。從此一點講, 任何人都不能奢望用自己所分時段作為劃分時間的唯一權威標準。史學界 一般將嘉靖十八年作為分界的標志,將世宗之在位分為前期與后期,其原 因是由于在本年世宗的人生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從早期的銳意進取 轉向晚期的消極荒唐,而明顯的外部標志則是自本年起世宗之不視朝的行 為變化。④筆者作出上述的劃分則是著眼于陽明心學的遭遇,即從嘉靖八 年世宗宣布王學為偽學而加以禁止,到嘉靖二十六年王門弟子徐階之入內 閣而握重權,則此一時段可視為是王學之遭受挫折與壓抑的一個時期。 記載王學被宣布為偽學最詳細的文獻是《明世宗實錄》,其卷八嘉靖 八年二月甲戌條記曰:“吏部會廷臣議故新建伯王守仁功罪,言:‘守仁 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 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相互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 或流于清談;庸鄙者借其虛聲,遂敢于放肆。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其門 人為之辯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瀆天聽。若夫剿輋賊擒除 逆濠,據事論功,誠有可錄,是以當陛下御極之初,即拜伯爵,雖出于楊 廷和預為己地之私,亦緣有黃榜封侯拜伯之令。夫功過不相掩,今宜免奪 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卿等議 是。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詐任情,壞人心 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移檄舉兵, 仗義討賊,元惡就擒,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夸張。近日掩襲寨夷, 恩威倒致。所封伯爵,本當追奪,但系先朝信令,姑與終身。其沒后恤典, 俱不準給。都察院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于非圣者,重治不 饒。’”看到上述內容不免令人吃驚,前此一直被許多人視為有入閣可能 的王守仁,如今卻成了被否定的人物;不久前還在利用其禮本人情的學說 作為議大禮依據的世宗皇帝,轉眼間卻視陽明心學為“壞人心術”的邪說; 如果說陽明心學是“詆毀先儒”,那么堅持先儒理論的楊廷和之輩為何要 被貶官治罪?而張璁、桂萼們議禮不依程朱之說是否也算詆先儒而倡邪說? 從《明倫大典》修成的嘉靖七年六月至宣布陽明心學為偽學的嘉靖八年二 月,時間間隔不到一年,朝廷態度竟然有如此大的轉變,實在令人吃驚而 費解。于是,關于陽明死后被革去恤典的原因便有了種種的說法。一種說 法是陽明得罪了因大禮議而得勢的新貴桂萼,《明通鑒》曰:“萼暴貴,喜 功名,風守仁取交止,守仁辭不應。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 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卷五二) 此處所言是有根據的,在嘉靖八年二月朝廷下詔禁偽學后,黃綰曾上疏為 守仁爭辯,其中說:“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 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構隙。……然以萼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 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歟?”(《王陽明全集》卷三五,《年譜》三) 可知桂萼的確與陽明存有矛盾并對其進行過攻訐,而他當時任內閣大學士 兼吏部尚書,既有條件也有能力影響朝廷的決定,說不定上述所引的那段 話便是出自桂氏的手筆。但如果仔細比較吏部會議的結果與世宗所下的圣 旨,可以看出后者的語氣要比前者更為嚴厲,則陽明之死后所受不公待遇 便非桂萼一人所能決定。故而便又有了第二種說法,即陽明得罪了世宗。 葉權《賢博編》記曰:“武宗大漸,先生密疏,預言世及之事,疏寢不報。 嘉靖初,桂大學士與先生有隙,微發其奏,幸先生卒,止削爵,不爾,且 有奇禍。”(《明史資料叢刊》第一輯,174頁)據葉權所講,此事乃聞之 其師柴后愚公,而柴氏系陽明弟子,故而葉氏之言不能視為全無根據。但 這也肯定不是世宗禁王學之主要原因,因為在大禮議中,陽明本人雖未介 入此事,王門弟子及與陽明交好者卻積極支持世宗,故而世宗起碼不應對 王學產生什么敵意。而且若就事論事,朝廷如此對待陽明道理并不是非常 充分。且不講其所言“兵無節制,奏捷夸張;”“掩襲寨夷,恩威倒置”乃 誣蔑不實之辭,其指控本身便留下了難以彌合的裂痕。因為在儒家士人心 目中,道德學術決定著事功,他們很難相信,一位大倡邪說者會有忠誠的 品格與杰出的事功。換言之,既然認定其學說“壞人心術”,則其罪莫大 焉,便應毫不遲疑地追奪其伯爵封號。如今既承認其事功與保留其爵位, 卻同時又禁絕其學術,這是很難令士人信服的。王學之在嘉靖一朝屢禁而 不絕,與朝廷之說法難以服眾當有直接關系。其實,世宗之禁王學并不僅 僅關乎陽明個人品格的優劣與事功的有無,而是與心學的特性有密切關 系。王學乃是一種追求個體自我突出的圣人之學,對于傳統的規則與外在 的禮儀均不甚重視,這在大禮議時,與世宗滿足自我心愿的追求適相一致, 而在過此之后,朝廷需要的是政治的穩定與思想的統一,不再需要士人突 出的個性與妄生事端,則自然會禁止自我意識突出的王學了。從本質意義 上講,陽明心學不是一種適于統治者的學說,因為它缺乏統一的外在標準 與具體的操作程序,而主要靠的是個體的體悟與信仰,因而也就不利于朝 廷去統一思想與穩定人心。實際上在有明一代無論王學遭禁還是風行,它 始終都未能成為朝廷的統治意識形態,也足以說明了此一點。 當然,王學的遭禁與世宗的個性也有直接的關系。世宗本是一位個性 突出而感覺敏銳的人,他不僅具有牢固的自尊意識而常常一意孤行,并且 能夠見微知著,通過很小的事物征兆而預測后來的發展趨勢。比如說輔臣 們當初為其所擬年號為“紹治”,他一眼便看出是欲其繼承弘治之意,于 是便堅決不予采用,而改為“嘉靖”二字,取《尚書·無逸》“嘉靖安邦, 至于大小,無時或怨”之意,亦即安定而和樂之意。如果他當時疏忽而接 受了大臣所擬年號,則后來大禮議定而不以孝宗為皇考,這“紹治”便成 了刺目甚至具有諷刺意味的字眼。而世宗在當時只不過是個十五歲的少年 而已。通過大禮議的激烈政治較量,不僅增強了他駕馭群臣的能力,更重 要的是大大刺激了他獨攬朝綱的欲望。而要獨攬朝綱,就必須迅速提高帝 王在朝廷中的絕對權力優勢,而要提高帝王之權勢,就必須壓制文官作為 理論基礎的所謂道統。而要達到此一目的,最有效的途徑之一便是通過更 定各種禮儀,于是,在嘉靖八年之后,世宗便對更定禮制表現出異乎尋常 的濃厚興趣,故而《明史》說:“帝自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 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議皇后親蠶,議勾龍、棄配社稷,議分祭天地,議 罷太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別建東、西二郊,議祀高禖議文廟設主更從祀 諸儒,議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議祈谷,議大禘,議帝社帝稷。”(卷一九六, 《張璁傳》)當然,無論議論何種題目,世宗都要先下禮部讓群臣合議, 群臣也往往引經據典,廣事探討,但最后的決定權則在世宗本人,這就要 求文臣們先要準確窺測世宗意向,然后附和其說并為其找出充足的論據; 如果一時未及窺得圣意,則在得知后須趕快改弦更張,拋棄舊說而順從圣 論,否則便會引起龍顏振怒,從而遭致罰俸貶官甚至更嚴重的處罰。世宗 立論當然也有根據,而且是從圣人處尋來的根據,他說:“夫禮樂制度自 天子出,此淳古之道也,故孔子作此言以告萬世。”(《明世宗實錄》卷一 0九)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將孔子授予的權力反過來用在了孔子本 人身上,誠可謂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范例。他認為孔子雖是儒家 道統的代表,卻不應享受與帝王同等的祭祀待遇。自漢代始,儒家便成為 官方的正統思想,漢平帝元年孔子被追謚為“褒成宣圣公”,唐玄宗時又 將其追尊為“文宣王”,至元武宗時則更追謚其為“大成至圣文宣王”,祭 祀時儀式之隆重不下于帝王。明代以文治而著稱,當然對孔子之推尊更甚 于前代。但此種情形至嘉靖時則起了變化,世宗認為:“圣人作天與尊親 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 正。”(《明史》卷五十,《禮志》四)張璁不知是已被世宗授意還是先窺 得了圣意,馬上提出如下更改建議:“孔子宜稱先圣先師,不稱王。祀宇 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同 上)于是,朝臣對此又展開了一場爭議,結果凡是順從世宗之意者一律受 到褒獎,而提出異議者則均受到處罰,最后終于取得了令世宗滿意的方案, 嘉靖九年十一月禮部會同內閣、詹事府、翰林院議定了更改后的孔子祀典, 其大致內容為:孔子稱至圣先師,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等封號; 將大成殿改為先師廟;撤塑像而改為木制牌位;春秋二祀,祭品為十籩十 豆,樂舞用六佾。世宗利用更改孔子祀典一事,再一次顯示了帝王之勢高 于一切的優越感,張璁對此可謂心領神會,因而在出現爭議時,便毫無保 留地說:“習俗難變,愚夫之難曉也,其所自為說者亦曰尊孔子也。蓋喻 于利,而實未嘗喻于義也。仰惟皇上仁義中正,斷之以心,所謂唯圣人能 知圣人者也。”(《羅山奏疏》卷六)在此,張璁不僅將制禮作樂的權力完 全奉獻給了世宗,而且還將其譽之為具有仁義中正之心的圣人,則世宗無 論從品德還是地位均已經具備了論定孔子祭典的資格,當然就可以為所欲 為地“斷之以心”了。于是,世宗也就毫不客氣地擔負起最高裁判者的職 責,他說:“夫孔子之于當時諸侯有僭越者,削而誅之,故曰‘孔子作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既如此,其死乃不體圣人之心,漫加其號是何心哉?” (《明世宗實錄》卷一一五)既然孔子本人都主張不能越禮,那么后人有 何道理為其加上“王”之稱號呢?為了糾正此種不合“禮”現象,世宗非 但不顧群臣非議,甚至可以突破祖宗成法,故曰:“夫成法固不可改。其 也一切事務,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時制宜。至于事關綱常者,又不可 不急于正也。”(同上)不能說世宗所言絲毫沒有道理,但其真實意圖顯然 并非替孔子著想,從而為其恢復應有的歷史地位,而是借壓孔子而壓群臣, 并突出自己至高無上的君主威勢。對此萬歷時的沈德符曾一針見血地指 出:“孔廟易像為主,易王為師,尚為有說。至改八佾為六、籩豆盡減, 蓋上素不樂師道與君并尊。”(《萬歷野獲編》卷十四)其實,“易王為師” 亦應為不欲孔子與帝王并尊之意。對此,已有人作過較詳細的研究,可參 考。⑤ 世宗在道與勢的較量中之日益占據優勢并最終獲得以勢凌道的勝利, 同時便意味著士人的逐漸陷入被動地位并最終拜倒在帝王之勢下,而放棄 守道的責任與獨立的人格。早在嘉靖四年,四川副史余珊即上疏世宗曰: “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圣意者,謫遣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 而后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 為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 寢成暌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明史》卷二0八,《余珊傳》)首先因溫 和而獲福者是費宏,史載“‘大禮’之議,諸臣力與帝爭,帝不能堪。宏 頗揣知帝旨,第署名公疏,未嘗特諫,以是帝心善之。及廷和等去位,宏 為首輔。”(同上卷一九三,《費宏傳》)并最終以功名而善終。第二位以柔 軟而獲利者是李時,史載“帝既定尊親禮慨然有狹小前人之志,欲裁定舊 章,成一朝制作。張孚敬、夏言用事,咸好更張。所建諸典禮,咸他人發 端,而時附會之。或廷意不和,率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嘗顯爭。以故 帝愛其恭順。”(同上,《李時傳》)因而他也得以君恩“始終不替”。而那 些仍然想守道諫君的士人,則須時刻具有遭貶入獄的準備,乃至在嘉靖二 十一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在上疏勸諫世宗時,事先令家人買好棺材準備料理 其后事,果然不出其所料,棺材雖未用上,卻依然獲得如下結果:“上震 怒,命杖于廷,錮之詔獄。”(《明通鑒》卷五八)但并非所有阿諛君上者 均可避免禍患而得到實惠,這要視帝王當時的心情而定,如嘉靖二十六年 群臣朝見后,世宗只不過說了些訓諭臣子的套話,然而給事中陳棐卻將敕 諭敷衍為十章箴詩獻給皇上,不料“上大怒,謂棐舞弄文墨,輒欲將此上 同天語,風示在外臣工,甚為狂僭,令自陳狀,棐服罪,乃降調外任。棐 即帝王廟斥去元世祖者,素善逢君,不謂求榮得辱。”可謂馬屁拍在大腿 上,也就不得不弄巧成拙地自認倒霉。可在此之前的嘉靖十四年,因正月 十五日下了場春雪,世宗諭大臣曰:“今日欲與卿等一見,但蒙天賜時玉 耳。”夏言當即獻上一首天賜時玉賦,此次則“上大悅,以忠愛褒之,甫 逾年而入相矣。”(《萬歷野獲編》卷二)從表面看似乎世宗喜怒無常,恩 威難測,但其中依然可以尋到其一貫之處,即都是以維護君主之獨裁為出 發點,前者怒其以己語同天語,冒犯了帝王的尊嚴;后者則以春雪為祥瑞, 悅君心而喜龍顏。當然,世宗與士人之間關系的演變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 即士人的人格是逐漸被摧折的,而世宗對于何種士人人格才適合自己的專 制統治也有一個摸索的過程。以世宗對內閣首輔的選擇為例。在專制社會 中。君主選擇臣子不僅需要其學問品德合乎標準,同時也包括氣質、性情、 愛好諸復雜因素。按一般原則講,君主也許樂意選擇與其性情相近者為臣 子,宋儒邵雍即曰:“擇臣者君也,選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為奈何! 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而必有桀紂之臣。”(《漁樵問 答》)其實此言只有理論上的意義,現實情形卻決非如此單。世宗曾以圣 君自任,卻未見選出幾個周公般的臣子,這且不講,即以性情論,世宗無 疑是位剛愎多疑的君主,故而他初始時對勇于任事的臣子是情有獨鐘的, 若張璁、桂萼、夏言諸位大學士,均有與世宗相近的剛愎氣習。他們與世 宗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在對待皇上時,他們必須盡量地克制自我。但就其 本質而言,又都以剛狠著稱,史載張璁“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 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明史》卷一九六,《張璁 傳》)而《明史》對夏言的評價更耐人尋味:“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 人莫能屈。既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 (同上,《夏言傳》)他本有豪邁之性,但身處嘉靖朝卻不能完全放任自 我,他的與張璁諸人向對抗不僅是本性使然,更重要的是窺測的了世宗希 望臣下相互爭斗以便駕馭的用心,所以方敢斗膽為之。不過,如果認為夏 言僅甘心做世宗的工具顯然也未能深入其本質,他的挾私報復的兇狠之性 在歷史上也是出了名的。據后來的湯顯祖所記,其同鄉徐良傅在科考時,夏 言因其為江西同鄉而叮囑考官關照之,但徐氏因不知內情,故未有任何感謝 之舉;徐氏任了三年武進知縣后,夏言特意將其留在京城任給事中,自以為 給了徐氏莫大恩惠。可他仍不見徐有什么感謝的表示,甚至有意暗示他也不 醒悟。于是夏言便轉恩為仇,借故入其罪而置之詔獄,并最終將其削職為民。 (事見《湯顯祖詩文集》卷五十,《徐子弼先生傳》)既然狠愎是其天性, 則在其與世宗相處時便會時不時地流露出來,以致造成君臣關系的緊張。 世宗對夏言可謂是又喜又恨,所喜者乃是其善于領會自己的意圖并作出積 極的反應,所恨者則是有時會頂撞自己,因而他就常常用各種方法來懲罰 教訓夏言。如在大禮議結束后,御史喻希禮、石金請求寬大當時獲罪諸臣。 世宗大怒,命令夏言彈劾他們。不料夏言卻說此二人并無惡意,并請世宗 予以寬恕。“帝責言對狀,逮二人詔獄,遠竄之,言引罪乃已。”(《明史》 卷一九六,《夏言傳》)從此以后,夏言便不斷地被世宗斥責,其原因大都 為嫌其“傲慢”,此種憤恨至嘉靖十八年終于表面化,世宗斥曰:“言自卑 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悉還累所降手敕。” 夏言恐懼,連忙上疏謝罪,“請免追銀章、手敕,以為子孫百世榮,詞甚 哀。帝怒不解,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少師勛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 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余,并銀章上之。居數日,怒解,命止行。復以少 傅、太子太傅入直,言疏謝。”(同上)但夏言并未能使世宗回心轉意,嘉 靖二十一年,世宗因崇信道教長生術而賜香葉束發巾給諸大臣,夏言則認 為“非人臣法服,不受,”加之嚴嵩的陷害,世宗下決心罷免他,本年七 月十五日日食,世宗下詔曰:“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閑職 住。”后來盡管又恢復了他的職位,卻終于在嘉靖二十七年因復河套失地 而被世宗斬首于西市法場,為自己的剛愎個性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夏言之 死實在是性格的悲劇,因為從他內心深處,他的確絲毫未敢忘記對皇上的 忠誠,他曾作有《輔臣賦》曰:“身代天工,口代天言。汝心非天,罪孰 大焉。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弗慎樞機,厥亂斯棼。生之殺之,予之奪之, 惟帝之命,惟汝之司。曰忠曰貞,曰公曰平,四善闕一,禍延蒼生。皋夔 伊周,千古稱賢。汝獨非夫,庶其勉旃。”(《夏桂洲先生文集》卷十六) 他要在世宗之下做“皋夔伊周”之類的賢相顯然只是一種幻想,因為世宗 根本不是周文王一類的圣君,但他表示要以己心為“天心”,要生殺予奪 “惟帝之名”,應該說是他主觀上希望做到的。說夏言對世宗缺乏忠誠之 心顯然是不公平的,即使在其遭貶家居時,他也依然是“夢中長侍君王側” (同上卷五,《王宸樓》)的。當他最終身陷囹圄時,其自我處于深深的矛 盾痛苦之中,他的《拘幽三首》(同上卷七)典型地體現了此種心態: 晝杳杳兮忘朝昏,夜冥冥兮孰知宵辰。方炎夏之勃郁兮,攸秋涼之蕭 森。此何地兮今何辰,嗟遘厲兮而豈無因。大哉圣主兮愚哉罪臣! 白日沉冤獄,青天網不疏。圣恩隆未報,臣罪固當誅。 白發吾已老,青史任他年。死去有余地,生來不愧天! 他感到了攸忽之間便由夏到秋的世態炎涼,也感嘆自己是遭逢了不白 的“冤獄”,但他依然不敢埋怨皇上,而寧可將其歸為他因。然而他還是 感到了冤枉,因為既然是“臣罪固當誅”,那又何必“生來不愧天”?既 然是無愧于“天”,那又有何當誅之罪?于是只好嘆一聲“大哉圣主兮愚 哉罪臣”,除了對赫赫君威的恐懼之外,似乎還透露出一種被愚弄的后悔 之感。但這一切都于事無補了,于是他唯有揮筆寫下一首《擲筆長逝》作 為生命的結束:“勞形生何為,忘情死亦好。游神入太虛,相伴天地老。” (同上)他謹慎小心地侍奉世宗,忍受著案牘勞形之累與精神緊張之苦, 如今卻得到如此下場,這人世還有什么值得留戀,還有什么不能忘情?當 自己的靈魂升入太虛之后,能夠相伴天地而無盡,沒有了勞累與驚恐,不 比這充滿是非的朝廷更令人愜意?他這看似通達的背后,實際上是對君恩 的絕望與不公待遇的控訴。后來的歷史證明,不僅是夏言,凡是性情剛愎 者都很難與世宗長久共事,因而也就被先后治罪貶官,當然,夏言為此而 丟了腦袋,是他們中間最不幸的。與世宗合作時間最長的,反倒是與世宗 性格并不相似的嚴嵩,盡管他后來也倒了臺,上臺的也是與世宗性格不相 似的徐階。因此,在一位剛愎自用的君主統治下,最終形成的必然是陰柔 的士風,尤其在官場中更是如此。當時及后來的許多史學家均注意到了此 一點,《明實錄》在總結夏言的失敗原因時說:“然其人才有余而識不足, 憑崇傲肆,威福自由,無所忌憚,上寢不能堪,稍稍以微旨裁之,言不為 懼。久之上益厭,屢加叱啐,麾斥來去,無復待輔臣禮,言亦不以為恥。 本年再入政府,一意下恩怨,人皆側目視。及為嵩所誣遘,遂致身首異處, 天下雖以惡嵩,而亦以言為不學不知道,足以自殺其身而已。”(《世宗實 錄》卷三四一)此段評語不能算是完全公正,亦不知其所言“知道”為何 指,但有一點是正確的,那便是夏言之死乃是由于傲慢的個性使世宗難以 忍受。而谷應泰則更是將夏言之失敗與嚴嵩之成功并舉對言:“桂洲胎禍 于香冠,分宜追思乎召鶴。批逆鱗者無全功,盜頷珠者有巧術也。況嵩又 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 帝以獨斷,嵩以孤立。贓婪累累,嵩即自服帝前。人言藉藉,嵩遂狼狽求 歸。帝且謂嵩能附我,我自當憐嵩。方且謂嵩之曲謹,有如飛鳥依人。即 其好貨,不過駑馬戀棧。”(《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四)可知夏言即使有忠 誠之心,而其跋扈之氣亦難容于世宗;而嚴嵩盡管有貪污好貨的丑行,而 其曲謹之性亦將獲崇于君上。是不是可以說,夏言的橫死與嚴嵩的得勢構 成了嘉靖朝士風轉折的明顯標志呢? 陽明心學在嘉靖中便是面對著如此的政治環境與官場風氣,由此也就 決定了它坎坷的命運。早在嘉靖元年,便有御史程啟允、給事中毛玉“倀 議論劾,以遏正學”,其實就是對陽明心學的攻擊;嘉靖二年,“南宮策士 以心學為問,陰以辟先生(指陽明)。”但此時或許與世宗尚關系不大,而 是“承宰輔意也。”(《王陽明全集》卷三五,《年譜》三)今所見世宗明 確對陽明及其學說表示不滿是在嘉靖七年:“王守仁報斷藤之捷,因言廟 廊諸臣推誠舉任,公心協贊,故臣得以展布四體,共成厥功,宜先行廟堂 之賞,次錄諸臣之勞。上不悅。先是上以守仁捷書示閣臣楊一清等,謂守 仁自夸大,且及其生平學術。”(《明通鑒》卷五四,嘉靖七年閏九月)究 竟是聽信了他人的挑撥,還是他自身的真實感覺,今日已難于得知,但世 宗已對陽明及其學說產生忌恨則是事實。至于他所忌恨的內涵,在次年禁 止王學的話中已顯露無遺,即所謂的“放言自肆”,尤其是桂萼等人所說 的陽明弟子對他的神化,什么“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不僅將陽明視 為圣人,且視為神人,作為專橫自大的世宗來說,是絕對難以接受如此事 實的。后來茅坤在回顧本段歷史時指出:“圣朝以來,弘治及今皇上,海 內文人學士,彬彬盛矣。而今皇上丙戌(嘉靖五年)、己丑(嘉靖八年) 之間尤為卓落數多,然往往不得擢用;間被用者,又不得通顯,或且不久; 其馀放棄罪廢者,不可勝數。……蓋人情樂軟熟,而忌奇偉;譽隨詭,而 惡激昂。而間有名賢,獨得薄日月,立功名者,非其偶會,必能竊黃老短 長之馀以自便于世也。”(《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一,《與李中麓太常書》) 而嘉靖八年對陽明死后恤典的剝奪,可以說正式拉開了這場禁錮王學的序 幕。首先是參加議禮的王學諸人,據《明史·方獻夫傳》曰:“霍韜、黃 宗明言事一不當,輒下之吏。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職二歲,三疏引疾。” (卷一九六)至嘉靖十五年后,眾人已被斥逐殆盡矣。下面看陽明弟子中 的幾位主要成員的遭遇:錢德洪(1496—1574),字洪甫,學者稱緒山先 生,浙江余姚人。嘉靖五年參加科考,不廷試而歸,十一年始赴廷試,出 為蘇學教授。后升刑部員外郎。因郭勛下詔獄,他根據獄詞定了郭的死罪, 可世宗不僅未治郭之罪,反將德洪投之詔獄,并且一直被囚到郭勛死方才 得出,被斥為民。(見《明史》卷二八三,《錢德洪傳》,又見《明儒學 案》卷十一)王畿(1498—1583),字汝中,號龍溪,浙江山陰人,亦參 加嘉靖五年科試,與緒山皆不赴廷試而歸,十一年始廷對,后官至武選郎 中。《明儒學案》曰:“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 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備顧問。貴溪草制:‘偽學小人,黨同妄薦。’ 謫賢外任。先生因再疏乞休而歸。”(卷十二,《王畿傳》)遂終生不仕。 季本(1485—1563),字明德,號彭山,浙江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 曾任御史之職。他先是因救他人而上疏獲罪,被貶揭陽主簿,稍遷弋陽知 縣。此時桂萼入居內閣,路過弋陽時,季本告知桂萼陽明之功不可被泯滅。 可桂氏非但未彰陽明之功,且奪其身后恤典。季氏后升任南京禮部郎中, 在任上與鄒守益相聚講學,“東郭被黜,連及先生,謫判辰州。”后來在 長沙知府任上又“鋤擊豪強過當,乃罷歸。”(同上卷十三,《季本傳》) 聶豹(1487—1563),字文蔚,號雙江,江西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 他在陜西按察司副史任上,“為輔臣夏言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 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系之。先生系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 既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逾年始出”(同上卷十 七,《聶豹傳》)當二人在詔獄中對面而坐時,盡管聶豹沒有埋怨夏言, 但他們的心情肯定是復雜而不平靜的。羅洪先(1504—1564),字達夫, 別號念庵,江西吉水人,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嘉靖十九年為左春坊贊善 時,世宗此時已常常不理朝政,“十二月先生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 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疾,遂欲儲 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也。’皆黜為民。”(同上卷十八,《羅洪先傳》) 羅洪先自此再未出仕,隱居終生;而唐順之以后尚出山御倭,并引起一番 爭議,此是后話。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江西泰和人。他的遭遇更帶有點 荒誕色彩。他是因上疏諫世宗在禁中建“雷壇”而獲罪的,“上怒,杖四十。 入獄,創甚,百戶劉經藥之,得不死。與楊斛山、周訥溪講學不輟,自壬寅 (嘉靖二十一年)至乙巳(二十四年),凡四年。秋八月,上齋醮,神降于 箕,為先生三人訟冤,釋之。未抵家而復逮,十月還獄,又二年。丁未(嘉 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夜,高元殿火,上恍忽聞火中呼先生三人名氏,赦 還家。”(同上卷十九,《劉魁傳》)晴川先生之得以生還,完全是靠了神 仙的大力幫忙,否則怕會就此死于詔獄之中,因為此時畢竟距世宗駕崩尚有 二十年之久,若指望新皇上登基而求得赦免,顯然是不可能的。陳九川,字 惟濬,號明水,江西臨川人。正德九年進士。他在正德時已經因諫武宗南巡 而被廷杖五十除名。嘉靖時復了太常博士的官位,但又遭到張璁、桂萼的算 計,因張、桂二人與費宏有隙,便指使通事胡士紳誣告他用貢玉賄賂費宏, 結果被“下詔獄榜掠,謫鎮海衛。”盡管后來他“遇恩詔復官”,但他已沒 有混跡官場的興趣,便致仕歸家講學去了。(同上,《陳九川傳》)魏良弼, 字師說,號水洲,南昌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他在任職禮科都給事中時, 因營救上疏言事而下詔獄的御史而被下獄拷訊。復職后又因彈劾張璁而 “受杖于殿廷,死而復蘇。”嘉靖十二年,“副都御史王應鵬上疏失職名下 獄,先生以細故當原,又下獄拷訊。”在短短的三年中,他“累遭廷杖, 膚盡而骨不續,”但卻“言之愈激”,連世宗都感到驚異:“上訝其不死, 受之輒赦,或且遷官,不欲其去。”真難說世宗對他是什么心情,鼓勵他 勇于直言嗎?但何以要將其折磨得“膚盡而骨不續”?是厭惡其直言放肆 嗎?那又何不將其貶官,或者斃之杖下以塞其口?真令人懷疑他是在玩貓 捉耗子的游戲。但張璁卻沒有世宗的耐性,當他復位后,終于利用京察而 將魏良弼罷官而去,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同上,《魏良弼傳》)沒有必 要再列舉下去了,僅此已足可見陽明心學在嘉靖中所遭受的挫折。王門弟 子的這些遭遇不能被視為偶然的現象,而是朝廷有意的舉措。世宗除了在 嘉靖八年下詔禁王學外,嘉靖十六年又下令明禁,《明通鑒》于本年四月 記曰:“壬申罷各處私創書院。時御史游居敬論劾王守仁、湛若水偽學私 創,故有是命。”(卷五十七)余繼登《典故紀聞》敘述更為具體:“嘉靖 時,御史游居敬請禁約故兵部尚書王守仁及吏部尚書湛若水所著書,并毀 門人所創書院,戒在學生徒勿遠出從游,致妨本業。世宗曰:‘若水留用, 書院不奉明旨,私自創建,令有司改毀。自今再有私創者,巡按御史參奏。 比年陽倡道學,陰懷邪術之人,仍嚴加禁約,不許循襲,致壞士風。”(卷 十七)看來世宗不僅對王學要嚴加禁止,而且只要有標新立異傾向者一律 在禁約之列。如果說這是從禁之一面而入手的話,世宗覺得仍然不夠,于 是他又在次年兼從正面立論,其詔書曰:“士大夫學術不正,邪偽亂真, 以致人才卑下,日趨詭異,而圣賢大學之道不明,要非細故。朕歷覽近代 諸儒,惟朱熹之學醇正可師,祖宗設科取士,經書義一以朱子傳注為主。 比年各處試錄文字,往往詭誕支離,背戾經旨。此必有一等奸偽之徒,假 道學之名,鼓其邪說,以獲士心,不可不禁。禮部便行與各提學官及學校 師生,今后若有創為邪說、詭道背理,非毀朱子者,許科道官指名劾奏。” (同上)本年在位首輔大學士為夏言,他于嘉靖十六年以少傅、武英殿學 士入閣。(見王世貞《內閣輔臣年表》,《弇山堂別集》卷四五)其實,早 在嘉靖十一年,夏言便向世宗上了《請變文體以正士習等事疏》,其中除 批評了“以艱深之詞飾淺近之說”的復古傾向之外,同時又指出:“刻意 以為高者,則浮誕詼詭而不協于中;騁詞以為辨者,則支離磔裂而不根于 理,文體大壞,比昔尤甚。”(《夏桂洲先生文集》卷十二)其矛頭顯然是 指向陽明心學的。故而上述世宗的那份詔書或者就是出于夏言之手也說不 定。然而夏言對心學的厭惡,對王門弟子的迫害又不能僅僅視為是個人間 的恩怨,正如他本人所說,他是以“天心”為心的,也就是說體現了朝廷 的意志。因而沈德符徑直指出:“世宗所任用者,皆銳意功名之士。而高 自標榜,互樹聲援者,即疑其與人主爭衡。”(《萬歷野獲編》卷二)則無 論是復古派還是陽明心學,均抹不掉這“高自標榜,互樹聲援”的特征, 當然也就在禁止之列了。 王門弟子萬士和曾如此概括嘉靖中期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之狀況: “明興,士大夫之學謹規矩,守格套,以為道在是矣,而或滯于事為形器 之末。有陽明先生者出,一剖其藩籬,倡良知以詔天下。世之從事其說者 欣欣然足矣,而或墮于空虛無著之歸。自是兩家角立,同異紛然。彼曰: 汝拘。此曰:汝放。”(《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訥谿周公墓表》,見《明 文海》卷四四四)可知當時譏心學為虛者不在少數,這種指責不僅來自程 朱理學,同時也包括陽明的朋友,如與其辯論的湛若水,以及著《明道編》 以批評陽明的黃綰等等。尤其是黃綰,他既是陽明的朋友,又是其弟子, 還是其兒女親家,從感情上他極為傾向于陽明是可以想見的,但他卻指出 陽明良知之學“空虛之弊,誤人非細。”(《明道編》卷一)這些批評當然 不是無中生有,王學在嘉靖中期的確有追求超越的虛無傾向,但這既不是 陽明的本意,也不是其弟子們的本意,而是時代壓迫的結果,只要看一看 當時士人的生存環境,便會對其有充分的理解。在此不妨以薛侃與周怡二 人為例。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他是王 門弟子中崇尚氣節的典型,亦具有為朝廷竭其忠誠的抱負。嘉靖十二年, 皇長子生二月而夭折,薛侃私下寫好一篇疏稿,根據祖制請求在親藩中選 擇一位賢達者,迎入京中作為守城王,等太子生下來時再令其至封國為王。 他本來是為朝廷而謀慮,不料卻卷入了夏言與張璁的黨爭之中。當時他將 此疏稿拿給同年進士太常卿彭澤看,而彭乃張璁之私黨,便暗自對張璁說: “儲事上所諱言,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為言所為,則罪不可解矣。” (《明儒學案》卷三十)于是便鼓勵薛侃說:“張少傅見公疏甚喜,可亟 上。”待上疏后世宗果然大怒,說薛侃私通藩王,欲窺皇位,敕令錦衣衛將 其逮捕,召集眾多官員審問他。葉權《賢博編》記此事曰:“上服朱衣,坐 便殿。命且不測。薛被拷,慷慨辯論,言臣具草,未敢奏,以示彭某,彼實 謄上之。就班中拽彭,并掠治,彭懵地。張遂大言,侃小臣,未應敢爾, 當是大臣主使為之,且言且目夏。薛知張意,因曰,幸寬臣刑,待臣拜命, 即招主使者。張令弛刑,薛叩頭畢,大呼太祖太宗皇帝鑒臨,張孚敬令臣 為稿,將有所中傷,不知其他。夏既得白,大罵孚敬奸臣,傾危善類。小 黃門入奏,上起更黃衣,有旨,張不問,夏罵朝失儀,以尚書致仕,而薛 與彭俱得謫戍。自是上遂主意于夏而薄張矣。”(《明史資料叢刊》第一輯, 第184—185頁)本條史料《明儒學案》亦有記載,只是細節略有出入而 已,故而應是實有其事。在此皇上時刻在猜疑士人存異心而危皇權,乃至 親自拷訊臣下;而張璁等人則在固一己之寵而排陷他人,薛侃夾在中間, 其為國之忠心不僅不能被理解,反倒遭到殘酷拷掠并被逼迫充任黨爭的工 具,他若聽任張璁的指使,也許會少受皮肉之苦,但卻成了十足的小人; 他若堅持自我氣節,則便會理所當然地領受百般地折磨。情急之下,他不 得不將內情和盤托出,顯示出其君子的風范。但夏言的得勢并未給王學帶 來絲毫的轉機,而且皇上在得知真情后依然不肯放過他,依然將其“謫戍” 而了事。在此種情形下,他還有什么理由不歸隱講學以終其生。從客觀上 講,他已沒有出仕的可能;從主觀上講,他在仕途上已難保自我氣節的完 善。那又何不歸山以獨善其身呢?因而,薛侃對陽明是深深理解的,他決 不信陽明之學為禪,故而逢有疑問者便予以辯難解答,誠如《明儒學案》 所言:“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有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涉虛。先 生一一辨之。”(卷三十,《薛侃傳》)周怡,字順之,號訥谿,宣州太平 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為吏科給事中。嘉靖二十二年夏,上 疏彈劾嚴嵩、翟鸞、許讚等大臣不和狀,其中說嚴嵩:“今嵩等在內閣則有 違言失色,見陛下則有私陳背詆,是大臣已不和矣,又安望其率下事上也。” 又解釋朝政敗壞之原因說;“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消; 開納銀之例,而府藏未能實;蠲租之令數頒,而百姓未能蘇。所以然者, 陛下焦勞于上而下無奉命之臣,凡所以利國家惠民生安邊徼者曾無遠慮, 惟知背公營私以市威福。”周訥之時論是否說到了點子上當然還可以討論, 但奇怪的是世宗的處理方式:“疏入,上以怡言諸臣不和論非不正,然其 本意直是謗訕,至其所論禱祠等事,咎在朕躬,何以不先言之,令具實對 狀。怡復具疏請罪。詔杖之闕下。”(《明通鑒》卷五八)既然所論“非不 正”,又何來“謗訕”之本意;既然承認“禱祠等事”是“咎在朕躬”,又 有何必要糾纏于“不先言之”?當然,無人能奈何皇上的強詞奪理,周怡 先生也只好趕快上疏請罪,但還是沒能躲過廷杖的刑罰,更嚴重的是,他 還與劉魁、楊爵一起經過了世宗一捉二放的荒誕而痛苦的經歷,而且這牢 獄生涯的時間整整長達五年之久。“丁未(嘉靖二十六年)冬,上修醮事, 三殿災,上大悟,下敕釋爵等,時漏下三鼓矣。公旦日謝恩就道。”(萬世 和《訥谿周公墓表》,見《明文海》卷四四四)周怡何以如此匆匆忙忙地 辭朝歸家,這務須先了解其在獄中所受的人生歷煉及其所產生的人生體 悟,方可得到滿意的答案。他有《囚對》一篇,是其獄中留下的產物,其 曰:“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枷,日有數人監之,喟然 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臥有枷則不敢以妄動, 監之眾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而始知檢也。’”(《明儒 學案》卷二五)此段材料除卻讓我們得知周怡先生在鎮撫司監獄中的具體 情狀外,同時也使我們領略了他亦莊亦諧的幽默。然而并非人人皆可具備 這份幽默,陽明心學的超越境界應該說幫了周氏不少忙。即使如此,在世 宗決定放過他時,他還是毫不遲疑地回鄉而去,再不愿在此享受那“疾徐 有節”的程朱理學功夫了。 在這種進退失據的境遇中,身處官場中非但難有作為,還要忍受巨大 的人生折磨與精神苦惱,要么成為君主專制的犧牲品,要么成為激烈黨爭 的犧牲品。當時的官場真可謂花面逢迎,人奸似鬼,那么正直的士人也就 理所當然地渴望歸隱而去。別的不講,就連批評陽明空虛的黃綰先生,最 終也不得不走向歸隱一途。對此,王慎中的經歷或可作為很好的證據。王 慎中(1509—1559),字道思,號南江,別號遵巖居士,泉州晉江人。嘉 靖五年進士,先后任戶部主事、吏部考功員外郎、禮部員外郎、山東提學 僉事、河南參政等職。他先是得罪了新貴張璁,被貶謫常州通判,然后又 得罪了權臣夏言,嘉靖二十年大計時,夏言“遂內批不謹,落其職。” (《明史》卷二八七,《王慎中傳》)從此他再未踏入官場。他有一首 《悔志》的五古詩,可以說充分體現了當時歸隱士人的心態,其曰:“早 受天刑拘,遂耽人爵貴。強學思干名,樂仕忘竊位。結交托時豪,然諾重盟 誓。只好朋友歡,拙為妻子計。約游見星移,赴急若飚至。掉舌常屈人,扼 腕獨憤世。出言譏王公,慕達不事事。傲睨多脫略,嘲謾無嚴志。輒希孔門, 自比周士肆。擇術謬毫發,千里遂不啻。反躬盡愆尤,考古何乖異?多憮豈 通方,易盈知小器。不聞長者言,下流良足畏。”(《遵巖集》卷一)這 其中當然有自傲的成分,也不能將其悔過看得太認真,但他通過這首詩畢 竟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如今這個世界已不再能夠容忍正直之士的存 在。因而他的自悔實際上是對時局的諷刺與控訴。否則他不必時時吟出如 此詩句:“已知直道非今好,莫向時人嘆路窮。”(同上卷七,《龍南崗久 謫不召詩以為嘆》)“從今雙眼看人世,攸忽浮云幾變更。”(同上,《生 日自述二首》其二)他甚至借溺亡者而憤激地說道:“鼓枻乘流一丈人,入 流不出返于真。厭盡世間塵垢濁,清川為濯去時身。”(同上,《挽王隱者 溺水死》)當這位老者入水歸真時,他的身上仿佛已堆積了過于厚重的世俗 塵垢,必須用清川之水洗濯潔凈,方可返回那干凈的另一個世界。其實, 在嘉靖士人的身上豈但堆積了世俗的塵垢,現實對他們的精神世界也造成 了壓力與傷痕,王慎中在五十歲左右即溘然而逝,難道與其精神的郁悶毫 無關系?嘉靖年間的確是士人歸隱傾向非常突出的,盡管他們歸隱的原因 與目的并不完全一樣,但都必須面對如何回避現實環境的壓迫與歸隱后如 何從新安排人生自我的問題,茅坤對此曾有過概括的敘述,頗可說明此中 情形,其曰:“中世以來,士大夫之棄官而去,能頹然恬勢利以飽丘壑者, 蓋罕矣!間有之,必其游且久,數郁郁不得志;或憤然憎世絕俗,而有所 不能容于時;不然,則他日故嘗有所憮于世之顯人巨公,而懼其以睚眥中 覆之也;又不然,則其位盈而年且逾矣,例當以請自去者也。若此者,彼 皆有所縻于中,特其遭困厭窘迫之故,不得不以釋而去,非所謂頹然恬勢 利以飽丘壑者也。是以去之久,稍稍或從而悔恨之。嗟乎,名之縻乎世, 抑久矣!茍非超然有所脫于外,以務悅乎其內,其能以介然無故去乎哉?”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十一,《送華補庵郎中還山序》)茅坤所概括的當 然不錯,士人的歸隱幾乎都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若非萬般無奈,很少有人 愿意放棄入世的追求,因為無論是為家族的利益還是為自我的成就,離開 現實的進取都無法實現。而難以歸隱的另一個原因便是歸隱后的難以持 久,在離開社會人群之后,歸隱者必須有忍受孤獨的勇氣與耐心,否則的 話,便會重新陷入世俗的泥淖,或造成極大的精神痛苦而有損身心的健康。 在正德時期,有李夢陽、康海諸人為例,在嘉靖時期,則有李開先為例。 李開先(1502—1568),字伯華,號中麓,山東章丘人。嘉靖八年進士。 官至太常寺少卿。他也是因得罪權相夏言而被削職為民的。關于他罷官家 居時的情狀與心態,殷士儋曾作過如此說明:“乃辟亭館召四方賓客,時 時以其抑郁不平之狀發之于詩。尤好為金元樂府,不經思索,頃刻千余言, 酒酣與諸賓客倚歌相和,怡然樂也。以是公之長篇短調幾遍海內,而名亦 隨之。人或以靡曼謂公者,公不顧。嗚呼!古賢智之士抱琬琰而就煨塵者, 或傍山而吟,或披發而笑,或鹿裘帶索而歌。要之,其中皆有所負而未庸, 故緣此以自泄。而世以恒度測之,遠矣!若公者毋亦有所負而欲泄歟!良 可悲也!”(《中憲大夫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李公墓志銘》, 《明文海》卷四三六)李開先象李夢陽一樣陷于酒中之樂,象康海一樣迷于 金元樂府,則其精神狀態顯然也是流于頹靡。所謂“有所負”,實在是難以 忘懷現實與不平;所謂“自泄”,實在是心底積蓄了太多的憤怒與郁悶。正 如茅坤所說,真正能夠棄官而去,恬然于勢利之外而欣然于山水丘壑者實 在太少了,也就是說,從人性的角度言,喜熱鬧而厭孤獨乃是人之共性, 或者說是人性的缺陷。要克服此種缺陷是非常艱難的,這除卻極大的忍耐 性之外,還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人生觀作為信念的支撐,而作為嘉靖士人 信念支撐的,恰恰就是王陽明的心學。因此,嘉靖時期陽明心學的演變趨 勢之一,便是求虛求適的傾向的加強,這既是王學中人解決自身人生困境 的必然,同時也為士人群體提供了人生信念的支撐。陽明弟子鄒守益在給 唐順之的一封信里說:“仆謂初入朝市恒懼紛華撓志,而渠謂久住山林無 良友,生意不免蕭索。因相顧以嘆,古今兩項癥候,耽擱了多少豪俊。安 得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繁劇而常定,岑寂而常充乎?”(《東郭鄒先生 文集》卷五,《簡唐荊川》)這既是鄒、唐二人的難題,也是嘉靖中其他士 人的難題,因而也就成了其心學討論中的重要論題。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