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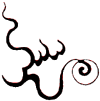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
|
第二章王陽明的心學品格與弘治、正德士人心態 第三節王陽明的求樂自適意識及其審美情趣 二、王陽明的審美情趣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 鳴。草露不辭芒屨濕,松風偏與葛衣輕。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王陽明全集》卷二十,《龍潭夜坐》)倘若隱去本詩的作者,也許讀者不 容易覺察是明代大儒王守仁的詩作。那暗暗花香與淙淙溪流,月下幽人與棲 鳥空山,露中草鞋與風中葛衣,都儼然一副隱士高人的情趣與襟懷,尤其是 “江北江南無限情”的結尾,更給人留下余韻悠長、含蓄不盡的無限暇想。 詩的確是寫得很美,若置之陶潛、王維集中,當無任何遜色之處。然而,它 又的確是陽明先生的詩作,那“臨流欲寫猗蘭意”的情趣,分明是一種高潔 的圣者境界,《樂府詩集》五八《琴曲歌辭猗蘭操》引《琴操》曰:“《猗蘭 操》,孔子所作,……(孔子)自衛返魯,見香蘭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為 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詞于 香蘭云。”原來在詩作高雅超然的背后,還隱含著作者圣人傷時之意與濟世 之情。因而陽明的情感便是如孔子“蘭當為王者香”的圣者生不逢時的意味, 其胸襟之高又非陶、王之類隱士所能比擬。圣者可寫灑落秀逸之詩,或曰哲 學家兼有審美情趣,這便是王陽明的特色。其實,對陽明此一特征學界早有 注意,《四庫全書總目》在指出其學術成就的同時,亦言其“為文博大昌達, 詩亦秀逸有致。”(卷一七一)近人錢基博之論述則更為明快:“而于時有大 儒出焉,曰余姚王守仁字伯安,特以致良知紹述宋儒象山陸氏之學;而發為 文章,緣筆起趣,明白透快,原本蘇軾;上同楊士奇、李東陽之容易,而力 裁其冗濫;下開唐順之、歸有光之寬衍,而不強立間架。”(《明代文學》26 頁)錢先生不僅指出陽明詩文之特征,還兼論其承前啟后之地位,確為透辟 之論。但陽明何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卻少有人涉及,即使有論及者,亦多為 浮光掠影之議。我以為陽明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由于他具有哲學家兼詩人 的氣質,或者說他除了有哲學家的思想外,更具備有文學家的審美情趣。但 認識到他有審美情趣并不算什么發現,可以說這乃是最普通的常識:能寫出 美學品味很高的詩文者,必具有高雅的審美情趣。然而若進一步追問,陽明 何以會具備此種審美情趣以及其審美情趣之具體特點,便決非三言兩語所能 解決,而這正是我們在此要解決的重點。 王陽明之所以具有高雅的審美情趣,首先是因為他擁有豐富飽滿的情 感。當年在陽明洞修道時,他曾一度有離世的念頭,后來由于難以割舍思親 之念而打消了此一追求,但由此也說明了他對于親情的執著。由此種儒家親 親的意念推廣開去,使他具備了萬物一體之仁的胸襟,也使其情感更加豐富。 在他悼念親友的一系列祭文中,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的這份深情。如他的 弟子徐曰仁亡逝,他撰長文以志念,文中追敘了二人的友誼以及共同求道的 志向,更表達了失去同志時的沉痛之情,所謂“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 又喪吾曰仁何哉?”(《王陽明全集》卷二五,《祭徐曰仁文》)此種以身相 贖的情感應該是真實的,否則他沒有必要在徐曰仁逝世十年之后,再寫下這 篇《又祭徐曰仁文》:“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 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窅嵯峨之遠岑。四方之英賢兮日 來臻,君獨胡為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欷歆,奠椒醑兮松之陰,良知之 說兮聞不聞?道無間于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云兮,誰同此音?” (同上)時間已過十年,他依然沒有忘記到這深山墓地,面對墳上青草而憑 吊這昔日的弟子,依然地哀傷之痛,依然地思念之深,依然地遺憾無窮。如 果說對親友弟子的情感尚帶有明顯的儒家倫理色彩的話,那么他在《瘞旅文》 中所表現出的情感,便是一種純潔高尚的詩人情懷。本文作于正德四年其遭 貶龍場時期,文中所祭之人是三位不知姓名的過路者。據陽明文中自述,那 是來自京師而先后病死于路旁的吏目及其所攜一子一仆。陽明出于同情心, 率二童子將其埋葬以免其暴骨于野,然后又為文以祭之。當然,在哀悼死者 的情感里,同時也包含著自悼的成分,此誠如他對不欲前往埋葬的兩位童子 所說:“吾與爾猶彼也。”從而引動得二童“憫然涕下。”但我以為主要的還 是對于不幸者的同情與安慰,此正如文中所言:“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 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群,陰壑之虺 如車輪,亦必能葬爾于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 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茍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 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可以說同病相憐是引發其 行為的原因,而為文致祭則是其強烈同情心的體現,我們聽一聽陽明為死者 所作的挽歌,便會更加體會到其視人若己的仁人之心:“連峰天際兮,飛鳥 不通;游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 之中;達觀隨遇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同上)最后,陽明 用自己達觀的人生態度來安慰死者,說盡管在這崇山峻嶺的隔絕之區,但以 天之角度視之,則廣袤的異域殊方又無不處于環海之一國,那么又何必一定 要生死于自己家中?又何必為不能生死于家中而悲傷恐懼?其實,從另一面 講,正是陽明具有這種異域殊方同處環海之中的寬闊胸襟,方使他有了仁者 的同情之心。陽明之所以能夠擁有如此豐滿深厚的情感世界,當然與其致良 知的心學有密切的聯系,他曾經說過:“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 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 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同上卷二,《答顧東橋書》) 良知的此種特性,實際上就是對他人發自內心深處的真誠關注,用儒學術語 講乃是萬物一體之仁的發露。然而,僅有此儒者仁人之心,對于詩人的審美 情感構成還是不夠的。因為審美情感是一種超功利的心靈境界,是只有詩人 才具有的獨特氣質,它不是要為對象提供實用性的幫助,自身更不打算從中 得到任何好處與回報,但卻又是發自詩人心底的最真誠、最純潔的關懷與體 貼。就象王陽明這樣,他在理性上當然知道自己對徐曰仁、無名氏吏目諸人 的悼念安慰沒有任何實際的價值,既不可能使之死而復生,又不能使之在天 獲知,但他依然不能控制自我的情感沖動,必欲一吐而后快,這便是審美的 情感,是一種雖無實用卻能夠深深打動讀者的藝術力量。沒有這種審美的情 感與藝術的力量,王陽明也許能成為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但卻不能成為一位 杰出的詩人。 王陽明之所以擁有高雅的審美情趣的另一原因,是他對自然山水的特殊 愛好。陽明的弟子欒惠在《悼陽明先生文》中,稱其師“風月為朋,山水成 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同上卷三八)此處所言的“風月為朋,山水 成癖”,指的正是他那與大自然相親融的濃厚興趣;而“點瑟回琴,歌詠其 側”,則是其超然自得的人生境界的寫照。用陽明本人的話說,叫做“性僻 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群。”(同上卷二九,《對菊聯句序》)而將此特性 進一步濃縮,陽明則將其稱為“野性”。而且這種“野性”并非其在某個時 期或某種場合方具有的愛好,而是貫穿其一生的性情,為此他曾在詩中對此 反復加以強調,如:“野性從來山水癖,直躬更覺世途難。”(同上卷二十, 《四明觀白水二首》其二)“風塵漸覺初心負,邱壑真與野性宜。”(同上, 《游清涼寺三首》其二)“混世亦能隨地得,野情終是愛邱園。”(同上 《林間睡起》)至于與此相近意思的詩句,那就更是不計其數了,略舉一二 如:“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同上,《寄隱巖》)“煙霞有本性, 山水乞骸歸。”(同上,《青原山次黃山谷韻》)“僻性尋常慣受猜,看山 又是百忙來。”(同上,《游廬山開先寺》)“平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 忘饑疲。”(同上,《江施二生與醫官陶野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芰荷衣。”(同上,《春日游齊山寺用杜牧之 韻二首》其一)“淡我平生無一好,獨于泉石尚多求。”(同上,《復用杜 韻一首》)完全弄清此種山水情趣何以會在某人身上產生的最初原因是相當 困難的,因為這其中既可能有先天的因素,也可能有后天的某種偶然機緣, 要解釋清楚這些,猶如要說明是什么原因使得某人成為了畫家、詩人或劇作 家一樣,往往是徒勞無益的。但有些東西卻是可以解釋清楚的,比如是何種 因素加強了這些自然山水情趣,以及詩人追求此山水情趣的主要目的等等。 陽明之所以如此地酷愛自然山水,是因為他在其中可以享受到人生的樂趣, 而這種人生的樂趣又往往是與官場中的人性壓抑與勾心斗角相對應的,這便 是所謂的“病夫久已逃方外,不受人間禮數嗔。”(同上卷十九,《山中懶 睡四首》其一)在陽明的詩作中,自然山水與官場功名往往被置于價值判斷 的兩端,并經過權衡比較,然后再顯示出其追求山水之樂的人生志趣,我們 看他的《次魏五松荷亭晚興》詩:“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 光于我能留意,世味酣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 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同上卷二九)盡管松陰野鶴的自然風光 是誘人的,但沉酣于“世味”之中者也大有人在,可見人生志趣的選擇是難 以避免的。如果要具備“窺物外”的“心神”,你便不能在乎“鄉評”的世 俗價值判斷。用他另一首詩中的話說便是:“但得青山隨鹿豕,未論黃閣畫 麒麟。”(同上卷二十,《別余縉子紳》)亦即你要鐘情于自然山水,就不 要再考慮功名的追求。當然,不能認為王陽明已將其人生價值定位在歸隱山 水的志趣上,他一生的主要追求無疑仍為救世濟民的現實進取。盡管他有時 仿佛非常厭惡官場,并為自己的入仕感到痛心疾首地后悔,說什么“一自浮 名縈世間,遂令真訣負初心,”于是便表示“最羨漁父閑事業,一竿明月一 蓑煙。”(同上,《即事漫述四首》其四),但我們還是寧可將此視為是他 對官場黑暗的批評與堅持自我節操的宣示。然而,王陽明向往山水自然的愿 望又決非一時的憤激之言,象李夢陽等人,他們口中說歸向自然是人生的最 大樂趣,但在山水中卻并不能做到心境悠然,而只能靠飲酒來排解心頭的苦 悶。陽明雖未將自然作為他唯一的人生歸宿,而始終是用之則行舍即休的兩 可態度,但他卻是從山水中真正獲得了人生的樂趣,你看他的《睡起寫懷》, 是何等地從容悠閑:“江日熙熙春睡醒,江云飛盡楚山青。閑觀物態皆生意, 靜悟天機入窅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未須更覓羲唐事,一 曲滄浪擊壤聽。”(同上卷十九)一覺踏實的春睡,起而坐對青郁的楚山, 在一片生意的萬物自然中,他心悟了“天”之玄機,于是他化身魚鳥,隨地 可樂,便渾然是羲皇上人,這決非未獲真實體驗者所能言說的。陽明將此種 人生之樂稱之為“自得”,所謂“鳴鳥游絲俱自得,閑云流水亦何心?” (同上卷二十,《山中示諸生五首》其一)此所言“自得”固然與其良知境 界難以分開,但卻與其所說的成物成己的圣人境界不全然一致,這種“自得” 是忘懷物我的個體人生受用,是在現實進取難以實現時的人生自我安頓,他 在正德八年所作的《梧桐江用韻》一詩對此作出過很好得描述:“鳳鳥久不 至,梧桐生高崗。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遺 音滿空谷,隨風遞悠揚。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顏子豈忘世,仲尼固遑 遑。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同上)他又一次表現了“歸滄浪”的人 生意向,而濯足滄浪無疑是潔身自愛的行為。他的“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 臧”的自得其樂,當然不是要否定孔子的“遑遑”濟世,而是因為世事難為, 不得不走向山水而保持自我的清白,盡管個體的受用并非其首要的人生選 擇,但一旦選擇它時,卻照樣獲得了從容悠然的審美快感。這種快感之所以 是審美快感,是因為它具有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心靈感受,它猶如前所言 “鳴鳥游絲”般的任意自由,“閑云流水”般的從容自在,表現在其詩歌意 境中,它既可是“恬愉返真澹,闐寂辭喧豗”(同上《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的平靜,亦可是“飲水曲肱吾自樂,茆堂今在越溪頭”(同上《寄浮峰詩社》) 的淡泊,但更可以具有如下的高超境界:“駕蒼龍,騎白鹿,泉堪飲,芝可 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黃庭》石上讀。”(同上卷 三二,《游白鹿洞歌》)從他這些詩作中,當然可以體味出濃厚的莊禪意識, 是其求樂傾向的另一側面,在中國歷史上,莊禪意識對于審美境界的貢獻, 的確較儒家思想要大得多,這在王陽明身上也不例外,當他高吟“吾儕是處 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游”(同上卷十九,《尋春》)時,他的確是自覺認 同了深受玄學影響的六朝名士,則其強烈的老莊意識也就不言自明了。 王陽明之所以擁有高雅的審美情趣的第三個原因,是他具有瞬間感受美 并將其表現出來的能力。此乃詩人所獨具的審美能力,也是決定其審美情趣 的最直接的因素。我們來觀其《山中示諸生五首》(同上卷二十)中的其中 三首,以具體感受其此種能力:“滁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 溪山正暮春。”(其二)“桃源在何許,西峰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 花去。”(其三)“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閑。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其五)在第一首中,作者已定下了“鳴鳥游絲俱自得,閑云流水亦何心” 的審美基調,即朝然自得的情懷,下面便是要從各個角度來突出此一基調。 第二首抓住“暮春”的季節特征,將眼前的“滁流”與孔子時的“沂水”相 聯結,從而使現實與歷史接通,當年曾點于暮春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的人生情調,仿佛與眼前景象相重合,取得了異時共域的審美效果。 第三首則又抓住溪邊桃花此一美的意象,將其與陶潛所建構的理想國桃花源 相溝通,當他沿溪踏花而去時,仿佛就要走向那美好的源頭,為人留下了無 限的暇想空間,非但有美之景色,更有陶潛高潔超然的人格蘊涵其中。第五 首則從正面來表述此種審美情調,坐于小溪之旁而靜觀流水,遂進入一派平 靜悠閑的境界,心猶如流水般清澈自然,不知不覺中,月亮已升上山頭,只 有斑駁的松影灑落衣上時,方才感到時間的流動。在此,作者將流水、山月、 松影三種景象迅速加以拼合,遂形成了自然、皎潔與搖曳多姿的格調,準確 地傳達出了自己超然自得的審美心境。正是有了這種準確感受自然美的能力 與迅速融歷史、自然、自我情感于一體的豐富想象力,才保證了王陽明作為 一個詩人的品格,因為再高超的人生境界也必須最終落實到詩境的構造上, 方可顯示出其審美的情趣。 從現代美學觀念看,王陽明所擁有的豐富飽滿之情感、對自然山水之特 殊愛好以及瞬間發現與把握美的能力諸種因素,適可構成一種意蘊深厚而又 超越功利的高級審美品格。他豐富飽滿的情感,使作為哲學家的王陽明在其 一生中重視情感因素對人生的意義,但又由于他具有擺脫世俗而向往自然山 水的超然胸懷,又使他不會固執于一己私情而顯得俗氣狹隘,他曾經如此論 述樂與情的關系說:“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于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于七情 之樂。雖則圣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 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 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同上卷二,《傳習錄》中)此處所言的 樂之所以不同于世俗中的七情之樂,是由于它已超越世俗的榮辱得失,它既 與現實利害拉開了一定的距離;但又其是人生自我所獲取的安順和樂的自得 境界,是一種高級的人生享受。當然,陽明此處所說并非專對審美而言,但 他主張圣賢之樂既不脫離七情之樂而又超越七情之樂的觀點,顯然是與其審 美觀一致的。他在作于正德八年的《書東齋風雨卷后》(同上卷二四)中, 則是專門論述了人生現實感受與其審美感受之間的不同,他說:“悲喜憂快 之形于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為愁苦凄郁之鄉,而今以為樂事者,有 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嘆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人之 情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與場合的改變而有所不同,這自然是人之常情,非詩 人所獨有。但陽明論述的重心顯然并不在此,于是下面才會接著說:“吾觀 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 其所如矣,而猶諷詠嗟嘆于十年之后,得非類于夢為仆役,覺而涕泣者歟? 夫其隱幾于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詠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 有幽閑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能將原來的凄苦之感遇轉化為幽閑 自得之趣,是衡量其是否達觀以及有無審美情懷的標準,如果一味執著于實 際感受而不放,則無異于夢中做了仆役而醒后仍涕泣不止。所以他又假設以 推言之:“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 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灑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 矣!而和者以為真有所苦,而類為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以與言夢者。” 真正美的情感是在經過一段時間沉寂之后,再加以反觀而產生的感受,而不 是當時感受的真實記錄。也就是說只有當事件經歷者從中抽身而出,與其保 持一定距離后,才能獲得真正審美享受。可那些和詩者卻依然認為“真有所 苦”,依然去寫一些“垂楚不任之辭”,則無異于癡人說夢,實在是不懂得 “灑然而樂”的美感。許多人之所以不能化凄苦經歷為自得之趣,是由于他 們不具備達觀的態度與超然的胸襟,也就與現實人生拉不開距離。陽明則恰恰 具此優勢,在達觀的人生態度上,他很少許可別人,連詩仙李白謫夜郎而“放 情于詩酒,不戚戚于困窮,”他認為也只不過是“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 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同上卷二八,《書李白騎鯨》)不少學者都認定 陽明之文乃出于東坡,其要在于“達”之一字,王世貞即曰:“文章之最達者, 則無過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王資本超 逸,雖不能湛思,而緣筆起趣,殊自斐然,晚立門戶,辭達為宗,遂無可取。 其源蓋出自蘇氏耳。”(《藝苑卮言》卷五)王世貞之評價是否恰當且置不論, 但他指出陽明之文的超逸放達乃出于蘇軾則是許多人的公論,而陽明本人卻 認為東坡尚未達此最高境界,故曰:“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 生自謂放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于世也。偶披此圖,書 此發一笑。”(《王陽明全集》卷二八,《書三酸》)這自然是戲謔之言,其 實,他的不容于世又何嘗下于東坡?在此無非借東坡以自況罷了,若稍加留意, 連本文風格亦酷似東坡。從此種達觀超然的人生態度出發,陽明如此描述他 理想中的創作心境:“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 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 閑坐時,眾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 造物者游。”(同上卷二四,《示徐曰仁應試》)這當然是在論科舉應試之文 而非文學創作,然而科舉之文尚且須有“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的超然 心境,更勿論審美的文學了。因此,關于王陽明理想審美心境的看法,我以 為下面一聯詩最足以概括:“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化前。”(同上卷 二十,《別諸生》)審美心境不能離開“日用常行”,倘若真正斷絕了世俗的 念頭,成為不食人間煙火的隱士,他便會視美而不見,更沒有必要去特加強 調,比如那得道的佛門禪師,他的人生境界便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平淡 無奇,或者說是“春來草自青”的悄然無言。只有象王陽明這樣,既超越了 現實的束縛,歸向了自然,卻又能翻轉過身子,去發現,去欣賞,去詠嘆自 身對自然之美的享受,才算是審美的情調。此種情調是超世而不離世,絕俗 但不絕情的人生境界。很難說陽明先生時時都處于此種境界中,但他曾經擁 有過此種境界則是無疑的。而這一切都得力于他那豐富飽滿的情感、超然離 俗的山水情趣及其捕捉美的能力的綜合效應。 就實際情形而言,由于王陽明一生的精力主要用之于講學與事功,文學 創作只不過是其副業。盡管他很看重人生的受用,也具備高雅的審美情趣, 但所取得的實際成就畢竟是有限的,因而文學史上未給他以重要地位并非沒 有道理。從此一角度,說他的文學成就被其心學所掩是可以成立的。但從文 學思想史的角度看,正因為其心學對其文學有直接的影響,從而使王陽明在 明代甚至在近古的文學思想的演變過程中具有了重要的意義。這主要體現在 對心與物關系的理解上。在宋代之前,感物說在文壇上占著絕對的主導地位, 從《禮記·樂記》的“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文心雕龍·物色》的 “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物在文學發生過程中都占據著第一位置,在唐代 形成的以情與景之勻稱渾融為主要特征的意境說,可以說是感物說所取得的 最豐碩的成果。此種感物的文學思想隨著中唐以后倡言見性成佛的南宗禪的 流行,以及宋代理學的發展,其一統的局面逐漸發生了松動。但由于禪宗的 宗教性質與理學的拒斥情欲,使它們在審美上未獲得應有的正面效應,因而 感物說的主導地位也就沒有受到根本的動搖。王陽明是中國文學思想從早期 的感物說向晚期的性靈說轉變的關鍵人物之一。在其心學體系中,對心與物 關系的規定,毫無疑問心已上升到主導的地位。王陽明當然沒有否定物,《傳 習錄》曾記曰:“先生游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 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 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 不在你的心外。’”(《王陽明全集》卷三)在此,物對于心當然不是可有可 無的,沒有它,便無法證得此心的功能;然而從價值取向上講,物的自在是 沒有意義可言的,是人的主觀心靈的觀照,才使得花一時“明白”起來。從 詩學觀念上看,這也可以稱是一種境界說,只有當心靈與物相遇時,才能取 得“明白”的詩意,其中缺少任何一項,也就構不成詩之境界。正是由于此 一原因,王陽明的詩可以用意境的理論加以剖析,并會得到較高的評價。但 從發生論的角度講,主觀心靈在心學體系中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在朱熹 那里,“格物”是究極物理之意,人心所具之天理與萬物所具之天理如萬川 印月,并無主次之分;而在陽明這里,“格物”是正不正以歸于正之意,物 的意思也被規定為“意之所在”亦即事之意。當王陽明說:“天沒有我的靈 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 辨他吉兇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萬物了。”(同上) 由此推衍,當然也可以說,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成其美了。在此,人之靈 明成了一切的主宰,而物則退居于次要的地位。盡管王陽明并沒有在文學理 論上明確地提出性靈說,但在實際創作中則已顯示出重主觀、重心靈、重自 我的鮮明傾向。且不說他的許多講學詩幾乎沒有什么物象的介入,如:“良 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卻是誰?”(同 上卷二十,《答人問良知二首》其一)此已屬有韻之講學議論,固無詩美可 言;即使那些表現審美情趣的詩,也多以賦體寫之,如:“中丞不解了官事, 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為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同上,《重游開先 寺題壁》)不少人認為陽明的詩有率意不計工拙的特點,究其實質,則是其 重心靈愉悅與心靈表現的必然結果。更須留意的是,陽明詩作中有許多表面 上看是詠自然景色的詩,但若尋其脈絡,依然是主觀心靈作為全詩的主線而 貫穿始終,略舉數首以為佐證: 老檜 老檜斜生古驛旁,客來系馬解衣裳。托根非所還憐汝,直干不撓終異常。 風雪凜然存節概,刮摩聊爾見文章。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從渠拂漢蒼。 (同上卷十九)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山鳥歡呼欲問名,山花含笑似相迎。風回碧樹秋聲早,雨過丹巖夕照明。 雪嶺插天開玉帳,云溪環碧抱金城。懸燈夜宿茅堂靜,洞鶴林僧相對清。 (同上卷二十) 太平宮白云 白云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暫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同上) 第一首是詠物詩,從表面看似乎與前此的同類詩作沒有太大的差別,也 是借物以詠人。但若稍加品味,便會發現該詩依然有其獨特之處,詩雖題名 為《老檜》,可老檜并沒有構成完整的形象,作者所關注的重心乃是其自我 人格與人生理想,也就是說在“我”與物之間未能達到藝術上的均衡狀態。 第二首好像是純粹的寫景詩,因為作者并未直接在詩中出現,整首詩全是由 景物組成的,然而在閱讀它時又仿佛處處都留有作者的影子,且不說那“歡 呼”的山鳥與“含笑”的山花是直接向作者表示欣喜之情的,即使那穿越碧 樹的秋風,雨后丹巖的夕陽,有意展開的雪嶺玉帳,含情抱城的碧色云溪, 乃至靜謐的懸燈茅堂,清高的洞鶴林僧,無不涂上了作者的主觀感情色彩, 無不是為了表現作者的喜悅之情,用王國維的話說,這些全都可視為有我之 境。最后一首則完全圍繞作者的主觀自我而展開,與其說白云有心,倒不如 說是作者有意,充滿了人情味的白云實際上是作者自然之趣的外化,白云對 作者的戀戀不舍實際上是作者自己對自然山水的一往情深,因而本詩也不再 需要用傳統的意境標準加以衡量,而須代之以自然活潑的人生之趣。此類風 格的詩在前人那里當然也可以時有發現,但作為一種整體風格出現在陽明的 創作中卻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因為在此種風格的背后有著深厚的思想背景 作為支撐,它預示著一種新的文學思想潮流已經產生。盡管這種現象在王陽 明身上尚未作出充分的顯現,或者說雖然已經顯現卻未能引起人們的足夠關 注,但在后來的文學潮流中,卻日益顯示出其巨大的影響力,如果認真追索 明代中后期文壇所流行的文學思想,比如唐宋派與徐渭的本色說,李贄的童 心說,公安派的性靈說,湯顯祖與馮夢龍的言情說,都或直接或間接地受到 過王陽明的影響。從此一角度講,說王陽明的思想是明代中后期諸多文學思 想的哲學基礎是并不過分的。正是從梳理文學思想的發展脈絡的價值上,我 以為應該對王陽明的審美情趣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學思想特征作出較為深入的 研究。 |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