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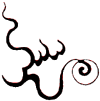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
|
第二章王陽明的心學品格與弘治、正德士人心態 第二節良知說所體現的陽明心學境界 三、“致良知”說產生的時代原因及其王陽明的人生實踐 正德十六年對陽明心學來說是個值得重視的年頭,因為在本年王陽明正 式提出了他的“致良知”的學說,而本年陽明先生恰為五十歲,依先圣的說 法,正好是知天命的年齡。這也許是個巧合,但就陽明的生平而論,他在本 年提出致良知卻有充分的人生依據,《年譜二》載:“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 教。先生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 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后圣,無弗 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 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自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 如意,雖遇顛風逆浪,柁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王陽明全集》卷 三四)在此,可將陽明所提出之致良知分為兩方面解:一是堅信良知在我, 保證仁者與萬物同體的儒者胸懷,無論在任何艱難境遇中均不失其責任感, 此即為“操舟得柁”、“柁柄在手”。二是超越的高尚境界,即不執著于任何 外在的利害榮辱,保持吾心之空靈虛明,從而擺脫險惡環境與自我焦慮的雙 重困惑,此即所謂“忘患難,出生死”、“免沒溺之患”。而這兩方面又是互 為關聯的,正鼬忘懷物我的超越境界,為萬物一體之仁的現實關懷提供了可 能性;同時良知在我的把柄在手的自信,又反過來增強了自我的超越。就陽 明心學的整體而言,仁民愛物顯然是其主要目的。然而就其當時提出的心理 動機而言,則如龍場悟道一樣,乃是為了解決其人生自我所面臨的困惑焦慮。 可以說,作為具備了儒者品格的陽明先生,仁民愛物是其終生一以貫之的、 不言而喻的人生志向,而如何實現此一志向才是他不斷探索的話題。陽明先 生曾說過:“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后便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 (引自錢德洪《刻文錄序說》,見《王陽明全集》卷四一)這固然突出了龍 場悟道對陽明心學產生的重要,但卻同時留下了一個疑問,即何以他長期提 不出良知二字,必待其五十歲時方始提出。其實,這與陽明本人的學術品格 直接相關。從陽明上述致守益的信中,可以看出致良知說對于他自身生命存 在的重要。他一貫主張心與理合一,“誠諸其身”,“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 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草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 (同上卷六,《寄鄒謙之三》)反過來,他的學說主張的提出,也都是以其 自我的人生經歷與人生體驗為前提的。因此,若欲回答陽明何以在正德十五 年前后提出致良知的疑問,就必須了解此時陽明先生的遭遇與心境。在這方 面,盡管已有人進行了初步的探索,但將其梳理得具體清晰者于今尚未見到。 ⑧陽明曾說良知二字乃是自己從百難千死中得來,但到底這百難千死包括哪 些內容?我以為起碼包括宸濠之變,忠、泰之難與嫉功陷害這三個主要階段。 以下便分而述之。 宸濠之變是王陽明在正德十五年前后所面臨的第一個嚴峻的人生考驗。 盡管寧王朱宸濠之反意早有跡象顯露,但在其舉事時依然造成了人心的極度 恐慌。這不僅是因為武宗的荒唐行為導致了朝政的混亂,以致人們很難相信 朝廷平息此次叛亂有必勝的把握,更重要的是這又牽涉到了皇室內部權力爭 奪的敏感問題。在這方面,明代士人留下了太多的人生慘劇與人生尷尬。方 孝孺氣節凜然卻被慘烈地禍滅十族,那可歌可泣的歷史場面已深深印在每一 位士人的心中;齊泰、黃子澄、練子寧因向建文帝建議削藩而被成祖列為奸 黨,他們被死后滅族的史實猶清晰地書之于簡冊;還有景泰年間的兵部尚書 于謙,他擁有再造社稷的大功卻終難免橫尸西市的下場,那凄慘的情景仿佛 就發生在昨日。因而凡是稍有頭腦的士人都不會去介入此一敏感的禍區,如 宣德元年朱高煦叛亂時,楊榮極力勸諫宣宗御駕親征,其原因便是臣子處此 類事顧慮太多,誠如夏原吉所言:“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臨事可知。”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傳》)正德年間此種情形并未有大的改變,鄭 曉后來曾回憶說:“寧藩反時,余時年二十一,應試在杭。見諸路羽書,皆 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曰江西巡 撫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只,傳言有變。惟陽明傳報,明言江西寧 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今言》卷四)這種徘徊觀望的態度固然 有對個人身家性命的顧慮,但也與當時政治形勢的復雜紛亂有關,據徐階說: “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為內應,方其崛起,天 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徐階《陽明先生畫像記》,見《王陽明全集》卷四十) 就在這形勢不明的情形下,陽明卻一面毅然“明言”寧王謀反,并且還詐稱 “欽奉密旨”;同時又上疏痛責武宗說:“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 心騷動,尚爾巡游不已,致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 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懔骨寒心。”(同上卷十一,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他可以說將雙方都指責了一番,沒有為自己留下 任何回旋的余地。拿陽明的精明與干練,他當然知道自己這樣做的危險,所 以才會采取如下的斷然措施:“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 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為賊辱!’”(《陽明先生畫像記》,同上卷四 十)是什么東西使他具有了如此義無反顧的決心?在當時,他既缺乏朝廷強有 力的支持,手中又沒有足以致勝的兵力,可他硬是要用地方的鄉兵義勇去平定 號稱有十萬之眾的寧王叛軍。唯一的解釋便是儒家拯亂救危的責任心,或者 是如其所稱的良知。然而在此千鈞一發的危急關頭,若沒有義無反顧的決心 與鎮定自若的心態,是絕對不會取得任何實際效果的。陽明靠了他的良知, 既態度堅決,又心境空明,所以才會象李贄所稱贊的那樣:“旬日之間,不 待請兵請糧而即擒反者。唯先生能之。”(《續藏書》卷十四)后來,有許多 明代士人雖不否定陽明的事功,但卻認為那是他善于用兵,與其良知之學沒 有關系。客觀地講,陽明在正德年間所以能屢次平亂立功,的確與其年輕時 的喜讀兵書,留心軍事密不可分。但也與其學術素養不無關系,他本人就曾 說過:“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焉。凡人智能相去不 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那么又如何使 此心不動呢?陽明認為:“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于欲, 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言。”(引自錢德洪《征宸濠反間遺 事》,見《王陽明全集》卷三九)依陽明的心學理論,人若能達超越生死利害 的無我境界,心便能虛,虛而能靜,靜而能定,定而能明,而明了便會有正確 的決斷。《年譜二》曾記述了他心定神明的實際事例:“先生入城,日坐都察 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后。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須 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眾咸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卻, 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后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 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偽,但傷死者眾耳。’理前語如常。旁觀者服其 學。”(同上卷三四)弟子們在為其師作年譜時,對此類事容或有些夸張的成 分,但陽明在行軍打仗之際常常講學不輟,卻是有很多記載的。也許鄒守益 的敘述更接近于真實些:“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軍中講學。 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 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退而就 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引自《征宸濠反間遺事》,見《王陽明全 集》卷三九)退一步講,即使并未完全做到心中絲毫不驚,但能夠做到驚不 亂其神,而喜不流于色,也可謂大智大勇了,而這應該是陽明從其自信良知 中獲得的真實受用。 忠、泰之難是陽明在正德十五年前后所經歷的第二個人生考驗。此次較 上次更加危險而難于應付,因為上次是對待叛亂的寧王,盡管危險但卻有措 手之處,而本次卻是來自朝廷內部,陽明完全失去了主動。所謂忠、泰是指 武宗的親信大臣提督軍務太監張忠與安邊伯邊將許泰。當武宗得知寧王反叛 時,認為正好為施展其軍事才能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便親率數萬士卒南下平 叛。然其剛至涿州,守仁擒獲宸濠之捷報亦至。武宗大為掃興,便將捷報隱 而不發,令大軍繼續南下,并命忠、泰先至南昌。張、許二人為討好武宗, 竟建議陽明將寧王釋放,以待武宗親自捉拿。陽明豈能拿國事做兒戲,自然 拒絕了他們的無理要求。于是,忠、泰二人及其黨羽便對陽明多方構陷,必 欲致之死地而后快。關于當時的危急情狀歷史上曾有過大量的記載,其弟子 陸深用了“讒構朋興,禍機四發”來形容此時陽明的處境,并說:“武宗南 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構陷,危疑洶洶,群小偵伺旁午于道,或來先生 家私籍其產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為,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陸深《海日 先生行狀》,見《王陽明全集》卷三八)可知當時確實弄得人心惶惶,不知 所措,仿佛大禍立時便要臨頭似的。那么,張忠、許泰之輩到底為陽明立下 了什么罪名呢?詳細情況已經被歷史的迷霧所遮飾,但有一點是確鑿無疑 的,那便是他們曾誣險陽明“必反”:“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 正保全之。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之?’對曰:‘召必不至。’有召面見, 先生即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 庵中,適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 有返江西之命。”(同上卷三四,《年譜二》)“謀反”的罪名非但有殺身之 危,且更有滅族之禍。故而當時陽明之父海日翁乃言“宸濠之變,皆以為汝必 死矣,”(同上)陽明本人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壓力,故《年譜》記曰: “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為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 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 以窺父而逃,吾亦終生長往而不悔矣!’”(同上)但現實不容許他逃走,所 以他依然要面對這危機四伏的艱險境遇。于是,他再一次動用其良知的理論, 在九華山上以“每日宴坐”(同上)的超越從容來忘卻現實對其自我的威脅。 關于此一段陽明之心境,我們可在其留下的游九華山詩中得到具體的感受。 他有過“盡日巖頭坐落花,不知何處是吾家”(同上卷二十,《巖頭閑坐漫 成》)的迷茫,也有過“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同上《重游化 城寺二首》其一)的不滿,但由此卻正好看到了他在危境中“忘世”的本領。 他自信良知,心無愧疚,故而他無畏無懼;他心地平靜,魂定神明,故而他 應付自如。“謾對芳樽辭酩酊,機關識破已多時,”(同上《勸酒》)盡情豪 飲,成竹在胸,是何等地灑脫,又是何等地自信!“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 月更清輝。”(同上《將游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其二)等九華于沂水,效曾 點之詠樂,是何等地超脫,又是何等地趣味盎然!而所有這一切,均取決于他 那“我本無心云自閑”(同上《登云峰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其二) 的良知境界。“飄飄二三子,春服來從行;詠歌見振興,逍遙無俗情。各勉 希圣志,毋為塵所縈。”(同上其一)倘若你不了解陽明的境界,你不把握良 知的真髓,你肯定不會相信這是出于身陷危境的陽明子之手。也許《登云峰 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一詩最足展示此時的陽明心境: 九華之峰九十九,此語相傳俗人口;俗人眼淺見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 我登華頂拂云霧,極目奇峰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劍長戟攢武庫。有如 智者深韜藏,復如淑女避讒妒。諳然避世不求知,卑己尊人羞呈露。何人不道 九華奇,奇中之奇人未知。我欲窮搜盡拈出,秘藏恐是天所私。旋解詩囊旋收 拾,脫穎露出錐參差。從來題詩李白好,渠于此山亦潦草。曾見王維畫輞川, 安得渠來拂纖稿?”(同上) 詩可分兩層意解。在表層上,它顯示了九華山千奇百怪的勝境,抒寫了 作者游山時的審美感受;但更重要的是其深一層的意蘊,因為那里邊有陽明 的苦衷,陽明的自負,陽明的智慧。“淑女避讒嫉”,是其飽諳世事險惡的苦 衷;“巨壑”藏玉林若大劍長戟之武庫,是其身懷奇才的自負;“有如智者深 韜藏”,是其避害全身的智慧。而“諳然避世不求知,卑己尊人羞呈露”之 句則更是隱含著陽明難于言說的一段史實。當時為使武宗滿足虛榮心而不入 江西擾害百姓,陽明乃重上告捷文書,聲稱其平定寧王叛亂乃事先已親奉“威 武大將軍”方略,故而方能取得如此大功。許多士人對此不理解,認為跡近 諛諂,但從上述詩句中,人們應該理解陽明的那份苦心。避世遠害是其智, 卑己尊人是其德,關心百姓是其仁,更何況還有其超然不群的高潔境界呢? 陽明后學萬廷言在其《陽明先生重游九華詩卷后序》(見《明文海》卷二六 九)中,曾將陽明此刻之心態及其與良知境界之關系剖析得條理清晰,深入 具體,不妨引述如下: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廷言誦陽 明先生重游九華諸詩而論其世,其毅皇南巡金陵召見之時乎?是時先生既擒 濠逆,兇豎攘功,陰構陽擠,入在左腹,召至采石,而咫尺不奉至尊,禍且 莫測,蓋亦危矣。彼怵于死生禍福之交者,垂首喪氣,伈伈俯俯不能自存; 而世稱敏略之士,又投機乘變,僥幸于須臾,固皆不足道。其豪杰君子善處 患難,不忘其忠,亦不過悚息待罪,達旦不寐,繞床嘆息而已。固未有損得 失之分,齊生死之故,洞然忘懷,詠嘆夷猶于山川草木之間,樂而不忘其憂, 油油然不失其恭如先生者也。嗚呼!此九華之詩所為作,而誦之者之當論其 世歟!蓋其良知之體虛明瑩徹,朗如太空,洞視環宇,死生利害禍福之變, 真陰陽晝夜慘舒消長相代乎?吾前遇者而安,觸之而應,適昭我良知變見圓 通之用,曾不足動其纖芥也。其或感觸微存凝滯,念慮差有未融,則太虛無 際,陰翳間生,蕩以清風,照以日月,息以平旦,煦以太和,忽不覺轉為輕 云,化為瑞靄,郁勃之漸消,泰宇之澄霽,人反樂其為慶為祥,而不知變化 消熔之妙實在。詠歌夷猶之間,脫然以釋,融然以解,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故觀此詩而論其世,然后知先生之樂,乃所以深致其力,伊川所謂學者學處 患難,其旨信為有在。益知先生千古人豪,后世所當尚論而取法者也。茍徒 詞而已,騷人默士工為語言者耳,何足知先生者哉!嗚呼!先生所處死生利 害之大猶若此,況富貴貧賤失得毀譽之小!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東溪人。他是羅洪先的弟子,受其師的影 響,他亦有隱居以求寂體的傾向,故能于陽明先生之超越境界有深切的體會。 陽明靠了自己的學養,不僅在千鈞一發的當口能保持鎮定自若的心境,從而 度過了生命的危境,而且為明代士人樹立了處亂不驚、臨危不懼、若鳳凰翔 于千仞之上的大丈夫榜樣。 嫉功陷害是王陽明在正德十五年左右經歷的第三個人生考驗。正德十六 年武宗病逝,世宗因武宗無子而以藩王的身份入繼大統,首輔楊廷和利用皇 權交接的關口而大力革除正德朝舊弊,朝政頓時為之一新。陽明在正德末曾 四上歸省奏折,名義上是因親老多病,而實際上是因“權奸讒嫉,恐罹曖昧 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為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嘉靖改元,使他 感到命運有了轉機,當時大有“若出陷阱而登春臺”的欣喜之情。但這顯然 是他的錯覺,正當朝廷要對其平叛之功進行封賞時,從內閣到科道都有不少 人嫉妒他的功賞,從而掀起了一股強勁的“讒構”陽明之風。(見《王陽明 全集》卷二,《年譜二》)其實,作為陽明朋友的方獻夫早就提醒過他,方氏 初始時語較含蓄地說:“朝廷賞功大典不日當下,然盛德者不居其功,明哲 者不保其盈,先生進退之間,可以自處矣。先正謂留侯有儒者氣象,非觀其 進退之際歟?”(《西樵遺稿》卷八,《柬王陽明》)他要讓陽明學漢代人張 良,做一個功成身退的明哲之士,言外之意是他將在功高賞巨之時遇到麻煩。 后來方氏干脆將話挑明說:“赤松之托,此正其時。古人云:功成身退,天 地之道。幸諦思之。時情固有大不可人者,不必論也。”(同上,《又柬王陽 明》)可尚未等陽明采取行動,攻訐之詞便接踵而來。當時對陽明的“讒構” 可分為兩方面:一是言其平宸濠之功不實。陽明的弟子陸澄在《辨忠奸以定 國是疏》曾對此類攻訐進行了概括,將其分為六條:“一謂宸濠私書,有‘王 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 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于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 城破之日,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力,一知縣之力可擒, 守仁之功不足多,而捷本所陳妝點過實。”(《王陽明全集》卷三九)各條之 間矛盾頗多,明眼人一看便知為誣蔑不實之詞,可當時人言洶洶,一時難以 置辨,尤其是前三條交通宸濠之言,均有殺頭之罪。二是誣其偽學欺世。任 士憑《江西奏復封爵咨》曰:“科道官迎當路意,劾公偽學。”(同上)可見 是有后臺、有組織的行動。錢德洪在《仰止祠記》中也說;“夫子始倡是學 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于陷阱者屢矣。”(同上卷三六,《年譜附錄一》) 面對這些攻訐,陽明心情異常憤激,在給兵部尚書王瓊的信中,他用了“惟有 痛哭流涕而已”(同上卷二七,《與王晉溪司馬》)的沉痛語氣,這在以前他 是很少用的,哪怕是在艱苦的龍場驛所他都沒有如此沉痛。當然,這沉痛之 中不全是對個人得失的考慮,更是對國家命運的擔心,他曾明確地說:“今 地方上事殘破憊極,其間宜修舉者百端。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 歸。繼是而后,遂以形跡之嫌,不敢復有建白。”此時他已知道,“地方事決 知無能為”,于是只好“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同上)他在《與胡伯 中》的信中作一總結說:“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 惘然,如有所失。”(同上卷四)在如此形勢與如此心境中,他還有什么理由 呆在這是非之地的官場而不歸鄉隱居呢?但此時的陽明先生已處于學術的成 熟階段,他已經受了太多的磨難,面臨過太多的險境,因而盡管蒙受了極大 的冤屈,他已沒有興趣去與對手爭辨曲直是非,從他的人生經歷中,他得出 的結論是:“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茍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 則安之而已。出之未盡于道而過于疾惡,或傷于憤激,無益于事而致其怨恨 仇毒,則皆君子之過也。”(同上)這當然不是有意苛責君子而放縱小人,而 是自信良知而卑視污濁,他決不會做同流合污的鄉愿,而是要做高傲的狂者, 他曾對弟子說:“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 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個狂者胸次,使天下之人都 說我行不掩言也罷。”(同上卷三,《傳習錄》下)他已沒有任何猶豫顧慮, 天下所有的人既然已不能改變其對良知的自信,那么他還有什么必要去與攻 擊自己的幾個小人計較勝負得失呢?他此時的確是要退出官場,但并沒有絕 世的打算;他固然想回歸自我,但并不要放棄社會的責任。《啾啾吟》是他 在江西任上的最后一首詩,其中所顯露的心態對他此一時期的人生態度作了 一個全面的總結: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 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蕩類虛舟。丈夫落落掀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 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钃鏤?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 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癡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 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同上卷二十) “不惑”是由于他擁有了知是知非的自我靈明,“不憂”是由于他具備 了廓然大公的超然胸襟,一句話,是由于他自信良知。正因為他一任自然而 無涉于私人謀智,所以他具有了“信步行來皆坦道”的心理感覺,同時也具 有了“用之則行舍即休”的無牽無掛。正是有了“丈夫落落掀天地”的精神 境界,因而也就不會在失意時如落魄的囚徒,小人盡管可以施其攻訐陷害之 伎倆,但你不必與之計較,不必用你這千金之珠去彈那些鳥雀,不必用你這 钃鏤利劍去切那些不值一提的糞土。只有自信良知以保持心境的平靜,才不 會自亂陣腳而被邪惡所害。人生只要達到了致良知的“不惑”“不憂”,就能 真正認識生命的真諦,從而也才能獲得灑落超然的自得境界。王陽明在他五 十歲時,自認為已達到了如孔夫子那般的“知天命”境地,“達命”不就是 了知天命嗎?當他嘉靖七年在征思、田回軍至南安青龍鋪時,他走到了生命 的盡頭;當弟子們向他詢問有何遺言時,他留下的臨終遺言是:“此心光明, 亦復何言!”(同上卷三五,《年譜三》)是的,他自信良知,心地光明,因 而也心中安寧,他還有什么可遺憾的呢?死而無憾,難道不是一個人最值得滿 足,最值得得意的事情嗎!陽明可以瞑目矣! 正德十五年左右,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現實的生命歷程中,對陽明先 生來說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后來曾如此回憶說;“君子之學務求在己,毀 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 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于外,惟日 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于武廟,當時禍且不 測,僚屬咸危懼,若此宜圖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 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同上卷六,《答友人》) 在此,陽明主要強調了本段經歷對于其學術的切磋砥礪之功。其實,應該說它 對于其學術與生命現實同樣重要,此段人生經歷固然促進了陽明心學的成熟 與完善,但也正是有了心學良知的支撐,才使他度過了現實生命的難關,并 使之始終保持一種灑落超然的心境。就實際而論,也許后者的意義更加重要, 因為這不僅是陽明心學發生的前提,即首先它是為解決自我生命存在的困惑 而進行哲學思辨與生命體驗的;同時,對于他同代與稍后的明代士人,這種 生存的智慧也將產生重大的影響。從李夢陽開始,直至嘉靖末的士人群體, 陽明先生“用之則行舍即休”與“人生達命自灑落”這種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生境界,都無疑是一劑極為難得的良藥。讀過上節文字者想必已有初步的同 感,以后我們會有足夠的文字進一步加以證明。 |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