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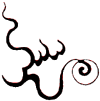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
|
第二章王陽明的心學品格與弘治、正德士人心態 第二節良知說所體現的陽明心學境界 一、致良知與四句教之關系與陽明之學術風格 從正德三年的龍場悟道至嘉靖七年病逝,陽明心學經過了近二十年的發 展演變。其大致發展階段為:正德四年在貴陽主要是倡知行合一之旨,正德 八年在滁陽教人靜坐息心以入道,正德十二年在南贛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以 復本體,正德十五年經忠、泰之難而揭致良知之說,嘉靖六年天泉證道而確 定四句教。由此可知陽明心學始終處于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倘若陽明嘉靖 七年未病故,或許依然會有新的悟解也說不定。這與王學的強調心悟與不執 定板有直接關系。但這也為研究王學造成了相當的困難,即陽明心學有無最 后結論,若有,則何為其最后定論。最早對此作出論述的是陽明的兩個得力 弟子錢德洪與王畿。錢氏說:“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 自滁陽后,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 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刻文錄序說》,見《王陽明全集》 卷四一)按錢氏所言,致良知應是陽明心學的最后定論,起碼是最后說法。 而王畿則與錢氏所說有出入,其不同處在于致良知之后又增添了“居越以后” 一個階段,其曰:“江右以后,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 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 是中節之和,此和之后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于收斂;此知自 能發散,不須更期于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 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 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是本心, 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后,又有此三變也。”( 《明儒學案》卷十)陳來先生斷定這“居越以后”是指的晚年四句教,并認 為它才是陽明晚年思想的最后階段。(見《有無之境》329頁)然而這種看法 我以為還是有商量余地的。 之所以不能輕易否定錢德洪致良知為陽明晚年定論的說法,是由于有陽 明本人的話作為支持。陽明曾多次強調良知或致良知的重要性:“良知明白, 隨你去靜處體認也好,隨你去事上磨練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靜的。此便 是學問頭腦。我這個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 (同上卷三,《傳習錄》下)“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門正眼法藏。往年 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同上卷三二,《年譜》二) “吾良知二字,自龍場悟道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 言,廢卻多少辭說。”(同上卷四一,錢德洪《刻文錄序說》)直至嘉靖六年 也就是陽明病逝的前一年,陽明還賦《長生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 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系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 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游 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 千生皆過影,良知乃我師。”(同上卷二十)本詩應視為是陽明對其一生為學 求道的總結,而他生命的最后歸宿依然要落實于良知二字之上。可見錢氏說 致良知為陽明晚年定論是言之有據的。當然,王畿的四句教為定論說亦非其 主觀臆造,《傳習錄》記天泉證道陽明解釋四句教后說:“已后與朋友講學, 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 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同上卷三) 《年譜》亦曰:“二君以后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 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 躋圣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同上卷三五)無論是《傳習錄》還是《年 譜》,都有錢德洪的參與,則王畿所言的四句教為晚年定論看來亦決非自我 杜撰。陳來先生之所以要將致良知與四句教區分開來并肯定后者,是與其分 陽明思想為有、無二境直接相關的,他說;“江西時的致良知思想還只是純 粹的道德理性主義,歸根到底還是‘有’的境界,四句教的提出,才實現了 境界的有無合一。因此從江西時期到居越末期的發展固然也可以看作‘致良 知教‘本身的發展,但確實可以看作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有無之境》 330頁)這種看法并不符合陽明心學的實際發展狀況,說江西時期的致良知 是‘有’的境界更與陽明思想不合,如陽明正德十六年在《與楊仕鳴》的信 中說:“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于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 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 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瞀變幻于前,自 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 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 不容染著,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著些意思,便不是 合一功夫。’”(《王陽明全集》卷五)陽明在此不僅更為堅定地指出了“致 知”(實即致良知)在其心學中地位的重要,而且突出了心學“如立在空中, 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著”的超越特征,也就是說江右時期的陽明心學 便具有了“無”的境界,更不必等到歸越后方才產生,以后我們會有更多的 例子來證明此一點,因而陳來先生的上述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致良知與四句教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呢?我以為是對同一種 哲學主張的兩種不同教學方法。其核心是良知,其方法則可分為江右時期所 提出的“致”與嘉靖六年在越中時提出的“四句教”兩種。從龍場悟道時所 提出的“吾性自足”到江右時期的“自信良知”,實際上都是陽明本人對人 生哲理的自我體悟。通過這種體悟,他有效地解決了自身所遭遇的人生困境。 但是如何將這種人生體悟傳達給弟子們,則需要恰當的教學手段。因為心學 是靠自我體悟而實現人生覺解的學術,因而其教學方法也就是獨特的。開始 時陽明用了“致”的手段。他所言的“致”包含有兩層意思:一是擴充自我 之善端,這顯然是遵循了孟子的思路。因為良知的觀念從學術淵源上說便是 來源于孟子的良知良能,則其為學手段自然也受孟子之影響。孟子認為人皆 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善端,而“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孫丑上》)陽明亦曰:“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 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于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 (《王陽明全集》卷二,《答顧東橋書》)這便是自信己心具備天然良知,若 加以擴而充之,即可達到圣人的境界。二是推自我良知于事物之中,亦即其 所言的格不正以歸于正之意,故而他說:“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 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 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 其理者,格物也。”(同上)用現代術語講,前者是道德認知,而后者是道德 實踐。應該說思路是非常清楚的,但這卻并不符合陽明心學的一貫風格。首 先,根據陽明知行合一的主張,決不能將知與行分開來講,所謂“知之真切 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同上)盡管他作出了特別的強調, 卻依然有割裂知、行的危險,因而用“致”來作為教學手段不能算是最好的 表達方式。其次,用“致”不能涵蓋良知之學的全部內容,比如良知的內涵、 良知的發用等等。其三,用“致”來說明獲得良知與實行良知顯得理性化成 分太濃,而理性成分的濃厚又導致了手段的單一與死板。這與心學講究個體 的體悟是背道而馳的,陽明本人便說過:“圣人教人不是個束縛他通做一般, 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同 上卷三,《傳習錄》下)正因為“致良知”并非其最理想的表述方式,所以 他必須尋找一種更具包容性,更富于彈性的教學方式來,于是就有了四句教 的出現。 其實,王畿在其《天泉正道記》中對此講得很清楚:“陽明夫子之學, 以良知為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教為法。”(《王龍溪全集》卷一)在以 良知為宗旨這一點上,四句教與致良知沒有區別,而只是將“致”換成了四 句教之“法”。盡管四句教在當時便引起了錢德洪與王龍溪的不同理解,并 且為后世留下了一樁打不盡的筆墨官司,但在陽明本人看來卻是相當滿意 的,所以才會說“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至于錢、王二人的 爭議,似乎他早有所預料,故言“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同上)那么,又為 什么要保留這種疑問與不一致的理解呢?陽明說:“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 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里接人原有二種。 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 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 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后,渣滓去得盡時,本體 亦盡明了。汝中之見,是我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里為其次立 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 人,便于道體各有未盡。”(《王陽明全集》卷三,《傳習錄》下)由此可見, 四句教對陽明心學的概括不僅是全面的,而且也是富于彈性的。這種彈性實 際上是一種模糊性,人們在接受它時必須動用自我的智慧去反復琢磨,在這 多指向的表述中去體悟其意旨,從而根據各自的天分資質進行獨特的體驗。 我以為這才真正合乎陽明心學的根本特征。 陽明心學將接受對象分為“利根”與“中下”兩類有著復雜的原因,其 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陽明心學往往可分為“自言”與“他言”兩個部分。 所謂自言是指對自我存在之關注,所謂他言是指對社會之教化。陽明龍場悟 道與致良知說之提出均帶有強烈的自我悟解色彩,即自我在身處險惡境遇時 應持何種人生態度。龍場悟道在于吾性自足,江右時期在于自信良知,其實 都是要超越利害得失的糾纏而保持心境之平靜。對此種超越境界的追求,是 陽明要解決的自我人生難題。在講學中盡管他也曾多次涉及此種境界,但他 通過詩歌的方式自言的時候更多。另一方面,作為儒者的陽明還要教化社會, 扭轉士風,則其所言往往是針對當時官場及知識界而發。此類人中的大多數 由于“習染太深”,必須痛下為善去惡的誠意功夫,方可達到較高境界。此 可視為一種“他言”,即對他人而言說。在陽明一生中講的較多者是他言, 而自言則較少,尤其用哲學的語言講的比較少。但這并不意味著“自言”在 其生命中是無足輕重的,有時這少量的“自言”甚至超過了大量“他言”的 分量。因而陽明下述這段話便需給予新的理解:“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 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 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 不過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同上)在此與其 說是在批評王畿,倒不如說是表現了陽明本人以“利根”的圣賢資質自居的 自信與自負。否則,他何以前邊剛肯定過王畿所言“是我這里接利根人的,” 后邊卻又馬上予以否定?這種將人群分為利根與中下的做法并不始于陽明, 起碼從宋儒朱子便已將圣人分為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兩種,至元代大儒許衡 則將此析之更明:“天生圣人,明德全明,不用分毫功夫,于天下萬事,皆 能曉解,皆能了干,見天下之人,皆有自己一般的明德,只為生來的氣稟拘 之,又為生以后耳目口鼻身體的愛欲蔽之,故明德暗塞,與禽獸不遠。圣人 哀憐,故設為學校,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 此圣人立教本意。”(《魯齋遺書》卷三,《論明明德》)觀此后人當明白, 陽明乃以圣人自居,天生有明德之良知,而后學弟子則未必可人人皆如此,故 須做為善去惡的功夫。同時他也未堵死天生圣人之利根一途,起碼在他的眼 中,王畿即與此較近。這體現了王學的巨大包容性及其陽明本人挽救世道人 心的迫切心情。 然而,王陽明也并未因追求這種包容性便將其學說降低為條分縷析的俗 儒教化,因為還有其學由心悟的心學宗旨必須得到貫徹。因而其四句教又顯 示了相當程度的模糊性。當龍溪、德洪弄明白了陽明先生的利根與中下應采 取不同的教法之后,仍存有疑問需要解答,于是又有了所謂的嚴灘問答,《傳 習錄》記曰:“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舉佛家實相 幻想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 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 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王陽明全集》卷三)而王畿 在《刑部陜西員外郎特詔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緒山錢君行狀》亦記此事曰:“夫 子赴兩廣,予與君送至嚴灘,夫子復申前說,兩人正好互相為用,弗失吾宗。 因舉‘有心是實相,無心是幻相;有心是幻相,無心是實相’為問。君擬議 未及答,予曰:‘前所舉是即本體證工夫,后所舉是用工夫合本體,有無之 間不可置詰。’夫子莞爾笑曰:‘可哉!此是究極之說,汝輩既已見得,正好 更相切劘,默默保任,弗輕露泄也。’二人唯唯而別。”(《王龍溪先生全集》 卷二十)兩種材料沒有太大的出入,盡管“此是究極之說”比“先生然其言” 更強調了王畿對自己見解的價值,但陽明對王畿的答案持贊許態度則是可以 肯定的。關鍵是師徒二人的問答究竟是談的什么問題,目前雖有人試圖予以 解答,但所得結論均難以令人滿意。⑦我以為此次問答所談問題不可能與天 泉證道之內容相重復,拿王畿的聰明及其與陽明的密切關系,卻反復緊追不 舍地探詢同一問題,這是難以想象的。理解此一問題的關鍵我認為必須與致 良知聯系起來才能得到合理的答案。所謂“本體說工夫”或曰“本體證工夫”, 是指的“致”的第一種內涵,即擴充自我善端的過程,也就是如何認識良知 本體,如何達到良知境界的問題。在這個時候,必須“有心”,亦即痛下為 善去惡的功夫。假如此時“無心”,則決不可能有任何收益。對此陽明本人 有過很具體的論述: 一日,論為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 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 其心意稍定。只懸懸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 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 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 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 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 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 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 何思何慮矣。(同上卷一,《傳習錄》上) 這便是“有心”,只有如此,方可收為善去惡之實功。盡管此“有心” 之工夫是為“無心”之本體而發,但為得彼之“無”必先行此之“有”。此 即為“本體上說工夫”。而“工夫上說本體”或曰“用工夫合本體”則是指 “致”的第二種內涵,即致吾心之良知于天下事事物物的道德踐履功夫。在 這個過程中,雖是要求得格不正以歸于正之實功,但卻需要“無心”,需要 廓然大公,而這才是陽明心學的最高境界。對此陽明解釋說:“圣人致知之 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曒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現形,而 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物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 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 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同上卷二《傳習錄》中, 《答陸原靜書》)此處所言“致知”顯然是屬于良知發用的道德踐履,它可 以取得“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的實效,但本體卻依然歸于“一過 而不留”的無之境界。此時,“無心”才是本體的真實狀態,故言“無心俱 是實”;如果心滯于物,則猶如明鏡中所生“纖翳”,即非本體之實相而為 “幻”矣。這便是以工夫之“有”證本體之“無”。關于這一點,我們留在 下面再詳細說明。這種近乎禪宗偈語的問學方式的確令人費解,遠不如用 “致”來得清楚明白,也難怪連其高足錢德洪也一時悟不出個所以然來,但 一向悟性高超的王畿卻立時透悟了陽明先生的立意,迅速作出了滿意的回答。 不過此種方式顯然不具備教法上的普遍意義,尤其不會被穩重的錢德洪所采 納,因而錢氏說:“但先生是因問偶談,若吾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同上卷三,《傳習錄》下)但通過對天泉證道與嚴灘問答的研究,使我們 認識到了四句教與致良知的關系以及陽明心學的風格特征。 這種特征對陽明心學也許是合適的,但卻給今天的學術研究帶來了一定 的難度。因為陽明心學的目的是要求得真實的人生體悟,只要實現了此種目 的,大可不必形諸語言。而今天的研究卻必須予以明晰的表述,則單靠體驗 是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的。不過我們既然理清了四句教與致良知之間的關系, 則也就找到了理解其內涵的門徑。即必須將四句教的表述與致良知的內容結 合起來,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其良知理論所體現的人生境界。 |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