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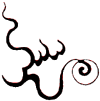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
|
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的流變 第三節、白沙心學與明代士人人格心態的變異 三、受用與責任——陳獻章的復雜矛盾心態 倘若認為白沙先生一生總是如此的瀟灑自適,總是充滿了詩情畫意,那 顯然不是一個真實的白沙。看一看他給兒子的這首詩,你會感受到白沙先生 的另一面: 日往則月來,東西若推磨。及時愿有為,何啻短檠課?強者能進取,不 能空墜墮四書與六經,千古道在那。愿汝勤誦數,一讀一百過。嗟余老且病, 終日面壁坐。古稱有志士,讀書萬卷破。如何百年內,能者無一個?書生赴 場屋,勢若疾風柁;不悟進退,反言勇者懦。吾聞邵康節,撤席廢眠臥;又 聞范仲淹,畫粥充饑餓。砥柱屹中流,有力始能荷。汝患志不立,不患名不 大。詩友為汝資,薪水為汝助。黽勉在朝夕,用為老夫賀。(《陳獻章集》 卷四,《景旸讀書潮連,賦此勖之》) 此詩之主旨在勉勵其子為科舉而刻苦讀書。以白沙之境界,當然不會讓 兒子做只追求功名的利祿之徒。但卻與其學術風格、人生態度適相背離。他 不是主虛靜而倡退隱嗎?此處何以又贊成進取之強者?他不是學主心悟而視 六經為圣人之糟粕嗎?又何以說四書、六經乃千古道之所在,并令其子“一 讀一百過”地“勤誦”呢?他此時倒是又想起了傾慕的前輩邵康節,但已不 是悟后而求樂的堯夫先生,而是早年汲汲于功名的邵雍。《宋史》卷四二七 《道學傳》載:“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始為學 即艱苦自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難怪他要將其與“先天 下之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并列為兒子學習的楷模了。可當他讓 兒子以其成功“用為老夫賀”時,他是否要為自身的出世行為而傷悲呢?他 既然認定人生的最高價值在于自我的適意,何以不讓自己的兒子走此道路, 而反勉勵其求取功名呢?究竟是他失去了自信,還是在向兒子說慌話? 要解釋清楚這種矛盾的人生態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我們仍然沒有必 要懷疑白沙先生的真誠。他的追求超世脫俗是真誠的,他的鼓勵兒子求取功 名也是真誠的。之所以產生價值取向的背離是由于其心理狀態的矛盾。此種 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一點是他未能忘懷儒者的社會責任與自身所擁 有的不朽情結。他曾反復吟誦過如此的詩句:“孔子萬世師,天地共高厚。 顏淵稱庶幾,好學古未有。我才雖魯莽,服膺亦云久。胡然弗自力,萬化脫 樞紐。頹顏無復少,此志還遂否?歲月豈待人,光陰隙中走。念此不成眠, 晨星燦東牖。”(同上,《冬夜二首》其二)“邈哉舜與顏,夢寐或見之。 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余獨何人,瞻望空爾為! 年馳力不與,撫鏡嘆 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無疑。請回白日駕, 魯陽戈正揮。”(同上,《自策示諸生》)兩首詩幾乎為同一意旨,前一首 為自策,后一首是自策兼策他人,應視為其真實心態。這種心態便是“舜人 也,我亦人也”(《孟子·離婁下》)的希圣情結,他看到了“孔子萬世師, 天地共高厚”的不朽名聲,更羨慕大舜“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的赫赫 功業,于是他想到了自己,他渴望追隨其后,而不空活此生。在此種理想的 支配下,他感到了時光的無情流逝,遂產生了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以致每念 及此,便深夜難以入眠。這些睡里夢里時時牽掛于懷的情思,你難道能說不 是白沙的真實心態?當然,他的希圣情結并非全是為了一己之不朽,同時也 有擔心“萬化脫樞紐”的社會責任感,他有《禽獸說》一文,充分表現了他 的這種觀念,其曰:“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 膿血裹一塊大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 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血氣, 老死而后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同上》卷一)他顯然不能坐視 此種人之為禽獸的倫理墮落,必須擔負起拯救人類的責任。于是,他提出了 作為一個儒者的最高人生理想:“一洗天地長,政教還先王。再洗日月光, 長令照四方。洗之又日新,百世終堂堂。”(同上卷四,《《夢作洗心詩》) 他要通過“洗心”而使天地長久,使天下再還復圣王之政教時代,此猶如洗 去掩覆日月之陰霾,使天下永處光明之中。總之,他要洗出一個新天地,并 使之百世而長存。如此志向不可謂不大,境界不可謂不高,他有孔孟堯舜其 君的宏愿,有宋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的理想,可謂達到了一個儒者所能達到的高度。 然而,這也只不過僅僅是陳白沙的理想而已,因為我們發現他在抒發此 種宏愿時,往往是在夢中。盡管是非常美好的夢,卻又是非常虛幻的夢。這 并不是他不愿實現自己的夢想,而是現實環境沒有實現的可能。后來錢謙益 深深地理解了白沙先生的苦衷,因而才會說:“余觀先生之為人,志節激昂, 抱負奇偉,慨然有堯舜君民之志,而限于資地,困于謠諑,輪囷結轖,發為 歌詩,抑塞磊落之志氣,旁見側出于筆墨之間。”(《列朝詩集小傳》丙集) 今查白沙詩文集,可證錢氏所言不虛,如其《行路難》曰:“穎川水洗巢由 耳,首陽薇實夷齊腹。世人不識將謂何,子獨胡為異茲俗?古來死者非一人, 子胥屈子自隕身。生前杯酒不肯醉,何用虛譽垂千春。”(《陳獻章集》卷 四)做潔身自愛的巢由、伯夷、叔齊式的人物已難以得到世俗的理解,更不 用說憤怒沉江的子胥屈子了。那么又何必不盡情享受生前的人生受用,而去 追求那無人理解的虛譽呢?于是白沙由人生的失意而對官場逐漸失去興趣, 轉而去追求超越的自由境界,追求人生的自我受用。這其間當然不是一蹴而 就的,經過了一個較長的摸索體驗過程。其中吳與弼對他的人生轉折起到了 不可低估的作用,吳氏的隱者風范與求樂傾向,引爆了他對人生價值認真思 考的念頭。盡管他當時尚不能將吳氏的人生理念內化為自我的人生體驗,尚 需要以后長期的閉門靜思體悟以及與山水親融的實際歷練,但從吳氏就學卻 依然是他從早年的銳意功名到后來的退隱自適之間的分界標志。但正是具有 早年的儒者進取情結,使得白沙先生在追求自我適意的過程中顯示出某種矛 盾與徘徊。比如他認為必須守靜求虛方可獲道,卻又擔心危及名教,因而感 嘆道:“近苦憂病相持,無以自遣,尋思只有虛寂一路,又恐名教由我壞, 佛老安能為我謀也。”(同上卷二,《與容一之》)因此他一面說,“應笑 書生閑未得,白頭憂世欲何為?”(同上卷四,《題閑叟》)真是通達瀟灑 極了;可另一面卻諄諄告誡其弟子說:“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為。 愿更推廣此心,于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 能獨存者也。”(同上,《與崔楫》)作為中國的一位傳統士人,尤其是在 明前期理學文化氛圍中浸泡過的士人,令其放棄“名節”而徹底超脫的確是 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家族的義務,親友的往來,士人的節操,這一切從幼年 起都成為其做人的基本前提,再往后退,真要令其自身懷疑是否仍有做人的 資格。從此一點而言,陳獻章之不能完全超越而存有矛盾的心態是可以理解 的。但在白沙本人卻又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情。從理想狀態講,盡管他已經 沒有進入官場的興趣,而寧可退居鄉野講學,不過講學也并非不能用之于世, 當年的孔子不正是在野儒者立德教化的楷模嗎?因而白沙論孔子曰:“孔子 不得其位,澤不被當世之民,于是進七十子之徒于杏壇而教之,擇善力行, 以底于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往圣繼絕學,與來世開 太平。若是者,誠孔子之教也。大哉,教乎!”(同上卷一,《龍岡書院記》) 但白沙所遇到的現實困境使他的用世理想不得不逐漸趨于暗淡,否則他不必 執著于隱居的生涯。其實白沙的困境不僅存在于官場,更存在于日常鄉居中, 從以下白沙信中所抱怨的內容看,后人會很清楚地感受到他的困惑與失望: 聞老兄近復假館禪林靜坐,此回消息必定勝常。耳根凡百所感,便判了 一個進退,老兄今日此心,比諸平時更穩帖無疑否?賤疾幸少脫體,但尋常 家中亦被聒噪,情緒無歡。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 尊卑老少咸在,才點檢著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咈和好之情。于此處之, 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憮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唳,非細 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只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 能不相責望,在己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 不堪,亦乖唳所宜有也。”(同上卷三,《與李德孚二則》其二) 信中有“此語非相知深者不道,惟心照”之語,可知所言乃其心中真實 之感,非泛泛虛套之門面語。有人認為本段話表現了白沙反對以理性戕害自 我情感的愿望,可算是一個不小的誤解。⑧其實,此處所講的乃是他在家庭 中欲按儒學(確切地說應為理學)的標準來治家,卻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他 的“情緒無歡”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意欲自我事事“點檢”,但“才點檢 著便有不由己者”,因為他要“抑之以義”便會令他人不自在,從而破壞了 家庭和諧的氣氛。在此種環境中,要做到“事理至當”而又不“憮逆”他人, 實在是太不容易了。如果再由此造成了家庭矛盾與破裂,則勢必事與愿違, 即導致了家族的不幸,故言“非細事也”。二是更需要用此種標準去要求家 庭其他成員,比如說諸兒女的婚嫁之事,不僅須耗費大量精力,而且又要“ 一切裁之以義”,便會使他們難以滿足過分的要求。由此也會引起其“乖唳” 之情。按照《大學》八綱目的設計,欲治國平天下者必先齊其家,可如今在 一己之家中便難以做到“事理至當”,又何望于“與來世開太平”呢?這是 白沙矛盾心態所造成的第一層痛苦。同時,難以割舍的“名節”情懷更妨礙 了他追求超越的求樂之學,使其人生適意的受用效果不免打了相當的折扣。 對此他深感苦惱,無奈只好向朋友抱怨說:“某別后況味如昨,但年來益為 虛名所苦,應接既多,殊妨行樂耳。平生只有四百三十二峰念念欲往,亦且 不果。男女一大俗緣,何日可盡?雖云道無凝滯,其如野性難拗,尋欲振奮 一出,又未能也。”(同上,《與陳德雍》)在信中,他使用了兩組對立的 詞匯,以“虛名”、“俗緣”指稱用世之意念,以“野性”、“行樂”指稱 超越之情懷。從其人生理想的主導方面言,他當然是想順其性而求其樂,故 而時時有“振奮一出”的宏愿,但到底被“俗念”所牽而“未能也”。于是 他也只好將此尋山覓水之樂形諸夢寐,并在此信中描繪道:“清江之去白沙 幾山幾水,一夕恍然與德雍先生葛巾青藜相值于寶林,拍手笑語,坐佛燈前, 促膝嬉戲若平生,不知其在夢也。及覺,始悵然若有所失,即復閉目入華胥 尋向來所見,……”白沙是一位真正懂得欣賞山水之美的詩人,所以才會說 “平生只有四百三十二峰念念欲往”的人生志趣,但儒者身份又使之無法滿 足其愿望,因而便不能不產生悵然若失的遺憾。歷史沒有為白沙提供出如晚 明時期那樣的文化氛圍,他也便不可能象袁宏道們那樣盡情地飲酒談禪,居 山游水,享盡天下之樂。這不僅決定了白沙先生必然會存在矛盾的心態,而 且也決定了白沙之學內在超越的基本品格。 其次,外在環境的壓迫也是造成白沙矛盾心態的重要原因。在第一節中 曾提及白沙之出山應召并接受翰林院檢討一職的溫和態度,乃是迫于朱英的 善意壓力與顧及朝廷的面子。其實,那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這些表層現 象的背后存在著更為沉重的環境壓力,那便是將其作為異端加以攻訐。在一 封題為《復趙提學僉憲》的信中,表現了白沙先生面對此種壓力時的沉重的 心情與極力的辨解。據信中所言,當時有人給他按上了兩條罪名:一是自立 門戶而流于禪學,二是“妄人,率人于偽者”。而且是“數者之詆”,亦即 形成了一定的聲勢。至于此類罪名的具體內容,由于史料的缺乏,今天已不 能詳細知曉了。但根據下面白沙本人的辨解,依然可知其大概: 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后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為要”。一者,無 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后圣可學而至矣。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 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于數息, 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于禪學者”,非此類歟?仆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 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申于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于仆,亦 非仆所能與也。不幸其跡偶與之同,出京之日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 輒涉于仆,其責取證于二公。而仆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 加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則凡責仆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以 偽者”,又非此類欲?仆嘗讀程子之書,有曰:“學者當審己如何,不可恤 浮議。”仆服膺斯言有年矣,安敢爭天下之口而浪為憂喜耶?且仆聞投規于 矩,雖工師不能使合;雜宮商于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方圓之不同, 緩急之聲異也。尚何言哉?(《陳獻章集》卷二) 所謂自立門戶而流于禪,大致是指白沙的治學方法。亦即其靜坐、悟解、 調息、定力之虛靜入學門徑;而所謂“妄人,率人于偽”,顯然是指其人生 價值取向,亦即其歸隱而超越世俗的行為以及對士人所造成的影響。盡管他 最后表現了“方圓之體不同,緩急之聲異”的不加置辨的態度,但根據他很 勉強地抬出孔子來抵御攻擊的做法,其心理上壓力的沉重還是清晰可感的。 因為無論是流于禪還是鼓勵士人棄仕歸隱的“率人于偽”,都是當時難以接 受的罪名。更何況這些攻詰并非毫無所據呢?白沙說應魁與克恭的棄官乃是 由于身體有病,但是恐怕并非事實,所以后來的史學家便沒有聽從白沙的說 法,而是如此記載克恭(即賀欽,其字為克恭)之生平:“欽時為給事中, 聞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 即日抗疏解官去。”(張詡《白沙先生行狀》,《陳獻章集》附錄二)如此 確鑿的證據,白沙先生怕是否定不了的。非但此也,查一查白沙的弟子,竟 然可以找出相當一批對仕途不感興趣者。 李承箕,字世卿,楚之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聞白沙之學而慕之,即 南行而師之。白沙與之登臨吊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久之而有所悟入, 歸鄉而筑釣臺于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不復仕進。 張詡,字廷實,南海人,白沙之弟子。成化甲辰進士。以養病而歸鄉, 六年不出,后朝廷召起之,授戶部主事。不久又丁憂守制,屢次被薦而不起。 正德甲戌,拜官南京通政司左參議,又極力辭去,僅進謁了一次孝陵便歸鄉 而去。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成化甲午舉人。從游白沙之門,白沙傳授其自 得之學。年五十始入仕,僅到任五日,因不能屈曲事人而解官,遂杜門不入 城市。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真子,廣州人。張詡引其入白沙門下,以布衣終 其一生。二十年不入城市,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間或出門,人們 便遠近圍觀之,以“奇物”視之。后人多稱其能繼承白沙抗節振世之志。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白沙弟子。筑室葵山之下,甘于清苦,談泊名 利,曾有寄湛若水詩曰:“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真 元機。”卒后附祀于白沙。 何廷矩,字時振,番禺人。初為郡學生。及師事白沙后,便棄去舉子業。 學使胡榮強其參加秋試,執意拒絕。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成化乙酉舉人。己丑年因入京會試而見白沙先 生,二人相語大為投機,便隨其歸于江門。筑室深山之中,往來問學者二十 年。白沙曾稱贊“其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成化甲辰復出參加會試, 中了乙榜,授平湖教諭,后歷任兗州、嚴州府學教授。白沙對此頗不以為然 曰:“定山為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 (以上材料均見《明儒學案》卷六) 所有的這些歷史事實難道還不足以證明白沙之學對士人歸隱傾向的深刻 影響?尤其是林光的例子,他歸隱了便得到白沙的贊許,一旦出仕便被白沙 譏之為“一齊誤了也”。則白沙的價值取向以及對其弟子的影響全都昭然若 揭了。面對這些事實,白沙的上述辨解是何等的缺乏力量,同時也可得知他 心中存在著何等的心理壓力。反復的辨說也許可以部分地消解自我的心理壓 力,但要應付外在的攻訐便需要更為審慎與周全的措施。于是人們便會時常 看到白沙一些近乎矛盾的人生態度,如他在言超脫時說:“眼中朋友,求可 與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亦為道之障,為其溺 也。”(《陳獻章集》卷二,《與鄧球》)但同一位白沙先生,他也可以如 此說:“夫士能立于一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長。 其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于同也。”(同上,《與王樂用僉 憲》)如果將兩段分而論之,均有其自身的道理與價值。但同出之于白沙一 人之手,便不能不令人產生疑惑,哪一句是他的真實價值判斷呢?就白沙的 主導傾向言,人們有理由認為前句更符合其一貫主張。那后句呢?是否應該 視為是他的違心之言?如此立論也許并沒有什么錯誤,但卻過于苛刻。其實 道理很簡單,前者是與弟子論學,當然不必客套,一抒己見便是;后者是與 官員講話,便須考慮對方的身份與觀念,如此可既不使對方難堪,也避免了 自身不必要的麻煩。此固可視為圓滑之舉,同時也是不得已之舉。鑒于此, 我們在讀白沙的詩文時,便不能將其每句話均視為由衷之言,比如他說“幸 逢堯舜,那無巢許”。(同上卷四,《題畫松泉,為張別駕》)你便不必認 為白沙是在真心贊譽他所處的時代是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盛世,充其量不 過是為歸隱尋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但也不可將白沙所有這些關心世事 的話均視之為裝點門面的空話,他畢竟是自幼飽讀詩書的儒者,倘若能夠出 世與入世兼得,他又何樂而不為呢?于是,下面的詩句出現了:“身居萬物 中,心在萬物上。”(同上卷五,《隨筆六首》其四)用散文的語言說便是: “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同上卷一,《夕惕詩集后續》) 這是在極力照顧兩端:既不脫離儒者所看重的人倫日用,同時又能享受到鳶 飛魚躍之樂。而且也合乎“心在萬物上”的內在超越精神,則此便應被視為 白沙的真實愿望。只是人們依然不可忘記,其中還是含有某種因環境壓力而 采取的權變心理。比如白沙說:“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 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圣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 壞了人也。”(同上卷二,《與張廷實主事六十九則》其十一)提倡博大、 中庸以容納各階層群體,這的確合乎儒家的傳統精神,但其中又很難說沒有 絲毫的避害自保意思,這在白沙給另一位弟子的信中也許講得更清楚:“接 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 氣象,方始是成就處。”(同上,《與賀克恭黃門十則》其十)此與上段話 為同一意旨,但要包容一切“賢愚善惡”,顯然已有了利害算計,說嚴重點, 已有滑入鄉愿的危險。白沙先生當然不是鄉愿,但由此卻讓人們看到了他面 對環境時的無奈,看到他力倡求樂卻又時常陷入矛盾緊張的復雜心態。此副 模樣的白沙先生也許不是特別的瀟灑,但我以為這是更接近歷史真實的白沙 先生。 一種學說要做到圓融而無懈可擊本身便是非常困難的,更何況它還要面 對不同的需要與各種現實環境的壓力。某種學說的有無價值除卻其自身所達 到的深度及其完善性外,同時也要看它是否有效地回應了時代所提出的人生 問題。從此一角度看,白沙心學已達到了其力所能及的高度。它為明代前期 士人的心理疲憊提供了較有效的緩解途徑,它使那些被理學弄僵硬了心靈的 士人尋到了恢復活力的方法,它為那些在官場被磨平了個性的士人提供了重 新伸張自我的空間。它既是明前期學術思想與士人心態運演的必然結果,同 時又是對時代需求的及時回應。然而,白沙心學又是只能在那一歷史時期產 生并得以流行的學說。在白沙心學流行的憲宗成化年間,是一個雖則平庸卻 也有自身特點的時期。是的,它的特點便是平庸。在憲宗當國的二十三年中, 沒有發生過太多令后世歷史學家傾注精力而研究的重大事件。盡管地震水旱 災害也屢有發生,四面邊境也時有戰事出現,但以偌大一個帝國,這些都不 能算是過于反常的現象。有些現象的出現是對后來的歷史產生了深刻影響的, 比如皇帝不經吏部而直接內批授官,大批侵占閑田以設置皇莊,成化初年對 建州(也就是后來與明朝對峙并最終取而代之的滿清政權)的用兵等等,均 成為后來明王朝的棘手難題,但當時卻很少有人意識到其性質的嚴重。然而, 成化年間還是出現了足以影響士人心態的歷史現象,這便是太監汪直的亂政。 盡管汪直為害的時間只有大約五年左右,而且真正能夠左右憲宗的是宮中的 萬貴妃,宦官亂政遠未達到危及皇權的程度。但以汪直為首的宦官特務勢力 依然對士人構成了嚴重的危害。他統領西廠,迎合皇上,對一批大臣進行迫 害摧折;又廣布爪牙刺探官員及民間隱情,使當時不少士人對朝廷產生了不 滿與失望。谷應泰曾集中筆墨指出過憲宗崇信宦官的失誤,說他:“乃欲刺 事暮夜,诇人床第,方言巷語,竸入宸聰;瓜蔓枝連,立成大獄。不知竹筒 鉤距,賢吏薄之,謂其行衰俗惡。況以萬乘之尊,行攻訐之智乎?而且委柄 匪人,寄權近寺,招致奸民,顯行系械。其始也,李膺破柱,將閭呼天。因 而權歸北寺,獄奏黃門,禍發情流,慘同白馬。繼也,姜桂皆鋤,脂韋成習, 呈身宮掖,屈膝私人,中官勢成,而主上孤立矣。”(《明史紀事本末》卷 三七)面對此種狀況,大學士商輅在給憲宗的奏折中說:“自直用事,士大 夫不安其位,商賈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明史》卷一七六,《商輅傳》)依實而論,商輅的話有些夸張,汪直之 害尚未對普通百姓構成太大威脅,故而憲宗聞后不以為然地說:“用一內豎, 何遽危天下。”但是,汪直之亂對文官集團卻著實構成了很大威脅,“士大 夫不安于位”已成為普遍的現象。我以為這是白沙心學產生與流行的直接時 代原因。然而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對于宦官的亂政,成化朝的士大夫何以沒 有形成如后來正德劉瑾專權時的舉朝抗爭的局面,反而樂于歸隱鄉野呢?這 就必須聯系到成化朝之前的士人心態。自景泰末于謙慘死后,對士人心態造 成了重大影響,此已見于上述。此種情形在成化朝依然會在士人心態中留下 深深的痕跡,使士人在遇到困境時想到的多是退隱而不是抗爭。這是白沙心 學所面對的時代情景與陽明心學的很大不同處,因而也造成了它們不同的學 術品格,對此我們以后會有足夠的文字展開論述。 注釋 此種說法見徐立新之《儒家之絕唱——方孝孺悲劇根源剖析》(《臺州 師專學報》1996年第 5期)。文中認為方孝孺的悲劇“實質上是以方孝孺為 主體的儒家文化與明初殘暴的封建專制政治的沖突和對抗。”轉換成本書的 術語,也可以說是儒家之道與帝王之勢之間的抗爭。從此一意義上講,筆者 同意將方孝孺之死視為“儒家之絕唱”的說法。但“絕唱”說依然有必要作 出進一步的說明。這是因為在明代以文人群體為代表的儒家之道與帝王之勢 的抗爭并非以方孝孺之死作為結束的標志。如果將儒家政治理想與帝王專制 的對抗作出寬泛的理解,而不是僅注目于恢復古代禮治與燕王纂位這一狹小 的范圍,則后來的于謙之死、海瑞之以死相爭、東林黨的群體悲劇,均可視 為此一性質。從此一角度講,說方孝孺之死為“儒家之絕唱”便不是十分準 確了。 關于閣臣與宦官影響皇帝的問題可進一步參見譚天星《明代內閣政治》 第三章。 如其中說:“由于閣權與宦權均受之于皇權,很自然,誰對皇帝具有優 勢的影響力,誰就會擁有更大的權力。以他們影響皇帝的方式而言,宦官多 根據皇帝同樣存在的人之本性去娛其心志,而內閣則更多是從道義上、從傳 統的君道與臣道上去試圖規范皇帝。一般說來,皇帝更喜歡宦官投其所好的 影響,而非內閣說教式的影響。”(見該書75頁) 關于姚廣孝著《道馀錄》以駁程朱的具體情況,可進一步參見臺灣學者 江燦騰先生的《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爭辯與發展》一書的《明初道衍的反排 佛論及其凈土思想》一章,其中“《道馀錄》在明代的流傳情形”一節說: “《明史·姚廣孝傳》和顧亭林的《日知錄》都提到‘廣孝著《道馀錄》, 詆訕先儒,為君子所鄙。’其實在道衍禪師圓寂后不久,亦即《道馀錄》問 世后的第十八年(一四三0 ),修成的《明太宗實錄》中,已出現了上述批 評《道馀錄》之語。此為官方文獻的正式貶詞。”“郎瑛的《七修類稿》則 提到張洪燒書之事。張洪為道衍禪師生前共修《用樂大典》的伙伴,曾受禪 師的照顧。他自供:‘少師于我厚,今無以報,但見《道馀錄》即焚之,不 使人惡之也。’商傳認為這樣的報恩,是‘十足的以怨報德的惡行。’說是 不錯,卻也反映出《道馀錄》的出版,在以儒家官僚為主的知識分子間,造 成巨大的壓力。”(見該書24頁)《道馀錄》在永樂間的出版并不說明程朱 理學受到了挑戰,而是姚廣孝利用自己與成祖的密切關系來為佛教作殊死的 頑抗。這其實正說明佛教在當時已受到極大的壓制。 ④此處所說的“偶然因素”是指某些帝王或大臣因個人的好惡而使取士 受到影響。 明顯的例子可舉洪武三十年的科場案,該年考官劉三吾、白信蹈所取的 五十二名進士全為南方士人。朱元璋認為所取有偏向,非常生氣,便命侍讀 張信等十二人重新閱卷,結果仍未有什么改變。太祖大怒,將許多考官及所 取狀元悉加誅戮,把劉三吾戍邊,然后自己親自閱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 人。六月復廷試,以韓克忠為第一。皆北士也。”(《明史》卷七十《選舉 二》)又如永樂二十二年廷試,“上初取孫曰恭第一,嫌其名近暴,曰: ‘孫暴不如邢寬。’遂擢寬第一。仍用朱書填黃榜。一時稱異事。”(《制 義科瑣記》卷一)此類事件對士子來說當然是不公平的,但是它們對科舉制 度本身并沒有太大的影響。因而本書也不對此類雖則有趣卻無關乎根本的歷 史事件作更多的關注。 ⑤關于明代后期的士人棄儒經商的情況,可進一步參考余英時《士與中 國文化》一書第八章《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新四民論——士 商關系的變化”一節。盡管余先生對此有強調過分之嫌,但其所提供的資料 依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明代部分的材料更應多加關注。 “鳶飛魚躍”之語出于《詩·大雅·旱麓》,其原句為:“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唐人孔穎達疏該句曰:“德教明察,著于上下。其上則鳶鳥得 飛至于天以游翔,其下則魚皆跳躍于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 化之明察故也。”(《十三經注疏》第 516頁)孔氏之解此句顯系受有漢儒 解經的影響,故而強調德化之內涵。但該句并非只有此一種解釋,朱熹《詩 經集傳》便引《抱樸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 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卷六) 就陳獻章的熟悉程度言,他應該受朱子影響更大一些,蓋朱子之注乃當時士 子科舉所必讀也。則白沙對該句之怡然自得的境界應有較深之理解。此亦合 乎其一貫思想。 王維譏諷陶潛語見于其《與魏居士書》:“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 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 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 忘大守小,不□其后之累也。”(靜嘉堂藏南宋刻本《王右丞文集》卷八) 此種誤解見于馮達文《宋明新儒學略論》之第五章。作者在引錄了《與 林郡博》和《與陳德雍》二書后評曰:“從此二書可見陳白沙‘心’之困頓。 這種困頓來自于公共生活中的角色擔當:身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 不可以不‘點檢’,即不可以不求助于道德理性,但‘才點檢著便不由己者’, ‘吾心’已不再有自由;而且,身為一家之主,承擔著一家人的日用供給, 還不可以不講求工具理性;加之,人不僅必須面對家庭,還必須面對社會, 應接各種人等與各類事務,一一需要講求理性。此‘心’又豈能不困頓呢?” (第232頁)說《與陳德雍》有突出主體情感的傾向尚可理解,因有“行樂”、 “野性”的話可以作為證據。但說《與林郡博》亦為突出情感則實屬誤解, 因其“正欲事事點檢”的是白沙自己,不是在老少面前不得不點檢,而是在 老少面前不能自我作主地去“點檢”。一語錯解,而意義全乖。 |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