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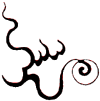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xué)與中晚明士人心態(tài)》 |
|
|
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tài)的流變 第三節(jié)、白沙心學(xué)與明代士人人格心態(tài)的變異 二、內(nèi)在超越與江門心學(xué)的價值取向 后世學(xué)者論及江門心學(xué)時,一般均將其納入宋明理學(xué)或者更確切地說是 心性之學(xué)的范疇。但具體到其學(xué)術(shù)品格時,便會有見仁見智的差異。直至今 日,意見也還是難以歸一,侯外廬《宋明理學(xué)史》認為:“他為學(xué)的根本目 標,乃是‘作圣’,即完成儒家主張的倫理道德修養(yǎng)。在這一點上,他和宋、 元以來的理學(xué)家是一致的。”(下卷一,155頁)而有人則認為他屬于道家: “白沙顯示的精神意態(tài),甚似莊周,非但與象山、陽明不類,即與濂溪、康 節(jié)亦截然不同。由于白沙使明代理學(xué)大放異采,亦毓成理學(xué)中的杰出人物之 一。我們?nèi)缱u之為新儒家中的莊周,亦無不可。”(林繼平《明學(xué)探微》第 43頁)但明清許多學(xué)者更傾向于指白沙為禪,如陳建、黃宗羲等均持此議, 故四庫館臣總結(jié)曰:“史稱獻章之學(xué),以靜為主,其教學(xué)者,但令端坐澄心, 于靜中養(yǎng)出端倪,頗近于禪,至今毀譽參半。”(《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0, 《別集類》二三)其實,即使白沙本人也未給自己限制固定的身份,他時而 稱佛,所謂“道人本自畏炎炎,一榻清風卷畫簾。無奈華胥留不得,起憑香 幾讀《楞嚴》。”(《陳獻章集》卷六,《午睡起》)時而稱道,所謂“山 人家世本陳摶,供奉何堪晚得官;”(同上,《至日病起四首》其四)又時 而稱儒,所謂“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fā)前;”(同上卷四,《夜坐 二首》其二)有時甚至對楊朱之學(xué)亦頗有好感,說“莫笑楊朱小,楊朱解愛 身。”(同上,《寄太虛上人二首》其二)可見若欲徹底理清白沙之學(xué)的屬 性是相當困難的,因為無論提出任何一家來指稱江門心學(xué),均可在其詩文集 中尋找到支撐的例證,但同時又難以排除其他反證。在此,我認為有效的途 徑是抓住其詩文中之主要意象,歸納出其主導(dǎo)傾向,最后再看其主要人生價 值取向。如此也許可大致理清白沙之哲學(xué)思想。 陳獻章的哲學(xué)思想具有獨特的表現(xiàn)形式,即他主要不是用論文或語錄去 宣揚其人生見解,而是常常用詩歌來描述其人生感受與人生理想。在其詩歌 中,涉及到許多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如嚴光、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 二程、朱熹等等,但出現(xiàn)最多并構(gòu)成其詩歌主要意象的則有兩個人,這便是 陶潛與邵雍。隨手翻檢即可得如下詩句:“或疑子美圣,未若陶潛淡。”( (《陳獻章集》卷四,《示李孔修近詩》)“從來少人知,誰是陶潛者。” (同上,《寒菊》)“我思陶長官,廬山一杯酒。”((同上,《題民澤九 日詩后》)“若道淵明今我是,清香還屬隔江人。”(同上卷六,《謝九江 惠菊四首》其一)“世人有眼不識真,愛菊還他晉時人。”(同上卷四,《 答惠菊》)“長驅(qū)李白詩中逸,不舍堯夫酒后溫。”(同上卷五,《廬阜書 舍和潘白石五首》其五)“弄丸我愛張東所,只學(xué)堯夫也不孤。”(同上, 《次韻廷實示學(xué)者》)“雪月風花還屬我,不曾閑過邵堯夫。”(同上卷六, 《答石阡太守祁致和》)“敢為堯夫添注腳,自從刪后更無詩。”(同上, 《讀韋蘇州詩四首》其二)“詩到堯夫不論家,都隨何柳傍何花。”(同上, 《得世卿、子長近詩,賞之三首》其三)……不必再多加征引,因為不僅仍 有許多同類的篇什,而且還有大量作品雖未出現(xiàn)陶、邵二人姓名,但其情趣、 境界、意象均與他們有一致之處。因而明人楊慎曰:“白沙之詩,五言沖淡, 有陶靖節(jié)遺意。”(《升庵詩話》卷十二)清人朱彝尊亦曰:“白沙雖宗擊 壤,源出柴桑。”(《靜志居詩話》卷七)都準確無誤地指出了白沙與陶、 邵二人之間的前后繼承關(guān)系。 現(xiàn)在須進一步追問的是,陳獻章到底繼承了陶、邵二人的什么,同時又 與之有何不同。關(guān)于白沙與淵明之關(guān)系,仍可在其詩中見出。若單從詩之數(shù) 量觀,他之重淵明實有甚于堯夫,他曾集中寫下過十二首和陶詩,雖未能趕 上有百首之多的蘇東坡,卻也足以顯示他對淵明的重視,其中一首寫道: 我始慚名羈,長揖歸故山。故山樵采深,焉知世上年?是名鳥搶榆,非 曰龍潛淵。東籬采霜菊,南渚收菰田。游目高原外,披懷深樹間。禽鳥鳴我 后,鹿豕游我前。泠泠玉臺風,漠漠圣池煙。閑持一觴酒,歡飲忘華顛。逍 遙復(fù)逍遙,白云如我閑。乘化以歸盡,斯道古來然。(《陳獻章集》卷四, 《歸園田三首》其一) 同時他還有一首《對菊》詩,可一并捻出作為對照,其曰: 淵明無錢不沽酒,九日菊花空在手。我今酒熟花正開,可惜重陽不再來。 今日花開顏色好,昨日花開色枯槁;去年對酒人面紅,今年對酒鬢成翁。人 生百年會有終,好客莫放樽罍空。貧賤或可驕王公,胡乃束縛塵埃中?簪裾 何者同牢籠!(同上) 此二首詩足以顯示白沙對淵明精神的認同與效法。他告訴我們,他之歸 隱乃是對人生透悟后的必然選擇。他感受到了生命的短暫與塵世的虛幻,不 愿再受世俗禮法牢籠的折磨。在貧賤而適意與富貴而受羈之間,他寧可選擇 前者。他告訴我們,他自甘作一只雖則微小卻能自由自在飛翔于樹間的鳥, 而并不是暫隱鄉(xiāng)野、待時而動的潛龍。于是他表示要義無反顧地投入大自然 的懷抱,學(xué)陶淵明種田采菊,游目高原,披懷深樹,與禽鳥作伴,與鹿豕相 游,做一個如白云般逍遙自如的人。應(yīng)該說,他的確把握到了陶淵明的精髓。 關(guān)于陶潛,也很難用一句話來概括其思想,他的復(fù)雜程度決不低于白沙先生。 單是他的人生態(tài)度到底屬于儒釋道哪一家,便又是個永遠說不盡的話題。但 我以為,白沙此處的“乘化以歸盡,斯道古來然”一句,方真正是陶詩的靈 魂。無論說陶潛是儒家也罷,佛家也罷,道家也罷,玄學(xué)也罷,但誰都不能 不承認,以委運任化的人生態(tài)度,去追求物我一體、心與道冥的人生境界乃 是其主導(dǎo)傾向。陶氏本人并無意專門繼承某家思想,所以才會在《神釋》一 詩中如此說:“三皇大圣人,今復(fù)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 同一死,賢愚無復(fù)數(shù)。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 甚念傷我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yīng)盡便須盡,無復(fù)獨 多慮。”(《陶淵明集》卷二,《影答形三首》其三)顯然,陶潛所看重的, 是對自我生命的珍惜,是現(xiàn)世的我如何活得充實而自在。這其中,也許包含 了儒家君子固窮的品格,佛教一切皆幻的義理,以及道家物我一體的哲思, 然而它們卻都需要融化在陶氏的人生境界中,最終構(gòu)成其委運任化的生命情 調(diào)。陳獻章看到了此一點,于是他也采取了這種人生態(tài)度,以便安頓從俗世 中擺脫出來的自我,從而架起了由“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到“乘化以 歸盡,斯道古來然”之間的思想橋梁。他象陶淵明一樣,主張超越小我,順 應(yīng)造化,一任自然,物我合一,亦即:“一痕春水一條煙,化化生生各自然。 七尺形軀非我有,兩間寒暑任推遷。”(《陳獻章集》卷六,《觀物》)他 之所以歸向自然而超越世俗,是由于看破人間是非、得失、榮辱的沒有把握, 為此而浪費生命毫無意義,即所謂:“費盡多少精神,惹得一場笑唾。百年 不滿一瞬,煩惱皆由心作。若是向上輩人,達塞一起覷破。歸來乎青山,還 我白云滿坐。莫思量,但高臥。”(同上卷四,《可左言贈憲副王樂用歸瑞 昌》)象陶淵明一樣,白沙先生的達觀是建立在對生死了悟的基礎(chǔ)之上,他 體悟到人生只不過是“造物一場變化”而已,又何必執(zhí)著于生死而與造化為 敵,故而說;“孔子曳杖歌,逍遙夢化后。我夢已逍遙,六字書在牖。圣愚 各有盡,觀化一遭走。問我年幾何,春秋四十九。死生若晝夜,當速何必久? 即死無所憐,乾坤一芻狗。”(同上,《夢觀化,書六字壁間曰:造物一場 變化》)其弟子湛若水評此詩曰:“蓋死生者晝夜之道,大數(shù)既速,何必欲 久,況人物如天地之一芻狗耳,死何足憐哉?觀于此詩,先生深明晝夜之道, 壽夭不二者矣。”(《白沙子古詩教解卷之上》,見《陳獻章集》附錄一) 超榮辱得失,明生死變化,倡物我合一,得自然之樂,白沙從淵明處所獲得 的這些價值觀念與人生態(tài)度,在本質(zhì)上顯然都更合乎道家的精神,從這個角 度說,可以認為陳獻章具有道家的特征。 然而,白沙并不僅僅留意于淵明先生,他還對堯夫先生同樣感興趣。其 實,白沙對邵雍的認同乃是對宋儒不同學(xué)術(shù)風格的一種選擇。就為學(xué)風格言, 大致可將宋儒分為二途,一途是以周敦頤、邵雍、程顥為代表的傳統(tǒng),為學(xué) 主張寬松和樂;另一途是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傳統(tǒng),為學(xué)主張莊敬嚴謹。 白沙的選擇從其一首詩中可明顯見出:“一語不遺無極老,千言無倦考亭翁。 語道則同門路別,君從何處覓高蹤。”(《陳獻章集》卷六,《讀周朱二先 生年譜》)從白沙的學(xué)風看,他自然喜愛不事言說的無極老,而對千言無倦 的朱子缺乏興趣。他最終選取邵堯夫作為宋儒的代表,我以為他是看中了邵 氏不事言說的風格與求樂的人生價值取向。他有《次韻廷實示學(xué)者》詩曰: “樹倒藤枯始一扶,諸賢為計得毋疏。閱窮載籍終無補,坐破蒲團亦是枯。 定性未能忘外物,求心依舊落迷途。弄丸我愛張東所,只學(xué)堯夫也不孤。” (同上卷五)他認為苦讀載籍乃糾纏于外物,而坐破蒲團恰恰是求心于迷途, 均無助于身心之涵養(yǎng)。正確的做法是應(yīng)學(xué)康節(jié)的求樂,所謂“真樂何從生, 生于氤氳間。氤氳不在酒,而在心之玄。行如云在天,止如水在淵。靜者識 其端,此生當乾乾。”(同上卷四,《真樂吟,效康節(jié)體》)“氤氳”即陰 陽之氣渾融一體,而欲達此境界便須保持心體之超越玄遠。猶如云行于天而 無心,水止于淵而澄徹。倘若能達此境界,便會擁有旺盛的生命活力,而這 也才是人之真樂。應(yīng)該說白沙也是對邵雍知之甚深的,邵雍之為學(xué)宗旨在于 求取自我之適意,他曾自稱:“君子之學(xué)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yīng)物皆余事也。” (《皇極經(jīng)世書》卷十四,《觀物外篇下》)又言其為學(xué)目的曰:“學(xué)不際 天人不足以謂之學(xué)。”“學(xué)不至于樂亦不可謂之學(xué)。”(同上)而要求樂, 便不能被世俗禮法所縛,放不開,便不樂,但又并非要破壞禮法,他已體悟 到禮法之真意,故言:“悟盡周孔道,解開仁義結(jié)。禮法本防奸,豈為吾曹 設(shè)。”((擊壤集)卷三,《秋懷三十六首》其三)心中有禮,而行不必拘 禮,此即孔子所言從心所欲不逾矩也。但此又非以年齒論,而是以獲道與否 論。待獲道放開后,便會心閑而自得:“動止未嘗防忌諱,語言何復(fù)著機關(guān)? 不圖為樂至于此,天馬無蹤自往還。”(同上卷六,《思山吟》)此種樂實 際上是內(nèi)在超越之樂,它主要指的是精神世界的自滿自足,即所謂:“心安 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 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同上卷十一,《心安吟》)邵、陳二人將此 種樂之境界同喻之為羲皇上人之樂,康節(jié)言:“北窗當日比羲皇。”(同上 卷五,《后園即事》)白沙亦曰:“悠然清唳外,一枕到皇羲。”(《陳獻 章集》卷四,《對鶴二首》其一)“江門水上廬山顛,蒲團展臥羲皇前,洗 手一弄琴無弦。”(同上,《枕上》)其實,二人之“羲皇”之樂的意象又 同受陶潛的啟示,淵明曾說:“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fù)歡然有喜。常 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陶淵明集》 卷七,《與子儼等疏》)綜合三人對羲皇的表述,可以作一大致的歸納。羲 皇本是中國遠古的圣人,羲皇之世乃是禮法未設(shè)、一任自然的盛世,則羲皇 上人乃是一任本真、渾樸自然、率意和樂的太古之人。邵、陳二人既然都對 羲皇之世充滿向往之情,那么他們也同樣對世俗之事不屑一顧,而寧可獨享 其樂,邵雍有詩曰:“人情大率喜為官,達士何曾有所牽。解印本非嫌薄祿, 掛冠殊不為高年。因通物性興衰理,遂悟天心用舍權(quán)。宜放襟懷在清景,吾 鄉(xiāng)況有好林泉。”(《擊壤集》卷三,《賀人致政》)白沙亦有詩曰:“官 府治簿書,倥傯多苦辛;文士弄筆硯,著述勞心神。而我獨無事,隱幾忘昏 晨。南山轉(zhuǎn)蒼翠,可望亦可親。歲暮如勿往,枉是最閑人。”(《陳獻章集》 卷四,《拉馬玄真看山》)白沙先生從康節(jié)處學(xué)來的求樂精神的確改變了明 代前期士人的風貌,與官場士人的案牘勞苦及理學(xué)之士的檢束自勵相比,白 沙的確使原本繃緊的心理獲得了極大的放松,并真正享受到了與自然相親融 的審美愉快。他在《東圃詩序》中對其弟子范歸之父生活情調(diào)的描繪實可視 為其自況: 翁寄傲于茲,或荷丈人蓧,或抱漢陰甕,興至便投竿弄水,擊壤而歌。 四時之花,丹者摧,白者吐。或飲露而餐英,或?qū)し级餍Γ豢祁^箕居,檉 陰竹影之下,徜徉獨酌;目諸孫上樹取果實,嬉戲笑語以為適。醉則曲肱而 臥,藉之以綠草,灑之以清風,寤寐所為不離乎山云水月,大抵皆可樂之事 也。(同上卷一) 然而白沙在獲得這些人生受用時,卻有放棄儒家社會責任的危險,因而 招致了不少人的非議,明末大儒劉宗周曰:“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 逮;學(xué)術(shù)類康節(jié),而受用太早。質(zhì)之圣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也。似禪非禪, 不必論矣。”(《明儒學(xué)案》卷一《師說》)清儒陸世儀說得更具體:“世 多以白沙為禪宗,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一主于灑脫曠閑以為受用,不 屑苦思力索,故其平日亦多賦詩寫字以自遣,便與禪思相近。或強問其心傳, 則答之曰:有學(xué)無學(xué),有覺無覺,言未嘗有得禪也。是故白沙靜中養(yǎng)出端倪 之說,中庸有之矣。然不言戒慎恐懼而惟詠歌舞蹈以養(yǎng)之,則近于手持足行 無非妙道之意矣。不言睹聞見顯而惟端倪之是求,則近于莫度金針之意矣。 其言養(yǎng)氣則以勿忘勿助為要,夫養(yǎng)氣必先集義,所謂必有事焉也。白沙但以 勿忘勿助為要,失卻最上一層矣。”(《鮚埼亭集》卷二八,《陸桴亭先生 傳》)陸世儀首先肯定了白沙之學(xué)是儒而不是禪,但它又不同于陸氏理想中 的儒,其要旨在于,其為學(xué)目的乃是灑脫閑曠之受用而無關(guān)于事,其為學(xué)之 法乃是詠歌舞蹈而不講戒慎恐懼,其為學(xué)內(nèi)容乃是勿忘勿助而不言集義。若 再加簡化,則他心目中的白沙之學(xué)便是“樂”與“放”二字。陸世儀身處清 初朱子學(xué)再興的學(xué)術(shù)潮流中,對心學(xué)自然不無偏激之弊。但此段論白沙之學(xué) 的話卻實為持平之論,查白沙詩文集,他不僅有“手持青瑯玕,坐弄碧海月” (《陳獻章集》卷四,《度鐵橋》)的逍遙受用,而且有“白頭襟抱胡為爾, 得放開時須放開”(《陳獻章詩文續(xù)補遺》,《次韻緝熙河源道中聞林琰兇 問》)的證據(jù),更重要的是明人夏尚樸還記述了下面一則往事: 章楓山遺予曰:“白沙應(yīng)聘來京師,予在大理往候而問學(xué)焉。白沙云: “我無以教人,但令學(xué)者看‘與點’一章。”予云:“以此教人,善矣。但 朱子謂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于禪。”白沙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朱子時,人多流于異學(xué),故以此救之;今人溺于利祿之學(xué)深矣,必知此意, 然后有進步處耳。”(《明儒學(xué)案》卷四) 因此,黃宗羲便十分肯定地指出白沙之學(xué)術(shù)淵源為:“遠之則為曾點, 近之則為堯夫,此可無疑者也。”(同上卷五)其實,比黃氏更早的林俊便 已指出白沙之學(xué)風為;“脫落清灑,獨超牢籠造物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 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續(xù)藏書》卷二一)所有的這些言論, 實質(zhì)上最終均可收歸為一個“樂”字,則白沙是否為儒的問題實又可歸結(jié)為 對“樂”之如何看待的問題。其實,在儒家的傳統(tǒng)中,很少有人公開反對求 樂,即使力主誠敬的朱熹亦然,其分歧主要是如何理解樂之內(nèi)涵。在宋明理 學(xué)中,較早提出學(xué)以求樂此一話題的是周敦頤,程顥曾回憶其從周子受學(xué)曰: “昔受學(xué)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二程集》第16 頁)而周敦頤本人是如此解釋孔顏之樂的:“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 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 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 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通書》卷二,第29頁,《顏子》)在此孔顏之樂分為兩層,一是“見其 大”,一是“心泰”,前者為后者之條件,而后者為前者之結(jié)果。后來程頤 又作過重要補充:“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 ‘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 不為顏子矣。’”(《二程外書》卷七,第35頁)依現(xiàn)代學(xué)者陳來先生的見 解,此所言乃指“‘道’并不是樂的對象,樂是人達到與道為一的境界所自 然享有的精神的和樂。”(《宋明理學(xué)》第45頁)此解可通,亦即上所言之 “心泰”,但在此又必須指出,雖所樂非道,然若未見其“大”,亦無“心 泰”境界實現(xiàn)之可能。可見“道”依然是“心泰”之樂的前提條件。后來, 明儒曹端又將此“道”落實到一“仁”字上,并重釋孔顏之樂曰:“孔顏之 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 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 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 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xué)者自得之。”(《明儒 學(xué)案》卷四四)可見仁乃是其強調(diào)的重點,故陳來先生引此說釋曰:“仁可 以包括樂,但樂卻無法包容仁。若把精神的和樂愉悅當作人生全部精神發(fā)展 的唯一目的,就仍然預(yù)設(shè)了一種自佚的動機,與追求感性快樂的快樂主義在 終極取向上仍不能完全劃清界線,也無法與佛家、道家劃清界線。從這個方 面看,曹端堅持仁的本源性,堅持仁是儒學(xué)的最高的完滿的境界,是符合儒 學(xué)傳統(tǒng)的。”(《宋明理學(xué)》第223—224頁)強調(diào)求樂的倫理前提當然是很 重要的,但又必須同時指出,這種觀點并不能概括儒學(xué)的全部傳統(tǒng),起碼從 曾點到邵雍再到陳獻章就未能包容進去。如果仔細觀察,會發(fā)現(xiàn)理學(xué)諸子更 樂意強調(diào)顏子之樂,而心學(xué)諸子更傾心于曾點之樂。白沙很明確地說要讓后 學(xué)看“與點”一章,恰好證實了此一點。“與點”出自《論語·先進》,曾 點所言之志的原文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孔子到底所嘆為何, 由于行文簡略而不易斷定,因而也就產(chǎn)生了不同的解釋。就文字本身觀,似 乎并未涉及倫理的內(nèi)容。在暮春的季節(jié),穿上輕便的春裝,約上幾個同伴弟 子,在沂水中沐浴,在舞雩臺上吹風,然后一路唱著歌歸來。的確有融合于 大自然的審美情趣與超越世俗的襟懷。故邢昺疏曰:“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為 政也。”(《十三經(jīng)注疏》2500頁)但此亦僅為推測之詞而已,并沒有什么 歷史的根據(jù)。不過在與子路、冉有、公西華等其他三人的事功志向相比時, 的確顯示出曾點的超越情懷。依此來看邢氏之疏,可許之為有一定道理。邢 氏之后對曾點之志影響最大的解釋當然要推朱子,他說;“曾點之學(xué),蓋有 以見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稍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 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 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于言外。 視三子之規(guī)規(guī)于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 四書章句集注·論語章句》)朱子畢竟是思想家兼文學(xué)家,能夠利用自我的 審美感受力去深入體悟曾點所擁有的美的人生境界,所謂“胸次悠然,直與 天地萬物,上下同流,”正是一種物我合一的渾融超越之境,而此種境界實 現(xiàn)的前提,便是具備“初無舍己為人之意”的超越襟懷。但象其他理學(xué)家一 樣,朱子也為曾點之志附加上了倫理的限定,即所謂“人欲盡處,天理流行,” 從而帶上了濃厚的理學(xué)色彩。不過這顯然不是曾點與孔子的原意,而是著作 本人的“創(chuàng)造性詮釋”。陳獻章對曾點之樂的理解顯然與朱子不同,而更接 近其原始意象。試看下面數(shù)則直接論樂的文字: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于流俗,斯可矣。(《陳獻章集》卷二, 《與順德吳明府四則》其三)……存存默默,不離傾刻,亦不著一物,亦不 舍一物,無有內(nèi)外,無有大小,無有顯隱,無有精粗,一以貫之矣。此之謂 自得。(《陳獻章詩文補遺》,《與緝熙書》) 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得山莫杖,臨濟莫喝。萬 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掇。(《陳獻章集》卷四,《示湛雨》) 在此,其論述的核心在“自然”二字,而其對立面則為“流俗”,若欲 “咸歸乎自然”,必須“不受變于流俗”。這便是陳氏最著名的立學(xué)宗旨: “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同上卷二,《與湛民澤》)因而此所言“天命” 并非朱子所言“天理”,而是自然之意。當然,白沙并不反對仁義教化,其 “鴛飛魚躍”之本意便是王化得行而萬物各得其所之意。⑥但白沙的立腳點 仍在于自我的受用,這便是所謂的“亦不著一物,亦不舍一物”,換言之, 即不離世俗而又超越于世俗,這顯然是禪宗所倡導(dǎo)的隨緣任運的態(tài)度,則其 目的也應(yīng)是自我的解脫與受用。其實,白沙的悟道方法比禪宗更為主觀化, 他甚至連禪家的棒喝也不再需要,只要悟得“萬化自然”的道理,便會獲得 “活潑”的心靈自由。也就是朱子所說的“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 同流。”而這才是曾點之樂的真意。明乎此,便會知道為白沙之學(xué)定性是頗 為困難的,因為它最終必須落實到如何為曾點之樂定性。如果說曾點之樂是 儒家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那白沙便是儒學(xué)的正宗;如果將儒家之學(xué)視為治 國平天下的學(xué)問,那曾點之樂便是儒家的旁枝,白沙自然也便失去了正宗的 地位。 依白沙的本意,他真地是想合陶潛與邵雍為一家,從而融會成他本人的 自然自得之學(xué)。我們讀他的《湖山雅趣賦》,便會有非常真切的體會,為印 象完整,不避文字稍長,全錄如下,以享讀者: 丙戌之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關(guān)而北涉彭蠡,過匡廬之下,復(fù)取道蕭山, 溯桐江艤舟望天臺峰,入杭觀于西湖。所過之地,盼高山之漠漠,涉驚波之 漫漫;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當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 泰然而安。物我于是乎兩忘,死生焉得而相干?亦一時之壯游也。迨夫足涉 橋門,臂交群彥;撤百氏之藩籬,啟六經(jīng)之關(guān)鍵。于焉優(yōu)游,于焉收斂;靈 臺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剝,真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蘊春風 之和,心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樂亦無涯也。出而觀乎通達,浮埃之蒙蒙, 游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以獻其一哂,而況于權(quán)爐大 熾,勢波滔天,賓客慶集,車馬駢填! 得志者揚揚,驕人于白日;失志者戚 戚,伺夜而乞憐。若此者,吾哀其為人也。嗟夫! 富貴非樂湖山為樂;湖山 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愧怍哉! 客有張者,聞余言拂衣而起,擊節(jié)而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 于我何有哉?爭如一笑解其縛,脫屣人間有真樂。”余欲止而告之,竟去不 復(fù)還。噫,斯人也,天隨子之徒與!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微斯人,誰 將與儔?(同上卷四) “丙戌”為成化二年,正是白沙之學(xué)的初步形成期。在第一段,他那“ 放浪形骸”、“俯仰宇宙”的胸襟,物我兩忘、死生無干的境界,“悠然而 適”、“泰然而安”的自得自足,正是莊子那種“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yè)”(《莊子·達生》)的真人境界。而 第二段那種優(yōu)游不迫、虛懷真純的風度,“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 的格調(diào),又展現(xiàn)了他“一回一點”的儒家圣人氣象。此二種傾向當然有相通 之處,那就是出世的胸懷。在這方面,非但儒道相通,且亦與釋通,因而在 白沙的生平中,便很難發(fā)現(xiàn)與釋道相齟齬的情形,他有與僧人交往的經(jīng)歷, 并稱賞佛教曰: “茍有得焉,則能以四大形骸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 安能使我戚戚哉?(同上卷三,《與僧文定》)他更有如太虛那樣交情頗篤 的僧友,認為其”真無累于外物,無累于形骸矣。儒與釋不同,其無累同也。” (同上卷二,《與太虛》)在陳獻章傾心陶、邵與會通佛禪的行為中,可以 發(fā)現(xiàn)他具有一以貫之的價值取向,那便是他對自我身心的安頓與求樂的精神。 他不屬于某一家思想的傳人,而是混合儒釋道后精心作出選擇的結(jié)果。 但如果認真加以比較,白沙又絕對不是陶潛與邵雍的混合體,甚至再加 上些禪學(xué)色彩也依然構(gòu)不成一個完整的白沙先生。陶潛有足夠的超越情懷與 物我一體的審美境界,但在其隱士的從容里不免透露出些許寒酸相,以致寫 下“扣門拙言辭”的《乞食》詩,讓后來不怎么寬容的王維抓住把柄大大譏 諷了一番。⑦白沙則沒有這副寒酸相。康節(jié)先生比陶潛要活的瀟灑得多,他 躲進洛陽的安樂窩中,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留下了他那“美酒飲教微醉后, 好花看到半開時”(《擊壤集》卷十,《安樂窩中吟》)的名句。但他的瀟 灑不免顯得俗氣了些,給人的印象是得了便宜又賣弄乖巧,比如其《龍門道 中作》曾如此寫道:“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 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云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似海,三 十年來探臂行。”(同上卷三)你已經(jīng)擁有了云山之樂與榮辱無驚的生活, 踏踏實實地受用便是,何必再賣弄卷舒自如的成算,用舍隨時的乖巧?至于 說自我宣揚三十年來出入侯門的榮耀,便有些近于無恥了。白沙則沒有這副 賣乖相。他比陶潛高傲,又比邵雍更高潔。無論是讀其詩還是觀其文,都給 人一種偉然屹立的印象與底氣渾厚的感覺。下面這段話只能是白沙先生的, 而不可能見之于陶、邵二集中。 宇宙內(nèi)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 辟,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為牛,馬自為馬;感于此, 應(yīng)于彼,發(fā)乎速,見乎遠。……人爭一個覺,才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 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 冕而塵金玉耶?”(《陳 獻章集》 卷三,《與林時矩》) 陶淵明在悟得此中“真意”后,只是達到了“欲辨已忘言”的默契,“ 悠然見南山”的從容,而陳獻章則有了與萬物一體、與天地并立的崇高感; 當邵雍在為能夠出入侯門深感得意時,陳獻章甚至沒有了錙銖軒冕而塵視金 玉的興趣,因為在他覺悟之后,已經(jīng)具有了“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 的永恒感。在如此感覺中,見六合如微塵,視千古若瞬息,怎么還會想到什 么富貴利祿之事呢?是何種因素給了白沙先生這塵視金玉、糞土王侯的勇氣 與力量?這其中當然不排除有個人氣質(zhì)與時代氛圍的原因,但也與其所汲取 的思想傳統(tǒng)有密切的關(guān)系。這便是孟子的思想與人格在白沙之學(xué)中占據(jù)了突 出的地位,對此他曾有過明確的表述:“……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 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 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 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并出 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 會得,雖堯瞬事業(yè),只如一點浮云過目,安事推乎?”(同上卷二,《與林 郡博》)“色色信他本來”是對自然之強調(diào),而“舞雩三三兩兩”的曾點之 樂,則必須用孟子“勿忘勿助”的工夫方可獲得。所謂“勿忘勿助”本是孟 子所言養(yǎng)氣工夫,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yǎng)我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 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充塞于天地之間。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 不慊于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孟子正義》卷三,《公孫丑章句上》)對后三句 諸家有不同的解釋,我以為宋人孫奭疏中所引一說較為可取,其曰:“言人 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后乃正其心而應(yīng)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不在 汲汲求助益之而已。”(《十三經(jīng)注疏》2686頁)此猶如孟子本人所引“揠 苗助長”所喻,倘若以為無益而舍之,便等于不耘苗,亦即“忘”;而倘若 揠苗助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亦即“助”。只有勿忘勿助,才能以心帥 志,以志帥氣,從而使自我的浩然之氣沛然若決江河,并最終成就其“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上》)的大丈夫人格。 當然,正如陸世儀所言,白沙言養(yǎng)氣但以勿忘勿助為要,卻未強調(diào)“必先集 義”,也就是說他只主張順應(yīng)自然,而未強調(diào)德性之主導(dǎo)。但有一點是明確 的,即白沙認為曾點之樂須和孟子之氣合而言之,才會具有“天地我立,萬 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崇高境界,否則便“一似說夢”而不著邊際。正是 有了孟子養(yǎng)氣理論與大丈夫人格的介入,才使白沙比陶潛與邵雍具備了更為 高傲豪邁的情懷,同時也具備了心學(xué)的品格。再合之以陶氏超越的境界與曾 點求樂的精神,終于構(gòu)成了白沙之學(xué)的獨自特征,黃宗羲曾對此總結(jié)說:“ 先生之學(xué),以虛為基本,以靜為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今來、穿紐湊泊為 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為功用,以勿忘勿助為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yīng)用 不遺為實得。”(《明儒學(xué)案》卷五)講虛,講靜,講湊泊,講勿忘勿助, 可謂全面,但不如其師劉宗周講的精練而得其要領(lǐng),即:“先生學(xué)宗自然, 而要歸于自得。”(《同上卷一,《師說》)綜合其師徒二人之語,可以如 此描述白沙之學(xué):它以虛為獲道的基本前提,以靜為獲道的基本途徑,以自 然為獲道的基本方法,以自得之樂為獲道的目的,以物我合一、瀟灑軒昂為 獲道的境界。此種品格顯然使白沙之學(xué)帶有了濃郁的詩學(xué)特征與審美特性。 的確,白沙的學(xué)說多用詩來表現(xiàn),白沙的人生也充溢著詩意。我們今天讀白 沙的詩,依然可以感受到他是真正獲得了美的享受,而不僅僅是停留于口頭。 試看下面二首: 撥悶無人致酒瓶,哦詩燈下一郎清。夜深笑拍胡床語,忽亂階前落葉聲。 (《陳獻章集》卷六,《與景星夜坐》) 遲遲春日滿花枝,江上群兒弄影時。漁翁睡足船頭坐,笑卷圓荷當酒卮。 (同上,《江上》) 前一首以動寫靜,笑語亂卻落葉之聲,以顯示環(huán)境之幽靜,并烘托心境 之平靜。若無審美之情趣與超越之境界,便很難感受到這物我交融的幽深細 微之處。后一首寫在花香日暖的春景中,群兒盡情地玩耍嬉戲,以致引動了 老者的童趣,也“笑卷圓荷當酒卮”了。這天真的情調(diào),簡直是天人的境界。 明代士人由于官場的奔波與理學(xué)的桎梏,疲憊木僵的心靈已經(jīng)很久沒有感受 到這種美了。白沙之所以能感受到這自然天真之美,不僅僅是他的歸隱生涯 為他提供了親融山水的條件,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觀及其心學(xué)理論陶鑄了他 那具有審美能力的主體心靈,對此白沙本人有著深切的體會,他說:“羅浮 之游,樂哉! 以彼之有入此之無,融而通之,玩而樂之,是誠可樂也。世之 游于山水者皆是也,而卒無此耳目之感:非在外也。由聞見而入者,非固有 在內(nèi)則不能入,而以為在外,自棄孰甚焉。”(《陳獻章詩文續(xù)補遺》,《 與林緝熙三十一則》其十三)羅浮之游可以產(chǎn)生“樂”的受用,但世人有那 么多游山水者,何以難獲此樂?可見此樂非在外而是在內(nèi)。山水之樂當然離 不開“融而通之,玩而樂之”的主客交融,但在白沙看來,“非固有在內(nèi)則 不入”,主體的審美心靈才是第一位的。可以說白沙是明代倡言主體性靈說 的第一人。因此,白沙的學(xué)說,白沙的人格,白沙的詩作,無疑為士人朽腐 的心靈帶來了一似清風與活力。直到近人梁啟超讀白沙時,依然可產(chǎn)生如下 的感覺:“白沙心境與自然契合,一點不費勁,……常常脫離塵俗,與大自 然一致,其自處永遠是一種鳶飛魚躍、光風霽月之景象,可見其人格之高尚, 感化力之偉大矣。”(《儒家哲學(xué)》第五章)由此便可知白沙之魅力。 |
|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版權(quán)所有 北京國學(xué)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