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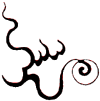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
|
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的流變 第三節、白沙心學與明代士人人格心態的變異 一、江門心學的內轉及其時代印痕 陳獻章(1428—1500),字公甫,號石齋。廣東新會白沙里人,故人稱 其為白沙先生。又白沙瀕臨西江入海之江門,故又稱其學為江門心學。其早 年曾銳意科舉,二十歲時中正統十二年舉人,后兩次參加禮部考試皆下第。 其間從吳與弼講學。五十六歲時因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薦而被征召入朝, 并被命就試吏部。屢以病辭不赴試,上疏乞終養,被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自 此后屢薦不起,在家鄉講學而終其一生。 江門心學在明代學術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盡管明朝是個思想活躍、名 家迭出的時代,但真正能夠作為劃分時代標志者,則應推薛瑄、陳獻章與王 陽明三人。李庭機在萬歷年間曾就此作過一次較具體的論述,他說:“國初 固多才,然而挺然任圣道者寡矣。自河津薛公起而引圣道為己任,卮言細行, 必準古則遺訓而繩之。蓋自是天下學道者四起,爭自濯磨以承圣范。豈謂盡 出河津哉?要之,默自河津啟之也。然而士知淳質行己矣,于心猶未有解也。 自新會陳公謂‘學必有源,靜而反觀乎此心之體,得其自然而不假人力。’ 以為至樂具是矣,其于世之榮名若遺也。蓋自是天下學道者,浸知厭支離而 反求諸心。豈謂盡出新會哉?要之,默自新會啟之也。然以其初知反本真也, 則猶隱然與感應二之也。自會稽王公于百難萬變中,豁然有悟于學之妙機, 以為天下之道原自吾本心而足也。于是揭人心本然之明以為標,使人不離日 用而造先天之秘,不出自治而握經世之樞,及其隨所施而屢建大勛,則亦由 學之約而達也。蓋自是天下學道者,浸知顯微之無間,體用之一源,劐然有 中乎道之窽卻。豈謂盡出會稽哉?要之,默自會稽啟之也。”(《從祀文廟 疏議》,見《陳獻章集》附錄四)就理學的范疇而言,李庭機的論述是相當 精彩的。薛氏的確有肩負圣道的熱情,但卻缺乏盛大氣象與開拓精神,而是 在具體的“卮言細行”上,遵循宋儒的規范而實行之,即所謂“必準古則遺 訓而繩之。”他代表了“濯磨以承圣范”的前期士人的品格。但其缺陷亦至 為明顯,即只知檢點自我以約束其行,卻沒有真切的自我體悟,陳獻章的特 異之處就在于其“反觀乎此心之體”的真實體驗,將圣學與安頓自我直接聯 系起來,認為這才是真正應該追求的,而對于外在于此的“世之榮名”則已 不甚留意。陳氏之學可以說扭轉了薛氏之學的方向,即“厭支離而求諸心” 代替了“淳知行己”。我們暫且稱此種學術品格的差別為哲學的“內轉”。 至于王學與陳學的差異“體用之一源”的知行合一,對此以后會有足夠的筆 墨加以論述。李庭機對明代學術思想演進大勢的概括確有高屋建瓴的氣勢與 通達透徹的明快感,尤其是對江門心學的定位,更顯示出其獨特的眼光。 倘若證之以江門心學的實際,人們將會認識到李庭機之言的分量,并將 進一步深入了解江門心學的具體內涵。陳氏之學的內轉特點是全面性的,在 為學目的上,它由面向社會轉而面向自我個體;在為學內容上,由依傍宋儒 轉而追求自得;在為學方法上,從學習圣賢典籍轉而強調靜中自悟。陳獻章 曾追述其為學經過曰:“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 圣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 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策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 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心與此理未有湊泊吻合處也。于是舍彼之煩,求吾 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后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 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圣訓,各有頭緒來歷, 如水之有源也。于是渙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茲乎?’”(《陳獻章 集》卷二,《復趙提學僉憲》)白沙此論,重在“自得”,“自”是對道的 自我真切體悟;“得”是對圣人之道的真實把握。即所謂“道也者,自我得 之,自我言之,可也。”(同上《復張東白內翰》)而自得的標志便是“義 理須到融液處,操存須到灑落處。”(同上)所謂“融液”亦即心與理之“ 湊泊吻合處”。而此“湊泊吻合處”亦即是“心之體隱然呈露”之“物”, 用現代術語講便是獲道之圣人境界。所以他才會說“作圣之功,其在茲乎”。 為了求取此自得的結果,便必須保證必要的前提條件與正確的為學方法。最 重要的是“靜坐”,因為它可以保持心境的平和寧靜,以便于自我的體悟。 就白沙先生所言的“靜坐”言,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首先它必須擺 脫世俗的干擾,不為各種名利所誘惑,他對此具有頗為深入的體會:“予少 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汩沒于聲利、支離于秕糠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 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游。然后益嘆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 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復長也。坐小廬山 十余年間,履跡不逾于戶閾,俯焉茲茲,以求少進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于 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陳獻章集》卷一,《龍崗書院記》)如果簡 單地講便是“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同上卷二,《與賀 克恭黃門》)其次是“求之吾心”的治學方法。不少人認為陳獻章為學反對 讀書,這自然有一定道理,因為他非但說過:“此者茍能明,何必多讀書。” (同上卷五,《贈羊長史寄賀黃門欽》)而且還表示:“他時得遂投閑計, 只對青山不著書”。(同上卷八,《留別諸友》)但他又并非主張絕對地不 讀書,讀與不讀,要視能否獲道而定,故曰:“夫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 求之書籍而道存焉,則求之書籍可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反而求之吾心而道 存焉,則求之吾心可也。”(《陳獻章詩文續補遺》,《與林緝熙書》)因 此他認為讀書應始終圍繞著自我體悟而進行,他深信“以我而觀書,隨處得 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陳獻章集》卷一,《道學傳序》)無 論是靜坐也罷,以我為主的讀書方法也罷,均是為了達到自我獲道的目的。 他將此種治學的特點稱之為重內而輕外:“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 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似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所謂 浩然而自得者矣。”(同上卷一,《李文溪文集序》)“重內輕外”便是內 轉,內轉便是更加重視自我,而重視自我的內涵便是“自得”。這可以說是 江門心學的主要特征,也是明代學術思想的一次大的轉折。 陳獻章的此種學術轉折與其現實人生經歷有著直接的關聯。他本來是頗 為熱中于仕進的,這從他多次參加禮部考試的行為中可以得到證明。但后來 當他被彭韶、朱英推薦于朝而有出仕機會時,卻又多般推辭,最終歸隱江門, 以講學而終其一生。關于陳獻章拒絕出仕的原因,黃宗羲說朝廷“令就試吏 部”是由于“政府或尼之”的結果,故而決意歸隱。(見《明儒學案》卷五, 《白沙學案上》)其實問題遠非如此簡單。早在被征召之前,陳獻章就已經 沒有了出仕的興趣,故黃宗羲言:“已至崇仁,受學于康齋先生,歸即絕意 科舉,筑春陽臺,靜坐其中,不出閾外者數年。”(同上)他在成化二年復 游太學,實在是非所得已,他在《與湛民澤書》中說:“久居于危,嘗兩遭 不測,幾陷虎口。不得已為謁銓之行,非出處本意也。”(阮榕齡《編次陳 白沙先生年譜》,見《陳獻章集》附錄二)阮氏于此下注曰:“按即習射事。” 所謂習射事發生于成化二年,《年譜》記曰:“講學之暇時與門徒習射禮。 流言四起,以為聚兵。眾皆為先生危,先生處之超然。時學士錢溥知順德縣, 雅重先生,勸亟起,毋詒太夫人憂。先生以為然,遂復游太學。”(同上) 可知他之不肯出仕乃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根據他在詩文中的表述,可以分為 消極與積極兩個方面。消極方面是全身遠害。他在《與張廷實主事》中談及 一位早逝的士子說:“文祥始從湖西游,頗見意趣,后為仕進累身,遂失其 故步,至不得一第而死,是亦命也。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 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陳獻章集》卷二)在《 悼馬龍》(同上卷六)一詩的小序中,他幾乎用了相同的語言,對為追求科 第而死的馬龍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與遺憾。其實不僅中舉前的苦讀是對生命的 戕害,即便在進入官場后,也會有更多的麻煩接踵而來。他曾追憶在京師的 經歷曰:“余頃居京師二年,間從貴公卿游,入其室,見新故卷冊滿案,其 端皆書謁者之詞。就而閱之,凡以其親故求挽詩者,十恒八九,而莫不與也。 一或拒之,則艴然矣。懼其艴然而且為怨也而強與之,豈情也哉?噫,習俗 移人,一至于此,亦可嘆也。天下之偽,其自茲可憂矣。”(同上卷一)在 官場中,僅此應付挽詩一項,就令白沙先生頭痛不已:倘若不能滿足眾人, 便會艴然而怨,這當然是很危險的;如果盡量滿足,則又必須違心作假,心 中便會充滿痛苦。于是,他感到官場實在是桎梏人的牢籠,便借詩感嘆道: “金籠鎖鸚鵡,山林綜斑鳩。巧拙知誰是,天機不自由。”(同上卷五,《 題畫》)在自由與羈鎖之間,他無疑選擇前者,便只好退隱而不入仕。此種 意念在《送李世卿還嘉魚其五》中顯示的最為清晰:“疾風起驚濤,舟以柁 為命。柁乎茍不操,舟也何由靜?是舟如我身,孰知身之阱?是柁如我心, 孰祛心之病?不如棄其舟,免與風濤競。”(同上卷四)由于人生世途的險 惡,故而要放棄人生的擔荷。既然自我不能向外伸展以建立功業,便只好收 斂內轉以悅己適志。積極方面則是追求個體自我的舒展與自我道德的完善。 他在《南歸寄鄉舊》中,用了十首五律來描繪其鄉居野處的自得情景,其中 第六首曰:“山童呼犬出,狂走信諸孫。乳鴨爭嬉水,寒牛不出村。墟煙浮 樹梢,田水到桑根。鄰叟忻相遇,笑談忘日曛。”(同上卷六)在遠離官場 的自然山水中,沒有了爾虞我詐的爭斗,沒有了利害得失的權衡,當然也就 沒有了機心,沒有了憂懼,面對墟煙田水,眼觀無拘諸孫,似乳鴨嬉水之自 在,如寒牛戀村之自得,在與鄰叟的開懷笑談中,不知不覺度過了一日的光 陰。這樣的生活在世俗的眼中也許過于平淡,但陳獻章卻認為它比高官厚祿 更值得珍惜,因為他有了自己的人生價值觀:“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 與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為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 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故 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貧賤、死生、禍 福,曾足以為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 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 逃,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 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 ”(同上卷一,《論前輩言銖視軒冕塵視金玉 上》)當他擺脫世俗的纏繞而體悟到道之境界時,便會與道合一,從而產生 超越天地萬物的崇高感覺,那么世俗眼中的什么富貴、貧賤、死生、禍福, 與道相比也就不值一提了。在此種人生體驗中,他想到了古人陶淵明,感到 自己在心靈上與之獲得了共鳴,大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相同感 受,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出如此詩句:“五斗之粟可以生,折腰殆非賢所能。 即生斯世須妨俗,莫道前身不是僧。廬阜社中期滾滾,潯陽菊畔醉騰騰。南 山歌罷悠然句,誰續先生五字燈。”(同上卷五,《懷古》)他象陶淵明一 樣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希望保持自我人格的獨立,從而追求那悠然自在的人 生境界。正是在這方面,他自以為理所當然地應成為陶淵明的香火傳人。 《明史·儒林傳》曰:“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直流馀裔,師承 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 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此處所言之“始”,當然是為了突出 其轉變學風的作用,而不應該理解為只有到陳獻章本人才開始了此種轉向自 我的關注。其實早在陳氏之前,便有許多士人顯示了此種傾向。在君臣關系 融洽、政治熱情高漲的仁、宣時期,大多數士人固然都具有入仕的愿望與較 強的社會責任感,但這僅是指主流而言,并不說明沒有其他思想成分存在。 比如那位出仕四朝、恩榮始終不減的內閣大學士楊士奇,也并非天天都在歌 功頌德,他有時竟也會吟誦出如下的詩句:“晝眠夢故里,扶竹過西家。鄰 翁敬客,延賞辛荑花。一觴歌一曲,不覺紅日斜。覺來空悵惘,漂泊尚天涯。” (《東里續集》卷四五,《紀夢》)該詩之當注意并不在夢境本身,那固然 也顯示了作者對平靜閑適生活的向往,更令人值得思索的是,他醒來之后依 然不能從夢中情調里擺脫出來,依然將為官做宦視為漂泊天涯。也許會有人 視楊氏之言為無病呻吟的矯情之舉,但我卻認為那的確是其真實的心態,因 為在他始終保持清慎狀態的過程中,心理的疲憊是難以避免的,故而他夢到 了故鄉,夢到了放松的生活,夢到了可以對之暢所欲言的鄰翁。當然,對于 楊士奇來說,如此的生活情調只能在夢中實現,他不可能放棄扶佐皇帝的責 任而自圖清閑,盡管他在晚年曾作過辭官歸鄉的嘗試,也肯定不能得到朝廷 的批準。而且可以推測,具有如此夢境的決不應該只有楊士奇一人。后來隨 著政治環境的惡化,士人的心態從疲憊走向失望與恐懼,那么他們對平靜生 活的渴望當更加強烈,這在我們曾經敘述過的于謙、岳正諸人的意識中均有 明確的表現。同時,還有相當一批士人自明朝立國以來始終便缺乏出仕的政 治熱情,而甘愿在鄉野詩酒優游。如曾在明初被朱元璋施以重法的吳中士人, 便有隱居的傳統。以沈氏家族為例,有人總結史料得出如下結論:“沈氏自 澄以高節自持,不樂仕進,后代以為家法。其族既富資產,亦重詩書。父子 祖孫常相聚一堂,賦詩倡和。三吳間當時論盛族,咸稱相城沈氏為最焉。” (陳正宏《沈周年譜》第5頁)從沈周的祖上到沈周本人再到后來的祝允明、 唐寅、文征明等,都曾有不樂仕進而高視自我的人格特征。因而,陳獻章的 人生追求不能被視為是個人的行為,而應是明代前期士人人格心態演變的必 然結果。在他的人格中,有著鮮明的時代印痕,比如張詡《白沙先生行狀》 載,成化二年復游太學期間,“祭酒邢讓一日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 詩,大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飏言于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 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昶、賀欽輩,皆樂從之游。”(陳獻章集) 附錄二)這首引起士人轟動的詩到底是何內容呢?其中自然有官樣文章,如 “吾道有宗主,千載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但他在客套幾句 后,即筆鋒一轉,大談其所悟之學曰:“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 六載,滅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幾一室內,兀兀同坐忘。 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同上卷四《和楊 龜山此日不再得韻》)在為朝廷培育人才的太學中,面對著太學祭酒,卻公 然宣稱要滅跡于聲利之場,退居于一室之內隱幾悟道,并對“中道奪我航” 者表示強烈的不滿。可祭酒竟稱之為真儒復出,陳獻章也由此聲名大振,并 得到那么多名士的捧場,則說他的追求體現了相當一部分士人的共同志趣, 該不是一相情愿的臆測。 不過,對陳獻章之人品學術造成最直接影響者應推吳與弼。作為師徒的 吳、陳二人,當然應該有直接的承傳關系,但二人又有區別于他人的特殊之 處。從人生經歷上講,他們都有辭官歸隱的舉措,至于白沙之退隱是否受過 康齋的影響,因無直接材料而不便遽下斷語。從時間看,康齋辭官于天順初 年,而白沙則在成化十九年,若言毫無影響似亦過分。所幸張詡《白沙先生 行狀》中存有陳氏本人比較二者行為的一段話,可以透露部分消息,其曰: “康齋以布衣為石亨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 時宰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后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 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愿仕,故不敢偽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 有攸宜耳。”(《陳獻章集》附錄二)白沙認為,其師康齋的本意是要與皇 帝保持一種師友的關系,避免被納入君臣尊卑的官僚體制,以便取得行動的 自由與人格的獨立,或許能起到啟悟君上的獨特作用。但他的良苦用心無人 能夠理解,便只好歸隱而去。他當然也想保持此種自由與獨立,但監生的身 份決定了他不能象乃師那般瀟灑,而必須采取更為迂回復雜的手段。他本無 出仕之意,只是被人強薦出于不得已方才應召,看看他給薦主朱英的書信便 會明白這一切:“然仆竊觀來諭之言,大意欲勸仆出仕耳。非直勸之,且加 責焉。”“伏承此月二十四日都憲老大人命使降臨衡茅,諭令某即日起程赴 京,春闈在邇,不許推延。聞命悚惶,為慰為懼。”(同上卷二,《與朱都 憲》)信中語氣容或有些夸張,對方的強硬也許并無什么惡意,但白沙先生 感受到了壓力則是事實。而且假如他一味堅拒應召,顯然會真地得罪朱都憲。 于是他不得不前往應召并象征性地接受了朝廷的任命。但他并未改變初衷, 依然達到了歸隱的目的,這便是白沙先生的高明之處。因為他獲有職官后, 在閑居時可以“有司以禮相待,免其雜派差徭。”朋友也認為如此可“以心 存道,以跡存身。”但陳獻章并不認為任何人皆可如此做去:“吾之所以見 疾于時,此朋友所共知,宜朋友所共憂也。然有可疑者:跡者,人之所共見; 心者,吾之所獨知。跡著而心隱。通變者,圣人也。執其道至死不變者,賢 人也。圣人任跡而無心,賢人有心而踐跡。因時有險易,故道有恒變。微乎, 微乎,惟圣人然后可以與權。”(《陳獻章詩文續補遺》,《與林緝熙書》 第十六)陳氏本人應召前后的所作所為,當然應被視為圣人之權變行為,其 跡雖已受官,其心則已歸隱。但從實質上看,吳、陳師徒間雖有簡單與復雜 之別,其歸隱以講學、遠害以全身的志趣則是完全一致的。從學術思想上看, 他們之間亦有相承之關系。《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如此論述康齋學術品格 及其與后學之關系:“與弼之學,實能兼采朱陸之長,而刻苦自立。其及門 弟子陳獻章得其靜觀涵養,遂開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篤志力行,遂啟馀干 之學。”(卷一七 0,《別集類》二三)可知康齋之學既有對明前期朱子學 的繼承,又有兼容陸九淵心學的新變。表現在為學風格上,便是既有痛自檢 束自我的竣厲,如:“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觀《 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 前之意。”同時又有追求自我適意的和樂,如:“月下吟詩,獨步綠陰,時 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澹,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 中堂讀倦,游后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 有何樂! ”(上所引均見《明儒學案》卷一,《崇仁學案一》)這后一種品 格顯然對陳獻章產生過深刻的影響。然而自從黃宗羲引用白沙本人所說從吳 聘君學而“未知入處”的話后,遂給人造成一種白沙之學乃得之自悟的印象。 其實白沙本人言之甚明,“所謂未得,謂吾心與此理未有湊泊吻合處也。” 亦即心與理未能渾融為一,用傳統儒學術語說乃是“未能打成一片”。如果 對比二家學術,便可見出無論是為學方法還是所學內容,崇門之學都對白沙 之學有過直接的啟迪。從治學方法上講,白沙之靜觀與心悟實源于康齋。康 齋曰:“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 薰風徐來,而山林闃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 眼明始會識青天,”(同上)盡管康齋未特意強調靜坐,但白沙靜坐的目的 依然是為了心靜,與其師所言并無二意。康齋又曰:“欲異于物者,亦曰反 求吾心固有之仁義禮智而已,欲實四者于吾身,舍圣賢之書則無所致其力焉。” (《康齋集》卷八,《勸學贈楊德全》)“反求吾心”即通過自我之心的體 悟使圣學之理有切于一己之身心,此與白沙之路徑亦無二致。所不同者,康 齋更重視通過圣賢典籍來進行心之體悟,白沙雖不完全反對讀書,卻更傾向 于自我獨立之體悟,這意味著他具有心學的品格。關于白沙從其師處所學之 內容,我以為主要是士人的節操與人生的志趣,阮榕齡曾記曰:“白沙先生 學于吳康齋先生。吳先生無講說,使先生劚地植蔬編籬。吳先生或作字,先 生研墨;或客至,即令接茶。如是者數月而歸,竟無所得于吳先生也。”( 《編次陳白沙年譜》卷一)康齋此種隱居的情趣當會對白沙有潛移默化的感 召作用。但此言白沙從吳先生處學無所得似不確,白沙后來在《祭先師康齋 墓文》中曾回憶說:“先生之教不躐等,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后依仁, 下學上達,日新又新。啟勿助勿忘之訓,則有見于鳶魚之飛躍;悟無聲無臭 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弟子在門墻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閾域。彼丹 青人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而徒摘其他一二近似之跡描畫之,又焉能足以盡 先生之神。”(《陳獻章集》卷一)既然白沙已體味到乃師之勿助勿忘、鳶 飛魚躍之自然與無聲無臭、渾淪一片之境界,則可謂已得其先生之神。其實, 康齋之不愿多加言說無非是令其弟子自悟而已,此種學風后來亦被白沙所繼 承。也許可以這樣講,白沙從康齋處已將其為學之法與人生境界基本了解, 所缺乏的乃是內化為自我的精神世界與真實的人生受用。后來他通過自我的 深切體悟,終于掌握了康齋的學說精髓并有很大的創造發展。因此,陳獻章 的江門心學就不是產生于嶺南深山中的孤學絕說,而是明代前期諸多士人人 格心態涌動演變的必然結果。 |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