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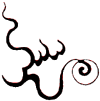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
|
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的流變 第二節、理學、八股與明代前期士風 二、科舉與圣學:手段與目的的顛倒 就明代設立科舉的本意講,是為了求得圣人之道與朝政之勢的有機結合。 盡管在每位皇帝那里對科舉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如太祖為“能以所學措諸 行事”而要求“惟務直述不尚文藻”。(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一《科 試考一》)成祖乃“欲以求博洽之士”而強調“貫通經史識達天人”。(同 上)宣宗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而“不尚虛文”。(余繼登《典故紀聞》 卷十)但在要求士人明圣學以達實用這一點上則是相同的。明代是一個文治 的社會,離開士人的支撐是不可想象的。而欲使士人有效地支撐朝政,其關 鍵在于培育士氣。而士氣的培育在歷代君主看來最重要的莫過于崇圣學而尊 程朱。就科舉所推行的實際效果看,在明前期的相當一段時間內還是卓有成 效的,從士人品格講,如況鐘之類的循吏顯系與其儒者身份直接相關;同時 此種科考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公平性,貧寒之士憑才德而有了入仕的機會,而 豪門貴族也難以獨霸仕途。如典史出身的曹鼐不顧他人嘲笑而刻苦讀書,也 中了宣德八年的進士,并因“對稱旨,上親擢為第一。”(《制義科瑣記》 卷一)雖還難說是朝為田舍郎而暮登天子堂,但稱其平步青云則是恰如其分 的。因而谷應泰曾比較薦舉與科舉說:“成周兼里選,兩漢舉孝廉,抑可通 行歟?曰:叔世也,而詐偽萌起。舍高棘重簾,封名易書,孰能為至公! 必 此而君不得私其臣,父不得私其子。”(《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二)作為 一種考試制度,目的明確與形式公平兼顧,應該說有其優越之處。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卻對此種制度不斷地提出批評,認為它正逐 漸地失去自身應具備的目的,同時也失去其公正的形式。一種制度在推行過 程中顯然不能保證絲毫不出仳漏,但在此卻并非指的一些人為的偶然因素, ④而是明明知其錯誤卻難以避免的總體趨勢。首先是對圣人與經典本意的背 離,從而導致士人品格的下降。嘉靖時的何良俊是較早對此種現象作出論述 的學者,他先從對比太祖與成祖二人對待經書的不同態度入手,來論述明代 科舉的失敗。他說;“太祖時,士子經義皆用注疏,而參以程朱傳注。成祖 既修五經四書大全后,遂悉去漢儒之說,而專以程朱傳注為主。夫漢儒去圣 人未遠,學有專經,其傳授豈無所據。況圣人之言廣大淵微,豈后世之人單 詞片語之所能盡。故不若但訓詁其辭而由人體認,如佛家所謂悟入。蓋體認 之功深,則其得之于心也固;得之于心固,則施之于心也必不茍。自程朱之 說出,將圣人之言死死說定,學者但據此略加敷演,湊成八股,便取科第, 而不知孔孟之書為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 《四友齋叢說》卷三)無論從“體認”“悟如”的學術方法,還是從對程朱 “將圣人之言死死說定”的公然批評,都帶有鮮明的陽明心學影響的痕跡。 但他對專尊程朱之學而難得真才的見解,卻顯然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他將此 種現象概括為如下兩句話:“始則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 朱子。”(同上)非獨此也,更進一步,連傳注亦不必讀,而只讀“舊文” 亦即前人所作八股文字,所謂“更讀舊文字千篇,則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 士子們既然僅讀舊文字便可中進士獲高官,而刻苦體認經書者卻窮年白首, 饑凍老死,那么“人何不為其易且樂而獨為其難且苦者哉?”但負面影響也 相當嚴重,因為“人人皆讀舊文,皆不體認經傳,則五經四書可盡廢矣。” (同上)科舉的本意是要通過考試而掌握程朱之學,再通過程朱之傳注而把 握儒家經典之真意,但在何良俊眼中卻適得其反,科舉的實行正好廢棄了儒 家的經典。與何氏同時的歸有光亦有同樣感受,故曰:“夫終日呻吟,不知 圣人之書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為攫取榮利之資。”(《震川先生集》 卷七,《山舍示學者》)可見此乃許多士人之共識。 其次是公平原則的喪失,以致考中者不必有德有才而抱憾終生者卻往往 才德過人。翻檢明代文人集子,會發現許多科舉失意者對此種不公平遭遇的 深沉慨嘆。以明中期的士人文征明為例,在其詩文集中先后撰寫了《戴先生 傳》、《顧春潛先生傳》(《文征明集》卷二七)、《杜允勝墓志銘》(同 上卷三十)、《王履吉墓志銘》、《東川軍民府通判王君墓志銘》(同上卷 三二)等科舉失意的士人傳銘。這些士人都曾經耗費一生的精力,從各個方 面探索科舉成功的方式,結果均以失敗而告終。顧春潛的失敗在于駁雜,所 謂“雅事博綜,不專治經義,喜為古文辭,習繪事,眾咸非笑之,謂非所宜 為。”他的失敗命運顯然是不可避免的。故“春潛自弘治己未至正德丁丑, 凡七上禮部不中。”但學問博大、議論高遠的戴冠先生也未能免于被絀的結 局,“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律歷,與夫稗官小說, 莫不貫綜。而搜彌刳剔,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為文必以古人為師,汪洋澄 湛,奮迅凌轢,而議論高遠,務出人意。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余為承 文,亦奇雋不為關鍵束縛。一時譽聞籍籍起諸生間。”可見他已得到周圍同 類士人的普遍認可,而且“先生亦自謂科第可得也,而八試皆絀。”這顯然 已不能令士子們心服了。更為令人費解的是杜允勝先生的遭遇,因為他并非 閉門自我摸索,而是得到過內行高人的指點,所謂“王文恪公歸自內閣,遂 往游其門,因得作文之要。”王鏊本是明代出名的八股時文大家,曾于成化 十一年乙未科會試第一,殿試第三。杜先生于彼處討教,所得理應算是“真 經”。就其實際學問看亦然,“其學粹而深,為文光潔而傳于理。”但“自 正德丙子至嘉靖戊子,凡五試,試輒斥。”最后“竟不售以死。”科舉士子 的命運如此變幻莫測,也難怪會使他們痛心疾首大發感嘆了。文征明對此類 失意士人所以深表同情并為之立傳,其中顯然包含有自我感嘆的情緒發泄, 故而在《戴先生傳》后意猶未盡地議論道:“以余觀于戴先生,一第之資, 豈所不足哉?迄老不售,以一校官困頓死,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謂 科目不足以得士者,固非也;而謂能盡天下之士,誰則信之?”痛苦的人生 現實迫使士人們不得不對科舉的公正性提出了質疑。另一位時文大家歸有光 亦曾深切地總結自我體會說:“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難,然亦不可不一 行也。七篇文字,頃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短;不然, 終歲俯首占畢何為者?不須問江東神,鄙人便是也。”(《震川先生集》卷 七,《與沈敬甫》)從自身數十年的科場屢次失敗的經歷中,歸氏得出的結 論是,科舉文字毫無定準可言,唯一的標準便是中與不中,所謂“時之論文, 率以遇不遇加銖兩焉。”(同上卷二,《會文序》)于是他嘆息說:“國家 以科舉之文取士,士以科舉之文升于朝,其為人之賢不肖,及其才與不才, 皆不系于此。至于得失之數,雖科舉之文,亦不系其工與拙。則司是者,豈 非命也夫。”(同上卷二二,《南云翁生壙志》)歸有光對待科舉的態度無 疑是認真的,他除了為自我的不幸遭遇憤激不平外,還為國家朝廷的人才培 養而憂心。但到了萬歷朝的湯顯祖時,他已將一切都看透,也就一切都釋然 了。他曾如此表述對時文的看法:“承以時藝下詢,不佞以為時文惟時是因。 ……時義入彀,何必高談。”(《湯顯祖詩文集》卷四八,《答卞玄樞》) 沒有了憤怒,沒有了不平,也沒有了憂慮,在平靜的語氣里顯示了對科舉取 士的絕望。明人沈際飛對此深有同感,因而在評“時文入彀,何必高談”時 說:“文章原無定相,平奇濃淡,入彀即佳,敲門磚管甚方圓粗細也。”也 就是說,隨著歷史的發展,科舉八股已與求圣人之道無關,也與才能高下無 關,當然也與入仕后的品格行為無關。于是,原本為檢驗治學求道的時文, 便逐漸演變成為求官入仕的技巧。如茅坤明知科舉設立之本意,故一再提醒 一位胡姓舉人說:“從經術中洞關竅,櫛骨理,譬則孫吳之治兵,本之正, 以出入變化,百戰百勝,無不如意,未有不以詘天下之敵者。”(《茅鹿門 先生文集》卷五,《與胡舉人樸庵書》)“圣學以洗心為功,而舉子業,亦 當以煉心為案。吾輩能煉其心如百煉之金之在冶,斯之謂自得而資深逢源也。” (同上卷六,《與胡舉人論舉業書》)其實上述這些言論顯然不是茅坤的由 衷之言,說它完全是應付朋友的門面話或許有些過分,其中也許還包含著扭 轉士風的苦心與自身對儒家理想境界的追求,但他沒有全部講出自己的心里 話也是實情,看一看下面他給自己的侄子茅桂的家書,就會明白此處的推論 決非虛言。 侄行年且五十,于舉子業可謂苦心矣。舉業而入苦心之路,其于名理, 雖或精研,而于風調,不免沉滯。嘗聞先輩舉業“三字符”曰:“典、淺、 顯。”予獨更之曰: “輕、清、精。”然“精”之一字,亦不易得;但能“輕、清,”而稍 加之以秀逸疏爽,則百試百中矣。嘗謂頭場七篇,最為吃緊,須如行云之出 岫,巧燕之穿市,荷葉之擎露,柳絮之飄風,萬無過思深構,必致重滯艱澀。 于二三場后,并聽侄之蹀躞馳驟,出經入史,千金之駿,絕塵而奔,亦無不 可者。……千萬令放“輕、清,”而加之以秀逸疏爽;斯則侄之老馬長途, 而姑從康莊以策轡而馳,亦所以慰我衰颯懸懸之望也。(同上卷九,《與侄 舉人桂書》) 倘若說與胡舉人的信重在談“名理”,與其侄子的信則重在論“風調”, 此種差別同一般學者論文章的內容與形式的各有側重不同,因為在二者之間 不存在必然的內在聯系,亦即他在此所談之“輕、清、精”風調并非是為了 更好地突出所謂的“名理”,而是如何能夠得到主考官的青睞,說的俗氣點 便是研討敲門磚的方圓粗細問題。當然,此種不同的談話內容也許針對不同 對象及不同場合的因素,但同時更應看到,茅坤所言的“輕、清、精”風調 乃是真正的內行之論。如明人對蘇軾的文章極為推崇,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 蘇文的便爽暢達、疏宕犀利更有利于博得主考官的好感。所以王世貞曰:“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為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于時 為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蘇文者。”(《弇州山人續稿》卷四二,《蘇 長公外紀序》)陳紹英亦曰:“當今以制義取士,學術事功,無所不備,而 尤以疏宕犀利為奪目,故最便子瞻文。”(《蘇長公文燧》卷首)李贄甚至 對自己所選蘇軾文集有如此的自信:“令學生子置在案頭,初場二場三場畢 具矣。”(《焚書》卷二,《復焦若侯》)稍加對比即可看出,茅坤所突出 的風調與眾人的推崇蘇軾文章風調是頗相一致的。由此可以得知,明代文人 經常聚會以講論揣摩時文,其中所揣摩的大都不是名理,而是當時流行的所 謂“風調”。當然,科舉既然已失去公平,欲中舉者所揣摩的便不會只限于 “風調”,而會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選擇最有利的手段,如婺源人倪進賢 “素不讀書,以房術進萬安。安大喜。適成化戊戌科,安囑考官劉吉、彭華 取之。遂登進士,選庶吉士。”(《制義科瑣記》卷二)這就更是等而下之 了。但從實質上講,它與揣摩“風調”并沒有太大的差別,同樣都是將檢驗 圣學的方式手段異化為人生的目的,從而使科舉制度變成僅具形式而無內容 的空殼。 至于說科舉制度何以會逐漸背離圣學本意與失去公平原則,明人亦曾作 過一些自我反思,他們往往將其歸結為利祿的侵蝕,其中以顧炎武的話為最 明快,而以黃省曾的話為最具體。顧炎武曰:“自其束發讀書之時,所以勸 之者,不過所謂千鐘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 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日知錄》卷十三,《名教》)所 有的禍患皆起源于利欲之求。正德時的黃省曾較之顧氏的籠統之言就更為具 體了,他認為士人之父師妻子對科舉仕宦的目的便是:“何不仕而華其宮也?” “何不仕而膏粱乎其口也?”“何不仕而積夫千金以侈老而利夫子孫為也?” 正由于此,“五尺童子方辨倉頡,而即皆以此為之心。所以分官以往,各以 其官而漁獵于億兆。環九州布四海去來乎守令,萬千乎南面,各求飽其谿壑 之欲而已。輕之者為貿易,加之者屠沽,極之者乃盜賊而已矣。”隨后他又 描述了當時的狀況:“夫今城衢之內有門將堂觀煌煌而窮極土木之麗者,必 進士之家也;郊遂之間青疇萬井柳碕百里而肆其畎畝之辟者,必進士之家也; 役奴下走文衣麂履泛鶿浮馬賤妾愚婦翠髻瑗冠一珠千金拱如后妃出則象輿者, 必進士之家也。”(《仕意篇》,見黃宗羲《明文海》卷九二)其實,顧炎 武、黃省曾都是把圣學與利祿對立起來加以論述,仿佛士人生來便只能追求 治國平天下的遠大理想,而不能有絲毫的利欲之需。這顯然仍是宋儒的利欲 觀而并不符合先儒的本意。《中庸》曾曰:“舜其大孝也與! 德為圣人,尊 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 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四書集注》25頁)此乃言舜因大孝之德而貴為 天子,故由此順推便得出大德必有位、祿、名、壽的結論。可見先儒也并不 排斥利祿的獲取。但這充其量亦僅為一種理想的狀態,在現實中才德與祿為 并不能完全對等,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孔子,其才德被后人廣為稱揚,他卻 未能獲致應有的祿位,不得不被后人遺憾地封為“素王”。在明代,才德與 祿位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巨,有才德者不必有祿位,有祿位者不必具才德。 于是,求取祿位的必然途徑——科舉制義便不能不被稱之為俗學了。這才應 該是問題的實質,而并非是顧、黃二人所痛心疾首的追逐利祿。這種簡單的 否定利祿的做法并不限于此二人,自唐宋時期科舉產生以來,便不斷有人提 出此一問題,認為它導致士人追求利祿而敗壞其心性,從而有違圣人之學。 宋儒朱熹指出,士人為了求取利祿,便不再有追求圣學真意的興趣,從而造 成如下之局面:“近年以來,習俗茍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 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仿,擇取經中可為題目 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蓋 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謬,乃反以置之高等,習以 成風,轉相祖述,慢侮圣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 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正也。”(《朱子文集》卷十三, 《學校貢舉私議》)拿朱子的話與何良俊所言明代科舉弊端相比,簡直如出 一轍。既然有人對此種目的與手段相顛倒的現象不斷提出批評,那么何以會 不能加以避免,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勢呢?這背后實際上隱藏著更深層的原因。 就本質講,科舉入仕乃是對社會知識精英的選擇,而被選入者也必將是這個 社會中利益的真正獲得者,被儒者經常痛斥的所謂“利祿”,盡管聽起來頗 為俗氣,但卻是士子入仕的真正目的,舉凡光宗耀祖,改換門庭,人生受用, 家族繁衍,無不與此相聯。而且這不僅是其本人的追求,更是其家族的共同 愿望。當然,一位真正的儒者決不應滿足于此,還應該將出仕視為治國平天 下的成物過程。但從朝廷設立官位尊卑與俸祿差別來看,其鼓勵士人的根本 手段仍是利祿。在儒家官員中,求名利與濟天下兼得者已是不易,而淪落為 只求名利者卻比比皆是。在此種為利祿而仕宦的社會結構中,無論采用何種 選拔方式,最終都會將高遠的理想目標淪落為謀利的手段。漢代以察舉為選 拔官員方式,但經師告訴弟子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 俯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漢書》卷七五,《夏侯勝傳》) 將“取青紫”與“耕”并列,可見其視利祿為當然。隋文帝廢九品中正制而 代之以科舉,其目的便是“設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 靡不畢集,”“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北史》 卷八一,《儒林上》)至宋代亦然,楊時曾曰:“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 僥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楊龜山先生集》卷二,《語錄·荊州所聞》) 由此看來,明代之八股制義既然作為一種文官選拔方式,選拔者與被選拔者 均以利祿作為目的,那么它就沒有理由不把圣學變為謀利的手段。如果仔細 觀察將不難發現,一旦失去利祿此一目的或者有更大的利益領域可供追求, 就會減少士人的入仕興趣。前者如明初的洪武時期。當時過低的俸祿與嚴酷 的政治環境,使許多士人視官場為危途,乃至使朱元璋專門制定出一條法律, 凡是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者,可以戮其身而籍其家。為此清代史學家趙翼在 其《廿二史札記》中,特意列出“明初文人多不仕”加以強調,認為“蓋是 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樂仕進。”并引用明初文人葉 伯臣之語曰:“取士之始,網羅無遺;一有磋跌,茍免誅戮,必在屯田筑城 之科,不少顧惜。”(卷三二)在此可以袁凱為例透視一下士人之懼仕心態。 袁凱,字景文,號海叟,華亭人。他以《白燕詩》而在元明之際的文人中享 有盛譽,人稱“袁白燕”。以他的名氣,理所當然地會被太祖征召入仕。但 他并不以此為榮,反而心懷憂懼,視若水火。“命嚴孰敢后,中夜去田里。 鄰友贈予道,切切語未已。妻孥獨無言,揮淚但相視。于時十月交,悲風日 夜起。輕舟溯極浦,瑟瑟響枯葦。警鳧亂沙曲,孤獸嗥荒市。回首望舊廬, 煙霧空迤邐。撫膺獨長嘆,胡為乃至此。”悲風枯葦、警鳧孤獸,一派凄清 荒涼的景色,配以鄰友的依依不舍,家人的揮淚無言,作者的一步三回首, 構成其灰暗感傷的詩境,使人很難將其與赴朝做官的事件連在一起,但這確 系作者入朝辭家時所作的詩篇。究其傷感原因,則正如詩中所言:“趨事深 為難,速戾將在是。皇恩尚嘉惠,還歸臥江水。”(《海叟集》卷二,《新 除監察御史辭貫涇別業》)而在京中為官時,他似乎也未感到有絲毫的快意, 地位權力仍難以沖淡他那凄涼的心境與濃郁的鄉思:“檐影望參差,霜氣紛 蕩漾。耳目幸無役,心意多遐想。園廬日應蔽,蘿蔦春還長。況茲綱紀地, 王事方鞅掌。安得春江棹,東原歸偃仰。”(同上,《察院夜坐》)他日夜 想的竟然還是回家。而一旦其歸鄉愿望得以實現,則心中頓時充滿喜悅之情: “欣然入場圃,兒女各來親。當軒釋負擔,拂去衣上塵。老夫行役久,歸來 志復伸。陶潛愛清風,張生思故莼。援筆為此詩,示我鄰里人。”(同上, 《京師歸別業》)與出家門時的心情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別。明初本是個百 廢待興的時代,急需大量士人輔佐王政,否則朱元璋求士之心不會那么急切。 然而,在入仕非但無益甚且有害的政治高壓下,什么自我抱負的實現,什么 天下蒼生的安危,什么服務王室的責任,被許多士人統統置于腦后,只有自 我生命的保存才是最為實惠的選擇。明代對士人入仕構成一定影響的另一時 期是商業經濟發達的晚明。一方面是有限的官僚隊伍難以容納所有的士子, 另一方面是豐厚的商業利潤的刺激,使相當一部分士人不再選擇仕途,而是 涌入商人的行列。《吳風錄》曾言“至今吳中士大夫多以貨殖為急。”所說 尚較為籠統,因為象徐階之類的官員雖以“貨殖為急”,卻只是令家人為之, 其自身并未失去士人身份。而晚明文人汪道昆所言便更為明確具體:“古者 右儒而左賈,吾郡或右賈而左儒。蓋詘者力不足于賈,去而為儒;嬴者才不 足于儒,則反而歸賈。”(《太涵集》卷五四,《明故處士溪陽吳長公墓志 銘》)汪氏之言是否有充足的根據,今已難以判定。但他說是“吾郡”如此, 則所指乃安徽歙縣之情狀。該地為明代商業最發達地區之一,凌蒙初在《疊 居奇程客得助》中曾如此概括道:“卻是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 科第反在次著。”(《二刻拍案驚奇》卷三七)此雖為小說家言,卻亦可從 一個側面支持汪道昆的看法。⑤從上述所論即可見出,無論儒家曾經為士人 設計出多么高遠的人生理想,但只要他們步入仕途,就無法避免利祿的追求, 因為利益驅動乃是這個社會顛撲不破的真理。或許在某些個別人身上與某些 特殊的歷史時期會表現出某些例外,如不計個人名利的獻身精神與拒斥個人 欲望的天理追求等,但最終支撐這個社會運轉的仍是名利二字。一個成功的 統治者不在于取消人們對于名利的追求,而是如何利用名利鼓舞其服務于朝 廷的熱情,同時又用倫理與法律限制其對名利的過分追求。作為擁有過于理 想化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儒的人生理念的那些士人,往往無視名利對這個社 會不可缺少的價值,而一味沉迷于理想的境界,以致對士人的生存空間作出 了過于狹隘的限制。這種限制顯然無法永久維持下去,名利的追求便日益強 烈,可許多思想家除了對其大加痛斥之外,并未能為名利的追求設計出應有 的法則與措施,于是便感到天下大亂、人心不古了。科舉制義正是這樣一種 制度,從本質上講,它是士人追求名利的途徑,但卻為它設計了過于高遠的 目標,最后便不能不走向目的與手段互為顛倒的結果。 作為有明一代心學的開創人物王陽明,無疑清楚地察覺到了此種歷史趨 勢,故而才會說:“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而相講究,然至考 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 汲焉惟功利之為務,而所謂圣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于外, 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王陽明全集》卷八,《書黃是重新確立圣學的 地位,再塑士人的儒家理想人格。但是從上述所言的復雜情形而觀,王夢星 卷》)因而陽明心學的建立,可以視為是對此種歷史現象的回應與反撥,其 目的之一便陽明為自己背上了過重的歷史負擔,在整個社會格局與基本特性 沒有改變的狀況下,要想挽狂瀾于既倒顯然是過于天真的想法。 |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