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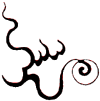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xué)與中晚明士人心態(tài)》 |
|
|
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tài)的流變 第二節(jié)、理學(xué)、八股與明代前期士風(fēng) 一、八股科舉制度的選擇與理學(xué)意識(shí)形態(tài)的確立 八股制度與程朱理學(xué)的關(guān)系是一種形式與內(nèi)容或者說手段與目的的關(guān)系。 八股制度是如何選擇人才的方式與手段,而程朱理學(xué)則是所選人才應(yīng)具備的 素質(zhì)與標(biāo)準(zhǔn)。而二者的共同目的是為明代官場(chǎng)與社會(huì)提供朝廷所認(rèn)可的理想 人才。因此明初朝廷對(duì)八股制度的選擇便不是一種盲目的行為,而是為達(dá)到 確立理學(xué)地位與選拔合適人才的目的而認(rèn)真謀劃、反復(fù)試驗(yàn)的結(jié)果。明代是 代元而起的王朝,其立朝宗旨便是恢復(fù)漢家的禮義傳統(tǒng),用朱元璋的話說就 是:“申明我中國先王之舊章,務(wù)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朋友 有信。”(《御制大誥》)以重新收拾“胡人綱常大壞”之殘局。而欲達(dá)如 此之政治理想,必先培養(yǎng)出具此禮義品格之士人,則從立國宗旨上說,便是 要建立一個(gè)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文治社會(huì)。在如此文化背景下來探究八股制 度與程朱理學(xué)的明初境遇,才能有一個(gè)合適而清晰的詮釋視野。 作為教育史的專業(yè)研究人員,一般是這樣概括八股制度的生發(fā)過程的: “八股之法,源于宋,定于明之洪武,而完備和盛行于明憲宗成化以后,泛 濫于清代。”(周德昌《中國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第161 頁)此種概括 的長處是簡(jiǎn)潔明快而易于突出主要脈絡(luò),需要補(bǔ)充的是產(chǎn)生的原因與不可忽 視的某些細(xì)節(jié)。八股何以會(huì)源于宋,其最初動(dòng)機(jī)是什么,其實(shí)早在明代便有 人作出過回答,比如嘉靖時(shí)的茅坤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仆嘗謂舉業(yè)一 脈,蓋由王荊公厭唐、宋來以辭賦取士,故特倡此經(jīng)義以攬?zhí)煜虏拿俊?br> 妄謂舉子業(yè),今文也;然茍得其至,即謂之古文,亦可也。世之為古文者, 必當(dāng)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為舉子業(yè)者,亦當(dāng)由濂洛關(guān)閩以溯六籍,而務(wù) 得乎圣賢之精,而不涉世見,不落言詮。”(《茅坤集》第321 頁,《復(fù)王 進(jìn)士書》)他從王安石廢詩賦取策論以重六籍之經(jīng)義的初衷,推導(dǎo)出舉子業(yè) “亦當(dāng)由濂洛關(guān)閩以溯六籍而務(wù)得乎圣賢之精,”應(yīng)該說是比較準(zhǔn)確地把握 了當(dāng)初立八股的本意的。此外,明代八股制度的設(shè)立并非直承宋人,而是承 自于元代,這就又牽涉到元人立科舉的動(dòng)機(jī)問題。元代本是由蒙古貴族建立 的王朝,開始時(shí)并未認(rèn)識(shí)到以科舉選拔人才的重要,故而在相當(dā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 廢除了科舉。但后來隨著統(tǒng)治的穩(wěn)定與漢化程度的加深,越來越感覺到無論 從爭(zhēng)取漢族士人人心還是選拔實(shí)際政治操作人才,都必須通過科舉來實(shí)現(xiàn), 所以決定重開科舉。而且其科舉取士的思路竟與宋人王安石出奇地一致,如 元仁宗皇慶二年中書省上奏的意見是:“學(xué)秀才的經(jīng)學(xué)詞賦是兩等,經(jīng)學(xué)的 是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勾當(dāng),詞賦的是吟詩課賦作文字的勾當(dāng)。自隋唐 以來,取人專尚詞賦,人都習(xí)學(xué)的浮滑了。罷去詞賦的言語,前賢也多曾說 來。為這上頭,翰林院、集賢院、禮部先擬德行明經(jīng)為本,不用詞賦來。俺 如今將律賦省,題詩、小議等都不用,止存留詔誥章表,專立德行明經(jīng)科。 明經(jīng)內(nèi)四書五經(jīng),以程子、朱晦庵注解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學(xué)。這 般取人呵,國家后頭得人才去也。”(《通制條格》卷五,《科舉》)盡管 所用漢語頗有元雜劇臺(tái)詞味道而缺乏莊重色彩,但所表達(dá)的意思還是清楚的, 尤其是決定以程朱注解為主作為四書五經(jīng)的標(biāo)準(zhǔn)解釋,更是開了明人八股的 先河。對(duì)此朱元璋也是認(rèn)可的,他在洪武三年的詔書中說;“漢、唐及宋, 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文學(xué)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待士甚優(yōu),而權(quán)豪勢(shì)要, 每納奔競(jìng)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其懷才抱道者,恥與并進(jìn),甘隱山林 而不出。風(fēng)俗之壞,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設(shè)科舉,務(wù)取經(jīng)明行修、 博通古今、名實(shí)相稱者。”(《明史》卷七十,《選舉》二)在此朱元璋并 不是認(rèn)為所行科舉制度本身不好,而是權(quán)豪勢(shì)要往往破壞此一制度,通過不 正當(dāng)途徑竊取仕祿,而如今自己要做的便是嚴(yán)格遵守此一制度,做到“非科 舉者勿得與官。”(同上)通過上述對(duì)明代八股制度在傳統(tǒng)取舍上的敘述, 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價(jià)值取向與基本特性,那就是由經(jīng)義學(xué)習(xí)到德行修養(yǎng)的選 士標(biāo)準(zhǔn)的確立。 但是必須同時(shí)看到,八股制度的形成與理學(xué)標(biāo)準(zhǔn)的確立并非一次完成而 是經(jīng)過了一個(gè)曲折的過程。嚴(yán)格地說來,八股制度的核心亦即程朱理學(xué)的價(jià) 值標(biāo)準(zhǔn)是在永樂時(shí)期由朱棣和他的臣子門確立的,而整個(gè)洪武、建文時(shí)期則 是其探索期。以洪武為例,其試驗(yàn)性質(zhì)可歸納為兩個(gè)方面:(一)各種選官 方式的綜合運(yùn)用而非限于科舉一途。此時(shí)所用的選拔方式主要有薦舉、學(xué)校 與科目三種。多種方式并用的原因當(dāng)然非一言所能盡之,有時(shí)是施行科舉的 條件尚不具備,不得不用其他方式。如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即敕令中書省: “今土宇日廣,文武兼用。卓犖奇?zhèn)ブ牛镭M無之。或隱于山林,或藏于 士武,非在上者開導(dǎo)引拔之,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 略出眾者,參軍及都督府是以名聞。或不能文章而見識(shí)可取,許詣闕面陳其 事。”(《明史》卷七一,《選舉志》三)這顯然是在戰(zhàn)事緊張而統(tǒng)治區(qū)域 又迅速擴(kuò)展、急需人才的特殊情形下所采取應(yīng)急措施。與此有關(guān)的原因是由 于元末戰(zhàn)亂所造成的明初官員及各種管理人才的奇缺,必須采取各種有效措 施迅速予以補(bǔ)充。《明史·選舉志一》曰:“初,以北方喪亂之馀,人鮮知 學(xué),遣國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擇其壯歲能 文者為教諭等官。太祖雖間行科舉,而監(jiān)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shí) 布列中外者,太學(xué)生最盛。”但最主要的原因則是尚未篩選出何者為最佳的 人才選拔方式。這從洪武朝選拔方式的多次反復(fù)即可看出。初年多以薦舉選 官,但時(shí)隔不久即發(fā)現(xiàn)所薦人才駁雜不齊,于是在洪武三年乃決定實(shí)行科舉 選拔。然經(jīng)過一段實(shí)驗(yàn)后又發(fā)現(xiàn),“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學(xué)措諸行事者 寡,”于是“乃但令有司察舉賢才,而罷科舉不用。”(《明史》卷七十, 《選舉志》二)但薦舉的方式畢竟隨意性太大而缺乏可操作性,故而至十五 年而復(fù)設(shè)科舉。至十七年才將科舉方法確定下來,而且直至明末基本未有大 的改變。本次除了在文章格式與經(jīng)書傳注等方面作出進(jìn)一步的規(guī)定外,同時(shí) 還制定了觀政制度:“使進(jìn)士觀政于諸司,其在翰林、承敕監(jiān)等衙門者,曰 庶吉士。進(jìn)士之為庶吉士,亦自此始也。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者仍稱進(jìn)士,觀政進(jìn)士之名亦自此始也。”(同上)稍加比較即可看出, 此次所采取的措施即可保持人才培養(yǎng)與選拔的有序性,又避免了新進(jìn)后生缺 乏從政經(jīng)驗(yàn)的不足,為以后的科舉取士提供了基本的模式。 (二)取士的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尚未歸于一元。如洪武三年選士標(biāo)準(zhǔn)為“經(jīng)明行 修,博通古今。”(同上)而六年時(shí)又重新強(qiáng)調(diào)說:“德行為本,而文藝次 之。”并將其具體分為八類: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 秀才,人才,耆民等。(同上卷七十一,《選舉志》三)盡管分類標(biāo)準(zhǔn)顯得 混亂不統(tǒng)一,但包括德與才二項(xiàng)是顯而易見的。加之對(duì)“能措諸事”的要求, 可見亦頗重視實(shí)際的能力。不過最足以說明問題的是有關(guān)科舉考試內(nèi)容的規(guī) 定:“初設(shè)科舉時(shí),初場(chǎng)試經(jīng)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chǎng),論一道;三 場(chǎng),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復(fù)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后頒科舉定 式,初場(chǎng)試《四書》義三道,經(jīng)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 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 《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 止用陳澔《集說》。二場(chǎng)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nèi)科一道。三場(chǎng) 試經(jīng)史時(shí)務(wù)策五道。”(同上,卷七十,《選舉》二)在此可以很清楚地看 出,洪武時(shí)對(duì)經(jīng)義注疏之歸定尚較為寬泛,只是到永樂時(shí)方一歸程朱,故陳 鼎所言自太祖繼位后,“一宗朱子之學(xué),令學(xué)生非五經(jīng)孔孟之書不讀,非濂 洛關(guān)閩之學(xué)不講,”(《東林列傳》卷二)就頗有些不著邊際了。洪武時(shí)取 士標(biāo)準(zhǔn)之不能歸于單一,是由于此時(shí)活躍于官場(chǎng)社會(huì)的仍為由元入明的一代 士人,他們?cè)谠^為寬松的文化環(huán)境里,其思想意識(shí)的構(gòu)成一般均比較復(fù) 雜,如宋濂之浸染于佛學(xué),劉基之雜有黃老謀略之習(xí),高啟之難除狂放不羈 之情等等,他們有的也想盡量改掉原有的習(xí)性,卻非短時(shí)所能奏效,如高啟 入明后曾明確表示:“近年稍諳時(shí)事,旁人休笑頭縮。賭棋幾局輸贏注,正 似世情翻覆。思算熟。向前去不如,退后無羞辱。三般檢束:莫恃傲才,莫 夸高論,莫趁閑追逐。”(《高青丘集》973頁, 《摸魚兒·自適》)但他 后來還是被太祖以交涉官員不守規(guī)矩而被腰斬于南京。其實(shí)即使主張以德行 為首的明太祖本人也未做到思想純一,直到洪武二十一年,解縉猶如此指出: “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jīng)》、《心經(jīng)》,臣 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多戰(zhàn)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 氏,抄輯穢蕪,略無可采。”(《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當(dāng)然,解 縉之言是少年氣盛而不諳世事的幼稚之舉。皇帝總是高高在上不受限制的, 觀覽一些非儒家典籍亦屬正常。但如果由個(gè)人的愛好而影響到士子教育,便 會(huì)涉及到士風(fēng)問題,洪武時(shí)國子監(jiān)太學(xué)生“所習(xí)自《四書》本經(jīng)外,兼及劉 向《說苑》及律令、書、數(shù)、《御制大誥》。”(同上,卷六九,《選舉》 一)其中所習(xí)《說苑》,與太祖所好當(dāng)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因而在洪武一朝未能做 到思想觀念的純一是顯見的事實(shí)。 但是,在朱元璋統(tǒng)治的三十馀年中,經(jīng)過朝廷的不懈努力,整個(gè)士人群 體的思想意識(shí)也逐漸地由駁雜向著純一趨近,其間種種的演變跡象亦頗可考 見。從朝廷方面對(duì)士人的要求而言,其標(biāo)準(zhǔn)愈益嚴(yán)格。如洪武三年首次舉行 科考時(shí),對(duì)五經(jīng)之釋義規(guī)定為:“《易》程朱氏注,古注疏;《書》蔡氏傳, 古注疏;《詩》朱氏傳,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張洽 傳;《禮記》,古注疏。”(李調(diào)元《制義科瑣記》卷一,《初設(shè)科舉條格 記》)拿十七年第二次科考規(guī)定與此相比,已將《易》與《詩》之古注疏剔 除而僅用程朱釋義。改動(dòng)雖不很大,但從中卻透露出對(duì)儒家經(jīng)典的兩種不同 態(tài)度:首次體現(xiàn)出不忽視經(jīng)典本意的求實(shí)精神,第二次則更重視程朱對(duì)經(jīng)典 的解釋發(fā)揮。可知程朱之學(xué)此時(shí)已有定于一尊的趨勢(shì)。從士人的人格意識(shí)構(gòu) 成而言,在洪武時(shí)成長起來的一代亦較其前輩更為純粹。依宋濂與方孝孺為 例,孝孺之學(xué)雖得之宋濂,卻又與其頗不相同。宋氏雖為明初大儒,其學(xué)亦 不離程朱淵源,但卻頗染于佛旨。孝孺則被譽(yù)為一代純?nèi)澹堑珜R悦鞯?br> 為己任,且甚嚴(yán)佛儒之辯。正如黃宗羲所述:“景濂氏出入于二氏,先生以 叛道者莫過于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qū)斥,一時(shí)僧徒俱恨之。”( 《明儒學(xué)案》卷四三)宋濂曾總結(jié)其為學(xué)經(jīng)過曰:“余自十七八時(shí)輒以古文 辭為事,自以為有得也。至三十時(shí),頓覺用心之殊,微悔之。及逾四十,輒 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雖深自懲戒,時(shí)復(fù)一踐之。五十以后,非惟悔之, 輒大愧之;非惟愧之,輒大恨之。自以為七尺之軀,參于三才,而與周公、 仲尼同一恒性,乃溺于文辭,流蕩忘返,不知老之將至,其可乎哉! 自此焚 毀筆研而游心于沂泗之濱矣。”(《文憲集》卷九,《贈(zèng)梁建中序》)根據(jù) 他文中那痛心疾首的態(tài)度,應(yīng)該相信這是他發(fā)自內(nèi)心的真誠懺悔。但他非但 抹不去其早年舞文弄墨的“劣跡”,而且飛逝的歲月也留給他改造自我的時(shí) 間太短,以致不可能再創(chuàng)造出一位新的宋濂來。方孝孺就不同了,宋濂的人 生終點(diǎn)就是他人生的起點(diǎn),他一開始的人生理想就是“末視文藝,恒以明王 道、致太平為己任。”(《明史》一四一,《方孝孺?zhèn)鳌罚┖茱@然,方孝孺 已經(jīng)以有別于其師輩的新生代而自居了。 如何來評(píng)價(jià)這一新生代,學(xué)術(shù)界并不是有很清晰的認(rèn)識(shí),有人說他“道 學(xué)氣甚重”。(《明代文學(xué)批評(píng)史》43頁)大致講也不為錯(cuò),但他們與永樂 后之道學(xué)卻又頗不相同。他們雖較其前輩理學(xué)味道更濃一些,但卻并不畏首 畏尾,而是意氣風(fēng)發(fā),信念堅(jiān)定。比如解縉甫中進(jìn)士即上萬言書對(duì)太祖之政 治措施進(jìn)行全面批評(píng),并自稱“率易狂愚,無所避忌。”(同上,卷一四七, 《解縉傳》)許多人不明白,方孝孺何以會(huì)一方面以講明道學(xué)、振作綱常為 己任,一方面又會(huì)對(duì)莊周、李白、蘇軾充滿向往仰慕之情。其實(shí),他對(duì)這些 前賢離經(jīng)叛道的思想內(nèi)涵并沒有太大興趣,而是由衷欽佩其意氣風(fēng)發(fā)、奔放 激越的精神。如其論三家之文曰:“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 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其選而為之哉?其心默會(huì)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 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 也。……莊周歿殆兩千年,得其意以為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于文, 猶李白之于詩也,皆至于神者也。”(《遜志齋集》卷十二,《蘇太史文集 序》)他之稱贊三家之文,蓋在其無不如意之縱橫自如;其所以能自如,則 在其能默會(huì)于神;而其能默會(huì)于神,又在其意氣之充沛。值得注意的是,朱 元璋對(duì)由元如明的士人非常嚴(yán)厲,以致不少人雖極力斂其鋒芒,仍不免遭致 摧折。而對(duì)這群年輕氣盛的新一代士人,卻又頗能容忍乃至優(yōu)待。或許他認(rèn) 為這些士人成長于洪武年間,盡管心高氣銳,可對(duì)本朝的忠誠是不成問題的。 他曾多次原諒方孝孺,目的是“此壯士,當(dāng)老其才。”(《明史》卷一四七, 《方孝孺?zhèn)鳌罚┓駝t也許早就大用之了。對(duì)于性情狂傲的解縉,他雖不滿其 “自恣”,也只是對(duì)其父曰:“大器晚成,若以爾子歸,益令進(jìn)學(xué),后十年 來,大用未晚也。”(同上,卷一四七,《解縉傳》)尤其是洪武十八年中 進(jìn)士的練子寧,他在殿試對(duì)側(cè)時(shí),竟放著膽子說:“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 以區(qū)區(qū)小故,縱無窮之誅,何以為治?”前人沒能記錄下當(dāng)時(shí)周圍人的反應(yīng), 恐怕都要替這位食了豹子膽的新科進(jìn)士捏著幾把汗,卻不料皇上反倒“大悅”, 親自將其“擢一甲二名。”(《制義科瑣記》卷一)難怪這些臣子到了建文 年間與惠帝的關(guān)系那般和諧而政治熱情又那般高昂。從士人的角度來說,也 許這短短的四年才是他們他們最理想的時(shí)代。 然而,這曇花一現(xiàn)的局面隨著燕王朱棣靖難大軍的攻入南京而旋告結(jié)束。 朱棣給建文政權(quán)所按罪名是變更祖宗成法,故而其掌權(quán)后便極力做出一返太 祖成憲的姿態(tài)。他繼承了太祖軟硬兼施的措施且更為嚴(yán)密殘酷。《明史·刑 法二》曰:“成祖起靖難之師,悉指忠臣為奸黨,甚者加誅族、掘冢,妻女 發(fā)浣衣局、教坊司,親黨謫戍者至隆、萬間猶勾伍不絕也。抗違者既盡殺戮, 懼人竊議之,疾誹謗特甚。”于是京城內(nèi)外遂形成普遍的告詰之風(fēng),陳瑛、 呂震、紀(jì)綱等殘苛小人也乘勢(shì)紛紛深文周納、株連多殺而邀寵。成祖又特設(shè) 特務(wù)組織東廠以偵測(cè)士民隱情,一時(shí)弄得人人自危。劉子欽之事例最足顯示 當(dāng)時(shí)士人之一般狀況。某次成祖派人至文淵閣去窺測(cè)庶吉士之講習(xí)情況,適 逢劉子欽因吃飯時(shí)飲酒稍多,此刻正“袒腹席地酣設(shè)置。”成祖聞報(bào)后大怒, 立即召其前來訓(xùn)斥說:“吾書堂為其臥榻耶?”遂即罷其官職,發(fā)配至工部 為吏員。劉子欽當(dāng)時(shí)也不加分辨,謝恩后即起身外出買來吏員衣巾,至工部 列身于吏員行列中,弄得工部尚書一時(shí)不知所措。此時(shí)皇上又派太監(jiān)前往查 看,得知?jiǎng)⑹线@般行為打扮,只好笑著說:“劉子欽好沒廉恥。”而后命人 還其官服,仍回內(nèi)閣讀書。(祝允明《野記二》,見鄧士龍《國朝典故》卷 三二)如此大起大落的變化竟發(fā)生在一日之內(nèi),似乎跡近荒唐,但從中卻令 后人得知成祖控制士人之嚴(yán)密,以及士人在變幻莫測(cè)環(huán)境中所領(lǐng)受的人格屈 辱與心理壓力。成祖對(duì)臣子們的心情憂郁也多有感受,但他并沒有表示同情, 而是深感厭惡,并加重了其猜忌心理。永樂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鄭賜忽然亡 故,成祖召翰林諸臣問道:“未嘗聞賜病,豈其自盡乎?”眾人一時(shí)不知如 何回答是好,楊士奇連忙解釋說:“臣觀賜有病數(shù)日,但惶懼不敢退即便安 求醫(yī)藥。昨日晚臣與賜同立右順門外,賜體力不支仆地,旁人怪其鼻口之氣 有噓無吸,臣遽令其屬官扶出午門外。”(楊士奇《三朝圣諭錄上》,《國 朝典故》卷四五)無論是因恐懼而自盡,還是因恐懼而有病不敢治療,其實(shí) 并沒有太大的區(qū)別,均為心理壓力過重的結(jié)果。 對(duì)士人的心理摧殘與政治高壓只是朱棣的控制手段之一,與此同時(shí)他還 在學(xué)校教育與科考內(nèi)容等方面從正面加以引導(dǎo),力爭(zhēng)使思想意識(shí)歸于一統(tǒng)。 于是在永樂初期他責(zé)令大臣們編纂了《四書大全》、《五經(jīng)大全》及《性理 大全》等三部士子必讀之書,將科舉考試內(nèi)容規(guī)定的更為狹窄,以使士子之 思想更為單純劃一。其狹窄單純的明顯標(biāo)志是,三部大全的宗旨以及對(duì)經(jīng)書 的解釋均以程朱理學(xué)為準(zhǔn)則,學(xué)校以此施教,士子以此應(yīng)試,臣民以此修身, 而不許有任何異議。正如主編者胡廣、楊榮、金幼孜等人在進(jìn)書表中所言, 其編纂目的為:“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非惟備覽于經(jīng)筵,實(shí) 欲頒布于天下。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學(xué)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 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圣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fēng),一洗相沿之 陋習(xí)。煥然極備,猗歟盛哉!”(胡廣《進(jìn)五經(jīng)四書性理大全表》,見《皇 明文衡》卷五)其實(shí),永樂十六年三部大全的成書與頒布只不過是永樂君臣 努力為程朱理學(xué)確立官方統(tǒng)治地位的結(jié)果。而早在永樂二年處理朱季友的事 件上,便已顯示出他們的此種強(qiáng)烈愿望。楊士奇《三朝圣諭錄上》記此事曰: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xiàn)所著書,專斥濂、洛、關(guān)、閩之說,肆 其丑詆。上覽之,甚怒,曰;“此儒之賊也。”時(shí)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xué) 士解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cè),上以其書示之。觀畢,縉對(duì)曰:“惑 世誣民莫甚于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遐裔。” 士奇曰:“當(dāng)毀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后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毀書 示儆足矣。”上曰:“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 敕行人押季友遣饒州,會(huì)布政司、府、縣官及鄉(xiāng)之士人,明論其罪,笞以示 罰。其搜檢其家,所著書會(huì)眾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毀所 著書最是。”(《國朝典故》卷四五) 這是記載朱季友事件較完整的一條,此外尚可補(bǔ)充的是:“杖之一百, 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焚之,仍不許稱儒教學(xué)。”(余繼登《典故紀(jì)聞》卷 六)亦即被打了一百棍子,然后被端去飯碗并被開除出士人行列。除了上述 二書外,記載該事的史籍還有許多,就手邊方便,即有:《獻(xiàn)征錄》卷十二 《楊文貞公傳》、《明通鑒》卷十四永樂二年七月壬戌、《萬歷野獲編》卷 二五《獻(xiàn)書被斥》、《國榷》卷十三成祖永樂二年七月壬戌、《明史》卷六 《成祖本記》、《明成祖實(shí)錄》卷三二永樂二年七月壬戌等七種之多。明代 史籍甚繁,未及筆者經(jīng)目者當(dāng)有不少,然僅此已足以說明明人對(duì)此事的重視。 其實(shí),朱季友既然敢于將所著書直接獻(xiàn)給朝廷,無論是出于邀功希寵還是維 護(hù)儒家道統(tǒng),朱棣都大可一笑置之,實(shí)在沒有必要如此興師動(dòng)眾地去折騰這 位七十余歲的老人。朱棣及其大臣們之所以如此重視此事并大張旗鼓地予以 懲戒,無非說明了他們對(duì)程朱理學(xué)的重視與渴求統(tǒng)一士人思想的決心。應(yīng)該 說他們的努力借助官方的巨大優(yōu)勢(shì)而基本取得了成功,盡管其間出現(xiàn)過姚廣 孝著《道馀錄》以駁程朱的小插曲,但并未影響程朱理學(xué)統(tǒng)治地位在永樂后 期的確立。③而后來有如此眾多的史籍對(duì)朱季友事件加以記載,則顯示了此 事的影響之大。明末的談遷在記述完該事后感嘆說:“先朝守宋儒遺書如矩 矱,毋敢逾尺寸,故懲朱季友,而經(jīng)學(xué)至深邃也。句沿字踵,等于苴蠟,于 是曲士鑿其隅見,稍有所緣飾,而矯異之竇,紛互四出,如近日李贄獄死, 紙更為貴,俗尚之觭久矣。彼季友一斥不再振,則當(dāng)時(shí)功令可想見也。”( 《國榷》卷十三,成祖永樂二年)談氏身處晚明異端思想紛起的時(shí)代,深羨 先朝能使“季友一斥不再振”的“功令”,足可見出該事件巨大的歷史效應(yīng)。 談遷認(rèn)識(shí)到“曲士鑿其隅見”是對(duì)“句沿字踵,等于苴蠟”的回應(yīng),但他卻 忽視了“句沿字踵,等于苴蠟”又是斥季友、尊程朱的直接結(jié)果。由此回顧 明前期朝廷對(duì)政治的設(shè)計(jì)與意識(shí)形態(tài)的建構(gòu),實(shí)在值得令人回味。依其設(shè)想, 政治的穩(wěn)定在于選拔出合格的士人群體,而士人的獲得在于具有合理的選拔 方式,而合理的選拔方式又必須與恰當(dāng)?shù)娜∈繕?biāo)準(zhǔn)密切結(jié)合,于是他們選擇 八股科舉與程朱理學(xué),并且最終得到了實(shí)現(xiàn)。然而后來的歷史發(fā)展證明,政 治局面似乎并不能由此而長治久安,倒是引來了許許多多的麻煩。可見歷史 遠(yuǎn)比人們想象中復(fù)雜得多。 |
|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版權(quán)所有 北京國學(xué)時(shí)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