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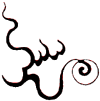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xué)與中晚明士人心態(tài)》 |
|
|
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tài)的流變 第一節(jié):道與勢之糾纏:明代士人境遇的尷尬 四、于謙之死——士人的尷尬與絕望 從臺閣體到于謙之死,其間跨度雖嫌稍大,但二者之間卻并非毫無關(guān)聯(lián)。 于謙初入仕途乃是由楊士奇所薦,此為其直接關(guān)聯(lián)。更重要的是,于謙之死 乃是仁、宣以來各種歷史因素運演的必然結(jié)果。簡而言之,于謙之死源于“ 奪門”,“奪門”源于土木堡之變,土木堡之變源于王振專權(quán),王振專權(quán)源 于仁、宣士風(fēng)的疲軟。其實王振當(dāng)時的勢力尚未達(dá)到后來劉瑾、魏忠賢的程 度,用歷史學(xué)家的話說是“勢若孤雛,根非磐據(jù),”(《明史紀(jì)事本末》卷 二九)最后卻弄得生靈涂炭,幾于亡國。這除了皇帝的昏庸柔弱外,與士風(fēng) 的疲軟也有直接聯(lián)系。誠如上述,三楊等閣臣與皇上的關(guān)系中師生情感占有 相當(dāng)?shù)谋戎兀S著仁、宣二帝的逝去,此種情感已不復(fù)存在。正統(tǒng)初年的短 時太平無事,實在是因為皇權(quán)尚握于太皇太后手中,而隨著她的去世,太平 的局面也就悄然隱去。就與皇上的情感而言,也許更有利于太監(jiān)而不是閣臣, 因為宦官多順從帝王的情趣愛好而得其歡心,閣臣則多以君道限制其欲望而 招致厭惡,②尤其守成之君更是如此。從王振引導(dǎo)剛登基的英宗在將臺觀看 比武,到唆使其御駕親征,再到土木堡之變的英宗被也先俘獲,該是一個順 理成章的過程。士人在失去了與皇帝的情感紐帶之后,顯然也失去了駕馭朝 政的能力。清慎的心態(tài)只能使大多數(shù)士人在宦官專權(quán)下走向無可奈何的自保, 更進一步,在自保亦難的情勢下,許多人便不免棄道從勢,撈取實惠。于是 王佑這類士人出現(xiàn)了,他為了討王振的歡心,竟使其面對“王侍郎何無須” 的戲弄作出如此回答:“老爺所無,兒安敢有?”(同上)無論是清慎的自 潔還是無恥的自污,都不能阻止宦官勢力的惡性膨脹,于是明王朝政治的惡 化也就勢所難免了。在這種背景下,出現(xiàn)了于謙。 于謙(1398—1457),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他從入仕為 官至奪門之變時被冤而死,共經(jīng)歷了永樂、洪熙、宣德、正統(tǒng)、景泰五朝。 他死后被謚忠愍,又謚忠肅,現(xiàn)代學(xué)者則大多稱其為抗敵保國的民族英雄。 于謙的確有忠誠無私的高潔人格與濟世為民的遠(yuǎn)大抱負(fù),這不僅有他那再造 社稷的蓋世功勛為證,而且凡是對中國古代文學(xué)略有了解者,可能都讀過他 那“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石灰吟》,以及“但愿蒼生俱 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的《詠煤炭》。然而這只是于謙人格心態(tài)的一半。 在王振專權(quán)的正統(tǒng)年間,他的確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做了不少實事,也保持 了清白的自我節(jié)操,留下了兩袖清風(fēng)的佳話。但面對混亂的政局,他也只能 表示無可奈何的苦悶心態(tài):“鬢花斑白帶圍寬,竊祿無功久曠官。岸幘恥為 寒士語,調(diào)羹不用腐儒酸。逢人只說還家好,垂老方知濟世難。戀戀西湖舊 風(fēng)月,六橋三塔夢中看。”(《忠肅集》卷十一,《自嘆》)在于謙數(shù)量并 不很多的詩歌中,有相當(dāng)?shù)钠且髟伩鄲炁c退隱的內(nèi)容,應(yīng)該說顯示的是 那一時代許多士人的共同心態(tài)。盡管于謙后來的赫赫世功曾一度掩蓋了此種 心態(tài),但如果仔細(xì)辨析,它不僅在其人格中存在過,而且在以后的歲月里還 將繼續(xù)存在,并對其人生產(chǎn)生重大的影響。 倘若孤立地看于謙之死,乃是由于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小人的報復(fù) 與陷害。但如果深入研究,其原因不僅非常復(fù)雜,而且其結(jié)果實難避免。土 木堡之變后的京城保衛(wèi)戰(zhàn)無疑成就了于謙的蓋世英名,顯示了他的耿耿忠心 與處危不驚、指揮若定的氣度才能,但同時也種下了他尸橫法場的死因。因 為他再一次陷入了在明代最為麻煩也最為危險的皇室權(quán)力之爭中。于謙的悲 劇在于,他深知陷入這口陷阱的尷尬與兇險,卻又義無反顧地投了進去。當(dāng) 也先擁英宗為奇貨而要挾明朝廷時,此刻以于謙為核心的明政府?dāng)嗳徊扇〈?br> 施,立英宗之子朱見深為皇太子,以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決不接受任何以英 宗為要挾的議和條件,于謙甚至表示了“社稷為重君為輕”(《明史紀(jì)事本 末》卷三三)的決絕態(tài)度。繼之又決定以郕王即皇帝位,改元景泰,遙尊英 宗為太上皇,徹底斷絕了也先的要挾念頭。當(dāng)也先感到英宗已失去奇貨作用 而欲送其歸國時,代宗又恐其歸后自己會失去帝位而一再拒絕,此刻又是于 謙從容地說:“大位已定,孰敢他議!”代宗這才放心地說:“從汝,從汝。” (同上)最終解決了英宗的歸國難題。再此過程中,于謙的處置可以說對國 家、英宗、代宗均無不利,尤其對英宗的歸國來說更有促成的作用,對此孟 森先生曾分析道:“景帝之于上皇,始終無迎駕之說致也先,其不欲上皇之 歸,自是本意。但其阻上皇之歸,乃縱令諸將奮勇御敵,而不與敵和,使敵 失貢市之利,則愈阻駕返而敵之送駕愈急矣。”(《明清史講義》上,第139 頁)但可惜的是英宗不僅不會領(lǐng)于謙這份兒人情,恰恰種下了殺于謙的最初 動機。這從勛戚郭登的同類事件中便可得到證明,當(dāng)時也先曾擁英宗至大同 城下索要金銀財物,謊稱得錢物即可送回皇上,守城都督郭登斷然閉門不納。 此時,英宗“遣人謂登曰:‘朕與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 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銜之。”(《明史》卷一七三,《郭登傳》)那 么對于始終主戰(zhàn)而不主和議,且聲稱“社稷為重君為輕”的于謙,英宗心中 又焉能不“銜之?”更何況在英宗歸來之際,眾人都不敢發(fā)表如何安置二位 皇上的意見,唯有他于謙斷言“大位已定,”英宗又焉能不“銜之?”再此, 于歉的二難在于,他要解決國家危機就不能不介入皇位更替的敏感問題,而 介入此一難題他便不能不冒身家性命的風(fēng)險。于謙的可貴處也許就在于,他 主動選擇了國家危亡的大局而置自我性命于不顧。否則他不必感慨萬分地說: “此一腔血竟灑何地!”(《明史》卷一七0,《于謙傳》) 如果說他在京城保衛(wèi)戰(zhàn)中的選擇具有強烈的悲壯色彩的話,那么在景泰 年間的一系列作為則處于一種無可奈何的尷尬境地。明人于慎行曾對于謙的 不幸發(fā)過一通感嘆:“嗟夫,于少保之功豈不大哉!然君父蒙塵,普天怛痛, 而少保以社稷為重,擁立新主,無一語及于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暇兩全耶? 吁,亦忍矣。是時,去建文時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如此。然天下莫以 為非,豈非利害之說深溺而不可返耶?少保嘗自嘆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其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惟其所遇,盡吾心而已,何所不可 灑耶。當(dāng)時群臣奉迎之請,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后易儲 之議,使少保以死爭之,憲廟亦未必出宮。徘徊隱忍,兩顧不發(fā),身死西市, 飲恨無窮,可不哀耶! ”(《谷山筆麈》卷三)于慎行的話盡管充滿激情, 但卻不能算是中肯。他似乎忘記了,于謙所面對的是兩位皇帝:一位是無權(quán) 的舊帝,一位是在位的新帝,他究竟該聽從何人或者說感情上該更傾向何人, 就不能不存在選擇的困難。在生死存亡的國家危難中,他可以毫不猶豫地作 出抉擇。但是在危機已過、二帝并存時,舊時的清慎心態(tài)不能不重新占據(jù)其 心頭。在京城保衛(wèi)戰(zhàn)中精明果斷的于謙,后來卻表現(xiàn)得那么猶豫不決甚至近 乎遲鈍,可見他的確已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首先使于謙為難的是更易太子 之事。當(dāng)初本是立英宗之子朱見深為皇太子,而令郕王監(jiān)國,意思顯然是待 英宗回來后復(fù)位。但后來代宗登基做了皇帝,朱見深的太子地位當(dāng)然也就存 在著危機。代宗無疑想傳皇位于親子,可對這樣的大事滿朝大臣沒一個敢于 提起。有一次代宗試探太監(jiān)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金英卻 頓首回答:“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盡管代宗當(dāng)時只好“默然”作罷, 但卻已打定了易太子的主意。他先分賜給諸內(nèi)閣學(xué)士各金五十兩與銀百兩, 以籠絡(luò)其心,但還是無人敢于出面挑明。正在此時,廣西潯州有一位姓黃的 守備都指揮因獲罪怕死,乃上疏請易太子。皇上得知大喜曰:“萬里外有此 忠臣。”遂令眾臣廷議,盡管“王直、于謙相顧眙愕。”卻依然全體通過了。 只有老臣王直扣案頓足曰:“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明史紀(jì)事本末》 卷三五)于謙卻并未有更多的表示。如果此事就此了結(jié)也就罷了,不料不到 半年,新立太子朱見濟卻又一命嗚呼,太子問題成了爭議更大的難題。是將 原太子朱見深復(fù)位,還是等皇上生下另外的子嗣,朝臣們見解各不相同,其 中不少上疏要求復(fù)原太子位者還獲罪遭貶。于謙顯然對獲罪者持同情態(tài)度, 如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鐘同為復(fù)太子事下獄時,進士楊集曾致書于謙曰:“ 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后乎?脫章綸、鐘同死獄下, 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 ”于謙將信拿給王文看,王文曰:“書生不知朝 廷法度,然有膽,當(dāng)進一級處之。”于是便讓楊集任六安州知州。(同上) 書生由于不知朝廷法度而放言高論,王文、于謙等人則知朝廷法度而不敢亂 說,看來這就是問題的實質(zhì)。這當(dāng)然不是說于謙膽小怕死,而是無論從情感 還是實際效果上,他都很難作出自己的選擇,在對待皇室問題上,以前曾有 過那么多的教訓(xùn),他于謙能不多方考慮嗎?一直到了代宗病危之際,于謙才 不得不與廷臣一起上疏請立朱見深為東宮。但是為時已晚,還未等議出結(jié)果, 石亨諸人已擁立英宗復(fù)辟,等待于謙的也只有死路一條了。于謙并非不知道 自己處境的危險,而是無可奈何。當(dāng)年在代宗因其功勛而賜其宅第時,他曾 堅決拒絕而未被允準(zhǔn),他只好將其封存,“取前后所賜樨書、袍、錠之屬, 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明史》卷一七 0,《于謙傳》)他似乎 已經(jīng)預(yù)感到那不幸結(jié)局的不可避免,而做好了一切準(zhǔn)備。看一看于謙臨終前 的言行,便會相信上述的推測并非毫無所據(jù):“文憤怒,目如炬,辯不已。 謙顧笑曰:‘辯生耶?無庸,彼不論事有無,直死我耳! ’”(《明史紀(jì)事 本末》卷三五)他面對死亡竟如此地平靜,是早已做好心理上的準(zhǔn)備,還是 對一切都已完全絕望。其實此二者應(yīng)該是兼而有之的,因為自景泰元年代宗 登基與英宗被尊為太上皇而入南宮,至今已經(jīng)整整八年了,于謙有足夠的時 間把其中的一切全想清楚。他知道英宗不會輕易放過自己,且不講曾說過“ 社稷為重君為輕”的絕情話,單是那長達(dá)八年的南宮生涯,就足以令英宗充 滿怨恨,談遷《國榷》曾如此記述其南宮生活:“在南宮重門內(nèi),前后兩殿 廡甚湫隘,侍衛(wèi)簡寂,膳自竇入,楮筆不多給,恐其通外也。皇后至刺繡出 賣。”(卷三二,英宗天順元年)長期的精神孤寂,極度的物質(zhì)匱乏,這一 切盡管不是于謙的初衷,但作為景泰朝廷的實權(quán)人物,他當(dāng)然不會被英宗所 輕易原諒,更何況英宗復(fù)辟的登基儀式也極需要合適的祭品,則他于謙的死 還能避免嗎?然而于謙死時又很難產(chǎn)生殉道殉國的悲壯感,因為他眼中的代 宗不可能再作為道義的代表。盡管他也做過于國于民有利的實事,也曾對于 謙有過充分的信任,但在其人格中也充滿了自私與狹隘,千方百計地阻止身 陷敵國的英宗歸朝,殘酷無情地虐待囚困于南宮的太上皇,不擇手段地更易 皇太子,心狠手辣地摧折稍持異議的大臣,所有這些難道會輕易地在于謙的 記憶中消失?他有什么必要象方孝孺那樣表現(xiàn)出慷慨陳詞、大義凜然的崇高 悲劇精神呢?在這場皇室內(nèi)部的兄弟之爭中,沒有正義,沒有是非,所擁有 的只是政治權(quán)力的爭奪與個人私利的算計。于謙的遲鈍是因為他沒有介入的 興趣,但最后卻成了這場鬧劇的犧牲品。因而于謙死前的笑是絕望的笑,他 已對朝廷失去希望,他對政治已沒有熱情,他感到將生命投入到如此的紛爭 中已失去其意義,于是他死得冷靜而從容。這乃是清慎士人品格在殘酷政治 斗爭中所得到的必然結(jié)果。 盡管于謙的冤案后來得到了昭雪,但于謙之死依然對明代士人產(chǎn)生了深 遠(yuǎn)的影響。首先是對朝廷的不滿,如袁帙曰:“己巳之變,至今可為寒心。 ……夫功蓋天下者不賞,于公之謂也。”(同上)所謂的寒心,顯然系指朝 廷的薄情寡恩,只是語氣稍微含蓄些而已。程敏政的話便講得更為直率:“ 故竊以為肅愍公之死雖出于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 之手,不誣也。首罪之禍,則通于天矣。”(同上)窺諸史實,程氏之論確 有見地,因為后來陷害于謙的石亨、曹吉祥、徐有貞諸人雖被斥逐殆盡,但 終天順朝仍未能給于謙平反冤案,就充分顯示了英宗對他的怨恨之情。這種 不滿對士人心態(tài)的轉(zhuǎn)變意義巨大。在仁、宣時代,對士人價值評判的標(biāo)準(zhǔn)來 自于皇上,如李昌祺曾自贊其像曰:“貌雖丑而心嚴(yán),身雖盡而意止。忠孝 稟乎父師,學(xué)問存乎操履。仁廟稱為好人,周藩許其得體。不勞朋友贊詞, 自有帝王恩旨。”(葉盛《水東日記》卷十四)帝王的稱許與恩旨成為他生 命價值的唯一根源,甚至連朋友的評價都是多余的,這固然說明了君臣間的 相互信任關(guān)系融洽,但是將自己的一切全都毫無保留地托付給皇上,是否能 夠永遠(yuǎn)得到公正的對待?于謙之死毫不留情地粉碎了士人的幻想,使他們不 得不在朝廷之外重新尋找生命的寄托。這就接觸到了本書的一個重要方面, 即陽明心學(xué)產(chǎn)生的原因問題。其次是對朝廷政治的恐懼。士人中也有象于慎 行那樣批評于謙優(yōu)柔寡斷的,但更多人則表示了對其尷尬處境的理解。王世 貞曰:“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 哉! 天命所昄,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猋發(fā),元勛甫就,膺此禍烈,智 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天乎! ”(《獻(xiàn)征錄》卷三八,《兵部尚書于公謙 傳》)王世貞除了對于謙的無奈表示充分的理解外,同時指出了兩點遺憾: “智不及避”與“勇不及決。”那么反過來看,王世貞心中合理的處置方式 便應(yīng)該是“避”與“決”的選擇。所謂避便是遠(yuǎn)離這是非之地,妥善地保全 自我;所謂決便是當(dāng)機立斷作出抉擇,從而在政局中處于有利的位置。王世 貞的話是有相當(dāng)分量的,因為明代后期的許多士人正是作出了此二種抉擇: 要么退隱自適以全身遠(yuǎn)害,要么奮身投入做一次政治的賭博。 其實上述影響當(dāng)時就出現(xiàn)了明顯的跡象,更不必等待王世貞加以指點。 比如在代宗易太子時差點兒“愧死”的老臣王直,在于謙死后便立即請求致 仕回鄉(xiāng),甘心于和佃仆們一起種地栽樹,過那種“擊鼓歌唱”的平淡生涯, 并對兒孫們發(fā)感嘆說:“曩者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閣,今上復(fù) 辟,當(dāng)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 ”(《明史》卷一六九,《王直 傳》)王直在宣德、正統(tǒng)年間名氣頗大,與王英一起稱“二王,”卻因楊士 奇的抑制而未能入閣,作為文臣其心中怨氣之大可想而知。但在躲過奪門之 變的災(zāi)禍后,他卻衷心感謝起曾壓抑過自己的楊閣老了。這說明對于奪門之 變這樣巨大的心理恐懼來說,其他的恩恩怨怨也就算不了什么了。此種刻骨 銘心的記憶在天順朝想必決非王直一人所具有。 當(dāng)然,也有未能吸取教訓(xùn)而依然故我者,則理所當(dāng)然地吃足了苦頭,其 中岳正便是個典型的實例。岳正(1418—1472),字季方,漷縣人,正統(tǒng)十 三年會試第一,賜進士及第。天順初年以于謙為首的大批代宗舊臣被殺戮斥 逐,隨后閣臣徐有貞、李賢亦下獄,英宗頗有無人可用之憂。此時他發(fā)現(xiàn)了 岳正這位年輕有為、又是自己所錄取的官員,心中大喜,立即命其入閣。岳 正也深感英宗知遇之恩,盡心盡力以圖報效。但他僅僅在內(nèi)閣呆了二十八日, 便以失敗而告終。他先被貶欽州同知,隨之又被逮系詔獄,受杖一百,謫戍 肅州,后被釋回鄉(xiāng)為民。岳正的失敗雖與石亨、曹吉祥等小人的誣蔑陷害有 密切關(guān)系,但其主要原因則是他的正直敢言與盡心圖報,《明史》本傳記曰: “正博學(xué)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內(nèi)閣才二十八日,勇事敢 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其實態(tài)度的過激英宗或可原諒,而敢于說真 話才是其獲罪的主因,比如他在借承天門失火而代皇上所撰敕文中,竟如此 寫道:“乃者承天門災(zāi),朕心震驚,罔知所措。意敬天事神,有未盡歟?祖 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用舍乖歟?曲直不辨,刑獄冤歟?征調(diào)多方, 軍旅勞歟?賞貲無度,府庫虛歟?請謁不息,官爵濫歟?賄賂公行,政事廢 歟?朋奸欺罔,附權(quán)勢歟?群吏弄法,擅威福歟?征斂徭役太重,而閭閻靡 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 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這全面的質(zhì)疑淋漓盡致,略無顧忌,難怪會獲致“ 舉朝傳誦”的轟動效應(yīng)。但同時也因有“賣直訕謗”的嫌疑而惹怒了皇上, 則其遭貶下獄的結(jié)果也就在所難免了。英宗曾為岳正下過如此評語:“岳正 倒好,只是大膽。”(《明史》卷一七六,《岳正傳》)他只要岳正的“好”, 而討厭其“大膽”,卻不知只有大膽了才會有好。于謙在景泰年間的隱忍徘 徊本是欲求一個好的結(jié)果,卻落了個橫尸法場;岳正在天順年間的大膽直言 也是欲求一個好的結(jié)果,也照舊落了個幾乎喪命的謫戍下場。則士人在當(dāng)時 官場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岳正的確是夠頑強的,在經(jīng)過了貶官流放 的折磨后,卻依然我行我素,他的兩首《自題小像》,不能不讓后人充滿深 深的敬意。其一曰:“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于甘曰:‘岳正倒好,只是大 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為寫陋容,遂隱括其辭, 題于上云: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dāng)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 敢。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他已獲知皇上沒忘記其好處,亦 深知皇上不喜其大膽,更知道倘若改掉這大膽的性情,就會重新得到皇上的 重用,但他卻斷然表示,寧死也不會改變。岳正在此對理想人格的認(rèn)識顯然 與皇上產(chǎn)生了分歧,故而又曰:“孔學(xué)不惑,孟心不動。汝年四十,物理猶 哄。四舉方售,非百中之材;一試輒敗,非萬全之用。既不能隨時以浮沉, 又安足為世之輕重。倘倀倀然以執(zhí)迷,徒嘵嘵乎而自訟。此蓋古人之所謂狂, 而今人之所謂蠢也。”(《類博編》卷八)可見他不僅知道皇上不喜歡自己 的率直大膽,而且更知道不會被這個社會所接受。但盡管舉世非之而認(rèn)其為 蠢,他卻在古人那里尋到了知音,這就是孔、孟對行不掩言的狂者的稱贊。 岳正也許并未意識到,他在明代士人的人格演變史上邁出了艱難的一步,即 從依附朝廷而走向獨立。此種獨立更顯示出另一種趨勢,即道與勢的出現(xiàn)裂 痕乃至初步分離。當(dāng)然,為邁出這一步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即永遠(yuǎn)地脫離 官場。他顯然已做好了準(zhǔn)備,并且沒有太多的遺憾。在晚年,他尋到了兩位 在生活情趣與人生理想上的知音,即超逸的陶潛與求樂的邵雍,他以詩言志 曰:“歸去來兮不是辭,陶家家數(shù)正如斯。近來次第施行盡,只欠臨流會賦 詩。”(《景陶》)“年才五十便休官,卻向床頭學(xué)弄丸。不覺囅然開口笑, 邵家生活這般般。”(《慕邵》,均見《類博編》卷二)這種生活情趣的轉(zhuǎn) 變是否也預(yù)示著一種哲學(xué)人生觀的轉(zhuǎn)向呢?因為在陳獻(xiàn)章的詩文中,陶潛與 邵雍也一再被作為人生理想的楷模而加以稱揚,這該不是偶然的巧合吧。 岳正在明代無論事功、哲學(xué)還是文學(xué)當(dāng)然都不是第一流的人物,之所以 選擇他作為士人心態(tài)研究的代表,是因為其前后聯(lián)結(jié)著兩位重要人物,這就 是于謙與李東陽。與于謙的比較價值已見上述,至于與李東陽的關(guān)系,我以 為四庫館臣在評岳正詩文時的一段話頗有啟示意義,同時也可為本小節(jié)提供 一個恰當(dāng)?shù)慕Y(jié)尾,其曰:“正統(tǒng)成化以后,臺閣之體,漸成啴緩之音,惟正 文風(fēng)格峭勁,如其為人。東陽受學(xué)于正,又娶其女,其《懷麓堂集》亦稱一 代詞宗,然雍容有馀,氣骨終不逮正也。所謂言者心之聲歟! ”(《四庫全 書總目》卷一七 0,集部,別集類二三)這的確是個值得深思的現(xiàn)象,李東 陽受學(xué)于岳正,又是其女婿,甚至連那篇洋洋灑灑的《直內(nèi)閣翰林院學(xué)士岳 公正傳》也是出自他的手筆,但他竟然與岳正的人格迥然不同,其原因究竟 何在?我們留待后面再詳加探討。 |
|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版權(quán)所有 北京國學(xué)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