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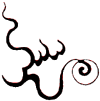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
|
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的流變 第一節:道與勢之糾纏:明代士人境遇的尷尬 二、成祖朱棣的政治策略與永樂士人的無奈 歷史有時往往充滿諷刺意味,那位在南京城內殺文人殺得眼紅并將儒家 之道踐踏得一塌糊涂的燕王朱棣,轉眼之間卻成了有明一代以儒家理論作為 治國綱領的真正奠基者,而且竟然得到了后來士人的認可,明中葉的李賢便 說:“吾道正脈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文皇帝,乃始表 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于正。”(焦竑《獻征錄》卷十三《薛 公瑄神道碑》)但實事求是地講,明王朝的真正成熟的確是從成祖開始的。 在此不必講他三次御駕親征漠北的武功,以及多次派鄭和率船隊下西洋炫耀 國威的盛舉,僅就對士人的控制訓化而言,他也較太祖與惠帝更精明煉達。 朱元璋對士人的反復催折盡管使之生氣喪盡,然而同時亦造成其多詐死佯狂 而求解職事的消極后果;建文帝雖寬仁重士,卻未顧及文人之徒托空議以致 天下不保。朱棣顯然是汲取了這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從而創制出一套剛柔并 濟的策略。他于永樂元年即擺出重道尊儒的姿態下詔曰:“惟欲舉賢材,興 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為治。”(《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三,永樂元年丙子) 其后便是一系列的實際舉措,諸如祭祀孔子,大興科舉,組織文人編纂《五 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永樂大典》等大型類書,對熱 衷仕途者廣開門路,有山林之趣者即放之歸野。尤其是三部“大全”的編纂, 更奠定了以理學為本的政治文化方略,朱棣在三部“大全”的序中說:“由 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國,而達之天下。 使家不異政,國不異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雍之治,將 必有賴于斯焉。”有人曾將洪武、永樂二朝作對比說:“國初右武事,上民 功。士之出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樂紀元,民庶且富,文教大興。 龍飛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時績學館閣試政方州者多其人。至今言進士科 者首稱之。蓋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礪天下,而為此盛舉耳。”(吳寬: 《匏翁家藏集》卷三二《吳縣儒學進士題名記》)身當其時的士人們自然更 是大為感激,胡廣便說;“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儒道光榮多 矣。”(《明太祖實錄》卷五七,永樂四年閏七月乙亥)楊士奇甚至說: “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東里文集》卷二《樸齋記》)此話雖給 人一種不倫不類的滑稽感,然激動感戴之情卻也溢于言表。但朱棣并未能始 終保持此副慈祥面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滿足自己好大喜功的帝王心 理與維護皇室至高無上的權勢利益。對于那些個性突出的士人與有損皇室權 益的行為,他決不會表現出絲毫的寬容。解縉是個足以說明問題的實例。解 縉(1369—1415),字大紳,洪武二十一年進士。他自幼穎敏,但卻同時養 成恃才傲物的脾氣。他在政治環境嚴酷的洪武朝,不僅對同聊上司出言不遜, 而且憑著年輕氣盛上萬言書批評太祖,尖刻地指出“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為 生殺。”(《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他未被太祖殺掉實在是萬幸。然 而到了永樂朝他卻沒能再保持這樣的運氣,焦竑《玉堂叢語》曾用極簡練的 文字概括了他的一生:“解大紳十八舉鄉試第一,以進士為中書庶吉士。上 試時,稱旨,賜鞍馬筆札,而縉率易無所讓。嘗入兵部索皂人,不得,即之 尚書所謾罵。尚書以聞,上弗責也,曰:‘紳逸乃爾耶?苦以御史。’即除 御史。久之,事文皇帝入內閣,詞筆敏捷,而意氣疏闊,又性剛多忤,中漢 庶人讒,出參議廣西,日與王檢討偁探奇山水自適。上書請鑿章江水,便往 來。上大怒征下獄,三載,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卷七,任達) 解縉的死是相當悲慘的,作為一位以天下為己任的儒者,他沒有實現自己的 夙愿,他甚至沒能象方孝孺那樣守道罵賊而死得轟轟烈烈,他就那樣被人灌 得爛醉,稀里糊涂地在寒雪中送掉了性命。其實,朱棣在永樂初年時是非常 信任他的,他是明代第一批入文淵閣備顧問參與機務的七人之一,然而,是 什么原因導致了君臣關系的惡化呢?其中自然有性情剛直的個人原因,但是 最致命的是他介入了皇室內部的權力紛爭,《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中 的一段話,不必加以任何引申就能完全說明問題: 縉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 然好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又以定儲議,為漢王高煦所忌,遂致敗。 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丘福言漢王有功,宜立。帝密問縉。縉曰:“皇長 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圣孫。”謂宣宗也。帝頷 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縉。會大發兵討安南,縉諫。不聽。卒平之, 置郡縣。而太子既立,又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逾嫡。縉又諫曰: “是啟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寢衰。 但朱棣對士人的處置方式顯然較其父朱元璋已更為老猾,除對個別“冥 頑不化”如解縉者需消滅其肉體外,他樂得讓不順眼者關進監獄中去領受坐 牢的滋味。與解縉一起入閣的黃淮、楊溥就曾以相同的原因在大牢中度過了 整整十年的痛苦生涯,這留待后邊再詳細解說。現在要說一件雖然細小卻也 足以說明問題的史實。朱棣在永樂二年對新科進士殿試后,親選曾棨等二十 九人入翰林讀書,顯然對他們寄寓了厚望。但令其大為惱火的是,這群年輕 進士竟敢不按其要求讀書上進,當令其背誦柳宗元《捕蛇者說》時,竟無一 能全誦者。盛怒之下他將此二十九人悉數發配邊衛充軍,繼之又令其充任搬 運木頭的苦役,這群身單力薄的讀書君子自然不堪忍受,便托人向皇上求情 表示悔過。朱棣料定他們苦頭吃足了,方令回翰林重操舊業,自然也就老實 服貼多了。(何孟春《余冬序錄摘抄外編》卷五)此法之妙不言而喻,他既 未讓朱棣落下嗜殺寡恩的惡名,同時又使文人逐漸懂得循規蹈矩的必要。 做永樂朝的士人的確是夠難的,因為他們很難達到朱棣的要求。朱棣理 想中的君臣關系是:“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憮,天下何患不治。” (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做臣子的要敢于大膽地講出自己內心的真實 想法,卻又要讓皇上聽起來舒服順耳。這實在是一種相當美妙的境界,但要 實現它卻幾乎是不可能的。真實的情形往往是,為了不觸怒皇上而險遭不測, 臣子們會將真實的情感與想法深藏于內心,而小心翼翼地選擇一些皇上愛聽 的話,從表面來滿足朱棣的要求。此種情形猶如一位膽顫心驚的女子想方設 法去討兇狠丈夫的歡心一樣,斷難達到平等和諧的情感交流,而只能形成一 種妾婦心理。當時曾入內閣的黃淮就非常典型地擁有此種妾婦心理。他有過 得寵的恩遇:“凡侍朝,特命解公縉與公立于榻之左以備顧問。上慮萬機叢 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公語。至夜分,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議論, 雖同列不得與聞。”(焦竑《獻征錄》卷十二,陳敬宗:《文簡黃公淮墓志 銘》)他也有過失寵的悲哀:“帝征瓦剌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重入高煦 譖,悉征東宮官屬下詔獄,淮及楊溥、金問皆坐系十年。”(《明史》卷一 四七《黃淮傳》)黃淮與其同僚們又是因介入皇室內部的權力而獲罪。在這 十年漫長的牢獄生涯中,黃淮有足夠的時間來思考自身的處境及其與皇帝的 關系,但他卻始終將自己固定在妾婦的位置上,并進行了長達十年的深深悔 過,后來他將這些悔過的文字收集起來,命名為《省愆集》。他回顧了自己 不幸的經歷,將其概括為《妾薄命》詩一首: 薄命妾,薄命妾,昔日顏如花,曷來頭半雪。翻思初嫁時,朝夕承恩私。 蕙蘭播清馥,羅綺生輝光。夜夜庭前拜新月,衷情訴與天公知。愿同比目魚, 游泳長相遂。愿同連理枝,百歲相因依。豈料衰榮無定在,遂令始終成參差。 參差良可嘆,命薄分所宜。報德未及已,妾心徒然悲。愿夫慎保金石軀,好 音慰妾長相思。(《省愆集》卷上) 反復思戀承恩的愉快,深深嗟嘆失寵的遺憾,不敢有絲毫的怨心,所流 露出的惟有對夫君的一片忠誠,因而后來四庫館臣在《省愆集提要》中評曰: “當患難幽憂之日,而和平溫厚無所怨尤,可謂不失風人之旨。”(見《省 愆集》卷首)然而在這枯燥而漫長的牢獄生涯中,黃淮的內心深處果真能保 持這種溫和平靜嗎?其實憑他敏感的文人心靈,不會感受不到歲月的流逝與 暮年的降臨。讀黃淮的詩,使人總感到有一種兩分的結構模式存在,即上半 首是對命運的嗟嘆與凄傷情感的抒寫,而下半首則往往是對忠誠之心的表白, 比如:“常時不對鏡,對鏡即傷情。自覺衰容惡,誰知白發生。松筠存晚節, 蒲柳謝春榮。喜有丹心在,常懷報圣明。”(《省愆集》卷上,《對鏡》) “人生七十稀,十載守圜扉。暮景還能幾,芳心半已非。秋霜風葉老,朝日 露華稀。俯仰默無語,悠然愧昨非。”(同上,《偶成》)這種結構模式透 露出作者的真實心理,前邊是其真情的顯現,是自言自語,當然也不排除有 自傷乞憐的意味,后者是他言,是對皇上言說并渴望得到理解的。用他自己 的話說就是:“中情無限憑誰訴,安得因風達九霄。”(《言志》,《省愆 集》卷下)他要讓皇上知道,他并沒有灰心,他理解皇上對自己的懲罰是對 自己的磨練與考驗,因此才會說:“謂陽舒陰慘兮,皆至仁之流形。彼困心 衡慮兮,庸玉汝于有成。”(《閔志賦》,,同上)當然,上述的所有良苦 用心,均是為了一個目的,即重新獲得帝王的青睞,在《擬去婦詞調風入松》 中,他又一次借“棄婦”的身份表達了此種愿望:“落紅萬點委蒼臺,春事 半塵埃。滿懷愁緒知多少,思量遍無計安排。好似風中飛絮,時時拂去還來。 當年魚水正和諧,兩意絕嫌猜。誰知命薄多乖阻,簫聲遠零落天涯。破鏡終 期再合,夢魂長繞陽臺。”(《省愆集》卷下)此種妾婦乃至棄婦的心理顯 示了永樂士人在君臣關系中的被動地位,而且此種心理還將在以后的相當一 段歷史時期內纏繞在士人的心頭,形成其牢固的人格心態。 黃淮的妾婦心態并非是永樂士人中的特例,與其抱有相同心態的尚有內 閣重臣“三楊”。且不說象黃淮一樣也蹲過十年牢獄的楊溥與沉穩持重的楊 士奇,甚至連多次隨成祖出征且勇于言事的楊榮,也竟然總結出與皇上相處 的如下經驗:“吾見人臣以伉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自 有方。譬若侍上讀《千字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非也,安知不 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為‘玄紅’?遽言之,無 益也。俟其至再讀再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未達此爐火純青的境界, ‘臣自幼讀《千字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葉盛《水東 日記》卷五)楊榮的經驗顯然是從自身以及同僚那種伴君如伴虎的人生現實 中總結出來的,無疑有頗強的針對性與實用性,倘若一味不知彎曲而使龍顏 震怒,非但本人要吃苦受辱,而且于事亦無補益。他楊榮則因“進諫有方” 而始終恩榮不減。并以此挽救過不少獲罪文臣的性命,據載:“夏原吉以兵 餉不給坐系,呂震言其柔奸;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賣直者。皆激上 怒。公悉委曲為之辨解。”(楊士奇《文敏楊公墓志銘》,《明名臣琬琰錄 后集》卷一)可見其效果頗佳。然而其中也并非無懈可擊,楊榮的個性已經 在環境的壓迫下極度地萎縮,在其患得患失的盤算中,也就根本談不上守道 與否了;同時還使其作為大臣的政治責任心也大打折扣,因為倘若皇上始終 未能醒悟而不加詢問,那么他亦將永遠把話留在腹中而不糾正那明顯的錯誤 了。“天地玄黃”與“天地玄紅”的區別也許無關緊要,但若是有社稷陷溺 的大事呢,是否也可以站干岸而不援之以手?更何況象黃淮、三楊那般謙恭 謹微地做人,倘不下長期而痛苦的水磨功夫,是斷難修煉到家的,尤其是要 做到表里如一身心俱化則更為不易,可以說永樂朝士人包括“三楊”在內都 尚未達此爐火純青的境界,他們只是在形式上服服帖帖并不斷表示“吾皇圣 明”的謙恭,至于他們心中盤算些什么那只有天知道了。 一向以圣明自居的天之子朱棣對此顯然尚未糊涂到毫無覺察的地步。余 繼登《典故紀聞》卷七曾記述了成祖與太子之間的一次私人談話,話題是由 陜西耀州百姓向朝廷供呈一只作為國家祥瑞征兆的玄兔而引起的。聰明的朱 棣深知“彼一物之異”實難證明國家已真達堯舜之盛世,因為“今雖邊鄙無 事,俄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深居皇宮的朱棣尚知不能 盲目樂觀,則飽讀詩書的文臣心中自然應該比他更為清楚。可他們非但不肯 講出實情,反倒爭先恐后地獻上溢美詩文,可見他們是言不由衷,朱棣則稱 之為“喋喋為諛。”為此他鄭重地告誡皇太子:“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 群下有言,切不可不審之以理,但觀此表與詩,即理了然而情不能遁矣。” 本條史料的真實性已難以考辨,是否為余氏的推測之詞或經過夸張潤飾,均 已不可知曉。但證之以上述其它史料,此則史料便不能被視為空穴來風。明 察秋毫固然是朱棣的聰明之處,但不也說明在其治下君臣間尚未達到知無不 言的融洽境地嗎? |
|
人民文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